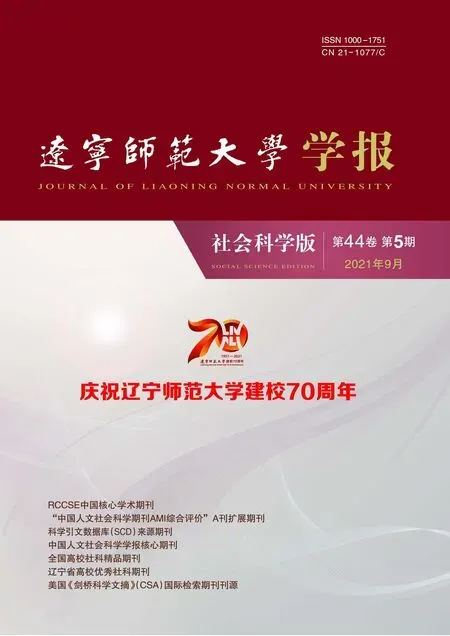清末民初报章文体欧化语法现象考察
——以“新文体”和“逻辑文”为例
刘 兴 忠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一、近代报章文体的产生及其代表文本
清末民初因其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时期。由于受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冲击与影响,旧有观念逐步失势、蜕变,新概念开始萌生、发展,所以此时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意识等开始走向多样甚至驳杂[1]。 “文章合为时而著”——面对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们所特有的思想和情感,清代前、中期居于文坛主流地位的“桐城派”在后期的古文创作上渐显颓势[2]。在此背景之下,冯桂芬、薛福成等学者产生了文法革新的思想。冯氏在《复庄卫生书》中说自己“才力苶靡不能振,天实限之,亦何敢侈口论文?顾独不信义法之说”;并且指出:“文者,所以载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3]薛氏原本出身于桐城派,随着个人对该派“义法”局限的认识,逐渐与之疏远;尝自述:“縻于使事,卒卒无余闲,不遑复研古文辞,时用自恧”[4],实则是在文法思想上突破了桐城派古文的束缚。龚自珍也在《文体箴》中说道:“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丁其时。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荍然而耻之。”[5]后世学者认为,龚自珍的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起着除旧创新的作用,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新文体的产生开辟了道路[6]。
与此同时,在当时改良派自强图存的变革诉求下,随着中西方语言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日益密切和深入,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由于受到翻译文本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汉语书面语与早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即为欧化形式的引入。关于汉语欧化的动因,胡适曾经指出:“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7]就此观点而言,将“白话”换作“文言”,这一论断也是无可争议的;唯一不同的是,“欧化的白话文”是以白话为基本框架,而“欧化的文言”则是以文言为基底。至于“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的汉语书面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报刊政论;这类文本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往往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雄辩力[8]。
清末民初的报刊政论文体在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香港《循环日报》的兴办者王韬成为这一时期报章文体的开创者。王氏自述其写作“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至其工拙,抑末也。”[9]王韬之后,报章文体的开拓者又有郑观应和梁启超等,后者将这一文体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成就了在当时以及后世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的“新文体”。关于新文体的特点,梁氏在其《清代学术概论》里提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10]梁氏新文体对之后的学者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以后白话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1]。民国时期,在新文体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文章体式。对此,钱基博说道:“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12]罗家伦认为,章氏政论可谓集逻辑文学之大成,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到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13]。通过罗氏的评价,一方面可以看出“逻辑文”称名的由来,另一方面也可对此类文本中的“外来”成分有所认识。也正是从后一点出发,胡适认为章氏逻辑文是“欧化的古文”[14]。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为清末民初不同历史阶段报刊政论文体的代表文本,梁氏新文体和章氏逻辑文同出一脉,并且在内部构成上也有相似性,均可归入“欧化文言”范畴。与此同时,考虑到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加之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文体观点和表达习惯难免会存在个性差异,所以两种文本也必然存在不同之处。此类文体在近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属性,曹而云通过对新文体的考察指出,“这种文体是现代白话的雏形之一,也是现代白话成为独立语言系统必须经历的重要环节”[15]。考虑到近代以来欧化形式的引入在汉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从近现代汉语欧化发展历程的角度,对上述过渡阶段欧化文言的代表文本进行较为系统的本体考察很有必要。
二、新文体和逻辑文欧化语法现象考察
就汉语欧化的具体表现来看,语法层面的欧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反映出汉语欧化的“内化”倾向。限于篇幅,下文具体考察对象的选择以虚词为主,兼及个别欧化内涵较为丰富的实词结构。行文过程中使用的语料主要分为两类:其一是梁氏新文体,文本来源于《饮冰室文集点校》(1)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所录梁氏于1896至1911年间所撰报刊政论,共116篇,约103万字(2)其中原载《时务报》14篇,《清议报》24篇,《新民报》47篇,《国风报》31篇。;其二是章氏逻辑文,文本来源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章士钊卷)》(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该文库共收录章士钊1903至1927年间的报刊文言政论152篇,总计约50万字。
(一)“一+量”结构
王力先生在讨论汉语对英文冠词的翻译时说道:“翻译英文的时候,遇到‘the’字往往没法子翻译它,因为中文里没有一个字和它相当。至于遇到‘a’或‘an’的时候,咱们却处处可以用‘一’字翻译。又依现代中国语法,‘一’字后面往往带着单位名词,‘一个’‘一种’之类……尤其是对于无形之物,更显得欧化语法和中国原有的语法的分别。”[16]514-515
总体来看,新文体和逻辑文中“一个”和“一种”均有用例,但是在数量和句法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在新文体中一共检索到“一+个”18例,其中作定语的有12例;就其所修饰的对象来看,9例是“人”或“人物”,只有3例属于抽象名词(分别为“民主国”“独立国”和“头脑”)。考虑到“一+个”在传统汉语中也可以修饰抽象名词[17],新文体中此类组合在数量上并无显著增长,所以其欧化属性并不明显(4)本文依照学界的主流观点,将汉语固有但在外语的影响下得到迅速发展的用法,也归入欧化范畴。。
逻辑文中作定语的“一+个”共7例,其中以“人”为修饰对象的有2例,与新文体相比,在数量比重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余5例中,“一+个”的修饰对象分别为“国家、方法、自治基础、‘蹈铭前失’、天下荒荒之际的局面”;从语义搭配的自由度以及搭配对象的复杂构成来看,较新文体有所发展。
与“一+个”相比,两类语料中“一+种”的使用频率均明显上升,欧化内涵也更为丰富。
新文体中,我们一共检到用作定语的“一+种”94例,其中直接修饰中心语的72例,在中心语前加“之”的22例,如:
(1)选举者必躬自投票,被选举者必须常列席,亦可称之为人民一种之义务。(《国会与义务》)
(2)夫举公债云者,一种之政治行为也。(《外债平议》)
(3)单税者,惟课一种之租税,而其他尽皆蠲除也。(《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
从“一+种”所饰对象的语义特征来看,具有[+抽象]特征的共56例,占比约60%,例如:
(4)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种妙相。(《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5)此一种仰庇于人之心,习之成性。(《国民十大元气论》)
(6)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释新民之义》)
上举文例中,“妙相”“仰庇于人之心”“独立之精神”均为抽象概念。除此之外,充当抽象义被饰成分的又有以下词语:
诐说、不良之结果2(5)下标数字为该词语出现次数,下同。、不赀之价值、道德、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反动力、姑容因循之念、好气象、架空理想、教法2、妙法、权利、社会问题、势力圈、手段、税目、所谓武士道者、探源论、特质、温良恭俭让之德、稳固之权利、无效之要约、新道德2、学说、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野蛮的自由、义务2、政策9、政体2、政治行为、中国之佛学、中国之欧学、状态、租税、罪恶2逻辑文中,我们一共检到作定语的“一+种”60例,没有见到被饰中心语前加“之”的情况,这一点与新文体有很大不同。例如:
(7)愚今请问行政裁判,是否为一种裁判,裁判之所由生,是否基于人民之权利。(《论行政裁判》)
(8)记者读时贤名著不多,尚无一种定义入于吾目。(《共和略说》)
(9)产出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一种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箴奴隶》)
从“一+种”所饰对象的语义特征来看,有[+抽象]特征的共56例,占比超过90%,分布如下:
裁判、定义、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6)原文中为“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恶反响2、反响、方法、方式、浮华虚伪之习、贵族教育、行政统系、欢乐雍容情文并茂之观2、激刺煽动之性质、坚忍不拔之气、健全之论2、解决意见、界、界说、梦想、魔力、排除障碍之手段、平民政治、普通代议机关2、契约、潜势力、情形、权宜之词、实力、事实、适应物、特待之权2、特权2、宪法、新官制、新旧痕迹、信仰力、轩教轾学之运动、言论所偶被之形式、有统系的政策有统系的舆论(7)原文中为“有统系的政策,有统系的舆论”。、有意识之盟约、政府、政府之形式2、政体、政制3、政治习惯、中央权力、主张与新文体相比,逻辑文中此类抽象义的被饰成分无论在数量比重还是内部构成的复杂程度上,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演进趋势,后者如“欢乐雍容情文并茂之观”“有统系的政策,有统系的舆论”等。
(二)介词“当”
王力先生在谈到“联结成分的欧化”时指出:“英文的‘when’在中国语里没有适宜的字可以翻译,只好勉强用一个‘当’字或‘在’字;同时,又依照中国语的老习惯,在时间修饰的后面加上‘时’或‘时候’。”[16]502谢耀基认同上述观点,并认为介词“当”的作用是表示两件事情的时间相当[18]。
我们在新文体10万字的样本语料中筛选出时间介词“当”23例(8)新文体和逻辑文中“当”的分布过于复杂,因此相关筛选工作在按照时间顺序抽取的样本语料中进行。,其中出现在介词框架中的8例,占比约35%,框架分别是“当……(之)时”(5例)、“当……之际”(2例)以及“当……之顷”(1例)。例如:
(10)如地动说、进化说等,当其初发明时,实为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专门之学识。(《说常识》)
(11)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过渡时代论》)
(12)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过渡时代论》)
与上述“合用”情况相比,更具有欧化色彩的“单用”文例相对较多,共15例,占比约65%。例如:
(13)当其初达美境,于彼中语文一无所识,二三年后,则咸可以入中学校。(《论中国之将强》)
(14)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政变原因答客难》)
(15)每当设立一公司,则所恃以当经营之大任者,其人约有四种。(《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此类文例中,“当”所介引的成分以“主+谓”式为主,共12例[如例(13)];此外另有“主+之+谓”式2例[如例(14)]、“动+宾”式1例[如例(15)]。
逻辑文约10万字的样本语料中,我们一共筛选出时间介词“当”12例,其中出现在介词框架中的8例,占比约62%,框架均为“当……(之)时”。例如:
(16)今《约法》不规之于事先,而谋之于事后,是当其行权时,已无限矣。(《国家与责任》)
(17)当袁氏执政之时,每闻人言曰,何者何者,举未若前清也。(《〈甲寅日刊〉发端》)
(18)当其厌然之时,即能辨其真我之所在矣。(《〈甲寅日刊〉发端》)
相比之下,“单用”的文例仅有4例,如:
(19)当法兰西新败于普,义愤莫堪,全国主战。(《新总统与内阁政治》)
(20)当帝国统一党之初出也,人误以为将统一全国之党派。(《帝国统一党党名质疑》)
(21)当旧者将谢而未谢,新者方来而未来,其中不得不有共同之一域,相与融化。(《进化与调和》)
由上可以看出,与新文体相比,逻辑文中的介词“当”数量相对较少,典型的“单用”文例在比重上也相对较小。从“当”介引对象的内部构成上看,也主要是“主+谓”[如例(19)]和“主+之+谓”式[如例(20)];至于上举例(21)中“当”所介引的典型复句形式,我们在新文体筛选范围内未能见到。
(三)连词“或”
在传统汉语中,“或”一般用于平行的动词或其他谓语形式之前,并且至少要有两个“或”前后照应[16]499,这其实是一种就总和的几个部分分别指称的用法[19]。新文体中的此类用法如下:
(22)且使馆等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政变原因答客难》)
(23)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释新民之义》)
与“或”的上述传统用法不同的是,在翻译英文时,一般把“or”“either…or”翻译成“或”,这种单用的“或”有着明显的欧化色彩[20]。
我们在新文体约10万字的样本语料中一共筛选出连词“或”单独使用的例句18个,相关结构总体上以两项联合为主,仅有1例为三项联合,即:
(24)例如以一私人或一阶级、一地方之利益为目的,而假国家之威权以行之者,皆非政治。(《说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上举文例中的“或”出现在了三项联合成分中的第一项之后,这与典型的欧化用法(用在末项之前)有所不同。
以单句或复句内的分句为视点,所有用例中以联结句法成分内部构成单位的用法为主(共17例),此外也有联结典型主谓小句的用法(共1例)。句法成分内部的用例如下:
(25)一人之自治其身,数人或十数人之自治其家,……虽其自治之范围广狭不同,其精神则一也。(《论自治》)
(26)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少年中国说》)
(27)国民全体之利益,与国民之一个人或其一部分人之利益,常立于相对之地位。(《说政策》)
上举文例中,例(25)的“或”联结“主+之+谓”结构中主语的内部构成单位,例(26)的“或”联结宾语内部成分,例(27)的“或”在定语内部起联结作用。总体来看,所有用例中的“或”主要用于主语、宾语、定语以及谓语内部。
所有此类用例中,从内部结构来看,“或”所系联的对象主要是“定+中”式体词性单位(共10例,上举3例皆属此类),此外还有7例谓词性单位,其中“主+谓”式1例,“状+中”式2例,“动+宾”“述+补”以及兼语结构各1例。酌举几例如下:
(28)其资本必广募于公众,乃能厚集,而与旧式之一人独任或少数人醵出者有异。(《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29)是故有绝对的不能实行之政策,虽有大力,无从构造,或无从抵抗者是也。(《说政策》)
(30)其族名皆以L发音,或加P、G为助音。(《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上举例(28)中,“或”首先联结前后主谓短语“一人独任”和“少数人醵出”,进而构成“者”字结构,该结构前加修饰语“旧式”之后再同其前的介词“与”构成介宾短语。(29)(30)两例中的“或”后分别系联状中和兼语结构,外部句法环境相对简洁。
除了以上例句之外,还有1例“或”所系联的对象比较特殊,不便归类,具体如下:
(31)是故人之持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上举文例中,“贷之于人以取息”近似紧缩复句,难以归入以上诸类,同时也并非典型小句。至于前文提到的“联结主谓小句”,指的是下面这样的用例:
(32)倘机关不备,或司机关之人不依国家目的以进行,则有目的等于无有也。(《说政策》)
上举文例中,“机关不备”以及“司机关之人不依国家目的以进行”均为比较典型的主谓句式。
样本语料范围内,我们发现少数用例结构相对复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例如:
(33a)又至今闽语,有以一字而读两音或三音者,或两三字而读一音者,此与日本人、安南人各以其语读汉字,相去几何也?(《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34a)旧式企业,率以一人或一家族经营之,或雇用少数人而已。(《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从形式上看,上举文例内部均由前后两个“或”起到系联作用,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两例中的“或”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具体分析如下所示:
(33b)又至今闽语,有以一字而读两音∥或三音者,/或(以)两三字而读一音者
(34b)旧式企业,率以一人∥或一家族经营之,/或雇用少数人而已
可见,上举文例中的“或”尽管数量成双,但实际上还是在不同句法层次内部单独使用的欧化用法。
逻辑文抽样语料中,共检索到连词“或”单独使用的例句42个,数量比重远高于新文体。就“或”所系联对象的数量来看,尽管仍是以两项为主(38例),但是却也出现了三项和四项联合的情况,如:
(35)今全国方迷于非民选主义,则以中央委任之县知事、道尹或州观察使,而兼理自治,是不啻自治全灭。(《联邦论》)
(36)无论政治方面,学术或道德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道而已。(《新时代之青年》)
(37)盖主甲说范围,即尽于甲说,至乙说、丙说或丁、戊诸说,皆非吾论职分所及也。(《告学部——为撤西洋留学法政生事》)
例(35)是典型的欧化用法。尽管例(36)中的联合结构在细节方面还存在过渡时期的某些特点,但是将其抽象概括为“A、B或C”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与新文体的“A或B、C”有很大不同。至于例(37)中的联合结构,虽然在语义层面均为四项联合,但是从句法形式上看最末两项之间的结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其抽象概括为“A、B或(C、D)”,与“A、B或C”并无本质差别。
从联合结构所充当的句法成分来看,逻辑文与新文体比较明显的不同在于被饰中心语内部连词“或”的使用,例如:
(38)人数过繁,宜去原额之半或三之一已耳。(《代议非易案》)
(39)第一人不足之票或有余之票,归诸第二,第二人不足之票或有余之票,归诸第三。(《理想之一院制》)
(40)英国如觉有政治之痛苦,断无不即时立法或变法以苏之。(《国会万能说》)
上举文例中,例(38)的“之半或三之一”以及例(39)的“不足之票或有余之票”均为定语所饰的体词性结构,例(40)的“立法或变法”则为状语所饰的谓词性结构。
此外,我们在逻辑文中还见到了“或”字联合结构作状语的情况,如下所示:
(41)易词言之,乃被治团体之利益,必治者随时可由被治者直接或间接以影响加之,而后能充分保全也。(《国家与责任》)
此例之中,“直接或间接”充当的是方式状语,新文体中未能见到此类用法。
从内部结构来看,逻辑文中“或”所系联的对象主要是“定+中”式,此外还有“动+宾”“述+补”等;与新文体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某些光杆形式以及特殊词类的出现,例如:
(42)义务可自修之,至一言责任,则必有相对之个人或团体,始生意味。(《国家与责任》)
(43)议员者,非由他人招请或委任者也,乃自往居之者也。(《告代表团》)
(44)顷之其地之左或右又见一影,人以为即前影之移动。(《进化与调和》)
上举文例中,仅就“或”所系联的对象来看,例(42)的“个人”“团体”、例(43)的“招请”“委任”以及例(44)的“左”“右”,分别对应光杆名词、光杆动词以及方位词。新文体中未能见到此类用法。
除了以上用法之外,逻辑文中,我们未能检到“或”系联典型主谓小句的用例。
(四)助词“的”
近代汉语史上表示偏正关系的结构助词最初写作“底”,由于语音的变化,宋代以后字形方面“底”“的”混用,元代中叶以后,通常写作“的”[21]。
王力先生在谈到英文翻译时指出,“的”字在翻译英文的时候有三种用途:一是对译英文的“of”以及做领格标记(9)如the son of my friend译为“我的朋友的儿子”。例句引自原文,下同。,二是用来做形容词和次品句子形式的记号(10)如a beautiful girl译为“一个美丽的少女”,the man who came here this morning was my school friend译为“今天早上到这儿来的那人是我同学”。这里的“次品”指的是定语位置的修饰限制成分。,三是用来做末品(副词)的记号(11)如he works carefully译为“他很留心的工作”。。其中第三种欧化程度最深,“是中国本来不大听见的”[16]490。
新文体中,我们一共筛选出结构助词“的”627例,其中表示领属关系或类似英文“of”的76例,用作形容词和次品句式标记的481例,用作末品(副词/状语)标记的70例。第一类用例如下:
(45)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开明专制论》)
(46)波氏之说,就论理的方面观之,其壁垒之森严也如此;就历史的方面观之,其左证之确凿也如彼。(《开明专制论》)
(47)殊不知人心之变,绝非此一二煽动家所能为力,惟政府所供给之革命的原料,日充积于人人之脑际。(《现政府与革命党》)
例(45)的“的”表示领属关系,(46)(47)两例的“的”与第一例不同,理解为“关涉”更为贴切。
第二类即用作形容词或次品句式标记的数量最多,具体用例如下:
(48)此论惟适于专制的国家,不适于非专制的国家。(《开明专制论》)
(49)暴动的革命所以自取干涉者有二:一曰对外之暴乱,二曰内部之冲突。(《暴动与外国干涉》)
(50)故所谓人类共同生活继续的团体者,即国家之实质也。(《开明专制论》)
前两例中“专制的”“非专制的”“暴动的”均可归入“形容词”(充当定语的词语)范畴,后一例的“人类共同生活继续的”则可分析为“次品句式”(充当定语的典型小句)。关于“的”的属性或归属问题,梁氏本人的补充说明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具体如下:
彼报原文只云革命,今冠以“暴动的”之一形容词者,如吾之政治革命论,可谓之秩序的革命,彼等所持者正暴动的革命也。(《暴动与外国干涉》)
尽管以上所谓“形容词”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特定词类,但是梁氏将“暴动的”视作一个整体,并认为其具有“形容”功能,无疑证明了“的”的标记作用。
如果说由于以上3例中的“的”或者可以省略(如前两例),或者可以替换为“之”(如后一例),因而其标记属性相对较弱的话,那么以下文例中“的”的必不可少则能更好地说明其标记功能。
(51)试为罕譬以喻之,则国民全体利益云者,乃化学的而非数理的也。(《说政策》)
(52)所谓必争者何也?……换言之,则彼乃种族的而此乃政治的也。(《杂答某报》)
(53)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为发达的为进化的而非为革命的矣。(《杂答某报》)
上举诸例中,“的”字既不可省略,也不可能替换为“之”。从语义上看,“X的”也不宜分析为体词性结构。所有481例中,此类表属性的非定语“的”字结构共58例,占比约12%。
至于上文所说“欧化程度最深”的末品(状语)标记,新文体中的用例如下:
(54)此标准者既已发现若干之除外例,其必非绝对的正确也明甚。(《开明专制论》)
(55)用之一时,虽或有利,然宪法者,比较的有固定之性质者也。(《开明专制论》)
(56)是故此等政务,虽非能积极的浚发财源,实能消极的保护财源,而保护之效,不仅在今日而兼在将来。(《外债平议》)
按照梁氏的观点,“绝对的”“比较的”“积极的”“消极的”均具有相对独立性,依照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这里的“的”均为状语标记。就此类“X的”中“X”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上词语,另有“相对的”“一般的”“单纯的”“具体的”各一例。
章氏逻辑文中,我们一共筛选出结构助词“的”70例,与新文体相比在数量比重上差距十分明显。就统计数据的内部构成来看,其中表领属关系或领域关涉的12例,用作形容词或次品(定语)标记的53例,用作末品(状语)标记的仅有5例。分别举例如下:
(57)吾谓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关系,乃契约的关系,感情的关系,面子的关系也。(《联邦论》)
(58)造成一种有统系的政策,有统系的舆论,以贡献于国家。(《帝国统一党党名质疑》)
(59)是论者,假定上院议员为不轻躁,或比较的不轻躁,殆无疑义。(《一院制之主张》)
上举文例中,例(57)的“的”表示关涉,例(58)的“的”为定语标记,例(59)的“的”则为状语标记。
第二类范围内,我们也发现了不可省略且不可替换为“之”的典型标记用法,例如:
(60)然此种独立性,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主权无限说》)
(61)盖各国宪法皆抽象的,而英国则实验的。(《国会万能说》)
(62)今日中央对于地方,非命令的,而协商的;地方对于中央,非从属的,而对等的。(《联邦论》)
第二类53例之中,此类用法共16例,占比约30%,高于新文体中的12%,由此反映出两类文本在结构细节上的不同。
至于第三类状语标记,尽管逻辑文中仅有的5例在数量比重方面与新文体相距甚远,但是后者除了“比较的”“消极的”之外,还出现了1例未见于前者的“根本的”,这也反映了两类文本的微观差异。
三、结 语
通过以上考察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近代报章政论的两种代表文本在某些特定的语法点上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欧化倾向,同时也可看出两者之间或同或异的复杂关系。
具体来说,在某一部分语法项目的数量比重以及欧化程度上,两者具有一致性。以“一+量”结构为例:与“一+个”相比,两类文本中的“一+种”使用频率更高,同时也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欧化倾向。与此同时,在另一部分语法项目的数量比重及欧化程度上,两类文本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以连词“或”为例:逻辑文中的连词“或”不仅在数量比重方面远高于新文体,并且在欧化用法(如“A、B或C”)方面也显示出了更高的典型性。与此类“总体差异”相比,两类文本欧化语法现象的不同之处更多表现在某类语法项目相关句法结构内部。这种差异或者表现为某一结构下位小类的有无之别或数量多少(如“当”+复句形式、“的”作状语标记),或者表现在某级结构单位的句法功能或搭配方面(如“或”字联合结构的整体功能、“或”系联光杆动词等)。
以上概括主要着眼于微观层面,而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近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以往学界谈到汉语欧化,大都着眼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的白话翻译或创作文本,对于同时存在或者更早的文言翻译或创作文本则关注较少。通过本文的实际考察,就近代文言政论文本来看,尽管不同时期的文章体式有所不同,不同作者的文体观念以及表达习惯存在差异,但是对于欧化语法的借鉴或吸纳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创作文本尚且如此,翻译文本自不待言。
其二,近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存在于近代文言和白话文本之间,也存在于某一类文本内部。前者表现为基于欧化白话文本的考察而得出的欧化语法现象分布结论同样适用于欧化文言文本,后者表现为不同欧化文言文本内部欧化语法现象的分布总体趋同。
其三,近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存在内部差异。以上述欧化文言文本为例,通过新文体和逻辑文两种代表文本的深入对比,我们发现这种差异不仅表现为同一欧化语法现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数量比重不同,而且表现在相关欧化语法现象的内部构成方面(12)参见前文“一+种”修饰的[+抽象]特征词语,以及介词“当”所在的介词框架等部分。。
其四,近现代汉语欧化的早期实践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以两类文本中助词“的”的状语标记用法为例:一方面,逻辑文中此类用例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尽管新文体中的相关文例在数量上相对可观,但是具体到“的”前的搭配对象,则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固定性或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