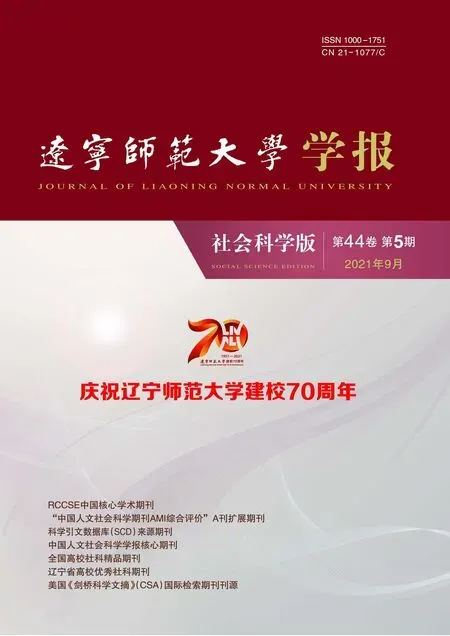兴隆洼文化“栽立式人形造像”初探
田 野, 魏欣欣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兴隆洼文化因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而得名。这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燕山南麓、乌尔吉沐沦河、大兴安岭及医巫闾山所环绕的区域,其文化核心分布区为辽海西部地区(1)本文所及“辽西地区”是指辽海西部地区,大体位于医巫闾山、燕山、大兴安岭、松辽分水岭之间。。目前发现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多密集分布于西辽河、大小凌河与滦河流域,其中较为典型的包括兴隆洼、兴隆沟、查海遗址及白音长汗遗址。在诸多遗址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器物曾一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它们的总体特征为石质、人形、状若裸身、双臂置于身前、头颅微仰、下肢或作楔形或化为底座栽立土中,故本文将这类遗物称为“栽立式人形造像”。
一、研究概述
目前有关兴隆洼文化栽立式人形造像的研究,见诸报道者多为对其发掘及发现情况的基本介绍及初步研究,鲜见专题性研究。现有成果中海燕、陈苇、马金花等人的研究相对系统。
海燕认为栽立式人形造像中的女性形象兼有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寓意,且祖先和生殖繁衍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发展,其内涵应发生嬗变,其女性特征逐渐不显,遂演化呈倚坐式人像。栽桩的消失使得人形造像便于移动,进而表明祭祀活动更加频繁。她在《赤峰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女性雕塑像及相关问题浅议》一文中指出,普遍发现人形造像的白音长汗类型与西拉沐沦河以南的兴隆洼文化(即查海类型)应分属不同的文化系列,到红山文化时期赤峰地区才统一于一个文化势力[1]。
陈苇在对兴隆洼文化祖先崇拜的研究中将居室墓和石雕像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女神崇拜是生殖崇拜的一部分,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是“转死为生”的关系,是以宗教形式挽回人口损失。兴隆洼石雕像是祖先崇拜在生殖繁衍上的反映[2]。
马金花在对我国北方地区史前女性雕塑的研究中认为我国北方最早的女性石雕像是对女性祖先神或家族保护神的崇拜,具有火神和生育女神等多重神格,生殖崇拜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祖先崇拜从生殖崇拜中孕育而出[3]。
除上述三位学者的学说外,王刚、马海玉等人也对部分人像进行过研究。王刚认为西门外出土的2件栽立式人形造像具有生殖崇拜的意义,产生于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自身再生产的需求中,与人形造像共同出土的石雕蟾蜍则说明动物崇拜的存在,先民通过不同的崇拜来祈求氏族部落的兴旺发达[4]。马海玉在对红山文化人物造像系统的研究中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人像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人形造像是祖先崇拜的载体,兴隆洼文化的人形造像蕴含了生殖崇拜的意义,这种生殖崇拜的单一模式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分化[5]。
目前能够相对准确认定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栽立式人形造像仅见于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中AF19出土的1件,因当时其他地区并未见出土同类器物,故发掘者郭治中先生未能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仅在此后出版的报告中将其纳入原始宗教用具。
以上所列各家之言多是认为兴隆洼文化栽立式人形造像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其中蕴含着生殖崇拜的意义,作为辽西地区年代最早的兴隆洼栽立式人形造像与辽西地区后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现的人形造像有着承继关系,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这些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开拓了思路。
兴隆洼文化栽立式人形造像是该文化所见较为特殊的一类遗物,其基本内涵应反映了当时人群精神层面的内容。限于学术水平笔者目前无法对这类遗物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此仅对其功能、内涵、年代等问题略做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二、基础材料及其内涵与年代辨析
目前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栽立式人形造像经报道者计有9件,分布于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及翁牛特旗。从地理位置上看,多为西拉沐沦河上游地区。
(一)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
白音长汗遗址位于林西县白音长汗村西南约500 m的一处山岗西坡,地处西拉沐沦河北岸约2 km处。该遗址最早发现于1987年文物普查。在1988—1991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林西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其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者在遗址的二期乙类遗存房址AF19中心的灶址西侧发现1件矗立于土层中的石雕人像[6]。人像通高36.6 cm,整体呈梭形;头部微仰,头顶稍尖,未见明显装饰结构;面部以凹坑表现出眼部及口部,鼻部隆起,双耳未表现;下颌稍仰,颈部内收为凹槽状;肩部较头部稍宽无明显界限;身前有凸起应做双臂;背部似未雕琢,呈自然弧状;下部双腿表现不明显,末端汇为锥状插入土内;其露出土层部分如踞坐状。人像头部、躯干和支座的比例约为1∶1∶1。因发现时该人像自然形态即插入土内,故本文将这类遗物称为“栽立式人形造像”。
白音长汗人像反映出的工艺水准较低,但其雕琢技法却不原始——人像面部神情及体态表现清晰。石像通体有被长期摩擦的痕迹,表明使用较为频繁。人像周围的遗存还见有石板灶址与1件蚌质的“蛙”形遗物。
白音长汗遗址AF19是该遗址二期乙类遗存的中型房址,发现的人形造像是整个遗址中唯一的1件栽立式石雕人像,应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房址作为聚落布局的一般单位视之,即便是以房址为专题性研究的科研成果也鲜有对房址功能、用途等层面的分析。从小河西文化时期房址被发现后学界多赞同大型或较大型房屋为聚落公共活动室,中型或小型房址为普通居室的观点。但以人形造像的视角观察,辽西地区的房址似乎还有较深层面的用途。
杨虎先生曾披露小河西文化榆树山遗址的探方布局平面图[7]。图中显示F9紧邻F11,且两座房址之间的墙壁是断开的,换言之,两座房址很可能属于“连屋式”建筑,即连体的两室。其中,F11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建筑,地面面积超过100 m2,属于大型房屋,F9面积较小,约40 m2,室内居中位置见有石板灶,灶址北部出土过1件泥质陶半圆雕人面像。这似乎可以表明F9和F11应是同一种使用功能,即聚落祭祀场所。由此可知,最迟在小河西文化时期先民已经开辟出独立空间进行祭祀,室内应是祭祀场所之一。兴隆洼文化年代较小河西文化偏晚,二者文化特性有较高相似性,特别是白音长汗遗址B区还见有兴隆洼房址打破小河西房址的实例,这些现象表明小河西文化应是兴隆洼文化的主要或绝对源头。那么兴隆洼文化遗存中也应包括类似上文中所述开辟出的独立祭祀址,而这个祭祀场所即是AF19。其实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的研究目前并不全面,如有关房址朝向一类的问题学界目前仅记录其大体朝向或方位角度,并不做细微观察。经笔者观察与研究,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房址,其门道通常与附近河道呈垂直角度,这可能是为出行便利,这种布局形式也影响到墓葬主人的头部朝向。换言之,河道弯曲,那么与河道保持垂直角度的房屋门道或墓主人朝向即有差异,从这一点进行观察,可以对房址及所及遗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总体来看,垂直于河道的房址内部所出人像即为让进入房址的人群得以第一时间观察且祭拜。以白音长汗遗址AF19为例,其门道垂直于河道,人像与门道呈直线分布,中间又设祭坛(灶址),这种布局形式足以说明当时人群对这类造像的重视程度。以人像为祭祀的目标,其地位应凌驾于人群社会。事实上学界也早有相近推断,如田广林先生就将AF19所出人像视为“家主”,其神格应为“中霤之神”[8]271。从宗教发展角度看,这类人形造像的性质应不是较为基础的生殖崇拜物、家族崇拜物或所谓的女神崇拜物,而应上升至族群崇拜的层面。
2016年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发掘了翁牛特旗南湾子遗址,出土两件栽立式人像(详见下文),但因相关报道及研究较少,有关此类人像的基本内涵还需再做斟酌。
(二)林西县西门外遗址
西门外遗址位于西拉沐沦河支流嘎斯汰河北岸,是1984年林西县防疫站工作人员偶然于一座带灶的房址南部约20 m处发现的,共发现2件栽立式人形造像及1件“石蛙”[9]。人像个体大小不一,均为花岗岩材质。较大的1件通高67 cm,头部呈圆形,面部微仰;眼部及口部为三个凹坑,头部两侧双耳与颈部相连;下颌与颈部结构分明,内凹呈槽状;肩部略宽,前胸有两处凸起,双臂叠起;双手相连置于胸腹之间;腿部化为倒梯形支座;头部、上半身和下部支座的比例约为1∶2∶1.5。较小的1件通高40 cm,头部呈椭圆状,头顶略尖;面部微仰以凹坑表现眼及口部,鼻梁隆起,耳部表现不明显;颈、肩部有一圈横向突起,肩部与头部宽度接近,腹部较宽;前胸似有两处凸起,双臂弯叠于胸腹,腹部不见明显雕刻痕迹,应是利用石块自然形态化为柱状底座;头部、上半身和腿部的比例约为1∶1.5∶1。
与白音长汗遗址出土人像相比,西门外发现的2件人像更易辨识体貌特征。两者除腿部处理不同外,其余部分反映出的制作观念极为相近,应是表现了一种端坐或踞坐体态。需要指出的是从两件人像的工艺及结构特征推断,应属不同时期的产物。遗憾的是该遗址并未经过科学发掘,发现者通过同遗址采集的陶器等其他遗物推断两件人像应为兴隆洼文化遗存,更因为人像表现的性别特征,将其定义为女性造像。但笔者认为较小1件胸前的凸起并不是双乳,而应是锁骨结构,故该遗物应为男性。
从两件器物的雕琢方式来看,其制作手法及观念明显不同,虽共出同一地点,但笔者认为二者间应存在年代上的差异。
林西县辖区范围内发现的3件栽立式人形造像总体特征相近,如面部微仰,以凹坑表现眼及口部,双手置于身前,双腿均未做表现而是化作底座。不同之处在于有女性特征者腿部较尖,而有男性特征者则似钝状底座。
(三)克什克腾旗山前村遗址
山前村遗址位于克什克腾旗万合永乡南部,地处西拉沐沦河上游支流北岸。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对该遗址调查期间采集到1件石质人像。人像通高40 cm,整体形象为一端坐高台身躯微俯者。其头部磨做圆形,两侧刻出双耳;头顶近中心位置有一圆形凹坑,作用不明;面部以凹坑表现出眼睛和口部,鼻梁稍残;头部与颈部凹槽不深;肩部略宽,双臂于身侧自然弯曲至身前,双手分开贴于腹部;背部利用石块自然弧度,未做雕琢;因人像较厚,故臀部及大腿表现明显,呈端坐状,小腿并拢自然下垂与石块结合形成底座;其头部、上半身和腿部的比例约为1∶1.5∶1.5。
(四)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遗址
克什克腾旗宇宙地村东北部水泥厂附近曾采集到1件栽立式人形造像。人像通高20 cm。头部呈圆形,两侧耳部受损,仅左侧似有耳郭;双目与口部为凹坑,面部略平,鼻梁不显;肩部稍宽,双臂弯曲抱腹,腿部状若盘坐于楔形支座之上;头部、上半身和支座的比例约为1∶1∶1。该人像将石材自然隆起的棱线作为中间线,其上刻制鼻梁,以加强面部立体感;其棱线于手部之下,有似形成“权杖”;整体观感若一位手拄权杖、身居高位的人物形象,极为传神。
(五)克什克腾旗花胡哨遗址
花胡哨村位于宇宙地村西南部,地处西拉沐沦河上游北岸。村民曾于田间采集到1件人像。人像通高37 cm,光头,头部呈蛋圆形,头顶略凸,两侧可见双耳;于眉部有横弧状隆起,似眉骨亦似头饰;下颌内敛,面呈俯状;眼、口做凹坑,鼻梁微隆;颈部似有装饰结构,肩部略宽;腿部表现不明显,于腹部以下即为圆柱状底座。与前文所及人像不同之处在于,该人像左臂弯曲置于胸前,右臂自然回拢贴于腹部。其头部、上半身和支座的比例约为1∶1∶1,从比例上看应为端坐状人像。
(六)克什克腾旗三义乡遗址
三义乡遗址位于克什克腾旗西部,西拉沐沦河上游北岸。其所发现人像与花胡哨遗址所出人像造型相近:通高27 cm,光头,头部呈圆形;眉骨处有横置棱线似冠饰,双耳不显;眼睛与口部为凹槽,鼻尖突出;颈部有一圈横向突起,肩部略宽,胸部和腹部略鼓;下部支座与上半身无明显界限;其头部、上半身与支座的比例约为1∶1.5∶0.5。从上半身和支座的比例看这件器物应为一件盘坐姿态的人像。
克什克腾旗所见4件栽立式人形造像均为采集品[1],未有伴出其他遗物。相关研究者根据《克什克腾旗文物县志》所载“山前村有红山文化遗址”的信息,将山前村的人像划归为红山文化遗物。从人像雕琢特征分析,山前村人像的体态特征虽有别于白音长汗人像,但其面部雕琢技法与之高度相似,而与红山文化人像的雕刻技法及体态表现手法差异更大。目前并未见有赵宝沟、富河、西梁文化遗存内发现过同类遗物,故笔者认为这件人像当属兴隆洼文化遗存。同理其他3件亦为同类。
(七)翁牛特旗南湾子遗址
南湾子遗址位于翁牛特旗广德公镇,地处西拉沐沦河南岸。2016年7—9月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翁牛特旗文物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据现有研究成果,此次发掘共清理兴隆洼文化房址9座,在F2室内石板灶北侧发现2件规格不一的栽立式人形造像[10]。
稍长1件人像通高45.6 cm,平面投影为三角形,整体呈三棱柱状。制作者利用石块较平一面作为背面,故整体造型立体感较强。其头部正视呈椭圆形,头顶略圆钝,不见装饰性结构;头部两侧用凹线刻出双耳轮廓;整体面部器官比例写实,眼部及口部为凹坑,鼻梁较直,鼻尖凸起;发现时双眼及口部均镶有蚌片,其中眼部蚌片为圆环状,使得眼球结构明显。但因保护不当现已不见左眼蚌片;下颌以凹陷勾勒区分出头与躯干;双臂自然弯曲,其左臂置于胸前,右臂贴于腹部;腹部以下未经雕刻,而是利用石材其余部分形成底座;头部、上半身和支座的比例约为1∶0.5∶1。因左胸部有凸起,故发掘者认为该遗物表现的应是女性形象。
稍短的1件因下部稍残,整体呈倒水滴状。上端头部近圆形,不见耳部;两边眉骨与稍长1件相似,均是自然弯曲,极为写实;眼与口部为小凹坑,鼻梁较低,鼻尖突出;发现时在眼部及口部未见任何装饰物;唇下未做过多装饰,仅是用棱线勾勒出大概形状,使整体形态状如一位留长须的男性头像。
南湾子遗址出土遗物中可资断代者较少,故有学者认为这2件人像不一定是兴隆洼文化遗物。笔者认为其他遗物虽不能反映出遗址性质,但据公布的资料来看遗址房址内有和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相似的“泥圈”状结构,故二者间从时间上看相去不远,应为同期;但从雕刻技法上看,南湾子遗址所见人像的年代应相对最晚。
南湾子遗址的人像与前文所及其他人像存在较多差异,其中最大差异在于(西拉沐沦河)北岸遗址所见人像若真有性别之分,则女性人像下部呈楔状,而男性则是梯形底座,但南湾子2件人像均为相反。
从造像特征上看,南湾子“女性”石像与宇宙地水泥厂人像雕刻理念相似,即均利用岩石隆起的棱线作为中线,且利用隆起刻制鼻梁。其手部特点与花胡哨村出土人像相似。将三者的形态联系起来看,如同一位手执权杖、端坐高台、俯视众生的上层人物。结合学界对这类遗物内涵的解读则可以断定,他们或是族群中身居高位的身前写照,或为族群假想而出的祖神形象。其内涵均是置于坛前供人奉祀的信仰化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南湾子人像眼部镶嵌的蚌壳,其制作或装饰观念应受大凌河流域查海类型文化影响所致。
目前这9件栽立式人形造像,仅白音长汗出土的1件能够相对准确地认定为兴隆洼文化晚期遗存,余者均无法准确断代。从制作技法应由原始逐渐进化的思路考虑,白音长汗遗址人像最为原始,当属最早;南湾子遗址所出人像最为精细,当为最晚。依据各遗址所见,其年代关系排序由早至晚应为:白音长汗→西门外“男”→山前村→西门外“女”→三义乡→宇宙地→花胡哨→南湾子“男”→南湾子“女”。
三、几点认识
兴隆洼文化栽立式人形造像是迄今为止在辽海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遗物,具有文化发生学意义。对其进行初步分析,可推断如下。
第一,绝大多数人像在造型上的共同特征,即以凹坑表现双目与口部。说明供奉石像人群的文化从始至终一脉传承。这类造像的视觉效果或仰首或俯身——无论哪种形态均应以有别于常人的族群高层人物为原型。其区别在于体态,白音长汗、西门外遗址所出人像面部微仰、口部大开、似举颈长啸;其余遗址所出人像俱端坐高位、俯览大地、手执权杖、号令众生。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族群有着统一的文化信仰且有高端权力阶层。可以推断在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白音长汗类型的地区性文化有着绝高的凝聚力与传承性。
第二,以今天的审美角度观察,这些人像无不粗糙、原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均刻画入神,惟妙惟肖。这不但体现了制作者的虔诚心态更表现出当时制石工艺的极高水准。此外将人像下部有意制作成可以插入土层的结构应意味着这类人像的放置并非保持不变,而是可以移动且携带,表明当时应有特定的人群负责移动、放置和使用这类器物。也即是说当时的族群已然分层。
第三,目前有明确出土地点的人形造像仅见白音长汗及南湾子。这两处人像按照笔者的年代排序恰好为最早和最晚,这表明这类遗物自出现之初,即是放置于石灶之畔。有学者曾指出这类造像的原初含义为“中霤之神”,即祖神或家主的化身[8]272。联系到兴隆洼文化早期人们在山岗顶端堆砌圆形石堆以祭祀族群英雄人物或祖神,至兴隆洼文化中晚期于方形灶前供奉祖神的情况,说明在白音长汗二期乙类时期,人们的设祀对象已然分化。而其设祀的圆形石碓及方形灶址与红山文化的石构圆坛、方坛应存在文化传承上的联系。
第四,从辽西地区石构遗存发展角度而言,石构遗存最早出现在大凌河流域,发展于西拉沐沦河上游地区,鼎盛于大凌河中游地带,最终衰落于红山文化晚期。单纯从人形造像的角度观察,这类造像发端于西拉沐沦河上游,至兴隆洼晚期已然式微。而其虽不多见却并未消失,其继任者即为发现于草帽山、兴隆沟等遗址的石质及陶质人像。事实上若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及之前的石构遗存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圆雕体石质人像自白音长汗地区出现之后其总体移动方向是向东的。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兴隆洼文化早、中期时西拉沐沦河与大凌河联系较少,至兴隆洼文化中晚期时白音长汗类型开始对查海类型产生影响。其实证诸多,单从人形造像角度观察,南湾子遗址所出人像即带有明显的地区文化交融的特征,如“女性”人像以蚌覆目、口,这种习俗与兴隆洼、兴隆沟居室墓中所见蚌饰的使用方法近似。而“男性”人像为片雕体人面形象,这种造物观念在之前仅见于查海类型遗存。由此推断在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两地文化互动逐渐加强,地方文化差异逐步弱化。至赵宝沟文化产生前夜,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三期遗存所见石墓——土坑墓、石灶——土坑灶共存即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2)本文采用陈国庆先生对兴隆洼文化的分期意见,即以查海F43为兴隆洼文化第三期文化遗存(详见陈国庆《兴隆洼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探讨》)。但至今查海中心墓葬区未做分期,笔者认为F43修建时间较中心墓地为晚。相关遗迹单位时间顺序由早至晚应为:F43M→中心墓地东部→F43。故相对而言,笔者所谓的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三期的大体时间应略早于陈国庆先生指出的第三期且稍晚于第二期。。
第五,石构遗存是辽海地区最具地区特色的文化遗存。其代表即是红山文化“坛、庙、冢”系统。事实上这一模式最晚在兴隆洼文化晚期已然形成,即前文所及的圆形石碓(积石墓)和方形石灶分别为“坛”及“冢”,而“庙”即是兴隆洼文化带有居室墓的房址与包括栽立式人形造像房址的组合体。
第六,对于石雕人像的“性别”之分学界有诸多见解。依笔者所见,至迟在兴隆洼文化中晚期阶段女性所代表的生育崇拜的观念应已淡出,即人像表现出的性别应均为男性——可能说无性更为贴切。据现有研究成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辽西地区与西亚一带即有较为频繁的文化往来,这种文化互动与人群往来的情况一直持续至今。西亚一带(亦有学者谓为近东地区)科尔提克丘遗址M4发掘资料表明,当时社群高层人物皆做蜷身葬式,并身前悬饰两个球状大理石质权杖头。这一现象从侧面观察为蜷身葬式与权杖头,但从正面观察,恰是踞坐式人形及胸前两处凸起物。
综上所述,兴隆洼文化时期社群崇拜应已脱离了原始的生殖崇拜阶段而升华至更高层面。结合兴隆洼文化时期栽立式人形造像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可知当时部族已经产生了阶层且由高层人物对整个族群进行统一管理。这种人群在生前是部族或地区的领导人物,死后即放置山巅设祀祭拜。而人像即为族群先祖的化身,置于聚落之内以供长期祭祀。这种祭祀模式或礼制形态即为当时社群的管理方式,具有极强的凝聚性与传承性。采用这一模式进行族群管理,其结果势必会促进地区性物质资源的不断发展、精神内涵不断丰富且深化,由此可推断当时社会应会产生一定的社会秩序,也即是说在距今7 000~8 000年间,文明曙光理应出现在广袤的辽西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