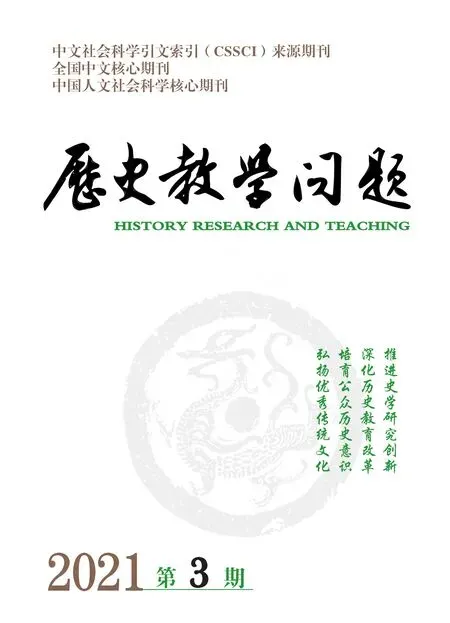新见俞樾藏札文献价值述略
张 求 会
德清俞氏是近现代名闻中外的文化世家。经学大师俞樾,光绪戊戌年探花俞陛云,现代著名学者俞平伯,数代人以诗文传家,继志述事,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传承和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曾祖到曾孙,俞氏四代人的姻亲师友不乏高官显宦、学人艺士和名流才子,这一点从俞氏家藏亲友往还书札中便可管窥一二。数年前,由俞陛云、俞平伯父子保存下来的一批俞樾师友手札——“俞樾旧藏友朋书札”——在拍卖会上现身,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1]中国嘉德2015 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近现代名人信札写本专场”,拍品号:1986,拍品名称:俞樾旧藏友朋书札。预展时间:2015 年5 月13~18 日,预展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北京国际饭店二层(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9 号);拍卖时间:2015 年5 月18 日13:30,拍卖地点: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三层紫金大厅南厅;拍卖结果:流拍。资料来源:孔夫子旧书网,网址:http://pmgs.kongfz.com/special/473/。几经辗转,这批俞樾藏札现由北京一位朋友收藏。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大力支持,这批手札文献即将以《俞曲园藏诗笺手札》为名正式刊行。笔者有幸和许恪儒先生一道整理了这批藏札,故而先睹为快,现将其文献价值择要述略如下,以期促动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一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简放河南学政;七年(1857)秋,因试题割裂经义遭劾罢归。此后寄寓苏州,潜心著述,又主持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上海诂经精舍等处讲席30 余年,作育人才无数,声名远播海外。俞氏学识渊富,平生所著近500 卷,统称《春在堂全书》,今人增补为《俞樾全集》,[2]今人编《俞樾全集》凡两种:赵一生主编:《俞樾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汪少华、王华宝主编:《俞樾全集》,凤凰出版社,2020-2021 年。日益丰赡翔实。
综观俞樾一生,笔耕不已,舌耕不辍,既享盛名,又获高寿,交游广阔、广通声气也是其为人为学的一大特色。他与师长、家人、戚好、故旧、友朋、门生或“粉丝”之间的书翰往还,正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在近代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谱系中,俞樾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特殊的位置,这一点,同样可以在来往书信中得到鲜活而频密的展示。因此,搜集、整理俞樾写给他人的书信以及他人写给俞樾的函札,理所当然地成为“俞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俞樾写给他人的书信。当年,由曲园老人认可,收入《春在堂全书》的书信仅231 通。[3]汪少华《俞樾书信集·前言》有云:“俞樾生前手订的《春在堂尺牍》六卷、《宾萌外集》卷二中的书信仅有231 通。”见俞樾著、汪少华整理:《俞樾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上册,“前言”,第5 页。此后,增补从未中断,成果堪称丰硕。最近几年,又以张燕婴、汪少华所获成就最为显著:张燕婴整理之《俞樾函札辑证》,所收已接近900 通;[4]张燕婴:《俞樾函札辑证·前言》,见俞樾著、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4 年,上册,“前言”,第14 页。扩展之作恢复《春在堂尺牍》的旧名,增至1148 通;[5]汪少华:《俞樾书信集·前言》,见俞樾著、汪少华整理:《俞樾书信集》,上册,“前言”,第5 页。按,张燕婴、肖景之合作整理之《春在堂尺牍》,收入趙一生主编之《俞樾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28、29 冊。新版《春在堂尺牍》其后再经补益,共辑录俞樾函札1444 通;[1]张燕婴整理:《春在堂尺牍》(全三册),见汪少华、王华宝主编:《俞樾全集》,凤凰出版社,2020 年。按,《古工委冬季书单》所引凤凰出版社推荐语有云:“本书为《俞樾全集》之一种。全书以人名为次序,共辑录俞樾函札1444 通,是为当今能见到的现存俞樾函札之总集。”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古籍新书报官微”,2020 年12 月18 日。而汪少华整理之《俞樾书信集》,更是高达1498 通的惊人数量(内含《宾萌外集》12 通)。
相比之下,学界对他人写给俞樾函札的整理、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迟至2011 年,始由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将馆藏“旧雨新知致俞樾之书简”与“俞樾致亲友知交之尺牍”合集影印出版,名曰《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全两册),[2]上海图书馆编:《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 年,上册,“凡例”,第1 页。其下册《曲园所留信札》乃收存孙衣言、黄体芳等99 人写给俞樾的103 通函札。从数量上看,“曲园所留信札”与已刊“曲园手札”相差甚远,尚不及其十分之一。
显而易见,北京这位朋友收藏的曲园藏札,与上图《曲园所留信札》一样,同属他人写给俞樾而由俞氏家族留存下来的函札文献,较之曲园致他人书札,珍稀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批文献不仅有书信,还包括大量诗笺、词笺,而且整理、保存的过程也有值得探讨之处。
二
北京朋友购藏的这一批俞樾藏札,内含《先友诗笺》四册、《先友词笺》一册、《袖中书》五册,收录了俞樾友朋、故旧、门生等86 人写给他的诗笺、词笺、手札,合计各体诗329 首、词43 阕、书札68 通。据云原装为十一帙,今存十帙。通览之下,斟酌再三,整理者代为拟制了今名——《俞曲园藏诗笺手札》。
上图所藏《曲园所留信札》,“系前人所编定,原装为八帙”,影印出版时“依原装池次序编排”。[3]《俞曲园手札·曲园所留信札》,上册,“凡例”,第1 页。然此“前人”为谁?信息不全,尚难遽断。与之不同,《俞曲园藏诗笺手札》的编定者却可以断为俞樾及其后人。
如果仅从“先友”二字推测,四册《先友诗笺》、一册《先友词笺》的题签者理应是俞樾本人。然而,俞樾卒年为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先友诗笺》第一至第四册,每册皆有逝年迟于俞樾之“先友”,如第一册之王先谦(卒于1918 年),第二册之陶濬宣(卒于1912 年),第三册之吴庆坻(卒于1924 年),第四册之章梫(卒于1949 年),而第五册《先友词笺》之郑文焯,卒年(1918)亦后于俞樾。此十余人,谓之“先友”,明显有悖常情常理。因此,《先友诗笺》《先友词笺》的题签者或许另有其人?[4]此承马忠文先生2021 年1 月29 日提示。经与《袖中书》五册相比照,其间的疑惑大致可以消除。
俞樾生前,有感于朋旧见寄之书“或情意殷拳,或议论剀切,即单词片语,亦往往有言外之意,寻味无穷”,“若任其散佚,供鼠蠹之一饱,非所以酬嘉藻、重芳讯也”,“于是手录如干首,以所得先后编次,或一人而数书,则并录之。写定后,厘为二卷。取古诗‘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减’之义,题曰《袖中书》。”[5]俞樾:《袖中书序》,见俞樾著:《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7 册,第545 页。这便是《袖中书》的由来。在《春在堂全书录要》中,俞樾又对这两卷《袖中书》介绍道:“然书实不止此,尚拟续编,而未果也。”[6]俞樾:《春在堂全书录要》“《袖中书》二卷”条,见俞樾著:《春在堂全书》,第7 册,第689 页。这两条自述,言词虽然简短,内涵却很丰富:其一,“袖中书”之名,由俞樾本人取自汉诗《孟冬寒气至》,以志珍视朋旧之意;其二,收存于《春在堂全书》中的《袖中书》,是俞樾从所得师友书札中选择性抄录而成;其三,《袖中书》各札之编排,以收信先后为序;其四,《袖中书》所录,只是俞樾师友书札的一小部分,未及抄存者仍有不少。
经过比对,新见俞樾藏札中的五册《袖中书》,其所收俞樾师友书札既不同于《春在堂全书·袖中书》,也未见于上图已刊《曲园所留信札》。这五册《袖中书》,封面长条题签空白,旁侧贴签分别写有“袖中书 后学”“袖中书 年世侄”“袖中书 门生”诸字。证以《先友诗笺第四册》俞平伯题识所云“今读此笺未有款识,只见于册上吾父所书目录”,可知此五册《袖中书》实由乃翁俞陛云代为题签,各册诗笺、词笺封面之名录(即俞平伯所称“目录”)也应同出俞陛云之手。
俞陛云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逝于公元1950年,其卒年较章梫——《俞曲园藏诗笺手札》86 位作者中最后一位辞世者——尚迟一年。值得一说的是,包括章梫在内的许多写信人同时也是俞陛云的交好,诗笺中反复出现的“文孙阶青太史”指的正是俞陛云。藏札内收存的章梫第四通诗笺《重题一首》,写于民国二十年辛末(1931),怀念的对象是辞世多年的曲园先生,题赠的对象却是一同寓居北京的俞陛云。因此,俞陛云代替祖父题签时,将数十位诗笺、词笺的作者统称为“先友”,在情理上也还是说得通的。推而言之,“先友诗笺”之题签,与其封面之“目录”一样,都有可能是俞陛云为祖父代题的。正因为是代题,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先友诗笺第一册》封面的名录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形——蒋超伯的一首诗,被误标在舒兴阿名下(详后)。
俞陛云代为题签、代书目录之年份暂难断定,俞平伯题识时间明确标为1982 年,此物由俞氏数代人传承有绪则无疑义。简言之,俞樾在世时似应对这批藏札简略编排,其孙俞陛云、曾孙俞平伯先后予以厘订,各自留下了墨迹。仅从这批函札文献的传承中,即可感知俞氏文脉绵延不绝的气息。
三
《诗笺》《词笺》中保留下来的370 余首诗词,为各家诗词集的校勘提供了最原始、最可信的底本,其中的集外之作又可增补各家诗词集的空白。当然,此项工作有待于专门之家倾注大量精力来做系统性梳理,笔者在此只能试举一例:
诗笺作者之一的严辰(1822—1893),字缁生(又作芝僧),号达叟,浙江桐乡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1862)散馆考试,任刑部主事。著有《墨花吟馆诗钞》《墨花吟馆病几续钞》《墨花吟馆文钞》《达叟文稿》《桐溪达叟自订年谱》等。严辰与俞樾往还之信札,已刊者仅有俞樾致严辰一通,录存于《春在堂尺牍》卷六,题为《与严芝僧庶常》,内容系指摘严辰所修《桐乡县志》在体例上的瑕疵。[1]俞樾:《致严辰》,详俞樾著、汪少华整理:《俞樾书信集》,下册,第752—753 页。至于严辰写给俞樾的信函,迄未闻见。《俞曲园藏诗笺手札》所收严作七古一首,不仅可以借而推见两人之交往,而且还能为已刊严氏诗集提供参校的底本。
《俞曲园藏诗笺手札》所收严诗如下:
串月弟子词,奉呈曲园年老前辈大人,
聊供喷饭,不足言诗
曲园先生天下师,师其经学兼文词。曲园先生亦我师,师其串月一事奇。中秋串月石湖畔,万人空巷夸吴儿。越人但识三潭印,那能一串如牟尼。先生高坐曲园内,独出新法思匪夷。镜无大小可纳月,正串侧串无不宜。何必石湖远跋涉,凡月到处皆可为。示我一篇《串月歌》,不觉欣羡情为移。先生所学学不到,此事却可颦效施。愿闻其详幸指示,每逢月望辄效之。果然明月不私照,镜中得月无贤愚。一个嫦娥化无数,岂月薄相相娱嬉。仰视天心仍一月,东坡化百复在兹。赢得儿童竞狂叫,破镜掬取惟恐迟。串月我堪称弟子,问以他学无所知。经学尤为门外汉,聊因问月一道难。《春秋》二百四十年,不纪月食义何在。离坎分宫非日月,似与雷风不相贯。一月壬辰旁死霸,谁定武成从后案。如月之恒平读去,诗有古音例何乱。大明生东月生西,曲台议礼何尝变。何为今月却生东,古月岂当里差算。先生笑谓串月耳,何必五经肉贯串。庚子拜经非我事,只合低头向月拜。文词说月却多名,请与先生约略评。烘云托月画家诀,吟风弄月诗家情。踏月只须安步去,载月不过泛水行。翦月未免涉荒诞,占月亦难通精诚。谁能跳月学苗獠,安得游月偕仙灵。吕錡射月固梦寐,吴刚修月亦杳冥。文士词人古不少,随月待月皆平平。太白捉月最奇事,捉之不获空骑鲸。先生创此串月法,捉一得十骄长庚。大神通作小游戏,想因年老将成精。愿月长圆人长在,先生弟子同长生。串月既容骥尾附,谈文可许龙门登。若把此词传唱出,定知私淑遍寰瀛。
光绪辛卯长至月望后二日,馆侍生严辰力疾作于吴下寓庐之墨花吟馆,时年七十
严辰诗集《墨花吟馆病几续钞》刊本作:
串月弟子词,赋呈俞曲园前辈樾
曲园先生天下师,师其经学兼文词。曲园先生亦我师,师其串月一事奇。中秋串月石湖畔,万人空巷夸吴儿。越人但识三潭印,那能一串如牟尼。先生高坐曲园内,独出新意思匪夷。镜无大小可纳月,正串侧串无不宜。何必石湖远跋涉,凡月到处皆可为。示我一篇《串月歌》,不觉欣羡情为移。先生所学学不到,此事却可颦效施。愿闻其详幸指示,每逢月望辄效之。果然明月不私照,镜中得月无贤愚。一个嫦娥化无数,岂月薄相相娱嬉。仰视天心仍一月,东坡化百复在兹。赢得儿童竞狂叫,破镜掬取惟恐迟。想比春在堂前月,沆瀣一气无参差。串月我堪称弟子,问以他学无所知。经学尤为门外汉,聊因问月一送难。《春秋》二百四十年,不纪月食义何在。离坎分宫非日月,似与风雷不相贯。一月壬辰旁死霸,谁定武成从后案。如月之恒平读去,诗有古音例何乱。大明生东月生西,曲台议礼何尝变。何为今月却生东,古月岂当里差算。先生笑谓串月耳,何必五经肉贯串。庚子拜经非我事,只合低头向月拜。文词说月却多名,请与先生约略评。烘云托月画家诀,吟风弄月诗家情。踏月只须安步去,载月不过泛水行。吕錡射月固梦寐,吴刚修月亦杳冥。文士词人古不少,玩月待月皆平平。谪仙捉月最奇事,捉之不获空骑鲸。先生创此串月法,捉一得十骄长庚。大神通作小游戏,想因年老将成精。愿月长圆人长在,先生弟子同长生。串月既容骥尾附,谈文可许龙门登。若把此词传唱出,定知私淑遍寰瀛。[1]严辰:《墨花吟馆病几续钞》,诗卷三,页二十一至二十二。此据《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689 册,第439 页。
诗笺与刊本相较,“太白”换成了“谪仙”,“雷风”改为了“风雷”;前者较后者多出四句:“翦月未免涉荒诞,占月亦难通精诚,谁能跳月学苗獠,安得游月偕仙灵”,而少了两句:“想比春在堂前月,沆瀣一气无参差”;“光绪辛卯”云云,则为刊本删汰,写作这首长诗的相关信息因而丢失,甚为可惜。
五册《袖中书》,收存38 人共计68 通手札,前此虽未刊布,但不少信札在内容上颇能与已刊俞樾函札相互印证或补充,既有珠联璧合者,亦有遥相呼应者。篇幅所限,聊举数例:
冯一梅在写呈曲园老师的一封信里,探讨俞著《七十二候考》所涉候应之名称异同;俞樾复冯一梅函开篇即云:“《七十二候考》承指示详明,感甚。”[2]俞樾:《致冯一梅》其一,见俞樾著、汪少华整理:《俞樾书信集》,上册,第92 页。一来一往,若合符节。
李滨为继母守制期间,函请曲园先生释答疑惑:“滨奉先继妣练主入庙,虽无迁祧之事,而有合享于先考元配先妣之礼。夫合享之礼,固待终丧行事。惟将来改立练主后,应奉于内寝?应藏于影堂?未敢臆决。”俞樾答曰:“此事《礼》无明文,……可知自汉至唐其奉练主入庙,皆在三年丧毕之后,三年内既未入庙,自然仍奉之于寝,于事为便,于情为安。”[3]俞樾:《致李滨》其一,见俞樾著、汪少华整理:《俞樾书信集》,上册,第244 页。一问一答,高下立见。
弟子陶然求问“‘方响’之制”;博学如曲园,亦不敢信口开河,求之载籍,查证无疑后,始函复之;陶然欣而再上一书,心悦诚服之余,又有所发挥。陶然第一书,迄未闻见;曲园复函,早经刊刻;[4]俞樾:《致陶然》,详俞樾著、汪少华整理:《俞樾书信集》,上册,第487-488 页。陶然第二书,埋没虽久,幸而终见天日。
桩桩件件,对俞樾研究者而言,不啻“天赐良缘”,然细绎情理,却也在意料之中。
四
新见曲园藏札内容的稀缺性、重要性,仍有必要进而言之。
在《俞曲园藏诗笺手札》中先后“出场”的86 位作者,既有祁寯藻、曾国藩、谭钟麟、瞿鸿禨、潘祖荫、陆润庠、恩锡、俞廉三、陈夔龙、曾纪泽等朝廷重臣,也有余联沅、江标、袁昶、徐琪、吴庆坻、汪鸣銮、费念慈等地方官员及门生故吏,还有孙衣言、孙诒让、王先谦、谭献、郑文焯、章梫、陶濬宣等学界名宿。这些中国近代政治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常客”,因为与俞樾的各种各样的关联,“相聚”在这本特殊的合集里,留下珍贵史料的同时,又呈现出各自的另一种面相。
比如,曾纪泽以工楷写呈俞樾的《演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首》,足以证明:素以折冲樽俎见称于世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不乏诗情才思的文学家。
又比如,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陈虬,与陈黻宸、宋恕合称“东瓯三杰”,是中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的创办人,一生以维新变法思想和中医实践两方面的光辉成就载入史册。[5]《陈虬先生传略》,见宫温虹编著:《温州中医药文化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年,第128 页。吊诡的是,在经学大师孙诒让的笔下,两位同乡陈虬、陈黻宸却是另一副面孔:
敝郡有举人陈虬者,谲觚诪幻,向系著名讼师,十年以来,以习西学为职志,藉此干谒当道。而于欧美学艺,实懵无所窥也。立利济医院于郡城,名为教医,实则教讼,邓析襦袴,习以为常。其党有举人陈黻宸者,书吏之子,尤惏鸷。前瑞安岁歉,宸纠众闹署,以术幸免法网。本年又为其妹夫黄姓求应小试。黄之祖为县胥,邑人稔知之,廪保公诉,温守王阻之。临考,宸辄率医院中徒伙,于王守案前攒殴廪生彭姓,几死。场内外大哗,乃散去。刻阖邑廪生公诉其事于学使,而陈虬为宸画策,转以诈索控各廪,邑中公论大为不平。
孙诒让所攻讦者是否属实,暂且不论;孙、陈冲突因公而起,抑或因私而成,倒是值得深究一番;此类私信面世的更大意义,或许在于真实地展现出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1]晚清温州维新人物之间存在的对立情况,学界近十余年来已有所涉及,孙诒让致俞樾此函所言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恰恰是这一对立情况的集中展现,邱林《二十年宿怨:孙诒让与陈虬——从温州戊戌府试打人案谈起》(《历史教学问题》2017 年第2期)即为研究该案的专文。邱文摘要有云:“1898 年7 月温州府试开考之际,因妹夫黄泽中应试一事陈黻宸在考棚外殴打廪生彭某,事件后来扩大为持续半年多的诉讼案,黄体芳、孙诒让、陈虬等也受到牵连。为此孙诒让对非直接当事人陈虬大加斥责,不过这与其说是针对打人案,不如说是孙、陈之间近二十年宿怨的总爆发。同在瑞安小城的孙诒让与陈虬,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都保持着不相往来的敌对状态。孙诒让对陈虬颇有偏见,陈虬也因狂傲不羁的个性饱受挫折,悲愤一生。”此承汪少华先生2021 年2 月15 日提示。
86 位作者中,有50 余位写信人在《曲园所留信札》里从未“露面”,如宋翔凤、张洵、蒋超伯、彭申甫、杨彝珍、蒋一桂、方鼎锐、杜联、金安清、潘祖同、郭传璞、王舟瑶、蔡世佐、戴兆春、朱福铣、李桓、严辰、谢抡元等,换言之,他们写呈曲园老人的诗笺、词笺、手札,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2]同时出现在《俞曲园藏诗笺手札》与《曲园所留信札》的各界人士,虽有孙衣言、许应鑅、俞廉三、陈夔龙、祁寯藻、曾国藩、曾纪泽、潘霨、王凯泰、袁昶、陆润庠、瞿鸿禨、谭钟麟、谭献、丁丙、陈璚、冯松生、吴庆坻、恩锡、王先谦、孙诒让、汪鸣銮、潘祖荫、郑文焯、江标、费念慈、沈树镛、秦缃业、陶濬宣、易顺鼎等三十人之众,但所收各札皆为原迹,无一相同,内容稍有关联者,仅许应鑅、吴庆坻、王先谦、孙诒让等数人而已。曲园师友书札之浩繁,由此亦可窥见,辑录、增补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日人长冈护美的数叶诗笺,此前同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而最令人意外之处,莫过于《袖中书第九册》竟然留存了章炳麟(号太炎)的一篇佚文《三大儒赞》——“三大儒”者,德清俞樾、钱塘高学治、定海黄以周也。众所周知,章太炎师从俞曲园数年间,亦曾问学于高学治、黄以周。[3]参阅陈旭麓:《章太炎传略》,见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249 页。三位师长辞世后,章太炎先后为他们撰写了传记,收入《太炎文录初编》。[4]章炳麟:《高先生传》,见《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八册,第215-216 页;《俞先生传》,同前,第217-218页;《黄先生传》,同前,第220-222 页。不过,将这三位师长并称为“三大儒”,以合传的方式予以评议和纪念,《三大儒赞》是目前所见第一篇。章文缘何而作?写于何时何地?手迹由何而来?此文的存在,能否间接证明“当初他写《谢本师》一文是出于不愿意连累老师的善良用心”?[5]孙荣华《章太炎书赠俞平伯》有云:“俞平伯生前曾告诉过家人:‘章太炎实际并未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当初他写《谢本师》一文是出于不愿意连累老师的善良用心。’看来俞平伯的话是有道理的。”见孙荣华:《文博探求:孙荣华文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217—218 页。所有这些谜团,仍有待一一解开。现将章氏佚文公布于下:
三大儒赞 (《史》《汉》赞体,范《书》之论,陈《志》之评,其实一也,与韵语颂赞不同。)
有动而不行者矣,未有不动而行者也。火之煴也,人炊而华之,其大者风。泠风动之,则小熛;飘风动之,则大熛。日之火不动,人动以燧,铁动于慈石,翕而相附。鱼龙之动而云起,如鬊者,如马者,如石者,如鱼鳞者。如林木之丛菀者,其本竭而止。人有情,情非动则不嬹。礼义动君子,名实动中人。其趋名实,騞然而无阏。曰知者利仁。茹鱼者动,蝇者也。得其所动,腐朽哝喉,而蝇扇其翼。抽簪之无粦火也,雉媒之无雕也,投糁之无鲸与鼍也。不得其所动也,御物者或动而反之。轶驹动于勒,蚁动于磨石,水动于汏,羽箭之逆风,动于江豚,膏其诸有鬼神,而不得已欤?其得所动者欤?情之动也,其有甚,爱恶相攻,其机械日长。礼义不能动,而名实动之,名实又穷,有动之者也。汉之士动于经术,其佣者为利禄,然伏生、贾、董,箕子、伊尹之流也。东汉渐学久,其行愈笃,上不负皇天,下不负夷齐,虽碎首不悔,不以利动者也。郑康成兼之,然操行也不激。其说经简,其蓄德则奥博,故风泽动,黄巾其死也。动先圣学乃如贾、董,躬行尚之,视贾侍中、许慎则远矣。昔周以六德动其民,其陵迟也,逃亡于坚白,而墨翟以兼爱之言动人。洎两汉,始反巍,又有稽、阮动人也,以庄老幻语之,士愿从而尸之,其流也未央。晋之东,浮图又大盛,搢绅人人以为宗师。夷俗之动华夏,遂以孳蔓,皇侃、雷次宗骫经术而趋之。悲夫,唐初有贾、孔,其后秏矣。其士动于词章,风节坏。反之者,宋有韩、富、司马以为相,其下有程、朱、吕伯恭,学术或少驳,其行谊动中国,使士知方,汽汽乎康成矣。明学虽不逮,以苦节相 ,其动如飙起,有足尚者。且夫经术者,礼义之名实也。背死忘生而就淫佚者,必先去其典常,故博人不以文约人,不以礼士行,必畔。清之士动于汉学二百年,惠、戴、段、王卓跞,比贾、许于贾、董,康成则未也。亦会世清晏,故饬行无所事。今大儒曰俞公。高先生曰:定海有黄元同,其经术皆谹远,足以动人。黄氏以《三礼》唱,高先生不言而信矣。俞公穷训诂经义,明疾夷俗如仇雠,时戏究梵书。其说经,摈不取一字。葱领以东皆宗之。乌虖,今中国以景教动矣。小人醉其道,士大夫习其伎。蓺蓺竘以制夷,则可矣。又不竘而假以求餔食天下,不耻驵侩行,簸荡以成之俗也。其名实已不惜,于礼义也何庸?而三大儒以经术动而反之,俞公又著论穷景教,以为佛氏之外道,窃午贯之术以为神,凫藻诸此,而阑楯诸彼。嗟乎,使无三儒者,则士人鞔郁其才力,于经术无所入,下而为科举,又不足尽其材,其铤而从彼决也。今不知其终事礼义也,否矣。而夃亦保居而无走,其犹有望也,抑所动故得其物矣。而用世之士以经术比谀闻,曰是徒为名实,何益于礼义也?则利仁之训其缪夫?钱唐章炳麟书。
此外,《俞曲园藏诗笺手札》留存了著名文人徐琪的六通手札,后四通的史料价值尤其不容小觑。徐琪为曲园得意弟子,光绪六年(1880)翰林,颇著文誉,曾在南书房行走,故生前有手书日记曰《南斋日记》,凡若干册,“卒后自其家流出,散佚不完”,著名掌故家徐一士“仅获见其第十五(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元旦至二月初九日)、第十九(己亥五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七日)二册”,因“有关掌故,可资循览”,故将其移入《近代笔记过眼录》。[1]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152 页。令人欣慰的是,新见徐琪手札之第三通,自题为《谢恩召对恭纪》,内容系光绪十七年八月十四日首次问对情形,第四通系同年九月初四日第二次问对之语,稍可弥补徐一士当年不克窥其全貌的遗憾。而第五通、第六通皆作于光绪庆亲王,王就上前观毕。慈圣命携出,与诸臣共观。庆王奏曰:“是。”并奏云:“再交军机述旨。”慈圣颔之。上御案前有绒鞳冠一、四团龙褂一。上取绒鞳冠授大阿哥,大阿哥跪接。慈圣曰:“当先为我碰头。”大阿哥遂免冠向慈圣前碰头。戴冠起,再免冠,向上前碰头。毕,起立于慈圣旁。慈圣命诸臣退出,于是,一一始退。甫至瀛秀门,军机传述,且缓散,须看谕旨。稍停,至军机处,陈硃笔谕旨于案上,一一敬观。字径三分,二十六年(1900),对影响重大的己亥(1899)建储和庚子(1900)义和团事件期间京城的混乱状况都有详细禀告,分别留下了当事者亲历亲见亲闻的难得史料。
第五通摘录如下:
上年腊月十四日,敕立大阿哥为穆庙皇嗣。琪等及近支王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俱蒙召见,侍郎以下不与焉。是日,慈圣与上并坐仪鸾殿东暖阁,大阿哥立慈圣旁,琪等均赐垫子。(向来一品始赐垫,是日琪等蒙赐,盖出异数。)慈圣略述圣意,即语皇上,可将前日颐年殿所书谕旨取观。上因取折匣一个,内有硃谕,示端楷,硃书,以奏折纸书之,皆上圣藻也。阅毕,始各退出。
第六通选登于下:
此次之变,先是拳民进城,无人过问。于是,择教民而焚之、杀之,遂烧无数教堂。最伤元气者,是烧大栅栏一药水店,延及炉房、珠宝市,遂上城楼,而至东江米巷。此上月二十日事也。炉房闭,而银市不通,米价大贵,典质库中百物不当,黄金皆无人要。始而京官十室九空,继而铺伙、居民亦纷纷散矣。幸菜市、油盐等店一切如常。银票不用,现银尚可。
慈圣于上月廿六日已还宫,人心尚定。惟董军屡以炮轰东江米巷及西什库(西华门西北),终日炮声不绝。琪处幸偏西,地尚平静。府尹署在东北,亦好。若东南之头、二、三条胡同,并非炮轰,乃是官兵乱抢。
……
出京诸人,有被阻者,有被伤者,有被抢者,不一而足。刘伯崇殿撰福姚,戴洋式靉靆,含吕宋烟而出,遇团至,曰:“此妖民也。”执之。其仆曰:“此皇上家状元也,不可。”团乃焚香,香不动。劈其箱,无禁物,曰:“我辈百姓尚为朝廷保护,尔官也,何去为?可仍回京矣。”乃纵之回。黄慎之殿撰送其眷,遇团,亦阻之,云有邪气。焚香,香不动,而微黑。再三求之,送至庄王府,住三日,闻昨交刑部矣,不得其详。大约伊创昭信股票,衔之者众。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利真不可轻言哉!其余湖南杜格生传胪,眷属被伤,折回;梁燕生(名士诒,粤人)编修,眷属被劫,更指不胜屈。包缵甫尊人避至津,不通,至河西务、杨村,皆不可,乃至保定。昨有书来,亦深以不动为然也。
五
从内容编排上看,曲园老人是将友朋唱和的诗词与书札分开装帧的,这一点也有必要稍作分析。
诗笺、词笺原本也可能与书信一并寄来,曲园老人将其单独汇集装帧,恰恰说明诗笺与书札是有明显区别的。古人将精致华美、尺幅较小的纸称为“笺”,因为颜色绚丽,也称“彩笺”。用以写信,便称“信笺”;借以题咏诗词,即为“诗笺”(“词笺”)。传统文人往还,常有诗文唱和,鱼雁传书,诗翰也随之而来。不过,诗笺较之信函,天生更具艺术审美之趣味。在精美的笺纸上用心抄录自己构思巧妙的诗作,往往还要钤盖反映作者情趣、心境的闲章。这样的作品,远比嘘寒问暖、互通消息的日常书信要雅致得多。
比如,广东番禺人许应鑅,在江西、河南、江苏、浙江等地辗转任职,游宦之余嗜好收藏晋砖。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的诗笺上会钤盖“丁卯诗人”“晋砖吟馆”“管领湖山”“大江南北东西第九度游客”等四枚闲章。
又比如,湖南湘阴人李桓所作三通诗笺,则钤有“黼堂词翰”“黼堂五十后所作”“西湖寓公”“奋勉可嘉”“遍游两浙”等印。
而江苏江都人蒋超伯在诗笺所钤闲章,则为订正俞陛云之误判提供了一条有力佐证。《先友诗笺第一册》封面贴签有该册诗人名录:“宋太守翔凤于庭、祁文端寯藻春圃、张文节洵肖庵、曾文正国藩涤生、舒阁学兴阿叔起、孙太仆衣言琴西、王文勤凯泰补帆、恩方伯锡竹樵、陈制府璚鹿笙、彭孝廉申甫丽松、潘明经承翰少梅、蒋太守一桂犀林、谭文勤钟麟文卿、王祭酒先谦益吾。”各家诗笺,即依此编次。其中“舒兴阿”一诗,题为《天祺节扈游同乐,获窥福海瑶台之胜,归得大集,率成一诗奉柬》,起句作“昨游昆阆循丹梯,海天一碧揩瑠瓈”。此诗笺未署名,篇末仅钤二篆印:一曰“叔起”,一曰“参佐桥头是我家”。恰巧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四录存了此诗:“旧箧中,尚有蒋叔起超伯七古一章,其题云:‘天祺节,扈游同乐,获窥福海瑶台之胜。归而得读大集,率成一诗,奉柬。’盖是时,叔起犹官比部,值枢廷也。诗曰:‘昨游昆阆循丹梯,海天一碧揩瑠瓈。……’”[1]俞樾:《春在堂随笔》,见赵一生主编:《俞樾全集》第十九册,第71—72 页。据而可知,作者实为蒋超伯(字叔起)。蒋超伯(1817-1871),初字梦仙,改字叔起,号通斋,又号南漘翁,江苏江都(今扬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刑部主事,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后任广西南宁知府,广东高州、潮州知府,摄广州知府,署广东按察使。蒋氏籍隶江都(扬州),参佐桥为扬州“二十四桥”之一,故有此闲章“参佐桥头是我家”。《先友诗笺第一册》封面所书“舒阁学兴阿叔起”,则指道、咸朝大臣舒兴阿。舒兴阿,生年未详(一作1796,一作1799),字旺山叔起,号云溪,[2]黄泽德编:《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33 页。按,《林则徐信稿》在《致舒兴阿》一函之注释中略云:“舒兴阿,字旺山叔起,号云溪,满洲正蓝旗人。”“旺山叔起”作何解?“叔起”是否为其略称?仍有待高明赐示。赫舍里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二十二年(1842),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及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后任伊犁参赞大臣、和阗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户部左侍郎、陕甘总督等职。咸丰八年(1858)卒。因蒋超伯、舒兴阿之表字皆为“叔起”,故俞陛云有此之误。此诗之所以“蒋冠舒戴”,固然因二人表字相同而引发误判,但也间接证明了名录贴签的书写者不是俞樾本人,而是其孙俞陛云。
不难发现,这些印章,不仅可以展现篆刻艺术,还表达出诗笺作者的情趣和思想,而且包含了不少作者的生平信息,其价值也超出了一般的诗文创作。这或许是曲园老人将师友诗笺、词笺单独保存的原因。
总之,此次曲园师友诗笺手札的整理、出版,为以往更多关注“俞曲园手札”的学术界,提供了拓展或推进研究的巨大空间。而只有通过往还书信的综合研究,才能共同绘制出以俞樾为枢纽的晚清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