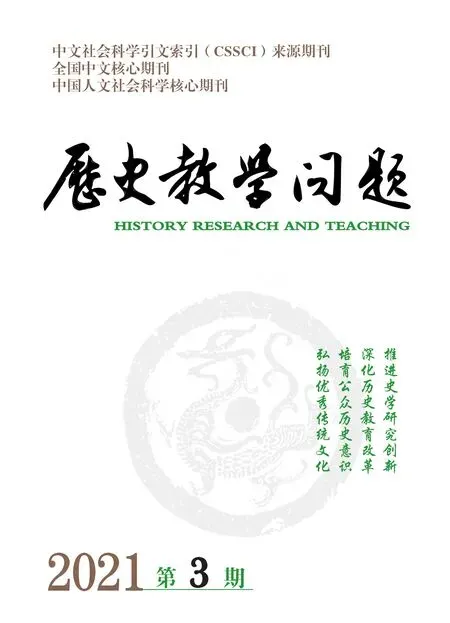吕思勉中国通史撰述对赵翼史学成果的借鉴与超越
单 磊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通史的优长在于系统地表达对历史的总体性认识。20 世纪上半期,史学界涌动起一股编撰中国通史的热潮,“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风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81 页。这些著作除《中国史纲》外,都对清代乾嘉史家赵翼(1727—1814)的史学成果有所借鉴。近代以来,许多著作“或直接摘引旧书之文,或据《廿二史札记》等书转引旧史之文,非出于自身熔铸成书”。[2]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 年,第194 页。《廿二史札记》“所搜辑锤炼的大量典型史料和精辟论述大多成为近代众多通史著作的史料来源和论述基础”。[3]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 年,第203 页。赵翼著作对吕思勉(1884—1957)的中国通史撰述影响尤大。本文以吕氏《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为中心,[4]《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约60 万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年初版。《吕著中国通史》是在上海“孤岛时期”(1937—1941)编撰的,分上、下两册,共约40 万字,先后于1940 年和1944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是对192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进行通俗化处理后的白话文著作,约40 万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初版。2015 年,中华书局重新整理出版该书,并将书名改为《中国通史》。运用史源学方法,以文献对照和逻辑推演的方式,对赵翼著作与吕思勉中国通史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以期揭橥两位跨越古今的史学大师之间的学脉关联。
一、赵翼著作与吕思勉中国通史学术关联考述
吕思勉在展开中国通史撰述时,对赵翼立论的诸多问题饶有兴味,对其考史、论史成果多有借鉴,并对其考证结论和历史认识有所拓展、深化或驳正。以下选取几例二人均有较浓兴趣的问题进行实证考察。
(一)战国、秦、汉封建政体反动和平民革命
政体反动和阶级反动,是吕思勉叙述战国、秦、汉史的两条线索。前者表现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后者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平民革命。两条线索彼此勾连,相互影响,共同构成这一历史变局的基本图景。其叙述和认识直接受到《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的启发。
关于先秦时期布衣将相之局的演进,赵翼考述道:自行封建以来,诸侯世袭君位,卿大夫世居其官,延绵数百年,似乎理所当然;随后此制度弊病丛生,荒淫暴虐之君层出不穷,贵族内讧频仍,王室遭到挑战,政治崩坏,积重难返;列国纷争,并为七雄,尔攻我伐,民不聊生;世侯、世卿之局相沿已久,难以遽然改变,故而自下而上开启变局;有徒步而为相者,有白身而为将者,布衣将相之局逐渐形成。[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华书局,2013 年,第36—37 页。
吕思勉标注参阅赵翼的这些成果,并从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因应封建制度破坏后的时局着眼展开叙述。他称:
到战国时代,贵族阶级,日益腐败。竞争剧烈,需才孔亟。而其时学术发达,民间有才能的人亦日多。封建制度既破,士之无以为生,从事于游谈的亦日众。于是名公卿争以养士为务;而士亦多有于立谈之间取卿相的,遂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2]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华书局,2015 年,第76—77 页。
赵翼采用历时性的论述思路,逐层深入,揭示变局,分析阶级反动的成因。吕思勉接受其见解,从官制、兵制和成文法改革着眼,结合交通、风俗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等因素进行分析。他断言:“封建郡县的递嬗,纯是世运的变迁,并非可以强为的。”[3]吕思勉:《中国通史》,第75 页,第167 页。他认为在世运渐趋统一的历史背景下,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难以抗拒的趋势。
关于平民势力抬头,赵翼作出了精彩的论述。他首先叙述了汉初君臣之出身,随后称:
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第36—37 页。
他认识到这一变局,富于洞见;但以“气运”来解释,有些乏力。吕思勉标注参阅其文,指出继卿大夫革诸侯的命之后,又发生了平民革贵族的命,并以“社会组织的变迁”来解释。[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177 页。结合语境,对照文意,借鉴关系一目了然。
不过,二人的视角、思路和具体见解有较大差异。在赵翼看来,刘邦集团大多出身平民,只有张良等极少数人出身贵族;他们最终夺取天下,乃时势和气运使然,是政权自贵族滑向平民的趋势决定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战国以降平民革命的最后一环,至此完成权力下移。在吕思勉看来,秦崩、楚亡、汉兴,是封建、郡县两种政体激烈交锋的结果;陈胜首义之后,封建制死灰复燃;刘邦集团崛起并定鼎天下,又摧毁了封建制;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封土建国的第一次失败和平民革命的第一次成功。
吕思勉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因应新形势,运用新史观,将这一变局纳入到阶级和政体的双重反动之中去考察,得出发人深省的见解。汤、武革命乃诸侯革天子之命。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天子式微,诸侯坐大。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开启战国时代,乃大夫革诸侯之命。秦吞灭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封建、置郡县,然而世人习于列国分立,视之为理所当然,秦行郡县反倒是一个变局,致使人心思乱,四海鼎沸。秦亡之后,封建政体的反动力大张其焰,诸侯纷立乃势所必然,项羽行分封也属顺理成章。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乃社会组织变迁使然,是平民革贵族之命的结果。汉朝建立后并未荡除封建制,侯国犹存,功臣、宗室、外戚三大集团对朝廷形成离心倾向,“七国之乱”也由此酿成。继后统治者逐步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直至武帝后封建制才名存实亡。[6]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169—173 页。
(二)中古文化、政治与社会
吕思勉对中古历史演进的叙述,深受赵翼考论成果的影响。此处从文化、政治与社会三个方面各选一例予以阐明。
赵翼考察了汉儒对灾异的认识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并将之纳入上古以来天人关系的认知框架中,揭示了时代愈古则愈敬畏天意、时代愈近则愈崇尚人力的演进趋势。[7]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儒言灾异》,第39—40 页。吕思勉隐括其意,叙述道:“两汉时代的迷信,并非下等社会才然,即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试看当时政治上,遇天灾而修省,或省策免之公等,都略有几分诚意,和后世视为虚文的不同。”[8]吕思勉:《中国通史》,第75 页,第167 页。此处明确标注参阅《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条。事实上,同卷之“汉重日食”“汉诏多惧词”“灾异策免三公”等条也与此大有关联。
不过,二者的主旨和认识不尽相同。受时代局限,赵翼对敬畏灾异的现象并不持全然拒斥态度。他称:“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儒言灾异》,第39—40 页。吕思勉对之虽有所借鉴,却未必完全接受。更重要的是,其主旨并非对此种历史现象进行历时性的考述,而是将此置于中古文化变迁的范畴内去审视。他认为:“从两汉到魏、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关。其要点,在破除古代的迷信,而从事于哲理的研究。”[2]吕思勉:《中国通史》,第167 页,第195 页,第173 页。将两汉迷信视为破除的对象,含有否定和贬斥之义。将由破除迷信到从事哲理研究视为中国文化转关的要点,是一种富于洞见的进步思想。
赵翼考述了周、唐之间千余年达官显宦自择下吏的现象:
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盖犹沿周制。……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又郡守置掾属并皆用本郡之人。……魏、晋、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实自隋始也。唐时亦尚兼用汉制。[3]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十六《郡国守相得自置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269—270 页。
其论据丰富(引文省略部分),论证有力,认识通达。吕思勉撷其精华,隐括大意,沿其思路,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叙述道:“汉世郡县之佐,都由其长官自辟。所辟的大都是本地人。历代都沿其制。隋文帝才尽废之,别置品官,悉由吏部除授。”[4]吕思勉:《中国通史》,第167 页,第195 页,第173 页。他借之阐述中古选举制度的变迁,指出官吏由长官自辟演变为朝廷任命, 用意主要是“防弊”,而非“求才”,由此引入到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吕思勉对中古时期阶级问题的叙述较大程度上因袭、借鉴了赵翼的考论成果,大多明确标注了出处。如,他隐括了赵翼关于六朝尊崇门第至唐末五代门第观念消融的历时性考述,[5]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第287—290 页,第290 页。并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一变迁的原因:“(一)因自六朝以来,所谓世族,做事太无实力。……(二)则世族多贪庶族之富,与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谱,及把自己的家谱出卖的。”[6]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71—72 页。前一点借鉴了《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和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后一点借鉴了《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财婚”条和《陔余丛考》卷十七“谱学”条。
赵翼对魏晋南北朝阀阅观念、忠节观念以及士庶地位升降等问题考辨颇详。他论述道:
历观诸史,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膴仕,本属分所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毋怪乎易代之际,莫不传舍其朝,而我之门户如故也。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记传所载,遂无一完节者,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转出于寒人。[7]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第287—290 页,第290 页。
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弊也。[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第268 页。
吕思勉对此借鉴颇多,通过叙述世家大族极少建功立业而寒庶势力功勋卓著的现象,阐释两大阶层权力变迁和地位沉浮之因;通过叙述士族鲜有与国同休戚者而庶族多与国共荣辱的现象,阐释世变之由。如,他叙述道:
魏晋南北朝,正是门阀制度如日中天的时代。此时的贵族,大抵安坐无所事事。立功立事,都出于庶族中人,而贵族中亦很少砥砺名节,与国同休戚的。富贵我所固有,朝代更易,而其高官厚禄,依然不改。社会不以为非,其人亦不自以为耻。这真是阶级制度的极弊。[9]吕思勉:《中国通史》,第167 页,第195 页,第173 页。
他不仅叙述了历史现象,还将赵翼所论风习积弊引向深入,用来论证阶级制度的弊端。此外,他通过叙述财婚现象,揭示以财币为纽带的跨阶层通婚模糊了门阀界线,通过叙述伪造谱牒和士庶通谱的现象,阐明谱牒遭到破坏反映横亘在士庶阶层之间的障碍被清除,同样借鉴并发展了赵翼的考论成果。
(三)古时金多而后世渐少现象
赵翼对上古至明代使用钱币的历史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梳理和考辨,[1]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银》,第562—566 页。又对金银由以斤计到以两计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述。他称:“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南北朝时犹以斤计,……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陈、隋之世也。”[2]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金银以两计》,第566 页,第567 页。接着分析道:“古时金银价甚贱,故以斤计,后世金银日贵,故不得不以两计也。”[3]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金银以两计》,第566 页,第567 页。此外,他还对惯称的“一金”进行了考辨:“今人行文以白金一两为一金,盖随世俗用银以两计,古人一金则非一两也。……古之一金乃一斤耳。”[4]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一金》,第567—568 页。综合而论,他认为金银的价格呈现出由贱而贵的趋势,计量单位呈现出由斤到两的趋势,前者是后者之因。他表达了“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的观感,举出嬴秦至新莽诸例论证;指出汉代以后黄金数量日渐减少而价格日渐昂贵的趋势,将之归因于两点:一是开采殆尽,产量减少;二是佛事耗损,难以复原。[5]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汉多黄金》,第66 页。
吕思勉受到赵翼启发,却不认同其见解。他叙述了金、银、纸币的演变历程,发出疑问:纸币之弊为人深知,为何不代之以金,而要代之以银?接着论述道:
从前的人,都说古代的黄金是多的,后世却少了,而归咎于佛事的消耗。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都如此说。其实不然。……古代人民生活程度低。又封建之世,服食器用,皆有等差。平民不能僭越。珠玉金银等,民间收藏必极少。……所以古代所谓金多,并非金真多于后世,乃是以聚而见其多。后世人民生活程度渐高;服食器用,等差渐破;以朝廷所聚之数,散之广大的民间,就自然不觉其多了。读史的人,恒不免为有明文的记载所蔽,而忽略于无字句处。[6]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第208 页。
无论是事实认定层面的考实性认识,还是原因分析层面的抽象性认识,他都对前贤之见提出了明确的否定性意见。他认为,古时金多而后世渐少只是一种直观感受,并非实然;究其原因,乃古时黄金积聚于朝廷和达官显贵家中而后世散落于民间所致;前人仅据文字记载的表象而未深察其故,以致形成错觉,得出不确切的判断。
二、赵翼与吕思勉在学缘、理念、旨趣、风格和方法上具有相通性
(一)地缘和学缘相近
赵翼的籍贯阳湖和吕思勉的籍贯武进,都属于今天的江苏常州。两人生活的时代虽相隔百余年,但共同的桑梓地是相近学缘的天然纽带。赵翼史学嘉惠后学,诚匪浅鲜。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吕思勉史学与家乡的学术文化底蕴紧密相连,自然受赵翼史学的影响。
吕思勉敬重这位同乡前贤,幼时便在父母、姐姐指导下阅读《廿二史札记》,“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7]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742 页。他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求学,之后在家乡执教,期间时常研读赵翼著作;后离开故里,先后在多所高校执教,仍研读不辍,终其一生都深受教益。
赵、吕均深受昆山顾炎武的影响。赵翼以顾炎武为人格楷模,将其思想、理念奉为圭臬,治学亦祖述之,《廿二史札记》即有模仿《日知录》的意味。吕思勉与顾、赵学缘关系较近,曾自述:“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8]吕思勉:《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第756 页。其遗稿中有一份“古书名著选读拟目”,首先开列的即是这两部书。他称:“此两种可先阅之,以见昔人读书之方法。”又在全部开列书目之后称:“以上所举,皆第一步必读之书,……过此一步,则自有门径,自有乐趣,不觉其茫无津涯矣。”[9]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965—967 页。向后学指示门径,也反映出自己步入史学门径所依凭的经典。
(二)淑世情怀,经世理念
赵翼是一位颇具淑世情怀的读书人,既有“内圣”之念,又有“外王”之意。其入世欲望强烈,中年以前沉浮于官场,致仕后济世理想犹存,报国之志弥坚。稽古揆今,经世致用,是其史学生命力强劲的重要因素。与同时代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的学人不同,他热切关注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尤为重视。《廿二史札记》“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1]孙星衍:《赵瓯北府君墓志铭》,《赵翼全集》第六册《附录二·赵翼生平与传记资料》,凤凰出版社,2009 年,第39 页。李保泰评价道,该书援古证今,指陈贯串,折衷往昔,斟酌时宜,对国家之大措置、民生之大兴建多能识沿革之由、利病之故,竭力探寻维持补救之方,于当世之务大有裨益。[2]李保泰:《李保泰序》,《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二,第922 页。
吕思勉为人、治学均受顾炎武、赵翼的影响,称赏《日知录》《廿二史札记》“钩考有关致用之问题”,[3]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史学与史籍七种》,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87页。同样十分关注社会现实、民生日用。他怀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针砭时弊,立志改革社会,密切关注社会形势的变化,有意识地将经世致用精神贯彻进研究和撰述实践中。其数部中国通史均是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完成的,均有略古详今、关切现实的特征,就反映了这一点。
(三)会通精神,明变意识
赵翼治史有大气魄,器局宏阔,融会贯通,善于把握大势。钱大昕评价道:“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4]钱大昕:《钱大昕序》,《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二,第920—921 页。舒位赋诗盛赞:“谁识三千风月外,胸中别有四千年。”[5]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一二《奉和赵瓯北先生八十自寿诗原韵》,清光绪十二年(1886)边保枢刻十七年增修本。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也称他擅长“对历史大势的通论”,“通论中蕴含着一种创新的见识”。[6]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264—265 页。蒙文通认为《廿二史札记》就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7]蒙文通:《治学杂言》,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 年,第3 页。赵翼史学还有知常明变的特点。《廿二史札记》着重考察“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首,第1 页。《陔余丛考》也有近似旨趣。
吕思勉“十分讲究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着重于探讨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注意摸索重要典章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其变化原因”。[9]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 年,第5 页。其史学不仅有通、变的特点,还试图求其因果,进而设法改良、补救。他称: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原来宇宙之间,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这个变迁,就叫做“进化”。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他的“原因”,就可以豫测他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10]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3 页。
他研治史学的基本路径是:首先摄其全体、观其会通,进而认识历史整体及其变迁,然后揭示因果关系,最终探寻应对之策。
以“通”论之,吕思勉是近代会通派史家的代表,治史有通贯、周赡的特点。他力倡“通人之学”,主张“观众事之会通以求其公例”。[11]吕思勉:《沈阳高师中国历史讲义绪论》,《吕思勉诗文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329 页。他一生著述宏富,但最能体现其治史风格的还是几部中国通史;以“变”论之,吕思勉重视历史现象的变迁和处于转折期的人物、事件。进化,是“变”的高级形式。他反复论说:“才说现在,已成过去,欲觅现在,惟有未来,何古何今,皆在进化之长流中耳”;[12]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38 页。“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13]吕思勉:《中国通史·例言》,第6 页。他自觉运用进化史观,善于以进化的思维纵论古今;以“因果”论之,吕思勉编撰中国通史的核心旨趣即在于从通、变之中抽绎演进轨迹及内在动因。他将“历史”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1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绪论》,第3 页。他对因果关联措意甚多,尤其善于探寻“从前——现在——将来”的因果关系,称:“史也者,所以臧往以知来。盖凡现在之事,其原因皆在于从前;而将来之事,其原因又在于现在。必明于事之原因,然后能豫测其结果,而谋改良补救之术。故史也者,所以求明乎事之原因,以豫测其结果者也。”[1]吕思勉:《沈阳高师中国历史讲义绪论》,《吕思勉诗文丛稿》,第333 页。职此之故,他总能见微知著、闵乱思治、盛必虑衰,既可对历史进行精辟的分析,又可对未来展开天才般的预测。
(四)推崇笃实,善作札记
赵翼是乾嘉历史考证学派的重要人物,治史崇尚笃实,是吕思勉效仿的主要对象之一。吕思勉称:“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2]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0 页。他之所以重视考证,是因为认识到确切的事实是揭示因果、阐释规律的基础。他一再强调:“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他的‘事实’”;[3]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5 页,第9 页。“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5 页,第9 页。他自述编撰中国通史时“所引的书,自信都较为可信;引据的方法,自信亦尚谨严”。[5]吕思勉:《中国通史·例言》,第5 页。
善于撰写札记,颇能反映二人务笃实的特点。赵翼自述:“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6]赵翼:《陔余丛考·小引》,第1 页。“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7]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第1 页。他运用百花采蜜的方法,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形成了一条条札记。《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均为札记结集而成。吕思勉也以读史、钞书为日课,自述:“往者吾尝昼夜孜孜,以从事于抄书矣。祁寒盛暑,罔敢或辍,即有小病,亦尝不肯自休也。”[8]吕思勉:《国体问题学理上之研究》,《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70 页。他自少年时代起即开始作札记,笔耕不辍,直至终老,撰写札记达数百篇,上百万言。有学者指出,其断代史著作“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直以札记体裁写出,每节就如一篇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9]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180—181 页。吕思勉深通博观约取之道,阅读大量资料撰写札记,将札记作为建构学术体系的基石,然后由博返约、厚积薄发,最后进行系统性研究和撰述。他的几部中国通史就是在平日所作札记的基础上形成的。
(五)重视正史,贵在识断
赵翼重视正史,自觉抵制炫博、猎奇、述远之风。《廿二史札记》书名虽为“廿二史”,实际上遍考“二十四史”,包括不被时人认可的《旧唐书》《旧五代史》。该书“小引”强调正史的价值,阐明采摭正史的缘由。以正史为宗本的史料观一方面是藏书不足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他对正史与野史地位的认识决定的。在其头脑中,正史处于史料序列的最高层级,经过了史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他主张以正史为考证的基本素材和依据,抵制野史对史学活动的干扰。章太炎称《廿二史札记》“将正史归类,其材料不出正史”。[10]章太炎著,傅杰编校:《清代学术之系统》,《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399 页。这一评断不尽符合事实,却可反映近人对赵翼史料观的基本认知。《陔余丛考》虽非全然考史,然第五卷至第十八卷列有近200 个正史考证的条目,同样多据正史参互考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重视正史的史料观。
20 世纪上半期,史学界兴起一股轻贱正史的学风。不少学人热衷于从“碧落”“黄泉”之中搜求所谓新史料、珍稀史料,而视正史等常规史料为废铜烂铁。与此学风有异,吕思勉并不刻意搜讨所谓珍稀史料,而是极重正史,常置于案头,随时翻检。他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曾通读数遍,早已在学界传为美谈。其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多以正史为基本史料。他盛赞《廿二史札记》“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是“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11]吕思勉:《吕思勉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年,第324 页。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正史在研治史学中的地位的肯定。
赵翼虽以考史家著称,但颇具识断。有学人称他“既非如考据家之僻搜,又非学究家之不考而击断,最为可法”。[12]刘咸炘:《刘咸炘论史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241 页。还有学人称他洞察力敏锐,“通达世故,所以有着相当敏锐的议论”,“笔触机敏,读起来很耐人寻味”,[1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第264—265 页。故而“能在众多纷纭的史实中,攫取最关系历史演进变迁者,予以排比综合,以致近乎西方历史解释的新论丛出”。[1]其书审订诸史曲直,既指其瑕,又彰其瑜;斟酌时事,既不蹈袭前人,又不有心立异,实乃有体有用之学。[2]
吕思勉治史不以材料见长,而以识断取胜。他认为学问之道贵在自得,“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3]杜维运:《赵翼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第297页。“心思要灵,眼光要远,方能辨别是非,开拓境界”。[4]钱大昕:《钱大昕序》,《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二,第920—921 页。他以一己之力编撰的几部中国通史,对许多问题的认识独具只眼。顾颉刚评价道:“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5]吕思勉:《丛书与类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41 页,第541 页。此言得之。
三、吕思勉中国通史为何借鉴赵翼史学成果
吕思勉在撰写中国通史时依凭的传统史学资源颇为丰富,仅以类别划分就有正史、杂史、别史、政书、史论、史评、方志、掌故、档案,以及经、子、集诸部文献,其中对赵翼著作的借鉴明显较多。除前述二人的诸多相通性因素之外,赵翼著作的特点与吕思勉中国通史的撰述旨趣相契合,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吕思勉的几部中国通史的编撰初衷,是当作大、中、小学生的教材或青少年自修读物。历史教材通常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开示门径,二是激发兴趣,三是呈现历史梗概、揭示演进大势。赵翼著作具有的便于入门、趣味性强、触及重大问题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吕思勉编撰教材的需求。首先,开示门径。吕思勉致力于为学生指示治学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6]吕思勉:《丛书与类书》,《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41 页,第541 页。且一贯主张治史当由正史入门。《廿二史札记》是绝佳借鉴对象。张之洞将该书视为“读正史之资粮”。[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81 页。梁启超将该书推荐为入门读物,称:“学者读正史之前,吾劝一浏览此书。”[8]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序例》,第1—2 页,第1 页。曾校注该书的王树民也称该书“为初读廿四史者指示途径之作”,“初读廿四史者,藉此得窥门径,实为其书主要价值所在”。[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27 页。其次,激发兴趣。无论是教材,还是自修读物,都主要面向青少年,“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10]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指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1 页。赵翼著作与乾嘉时代其他著作相比少了几分艰涩、枯燥。梁启超称《廿二史札记》可为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11]王树民:《前言》,《廿二史札记校证》卷首,第1 页,第3 页。金毓黻也称该书“本末洞然,富有逸趣,读其书者,乃至不忍释手”。[12]吕思勉:《中国通史·例言》,第2 页,第4 页。再次,呈现历史梗概、揭示演进大势。历史容量广阔无垠,发展线索千头万绪,唯有触及重大问题,抽绎出主线,采取以简驭繁的策略,方能勉力为之。吕思勉深谙此理。他称:“须知‘常事不书’,为秉笔者的公例。”[13]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348 页。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不必尽记,只须记得“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1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345 页。“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15]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史籍七种》,第18 页,第4 页。就足够了。他将这一理念贯彻进中国通史撰述中,表示要把中国历史上紧要之处的重要史事通过钞录原文(有删节而无改易)的方式摘拣出来,而将己意注明于后。[1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史籍七种》,第18 页,第4 页。赵翼的考论成果能够触及关乎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梁启超曾论:“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17]吕思勉:《中国通史·例言》,第2 页,第4 页。这种理念和风格驱使他能够“很快找到历史上富有关键性的大问题”。[18]杜维运:《赵翼传·序》,第8 页。赵翼著作注重对国计民生、盛衰兴亡、经验教训以及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史事的考证和评论,与吕思勉的撰述需求相契合。
四、吕思勉中国通史对赵翼史学成果的超越
吕思勉中国通史对赵翼史学成果既有因袭和借鉴,又有发展和超越。统归起来,大略有如下诸端:
其一,科学精神和方法。中国传统史学科学精神淡弱,以致史料虽丰富却如无序乱丝,阻碍了史学事业进步。欲摆脱这种困局,就要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史料。乾嘉历史考证学是前现代科学化史学的典范。赵翼治史颇具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的技艺较娴熟。吕思勉史学更胜一筹。他认为治史宜有科学的眼光,“处处以科学之方法行之”;[1]吕思勉:《沈阳高师中国历史讲义绪论》,《吕思勉诗文丛稿》,第329 页。倘若缺乏科学精神,不运用科学方法,实难有所成就。[2]吕思勉:《研究历史的感想》,《吕思勉诗文丛稿》,第356页。所谓“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3]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序例》,第1 页,第2 页。实际上就是科学精神和方法。
其二,历史观。赵翼批判厚古薄今和一治一乱的历史观,认为今胜于古,后胜于今,呈现出朴素的历史进化观,但受时代局限仍难跳脱旧史家的思维。吕思勉头脑中的历史进化意识很强,一扫崇古卑今和循环往复的历史观,转而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撰述。历史分期颇能反映这一点。赵翼著作以时代、文献、问题和类别为线索展开考述,先后次序基本上按照历史发生的时代和文献出现的时代,分期意识较弱。吕思勉著作的历史分期意识较强,且突破了以朝代更迭为线索的分期标准,以社会、制度、文化、风习等的变迁为准绳来划分历史阶段,并呈现阶段性特征。如,《白话本国史》分为上古、中古(上、中、下)、近古(上、下)、近世(上、下)、现代五个阶段。吕思勉除了运用进化史观外,还运用了唯物史观。如,他认同百姓日用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重视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因,赞赏从物质经济因素解释历史演进脉络和法则的思路。
其三,民族国家意识。赵、吕均具有强烈的淑世情怀和经世意识。所不同者在于,赵翼生活在由盛世向衰世转折的时代,充满忧患意识,著作多关乎国计民生;吕思勉生活于内乱不绝、外患频仍的时代,其著作是风云激荡的产物,重在启迪民智、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具体论之,赵翼眼中的“天下”大略是指“中原”和“四夷”,所谓“国家”依然是指旧史书中一家一姓的朝廷;而吕思勉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天下”是指新航路开辟以来的全世界,与之相对应的“国家”已经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中国通史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措意较多,一方面表彰汉人抵御异族的斗争,另一方面逐渐突破华夷秩序的叙述框架,对关涉“其民族遂入于中国,变为中国之一民族者”叙述较详,[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序例》,第1 页,第2 页。撰述宗旨是阐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这对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忱、鼓舞民族斗志大有助益。
其四,体系性。赵翼著作是退居乡里期间读书心得的汇集,体系性较弱。《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中的每一条或一组札记相对独立,与其他条目和组别的关联度不高。吕思勉各种著作是一个整体,联系紧密,浑然一体,往往由一个共同主旨统摄全书。这与其“全史”意识有关。他主张开阔学术眼界,不能拘拘于局部的、狭窄的范围,“求学的初步,总以博涉为贵”。[5]吕思勉:《孤岛青年何以报国》,《吕思勉论学丛稿》,第360—362 页。他注重将历史与社会相结合,称:“夫历史者,说明全社会者也,惟全社会能说明全社会,故昔之偏举一端,欲以涵盖全史者,无有是处。而在今日,则历史与社会两学,实相附丽。历史所以陈其数,社会所以明其义也。”[6]吕思勉:《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43 页。
其五,平民性色彩的社会史叙述。作为18 世纪的作品,赵翼著作打上帝制时代的烙印,关注对象主要是帝王将相、军政大事、宫闱秘闻、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科举文化、谶纬迷信等,对下层百姓虽有同情之心,却终究不能站在他们的立场,对自下而上的反抗斗争多持贬抑的态度。总体来讲,其著作体现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士大夫对历史和现实的体认。作为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积极践行者,吕思勉激烈批判旧史书不知社会为何物的弊端:
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改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1]吕思勉:《中国通史》,第5 页。
旧史书侧重于记载所谓“大历史”,而对社会生活层面的“小历史”记述较少。其中国通史则较多地记述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等,力图动态地呈现社会发展全貌。旧史书往往以“君”为中心、以政权兴衰更迭为线索,贬抑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和价值。其中国通史以“群”为中心、以“群”的演进为主线,重视平民性色彩较重的社会史,尤其重视百姓日常生活史,充分肯定民众的力量。
其六,古为今用。赵翼史学有以史为鉴、借古讽今的特点,已为学界周知。吕思勉具有更加强烈的镜鉴意识和现实关怀。他批判只在纸上而不在空间的学问,主张治史既要能为古人作忠臣,又要能为当世效实用,否则读书似极无用。[2]吕思勉:《论国人读书力减退之原因》,《吕思勉诗文丛稿》,第525 页。他称:
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3]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15页,第204 页。
绳古以论今,鉴往以知来,将历史、现实、未来三者视为一个连贯性的整体来审视,是吕思勉史学的一大特色。他善于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之事互勘,“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15页,第204 页。又能根据对历史的研判和对演进逻辑的认识,做出对未来的预测,提出建设性倡议或主张。其中国通史对历史的记述不是盲目无序的,而是带有明确而强烈的主体意识的,体现出古为今用的理念。
结 语
吕思勉兼具旧学和新知,传统学术根底深厚,又追求治学理念、路径和方法的新取向。其中国通史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新与旧、中与西有机融合的结果。其中,本土传统史学的滋养是一个重要因素。吕思勉史学植根于传统史学的沃土,对乾嘉史学的借鉴尤为显著。处于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环节的乾嘉史学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既有清理、总结既往成果的功绩,又有开启新型史学形态、范式、理论和方法的贡献。在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域外碰撞的过程中,乾嘉史学蕴涵的现代性因素十分丰富。近代以来,许多史学流派和不同风格的史学家均从中汲取学术养分。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直观地呈现本土传统史学的近代价值,旨在阐明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传承与创新,企望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吕思勉的治史理念、风格、方法在当时并非主流,因而时常有知己落落的孤寂感,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治史道路,对自己的学术充满信心。他曾赋诗《后三日复集》云:“岂以知音少,而疑吾道非。”[5]吕思勉:《蒿庐诗稿》,《吕思勉诗文丛稿》,第67 页。或许,他在同时代的知音很少。不过,百余年前的桑梓之地出现的一位大史学家,却可以将他引为知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