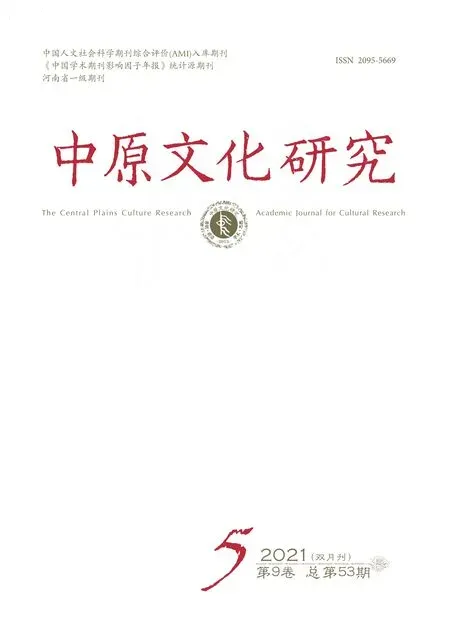浙东唐诗的空间想象*——以安放心灵为中心的考察
房瑞丽
19世纪,德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学者F.拉采尔认为,地理因素,特别是气候和空间位置,是人们的体质和心理差异、意识和文化不同的直接原因,并决定着各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和历史命运。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的历史学基本框架是:地理、气候条件影响人的生理,生理差异导致人的不同精神和气质,从而有不同的历史进程。虽然两者的说法因为走向极端而受到批评,但也都表明了地理空间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特定的地理空间会形成特定的文化心理则是必然的。就唐诗来说,如果说塞外风光为唐诗提供了豪迈的气势、巴蜀之地为唐诗提供了奇险之美、楚湘之地为唐诗提供了哀婉绝唱的萧瑟之风、金陵古道为唐诗提供了悠悠怀古之情、两京关中为唐诗提供了积极进取的壮志情怀的话,那么,浙东这片风光迤逦的佳山秀水之地,很显然为唐诗提供了清流婉转的风尚。
浙东地理景观或者说奇山秀水的自然条件是诗意空间建构的前提,其作为山水模范由来已久。如果只有这样的自然条件,没有东晋名士的活动,没有南朝文人的发现,那么这些自然山水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在这片自然山水经过东晋南朝文人的活动渲染和主观加工后,成为诗意的审美空间,上升为具有超自然地理的审美观照对象。《嘉泰会稽志》卷一《风俗》载:“自汉、晋,奇伟光明硕大之士固已继出。东晋都建康,一时名胜,自王、谢诸人在会稽者为多,以会稽诸山为东山,以渡涛江而东为入东,居会稽为在东,去而复归为还东,文物可谓盛矣。”[1]1626《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号。”[2]2098-2099这里是魏晋名士畅游遁迹之地。《世说新语》“言语”记载:“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3]145刘孝标作注引《会稽郡记》云:“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3]145这是让行走于其间的人难以忘怀的留恋之地。唐越州太守李逊在《游妙喜寺记》曰:“越州好山水,峰岭重叠,逦迤皆见。鉴湖平浅,微风有波。山转远转高,水转深转清。故谢安与许询、支道林、王羲之常为越中山水游侣。”[4]5537奇山秀水的地理环境和魏晋名士游旅畅怀的人文空间是浙东特有的空间地理感觉。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一书中说:“在青史之外的青山没有意义,只因无人在场,无人提问,自然也就没有被赋予任何精神附加值。”[5]29反言之,被人进行审美观照,被赋予人的情感的青山就是有意义的,特别是这里的“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唐人仰慕钦羡的有着共同心理记忆的群体。因而这里的青山就更加具有“精神价值”了。唐人用诗歌的语言表达对浙东的想象。当然,他们在诗中的描绘和想象绝不仅仅是因为兴趣,更重要的是寻求心灵的慰藉,给自己的心灵建构一个适意和诗意的空间。也就是说,历时的文化底蕴和共时的山水风物共同建构起唐代诗人对浙东空间的想象,或者说空间记忆,使得只要与此地发生联想或者置身其中的诗人,都满足了自己的心里的诉求或完成了心灵的建构。
张伟然先生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一书中提出“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即:“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来说,一个具有确定空间范围、能获得广泛认同的区域,其实也就是一个感觉文化区(或曰乡土文化区)。因为这些区域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其背后必然有着自然山川、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支撑。”[6]1-2那么浙东作为一个唐人安放心灵的诗意空间,这样的一个感觉文化区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具有儒家理想的诗人在追求事功的过程中受到挫折后,由于向外寻求政治理想的道路不通,而将目光转向内寻求心灵的安放之所。心灵的建构是一个内心深处的小空间,浙东是一个地理范围内的大空间,唐代诗人的浙东诗歌中是如何处置这外在客观的大空间与内在主观的小空间的呢?有着儒家理想的诗人,在面对不同的人生境况时,需要的心灵诉求是不同的,并且诗人的敏感和士人的体验,又使得他们对于心灵深处的空间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度有较高的要求。这时,给心灵找到可以“憺忘归”的安放空间就非常重要了。
一、“山水寻吴越”:失意慰藉之所
浙东山水的发现以谢灵运的山水诗为代表。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7]1165这就是“清晖”的氤氲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名士们“借山水以化其郁结”[8]907。再进一步说,虽然东晋南朝文人发现了浙东山水,并进行了文学创作,如果唐代诗人不关注他们的笔下描绘了什么样的山水,那些名士们活动的地方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能也不会在唐诗中形成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唐人的关注和重视,东晋名士的活动和南朝文人的创作在唐代诗人中广泛传播,对唐代诗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产生了名人效应。于是唐人在诗歌中仰慕曾经作为历史存在的那批名士的风范,对他们生活的山水以及那片山水所孕育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正如蒋寅先生所说,从谢灵运开始,浙东山水就成为了“逃避官场和世俗,寻求精神安宁的场”[9]235。
孟浩然《自洛之越》:“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10]323洛京是政治的中心,是权力的角逐场,而吴越不仅是距离和地理方位上是西北与东南的相对,更重要的是两个“感觉文化区”所具有的文化气场和氛围截然不同。吴越以“山水”为主,京洛则是“风尘”之场,风尘的背后是政治,而“山水”作为中国式诗歌的特有意象,除了象征着适意和自由以外,还有“山水意象一经成为自觉意识,就有着一种普遍的精神传染力”[5]80。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形成了一种气场,一种感觉文化区。浙东的山水成了诗人挥毫泼墨书写自己情志的自带底色的诗意空间。如果说“巴山楚水”让人想到凄凉地,而“稽山镜水”就是栖息地。同样有山有水,因为地理位置不同,因为曾经在各自的空间里上演的历史不同,而具有了不同的文化记忆底蕴。所以,想要逃离长安洛阳政治中心,想要从消磨人世的京洛风尘中解脱出来,最好的选择就是来到东南形胜的吴越之地。“山水寻吴越,风尘厌京洛”,这里可以“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有山水、有文化、有记忆,“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足以托此生。可见这个巨大的“感觉文化区”,可以荡涤三十年求取功名而不遇的失意,人生因此获得感悟和升华。借由对南朝的文化记忆而上升为对整个地区的想象,从而使这一地区符号化,代表着一种游离于社会政治体制之外的舒适自由的空间。
又如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乙子》:“问余涉风水,何处远行迈。登陆寻天台,顺流下吴会。兹山夙所尚,安得问灵怪。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10]64在一问一答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场域从天台到吴会,也就是整个浙东,都是自己所要追寻的山水之所,是自己所要游历的目的地。“兹山夙所尚”,可知对浙东山水的印象由来已久,有关浙东的记忆和想象早已内化为一种情感、一种情结。“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天之青色就是天的真正颜色,《庄子》载:“天子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11]4苍色就是青色,这里能够看到天的真正颜色,这里没有浮云蔽日,这里远离是非之场。俯仰天地间,浙东临海是地缘所在,而“沧海”所代表的是孔子“道不行,乘浮桴于海”的对自由的追求,是庄子的欲展翅九万里高空的大鹏所能够凭借的奋飞之所。所以,“青天”“沧海”本身就代表着自由,代表着对世俗的超脱,而孟浩然的越中之行就是寻找天地间可以超脱的自由之所,是可以托付终生的“永此从之游,何当济所界”。虽然最后孟浩然并没有在此托身,但至少在置身于中的时刻,他被周围的山水所形成的文化记忆的氛围笼罩着,同化了自己的身心。可见,浙东或者越中作为一个超脱之所的空间想象在诗人的意识中是非常强烈的。这里,与山水景观、名士风流、佛道仙源等所形成的空间记忆有关,也就是整个浙东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超脱之境的符号化意象而存在。
二、“越水洗尘机”:禅意栖息之居
顾云在《在会稽与京邑游好诗序》中云:“造化之功,东南之胜,独会稽知名。前代词人才子谢公之伦,多所吟赏。湖山清秀,超绝上国。群峰接连,万水都会。”[5]8586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云:“会稽山水,自古绝胜,东晋逸民,多遗身世于此。夏五月,上人自炉峰言旋,复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则向之境物,又其稊稗也。”[5]5027“群峰接连,万水都会”的越中能够引人“深入空寂,万虑洗然”,自支遁“遣使求买岇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12]58,谢灵运“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13]1754。这里就成为了文人向往的禅意栖息之地。
刘禹锡《送元简上人适越》:“孤云出岫本无依,胜境名山即是归。久向吴门游好寺,还思越水洗尘机。浙江涛惊狮子吼,稽岭峰疑灵鹫飞。更入天台石桥去,垂珠璀璨拂三衣。”[14]404“孤云出岫本无依”的“孤云”在文人笔下本就是漂浮无定、孤独无依的自我形象,一个“本”字界定了自己此刻的状态。而“胜境名山即是归”的“胜景名山”不仅仅是身体的暂宿之地,更是心灵的安放之所。“孤云无依”是佛家本性,而无依之“归”更见“胜境名山”的巨大吸引力。葛兆光先生在《禅宗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士大夫追求的是内心宁静、清静恬淡、超尘脱俗的生活,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诗意人生哲学使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清、幽、寒、静。……在暮色如烟、翠竹似墨的幽境中,士大夫面对着这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又在对宇宙、自然的静静的观照中,领略到人生的哲理,把其熔化到心灵深处。”[15]122越中的胜景名山是符号化了的空间勾勒。“久向吴门游好寺,还思越水洗尘机”,这里的“吴门好寺”实际上也是越中好寺,是互文的修辞手法,好寺的宁静之所;“尘机”则是世俗的尘念和心机,与佛教的“空无”与超脱是一对相反概念。“万水都会”的越地是佛教圣地,这样的空间场域都足以实现佛教所追求的“现世的内心自我超脱”[16]122。
“永嘉之乱后,剡县、始宁一带成为过江高僧的重要修行之地”[16]164-165,《续高僧传》卷十七《释智传》载“会稽之天台山也,圣贤之所托矣。昔僧光、道猷、法兰、昙密,晋、宋英达,无不栖焉”[17]282。因而智将石城山作为“处所既好,宜最后用心”的佛教中心地。这些远离人间热闹地的山林深处的那一座座佛寺庙宇,正是厌倦或饱受世俗不公的诗人为心灵找到的寄寓之所。鲍溶《送僧择栖游天台二首》:“师问寄禅何处所?浙东青翠沃洲山。”[18]5027齐己《默坐》:“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满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18]9592方干《游竹林寺》:“得路到深寺,幽虚曾识名。藓浓阴砌古,烟起暮香生。曙月落松翠,石泉流梵声。闻僧说真理,烦恼自然轻。”[18]7457德圆《云门寺》:“若耶溪边寺,幽胜绝尘器。”[19]695刘长卿《赠微上人》:“禅门来往翠微间,万里千峰在剡山。何时共到天台里,身与浮云处处闲。”[20]393孟浩然《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夕岚增气色,余照发光辉。讲席邀谈柄,泉堂施浴衣。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10]164这些都表明了这里是佛教圣地,是可以绝尘养心之所居。
浙东也有道家仙踪,天台赤城山在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中位列第六大洞天,葛玄曾在此修道。陶弘景《吴太极左仙公葛公之碑》提到:“公驰涉川岳,龙虎卫从,长山盖竹,尤多去来,天台兰风,是焉游憩。”[21]164由天台而赤城到石桥,则是进入神仙洞府之途径,可以“寻不死之福庭”[8]907。卢象《紫阳真人歌》中云:“镜湖之水含杳冥,会稽仙洞多精灵。”[22]35许浑《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18]6090-6091张籍《送施肩吾东归》:“世业偏临七里濑,仙游多在四明山。”[18]4339刘沧《赠道者》:“真趣淡然居物外,忘机多是隐天台。”[18]6793这些都是把这里当作仙游忘机求真诀之居。
三、“官适莫羡侯”:吏隐官适之场
如果说孟浩然诗歌所建构的浙东空间使得失意文人寻求慰藉、安放心灵,那么,李嘉祐《送越州辛法曹之任》“但能一官适,莫羡五侯尊。山色垂趋府,潮声自到门。缘塘剡溪路,映竹五湖村。王谢登临处,依依今尚存”[18]2152则把浙东想象成了在官场同样能够适意的理想空间。在人们的记忆中,为官要么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要么像李白那样“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否则只能像岑参“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只能“只缘五斗米,辜负一鱼竿”[18]2089。想要在官场上适意,哪怕只是想象,可能也只有存在于浙东了,如果辛法曹所任之地是京洛之政治中心,即使再是好友的祝愿,恐怕也不会起“官适”之意。在诗人李嘉祐看来,越州是能够“官适”之地。对于能够追求适意而又能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来说,能够“官适”之地当然是最佳的选择。对于理想中的儒家知识分子来说,能够“官适”的追求自由,其人生意义是大于“五侯尊”的。为什么越州能够成为“官适”之地呢?接下来诗中所描绘的适意空间结构,就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支持。“山色垂趋府,潮声自到门”,是诗人对友人所往之越州府郡地理环境的想象和认识。“山色”“潮声”不仅是动静的结合,更是不同于他处的所独有之景。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序》说:“山水,性之所适。”[8]2616远离社会,接近于自然属性,有利于社会中的人实现和追求与自然相似或相一致的人性。山水则是人可以造访居留之所,因而人更容易在那里见“道”,所以在提出“官适”之后的山水描绘,就蕴含着这里本身就是接近自然的“保留地”。而“垂”和“自”两个关键词的选取,也正是为“官适之所”服务的。“垂趋府”“自到门”,本身都是带有非人为的自然状态,非刻意为之,这种自然而然,就是能够官适的前提和空间氛围。如果说这里是大处着笔的话,接下来的“缘塘剡溪路,映竹五湖村”则是近距离的具体描绘,非亲身到过此地的人不能有如此细致的描绘,使得一开始的“官适”落到了实处。在展示了自然的空间之后,既然是为官之所,岂能没有文化内涵做支撑呢?“王谢登临处,依依今尚存”,这里是东晋名士王谢昔日优游之所,这里有六朝的文化底蕴,名士文化的遗韵依然尚存。山水与文化,大背景与小环境都构成了浙东“官适之所”的理想空间。也正如蒋寅先生所说:“大历诗人思想上的矛盾:他们有体恤百姓之心,愿尽忠职守为民谋福,但同时厌烦俗务,希求一种逍遥闲适的生活。”[9]94
韩翃的《送山阴姚丞携妓之任兼寄山阴苏少府》:“山阴政简甚从容,到罢唯求物外踪。落日花边剡溪水,晴烟竹里会稽峰。才子风流苏伯玉,同官晓暮应相逐。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仍怜甘蔗熟。知君炼思本清新,季子如今德有邻。他日如寻始宁墅,题诗早晚寄西人。”[18]2728大历年间的诗人,他们理想中的为官状态就是逍遥为官,在仕宦中实现“吏隐”,韩翃的这首送姚丞之诗,“山阴政简甚从容”就是当时文人对于浙东为官的普遍现象,这里政简,这里可以从容为官,这里可以携妓优游,可以说是理想的官宦之所。这与盛唐诗人对于浙东的情感是不一样的,盛唐诗人,他们来此疗伤,来自漫游,来此访禅寻仙都是暂时的,在心灵得到暂时的栖息之后,他们还是心向魏阙,洛阳长安才是他们实现理想的地方,才是他们追求官宦生涯的最高目标之所。但是到了大历年间,这样的理想被压缩,收回到了关注自己内心的体验,因而心中的那份理想也由西北转向了东南,远离长安而又生活环境相对安逸的浙东就成了理想的为官之所。这也是安史之乱以后,浙东在文人心目中地位的转变,由单纯的到此一游的完善或疗伤成为了适合避难和为官的场所。“到罢唯求物外踪”,“物外踪”是道家的那份逍遥与自我,“唯求”二字就消解了杜甫们的“再使风俗淳”的高尚的道德理想。“落日花边剡溪水,晴烟竹里会稽峰”的状物描绘对仗工整。“剡溪水”“会稽峰”不是实见,而是想象与印象,蒋寅云:“唯其如此,所以更具有选择性和特征性。”[9]102他们对于浙东的现象就体现在这一山一水之中,这是浙东山水的见证,是浙东历史人文的见证,也是浙东整个场域氛围的构建。“才子风流苏伯玉,同官晓暮应相逐”则表明这里不是孤独寂寞的,这里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此内外环境,再加上“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仍怜甘蔗熟”,大历年间政府财政极度窘迫,这里肥鱼美酒的物质生活图景的描绘,让许多“俸薄不自给”的清廉士大夫免遭“家人愁斗储”的窘况。这里还有精神的指引,仰慕已久的东晋名士谢灵运的“始宁墅”可供追寻,如此理想的官宦生涯和精神追求合一的境地,就是大历诗人对于浙东这片土地的描绘,这里有他们出于对京城长安的失望,而寻求内心寄托的希望所在。这里能够将他们留恋官场和归隐山林所导致的矛盾双重人格进行消解。这也是浙东提供给唐诗的空间场域,让在长安官场窘迫生存的士大夫们有了一片心中的安闲之所,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将诗情才思转化为内心的细腻描摹,提供了“素以为绚”的底色。这也可以说是浙东地域对于唐诗的贡献之一吧。
刘长卿的《送荀八过山阴旧任兼寄剡中诸官》写到:“剡溪多隐吏,君去道相思。”在这里,他们追逐官场的疲倦心灵暂时得到安歇,或者是暂时的放缓一下脚步,稍作修整,为下一次的征程做好准备。也就是积极昂扬的奋进和儒家的兼济天下的价值观是唐代文人心底的终极追求。但在追求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瓶颈,也会经受到现实的残酷打击,这时受伤的心灵就需要被抚慰,而浙地优异的自然风光提供的不同于关中地区的审美感受,有助于将他们从烦扰的争斗中解救出来,同时浙地所具有的独特的东晋南朝的名士风流底蕴又使得尚古的诗人们找到了心灵的知己。这里的佛道气场,又具有荡涤他们烦扰的心灵的作用,从而使得他们从心理上接受了自己暂时的解脱,能够坦然允许自己暂时的放纵自我灵魂和疏离社会政治,为心灵找到一片净土,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自我的拯救。但当他们调整好以后,又会重新整装待发,也就是政治上的追求永远是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的社会主流,“他们是在尽忠职守的前提下寻求安宁适意的生活,作为对颠沛转徙、羁旅辛勤的宦游生涯的调剂和补充”[9]99。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的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23]33闻一多先生谈到的唐代诗人的这种矛盾人格,也许可以作为唐代诗人浙东“吏隐”的另一种注解。
四、“此中多逸兴”:乘兴恣意之地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世说新语》中记载王子猷在山阴时,雪夜访戴逵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3]759王子猷的这种但凭兴之所至的任诞放浪、不拘形迹的行为,给世人的既有观念带来的极大冲击,特别是这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潇洒率真的个性,同时也反映了东晋土族知识分子任性放达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态度,展示了名士潇洒自适的真性情。这不仅成为当时世人所崇尚的的“魏晋风度”,也是唐代诗人所追慕的“魏晋风韵”。唐诗中的“访戴、忆戴、思戴、寻戴、觅戴、戴家、寻剡客、访剡溪、山阴道、子猷溪、子猷船、王氏船、徽之棹、剡溪船、剡溪棹、乘兴船、乘兴舟、雪舟、雪下船、子猷兴、山阴兴、剡溪兴、回舟兴、雪中兴,乘兴、剡溪雪、山阴雪、子猷归、子猷去”等,都是对这一典故的借鉴。在诗里,诗人们写朋友思念、见访,或写洒脱任诞、随兴会所至,或写山阴风光、睹景思人,这种子猷访戴相类的情趣及雪夜景色成为了唐诗中特有的意象,而尽兴优游此地也成了诗人们的游历心态。
李白《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24]1604一个“寻”字,意趣尽在其中。“此中多逸兴”,正是在此地敞开心灵,与自然与自我热情拥抱。醉在逸兴中,将山水与文化融合在了一起。“早晚向天台”,不仅仅是空间的地理距离,而是心里的方向,心向往之。舒展自我内心的追求一以贯之,不会改变。
罗隐的《寄崔庆孙》:“还拟山阴已乘兴,雪寒难得渡江船。”[18]7597诗人也想向王子猷一样,潇洒乘兴随访老友,但一句“雪寒难得渡江船”,多少道出了现实的无奈。还有《送裴饶归会稽》:“笑杀山阴雪中客,等闲乘兴又须回。”“两火一刀罹乱后,会须乘兴雪中行。”[18]7596武元衡《中春亭雪夜寄西邻韩李二舍人》:“却笑山阴乘兴夜,何如今日戴家邻。”[18]3574姚合《咏雪》:“其那知音不相见,剡溪乘兴为君来。”[18]5669这些都是围绕山阴美景与雪夜访戴相结合,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与思念,因为王子猷、因为戴逵,这里成了乘兴恣游之地。
五、“此处是家林”:避难安居之寓
安史之乱爆发,士人多避难南迁,浙东也成为了诗人们理想的避难之地。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是时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25]4720《旧唐书·权德舆传》:“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26]4002皇甫冉《送陆鸿渐赴越诗序》:“夫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进可以自荐求试,退可以闲居保和。”[18]2820独孤及:“属中原兵乱,避地于越。”[25]4704皎然在《诗式》中,概括了这样一个避难浙东的诗人群体:“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27]273-274“吴中诗派”和以鲍防为首的浙东联唱集团都是这一群体诗人的代表。他们“一方面改变了初盛唐大致以京都为中心的文学格局,一方面也使文学创作集体活动具有了鲜明的地方区域文化的特点”[28]112。关于这一问题,胡可先在《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一书第二章《安史之乱与唐代文学转型》中有较为详细的考述[29]。
方干《镜中别业二首》其一:“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梁燕窥春醉,岩猿学夜吟。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沈。犹自闻钟角,栖身可在深。”[18]7443“寒山压镜心”之“寒”是对人事的体验,“镜心”表明自己内心的平静,原因在于自己所处之地是“家林”,家园总是给人温馨之感。中间四句细致描摹家林周身的环境,动静结合,更显幽境。“栖身可在深”呼应首联的“家林”,都表明自己托身镜中,以此为家的志向。这不仅仅是寄身的容纳之所,也是安心的归属之地。其二:“世人如不容,吾自纵天慵。落叶凭风扫,香粳倩水舂。花期连郭雾,雪夜隔湖钟。身外无能事,头宜白此峰。”也是首尾呼应,开头直接表明自己不容世人,索性“纵天慵”。“头宜白此峰”,一个“宜”字是仕途无门,退而求其次的上佳选择。中间四句亦是对于周遭环境的细致刻画,格局不大,但足以安放内心。《鉴戒录》云:“方干处士号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与科名,遂隐居鉴湖,作《闲居》诗。”[30]123说的就是以上二首。以此为家,成为了安史之乱后避难和不得志文人的选择。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三《陆羽传》:“至德元载,乱军入据关中,关中士大夫纷纷渡江南,陆羽亦随之避乱,殿转至越中,于上元元年隐居于吴兴苕溪之旁。故《自传》又云:‘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读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31]625《唐才子传》卷五《朱放传》:“初,居临汉水,遭岁歉,南来卜隐剡溪、镜湖间,排青紫之念,结庐云卧,钓水樵山。……时江浙名士如林,风流儒雅,俱从高义。如皇甫兄弟,皎、彻上人,皆山人良友也。”[31]343-344《唐才子传》称:秦系“天宝末避乱剡溪,自称东海钓客”[31]592。贾晋华说这批诗人“从盛世回忆中得出的不是中兴帝国的责任感,而是无可奈何的感伤哀婉,结果只能是充耳不闻北方中原的喧喧鼓鼙,把注意力转向眼前的相对平静的江南美景,以此麻醉自己”[32]104。
结语
综上,本文从五个方面,或者五个角度分析了浙东在唐诗中作为一个记忆的空间,是如何建构安放诗人们心灵的舒意空间的。其中,在此空间中寻求“失意慰藉”和“乘兴恣意”是从“游”的角度来说的,其他三方面是从“居”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游”是“居”,或者说是行是止,以上五方面关于浙东空间的建构,满足了不同的身份或者抱着不同目的来到浙东之地的诗人的心灵需求。但行游和寓居于此地的不同目的所呈现出来的诗歌的空间维度是不一样的。游历其中的诗人的精神是外向的,是带着欣喜的眼光与发现或者发掘这里的山水的,所以所呈现的心灵维度是发散型的。而寓居其中的群体则多是安史之乱后受到打击或者被动避乱的选择,所以诗人观察空间的心灵维度是内敛型的。他们精神的指引方向是向内收缩的,是呈现自我保护状态的。所以选择的观照对象往往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反映出来的就是狭小空间就是诗人宇宙观的缩小。因为他们是时代之殇,所以他们从内心里把自己收缩和限定在一个最小的空间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到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自己才是安全的。而游历于此的诗人,由于从未考虑过安全的问题,所以他们是来放松自我,或者寻求自然环境对自己心灵支持的,所以他们是积极向外探索的,架构起来的空间结构是宏大的。疗伤和避难的心理诉求是不同的,疗伤游历山水慰藉心灵后,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追求那现世的理想。而避难则是拖着疲惫的心灵,试图寻求能够容身的稳定寓所。所以一个是向外的,另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是探索扩张型的,另一个是内敛保护型的。两种不同的心态,面对同样的环境所建构起来的空间必然也是不同的。
——以《全唐诗》为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