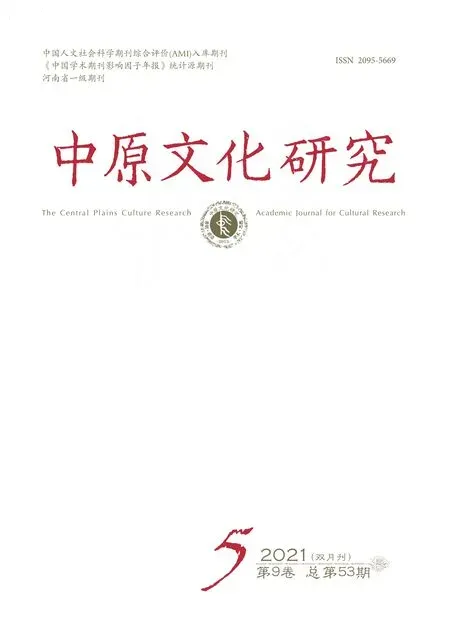《邵氏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
宋春光
《邵氏闻见录》(以下简称为《闻见录》)多处涉及“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时同异之论”的相关叙事(以下简称为“王安石叙事”)[1]1861。这些叙事展现了邵伯温在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生态中对王安石及其相关事件的记忆。邵伯温自序称:“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并说:“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2]1据此,则《闻见录》中包括王安石及其相关事件在内的叙事,在一定意义上隐含着以邵雍、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为代表的对熙宁变法主要持反对态度的“前辈”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章学诚曾言:“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3]219在《闻见录》的“王安石叙事”中,其“义”可泛指包括价值判断、精神追求与道德训诫等在内的语义指向;其“事”可指代事件情节;其“文”可泛指包含结构、逻辑和词汇等在内的话语模式。其理想模式恐应是因“事”而运“文”,据“事”以表“义”。但《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往往视“义”为目的,以“事”与“文”皆为手段,不仅为“义”而择“事”,甚至为“义”而改“事”、为“义”而造“事”,并运用其“文”使其“义”蕴于其“事”中。这种以“义”为目的的“王安石叙事”并非邵伯温的独创,其固然受到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前辈”“前言往行”与邵伯温自身“后死者之责”的共同作用。
一、《闻见录》中“王安石叙事”的“义”与“事”
《闻见录》中的王安石趋于“心若公孙弘,学若商君,愎若阳处父,(不臣若王处仲),怙子若石季龙”的形象[4]218。这与“王安石叙事”中以旧党之“义”为指归,进而为“义”而择“事”、改“事”、造“事”的书写方式密切相关。
《闻见录》中“王安石叙事”之“义”往往源于旧党的表述。如卷九记有邵雍对王安石与吕惠卿关系的判断,同时述及这一判断在此后王、吕关系的走向中得以证实:“康节曰:‘公无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利合。惠卿、安石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至。”[2]199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载:“(司马光)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5]478据邵伯温与苏轼所撰文本内部时间推测,司马光之言当早于邵雍之言①,但两者对王、吕关系的判断却如出一辙。无论是邵雍与司马光“英雄所见略同”,亦或是邵伯温以司马光之言附会于其父,邵伯温此处所载之“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旧党。又如,卷十三记有王安石擢用章惇之事。《闻见录》先述及章惇被擢用前的几件事:私通族父之妾,逾墙逃跑以致误践老妇,被老妇所讼;科考不如意便讥诮考官;人欲观其文,章惇掷文于地,极为不恭。以此证明章惇确实“无行”。此后《闻见录》述及王安石当政后,章惇被张郇、李承之举荐,王安石以“闻惇大无行”表示顾虑,李承之则言“惇才可用于今日,素行何累焉”,因章惇“素辩,又善迎合”,王安石“大喜,恨得之晚”,即擢用至两制、三司使[2]143。这段叙事其“义”在表明章惇、王安石、李承之等皆是“小人”:数“事”已经可证章惇“无行”,且其“无行”也是被王安石等人所知的,在“道德判断”先行的逻辑中,章惇已经是“小人”;李承之因章惇之“才”而不顾其“无行”,行文中所见章惇之“才”仅“素辩,又善迎合”,王安石因之相见恨晚、擢至高位。引荐、拔擢“无行”之人窃取高位,则引荐、拔擢之人固为喜人阿谀、助纣为虐的“小人”。在这段叙事后邵伯温已自陈其源:“右司马温公记惇如此。”司马光所撰《涑水记闻》中亦见上述叙事,且邵伯温所记之“义”确同于司马光[6]415。无独有偶,卷十三亦记王安石擢用曾布之事:王安石因吕惠卿丁忧而无人可与谋事,“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日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2]144。此处叙事和前述王安石擢用章惇之事相较,其行文逻辑、对王安石及其擢用之人的定位几乎如出一辙。而王安石擢用曾布之事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且李焘注称:“此段据《司马光日记》。”[7]5236则此段叙事之“义”亦源于司马光。
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2]36
这段叙事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在宋人记述中是存在争议的:其一,文彦博和曾公亮是否“皆主不与之论”?其二,王安石是否主张割地并有上述言行?李焘注称“韩宗武记其父韩缜遗事”载韩缜馆伴辽使萧禧,并劝神宗不要接见萧禧:“朝廷自来与北人议事,皆委自臣下,事有差误,易以改易,兼恐禧不肯便已,烦渎圣听,至时难以止约。”而神宗却接见了萧禧,且“至驿,神宗又令御药李舜举御前以朱笔画一图子以示禧,依次分发”,韩缜认为此事不妥便急见神宗、面陈利害,神宗虽言“卿言大是”,却最终因“地界事久不决”而令刘惟简拟御笔责备韩缜,其中提及:“疆界事,朕访问文彦博、曾公亮,皆以为南北通好百年,两地生灵得以休息,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副。”[7]6379这段叙事中,是神宗主导了“以朱笔画一图子以示禧,依次分发”,不同于邵伯温所记王安石主导“以笔画其地图”;且文彦博、曾公亮所言既以“南北通好百年,两地生灵得以休息”为割地找到“正当”理由,又以“当且随宜应副”为自身避免了明确谏言割地带来的政治风险,这亦不同于邵伯温所记文、曾二人“皆主不与之论”。另外,据《长编》载,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曾言于神宗:“萧禧不当满所欲,满所欲则归而受赏,是开契丹之臣以谋中国求赏,非中国之利也。”[7]6372此处“所欲”即割地一事,则王安石是不主张割地与辽国的。且熙宁六年(1073年),契丹生事争地,神宗深以为忧,王安石对神宗言:“契丹无足为忧。”并称:“事缓即缓措置,事急即急措置。”[7]6046此亦是不主割地之意。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主割地之说见于苏辙所撰《龙川略志》。苏辙称:
予从张安道判南都。闻契丹遣汎使求河东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谓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及北使至,上亲临轩,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挥边吏分画。”使者出,告人曰:“上许我矣。”有司欲与之辨,卒莫能得。[8]20-21
邵伯温所记王安石“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之言正合此处“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之“义”。窥苏辙整段叙事之“义”,恐是欲彰显神宗被王安石所误,有司难以作为,终致割地,故而王安石是割地的罪魁祸首。但自“及北使至”之后,述及神宗答应割地“即指挥边吏分画”、辽使以神宗已允诺为由致使有司无法与之再争论割地之事。这正暗合前引韩宗武所记神宗主导“以朱笔画一图子以示禧,依次分发”,以及韩缜劝谏神宗不要见辽使的原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王安石并无“以笔画其地图”之事。综上可见,邵伯温所记熙宁年间割地与辽国之事恐有讹误,其“事”与“义”皆是源于旧党的,而王安石自身的言行则是“被代言”的,新党在此段叙事中失语。
此外,《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往往以旧党之“义”为指归,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其“事”与评论是否有悖情理。如《闻见录》记王安石早年读书达旦却被韩琦误以为夜饮放逸,王安石耿耿于此,故而“召试馆职不就”“《熙宁日录》中短魏公(韩琦)为多”“作《画虎图》诗诋之”,甚至为韩琦薨逝所作挽诗“犹不忘魏公少年之语也”[2]94-95。邵伯温认为王安石挽诗为怨愤之意,清代学者蔡上翔已辨其非[9]501。且《长编》载韩琦薨逝后,王珪认为宜依吕夷简例赠官,而王安石称韩琦定策之功非吕夷简可比,应特赠。据此,邵伯温以王安石为韩琦所作挽诗为怨愤之意,恐不合情理,但却合以王安石为小人之“义”。又如,《闻见录》提及王安石推行变法称其“急于功利”,评论司马光限五日内废止免疫法则称:“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故利害未尽。”[2]118-119邵伯温认为司马光之所以废止新法的过程中存在限期过短等不妥之处,是因为司马光重病在身,怕不能在有生之年废除恶法,即邵伯温以司马光动机之“是”力辩其行为之“非”。王安石与司马光同是“急”,邵伯温对两人的判断却迥异。无独有偶,邵伯温记王安石对吕公著前后评价不一致,并于其后评论称:
方其荐申公(吕公著)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2]125-126
邵伯温意即王安石以个人喜怒评价他人,以致对吕公著的评价前后有天壤之别。而《长编》载吕公著等人对王安石的评价亦前后不一:
布(曾布)曰:“谁以王荆公为真人、至人、圣人?”惇(章惇)曰:“吕公著等皆尝有此语,后又非之。”[7]11532
用Matlab对壮苗指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曲面如图2,得到的拟合方程为:Y1=-0.0046x12+0.1692x1-0.1387x2+0.0043x1x2; 其中Y1为壮苗指数,x1为昼温,x2为夜温,在取样点附近温度范围内,根据回归方程,昼温在30 ℃时,与夜温有关的后2项加起来是一个较小的负数,因此,夜温与壮苗指数呈负相关,且相关性小。反之,若夜温恒定,昼温与壮苗指数相关性较大,且随着夜温的降低,其相关性增大,并且昼温与夜温有一定的耦合性。由此图可以看出,在一定范围内,昼温越高,夜温越低,幼苗壮苗指数越大,超过一定范围,则幼苗指数减小,根据曲面梯度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
此外,司马光言:“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10]550钱景谌亦言王安石曾“称重于公卿间”[2]132。后来吕公著、司马光、钱景谌诸人却皆以王安石为非,亦是前后毁誉不一。虽均是对人评价前后不同,邵伯温以王安石为“非”、以吕公著诸人为“是”。再如,《闻见录》卷十一载王雱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无礼于程颢,并扬言“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等事[2]121,前人已辨其非,兹不赘述。唐坰于熙宁初曾上书称:“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11]10552邵伯温所记王雱之言与此如出一辙,内中关联颇值得玩味。而卷十三又记唐坰弹劾王安石称:“吕惠卿、曾布,安石之心腹;王珪、元绛,安石之仆隶。”[2]144据此,唐坰对王安石的前后褒贬不一亦可想见,而邵伯温并未录唐坰此前支持新法之言,却记后来弹劾王安石之语,并以该弹劾力证王安石之奸。这类不甚合情理的述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邵伯温对旧党之“义”的生发。
二、《闻见录》中“王安石叙事”的“义”与“文”
王夫之曾指斥王安石:“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查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受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12]117这里所提及的王安石之“非”几乎在《闻见录》中都可以找到对应,而这种近乎扁形人物形象的呈现与“王安石叙事”的“义”“事”“文”均密不可分。《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不仅“义”“事”与旧党所述存在史源层面的关联,其“文”亦源于旧党的话语传统(即旧党之“文”):就总体而言,《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具有基于“后死者之责”的泛道德化倾向,即囿于“后死者之责”而以旧党为“是”,以新党为“非”,并以此“是”“非”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抛却对具体情境中人、事的辨析,而以“道德判断”先行,不惜“调整”“臆断”乃至“创造”“事”,使其符合此前预设的“道德判断”。具体到行文中,旧党之“文”表现为:以二元对立的视角,依据对新法的依违将士人分为“小人”与“君子”,并弱化君主的现实主导性,使君主成为“道德”的仲裁者,进而借君主的“道德权力”佐证“君子”之“是”,而将君主之“非”归咎于“小人”。如《闻见录》中除多次直接以“君子”“小人”作为指代外,还曾以“贤者”“不肖者”对举,又或称不与变法合作者为“正人”等,诸如此类都是旧党话语传统(即旧党之“文”)的显性体现。
旧党之“文”在《闻见录》“王安石叙事”中还以多种形式存在。如,直接引述旧党之言,其中自然包含旧党之“文”。卷十五载程颢对熙宁变法的反思:
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以去,范尧夫辞同修《起居注》得罪,张天琪自监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谪。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五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2]164-165
四库馆臣称程颢之言为“平心之论”[1]1861。但就程颢之语的内部而言,直接将王安石“斥去”之人称为君子、“用之”之人称为小人,且以范道德性语汇对其进行无差别概括,如称被斥去者“正直不合”、被用之人“苟容谄佞”等,这本身就是以反变法者为“是”,以参与变法者为“非”。程颢以此为前提对“君子”行为的反思是“居高临下”的,恐难称“平心之论”。就程颢之语的外部而言,邵伯温载录程颢的反思,并称“天下以先生为知言”,这不仅是对程颢君子身份及其话语内部“义”“事”“文”的认同,更表达了君子如程颢不计个人荣辱,公忠体国;狠愎如王安石致使小人甚嚣尘上并最终祸及天下的语义指向。而上述程颢之语的内、外部之“义”正是借由旧党之“文”实现的。
旧党之“文”在《闻见录》“王安石叙事”中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即以旧党之“文”化用旧党之“义”,而屏蔽新党之“文”与“义”。卷十二记载:
(王安石)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宋次道当制辞,荆公使之明著其语,陈相阳叔以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实,援据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申公素谨密,实无此言。或云孙觉莘老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须,误以为申公也。[2]126
经由对勘可知《闻见录》与王安石所录《时政记》对此事的记载差异颇大,其差异主要在于:其一,吕公著是否确有“(韩琦)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的相关言论(以下简称“清君侧”言论)?《时政记》记载确有其事,而《闻见录》认为“清君侧”言论出于孙觉,但神宗误记为吕公著。其二,贬谪吕公著的主导者为何人?《时政记》记载主导者为神宗——“上察其为奸,故黜”,而《闻见录》认为主导者为王安石——“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与此同理,《时政记》记载制辞中明言吕公著罪状并因此与陈升之等人论难之人为神宗,且“上终弗许,而面令升之改定制辞行之”[7]5097,即吕公著制辞最终是依神宗之意改定的,而《闻见录》却将上述行为皆归于王安石。《闻见录》的这段叙事中,显然带有“道德判断”先行的倾向。邵伯温以吕公著为“素谨密”之君子,故而作为君子的吕公著不会有“清君侧”言论;以王安石为欲“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的小人,故而作为小人的王安石是罗织冤狱陷害君子的主导;神宗的主导性被极度弱化,且其“非”亦被归咎于王安石。而《闻见录》此处之“义”与“文”实化用自旧党。一方面,吕公著本人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提及发生在神宗熙宁年间的这件事,称自己“不曾语及韩琦一字”,“被诬遭逐,全不出于圣意,止是王安石怒臣异论,吕惠卿兴造事端”[7]5097-5098,即否认自己有“清君侧”言论,撇清神宗与自己被贬的关系,将自己“被诬”归咎于王、吕二人。另一方面,《闻见录》此处所述与《长编》所载“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以下所述如出一辙,且《闻见录》所谓“申公素谨密,实无此言。或云孙觉莘老尝为上言‘……’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须,误以为申公也”与《长编》记司马光所言“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并无二致[7]5098。不仅如此,邵伯温叙事中对神宗之“非”的规避也承自旧党之“文”。如,贬谪吕惠卿的制词最初由范百禄草制,其中有云:“朕承先帝(神宗)大烈,惧弗克胜,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张,民劳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为厉阶。”吕公著认为此处表述不妥,称:“恐彰先帝之失,宜删去之。”后来由苏轼草制,其中提及:“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鯀;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吕惠卿)始与知己共其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7]9240-9241可见,邵伯温所述乃以旧党之“文”化用旧党之“义”。
《闻见录》“王安石叙事”中还存在综合引述旧党奏章、化用旧党之“义”、以既成事实“裹挟”人物意愿以论证旧党之“是”的情况,且因旧党之“文”的运用,使各部分合成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如卷十一引述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知永兴军后向神宗所上之章。司马光于奏疏中以退为进,称自己“先见”“直”“敢言”“勇决”不及吕诲、范纯仁、程颢、苏轼、孔文仲、范镇诸人,实是认同诸人的判断,认为王安石“汲引亲党,盘踞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已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且“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2]113-114。一方面,司马光奏疏本身就是运用旧党之“文”的典型,其逻辑、语汇等具有较强的排他性,除“忠”“佞”“是”“非”这类带有明显褒贬色彩的语汇外,其叙述多包含是己非人的意味,如“挤排异己”是对异己者的贬义表述,其褒义表述或可为“不附流俗”[7]5429。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奏疏是嵌套在邵伯温的叙述之中的,除司马光的奏疏外,邵伯温于同条中述及司马光外放是因其“与王安石议论不同力辞”,并辅以程颢所言“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由此表明司马光作为君子对政见的坚守。邵伯温不仅以上述两方面互为表里,更一再强调神宗对司马光道德与才干的称许,如:“帝叹曰:‘汲黯在庭,淮南寝谋。’”“帝曰:‘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2]115这正是以神宗作为“道德”的仲裁者,从而使司马光的“君子”定位更加毋庸置疑。在本条叙事的最后,邵伯温以旧党之“文”述、评结合,尽显旧党之“义”:
当熙宁初荆公建新法之议,帝惑之。至元丰初,圣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司马光)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盖将倚以为相也。呜呼!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后世所以有朋党之祸也。[2]115
这里以神宗熙宁初对新法“惑之”与元丰后“退荆公不用者七年”表达对王安石与新党的否定;以神宗对司马光的倚重——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为相表达对司马光与旧党的肯定。而事实上,文献中不乏异于邵伯温之“义”的记载。如,任用王安石施行变法乃神宗主导,而非邵伯温所谓“帝惑之”②;邵伯温所谓“圣心感悟”的元丰年间,王安石受神宗眷顾日隆,由舒国公拜特进改封荆国公[13]1087,诸如此类。但因神宗驾崩后,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即拜相并迅速废止新法——这一既成事实使得前引邵伯温所述看似甚合情理,而这种称弃用王安石、废止新法出自神宗之意的做法,亦承自旧党,如苏轼便曾称:“先帝明圣,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然先帝终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复召。”[5]489且章惇称:“云神宗晚年疏斥王荆公不用,此乃是苏轼之语。”[7]11532可见这种说法恐始自苏轼。综上,在这条叙事中,邵伯温以既成事实裹挟神宗对变法的态度,进而以旧党之“文”尽显旧党之“义”:君子如司马光因不能无视王安石“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2]114,因而忠言直谏。当忠言不被采纳,君子仍然坚守正义的立场,爵禄亦无法改变其出处去就。且君子的上述行止是以苍生社稷为念而与王安石并无私怨。两者的对立,是“君子”“老成谋国”与王安石“专逞狂愚”的对立。而神宗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不幸被王安石所误,终虽悔悟却未及更张。在以司马光为“是”、以王安石为“非”、以神宗为道德仲裁的叙事中,包含着对小人之“非”终致国难的悲愤,亦以此反证旧党之“是”。
三、邵伯温的“后死者之责”
邵伯温作为邵雍之子,得以亲侍“前辈”,不仅“入闻父教,出则侍司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11]12851,且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去世后,邵伯温亲自教授其子司马植。另外,邵伯温自述:“以经明行修命官,见公(吕公著)于东府。公语及康节,咨叹久之,谓伯温曰:‘科名特入仕之门,高下勿以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起谢焉。公三子,希哲、希积、希纯,皆师事康节,故伯温与之游甚厚。”[2]126即邵、吕两家亦为通家之好。且邵伯温自称是富弼唯一亲传弟子[2]200。同时,据《宋元学案》记载,邵伯温曾师事二程,邵雍墓志又为程颢所撰。从家学师承的角度而言,邵伯温不仅在亲侍邵雍、司马光、吕公著、富弼、二程等人的过程中接受诸人的政治立场、学术观念和文化理想,更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我身份认同。所谓“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11]12853,即为邵伯温身份认同的明证。邵伯温遍历熙宁变法、元祐更化、靖康之变、高宗嗣统后,在暮年追述王安石及其相关事件,是在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将自己作为旧党群体的“后死者”以尽自身之“责”——为包括父辈与自己在内的旧党群体“正名”。
在北宋尊韩思潮的背景下,士人继承了韩愈的道统谱系话语③,并将韩愈道统谱系话语中本就包含的社会政治批判的内涵进一步强化。从而,士人希求以自身学统为道统之所在,进而以道统为凭借,在理论上实现与政统的制衡。北宋后期以王安石变法为导火索而引发的党争,便隐含着政统、道统、学统之间的相互博弈。王安石变法之前,虽已然“学统四起”[14]2,但政统未与任何一派学统进行政治层面的合作,即未以政统的世俗权力承认任何一派学统在道统中的合法地位。而王安石变法的特殊之处或许就在于,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利用道统谱系话语实现了政统与道统的合作。王安石变法之时,诸多学派亦有变法的倾向,即以自身学统与政统合作并获得政统所确认的道统合法继承者地位的倾向。《程氏经说》所谓“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即为明证[15]1035。傅尧俞以“主上(神宗)眷意异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劝司马光不要力辞枢密副使之职亦属此意[16]217。只不过,唯有荆公新学达成了与政统的合作而已。而这种合作一旦达成,道统谱系话语的排他性则导致:一方面,荆公新学以道统之尊、政统之助形成对异己的打压,以且仅以自身的学术与政见推动变法;另一方面,未能与政统达成合作的诸学派极力否认荆公新学道统地位的合法性,并以道统自任,以近乎“清君侧”的态势对王安石学术、政见及新党进行口诛笔伐。
又由于以道统制衡政统往往只是理论上、理想中的,现实中的道统地位往往是政统赋予的。因此,即便是与政统达成合作的道统,虽然其主观上强调“道”在“势”上,但客观上却不得不依附于政统,这种悖论造成以道统自任的士人某程度上的进退维谷,而那些未被政统确认为道统的学统与士人便更是如此。旧党便是“熙、丰”与“绍述”时期未与政统达成合作,以道统自任,否认荆公新学的道统地位、反对新法、反对变法者的一个群体性存在。邵伯温以其家学师承进而形成与旧党同质的身份认同。前述以二元对立视角、依据对新法的依违将士人分为“小人”与“君子”,弱化君主的现实主导性,使君主成为“道德”的仲裁者,借君主的“道德权力”佐证“君子”之“是”,而将君主之“非”归咎于“小人”——此旧党之“文”正是旧党利用道统谱系话语的排他性是己非人的结果。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当政府与国家权力逐渐占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皇权已经逐渐巩固甚至强大时,‘尊王攘夷’的紧张,就逐渐从士大夫全体的关注焦点变成了政府官员的政治行为。当它只是没有权力的士大夫思考的遥远背景而不是行为的直接动因时,士人只能把焦点从‘国家权威’转向‘思想秩序’,只能通过‘道统’来制约‘政统’,借助历史与文化来批评权力,运用思想的力量来赢得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认同,在皇权强大的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17]
邵伯温不仅因舞勺之年亲侍“前辈”,从而以旧党“后死者”身份自居,并在史源意义上承袭旧党之“义”“事”“文”,更因他经历了“前辈”所未曾经历的靖康之难,故而《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力证王安石是导致靖康之祸的始作俑者。邵伯温借靖康之难反证旧党之“是”、王安石之“非”,其逻辑理路近似于旧党“前辈”以元祐更化反证神宗对旧党的肯定、对王安石的否定——均是借既成事实“裹挟”叙事以加持旧党之“义”。如《闻见录》记王安石以“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劝神宗割地与辽国后,邵伯温评论道:
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具载以为世戒。[2]36
前文已述王安石主张不割地,而神宗恐为主张割地之人。但此处,邵伯温以二元对立的模式建构了韩琦、富弼与王安石在割地问题上的矛盾,以神宗为被王安石蒙蔽者,并以“天下大乱”的既成事实证明王安石之“非”与韩、富之“是”。其论述的语义指向和话语模式与旧党之“义”、旧党之“文”一脉相承,而“天下大乱”即靖康之难的客观存在,又使其论证的内部逻辑得到更有利的支撑。不仅如此,邵伯温还以“祖宗之法”和邵雍谶语来论证王安石为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闻见录》卷一载:“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2]4该书卷十九载邵雍于天津桥闻杜鹃声,随即称:“不三五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邵伯温称:“至熙宁初,其言乃验,异哉!”[2]214在此逻辑中,以“南士”王安石为相,既有悖“祖宗之法”,又正应邵雍的谶语。有学者认为“无用南士作相”并非“祖宗之法”,而是被“制造”的政治流言,且这一政治流言的产生并非源于南北矛盾,而是要将靖康之难的责任推给以南士身份为相的新党[18],笔者认同这一观点。邵伯温所言即将亡国的矛头指向王安石。
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具载以为世戒”一类的表述在《闻见录》“王安石叙事”中频见,如“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祸至于此。因具载之以为世戒”,“伯温自念暮景可伤,不可使后生无闻也,因具载之”[2]22,43,162等。可见,邵伯温具有极强的“史”的意识。正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对于亲侍旧党“前辈”又亲历靖康之难的邵伯温而言,反思亡国的教训、追溯亡国的罪魁祸首并“具载之”,不仅是为清算恶首,更是为自己曾亲侍的“前辈”“正名”,又因邵伯温自视为旧党“前辈”的“后死者”,故而,这同时意味着为自身“正名”——这正是有意无意地撇清旧党“前辈”、邵伯温自己与靖康之难的关系。而这又与欲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南宋新政权不谋而合。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北狩”,皇族尽皆随行,唯哲宗废后孟氏与康王赵构幸免于难。张邦昌复孟氏“元祐皇后”尊号,迎其入禁中垂帘。元祐皇后随即迎时为康王的赵构即皇帝位,并昭告天下:“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且以“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誉赵构[19]107。这一嗣统方式使赵构必先保证元祐皇后的合法性,才能保证其自身帝统的合法性。史载元祐皇后于元祐七年(1092年)入主中宫,于绍圣三年(1096年)被废,元符末复位,崇宁初再度被废。孟氏的废立几乎成为新、旧两党政坛荣枯的晴雨表,从这个意义上说,肯定旧党是赵构证明孟氏元祐皇后地位的合法性,进而证明自身帝统合法性的必要选择。“作为一桩道德义务,人们需要尽可能地发掘和保全(尤其是对于苦难和不公的)历史记忆;而对于社会政治的现实进程而言,需要的只是适度的历史记忆。也许,历史正义要求的,是记忆得以发掘,真相得以揭示;对于转型期社会而论,不同族群甚或不同阶层的和解,是在特定时期更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历史过程当事人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的追究,往往会危及这样的目标。”[20]因而,身处代际之间的赵构所需要的只是利于证明其帝统合法性的旧党的历史记忆,而不会从历史正义出发,将新党与旧党的历史记忆互参以辨析何者应为靖康之难负责。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以帝统合法性为核心的南宋初期政治路线为邵伯温的叙事提供了政治保障,但邵伯温自认的“后死者之责”恐是使《闻见录》“王安石叙事”以前文所述面貌呈现的更为重要的内在动因。吕中称:“当靖康元年二月,敌退之后,士大夫争法新旧,辨党邪正。”[19]117这可视为靖康之难后旧党对新党的一次反扑,其时,师承程颢的杨时曾上疏称: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廷。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11]12741
这份将靖康之难源头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党的上疏,在当时引发议论纷然,并导致杨时罢职。而杨时这次“不合时宜”的上疏,恐与其师承伊洛的学统身份认同有关。就不因政治环境改变其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杨时上疏的内在动因与刘安世所言“吾欲为元祐全人,见司马光于地下”并无二致[11]10955。邵伯温在《闻见录》“王安石叙事”中对旧党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的彰显,其内在原初动因亦与刘安世、杨时同理。不同的是,刘、杨并未遭逢政统与其“同仇敌忾”的政治环境。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南宋初期的政治、文化生态恐非“促生”《闻见录》中“王安石叙事”的决定性因素,而邵伯温接续旧党“前辈”以道统自任并为之“正名”的“后死者之责”,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
结语
对于《闻见录》应属子部抑或史部的问题,诸家莫衷一是④。学者也注意到《闻见录》中一些叙事在史料层面的讹误。从邵伯温存“前辈”“前言往行”的意识而言,《闻见录》具有“史”的倾向。而《闻见录》中之“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为“义”而择“事”、借“文”以达“义”的情况,从这个角度上说,其具有“子”的属性。《闻见录》中之“义”是在“前辈”“前言往行”与“后死者之责”中生成的,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邵伯温对王安石及其相关事件的记忆与书写。此后,随着《闻见录》成为后世官方文献与私人著述的重要史源,其中的“王安石叙事”亦对后人认知王安石及其相关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邵伯温记载,某日邵雍见富弼因“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凶暴过安石”而面有忧色,故而有上述对王、吕二人关系的判断,则邵雍之判断不早于“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即不早于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记载司马光对王、吕二人关系的判断发生在“惠卿叛安石”之前六年,即不晚于熙宁三年(1070年)。②如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参知政事,神宗对王安石言:“朕初亦欲从容除拜,觉近日人情于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故急欲卿就职。”可见是神宗力主以王安石为宰执。参见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15 页。又如,熙宁初,神宗对王安石理财之“议”甚为认同,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并创制置三司条例司总理变法之事。参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神宗并非“惑之”。③刘成国先生认为,道统不是一个概念或学说,其本质是一种谱系话语,且具有排他性。详见刘成国:《9—12世纪的道统“前史”考述》,史学月刊2013年第12 期。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闻见录》归属于“子部·小说家类”,持相同归类意见的如《艺风藏书记》《郑堂读书记》等。《直斋书录解题》将《闻见录》归于“史部·杂史类”。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