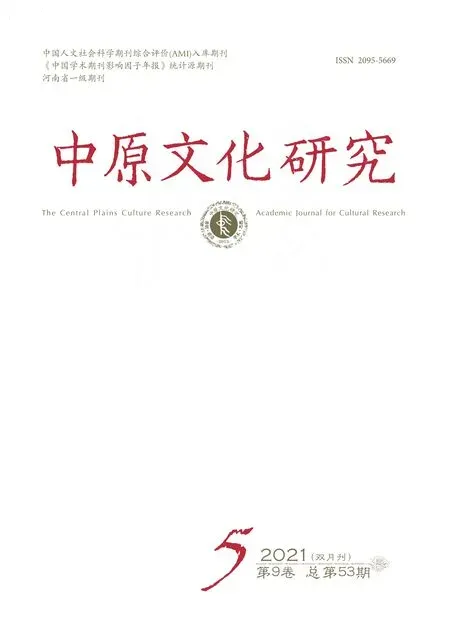修身成德之学:先秦儒家“学”观念的起源及其思想演进
霍艳云
“学”是十分古老的话题,亦是先秦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论语》以《学而》为首篇,其中高达十五篇均提及“学”;《孟子》中包括的个人之学、导人之教以及孟子对“学”的体会不容忽视;《荀子》第一篇是《劝学》,在《不苟》以下五篇及《大略》等篇章中又反复论及“学”;《大学》《中庸》的内容更是无不与“学”相关。可见,“学”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刘宗周认为:“学字是孔门第一义。”[1]255亦或言先秦儒家精神要旨尽现于此。故本文重新审视、估量先秦儒家“学”观念的起源及其思想演进。
一、溯源:“学”之字源的三重含义疏解
在此基础上,结合训诂学和原典资料对“学”之一字的解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涵义。通过研究发现,“觉”“效”“行”是对“学”之一字最为主要的三种解释。首先,“学”有“觉”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以“觉”释“学”,“学,觉悟也”。段玉裁注:“尚童矇故教而觉之。”此处均以“觉”为“学”之义,而“觉”含有“去弊”“去惑”“悟知”之义,也就是说“学”有悟其所不知之义。其次,“学”有“效”义。《易·系辞下》云:“爻也者,效此者也。”南宋理学家张栻引真德秀言:“学之为言效也,效夫善而勉之于己也。”[3]95可见,“学”有“效”之效法以求知之义。最后,“学”有“行”,即“实践”之义。“学”本来就是在学习生存技能、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据上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首先,“学”的活动原本是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以缝补衣物、搭建房屋、结网捕鱼等生活技能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其次,“学”之一字笔画的增加说明“学”的产生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这也反映出人们学习内容、活动日益复杂、深化的现象。此外,“觉”“效”“行”生动地体现了“学”之一字的深层含义。“觉”通过觉悟、反省而自得于“内”,偏重于意识层面的觉悟;“效”通过效法、模仿学习榜样而体现于“外”,偏重于实践层面的效仿;如果说“觉”和“效”所体现的是学习之人由未知到求知的内觉、效仿的过程,那么“行”体现的是其由知经多次练习到加以运用、实践的过程。
二、线索:前儒家时代“学”之践行由“野”向“文”的次第演进
夏代主要以军事技能、政治伦理道德、祭祀祖先作为学习践行活动的主要内容。《文献通考》载:“夏后氏以箭造士。”《礼记·射义》载:“立德行者,莫若射。”夏代,骑马、射箭等训练是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其中,习射不仅仅是武艺、军事活动的学习,亦包含礼仪规范的学习。
殷商时代是崇尚鬼神的时代。《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马端临认为“殷以乐造士”。在商人看来,敬事鬼神、祭祀祖先是十分重要的活动。出于祭祀以及渲染祭祀活动的需要,音乐、舞蹈的学习在商代的学习教育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时,贵族子弟主要以礼乐、祭祀知识和伦理道德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而且施教者也多为明礼、有德之人。
西周不仅将乐舞、射箭、御车、书法、计算等纳入到学习内容之中,亦将人伦道德、礼仪行为准则纳入其中。以西周国学之“大学”为例,周天子创办的“大学”规模很大,其中“辟雍”位置居中,四周环水,以“辟雍”为中心,又有东南西北四学。然则何谓“辟雍”?班固认为,“辟雍”乃“行礼乐、宣德化”之处。所谓“辟”象征“效法天地”“积以道德”,“雍”象征“教化流行”“壅塞残贼”。此外,毛邦伟认为,“辟雍”还是国老咨询政事的场所。可见,在“辟雍”中,贵族子弟主要以礼乐、道德、政事为学习内容。同时,在“东西南北四学”中还包含有射御、奏乐、舞蹈、祭祀等学习内容,这反映出西周学习内容的多样化、均衡化。自西周开始,礼乐文明、道德规范正式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
夏商时期,人类的道德意识渐趋觉醒,行为渐呈自觉化、伦理化的特征,以伦理道德规范为学习内容的实践活动开始出现。这一时期,道德规范多作为军事技能和宗教祭祀的衍生品而出现,人们对道德规范的学习,大多只停留于神对人的要求阶段以及被动地学习外在规范的程度,并非后世儒家人伦意义上的对道德的主动学习。中国古代比较系统的以伦理道德规范为学习内容的现象出现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以德配天”观念的支配下,订立了一整套典章礼法制度,由此确立了中国以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基本发展趋向。纵观夏商周时期的学习内容可以发现,学习内容与当时的生活需要、生产力水平、文明程度等密不可分。夏重武尚射,商敬神尚乐,周尊礼尚施。可见,在前儒家时代,学习践行活动经历了一个由“野”到“文”的过程,这极大地反映了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三、定位:先秦儒家“成德向善”之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孔子继承了自西周以来“学”以“德”为内核的思想遗产,孟子、荀子亦恪守孔子以“学”为角度观察世界、建构世界的传统,奠定了中国社会重“学”的风气与习俗。先秦儒家的学习内容广博而宽泛,核心要旨则唯有“成德向善”而已。其学习内容可分为事实知识和德性知识。其中,六艺偏向于事实知识之学,而四教、三达德、五伦等德目偏向于德性知识之学,由此确立了先秦儒家“成德向善”之学的主导地位。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游于艺”时称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就六艺之“礼”而言,孔子指出,君子应“立于礼”(《论语·泰伯》)“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礼在最为具体的层面涵盖了人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的行为,它通过神圣的仪式或对个人行为举止仪态的要求将人纳入到社会角色的关系网络之中,并用以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正如本杰明·史华兹所说:“礼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人们在社会中完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4]88就“乐”而言,孔子意图使人们通过对“乐”的学习,熟悉并遵守当时流行的礼乐规范以培养人的德性、完善人的德操。孔子听到雅乐,可“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蕴含伦理道德意蕴的乐才是君子所尚之乐。如果说礼多通过外在的行为标准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从而起到引导、约束的作用,那么(雅)乐则直击人的心灵,通过旋律影响人们的内心感受,正所谓:“致乐以治心。”(《礼记·乐记》)就“射”“御”而言,先秦儒家意在使人们通过射箭、御车技术的学习,培养其勇敢、守礼、专心致志等品格德操。孟子讲:“仁者如射。”(《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射之贵在于合德、养德。就“书”“数”而言,在先秦儒家看来,它们是人们应当具备的最基础的文化知识,是增强人的能力、培养健全人格、履行政治职能、完善国家治理等必不可少的前提。可见,六艺的学习是一种帮助人们健全人格、完善道德的存在,正如杜维明所说:“‘六艺’不仅包括身体方面的训练,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化育,两者的协调一致,意在将举止行为转化为内在思想与精神资源的适当表达。”[5]43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也是孔子认为人应该学习的内容。“文”主要是指对《诗》《书》《礼》《易》《春秋》《乐》这六种经典文献的学习;“行”指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尤指道德实践;“忠”“信”主要指德性修养,“忠”指对待他人要忠心不二、尽职尽责,“信”指与人交往时要诚实守信。孔门所重视的学习内容,始于文学,运用于践行,最后达之于德性,这不仅涵盖了先秦儒家在德性与知识两方面的为学要求,也体现了孔子重视践行、推崇德性的学为成人目标。
就“文”而言,《礼记·经解》中记载《诗》《书》《礼》《易》《春秋》《乐》各有其功效,如《诗》教人以“温柔敦厚”,《书》教人以“疏通知远”等。通过六经的学习可以使人通晓修养自身、立身处世的道理,从而激发、涵养人的善心,抑制、消弭人的恶念,使人的心性复归于正,合乎于善。如果说六艺是通过技艺、能力的获得来培养君子,那么六经则通过学习经典文献中的道理,陶冶人的性情并加以践行来培养君子。
关于“行”,皇侃引用李充的观点,把“行”解释为“孝悌恭睦谓之行”“行以积其德”[6]172。可见,“行”与孝悌恭睦等道德实践相关。换言之,只有把从经典文献中学习到的道德修养知识,通过躬行实践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才有意义。钱穆也认为:“轻言矫之以讷,行缓励之以敏,此亦变化气质,君子成德之方。”[7]96在钱穆看来,“行”显然是变化气质、学习做人、成己成德的重要方法。“忠”“信”均属于德性修养的范畴。孔子四教以“文”为始,以“忠”“信”之“德行”为终,可见,“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到德性修养实践上来,这也是孔门倡“学”主旨之所在。正如朱熹引子善言:“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当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8]802
“忠”“信”与三达德、五伦等虽属同一德目,但层次却有所不同。“忠”在春秋中期以前,并不仅是下对上的臣德,还是待人接物、与人交往时的普遍之德,“信”则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普遍适用的德目,“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论语·学而》)。人在处理五伦、乡党、邻里等人际关系时,均以“忠”“信”贯穿其中。二程认为,五达道、三达德为古今天下共行之道,即便对此有所觉悟、体察,如果“不一于诚,则有时而息”。也就是说,有“诚”才能贯彻、落实三达德,有三达德才能贯彻、践行五达道。这里所提及的“诚”和“忠”“信”释义相近,陈淳认为:“忠、信两字近诚字。”[9]27明代学者李湘洲认为:“‘忠信’两字,只是一个诚字。”[10]390可见,“忠”“信”相较于三达德、五伦等德目而言更为基础。
先秦儒家的学习内容、学习要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应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志于道”指学习之人应以贯通天地人之道为最终的努力志向;“据于德”指学习之人应以对“道”的把握为前提,彰显自身的善性,使己成为有德之人;“依于仁”指学习之人为人处事时应以仁爱之情为行为准则;“游于艺”,指学习之人应学习六艺等技能,从而更好地将德性修养融入到生活实践中,使己之技艺进可通乎道,退可贯乎德。这十二字以“据于德”为“学”之核心,以“志于道”为上达,以“依于仁”“游于艺”为下学,为学习之人构建了健全自身人格、修养自身道德的方法,并为社会有序化、良俗化发展开创了一条下学上达之路径。
此外,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生命是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实现需以“学”贯穿于始终,因为“学”不仅是学习者对自我生命的体认过程,也是行为主体的道德生命不断塑造完善的过程,更是学以至于圣人必须伴随终生的过程。这一动态的过程,是不断超越自我、更新自我的过程,需要以乐的态度、志的指向、弘毅的精神去实现,正所谓“言圣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学至于乐则成矣”[11]127。
此后至清代,有影响力且详细论及“学”的儒家经典均将“学”看作伴随一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并多将“学”与“成德”“明善”“君子”“圣贤”联系起来,最大程度地完善自我,做有德之人是儒家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义所在。西汉刘向言:“成人有德……大学之教也。”[12]62只有“学”才可以使人治性尽材、广明德慧。徐干认为:“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13]1只有“学”才能使人成为成德立行之君子。二程认为:“须是学颜子……存乎德行。”[11]62反复指出人需向颜回学习,存乎德行,入乎圣人气象。朱熹认为:“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乐)而得之,是学之成也。”[14]47学者应以仁义之精熟、道德之和顺、圣人之达成为学之终点。可见,二程、朱熹均以成为有德之君子作为“学”之主旨内容,只是在“学”之方法上较先秦儒家有所突破,指出为学方法应以穷理为先。二程认为:“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如此则方有学。”[11]115而“人伦者,天理也”[11]394,“理”首先表现为对人类社会君臣、父子等纲常伦理的遵守。
王守仁认为,学者应充实善念,遏制恶念,“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他同样指出,学者应当以成就圣贤人格为学问之要,并在为学方法上与前儒有所区别,指出人的心体是纯粹、绝对的至善,人应当依据本心良知的指引,去除私欲的蒙蔽,进而为善去恶。戴震指出:“解蔽莫如学……得所止莫大乎明善。”[15]72刑昺认为,《论语·学而》一篇以“学而”为始,以“君子”为终,意在告诉人们“学”之主旨内容在于成为有德之君子。清代学者朱柏庐提到:“要知圣贤之书……是教千万世做好人。”[16]232张伯行指出:“所谓学者,乃为士者所以求至乎圣人之道也。然自秦汉以来,学有殊途,而吾人为学当知所尚。”[17]40可见,千万世做好人、成德向善、至乎圣人之道是后儒们反复强调的学之主旨。
概言之,虽然二程、朱熹、王守仁、戴震等人所特别强调的“学”之正心养性、中正至诚的内求自省之方为先秦儒家“学”至于君子、圣贤的进路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但这些后儒学者们仅仅是在有限的意义和范围内探讨了先秦儒家“学”的涵义、内容,似乎基本沿用了先秦儒家以“德修”“向善”“成圣”为“学”之内涵、主旨的思想理路,虽然在学习内容、方法等层面对这一理路有所丰富,但却未赋予其更有新意的探讨,这一不足被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所弥补。
四、生活之学、境界之学、关怀之学的思想特色与近现代转生
近现代时期,关于先秦儒家“学”之内容的阐释研究,按性质划分,大概可分为“读书之学”“德性之学”“生活之学”“境界之学”“关怀之学”五类。
胡适认为,孔子所讲的“学”只是词章、训诂读书之“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18]74。仅将孔子之“学”理解为狭义的读书、知识之学,这显然有违先秦儒家“学”之本意。梁启超便尖锐地批评了胡适的这一观点,他指出,孔子所谓的“学”,是用以养成人格之学。在孔子看来,“读书不过其一端”[19]15。孔子之学,重于强调实践,“智识方面看得轻”[19]18。此处,梁启超将“学”重新向近代以前的“德性之学”“人格养成之学”靠拢。钱穆、南怀瑾、李泽厚的观点与梁启超的观点颇为相近,均认为“读书就是学问”的说法较为狭隘。南怀瑾指出,在先秦儒家看来,学问不只是知识渊博之义,他认为《论语》通篇所讲,不过是“如何完成做一个人”[20]10而已。在修“学”的途径上,钱穆、南怀瑾、李泽厚等学者兼重了其内在自省与外在实践之义,指出为学者在学习时,要自己学会探究“学”的虚实深浅,要当知反求诸己之义,时时反验于己心,要想理解孔子之“学”的真正意蕴必须经由真修实践中来,若无此真修实践,即无法明此意蕴。
梁漱溟则把儒家之”学”释为“生活之学”,他指出,儒家“学”之实质是一种“体认人的生命生活”的学问,不应当以哲学的思维惯性对其进行思考[21]497-498。他也同意先秦儒家之“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学”,且在德性基础上,更突出了“学”在实践层面的价值,指出其旨要在于“反躬修己的实践”。他认为,孔子一生为学所经历的进境,虽无法知晓,但孔子所说的学问不是知识之学或虚幻的哲学玄想,而是贯穿于其自身生活中的“一种力争上游的学问”[21]330。这种学问亦可称为人生实践之学,说得再详细一点,便是“力争上游者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立,自如也”[21]330。
冯友兰关于先秦儒家之“学”则提出了“境界之学”的看法。他指出:“道家以为儒家所讲,只限于仁义;儒家所说到的境界,最高亦不过是道德境界。这‘以为’是错底。”[22]779冯友兰认为,孔子及其后儒所说的志于学之学,是学道之学,“儒家所谓学,则即是学道之学……人生于世,以闻道为最重要底事”[22]780。在他看来,儒家“学”的范围很广,“学”除具有伦理学层面的意义外,还具有美学的意义。也就是说,所谓“境界之学”不仅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化,还意味着审美层面的精致化。陈来明确指出,不能将孔子的“学”仅仅理解为摄取知识,哲学抽象思维的提升亦是其所学内容。“上达是经由下学而达到对天命的理解,也是对宇宙、社会、人生统一原理的把握”[23]13。这便一下将“学”由成德、成贤、成圣的境界提升至道的境界。在冯友兰、陈来看来,知识、实干、道德、审美能力等的集合,才是先秦儒家“学”的全部内容。
杜维明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层面对先秦儒家之“学”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学”是关怀的伦理,而不只是简单的德性伦理,王守仁讲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例子,便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王守仁更希望“学”所表达的是一种关怀,而不仅仅只是了解、认知,其关怀的对象不仅包括人,还包括物[24]82。安乐哲和罗斯文的观点,有助于加深对“关怀之学”的理解:“根据儒家的道德人生观,我们不是抽象分离意义上的个体,相反,却是存在互相影响的人,过着——而不是‘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些角色构成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并且,这样我们可以在行为上追求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和技艺。”[25]19-20也就是说,孔子所倡导的“学”,在单独的个体那里不成立,所谓的个体不是抽象分离意义上的个体,必须有他者,有更多人、物的介入,此意义上“学”带有一种社会性。其大致包含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先秦儒家之“学”涵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先秦儒家之“学”涵盖了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即天地万物为一体,人和万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与关联。
近现代学者对先秦儒家之“学”有着不同的侧重及理解。以胡适为代表的“读书之学”的观点,有偏离先秦儒家“学”之原义之嫌;以梁启超、钱穆为代表的“德性之学”的观点,是对先秦儒家“学”之含义的正面确证;而以梁漱溟、冯友兰、杜维明为代表的“生活之学”“境界之学”“关怀之学”的观点则对先秦儒家“学”之含义做了一定的补充发展。
可见,“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学指生活技能、词章知识之学;先秦儒家之“学”更多地是从广义层面而言,主要指修己立身之学,即它不仅是完善人格的学问,也是抵达理想人生境界的学问。就为学途径而言,包括内省和外求两种,即内在自省、觉悟体察与接受教化、向外实践两个层面,只有将这两种学习途径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完善个人的道德品格,构建理想的道德社会。
综上所述,通过对先秦儒家“学”观念的起源与思想演进的探讨,可以看出,“学”所指称的是在知识、技能、德目学习以实现道德认知的基础上,自主自觉地以乐的态度、志的指向、弘毅的精神,以内省与外求的理性方式展开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习惯和道德实践等诸因素相统一的,不断超越自我、更新自我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与处理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相联结,以学以为己、学以成人、学以化俗为价值目标,以实现完善的道德人格、理想的道德社会为价值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