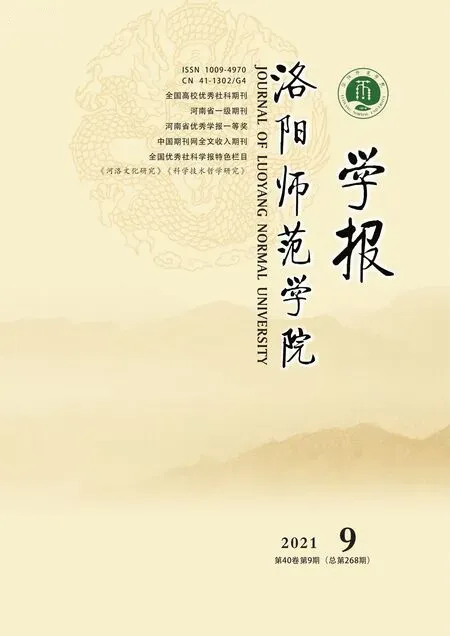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角下《老人与海》的悲剧解读
关 华
(吉林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7)
生态批评从文学作品中挖掘生态价值,有利于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待自然的行为和态度,建立和谐的生态观。学者梁军指出,生态危机下的生态批评理论一方面是为了丰富文学研究,挖掘文学作品新的内涵,拓展文学视野;另一方面还肩负着社会责任[1]。《老人与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书中描绘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一位坚强刚毅、勇敢正直的古巴渔民。《老人与海》一直被人们视作体现自我价值、征服自然的圭臬。随着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这类“以人为尊”的作品以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在肯定其人文价值的前提下,开始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基于此,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审视《老人与海》这部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对文本中悲剧结局进行研究,更要从其生态问题中得到启示,唤醒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和尊重。
一、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批判文学: 生态批评
(一)“生态批评”概述
生态批评是在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背景下产生的,起源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W.米克1974年出版的《生存的喜剧: 文学生态研究》[2]。生态批评探究的是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重审经典文学作品,目的是发现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义,重视生态文化,进而关注生态环境,重审人类、文化、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生态批评视角解读英美文学作品,能够重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思考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揭露和批判导致环境恶化、引发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批评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并非与人类对立,其反对的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破坏行为,而非反对人类对自然的一切索取行为。可见,生态批评是有选择的批评,其体现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也较为客观,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精神和人的价值的前提下,对过度的反生态思想进行批评。
(二)“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
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发展至今,历经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阶段被称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最初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并未击中要害,因此产生了第二阶段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1997年生态批评学者T.V.里德提出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张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上,透过种族的视野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将生态批评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关于生态批评的文学理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呈现两种生态理论: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其代表作有李心浮的《论生态美学》和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学的哲学思考》[3]。我国的生态批评研究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学者胡志红在《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生态批评仍处在初始阶段,理论建构、学术实践等方面都还与西方存在一定差距[4]。鉴于此,我国学者要针对英美具有代表性的生态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丰富自己的生态批评文学。海明威的作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生态学思想,他被誉为“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其在《大双心河》《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所体现的生态美学,在《非洲的青山》中体现的自然观,均为其生态文学的代表。然而,在海明威的众多生态文学作品中,《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思想最为浓厚,生态批评要求学者重审经典。因此,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悲剧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态批评视角下圣地亚哥的悲剧解读
(一)物质与精神需求: 悲剧结局的诱发点
《老人与海》的悲剧结局并非突兀的“欧·亨利式结尾”,而是在特有情节下逐步推进的、具有合理原因的。从作品中,读者能够直接找到圣地亚哥悲剧结局的诱因,即基本的生存需求(物质需求)及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小说中描述到圣地亚哥已经八十五天没有打到鱼,作为以打鱼为生的渔民,圣地亚哥缺失了基本的物质来源。一方面,由于生存需求,圣地亚哥必须出海打鱼,这成为其走向悲剧的一个诱因。这也与一直以来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有关,人类为了维持生计,只能向自然索取,这种最直接、最简单的“供需关系”已经常态化和固化,得到食物、满足身体需求成了出海打鱼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圣地亚哥的主观精神需求,是其走向悲剧结局的另一大诱因。圣地亚哥一直都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强者,他与黑人码头工比扳手腕能够坚持一整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人都叫他“冠军”,他确信,只要他想赢,没有人能将他打败。当人们嘲笑他是“倒霉鬼”时,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决定将船驶向深海,一定要打一条大鱼回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老头”。圣地亚哥希望被重视、不服输的精神需求促使他走向深海,最终迎来了自己的悲剧结局。
(二)自然的惩罚: 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老人与海》的悲剧结局升华了作品,作者通过圣地亚哥的死亡,体现出圣地亚哥不服输、永不言败的精神。悲剧的英雄形象使主人公更加深入人心。然而,从生态批评视角来看,圣地亚哥的悲剧结局具有必然性。著名生态批评学者格伦·A.洛夫曾说:“很多悲剧的本质在于通过集中表现人类的狂妄,把个人意志置于一切之上,即悲剧产生于无畏和狂妄。”[5]圣地亚哥所认为的对手只是那条大马林鱼和后来与自己夺食的鲨鱼群,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所真正面对的对手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和同样“打不败”的、无法征服的自然,那才是他真正失败的原因。圣地亚哥如果在斗争中成功,《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意识便会被大大削弱,作者设计圣地亚哥的悲剧结局具有必然性。
(三)生态矛盾观: 悲剧结局的双重性
小说中的圣地亚哥是一个拥有矛盾生态观的人。学者刘见阳指出,圣地亚哥性格的双重性,也体现了海明威矛盾的生态观[6]。一方面,圣地亚哥尊重自然,他将自然界中的鸟、鱼等作为自己的朋友和兄弟,体现出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小说中多次提到圣地亚哥独自在海上时,与来往的飞鸟说话,他担心那些海鸟找不到休憩之处。当人们残忍地对待海龟时,圣地亚哥想到的是自己也和海龟一样,拥有一颗跳动的心脏,他对动物产生了关爱与同情。除此之外,他与其他的渔民不同,其他的渔民都将大海当作一个男性,而他却认为大海是一个女性,他热爱大海。另一方面,当圣地亚哥回归到他渔民的身份后,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却变得截然不同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在圣地亚哥的身上没有消失,反而随着被他人嘲笑的挫败感逐步加强。圣地亚哥在与大马林鱼搏斗时,内心是充满了取胜欲的,他一面说着大马林鱼是他的朋友,却用工具结束了大马林鱼的生命。他一直以武力去征服它,他甚至已经在脑中计算他的这个“鱼兄弟”可以卖多少钱了。海明威在赋予圣地亚哥矛盾的性格时,也设计了其悲剧结局,这不仅仅是人类的悲剧,也是自然的悲剧,圣地亚哥的死亡看似结束了其所代表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自然似乎取得短暂的“胜利”,但大马林鱼也同样被杀掉了,人与自然对立后,自然(即生态)也遭到了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是人与自然的双重悲剧。
三、生态批评视角下圣地亚哥悲剧结局的启示
(一)解析生态危机根源
通过解析《老人与海》悲剧结局的原因,从而解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基于《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悲剧结局的诱发点可知,人类无论是因客观因素索取自然资源,还是因主观因素想要征服自然,都会导致悲剧的结果发生。而其诱发悲剧结局的因素,同样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广义来说,生态危机是经济发展下的过度开采以及人类征服欲的强烈体现。深入分析可知,人类征服欲的精神需求,与人类所处的社会及文化息息相关。莫尔特曼指出,西方宗教文化思想对世界生态危机有一定责任,还提出我们需通过解构残留至今的部分糟粕文化,才能够解析出生态危机根源。因此,必须重视生态文学,加强生态批评研究,深入分析生态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
(二)摒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
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价值论是生态批评历来研究的重点。《老人与海》中蕴含着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作品通过与自然的搏斗来肯定人类的崇高精神,虽体现出高度的人文价值,但作品所描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结局,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与重构自己的主体地位和自然客体地位。《老人与海》的悲剧结局给人们带来启示,即人们必须摒弃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保留适度的人类中心论。自然并非人类的“所有品”或“附属物”,诺顿在《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界的变动性》中指出,自然并非“无意识的客体”,生态及自然有其自身的保护及循环系统,只有将作为“客体”的自然,放到主体地位,才能够弱化生态危机带来的弊端,避免类似《老人与海》中人类必然的悲剧结局[7]。
(三)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双赢
有学者认为《老人与海》是反生态文学的作品,学者闫从军就指出,作品中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让圣地亚哥失去了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悲悯和珍惜,而作品中宣扬的“孤独英雄”的精神,以及作品中“你可以消灭他,但是打不败他”这句歌颂圣地亚哥的名言,也体现了海明威的反生态意识[8],此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生态批评论。然而,无论是反生态文学还是生态文学,《老人与海》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作品的主题是否偏向生态的认定,也正是由于圣地亚哥悲剧结局的双重性,给读者带来的不同文学观感。《老人与海》中人与自然不是一直对立的,圣地亚哥与自然也有和谐相处的时候,然后“出海太远”正是意味着这次出海捕鱼已经越线了,已经超出了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界限,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走向对立,圣地亚哥想要征服大自然,从而遭到自然的反噬。这是老人的悲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悲剧。作者通过圣地亚哥的悲剧启示人们,在对立面下的人与自然,谁都无法赢,只有当对立转向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够获得双赢的胜利。
《老人与海》作为一部同时体现个人精神和生态主义的佳作,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值得人们反复研究探讨。通过生态批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不仅对圣地亚哥悲剧结局的根源进行了解构,更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复杂性格探析了悲剧结局的双重性。由此可知,只有尊重自然、赋予自然主体地位,才能弱化生态危机产生的后果,促进人与自然的互惠双赢。
——运动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