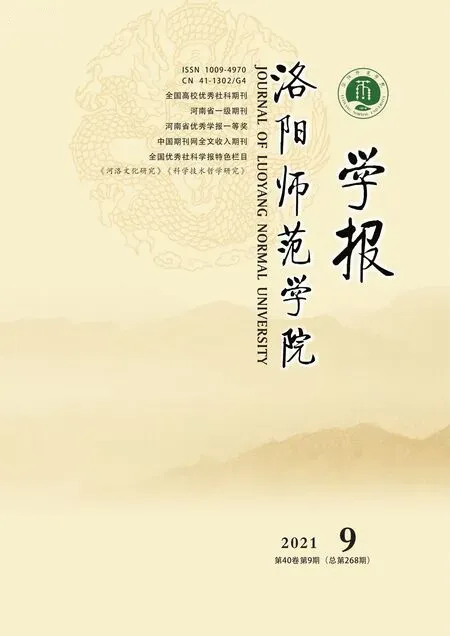《外婆的日用家当》主人公的心理探析
——以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为视角
尹雅婷,张凤梅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当代著名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讲述了一位黑人母亲与两个女儿的故事。大女儿迪伊在大城市求学,多年后回家探望住在偏远农村的母亲与妹妹麦姬,迪伊代表的新一代黑人的文化背景与母亲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冲突。迪伊想要拿走家里由外婆和姨妈等人用旧衣服缝制的两床百衲被,将其挂在自家客厅的墙上作为艺术品来欣赏。但是母亲早已许诺将被子送给一直陪在她身边的小女儿麦姬做嫁妆。麦姬从祖辈那里学会了修补百衲被的手艺,会把这两床被子当日用品来使用,母亲认为这才是黑人文化传承的正路。这篇小说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蕴含的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在于它潜藏的多层解读的可能性。本文拟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对其进行心理分析。
根据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人的心理结构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部分构成。“本我”受本能控制,蕴含巨大的能量,按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行事;“自我”代表理性,受到“本我”与“超我”的双重挤压,既受外界的影响,又要满足本能需要,按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行事;“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morality principle)行事。小说中三位女主人公的性格恰好与本我、自我、超我对应:迪伊代表被“本我”控制,追求快乐的人;母亲对应具有健康心理、能够自我控制的“自我”;麦姬则代表高尚又自卑的“超我”。
一、象征本我的迪伊
“本我”是所有心理能量的源泉,它没有理性的外壳,只是一团巨大的无形的生命力。弗洛伊德把这一隐蔽的心理区域描述为“一团混沌,一锅沸腾的兴奋,没有组织,没有统一意志,一心只为满足本能需要的冲动,按快乐原则行事”[1]141。迪伊出场时的华丽耀眼正暗示她是“本我”的象征。她身穿长裙,裙子的颜色亮得几乎要刺伤母亲的双眼,母亲感到整个脸颊都被它烫得热烘烘的。迪伊从小就盛气凌人,离家求学前,她经常念书给母亲和妹妹听,但只是把她们当作傻瓜一样,把一些无用的东西强塞给她们。她还喜欢要这要那,而且“要什么东西时总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地要,不达目的不罢休。她可以一连好几分钟不眨眼地死瞪着你”[2]390。即使是在面对白人时,黑人女孩迪伊也不会像母亲一样躲躲闪闪,而是直视对方。用麦姬的话说,她的姐姐是生活的主人,想要什么便能得到什么,世界还没有学会对她说半个“不”字。本我的这股力量有时颇具破坏性。根据小说暗示,造成老屋被毁、麦姬被烧伤的那场大火很有可能与迪伊有直接关系,因为她对那老屋代表的贫穷恨之入骨。
本我的这些特征并不随时间、环境改变而变化。“本我中没有对应于时间观念的东西,没有对时间流逝的承认,而且时间的流逝也不会造成心理过程的改变。”[1]156迪伊在母亲的资助下上了大学并在外工作,但是我行我素、蛮横霸道的性格与她离家上学之前并无二样。一下车她就开始咔嚓咔嚓地为母亲和这间老屋拍照片,既未征求母亲的同意,也未说明用意。迪伊仍然要这要那,午饭后,她在家里转来转去,一会儿看上家里的条凳,一会儿看上搅乳棒,这些过去她看不入眼的东西一下子成了宝贝,统统要拿走。她更是看上了两床百衲被,紧紧搂在怀里。甚至母亲走过来要摸一下,她都赶快退后避开,好像被子已经属于她了。迪伊更是直呼自己多年未见的妹妹长着“大象的脑袋”,毫不顾及内心已十分脆弱的麦姬的感受。迪伊的咄咄逼人源自“本我”无穷能量的释放。“本我”中没有类似否定的东西,它只为满足本能的冲动,这些冲动是“长存不灭的,可以整整保存几十年,只是看上去像新近才产生的一样”[1]151。
二、象征超我的麦姬
“超我”是与“本我”完全相反的心理能量。“本我”可以把人变成魔鬼,“超我”却可以把人变成天使。弗洛伊德在《心理性格分析》一书中指出:“超我代表各种道德准则,倡导品行完美,简单来说它就像生活中人们称之为‘高尚’的那种东西(‘higher’ things)。”[2]130-131弗洛伊德把超我的形成归结为父母的影响,父母依照社会规范进行奖惩强化了孩子身上超我因子的形成。麦姬长期与母亲、外婆、姨妈等生活在一起,长辈的勤劳善良在她身上完美体现。故事发生的场景——干净整洁的院落就是她和母亲一起布置的。午饭后,麦姬不声不响地在厨房里刷洗。她还从长辈那里学会了制作百衲被,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更难能可贵的是,当迪伊提出要拿走麦姬作为嫁妆的百衲被时,尽管心里不情愿,但经过一番心理斗争,麦姬还是大度地做出了让步:“让她拿去吧,妈妈,不要那些被子我也能记得迪伊外婆。”[2]396母亲听到这话就觉得“似乎头顶上受了什么东西的敲击,其力量自头顶直透脚心”[2]396。
负罪感(guilt complex)也是超我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麦姬,迪伊就从未有过负罪感,似乎做什么都理所当然,麦姬却恰恰相反。一场大火在她手臂、腿上留下了伤疤,更在她心灵上留下抹不去的阴影。麦姬总是躲躲闪闪,羞于见人,像一只跛脚的动物一样拖着脚走路,眼盯着地面。麦姬可能是在幼年时遭到外部世界的讥笑而将自己封闭起来,越是这样,她越看重内心道德的完善,希望用道德上的完美来弥补外形的缺陷。但是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又往往是脱离现实的。弗洛伊德认为,超我与自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超我不能与外界接触,因而它对完善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3]26。也就是说,超我是没有行动能力的。麦姬在迪伊出场之前一直处在焦虑之中,迪伊和她的男友一下车,麦姬就要夺路而逃,幸而被母亲拽住,之后她又开始不由自主地吸气,发出“呃——”的响声。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有羡慕、敬畏,更有对内心冲动的压抑。这里沃克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你路上突然发现一条蛇尾巴在你脚尖前蠕动时发出的声音,呃——”[2]391蛇是本我的象征,本我的突然出现是对超我的引诱,使超我不由得乱了方寸。当迪伊的男友作势要拥抱麦姬时,麦姬吓得直退到母亲的椅背挡住退路,并全身发抖,冷汗直流,超我已无抵御之力。午饭后,听说姐姐要将百衲被拿走,麦姬失手将手中的碟子滑落,这显示她内心的恐慌,但是紧接着,她不是冲出去抗争,而是关上了厨房门——与现实隔绝,最终放弃了百衲被。麦姬有一颗至善的心灵,遵从社会规范的教导,却没有行动能力,当母亲(有行动能力的自我)将百衲被从迪伊手里夺回,放到她的腿上时,麦姬笑了。“超我”在“自我”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焦虑才得以解除,心情复归平静。
三、象征自我的母亲
“自我”代表理性与审慎,是连接“本我”与“超我”的桥梁。但是“自我”与二者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它要遵从超我代表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又不能一味否定或压抑本我。弗洛伊德曾用骑士与马作比喻来说明自我与本我的关系:“骑士控制和阻止马快速奔驰的力量,但他又最终得听任马的摆布。有时他必须放松缰绳以免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同样,自我像骑士一样,控制与阻止各种冲动,但是往往又或多或少地受放荡不羁的本我的支配。”[3]26母亲在院落里等候迪伊归来的空闲里做起了“白日梦”,她梦想着和迪伊一起登上舞台,接受著名白人主持约翰尼·卡森的采访,讲述迪伊在母亲的帮助下走向成功的故事。舞台上迪伊含泪热烈拥抱她,并在她衣服上别了一朵大大的兰花。她有一刻沉浸在这温馨的梦境中。弗洛伊德在《创造家与白日梦》一文中指出,白日梦就是人的幻想,“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4]。换句话说,由于人的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便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表现在梦境中。梦的内容分为“显现内容”与“潜在思想”两部分,显现内容是梦中的事件,潜在思想是隐藏在这些形象与事件背后的欲望。母亲在白日梦中期望与女儿一起登上舞台,潜在的就是对迪伊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以及对她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向往。所以当迪伊一身华服出现在家门口,母亲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喜欢她走起路来裙裾飘荡的样子。母亲片刻陶醉于自己导演的这一幕母女温馨相对、喜极而泣的场景。甚至她还幻想自己的形象大大改观,身材苗条,皮肤细滑,头发闪亮,伶牙俐齿……这些不着边际的幻想代表着“自我”片刻被“本我”代表的快乐原则所驯服,“自我”在意识松懈时不自觉地滑向了“本我”一边。但是“自我”很快恢复了理性,回到现实当中。母亲意识到现实中的自己不可能像有钱人家的小姐那样身材窈窕、细皮嫩肉、无所事事。现实中的她是个大块头、大骨架的妇女,有着干男人活的粗糙双手,她能像男人一样杀猪宰牛。母亲的体型与劳动能力是在贫穷现实生活的磨砺中形成的。一身厚厚的脂肪尽管不美观,却能使她在严冬户外干活时抵御寒冷。她不会在白人面前伶牙俐齿,总是把头转向离他们最远的方向,随时准备逃走。这是20世纪初黑人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下为保护自己而形成的普遍心理与行为习惯。严酷的现实不仅塑造了母亲健壮的体魄和自我保护的心理,也促使她总结出一套勤俭持家的实用哲学——物尽其用。穿破的衣服剪成碎片拼缀起来,就成了一条崭新的百衲被。被子破了,可以再修补,继续使用。在这个周而复始的“破损—修补”的循环中黑人的文化传统得以在一代代人手中薪火相传。母亲在实践中总结出的这套实用哲学使她看到,黑人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是善良怯弱的麦姬,因为她会像祖辈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修补它,而不像迪伊那样要把被子挂在墙上供人观赏。所以,当迪伊一会儿看上条凳,一会儿看上搅奶棒时,母亲都不动声色;但当迪伊坚持要将给麦姬准备做嫁妆的百衲被据为己有时,母亲果断地将百衲被夺回。在“本我”强大的攻势对“超我”造成破坏之时,“自我”毫不犹豫地站在“超我”一边。
四、结语
象征“本我”的迪伊一心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追赶当时流行的非洲寻根文化的时尚,坚持将百衲被据为己有;象征“超我”的麦姬遵从社会伦理的教诲,愿意忍痛割舍百衲被;而象征“自我”的母亲看清迪伊的企图后,果断夺下了百衲被,交还麦姬。百衲被是黑人文化传承的象征。因此,将心理分析与文化解读相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到,母亲的这一果断举动代表了艾丽丝·沃克对黑人文化遗产继承的明确态度。沃克写作这个故事时,许多黑人开始摆脱对白人文化的依附与崇拜心理,转而到非洲去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民族文化缺乏深刻认识而只追逐表面形式的现象。“不少年轻人就像故事中的大女儿迪伊一样,以为梳非洲人的发型、穿非洲人的服饰就是表现文化之根的最佳方式;将手工制品当作艺术品悬挂起来就是体现文化遗产价值的最好途径。”[5]沃克通过小说对这种对民族文化流于形式的理解进行了批判,揭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传统。正如美国评论家戴维·柯沃特所说:“艾丽丝·沃克辛辣讽刺了60年代黑人意识中对文化的误区,否定了他们的虔诚,特别是对黑人文化的寻根举动,坚定了被忽视的文化价值观。”[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