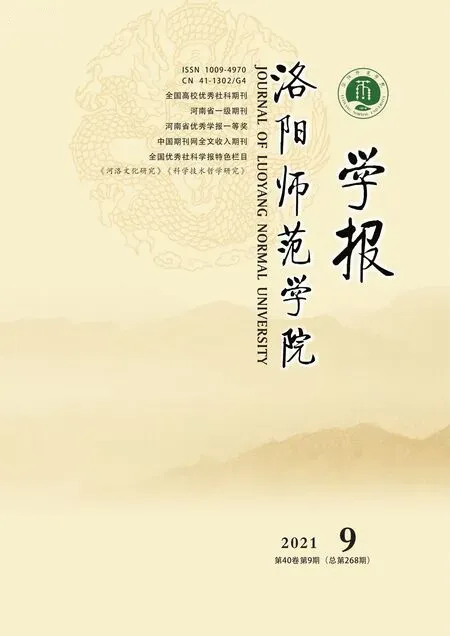张衡的“笔误”与朱熹的“尬解”
沈叶露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曾对语录体文字有所批评:“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自称教外别传,直指心印。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甚者呵佛骂祖,略无忌惮。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尚之,以为胜于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1]钱氏的这一观点当世的研修者是颇不赞同的,因为率直其心浅白其辞的阐理方式和语出当面不假雕饰的语体特征,均使其“鄙倍”之瑕不掩传道之功。对朱熹讲学语录详加记载的《朱子语类》在后世流行不衰,作为主讲人,其“道”赖以更广泛地传布,《语类》之知名度甚或强于其集注、集传之属,而其中某些或囿于时地知见而未及详加考辨的即兴言辞,则难免有所过讹。后世对这些讹失的“刊行不误”,当事人如或有知,不知将对钱氏“鄙倍”之责怀抱怎样的心情。
朱熹晚岁与学生论道,论及《老子》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句,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车’,是一句,谓以走马载粪车也。顷在江西见有所谓‘粪车’者,方晓此语。”门人沈僩记下该则语录,并于其后注云:“今本无‘车’字,不知先生所见何本。”[2]2998关于《老子》的这一出典和晦翁的这一解说,近代学者马叙伦有过考察总结:“各本及韩非《解老》篇、《喻老》篇、《汉书·西域传》注、《文选·七命》注引,并无‘车’字。”[3]今就马王堆帛书看,《老子》甲乙本虽各有损掩,但“粪”下均无残损,亦无“车”字,均可证《老子》该处原文之真。[4-5]既然“走马以粪车”的表述并非老子原句原意,朱子误记且于江西见所谓“粪车”前一直对此感到疑惑,那么,导致其有“江西粪车之悟”情节的因缘是怎样呢?
一、朱子是“走马以粪车”之误的“首犯”吗——“粪车”连缀的缘起
其实,这个事件不可尽归为朱子一人之过,其首先牵连到汉代张衡创作的被后人视为“长篇之极规”的《二京赋》之一——《东京赋》。其中有句“却走马以粪车,何惜騕褭与飞兔”。騕褭、飞兔都是骏马的品种,薛综《二京解》详其前句出典:“却,退也。老子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河上公曰:粪者,粪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马以务农田。然今言粪车者,言马不用而车不败,故曰粪车也。”(该解为《文选》李善及六臣注本所保留征引)是先明确其句来源于《老子》,又指出“走马以粪车”是化用老子意而别呈“马不用而车不败”的新意。也就是说,其表意由元典之“掉转战马以粪田”转而为“掉转战马以拉粪车”,因而言边境无事(“马不用”)而农耕丰勤(“车不败”)——“礼义大布,甲兵不起,却走马以务农,虽有骏马终无所用,谁复爱惜之”(吕延济注)。但这显然更多是意会之解,因为这样的语法表述是有问题的:《老子》本文“却走马以粪”,“以”作使令义讲,高诱注《淮南子·览冥训》“故却走马以粪”:“止马不以走,但以粪,粪田也”,皆用“以”为“使”,“以粪”,即使之粪(田)。而《东京赋》“却走马以粪车”,“以”无法再作使令义解,且找不到其他合适的释解——比如是否可以理解“以”为介词“于”,表示“退转奔马于粪车(之旁)”呢?首先,释“以”作“于”,上古汉语确有其例,如《左传·桓公二年》:“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两处“以”字短语分别表示“于条之役时”“于千亩之战时”。(1)何乐士指出该例为“用战役名称表示时间”(《左传虚词研究》);杨树达亦认为该句“以”“用同‘于’,表时间”(《词诠》);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以“训见《词诠》”赞成杨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作‘于’用,以条之役,犹言于条之役。”[6-9]杨伯峻《古汉语虚词》在用例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以”作“于”用的两种情况即“一表时间,一用在形容词下”[10],却没有如“却走马以粪车”般“以”接地点表方所的用法(2)又如《汉语大词典》于“介词。在;于”释下除引上《左传》例外,另举二例为《旧唐书·方伎传·神秀》“神秀以神龙二年卒,士庶皆来送葬”及鲁迅《二心集·柔石小传》“柔石,原名平复,姓赵,以一九○一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宁海县的市门头”,“以”亦皆作表时间的介词用。[11],更何况“止(却)马”的地点不在“粪车”,而在“粪车之旁”。由之,到了讲求实学的清学家那里,易顺鼎就对张衡“粪车”句作有详细的辨识,大意如下:《文子·精诚篇》有“夫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马以粪,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是谓坐驰陆沉”句,人或以属下句的“车”字连上读而成“粪车”。而《淮南子·览冥训》亦有句“故却走马以粪,而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粪”下“而”字可明证“车轨”连读。许慎、高诱两注《淮南子》皆以“却走马以粪”出于《老子》且“粪”作动词“粪田,播种”解。傅奕本“粪”作“播”,毕沅云:“粪、播,古字通用”,并皆可作“粪”用为动词义的旁证。(3)朱谦之《老子校释》详引易氏之说。[12]这就对“粪”字的用法、表义以及“粪车”误为连缀的缘由分析得颇为明确了。由此,该问题或可作如是观:张衡“走马以粪车”表述的元典来自《老子》,而其造句所因则或源于对《文子》句的误读,而就“赋”之体裁言,其文句虽然含有某些不合理的语法因素,但文章“雕缛成体”,结字造句不必太苛矩矱,且从其流传的“实效”看,文人争相“仿句”,注解家“将错就错”地作出阐发,亦当可认其为“美丽的错误”。
二、朱熹误平子句为老子句原委
张衡,字平子。由前述可知朱子所谓在江西见“粪车”而悟“以走马载粪车”义,实际解释的是张平子《东京赋》里的句子,而非《老子》“天下有道”章的原句原意。那么朱文公为何会误平子句而为老子意呢?在其弟子录下该语录后又特别写下“今本无‘车’字,不知先生所见何本”的思惑中,也使我们更生费解:既然当时的《老子》传本与诸家注解均无“车”字,朱熹又何以独为《东京》句所蒙惑,明觉其有疑却不查知本文,直至“在江西见有所谓‘粪车’”而方自以为“晓此语”?或许当时文选学的影响之盛是对该疑问的解答。如众所知,唐及宋初的科考对诗赋的推崇使文涉三代至六朝的《文选》受到很大重视,而对宋代《文选》的传播态势,宋人及后代儒士都有所注意与记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13]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也说:“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14]清代吴锡麒为张云璈《选学胶言》所作的序中也说:“大抵选学者,莫重于唐,至宋初犹踵其盛,故宋子京曾手抄三过……自熙、丰以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及后帖括盛行而选学益废。”[15]是皆描述了唐及宋初文选学极盛的景况,同时也指出熙、丰变法是《文选》传播的一道分界线,殿试罢诗赋而只试策的科举改革从理论上对选学的长盛起到了不小的抑制作用,阻碍了士子们对《文选》的热情。其实,就朱熹本身来看,他一贯的治学主张本不推崇科举,《朱子语类》记载了多条其对门徒的相关教诲:“学须做自家底看,便见切己;今人读书,只要科举用……皆做外面看”[2]182“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圣人教人,只是为己”[2]243“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2]246……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为学体道的理念始终为理学家们所遵奉恪守。因此,无论时代科举局势的风云变幻还是朱熹的主观觉识与倡导,《文选》之于朱子,都不应是受到特别重视的。然而,由其对“却走马以粪车”句的“全盘接受”,又似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讯息:虽然《文选》在朱熹的学习目标与结构中不占据主要地位,亦虽然彼时科举的指针在摇摆中扑朔变化并在客观上抑制了选学的发展,但《文选》的热度并未太快消散,“选学废矣”“选学益废”的情况当是经历了较长的时期才逐渐显现出来,而非如笔记中记载的那样于熙、丰之后很快显露。(4)郭宝军《科举视阈下的宋代〈文选〉传播与接受》对宋代历次科举改革作了梳理介绍,并对各个时期《文选》的刊刻情况作了详细的列表比较,得出结论:“熙丰变法对《文选》及其传播的确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并未如前人所言《文选》的传播与接受因为王安石的变法而被截断、被终止。”[16]而时代的烙印、接近于集体无意识的对诗赋的接受与熟稔,或可为晦翁这则版本文句失察事件的解释。
三、尾声: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东京》之为赋,其影响是很大的。同为《文选》所收录,年代稍后的西晋张协《七命》篇有句“却马于粪车之辕,铭德于昆吴之鼎”,继承了张衡“粪车”的句意与表述,却作了合乎文法的改造。《文选》六臣注本于《东京赋》“却走马以粪车”句“以”字下出注云“五臣(本)作‘于’”,“却走马于粪车(之旁)”的表达显然要更准确。“五臣”改字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据张协句以“修正”张衡原句,二是其读至《东京》“粪车”句时感到文句难通而做出的自觉修改。清人治《文选》有所谓“五臣乱善”的提法,但由是例也可窥到一些“五臣”的思理。由张协的“仿句”已可见张衡“粪车”句之流行,至宋初,杨亿则又有一则“仿篇”的故事,据《枫窗小牍》载:“杨亿作《二京赋》既成,好事者多为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17]宋及宋前,文士对平子赋的热衷,是皆各见一斑。
易顺鼎曰:“汉末传《老子》者皆无‘车’字,张衡殆误读《文子》与!”其实,从稍后的张协“改句”与唐代五臣“换字”来看,张衡的这一“误读”造语并未造成太大“学术后果”,然而惊人的是,一到朱子的“语录”里,此事就出现了“文献性”的转关,从此,“粪”下有无“车”字成为校注《老子》句无可回避的问题。其实,第一个对该问题作出全面考察的学者并非上文所引的易顺鼎或马叙伦,朱熹门人沈僩先启其疑,其后元代经学家吴澄于《道德真经注》中作出校注“‘粪’下诸家并无‘车’字,惟《朱子语录》所说有之,而人莫知其所本。”首先做了确定的考证——只是,吴文正公继而导出了错误的认识:“今按张衡《东京赋》云‘却走马以粪车’,是用老子全句,则后汉之末,‘车’字未阙,魏王弼注去衡未远,而已阙矣。盖其初偶脱一字,后人承舛,遂不知补。‘车’‘郊’叶韵,阙‘车’字则无韵。”[18]这显然是由迷信朱熹而导致了对张衡的“迷信”,故而竟有诸家皆误唯此独是的偏断。到底还是清学家冷静,易顺鼎云:“‘车’‘郊’音亦相远,吴氏以为叶韵,尤所未详。”
汪维辉先生曾谈道:“中国上古时代拥有丰富的文献典籍,被后来的历代读书人奉为经典,他们熟读这些典籍并以此为创作诗文的词语来源和语法规范。”[19]而在本文的案例中,张衡作为“误解误用”的“首犯”,或来源于对《文子》句的误读;朱文公的“误用误解”又因缘于对他“熟读之典籍”的承袭。有意思的是,张衡因误识句读而制造新句,本源自错误的“读码”与率意的“编码”,但这仅是限于其个人文辞“言语”层面的使用,既不会对《老子》原句构成威胁,亦不必担心形成所谓“语言”的“规范”,张协等对其辞句的“再化用”可为之证。而朱熹为之作了“在江西见粪车”云云的口头注解,是又对“误码”进行了新一层的解码,但因立足于对《老子》句的解读,又因其集理学之大成的身份,再加之“其徒众”而“语录兴”,“支离之言”已为鸿宝,就难免构成一个事实上的错误,并开启了对《老子》文句真否的乌有之案。
元明两代在尚导理学的大氛围下,吴澄《道德真经注》力挺朱说,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粪”下亦保留“车”字,成为代表主流学界与官方的两个版本,则盛名之下,可不慎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