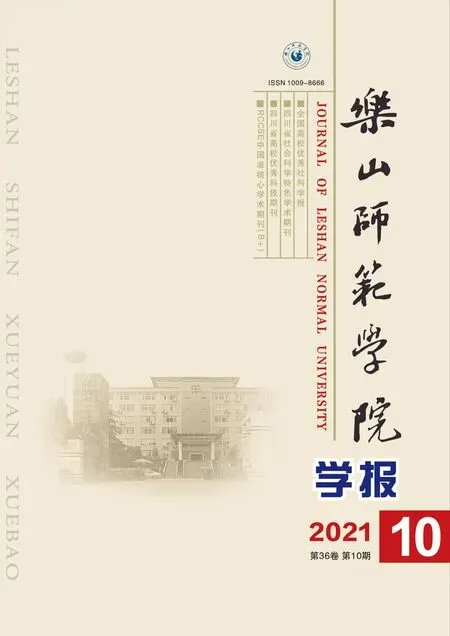“反现实倾向”的生成与“诗意家园”的兴建
——王小波《万寿寺》论
史鸣威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众所周知,“时代三部曲”是王小波创作的主要成就,《青铜时代》三部娓娓道来的长篇里蕴涵了王小波的艺术创造和人文思想。《青铜时代》中的《万寿寺》是当之无愧的成熟之作:其一,《万寿寺》叙事方式精致。王小波自述道:“我写《寻找无双》时,还是中规中矩的。写《红拂夜奔》对叙述本身就有点着迷,不再全神贯注于写故事。《万寿寺》则全然不关注故事,叙事本身成了件抒情。”[1]154研究者也为我们指出:“《万寿寺》是解读王小波叙事艺术最好的文本。”[2]黄平认为《万寿寺》是王小波小说艺术集大成的代表。[3]其二,从王小波创作年谱来看,1996 年夏,王小波使用繁复精致的叙述策略对早年作品《红线盗盒》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了一部擅于挑衅禁忌却又富于优美的长篇佳作——《万寿寺》。[3]质言之,除了未竟稿,《万寿寺》是王小波生前最后一次成熟的艺术创造。因此,应当重视《万寿寺》的价值,也应当注意其在某些方面所展现出的能够破解王小波创作谜团的重要线索。
黄平在《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里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为案例分析“局外人”视角,试图勾勒出一条新的线索理解王小波,即“历史创伤—反讽—虚无—自由”,并总结出一条命题:王小波之所以在读者群体中引起如此广泛的影响,之所以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叙事魔力,就在于其实质上治愈了时代主体对于当代史的负罪感。[4]“历史伤痛”所纠缠的因素如此复杂,王小波所建构的小说空间又是如此广阔,同样以“历史伤痛”
为思考的起点,结合别具启发性质的因素去接近《万寿寺》的文本实质,也许能够在理解《万寿寺》的同时,理解王小波创作的深层逻辑。笔者以为,这个“X因素”即是王小波所展现的“反现实倾向”。
一、“反现实倾向”:概念的缘起
所谓“反现实倾向”,主要是指王小波本人对于“现实主义真实论”“现实主义美学”的逆反心理。李银河在采访中提到,王小波非常抵触车尔尼雪夫斯基“真即是美”的理论,他认为真实与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真实不可能成为美,美只有通过创造和想象的世界才能实现。[1]159王小波所展现的立场尤为鲜明,其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其人大名鼎鼎,可以说是一位“经典化”的文学评论家。举例而言,列宁就用“哲学唯物主义”的“桂冠”给车尔尼雪夫斯加冕。其二,此处涉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真即是美”的命题,其本身又指向何种理论与现实的问题?平心而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这种理论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王小波的这种逆反情绪是否源于对前者的误解?如果存在误解,这种误解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参考王小波对“郭鲁茅巴”和托尔斯泰的态度,参照这些文学大家在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笔者以为王小波之所以出现这样“消极”的态度,与当代存在的高度一体化之“秩序”带来的重大压力是分不开的。这种秩序赋予的压力一方面表现在王小波对文学秩序的反叛和逃离,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王小波与“体制”的龃龉和分歧。
此外,“反现实倾向”并非全然指向一种与“现实主义”的对抗意识,而是表现为对现实逻辑的某种厌恶。在《<未来世界>自序》里,王小波指出喜爱奥威尔和卡尔维诺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在于讨厌真实逻辑之限制,其二在于憎恶现实生活之乏味。[1]37在黄集伟对王小波的访谈中,王小波表达了在虚拟时空中写作的创作趣味。[1]91王小波对真实有着清醒而独到的认识,对王小波来说,被现实生活所限制是令人生厌的。王小波与“自由主义”有着说不尽的话题,这不仅仅表现在他辞职做自由撰稿人的经历,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不可抑制的逃脱枷锁的冲动。对于“现实逻辑”的厌恶,王小波在作品中的阐释可能更为清晰且富有灵气,他大胆地宣告一个人的生命必须要有“诗意”的支撑,否则即是一种未完成的缺憾[6]246,并且,他也不无悲观地指出“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6]247。回到历史现场,王小波所见证的生活并不像文论家所说的那样具有深刻玄妙的美感,反而只有无可挽回的庸俗、堕落以及伴随着这种庸俗的深深的无奈与悲哀。通过对王小波文论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王小波的“反现实倾向”的内涵,既指向了对“现实主义”文论的逆反情绪,也指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厌恶。而要更深入地了解和求证这种倾向,则必须结合文本的细节和王的生活经历,进行一番细致而清晰的考察。
二、“探索者”:从“秩序”到“文本”
王小波是个秩序外的“游离者”,也是秩序外的“探索者”。“文革”后恢复高考,王小波曾经报考戏剧学院,考的是编剧系,考官问他喜欢什么剧作家,“他立即回答一句‘萧伯纳’。没想到接着竟是一片冷场”[1]178。由此可见,王小波有过向“体制”靠拢的倾向,他参加了戏剧学院的招生考试却遭遇失败,之后王小波也并没有放弃学业,通过高考进入人大学习。王小波是怎样成为人们眼中的“文坛外高手”的呢?这期间伴随着他自身的体认,可以说是与“体制”的多次互动下,一种反叛的意识逐渐觉醒了。王小波自北大离职转到人大,又辞去大学教职转做自由撰稿人,既是对自身工作的不满意,也是对体制的约束感到难以适应。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获得台湾联合报大奖给了王小波做专职作家的信心。有学者高度评价王小波的人格操守和人文素养,用“经典人文知识分子”“自由人”“通才”“特立独行”等一系列闪闪发光的词语来建构王小波的光辉形象[1]293,却忽视了这些词语的堆叠或许已经脱离了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和注重事实依据的学术准则。事实上,考察王小波生平,他与“秩序”的诀别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王小波必然走向“秩序”之外,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受经验哲学影响颇深的自由主义者,还因为他对多年来形成的文学秩序产生了“质疑”。
“有些东西,像郭鲁茅巴,他是完全不喜欢的,完全不在他的范围里……而郭鲁茅巴他是一个也看不上……说难道是个日本人么?”[1]3对于主流所肯定的文学家,王小波的态度是值得深刻思考的,因为这一系列的作家无一不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事实上,王小波不仅反“郭鲁茅巴”,他还反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他的笔下是一个恬不知耻地喋喋不休的老头,是自由派的死敌。[7]虽然王小波强调这等“人物”皆是自由派的死敌,自由派却未必反感“鲁迅”和“托尔斯泰”。尽管王小波这些带有强烈喜好的言论未必谈得上深刻,但是他至少指出这样一个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忽略的事实:当代文学秩序常常处于暧昧不清的境地,众人皆知的作品并不一定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一流的文学作品常常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更令人痛惜的是,那些本应涌现的文艺精品却根本没有写作和发表的机会。[6]5这里言下之意是要颠覆文学史书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如果说王小波对已经形成的文学秩序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一大传统也就成为王小波的重要质疑对象。为什么这么说?茅盾是公认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夜读偶记》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文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背景呢?从五四开始,文学并非逐渐形成百花齐放的园地,反而是逐步走向了“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领域爆发了频繁又剧烈的冲突,也渐渐形成了评判文艺的法则和尺度[8]20,此外,中国革命的大功告成也为左翼文学确立了不可逾越的唯一性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8]21。在洪子诚看来,革命成功之后的文艺界业已形成了“一体化”的文学秩序,形成了僵直却有强大惯性的文学规范。在这种左翼文学、现实主义和文学秩序难以相分割的历史背景下,王小波面临着不小的抉择,是选择在“秩序”内蹉跎,还是走出“秩序”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王小波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王小波的“反现实倾向”终于由个人的经验和性格落实到文学创作的理念中去。
伴随着王小波对旧文学秩序的否定,一个新的秩序就王小波那里被建构出来。这个新的文学秩序则有如下要点:其一,要求文字能够极尽丰富性,要求在书写中寻找思想、语言和文字同步和谐的可能性,不但需要表达之准确,还需要表达之深刻,更需要表达之韵味。[6]5其二,王小波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学习对象也有清晰的认识,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高度赞扬了已故诗人翻译家查良铮和王道乾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作用,他肯定了诗人的译笔及其对现代汉语韵律的发现,因为正是这种韵律发现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石。[6]6王小波的文学秩序重构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小波是如何走出他的文学之路?一个横空出世的小说家和杂文家,一个“文坛外高手”,王小波并非天生而知之者,他的文学生涯也充斥着探索的经验。王小平对此是深有体会,他在《我的兄弟王小波》中记载了兄弟二人少年时读书的场景,“我们躺在地上,半睡半醒,看得昏天黑地,迷迷糊糊,什么也记不住,这就是我们在饥饿年代的养生之道”[9]61。王小平还高度赞扬王小波的读书天赋,他指出王小波不仅读书飞快,而且这种快根源于圆转融通的语感和虚极静笃的凝神。[9]87由此可见,王小波是在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之后,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王小波的探索之路,还隐藏在他对小说的修改增删上。王小波曾经详细描述自己怎样写小说:通过电脑反复调动小说的结构段落,逐渐摸索出一条叙事的线索,最终花上三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远胜前作的新小说。[10]60王小波从杜拉斯写作《情人》的方法中学习了如何写现代小说,那种对结构的孜孜以求从侧面反映了一位小说艺术家的匠心独运。《万寿寺》改编自唐人传奇《红线传》,这一点与鲁迅改编先秦故事而成的《故事新编》很像,因此,房伟常拿《故事新编》跟《青铜时代》相比较。但是王小波有他的独特之处,他对唐传奇题材十分钟爱,《万寿寺》并不是最早的改编作品,王小波早年还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唐人密传故事》。王小波与鲁迅的区别在于,他将生命中宝贵的时间投入到他的唐人故事里,在十多年后重新选材、扩展成三个长篇:《万寿寺》《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质言之,《万寿寺》的成书历程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王小波的创作历程始终是探索的、不断发展的,直到他死前的短短几年才成型。再细分《青铜时代》内部的区别,从《寻找无双》到《红拂夜奔》,王小波越发沉迷于叙事本身,等到写《万寿寺》时,王小波就不再关心那些具体的故事,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业已成为“抒情”的叙事上去。[1]154可以说,“探索者”的形象始终与王小波紧紧缠绕,理解王小波的小说需要这一事实背景。
王小波是秩序外的探索者,《万寿寺》里的叙述者其实也有着“探索者”的影子。故事的叙述者在失忆之后重新阅读自己的手稿,故事就这样展开序幕,“我面前还放了一个故事。除了开始阅读,我别无选择了”[6]10。而手稿中的故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故事”[6]10,也正是验证了“我”的“探索者”身份,这是《万寿寺》的第一层“探索”。王小波为什么要将叙事者写成一个失忆者?王小波想要籍此达到的效果与他的“反现实倾向”是分不开的,因为在一种不确定的叙述策略下,色彩鲜明的想象才能插上飞翔的翅膀,读者在小说空间里才能做到举重若轻,释放心灵的重负。这种“反现实—元叙述—想象”的思路在小说中就表现为不厌其烦的故事改写,即“叙述者”始终不满意故事的结局,对之多次进行改写。小说里薛嵩抢红线的过程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里的薛嵩行动非常笨拙,惹得红线非常不满:“你难道连条正经绳子都没有吗……你真笨蛋——还敢吹牛说自己是色狼呢。”[6]45薛嵩被红线嘲讽得丢了面子,性格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紧接着在下一节中,叙述者就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薛嵩在水边截住了红线,红线很配合,薛嵩找不到棍子,用拳头敲红线,她顺势装作晕了。叙述者在这之后狡猾地说:“自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薛嵩在树林里遇上了红线。”[6]47三种说法,各不相同,让读者实在无从凭信,对于这种不确定叙事、“元叙事”,相信很多喜爱传统小说的读者难以接受,叙事者在说些什么呢?叙事者想表达什么呢?事实上,“表达什么”恰恰不是作者的重点,“薛嵩抢亲”的三种说法的结果都不美好,但是通过“抢亲”这件原始富有浪漫色彩的事情,反衬了生活真实的庸俗无奈。之所以用眼花缭乱的说法来表达,恰恰是用想象力来解构“庸俗”,达到举重若轻,逃脱现实逻辑的诸般限制和束缚,抵达纯粹的文学艺术之本真境界,[1]91从而发挥“无中生有的才能”[10]65,探索小说的“虚构之美”。
事实上,叙述者的“探索”视角不仅可从微观的“薛嵩抢亲”中找到蛛丝马迹,而且隐藏在作品的整体架构中。叙述者描述了多个薛嵩的可能,正像文中所述“我的故事重新开始的时候,薛嵩已经不是个纨绔子弟,成了位能工巧匠”[6]98。叙述者紧接着就对能工巧匠的薛嵩加以详细刻画,又写出一连串的“造囚车”的故事,以至于白衣女人朝他怒吼:“瞎编什么呀你!”[6]127
叙述者通过想象兴建“诗意家园”的深层动因可以在《万寿寺》的主人公薛嵩那里找到答案,因为薛嵩是个“探索者”,薛嵩生活在一个毫无生气的长安城,长安城的意象贯穿《青铜时代》三个长篇,《红拂夜奔》里的长安城就是压抑人性、无趣的代表,薛嵩的长安城也是如此,长安城上空笼罩着永不飘散的灰雾,不仅买不到漂白布,而且市面上最白的布实际上也被雾染成灰色。[6]14薛嵩却是个想做大事的人,所以买了官跑到湘西当节度使。故事的内层逻辑已经清晰,无论是叙述者还是薛嵩,都形成了“反现实倾向——探索”的线路,只不过叙述者停留在“想象”中,薛嵩却将“叙述者”的多种想象一一实践。
三、从“童年经验”到“诗意家园”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提示文学研究:想要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理念,其童年经历便不可忽略。现存的资料表明,王小波的童年确实有着不少独特经验,而且这些经验也在王小波的思想和人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至于王小平在《我的兄弟王小波》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王小波的童年和少年。房伟在用了《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命名自己撰写的王小波传,已经领会到了童年对于王小波的重大意义。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王小波生于1952 年,死于1997 年,他的生命是短暂的,那些传奇的、复杂的历史年代,像一条条激流冲刷了他流星般闪过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相形之下,晚年无从谈起,中年也显得无关紧要。
据王小波回忆,1958 年,他八岁时曾爬进大练钢铁时期的炼钢炉中,“等我爬了起来,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东西来……所以后来我一直以为自己体内长满白滑滑黏糊糊像湿棉絮似的东西”[6]183。王小波评价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反映,表面上一幅迟钝呆滞、老实忠厚的形象,但却有一颗敏锐丰富、悲观厌世的心灵。炼钢炉事件对王小波的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可以代表那种大跃进运动里的魔幻现实对人的戕害。从这里开始,王小波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湿被套”,黏黏糊糊,令人反感。这种情绪进而蔓延到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同样令人悲观厌恶。王小波在《万寿寺》中提出了“历史的脐带”的说法,万寿寺破败的景观令人直接产生的厌恶感让叙述者想到“老佛爷”和“历史的脐带”,令叙述者想到历史疲惫的本来面目,与那些发黄的陈旧纸张别无二致。[6]32此处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叙述者在《万寿寺》的结尾讲道:“当一切都不可挽回地沦为真实,我的故事就要结束了。”[6]246故事的结束,是真实的开始,故事与真实形成一种二元对立,叙述者在故事结尾不无惋惜地慨叹“不可挽回”,言下之意即:真实是更为沦落的、庸俗的。由此可见,成熟的王小波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念,这一独特的“历史的脐带”论来源于童年王小波的创伤经验,王小波在创伤经验的影响下选择了反现实的创作道路。王小平将这一事件对王小波的影响引向“神秘主义”,他认为王小波就在那一刻陷入了蛮荒气息的漩涡,里面充斥的当然是荒诞和怪异,但正是这种怪异荒诞使王小波抵达艺术的园地和抽象的彼岸。[9]53王小波与童年创伤、王小波与历史创伤,似乎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也有学者从一种“伤痕文学”“文革叙事”的角度来解释王小波,即便是上面所述黄平的《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仍然着眼于王小波与文革的关系,试图从“文革历史”对人们造成的精神伤害出发,指出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导向虚无和治愈。但是笔者认为,此条线索不能完全解释王小波。在童年的神秘主义氛围和创伤经验之下,王小波走上了一条“反现实倾向”的道路,王所目击的历史真相常常令其想起与美判然不同的“湿被套”和“历史的脐带”。因此,必须去寻找一种纯然轻灵的东西来洗涤沉重、迟滞和历史的伤口,用轻灵的想象去建造一种纯然的美,不再囿于现实的庸俗和丑陋。正像叙述者自己在《万寿寺》结尾所总结的那样:一个人的生命要有诗意世界作为依托,仅有此生此世的人生不够完整[6]246,也只有诗意的世界才能带给沉重历史的背负者轻盈与解脱。
王小平分析了王家的居住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尤为关键的一处是,王家搬到的“铁一号”院子正面有一座“西式钟楼”,王小平兄弟后来参与了钟楼冒险活动,“神秘而古怪的气息扑面而来,木头在脚下格格作响,以一种怪异方式割裂的空间一层层在眼前展开。”[9]23王小平对这次钟楼冒险看得很重,并且认为“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那些神秘的情绪实际上是处于萌芽状态下的情欲的隐晦表现”[9]25。显然,王小平也试图从钟楼和情结(弗洛伊德的术语)来阐释王小波的创作,“在他的小说《黄金时代》里,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钟楼情结”[9]25。回到文本不难发现,在《万寿寺》中也存在着钟楼意象。其一,凤凰寨是一个类钟楼的意象,凤凰寨的中心永远被绿色所充斥,到处是肆意生长的青苔,即便在房里仍然躲不过无孔不入的绿色光线[6]21,这当然是一个针对当代人生存境遇的微妙隐喻。叙事者对凤凰寨最为鲜明的感受就是古怪和奇诡,凤凰寨浸泡在一片绿荫里,绿色在日常生活中代表着健康,但是绿色无处不在,绿色充斥天地,于其中生活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压迫力可想而知。[6]22其二,凤凰寨并不完全等同于钟楼,凤凰寨是一个带有隐喻色彩的建筑,隐藏着王小波的历史人生观。凤凰寨不仅是座被单调绿色填满的神秘营垒,凤凰寨还是座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兵营,到处都是四方工整的帐篷以及棋盘一样刻板规整的道路,可以说僵硬无趣,更不必说在营地正中还住着一位丑陋的老妓女。这样的凤凰寨是叙事的起点,童年记忆里的钟楼体验已经淡了,凤凰寨展现的更多是文化的喻义:一方面是对极权统治下生命之单调与无聊的多维呈现,另一方面是对国人现实人生与历史境遇的寓言式书写。由此可见,特殊的童年体验是王小波日后形成自己风格的重要素材,一种奇幻的风格事实上与之早已产生了深刻的纠葛,王小波在他的写作旅程中选择唐传奇作为创作的源泉,可能是早已命定的渊源。
除此之外,王小平笔下的童年王小波还是个“玄想者”,经常“陷入一种与少儿身份绝不相称的冥想,好像是在试着引发什么事情,把握什么朦胧的线索,同时为那些难以参透的前因后果而苦恼”[9]19。童年王小波并不像小说中的多次出现的王二那么活泼,有时甚至会沉默寡言,“显得不合群”[9]14,是一副呆呆的样子。童年王小波是个“玄想者”,在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孤独的、胡思乱想的孩童形象是王小波的注脚,这个“玄想者”的形象必然还会继续延续下去。王小波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条暗线在游动——玄想,从琐碎小事,到爱恨情仇,建构起一个精致复杂的想象的“诗意家园”。
值得注意的是,虚构的凤凰寨、薛嵩、红线和妓女究竟会在现实的层面发挥怎样的作用?建立奇幻的富于想象的“诗意家园”又意义何在?有论者认为王小波的杂文比小说好,未尝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其实《万寿寺》的所展现的意义是多重的:其一,作为沉重的历史背负者,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脚步,摆脱沉闷的历史重负,回归真正的诗意世界,达到“轻逸”的境界。其二,在“诗意家园”的想象中恰恰形成了寓言式的效果,这正是王小波大力赞扬的卡尔维诺的写作,在小说中不追求批判,讽刺却往往犀利无比。其三,《万寿寺》这种精致的叙事和奇幻的想象构成了王小波文风的“虚构之美”,这种专注于“子虚乌有”的奇特美感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有其独特价值。
四、结语
黄平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梳理出了一条“历史创伤—反讽—自由—虚无”的线索。笔者试图在这些线索的基础上,结合王小波对于现实主义、历史真实和文学秩序的看法,指出王小波自身存在的“反现实倾向”。王小波所存在的反现实倾向并非空穴来风,这与他童年时期就彰显的个性,与他少时经历的“创伤经验”不无关系。正是一种对历史真实的反感情绪让王小波走向了体制之外,也让他远离了以鲁迅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正统文学秩序,这必然导致了一个可能:一个“探索者”的可能。如果说从“历史创伤”走向了“反现实倾向”,走向了“探索”,以《万寿寺》为代表的《青铜时代》的成书就贯穿着这一段探索的历程,这个历程里有穆旦、王道乾等诗人翻译家对语言的珍视,也有杜拉斯对小说结构的执着,还有卡尔维诺和奥威尔对艺术想象的钟爱。
“探索”对于王小波来说,并不仅仅是读万卷书,还是对想象的重视,伴随着对“诗意家园”的企望,一种虚构之美充盈在《青铜时代》里。这种对“诗意家园”的追求在万寿寺里表现为叙述者对故事的不断更改,这又是一种探索。小说主人公薛嵩更是一个“探索者”,从充满压抑的长安城内跑到凤凰寨去当节度使。种种迹象表明,“探索”与“想象”密不可分,作为“探索者”的王小波试图走出另外一条路——营造自己的“诗意世界”。因而我们也可以整理出理解《万寿寺》《青铜时代》和王小波的另一条线索链:“秩序重压—反现实倾向—探索—想象—诗意家园”。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写作虽然从“反现实倾向”出发,却并不意味着王小波的创作完全无益于社会,也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价值,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路径超越现实的丑陋表象,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真实而书写。
然而,理解了王小波不能证明王小波已经成为了“主流”,也不能证明王小波的文学遗产已经被人所接受。在消费对文学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今天,文化工业严重侵占了纯文学的文化领地,如《万寿寺》这样精致繁杂的文本是否还有读者真心喜爱,仍是一个亟待确认的问题。如果王小波不能像鲁迅等名家那样走入当代文学史的主流,王小波的作品又如何对后来人产生自己的影响?对一个“非主流”作家进行研究又该如何发掘其深层的价值,并建构超克以往文学史傲慢与偏见的新话语体系,这将是王小波研究要继续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