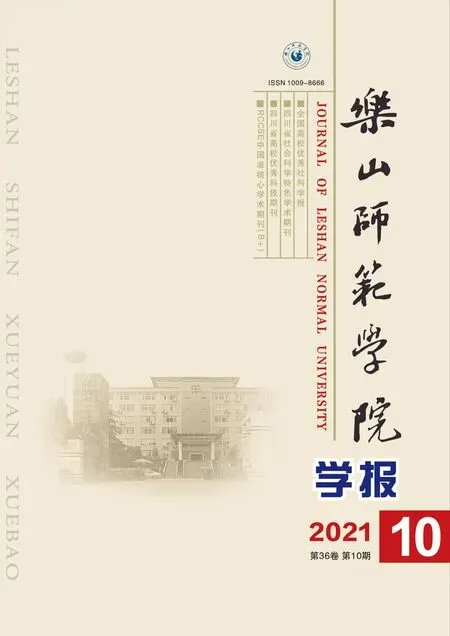孙复“尊王攘夷”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张 磊,陈力祥
(1.南昌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孙复,字明复,宋初三先生之一,曾因居泰山聚众讲学,学者习称之为“泰山先生”。《宋元学案》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1]1,又云“安定之经术精矣,先生复过矣”[1]73,足见其学术之功与道术之精。明复善治《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2]568,孙复认为《春秋》乃“圣人之极笔,治世之大法”[1]102,故而其着意“著诸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3]5359,形成了他特有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在晚年著录《春秋尊王发微》①一书,成为宋代《春秋》学史上的首座高峰,对宋代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一、唐宋变革与儒门重振
孙复生于公元992 年,其所经历主要在仁宗一朝。仁宗之世,在政治层面上的大一统局势已然形成:公元979 年赵宋攻克北汉,结束了中原大地自安史之乱后长达225 年的混乱局面,自此实现了军事意义上的统一;随后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4]9核心原则的指导下,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不断制定一系列制约文臣武将的“家法”,如设枢府、分三司,用台鉴风闻之策、创异论相搅之术、用募兵之法等手段,不断强化皇权,最终使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宋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全面彻底地构建完成,正如王国维所言:“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5]54,这一点亦得到李泽厚[6]55的认同。回观安史之乱带来的影响,不独是使得中原大地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政治无主与军阀混战,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打破了大一统王朝的固有社会秩序……因彼而就的往日纪纲伦常也随之崩乱失序”[7]28。就如傅斯年所言:“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8]45内藤湖南亦曾提出过“唐宋变革论”理论,他做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衡断亦可为本文借资以为佐证。尽管国内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过异议,②但是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唐宋间在政治领域表现出了贵族政治衰颓和独裁兴起的特征以及在文化领域表现出了士族文化的消亡与庶族文化的崛起特点。可见在一片“瓦砾”中实现文化的重塑、在一片新形式下实现文化的革新又是当时政治家与文人学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赵宋又面临着新的困境。首先,北宋外部所面临的艰难处境,直接影响着宋代在进行文化重建时不能再单纯地复制唐时的轩冕,唐王朝的文化是一种“宽容开放、驳杂纳异”[9]27类型的文化,秉持着华夷一家的观念。但是这种四海一家的良好态势却是建立在对外战争屡屡获胜的基础之上,据傅乐成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初年至玄宗天宝年间,外族威服于唐室的人口保守估计约有170万人。[10]357-358对外战争的大获全胜自然滋养了汉民族在对待其他少数民族时态度上的和谐顺畅,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吐蕃、南诏的相继入侵,便激起了国人对外族的仇视,及至北宋时期,这种在国人心中累积百年的积怨似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种高潮之下却恰恰是北宋王朝遭遇契丹、党项侵扰时的屡屡失利,面对此等纠扰,更加敦使着北宋学者在文化层面需特意强调自强。
政治上过分强调权力集中,并不惜以“利欲”淡化臣僚之“权欲”,这种“以富兼人”[11]117的御人手段不可避免地会在官场和社会中蔓延出低迷享乐的流弊,无形间走向“自强”的对立面。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人生如白驹之过隙”之言,劝石守信等人“择便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12]11-12,这无疑是开启了宋代官场消极作为、安逸享乐之风气。至于后来“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13]83的景象,不绝于世,悉以为平常。北宋皇帝对臣子的统御不仅是在利益上的笼络,更有在精神上的钳制。北宋帝王常常借各种机会鼓吹隐者风采,《宋史·隐逸传》所收入的49 位隐士当中,被荐被召过的隐士就有28 人,对于应召而来的隐士,帝王皆礼敬之,如太祖、太宗待陈抟犹帝王师,真宗更是手携大隐士种放共登龙图阁。不可置否的是这种“尊隐”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息贪竞、淳风俗的功效,但更多地是带来了官场上的因循无为和社会群体的钓名射利。
与官场糜弊风气相应和的是佛老思想在文化界的广为流行,“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14]198。太祖兴隆元年长春节“诏度童子及行者八千人”,随后“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元年,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复兴龙兴寺、立开先殿,又在寺庙西址设立译经院。译经院作为国家经营事业,新译出的佛教经典达六百余卷之多,且多数开版流通。③译经业与印经业的发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思想风气,又在某种程度上崇长了这种风尚,遂至于“士大夫好禅”[15]67已然成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
这种儒门重振契机的背后,实际上更是对当时儒者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六朝五代的断续中实现破立与精神存继,挽儒门于殆危?如何为统治者提供掌权的理论需要,以实现“奖王室,尊君道”?又如何扫灭废惰之积弊,使朝士以天下为己任进而攘斥异族的张目?成了当时心怀天下的读书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面对此等复杂的境况,“便为灰烬亦无辞”的孙复“不惑传注,不为曲说……考时之盛衰以推见王道”[18]389-390,以《春秋》为基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伦理思想。以《春秋》为基凸显了他尽心于圣人之道的本色;“尊王”之意乃在于重振纲常,以祛“五季之极弊”[19]759;“攘夷”即则在于“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20]79,严守华夷之辨以自强。而三者的结合又是“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必皆临事撅实,有感而作”[21]294的践行。
二、王权挺立与正以王法
孙复《发微》一书,将“尊王”二字列入书题已然指明关键所在,前人虽对《春秋》一书中的“尊王”思想亦有发挥,而递及孙复几乎势成极端。作为其著书的思想核心,孙复言必称尊王,但通观全书“尊王”的含义却绝非单一所指。
孙复在书中曾言:“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22]卷一1 可见孙复之“尊王”的首要含义便是“尊君”。在这一点上,孙复曾不遗余力地进行过细致阐释,如:
《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发微》言:“王人,微者也,序于诸侯之上者,《春秋》尊王,故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也。”
孙复认为“王人”虽身份卑微,但因受命于王,故而可以“序于诸侯之上”[22]卷五8。对于“王人”之理解,孙复并无过错,如杜预曾言:“王人,王之微官也。虽官卑,而见授以大事,故称人而又称字。”[23]89孔颖达疏引王肃云:“王人者,犹君人也。”[24]887可见“王人”确实乃担任天子使臣却又身份低微的人,但是他所特重的“序于诸侯之上”是否真是出于“尊王”的意图却是有待商榷。因为“尊王”的具体展现并非仅仅是对君王的尊崇,更是一个系统化的秩序规范,诚如襄王所言:“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馀,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25]51-52而“洮之盟”虽将王人置于尊位,但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的位次却并不符合当时礼制④,综合桓公行霸、甯毋之盟常会者不至以及陈蔡遣世子而来得历史背景,不难看出此时的王人衔王命南面而受,与其说是“《春秋》尊王”,毋宁说是“(桓公)假王人之重以自助”[26]212。凭孙明复之学能养识,非不能窥得其中机楗,而仍旧以“尊王”之语释之,虽有矫擅之嫌,但亦足见其操持尊君之切。
孙复在《发微》一书中关于“尊王”要义的阐发是多方位的。除上文所提及的对“尊君”的奔忙之外,尚体现在他对“《春秋》有贬无褒”的认识与发挥上。孙复认为《春秋》之所以自隐公始,乃因天下无王而频出“变礼乱乐”“弑君戕父”“征伐四出”等现象所致,孔子作《春秋》正是对此二百多年间不正之事的口诛笔伐,并以此来申明大义,即“孔子作《春秋》专其笔削,损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22]卷二13。所以在孙氏看来经文中所隐含的“贬斥诸侯”乃“圣人要旨”,不可不发,故在《发微》一书中诸如“言……以著其恶”“……之恶,从可见矣”“……以诛其罪”“……其恶可诛矣”等语比比皆是,而对经文的解释,亦十有八九落脚到“彰其恶”“诛其罪”的结论上,这一改以往注疏风格,乃孙复独出手眼之所在。如:“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历代注疏均强调“世子贵也”[27]217“天子世子,世天下也”[28]117,以体现对王世子郑的尊崇,《发微》亦言“后言会王世子以尊之,尊王世子”[22]卷五6,可见孙复对前人的注疏的吸收与借鉴。但孙复又言“所以重桓之恶也”[22]卷五6,以为凭王世子地位之尊崇根本就不能够被齐桓公组织参会,其召见王世子本身就是一种僭越,而在这种僭越基础之上的尊荣只能凸显桓公恶之重。站在客观的历史情形下而言⑤,孙复的结论难免略嫌苛刻,但就是在这种“尊”“贬”之间却无疑将君王的独特地位超拔地提升了起来,甚至将其政治身份与地位塑造为独立与绝对,且与其政治能力与作为无涉。
孙复作为一位儒者,他眼中的春秋是儒家眼中的春秋,他深深地意识到单纯地强调君王地位之尊,是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儒家政治理想的达成似乎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即“名分”与“善政”。尊君是儒家名分观念的体现,而善政则主要体现在对王道政治的推崇,前者关涉社会秩序稳固,后者则关乎政治理想的具体践行。这就引出了孙复“尊王”思想的第二重内涵:“尊王道”或言“尊王法”。孙复在《发微》中亦有表述,如孙复曾频数提及“故孔子从而录之,正以王法”便可引以为力证。然而,如果说“尊君”的目的是将君主的地位凌驾于王朝政治的框架之上,为君主获得绝对的政治能量提供保障;那么“尊王法”无疑却是将君主又置于了王道政治的框架之内,对君主的个人行为和意志实施监督,所以“责君”便成为了“尊王法”的实质内核。在《发微》一书中孙复便不乏责君之语:
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
《发微》:襄王也。周无出,此言出者,恶襄王自绝于周,则奔也。其言居于郑者,天子至尊,故所至称居,与诸侯异也。
周天子乃天下之所有者,天下乃周天子之私有物,故周天子无论行止何处,都不该言“出”。而此处仍以“出”言之乃是“圣人要旨”,即圣人“恶襄王自绝于周”[22]卷五18,是对襄王不能施行王道的贬斥。若是进一步探讨襄王不能施行王道的原因,孙复认为是“自绝”,也就是自己遭成的。按照孙复的逻辑理路,由于君主地位的绝对性,使得王朝兴衰系于天子一身,因此“周室不竞,干戈日辱”[22]卷一16的局面,一定程度上看来皆为君主一人所致,虽然孙复未能确切且详细地提出君主所应“尊王法”的具体内涵,但是也逃不脱儒家的政治理念,况且这种身系天下安危的巨大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足以引起帝王的警醒。即便如此,圣人仍因“天子至尊,故所至称居,与诸侯异也”[22]卷五18,这又从根本上维护了君主身份的尊崇。由此不难看出,孙复所认为的君主地位是绝对超越且独立于政治作为之外的,必须无条件地认可与尊崇;而“责君”又体现为一种责任使命的内在驱动和自觉生发;从而使君主制度既获得了外部维护又具备了内部规制。
孙复有感于晚唐、五代的政治乱象,提出了“尊君”与“责君”的政治伦理思想,将君主权威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君君臣臣”纲常伦理次序,可以说是在学术层面对北宋大一统政治的声援与支持。与之相应的是孙复亦对君主集权有所忧思,故而他在“尊君”的基础上提出了“责君”的主张,赋予了君主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希冀君主能自觉担当。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责君”的约束在“尊君”的权威面前会尤显乏力,没有制度层面的制约而单纯强调心性的自觉未免显得太过理想化。但是若站在孙复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出发再去探讨这一问题,或许我们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首先,北宋初期朝局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并非是君主荒淫滥政,而是要力祛五代乱象的延宕,故而“尊君”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务实且实际的;其次,就儒家精神而言,儒家之学本身就是为己之学,而“责君”亦旨在强调为己自觉,这和孔孟之学一脉相承,而在一位笃信孔孟的儒者看来这种规制恐怕是最根本与紧要的,故而从学理上讲亦无可厚非。所以孙复之得失,非一人之得失,乃历史之长短,同时孙复的这种强调亦成为了宋明理学心性思潮的发轫。
三、攘夷自强与文明担当
“王”作为一个政治思想范畴,在不同的对应关系下,其内在含义会不断发生变化。就华夏内部而言,“尊王”强调的固然是君臣关系;而就华夏外部而言,“尊王”则更关注的是华夷之辨。因此就某种层面上而言,“攘夷”始终是与“尊王”相互联系的。
而“孙复《发微》一书以‘尊王’为核心,无论是从‘尊王’含义的推衍还是从北宋现实政局的关照,都会自然而然的涉及如何看待华夏与夷狄的关系问题。”[29]59孙复在《发微》一书中大力宣扬华夷有别,其态度可略见于以下三事:(1)隐公二年,隐公曾两次与戎会盟。孙复便感慨道“圣王不作,明堂失位”[22]卷一3,并连用“尤”“甚”等词表现他对“与戎盟”的愤慨之盛与批评之烈。(2)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伐鲁,公子遂如楚乞事。“孙复认为‘鲁不能内修戎备,而外乞师于夷狄’,故《春秋》直书其事以‘恶’之,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孙氏自己的态度,即以乞师于夷狄为耻、为恶。”[9]95(3)僖公二十八年,齐、晋、宋与楚、卫、鲁相抗,鲁公子买不卒戍,僖公杀公子买以悦楚君。孙复认为是“内残骨肉,外苟说于强夷”[22]卷五20,后世势必要“以著其恶”[22]卷五20。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孙复严防华夷的强烈态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孙氏为分辨华夷不惜忽略客观史实,如:
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与盈,执宋公以伐宋。
《发微》:宋襄合诸侯于盂以致楚子,楚子怒,执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子执宋公以伐宋者,不与楚子执宋公以伐宋也。故以诸侯共执为文,所以抑强夷而存中国也。
在此条经文的解释中,我们便可发现,尽管孙复承认宋襄公的狂妄自大是此次不义之战的直接诱因,且宋襄公“合诸侯”“致楚子”亦属于不尊王命的僭越行为。但是考虑到夷夏问题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影响,他又不得不舍弃客观立场以维护价值观念而刻意曲笔。这几与《公羊》“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20]79同义,这也体现了孙复“比较倾向于《公羊》学”[30]41的主张,而《公羊》学的特征又是立法当代、内华外夷。孙复除了在《发微》一书中严防华夷之辨外,还积极褒扬攘夷之功。尽管他对齐桓公、晋文公在僭越之事上并不抱有友好态度,并不惜在《发微》中多番批评乃至痛斥其为“恶之大者”,但是在对二者能够免夷狄之祸乱、救中国于困危上却大加赞扬,言之曰:“截然中国无侵突之患,此攘夷狄、救中国之功可谓著矣”[22]卷五4-5,“孔子遽书爵者,与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不旋踵而建也”[22]卷五21。然而,这其中仍有幽微以待申发:诚如上文孙复提倡“尊王”,“攘夷”又是“尊王”逻辑的延伸,但他又因“救中国之功”而盛赞有僭越之嫌的齐桓、晋文,那么孙复此一做法就意味着默许了不“尊王”亦可“攘夷”的做法,这一默许无疑是对“尊王”宏旨的一种戕害与削弱,这是逻辑矛盾的。但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上言,也可以说孙复是务实的,他并没有拘泥于一套成法,而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其立言立论的根本。
究其孙复对夷狄深恶痛绝的缘由,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吴楚僭极恶重”[22]卷七11、不尊王化。但这也意味着孙复所认为的华夷之辨,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也非是血缘或地缘标准意义之上的,而是以文化礼制为矩镬而进行区分的,并可以通过后天的文明浸润加以改造。如孙复认为《春秋》中对楚国称呼变化之始末,便可体现了此中涵义:
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庄公二十三年,别人来聘。
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许穆公。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楚人救卫。
孙复认为圣人之所以对楚国的称呼实现了由“荆”向“楚人”的转变,其根本原因是“以其能慕中国修礼来聘,少进之也”[22]卷三15-16,遂至后来“以其渐同中国与诸侯会盟及修礼来聘,称人少进也,称子复旧爵也”[22]卷五16。这也辗转说明,在孙复眼中“中国”或言“华夏”并非是一个封闭的政治利益共同体,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联结体,孙复极力奔走呼号攘夷的内在原因也并非是单纯民族本位的拒斥与排外,而是因为夷狄的蛮横往往会对华夏文明与华夏子民造成深重灾难,这种灾难一则是对百姓生命的褫夺,再则是破坏了历史文明的进程,是一种血腥的倒退。但是一旦夷狄有意改变本身的暴虐,愿与中国修好,我们都可以给予最大程度的谅解与认可。在这一点上,就其精神气韵而言,赵宋可谓未改盛唐本色;而就其哲思理路而言,孙复也确是保有并继承了孟子“用夏变夷”[31]147的思想内核。
反观夷狄可以进为华夏这一逻辑的背后,其实也向人们昭示着华夏亦可以退为夷狄。如“秦不顾人命,见利而动,又起此役”[22]卷六8,孙复认为秦国不听王命、不受王制约束的行径乃“夷狄之道也”[22]卷六8;除此“不尊王”的行径之外,孙复还认为“背华即夷,与楚比周”[22]卷八3亦“故狄之”[22]卷八3,即与夷狄为伍,也已经超出道德文明的底线,是为文明向野蛮的屈从与却步,亦足以成为被世人大加鞭挞的对象。对于孙复的这种致思理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简化为对封建王权的捍卫和面对外来入侵的不妥协,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坚守与责任感,以及对个人人性品格的高度要求。“攘夷”在某种程度上攘去的是野蛮与内心的私欲与不文明,这与后来的宋明理学所积极倡导的天理人心工夫论何其统一。
由上述分析可见,孙复是从华夏进退两个维度来构建其攘夷思想的。仅就夷狄可以进为华夏而言,孙复是想通过夷夏之分,鼓励诸夷修中国之礼,慕中国之举。然而仔细分析北宋王朝的实际境况不难发现,这一逻辑进路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北宋的国力决定着赵宋一朝很难像盛唐一样威服天下、德治万邦,而德治教化的首要前提往往是威服,这就意味着在敌对情势中处于不同文明制度下的夷狄要接受华夏文明从而进为华夏的道路进程基本是堵塞的。所以,孙复的华夷之辨对外而言,其首要意义仍在于攘夷狄与救中国,这是符合北宋实际与需要的。而就中国内部而言,华夏退为夷狄其意义则在于敦使朝臣万民不断顺应王道、遵从王制:一方面要“反对非天子而执‘礼乐征伐’权柄”[32];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以价值观念为纽带来团结民众共御外辱,这是儒者自身文明责任感使然,也是儒士气节的展现。因为毕竟在孙复的理解中华夷之别是文明观念的“有道”与“无道”之别,而此二者正是“道”与“不道”的分水岭,这也正与其“尊王”思想遥相呼应,符合北宋时期的政治诉求。
四、孙复政治伦理思想的意义及影响
孙复“尊王”思想的提出是对彼时社会政治文化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尽管其致思路经与逻辑展开仍有不到之处,如未能圆满处理“尊王”与“攘夷”之间的潜在矛盾,亦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对君主权力的有效规制等。但这却无碍于其深远意义和对当时现实影响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就实际功用而言,孙复的这种思想完美地顺应了北宋初期的政治需要——中央集权与攘御外辱,直接奠定了赵宋一朝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走向,而这一顺应的背后带来的显著效益便是儒门再次受到了北宋帝王的青睐,为儒门重振提供了政治保障。其次,就文化意义而言,孙复的尊王思想也是对既往儒学精神的继承与改良,一方面强调责任的自觉与担当,一定限度内扭转了官场因循之风,也对佛老之学给予了颇有力度的回击;另一方面注重秩序的规范与有序,在社会观念层面强调法则规制的培养,而这两种精神又不断地反哺于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了两宋制度森严而又强调有为的政治风貌。最后,孙复尊王的思想无疑对今后的两宋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孙复的“责君”思想尽管在孙氏理论中其内涵尚局限于君主的自我约束,但是随着士大夫精神的不断显扬,“责君”的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君主本身,而是成为了所有士大夫共同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君与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开始形成,这也成为了宋代政治的最大特色。另外,强调“攘夷”思想:一则呼号“攘现实之夷”,提振了华夏人民抵御外侮的士气;再则自觉“攘心中之夷”,其中所谓“夷夏进退”观点也被持续保留了下来,并进一步学理化,成为两宋乃至明代文化的思想主题与重要工夫论,即如后来阳明所说的“破心中贼”。
注 释:
①孙复平生事迹交游多扞格不显,甚至对其著述详情亦多含混,据载孙明复平生著述颇备,有《春秋尊王发微》《春秋总论》《睢阳子集》《易说》等多种论著,而今除《春秋尊王发微》留世外,其它多已散佚,仅有部分篇章辑佚为《孙明复小集》,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尽管《春秋尊王发微》保存相对完好,但后世学者对该书卷数仍有争讼,目前学界主要集中于三种观点:“十七卷说”“十五卷说”“十二卷说”。(参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版;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1984 年版;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葛焕礼《孙复生平事迹及著作考辨》,《中原文化研究》2016 年第6 期。)
②很多大陆学者对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开端说”持有审慎态度,如胡如雷先生就认为唐宋间的巨变只是封建社会前期与后期的转化,并不是社会形态的转化;张其凡先生则认为唐宋之间是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化的时期,亦并不牵扯社会形态的转化。(参阅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版;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1 期。).
③按:“长春节”是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至开宝九年(976 年)间庆祝宋太祖赵匡胤诞辰的节日。“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元年”书中原文作“宋高宗于太平兴国元年”,“高宗”疑为“太宗”之误,故改。(参阅野上俊静《中国佛教史概论》,(释)圣严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第125-128 页。)
④按:自春秋早期至晚期,诸侯之爵称是基本固定不变的,如“宋”一直称“公”,“陈”、“蔡”一直称“侯”,“郑”一直称“伯”,“许”一直称“男”。唯“楚”的称号有所变化,这是因为春秋后期,“周室既卑,诸候失礼于天子”,这些实力强的诸侯国君开始僭称“王”。同时,在春秋经传对各诸侯国国君的称谓中,自始至终基本都带有以上的爵称,瞿同祖先生对这方面有详细的整理,并由此认为各国爵位基本是固定的如“宋永称宋公;齐、鲁、卫等永称为侯;郑、曹、秦等总是称伯;楚、吴等国总是称子;许永称为男”。目前从春秋文献记的内容来看,这个结论是完全可信的。既已如此,洮之盟之位序当为宋公、齐侯、卫侯、曹伯、许男,而实际却与之不符,足可见当时社会秩序之崩乱。(参阅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1页;刘芮方《周代爵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1 年,第75页。)
⑤按:公元前655 年,周惠王在位,王世子郑是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周襄王,而周惠王之后则宠爱郑的弟弟带,劝说周惠王废郑立带为太子,周惠王欲废之。此次齐桓公召集诸侯与王世子郑会见,是为了支援他并商量如何平定周王室内部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