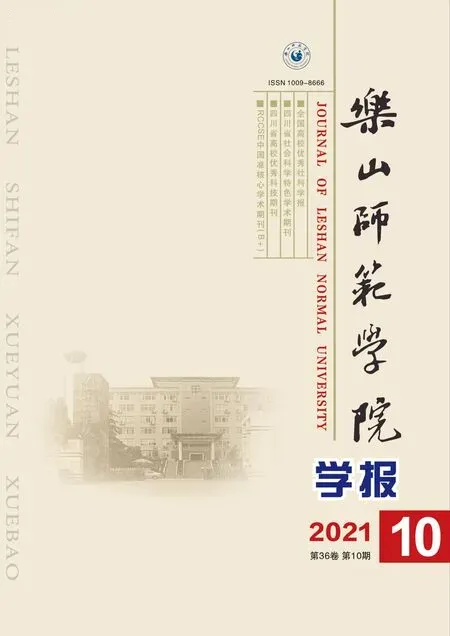“白衣天使”的阈界书写
——林浩聪《放血与奇疗》中的医学人文
温晓媚,刘玉梅
(1.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2.岭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
短篇小说集《放血与奇疗》是加拿大华裔作家林浩聪的处女作,2006 年首次出版即摘取了加拿大文学大奖——吉勒奖(Giller Prize)桂冠。该小说集共有12 篇故事,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深刻而有意义,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表面看来好像是纯医学、实际却是富有寓意的世界。”[1]25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放血与奇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族裔文化、叙事策略和译介研究三方面。国外学者则侧重作品介绍和作家访谈,稍微涉及对书中生命伦理的探讨,而本文则从阈界这一过渡性空间视角切入,不仅丰富人物形象,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故事情节和作家创作意图的理解,为该作品后续的空间研究抛砖引玉。阈界(threshold)最先起源于人类学中的阈限(limen),后者更多指的是一种非此非彼的状态,而文学中的阈界则是具有过渡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的空间。通过分析医护人员斯里,菲茨和陈的身份阈界、意识阈界和身体阈界,分析他们在其中面临的精神斗争,道德考验,以及生死抉择,最终揭示其职业素养,个人品行和人生信念。林浩聪也得以向读者展现其医学人文关怀,即对人体及人体病征的关注,以及对当今医疗行业现象的分析和建议。
一、“白衣天使”的身份阈界
阈界最先源于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过渡礼仪》(The Passageof Rites,1908)中的阈限。范热内普认为个体需要经过前阈限(分隔)、阈限(过渡)和后阈限(聚合)三个阶段才能进入社区生活;凡是从此地域去另一地域的人都会有如下特别的体验:游移于两个世界之间[2]14。而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则认为阈限的适用范围甚至可以拓展到一系列社会、文化和个体心理现象的研究中,以及个体从一状态到另一状态的转变中[3]256。特纳认为阈限或阈限人(“门槛之处的人”)的特征不可能是清晰的,他们即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4]95。由此可见,阈限更多的是一种状态,而阈界则是一种空间概念,可以生发出更多其他类型的空间,如具象的、认知的、表现的,甚至是批评的[5]xviii。它具有模糊性、过渡性、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的特点,此时此刻缺乏清晰,无法界定[5]xvii。
《放血与奇疗》中的医护人员斯里,游走于医生与朋友之间的身份阈界,他在诊断病人的时候犹疑于医生和朋友身份之间,此处斯里陷入能否成功克服“反向移情”的精神困境。在《温斯顿》(Winston)中,斯里碰上22 岁的病人温斯顿,后者认为自己因为在一场派对中被楼上邻居下毒而出现幻听和妄想,终日惶惶不安。斯里在刚接触温斯顿时给出了专业的医学判断,他说:“我们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甚至疾病,也会影响思维。有人以为生病就是一种中毒……有时,我们没发现毒药,就是看病罢了。”[6]95他对温斯顿的第一诊断是精神病初发期,但在听了温斯顿对自己病情义正言辞的解释后,他又作出第二诊断——甲亢和中毒综合征,这引来了自己导师米尼亚迪斯医生的嘲弄,后者认为斯里作的第二诊断有失专业性,是受病人影响的结果。尽管如此,导师仍然鼓励斯里仔细检查,查明真相,“两难啰,又要建立友好关系,又要措施得当。不过,千万别把假的当真的说来说去。”[6]99遗憾的是,斯里仍然无法确定温斯顿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病,甚至怀疑有一种新的、能够使人短暂失忆且失眠的合成毒药。
身份阈界中的个体处于非此非彼的状态,这意味着斯里无法界定自己作为医生和朋友的身份。斯里在医生与朋友的身份阈界中挣扎,这种非此非彼的状态使其犹疑不决,无法果断地对温斯顿的病情作出诊断。斯里与温斯顿第二次见面时,本已确定后者乃精神病初期患者的斯里犹疑了,觉得自己“应该在谷歌上搜索一下‘娱乐性健忘症’”[6]106。此时,斯里的医生身份受到了朋友身份的干扰,陷入了身份阈界当中。在这一次见面之后,斯里甚至为温斯顿做了医学检索,想找找这类中毒综合证的病例,结果一无所获(事实上,温斯顿患的就是精神病)。斯里对身份的挣扎影响其医学诊断,“斯里对自己说,这明显就是精神病”[6]123,但他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直觉低声说,斑马(即毒药)确实存在……”[6]123显然,斯里在医生和朋友身份之间犹豫不决。他一方面同情和担心温斯顿,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想诱导其接受精神病治疗而“有种罪恶感,觉得自己在用套索往温斯顿头上抛”[6]108。
身份阈界中的个体会产生焦虑心理。罗洛·梅认为,焦虑是人的某种重要价值受到威胁时产生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它是非特定的,模糊的,无对象的(并不针对特定个体)[7]172。斯里身份的模糊不清使整个医疗过程面临失控,这让他因为自己无法给出明确的医学判断而产生焦虑情绪,“状况不明或失控,二者之一均可接受……可二者凑到一起就令他心烦意乱了。”[6]124最终,斯里决定前往温斯顿住所,了解温斯顿被邻居下毒的来龙去脉。途中,他想到“反向移情”,“老师说过,要提防反移情,当心对病人动真感情。”[6]125在见到温斯顿口中的楼上邻居“阿德里亚娜”,确定了前者的确办了场派对以及有一个名叫“克劳德亚”的女性室友(并非温斯顿口中女子的丈夫“克劳德”)时,斯里开始警惕,暗暗觉得温斯顿也许真的被下毒,担心自己此前对斯里的精神病诊断出现失误。直至二人到达温斯顿家中并见证后者的精神崩溃后,斯里才最终确定温斯顿的病情并报警,而后又为此感到内疚与难过,可见斯里仍然在医生与朋友身份之间犹疑不决——他最终还是未能跨越身份阈界,又或许他已经明确自己的医生身份,却仍然深受朋友身份的影响。
一旦摆脱不了身份阈界带来的身份危机与焦虑情感,医护人员就无法保持自己专业的医学判断,最终将在医学诊断上优柔寡断。林浩聪认为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病征来考虑多种患病的可能性。不适与病征相伴而生,在某些情况下病征就是在不适中诞生的;病人会产生惊喜,焦虑,甚至恐惧的情绪,病征的消极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的本质,还在于它们对病人的影响[8]119-120。斯里不仅考虑到病征对病人的影响,还考虑到病人的病征会否构成他人生命的威胁,这一点显然是作者欣赏之处。林浩聪曾经在访谈中提及自己在倾听病人病征时就像在听故事,在明白病人的症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给故事一个结尾,让病人了解自己病征的潜在危害,然后为病人提供合适的治疗[9]。阈界或阈界状态是短暂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对个体而言,我们发现它并非是固定的,过去就过去了,而似乎有着反复出现或同时存在的可能[10]7。因此,医生有可能会时刻因“反向移情”而陷入阈界状态。林浩聪在《放血与奇疗》出版不久后接受了一次采访,他提到每一个医学院学生在正式成为医生的过程中都会变得与过去的自己有点不同。每一个医学院学生都想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出发点本身是好的,但是,“在医疗训练中最基本的其中一条道理就是:尽管作为个人必须得具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则需要‘冷眼旁观’(observe with detachment),就算情绪波动再剧烈也得保持头脑冷静。”[9]唯有如此,医生才能保持医学判断的科学客观性,为病人提供最合适的医疗服务。
二、“白衣天使”的意识阈界
意识阈界是由于社会背景、历史环境、文化素养等主观或/和客观因素造成的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对事物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矛盾的言行,形成冲突的潜在文本世界[11]73-86。在《艾里》(Eli)这一故事中,书中的另一位医护人员菲茨游走于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意识阈界,非正非邪,“善恶一念间,我们在医学院上都明白。”[6]135菲茨在治疗被警察胁迫的艾里的同时,又以旁观者和玩乐者的姿态陷艾里于不义,最终作出与“白衣天使”相违背的行为,也与自己曾经为人服务的人道主义理想渐行渐远。
阈限或阈限之人(“门槛之处的人”)的特征不可能是清晰的,他们即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4]95。进一步地说,在意识阈界游走的个体具有模糊不清的意识状态。在《放血与奇疗》的开篇故事《医学院入学秘籍(一)》(How to Get into Medical School,Part I)中,菲茨和明谈论各自当医生的理由,“他们一致认为,其他人都动机不纯,当医生只为了名利双收。而明和菲茨杰拉德则不然……学医是出于服务、人道和给予的目的。”[6]9然而,在《艾里》这篇故事中,成为医生后的菲茨似乎把行医当成了一种例行公事,抛弃了最初的人道服务精神,开始逐渐显露自己的阴暗面。在《医学院理想主义的命题》一文中,霍华德·S·比彻和布兰奇·格尔指出医学院“学生们早些时候曾期望,一旦他们进入了临床学习阶段,他们就能够学会那些有益于病人的东西以实现他们理想主义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只是为了把病例理解为医学问题,而并非为了帮助病人。”[12]168在对艾里伤口进行检查和清理时,菲茨的确是在承担自己的医疗职责,但一切似乎只是医理常识的实践,而非对病人的关心:
老师教过,坐在病人身边,显得你愿意花时间,你关心他们……缓慢响亮的讲话既可以抚慰病人的不安,又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医学上,我们假定,医生的名字能够控制局面……我学过,医生绝不应该割伤自己。工具是用来在病人身上刺、戳啊,或划开表皮的……把自己弄伤才叫罪过的暴力呢……我用肘尖抵着他的胸骨,这么做不会留下什么瘀伤,我们通常会用这种疼痛法将人从昏迷中激醒。[6]135-143
根据霍华德·S·比彻和布兰奇·格尔的观察,医学院“学生的思想中有了太多的玩世不恭态度,他未能足够地把病人当作人来对待”[12]168。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菲茨身上——菲茨把艾里比喻成牲畜,“我用压舌板拨开他的嘴唇,就像翻开马的嘴唇看马齿,齿龈完好”[6]146。在给艾里缝合脸部伤口时拒绝为其使用麻醉剂,而且选择用于做头皮和腿部缝合的缝合器,这显然不符合医疗规定。“缝合器的缝合相当粗糙,订针拆线后,会留下铁轨般的齿印。”[6]143缝合期间,艾里因为疼痛不已而激烈反抗,菲茨竟如同权力支配者般让警察按住艾里,“一旦他们知道谁是老板就好办了,就像驯马——老师就这么讲的。力大势不亏。手脚全按住——看看谁说了算,到那时他们就不再反抗了。”[6]142此时,菲茨处于正邪的意识阈界当中,他并非完全正义与善良——他抛弃了自己的人文关怀;但他也并非十足的邪恶——他至少还会为艾里检查和清理伤口。再后来,因为警察突然松手,艾里咬了菲茨的手背,使得菲茨怀恨在心,便在艾里脸上多订了两下以解心头之恨。
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说过:“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治理疾病,而一名伟大的外科医生则治理患有疾病的人。”[13]1这说明医生要对人体保持敬畏之心,与病人交流并与之建立互信,才有助于后续的治疗。显然,菲茨与艾里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医患之间的互信关系。交流与信任是建立健康医患关系的最关键因素;病人期望医生能够拥有同理心,医生也同样需要病人的信任[13]1-2。而且,有效的交流能够保证后续治疗的质量[13]3。然而,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常常带有哄骗性质,作为弱势主体的病人没有主导权,无法为自己发声[14]156,换言之,医生在治疗病人时如同掌权者,他/她可以掌控病人的命运,这体现的正是医疗行业中的灰色地带。从故事开头,菲茨就一直享受操纵一切的权力快感,因而并未用心与艾里交流以取得后者信任。在被艾里的言行冒犯后抛弃自己的医德,在知道警察对艾里滥用暴力时听之任之;更有甚者,菲茨除了陷艾里于不义,也陷警察于水火之中——他故意在艾里病房留下剪刀,以便艾里能够事后对警察进行报复。游走于善恶意识阈界中的菲茨并非丧尽医德,但也并非称职守纪。
通过描写菲茨的意识阈界,作家林浩聪暗示了医学院教育的重要性。首先,医学院的教育需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与态度[15]8。学生在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立场时,事实上还依赖于他们头脑中的其他人,也许是外行的公众,其他学生,又或是自己的导师[12]172。因此,医学院中受到的教育,尤其导师的教导,无疑会影响学生的医学实践。斯里的导师——米尼亚迪斯医生能够在斯里迷茫时鼓励他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而菲茨的导师在医疗教学的过程中处处透露出自己对人体的轻蔑与侮辱,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菲茨的玩世不恭,以致后者随意逾越善恶边界,对人体丧失敬畏之心。“虽然学生会认为,他不关心某一特殊病人独有的个人问题是正确的,也是科学客观性的表现,但外行人会把这种客观性认为是铁石心肠的冷漠态度。”[12]172也许菲茨以为把艾里当作牲畜毫无不妥,但在大部分读者看来则是有违医德的,是医者仁心失落的表现。医生的专业性会在追逐名利、成就、权力和金钱中丢失,医生想要拥有专业性,但通常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专业而已[15]37。菲茨的玩世不恭正是体现在与伤患和警察的权力角逐中,最终也因而丧失对职业与病人的敬畏。作者林浩聪借此道出了医学院教育的弊端以及医患交流互信的重要性。交流技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生疏,因此,医护人员必须持续进行交流技巧的训练[13]4。不仅如此,林浩聪也揭示了当今医护人员面临的困境:行医过程中,并非所有病人都能让医护人员与之自在相处的(如故事中的艾里),届时,医护人员是否还能有效与病人沟通并取得后者信任?是否还能客观对待病人并承受住道德的考验呢?
三、“白衣天使”的身体阈界
身体本身带有阈界性,是自我和物质世界之间的门槛[5]xix。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他的著述《可见的与不可见的》(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1964)中提及,有感知的身体既是施事者,也是受事者,既可触摸,也可被触摸,既可看,也可被看,可重叠或被入侵,所以我们必须说,事物穿过我们,我们也穿过事物[16]123。换言之,身体是开放的、联系的,有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生理和心理实体),而且总是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中[17]12。福柯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1995)中提及历史学家对历史人口学或病理学领域中的肉体的研究。他们把肉体看作是心理变化和新陈代谢之所,细菌和病毒的侵害目标[18]25。小说集中的《传染追踪》(Contact Tracing)正好与病毒有关,它以“非典”(SARS)为背景,故事中,菲茨因为感染非典而被隔离,在其病情恶化之时,另一名医生陈因未采取保护措施便对其进行急诊而感染病毒,两人因而被送进隔离区,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身体阈界:介于生存与死亡之间。一旦感染了非典,生死未卜;身心也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身体阈界的模糊不清也体现在身份阈界的模糊不清。感染病毒后的菲茨和陈既是医生,又是病人。尽管不能继续医疗工作,但已被隔离的他们时时关注非典的动态,并且可以通过自己的病征来判断自己的病情。疾病不仅仅意味痛苦,而且还意味个体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为了得到某种程度的安慰,他/她需要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陌生人;同时,疾病也意味着停止,它代表脆弱[17]68。“非典”使菲茨和陈完全丧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进入隔离区的他们就是病毒感染者,已然无法再投入医疗工作中。感染病毒后的菲茨更是自觉配不上“医生”的称号,“因为‘医生’一词暗含着——他应该部分凌驾于疾病之上,将其牢牢掌控。‘医生’一词还连带着责任,而他现在却负担不起了。”[6]218菲茨和陈处于非生非死的身体阈界当中,面对未知的传染病,身体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可能陷入生命危险。
身体阈界具有无限之可能性[5]xvii。正是身体阈界的模糊不清促使无限可能性的发生。病征之严重完全夺走病人的注意力,病人与世界以及他人的联系也因此被严重削弱[8]39。病征之严重侵占病人的思绪,肉体的疼痛侵袭人体的生命力,使生存变得苍白无力[8]44。在非典的折磨下,菲茨和陈展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信念。具体说来,某些症状意味着一种能力的失去,其他则更像是能力发挥的阻碍,还有一些则表明身体被不适、折磨、焦虑侵袭[8]42。症状的持续不断,使得病人在接受病情的过程中改变着自我认知[17]43。菲茨和陈因为感染病毒而失去了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病毒在折磨其身体的同时也在消磨其意志。菲茨知道自己的病情在不断恶化之后态度消极,首先自觉没有生存希望,其次担心自己的治疗会传染更多的医护人员,因而最终放弃插管手术,“我已经告诉甄济医生,在我表上注明放弃心肺复苏……你看,每个接受插管术的人都没救活。而且,给他们插管的医护人员也被传染了……拜托,你想过没有,我们什么时候打败过传染病。”[6]238-239陈则与菲茨相反,他乐观向上,并且打算明年和妻子明要个孩子。在得知菲茨放弃心肺复苏时,陈认为,“你简直疯了……对一种新病症来说,未免为时过早吧。也有没死的插管病人啊。”[6]239可见,身体上遭遇病毒入侵的菲茨在症状不断加剧的同时,自我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其求生意志越发消沉。最后菲茨不幸地在“非典”中逝世,而陈得以存活,两人不同的结局恰恰说明了身体阈界的无限可能性。
作家林浩聪曾经在访谈中提及,为了帮助病人,医生必须如作家般以全知视角来观察病人,但事实上医生并非全知全能,尽管有时候他们必须作一些“上帝般”的决定[9]。因为身体阈界的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菲茨和陈在感染病毒后生死未卜,处在隔离区的他们俨然成了边缘人,但是作为医生的他们又能够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来推断自己的病情,甚至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死。菲茨因为感染病毒而意志消沉,最终黯然离世;而陈则积极配合治疗,最终战胜病毒,克服身体阈界带来的不确定性。作家林浩聪曾在访谈中表示,灾难性的传染病是难以预料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充满无限可能性,人们需要尽自己的能力去了解某个传染病,唯有如此,防治才有意义;然而,也正因为传染病的无法预料,所以无人能够保证所作的防治都能够发挥作用[19]。这番话无疑透露出作家林浩聪对菲茨结局的惋惜,同时又对陈乐观态度的支持与认可。通过描写菲茨和陈的身体阈界,林浩聪表达了自己对传染病的态度以及对遭到传染病侵袭的医生群体的关注。部分医生(如菲茨)在感染病毒后,求生意志之消沉并非稀奇之事,这事实上也存在于当今的医疗行业中,即对病情的消极描述往往多于积极的[15]20。尽管如此,医学界中如陈一般的医生更是不在少数,他们积极的人生信念使其在面对传染病时乐观勇敢;他们对医疗技术保持信心,并以冷静和专业的态度与传染病对抗,这实在令人赞叹。
四、结语
阈界起源于人类学中的阈限,前者更多指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而文学中的阈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可以生发出其他更多类型的空间,包括具象的、认知的、表现的,甚至是批评的;是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的过渡性空间。阈界之人的特点也同样模糊不清,处于非此非彼的状态,并在阈界中产生焦虑等复杂又模糊的情感。根据阈界理论分析医护人员斯里、菲茨和陈的阈界现象,不仅拓宽了《放血与奇疗》的研究视角,深化读者对小说中人物以及作家创作意图的理解,同时还能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让其得以深入了解医生群体甚至医疗行业。然而美中不足的则是,本研究主要选取了小说集中的四篇短篇故事,对剩余的八篇并未进行过多讨论;此外,本研究只涉及医护人员的身份阈界,意识阈界和身体阈界,其他类型的阈界以及它们在小说文本和主题揭示等方面的功能则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