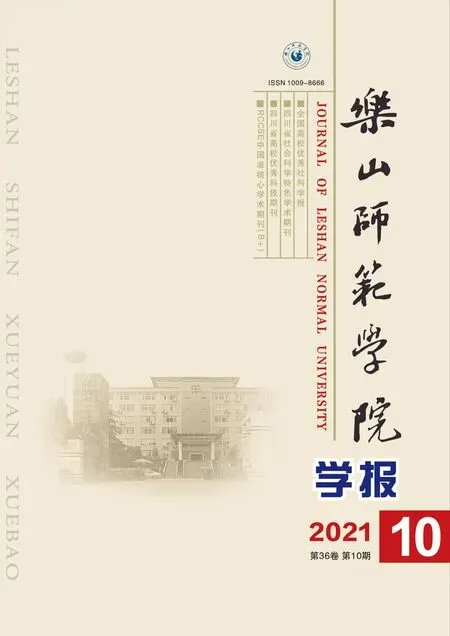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反表征探究
陈燕琼
(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文化表征理论由英国后殖民主义的代表斯图亚特·霍尔在20 世纪90 年代构建。霍尔认为表征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种文化中的众成员运用语言生产意义[1]90,即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人或事物当中的,而是被表征的体统建构出来的。霍尔认为,在文化中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 (人、物、事、抽象观念等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表征”的东西。[1]25由此得出意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表征过程中,语境、用法和历史背景都可能随意义发生变化。但是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形象群,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各个有关已经获得广泛权力的某主题的知识领域,即米歇尔·福柯在提到表征的主体时所认为的,“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权力谈论某些话题”[1]62。因此意义的这种表征的特征就是观念系统的再现、对身份的表现、或建构一种有误的再现。而文化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难界定的概念,往往通过语言来承载,而语言是作为一个表征系统来运作的,因此运用文化表征理论来研究同样以语言为表现形式的华裔美国文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根据霍尔的表征理论,作为意义被生产出来的美国英语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也是在一定历史和文化中生产出来的。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美国英语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受制于表征主体的权力话语而被刻板的套话错误地再现。但与此同时,生产意义的语言作为符号,是任意的,它受制于历史,即意义与表征向历史和变动开放[1]46,这也就给美国文学,尤其是华裔作家的作品,对中国形象进行文化反表征提供了可能,即修正那些被错误再现了的中国文化形象。华裔美国文学一直致力于反抗西方主流文化表征,在其反表征的过程中经历了排斥、融合以及自我整合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抗拒西方主流文化
由于19 世纪中期的排华法案,否定西方主流文化,强化中国的族裔文化/族裔身份便成了“反表征”的最初自发表现。这一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代表作品——《我在中国的童年》和《春香夫人》——通过排斥西方主流文化完成了其文化反表征的使命。
华人移民至美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彼时中国由于鸦片战争国力削弱,而美国西部发现金矿以及西进运动需要大量劳动力,使得大量华人移民到美国,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随着1869 年泛美铁路竣工美国经济陷入缓慢发展甚至危机之中,华人成为了白人就业压力的替罪羊,遭到了主流社会的歧视和丑化。从1870 年美国政府颁布的“移民法”到1882 年颁布的“排华法案”,一系列限制华人入境和损害华人在美权益的法案,使华人一步步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在文化和文学领域华人的形象也相应地被妖魔化丑陋化。这种妖魔化丑陋化的中国人形象在西方主流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构成了对中国的文化表征,这就是斯图尔特所说的,“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之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1]6。通过语言编码功能,美国英语文学文本对华人、中国文化加以再现甚至误现,并将其真实意图隐藏起来。布莱特·哈特在《异教徒中国佬》中塑造的阿辛衣着古怪,唯利是图;弗兰克·诺里斯在《中国独身行》把中国人刻画成残忍野蛮的怪人,即使是同情社会主义的杰克·伦敦,仍然在其作品中渲染中国人麻木不仁、丑陋肮脏;甚至在赛珍珠眼里,中国人“主要是勤劳坚忍但惟利是图、缺乏诗意”的农民形象[2]38-46。因此这一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文化反表征的努力主要表现为重塑中国人、在美华人的积极正面形象。
(一)《我的中国童年》的文化反表征
李恩富的《我的中国童年》是华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英文作品。该书出版于《排华法案》(1882)颁布之后的第五年,这绝不是巧合。事实上作者李恩富作为清朝第二批选派到美国的留学幼童,在目睹乃至亲身体验了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人形象、中国文化的文化表征之后,受波士顿罗斯罗普出版社的邀请写了这本旨在向美国白人主流社会介绍中国的书。该书从作者亲身经历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家庭、饮食、娱乐、教育、节日以及其他传统文化。
李恩富介绍了中国的家庭伦理,以此来反驳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表征。在提到中国传统家族维护宗法的时候,作者说,“之所以提到这些,并非意在说明中国人生来就比较残暴。中国人并非生来如此,只是希望依托这些宗法礼仪来治家而已”[3]13。该书还颇为详细的介绍了中国日常生活的基本步骤,从清晨起床到夜晚入睡的生活画面:最具生活气息的菜市场、充满家庭温馨的厨房炒菜、不失礼仪的下午茶……作者不厌其烦地描绘了一幅平静祥和、礼让有序的家庭生活的画面。谈及中国传统休闲娱乐活动时,尽管开篇说“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可以称之为运动的运动”,但作者在这一章里还是花了很长的篇幅介绍风筝,并称赞绑有芦苇弦的风筝的声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并表示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风筝真的应该向中国学习”[3]29。同时还刻意介绍了中国女孩子,“这些女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脾气特别大,说话特别直接;有的温文尔雅,有礼貌有教养;有的天生丽质,有的则貌不惊人”[3]37。作者以此反驳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的刻板套语印象:“长久以来,一提到中国女孩,大家想到的就是怨妇的形象:容颜憔悴,百无聊赖地坐在闺房里冥想,向往着墙外的美丽世界。的确她们没有美国女孩那样的自由,但她们也没有被锁链锁起来”[3]42。在谈到学校教育时,虽然作者对中国传统私塾的严格要求似有微言,但实际却是在强调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虽然政府不向普通学校提供资金扶持,但是中国到处都是学校,村镇有村镇的学校,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学校。虽然没有所谓的义务教育,但即便最贫穷的地方也渴望自己的孩子受到一些教育”[3]45。为了驳斥关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文化表征,该书介绍了中国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其间作者客观理性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神像崇拜比印度血腥的祭祀习惯要好,也优于埃及人残暴的拜祭风俗。”[3]64该书最后一部分选取了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说书来实现文化的反表征:“说故事的人的神色更是疏忽百变,语调忽高忽低,动作生动形象。……这一切跟留在外国人心目中的所谓中国人木讷、呆板、僵硬、漠然的固有形象完全两样。”[3]75
简而言之,《我的中国童年》以作者自传的形式讲述了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群体形象,有力地对抗了之前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对中国的文化表征。但李恩富绝不是此阶段唯一一个进行文化反表征的华人。另一本以小说的形式、通过生活在美国的个体华人来为中国文化反表征的作品在《我的中国童年》出版的次年开始酝酿写作,这就是《春香太太》。
(二)《春香太太》的文化反表征
《春香太太》是艾迪思·伊顿(Edith Maude Eaton,笔名水仙花,Sui Sin Far)从1888 年开始陆续创作、并发表的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由两部分组成,即《春香太太》和《中国儿童故事》。后来美籍华人林英敏(Amy Ling)和怀特·帕克思(Annette White-Parks)重新选编的《春香太太及其它作品》(1995)包括从第一部分中选出的15 篇故事和从第二部分中选出的9 篇故事。
《春香夫人》文化反表征的努力主要表现为对美国华裔的客观描写和刻画,尤其是对华裔男性的塑造具有明显对抗之前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各种负面形象的意味。
例如,《春香夫人》中的春香先生追求进步,入乡随俗,但仍然恪守中国传统文化;《新世界的智慧》中的吴三桂宽厚为人,在妻子宝琳杀子之后并没有失去理智而怪罪妻子,相反体谅妻子的感受,并最终带她回国治疗;《她的华人丈夫》中的刘康喜心地善良,在收容无家可归的白人妇女后对她悉心照顾,体贴入微;《自由之邦》中的宏兴爱孩子,疼惜妻子,为了孩子不惜倾家荡产;《林强》中的华人劳工林强拼命挣钱,只是为了能把妹妹从妓院里赎出来,送回中国过正常人的生活。即使后来发现钱不翼而飞之后他仍锲而不舍,继续辛苦二十年挣钱赎回妹妹;《中国百合花》中的林强照顾妹妹,勤劳工作;《复原之神》中的大罗宽厚仁义,以德报怨,另一位男主人公小罗虽然犯错在先,但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自强不息、发奋图强;《天山的真心》中的天山为了与恋人相见,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边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精神;《歌女》中的柯良具有男子汉的担当:当发现一个陌生歌女冒充原来新娘并被非难时挺身而出保护她。
与此同时,《春香夫人》中的女性也努力挣脱之前被强加在华裔身上的刻板形象。《春香夫人》中的春香夫人思想开化,具有当时代少有的女性平等意识;《摇摆形象》中的潘爱恨分明,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宝珠的美国化》中宝珠知书达理,在反抗男权的斗争中机智勇敢;《中国百合花》中的百合花舍生取义,在灾难面前牺牲自己拯救别人;《复原之神》中的塞拉忠于爱情,坚贞不渝;《中国宝宝的价值》中的芬芳作为妻子任劳任怨,作为母亲爱孩子胜过自己;《天山的真心》中的芬芳,性格独立,富有浪漫情怀,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歌女》中的阿琪原本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唐人街歌女,但她独立自主、足智多谋,敢做敢当,最终阴差阳错通过勇气和智慧为自己赢得了幸福的婚姻。《偷渡女郎泰苦》中的泰苦爱上了偷渡犯杰克.费边,在偷渡险被发现的紧要关头不惜主动跳江来保护费边。
水仙花的反表征努力还表现在其作品中对一些白人形象的负面刻画上。不同以往涉及华人的美国文学中的白人形象,《春香夫人》委婉提及了白人对在美华人的种族迫害以及其他负面形象。《摇摆形象》中的白人记者马克打着爱情的幌子,欺骗唐人街女孩潘的感情,并利用潘的身份深入唐人街,丑化其间的华人及唐人街形象;《在自由国度》里贪婪无耻的白人律师利用华人夫妇急于见到被美国海关带走的初生孩子迫切心情,数次索要高价费用,几乎让这对华人夫妇倾家荡产;《她的华人丈夫》中的白人前夫卡森自私自利,不仅不愿保护照顾自己的妻儿,反而在前妻遇到了善良宽厚的华人刘康喜后嫉妒心作祟,威胁恐吓前妻。
二、第二阶段:并置中西方文化,努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美国民权运动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主要是指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长期以来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其他少数族裔的族群政治意识逐渐觉醒;与此同时,1965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移民法,取消了之前各移民的单一配额,从而使得中国移民在美国数量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在美华裔,尤其是深受民权运动影响的年青一代华裔,他们如同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非裔黑人一样开始意识到,中国形象依然被表征为愚昧落后,残暴冷漠。不同于第一代华裔移民,第二代华裔子女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强烈感受到作为“他者”被美国主流文化差异化对待,因此他们希望疏远中国文化,以积极的形象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另一方面华裔家庭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对他们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形成自己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感到迷茫,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尴尬身份感到不知所措。因此发展至第二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受20 世纪中期民权运动和新移民法案的影响,表现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征。这一阶段的美国华裔文学文本把西方主流文化同中国族裔文化并置展现,试图消解权力阶层所刻意构建的文化表征,代表文本为《女勇士》和《喜福会》。
(一)《女勇士》的文化反表征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于1976 年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女勇士》。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无名女子”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听母亲讲发生在中国家族的姑姑婚外生子,被迫抱子投井自尽;第二部分“白虎山学道”是根据中国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杀敌立功的故事改编而成。作者想象自己成为“花木兰”进白虎山修炼十五年,然后带兵打仗报了国恨家仇,回到故乡成了英雄。第三部分“乡村医生”描述了母亲“勇兰”在中国学医和行医的经历,以及她能捉鬼和招魂的故事;第四部分“西宫门外”写的是姨妈勇兰的妹妹月兰到美国千里寻夫未果,终郁郁而终的悲惨境遇;最后一部分“羌笛野曲”写的是“我”回忆从幼儿园到成人的成长经历的几个细节,如幼年的“我”毫无原由地在学校地下室折磨一名沉默寡言的华裔女同学。
汤亭亭在《女勇士》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女性(无名女子、花木兰、勇兰,“我”等)对中国父权制的反抗,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女勇士》是一本女性主义作品。但在美国文学对华人文化表征的大背景下,华裔女性除了感受到父权制给她们带来的不公正待遇之外,更让她们感到痛苦的是种族歧视。正如华裔学者埃丝特·曹(Esther Chow)所说:“亚裔妇女强调首先要消除的是种族压迫,其次才是性别歧视。她们愿意团结在整个族群中,要求改善其种族整体的生活状况,而不仅仅只是强调妇女自身的问题”[4]68。因此对于作者汤亭亭——一名出生、生活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作家——而言,把对性别歧视的反抗同文化反表征结合在一起就是《女勇士》的叙事策略。《女勇士》一方面通过母亲勇兰所讲述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来反抗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又通过“我”在美国的经历来展现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加诸在华裔身上的种族歧视。但恰恰也是因为当时美国出版环境所限,《女勇士》不可能将后者直接表露出来,而是借助其中的“中国故事”来完成其文化反表征的意图。汤亭亭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曾说过,“我并没有讲过那些故事是中国神话,我要说的是,我所记述的是美国神话,花木兰及其背上的刺字是一个属于美国的神话;那是我所写的美国神话”[5]76。《女勇士》的前三个故事基本上是勇兰讲给“我”——这个出生在美国的、没有去过中国的华裔女儿——关于中国的传说,因此可以说是给“我”这个美国人塑造了一个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不同于以往的美国英语叙事文本里的中国形象:无名女子不再是一个被压制在父权下的懦弱女性。作为一个“不守妇道”的非传统女性形象,她以怀抱初生婴儿投井的决绝行为表达了自己对村民、家人乃至当时整个社会对女性戕害的抗议;白虎山学艺中的花木兰更是被汤亭亭塑造成了一个刻苦学艺、领兵打仗最终推翻昏聩皇帝的女勇士。这个挪用了岳母刺字的美国版花木兰完全颠覆了传统中国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刻板形象。乡村医生中的勇兰更是不遗余力的展现了一名中国女性的独立自强的精神。小说的第四部分在讲述勇兰将妹妹月兰带到美国寻夫认夫时所展现出来的女性独立意识让人印象深刻:“妻子的作用正在于此——训斥丈夫,让他变乖。告诉他不许娶三姨太。告诉他,你高兴什么时候去找他,就什么时候去找他”[6]130。这些独立、有主见、勤劳、聪慧、有行动力的中国女性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美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女性的套语形象。在“羌笛野曲”中“我”在学校地下室欺负那个无论如何也不肯说话的华裔少女也只是为了“迫使她说话”[6]179。“沉默”在这一部分反复出现,“我”作为美国华裔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因此当“我”长大到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时候,“我”比谁都希望同一个学校里同族裔的女孩不再沉默,能为自己发声。因此不难看出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文化反表征的意图得到彰显:前面四个部分所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为身处美国的“我”——一名正在成长中的华裔少女提供了反抗种族歧视的精神参照。这也是美国华裔精神成长的见证。
(二)《喜福会》的文化反表征
《女勇士》出版不到十年,谭恩美在1987年出版《喜福会》。如果说《女勇士》通过挪用、改写中国神话、传奇将中西方文化并置从而消解美国英语文学对中国的文化表征的话,《喜福会》则是通过直接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到这四对母女的日常生活中来实现其文化反表征。
从整体结构上看,小说一共有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分别以极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故事、传说作为引子,开始这四章的叙述。第一章的引子——“千里送鹅毛”讲述了一位中国母亲移民美国时带了一只由鸭子变来的天鹅,寄希望于今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也能蜕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讽刺的是在入境美国时这只天鹅被海关没收了,母亲手里仅剩下一根鹅毛但她仍然想把这根鹅毛送给她未来的子女。沿用了中国这个典故的含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作者想传达的是母亲对于子女的美好愿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美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小说第二部分的引子“二十六扇凶门”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八卦。中国母亲手里总是拿着能预示未来的卦书告诫出生在美国的女儿如何才能逢凶化吉,但根本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女儿不信卦书之说,自然也对母亲的告诫置若罔闻,但结果就是女儿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受了伤。第三部分的引子虽然以“美国翻译”为题,但其仍然以中国迷信为讲述的核心:深受中国迷信影响的母亲在女儿新装修的房里看到床脚有一面镜子,认为其为不祥之兆,于是送她另一面镜子置于床头,但女儿却不以为然。第四部分以“西天王母娘娘”为引子,主要讲述年迈的中国母亲在跟美国出生的孙女嬉戏时把天真无邪的孙女称作中国神话里的西天王母娘娘,因为小女孩的笑声启发她对世间种种艰难困苦的理解。这里作者想要传达的是中国母亲以其一生的人生阅历告诉身处美国的年轻女儿:再难也要笑着面对。这样的四个引子把母亲在中国的几十年经历和女儿在美国的生活用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起来,让读者容易感知到作者并置中西方文化的意图;通过这样的并置,小说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大量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冲突。这种冲突以中国母亲和美国女儿之间的各种矛盾来展现,诸如素云强迫女儿精美学弹钢琴,琳达炫耀女儿薇福莱下棋的天赋,安梅抱怨女儿露丝在婚姻危机之时不找自己寻求帮助,盈盈嘲笑丽娜和她丈夫为她安排的所谓的“客房”其实很不得体。但《喜福会》文化反表征的努力恰恰体现在这些矛盾最后的化解之中:无论是最后前往中国找寻双胞胎姐姐的精美,跟母亲就自己再婚一事达成一致的薇福莱,为离婚而争取自己应得权益的露丝,还是终于意识到自己婚姻问题的丽娜,都是在母亲的故事里找到了自我,“身份的焦虑症得到了治疗,灵魂得到了充实,个性变得强壮”[2]107。这里“母亲的故事”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她或许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对身居美国的华裔女儿来说“千里鹅毛”是爱的力量,“二十六扇凶门”是善意的告诫,床头的镜子是良好的祝愿,“西天王母娘娘”是长者对生活感悟的传达。作者中国文化反表征的实践体现在揭示出中国文化为身在美国的华裔提供了恢复种族记忆来恢复完整人格的正面积极力量。
三、第三阶段:自我整合
人类进入21 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晚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发展、变化,经济、政治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族裔身份、族裔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凸显。正如美国国家文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拉蒙·萨尔迪瓦教授的观点:“在二十一世纪,种族与社会公平,种族与身份,以及种族与历史都要求作家对思考一个公平社会的本质以及种族之于社会公平的建构,做出新的‘ 想象’。这也要求创作出新的形式来再现它”[7]7。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人口比例发生较大改变,少数族裔人口不断增加。身处其中的华裔美国作家们用一种混杂性的、对话性的话语来体现华裔对其差异的文化身份的追求,从而进入了对自己族裔身份构建的自我整合阶段。这一阶段同时也需要界定一种新的华裔美国文学评论,不是给华裔美国文学戴上任何神秘的面纱,而是表明华裔美国文学艺术的确精彩纷呈,从而实现对西方主流所构建的文化表征的抵抗和颠覆。
第三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以“走出唐人街”作为文化反表征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阶段的两本小说分别是伍慧明发表于1993 年的《骨》和伍邝琴于1998 年发表的《裸体吃中餐》。与之前华裔美国文学文本相同的是,这两本小说中的故事叙述者也是吃着汉堡喝着可乐、在唐人街长大的华裔女孩;但不同的是这两个在唐人街长大的女孩最后都走出了唐人街。这一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并不强调族裔的差异(尽管差异一直存在),而是通过讲述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华裔作为普通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着重刻画作为共性存在的人性。因此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华裔美国文学的作家们把视角选在唐人街这个最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地方,通过两位最终走出唐人街的华裔女性来消解之前美国英语文学文本中对中国所做的文化表征。
(一)《骨》和《裸体吃中餐》的文化反表征
《骨》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华裔家庭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唐人街华裔家庭:父亲里昂是一个作为“契纸儿子”来到美国、从事苦力工作的底层华人,母亲一如既往的是衣厂女工。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大女儿莱娜是一所小学的教育协调员。二女儿安娜由于恋爱受阻跳楼自杀,最小的女儿尼娜离开唐人街去了纽约,剩下莱娜在父母最艰难之时照顾他们。故事最后以莱娜帮助父母度过难关之后与华裔男友结婚并搬出唐人街为结束。《裸体吃中餐》则讲述了一个位于纽约皇后区唐人街的华裔家庭的故事。跟大多数唐人街华人一样,故事主人公鲁比的父母以开洗衣店为生,父亲粗暴冷漠,母亲逆来顺受。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小女儿鲁比在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回到唐人街的家中。在家里居住的这个夏天鲁比洞悉了父母、兄妹、恋人之间种种矛盾,最后故事以鲁比同白人犹太男友分手、但同时也搬出唐人街为结束。
笔者在此把这两本小说合并在一起分析,是因为在文化反表征上这两本小说有大量的相似共通之处。首先,两位作者都选择了以唐人街作为文化反表征的阵地。其次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都曾因为母亲而选择留在唐人;最后这两位故事的女性言说者都以走出唐人街来展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确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
(二)唐人街形象
唐人街在这两本小说中的形象跟以往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几乎一样。地处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唐人街是《骨》中莱娜一家生活的地方。无论是他们一家居住的鲑鱼巷,还是后来里昂搬去单身公寓的克莱街,作者伍慧明笔下的唐人街充斥着一种破败、肮脏的景象。里昂的公寓有一股“垃圾场”的味道,“过期的油料、润滑油,还有生锈的金属。在那间半阴暗的房间里看到的东西比我闻到的还要糟。…… 旧的面包机、收音机的零件、旧天线——都是该进垃圾箱的东西”[8]181。唐人街上有“尿味浓烈呛人的乞丐拐角”[8]7,无所事事的华人“到处瞎转悠的、随处吐痰的、走哪儿坐哪儿”[8]13;“化妆品街上带着塔顶的灯,搭配着很怪异的颜色:红配绿,绿配海蓝,黄配粉红[8]172。“这些奇怪的颜色组合,狭窄的街道”[8]172让身处其中的第二代华裔深感压抑:莱娜说“唐人街给人一种闭塞压抑的感觉”[8]150;远走纽约的尼娜这样评论旧金山的唐人街,“那儿吃的倒是不错,……,但生活太苦了。在那儿吃饭我总感觉要赶快把盘子里的饭吃完,然后赶快回到家里去缝裤边儿,或者回去组装收音机零件什么的”[8]29。
在《裸体吃中餐》里,唐人街虽然换到了美国东部的纽约皇后区,但仍然呈现出相同的阴暗、压抑之像。作者伍邝琴将视角缩小到唐人街的一座洗衣房里。鲁比父亲用尽毕生积蓄买下了洗衣房,但一家人还是只能挤在洗衣房后面的狭小空间里生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鲁比的母亲为了躲避自私冷漠的丈夫富兰克林,与三个孩子住在了一个房间。四张首尾相接的床构成了鲁比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环境;待鲁比长大一点,由于母亲外出工作,她就只能跟随父亲待在洗衣店的柜台下面,被迫忍受前来洗衣服的一些顾客的打量。连鲁比母亲早上想在家里做个运动都是奢望,只能在熨衣板和一包包衣服形成的狭窄通道中间伸伸胳膊蹬蹬腿[9]67。
(三)唐人街的文化反表征作用
两位作者文化反表征的努力在于赋予了唐人街作为美国华裔精神港湾的作用。尽管唐人街有上述种种压抑闭塞之感,尤其是第一代华裔移民在其中只能从事传统的华人行业,(《骨》中莱娜母亲是衣厂女工,父亲常年出海,靠出卖苦力来养家糊口;《裸体吃中餐》中的父母靠开洗衣房为生)但对于生长于此的第二代华裔而言,唐人街同样以家庭温情、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了这些吃着汉堡喝着可乐长大的美国华裔,在他们遭遇挫折苦痛之时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当《骨》中二女儿安娜跳楼自杀后,全家陷入了无尽的伤痛:母亲以泪洗面,父亲懊恼暴怒,小妹干脆远走纽约以逃离唐人街。唯有长女莱娜选择留在了父母身边。但安慰失去至亲的年迈父母和自己都需要勇气,这勇气正来自于唐人街:
我听到了从老巷中发出的所有声音——有老林先生隔墙传来的咳嗽声,有林太太为他找药的声音,屋外是长长的雾角声和厄尼.张家卡梅罗车隆隆开过的声音……这些昔日的声音让我平静了许多。它们使鲑鱼巷又恢复了往日所带给人们的那种轻松感。这些熟悉的声音像蚕茧一样把我包裹着,使我有了安全感,使我感到像是待在温暖的家里,时间也静止了[8]126。
此时唐人街的嘈杂、拥挤不再让人生厌;相反,其嘈杂的声音、拥挤的街道代表了鲜活、真实的生活,衣厂女工的乡音成了治愈莱娜母亲丧女之痛的良药,“听到别人(衣厂女工)叫她小名一定有安抚的作用……多少次这些传播流言蜚语的女工让人烦恼不已,可又有多少次她们给我们带来了安慰”[8]102。
唐人街给身在其中的美国华裔带来的心灵归属感在《裸体吃中餐》中被作者刻画得较为抽象。不同于一直待在唐人街鲑鱼巷的莱娜,故事伊始鲁比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与白人男友一起居住在曼哈顿,毕业之后回到皇后区的唐人街同父母暂住一个夏天。尽管唐人街的家有上述各种拥挤、不适,让“鲁比讨厌整个皇后区,尤其是洗衣店和住在其周围的人们”[9]24,但鲁比还是回来了,表面上是因为其刚毕业经济拮据,但真正的原因作者其实在故事尚未正式展开之前就有所暗示了:鲁比一直被一种不安的感觉困扰。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四年里,这种不安从未消失过。“她努力想摆脱这种感觉,但却变得愈发强烈。于是最后她只得打包行李回到位于皇后区唐人街的家”[9]17,直到她回到家后,她才意识到“这份不安的感觉来自她的妈妈;她把妈妈忘在了唐人街的家里,她必须要回唐人街重新找到妈妈,这份不安才能渐渐褪去”[9]16。小说中此处提到的“妈妈”既指养育了孩子的母亲,也寓指提供精神养分的文化之根。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唐人街就有了母亲的温度和价值。曾经走出唐人街的鲁比,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有一个白人男朋友,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没有在象征着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曼哈顿找到归属感。相反,她回到了那间摆了四张床的拥挤的房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不得不说作者是刻意构建了这样一个只有母亲、哥哥、姐姐和鲁比的母子空间,暗示了母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隐喻了从唐人街走出去的华裔子女仍然需要回到唐人街汲取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让鲁比审视自己同白人男友尼克的关系:当母亲警告说“不知道怎么吃东西比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更糟糕”[9]241时,鲁比意识到白人男友对自己的感情更多是建立在对“他者”文化的猎奇心态之上,因而最终决定与之分手。
因此这两本小说中的唐人街拥挤、嘈杂、肮脏如同其他描写华裔生活的唐人街,但伍慧明和伍邝琴却通过赋予唐人街医治华裔心灵创伤来实现了文化反表征的目的。
(四)走出唐人街,构建开放的文化身份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小说中的主人公必然要正视自己构建文化身份时的多重要素。他们不可避免的面对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生活方式,他们对唐人街爱恨交织。他们出生在唐人街,但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唐人街以外的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比如莱娜,作为一所小学的教育协调员,主要工作就是帮助移民的孩子与学校和老师沟通交流,因此莱娜深谙两种文化的交流;鲁比甚至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专业是女性研究,但她对中餐却有着深深的迷恋,以至于在深夜的大学宿舍里煮中餐给其他同学吃。因此,对于这样两位一度回到唐人街的年轻华裔而言,走出唐人街又是必然的选择。他们对家的定义既不是遥远的、只能想像的中国传统家园,也不是被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鲑鱼巷或者华人洗衣店,当然更不是白人主流文化占主导的曼哈顿。所以当这些多重文化交织在一起时,他们没有像《骨》中的小女儿尼娜一样彻底远走纽约,或是《裸体吃中餐》中的哥哥凡一样十多年不与父母联系从而切断与唐人街的一切关系。相反,他们只是走出唐人街,但又同时保留同唐人街的联系。
莱娜留在唐人街照顾父母时与同是华裔的男友梅森感情加深,其结婚的地点被作者安排在远离旧金山的纽约。没有唐人街的华人传统婚礼,甚至在是结婚后才告知父母,这其实已经是莱娜走出唐人街的第一步。故事快结束时,莱娜从唐人街搬出,与丈夫梅森住到教会大街,莱娜想“还是留在妈的身边,做妈的好女儿,让她成为我生活的全部”[8]227,当载着所有东西的车子开出鲑鱼巷时,莱娜说“我重又有了信心,我知道藏在心里的东西会指引我向前”[8]228。鲁比在唐人街的家中呆了一个夏天之后也离开了,但与莱娜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回到尼克的公寓,而是搬进了曼哈顿的一个女子公寓。在这个女子公寓里鲁比没有挂窗帘,这是对白人主流社会凝视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的一种反抗。与此同时搬离唐人街的鲁比开始把衣服送去洗衣店清洗,不再把洗衣店看作是只有华裔才从事的低贱工作;甚至鲁比的母亲,这个一直只在厨房、洗衣店做饭、工作的老一辈华裔,在故事的结尾处也开始走出厨房,穿上女儿给她买的新鞋开始跑步,逐渐跑出她们所在的街道,街区,跟外面的人打招呼;甚至几乎不出门的父亲在后来也发生了转变,竟然买了两张去佛罗里达的机票送给妻子作为她六十岁的生日礼物。
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以各种方式走出唐人街,但却并没就此远离唐人街。唐人街作为他们精神力量的源头,当他们在唐人街以外的多元文化中受挫失落的时候,以各种形式为他们提供心灵的治愈和庇护;与此同时,多元文化的影响势必引领他们走出这个相对封闭嘈杂的空间,反思在多元文化中如何构建动态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不应该被贴上华人洗衣店或者廉价中餐的标签。所以这两本小说彰显出美国华裔文学势必要突破以往文学文本中的文化表征,建构一种混杂、开放、流动的华裔文化身份。
四、结语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为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使得这些族裔文学的读者、评论者,修正那些被错误再现了的种族文化形象,积极进入意义生产的环节中来。本文在文化表征理论指导下,将华裔美国文学从19 世纪中期至20 世纪末至21 世纪初期的排斥、融合以及自我整合三个发展阶段纳入研究范围,从每个阶段分别选取了两本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对其中的文化表征和文化反表征进行了分析。以《我的中国童年》和《春香夫人》为代表的第一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由于19 世纪中期的排华法案,主要通过否定西方主流文化,强化中国的族裔文化/族裔身份实现文化反表征。第二阶段在美国民权运动和新移民法案的背景下华裔美国文学表现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征。以《女勇士》和《喜福会》为代表的这一阶段华裔文学文本把西方主流文化同中国族裔文化并置展现,试图消解权力阶层所刻意构建的文化表征。进入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华裔美国文学第三阶段以“回到/走出唐人街”作为文化反表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伍慧明发表于1991 年的《骨》和伍邝琴于1998 年发表的《裸体吃中餐》展现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确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通过分析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发现华裔美国文学一直致力于反抗西方主流对中国文化刻板化描写的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