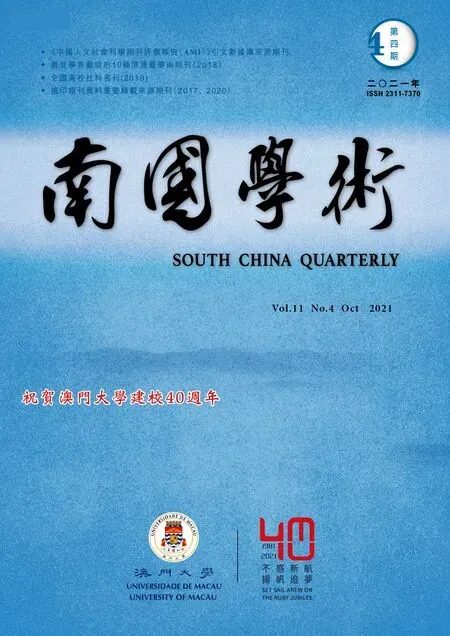國家化:基於中國國家實踐的理論和方法
陳軍亞
[關鍵詞]國家化 理論 方法 趨向
國家是一個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的歷史演進過程。在當下,國家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廣泛和深入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人類社會的國家化已是普遍的政治現象。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如何出現,如何發展,呈現何種規律,體現了何種邏輯,在不同時空中存在何種差異,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以政治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爲研究對象的政治學,衹有將人類社會的國家化進程提升爲一種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理論與方法,纔能對豐富且普遍的國家化現象及其過程做出解釋。本文試圖將“國家化”作爲一種政治學理論與方法,闡述其理論內涵與研究維度,以期對政治學研究範式創新以及“國家”研究的拓展有所裨益。
一 “國家化”的內涵與分析框架
關於“國家”,人們有多種理解。如果從靜態特徵上看,它既可以視爲權力機構,也可以視爲制度形態;但如果從動態來觀察,它並非是一個孤立的機構或制度性存在,而是建立並運行在一定社會基礎之上的。這些社會基礎,構成了作爲機構或制度形態國家的運行環境。如果說國家是一種公共權力的話,那麽,社會則構成了國家權力的實踐場域。所謂“國家化”,就是國家權力與實踐場域之間的動態過程。
國家形態的演進有其歷史進程。在前國家時期,社會以血緣紐帶所形成的人身、純人身關係爲基礎,實現自我整合。國家誕生以後,便有了脫離社會的公共權力和對社會的強制力。但由於強制力的有限性,大量的公共事務仍由社會依靠歷史延續下來的習俗自我解決。進入現代國家階段後,國家形態則表現爲,不斷向社會擴展其官僚制度和滲透其協調社會的能力。因此,從國家誕生以來,國家即面臨着向社會輸入其意志,實現與社會的有機聯結和整合過程。
這一過程在中國具有豐富的內容和鮮明的路徑。古代中國,權力大量散落於社會之中,家族、地方性團體、宗教組織等在不同的區域社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並形成治理鄉村社會的地方性權力。高高在上的“皇權”與基層社會中的“鄉治”並行,大體囊括了王朝時期中國的權力格局,兩者保持着鬆弛的聯繫。到了現代時期,國家建設導致地方性權力向國家集中,由此帶來了國家權力內容的擴大,這些集中並擴大的權力向社會再滲透。從“散落”到“集中”再到“滲透”,呈現了權力從社會到國家再進入社會的演化路徑,構成了國家化的連續進程。但是,這一演化路徑在不同空間、區域有不同的表現和實踐。即使在王朝時期,國家公共權力的構成和表現形式也存在顯著不同。例如,國家權力介入較多的領域是賦稅和治安,除此以外的其他事務則呈現“選擇性介入”。①相關研究,參見楊國安:《國家權力與民間秩序:多元視野下的明清兩湖鄉村社會史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所以,衹有從國家的角度觀察社會的多樣性,纔能更好地揭示國家形態的豐富性。
王朝國家形態的豐富性,意味着國家化進程的複雜性。徐勇教授用“農民性”來分析20世紀中國“國家化”進程中的複雜性②徐勇:《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第61頁。。然而,“農民性”在不同時空也是有不同內涵的。在古代中國,農民的孤立性、分散性更多是與地域性相結合,呈現出多樣性特徵。在一些地方,多是與家族性相聯繫;在另外一些地方,多是與村莊相聯繫,強化了村莊共同體的屬性;還有一些地方,更多是與市場相結合,表現出親市場性、個體性。因此,“農民性”是一個複雜的地方性概念。對於國家化進程而言:一方面,複雜的地方社會面對國家權力的滲透,以其自身特有的地方屬性做出回應;另一方面,面對不同的地方社會,國家權力滲透和進入的起點、方式、策略、路徑也不同。國家化是一個將差異化、異質性的地方社會,整合爲一個與國家之間形成有機聯結的政治共同體的過程。衹有從社會的角度觀察國家,纔能揭示國家化進程的複雜性。因此,研究“國家化”,需要將“自上而下的國家視角”與“自下而上的社會視角”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決定了國家化的分析框架,即“國家整合社會,社會回應國家”。
“整合”是一個廣義概念,它描述的是國家意志或體現其意志的公共權力進入社會之中的行爲。一方面,國家公共權力打破了傳統地方性權力的運行空間,改變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鬆弛聯繫,從而與社會建立有機聯結;另一方面,統一的國家公共權力建立了社會的“整體性”,將外在於國家權力的分散的地方社會整合爲一個具有“統一性”“整體性”的政治共同體。國家整合社會的結果,即實現社會從忠誠於地方性權力和意志向忠誠於國家權力和意志的轉移。從權力形態而言,整合所體現的,既包括不需要與社會協商而直接進入社會的權力,即馬克斯· 韋伯(M.Weber,1864—1920)意義上的官僚政治的控制力;也包括邁克爾· 曼(Michael Mann)所言的貫穿社會的基礎性權力,即國家在其統治領域之內進行決策並協調社會的能力。“整合”是一個包括意志、權力、能力在內的綜合概念。
在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建立有機聯繫的過程中,還面臨着地方社會的回應。社會是由具體的人構成,人處於不同的歷史關係之中,其行爲具有特殊性、差異性、能動性、調適性、理性等多樣化特徵,這就決定了人在國家整合過程中的回應性。這種回應,既可以表現爲接受或順應,也可以是反對或抵制,還可能做出策略性的變通和適應。在不同地域空間、不同構成和屬性的社會之中,回應的方式、手段、表現、特徵各有不同。面對不同的社會回應,國家整合社會的方式、手段、策略等也會做出調適或變通,由此産生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空間呈現複雜多樣的模式和特徵。20世紀以來中國的國家化實踐進程表明,國家以其意志整合並建構農民社會的過程,同時也是農民社會以其“農民性”回應國家建構的過程。①徐勇:《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第61頁。兩者的關係,決定了中國20世紀以後國家化過程的複雜性。
如此說來,“國家化”的分析框架應當包含六個要素:
一是主體要素。國家化的主體是國家。國家由具有思想意識的人所組成,是一個具有能動性的行爲主體。制度主義的國家理論強調國家的制度特徵,制度對處於特定制度中的人的行爲具有“規範性”“約束性”,社會的存在因此依賴於國家和法律的界定。但是,離開了對社會中的人、人的行爲的分析,無論是舊制度主義,還是新制度主義都無法解釋制度變遷如何發生。當進入社會中的國家權力(無論是以組織或機構的形式,還是以制度或政策的形式),與社會中處於特定歷史關係的人的行爲價值發生分裂或衝突時,國家能夠以主動性的調適對社會做出回應。調適的結果,既可能是制度的強化,也可能是制度變遷的發生,但均體現着向社會貫徹意志、實踐意志所採取的策略及策略的調適性。自從國家産生以後,便開始了向社會輸入意志的過程。衹不過,其輸入和滲透的方式、策略及其實現程度,既受到國家意志和能力的制約,同時也面臨着其輸出對象接納或抵制的回應。而能動性的國家,可以據此作出反應。
二是客體要素。國家化的對象是社會。國家化將社會視爲其行動的對象,同時強調社會對國家行爲的影響。但不同於“社會中心論”的立場,社會對國家並非一種單向的決定性影響,社會對國家的影響通過國家的能動性得到承認和體現。社會作爲國家行動的對象,具有動機上的被動性,而非一種主動的決定力量。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空間內,社會具有不同形態和特性。面對國家持續輸入其意志的行爲,不同形態、特性的社會會做出不同的回應。
三是方式要素。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需要通過不同的方式和手段進行,它構成了國家整合社會的策略。在王朝國家時期,主要依靠暴力爲基礎的強力控制。進入現代國家階段後,隨着越來越多的權力向國家集中,國家在行爲能力上得以擴展,整合社會的方式和手段更加多樣化——或者通過政黨、行政、法律等直接滲透,或者以市場、經濟活動等策略間接控制,或者採取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緩慢改造。國家採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帶來了整合社會的不同結果。
四是互動要素。國家將可能分散、分離於國家意志之外的社會,塑造爲與國家之間建立有機聯結並體現國家“整體性”的社會,這一過程並非是一個單向的進程;作爲被整合、塑造對象的社會,會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國家的整合和塑造。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性質不同,互動的方式和機制也不同。在彼此爭奪控制權的關係中,互動可能表現爲衝突、對抗、博弈或妥協;在社會不具備控制權的關係中,互動更多表現爲一種策略性的回應或變通。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性質,決定了互動方式和機制的屬性差異,這一差異又反作用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從互動要素觀察國家與社會,二者之間呈現互爲因果的決定關係。
五是過程要素。過程要素的國家化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國家化的階段性過程,即在實現國家特定意志的特定歷史階段,國家化是一個包含“整合—回應—調適”並持續進行的過程。二是國家化的長期歷史過程,即國家自産生以來,就開始了對社會輸入其意志的進程;但在不同歷史階段,國家化的內容不同。這一長期過程,形塑了社會對國家意志的認同,實現了國家對社會的有機整合和國家“整體性”“一致性”的構建。
六是方法要素。在研究方法上,“國家化”強調行爲的意義和特徵,但認爲行爲是在特定制度或結構中發生。特定的制度或結構,賦予行爲“累積性”“約束性”特徵。處於特定歷史關係中的行爲對制度或結構也具有反向作用,既可能是順應型的行爲帶來制度的擴張或強化,也可能是抵制性的行爲帶來制度或結構的衝突和變遷。因此,“國家化”不同於缺乏歷史情境關照和現實情境選擇的結構主義,也不同於將行動者的過程和行爲選擇作爲分析視角的行爲主義,而是以不同歷史與社會關係結構中的人的行爲表現爲依據,從中觀察其行爲模式,解讀模式中蘊涵的意義。“國家整合社會”強調國家的行爲特徵,但國家行爲也受到社會條件的約束,以及歷史情境的影響;“社會回應國家”強調人的行爲選擇的自主性,但這種選擇並不具有過程的隨意性和結果上的無限可能性。它發生在特定的關係結構之中,其選擇的結果和意義需要在“國家調適”的能動性中得到體現。
二 作爲 理論的“國家化”研究維度與命題
“國家化”是一個從中國國家實踐中提煉並將之一般化的理論和方法。它注重三個研究維度,並獲得相應的命題。
(一)歷史的維度:國家化的歷史起點與進程
在國家與社會形態、國家與社會關係模式中,歷史的重要性表現在“形態”“關係模式”上所具有的連續性、持久性特徵。即使經歷重大危機或轉向,可能依然持續存在的歷史的生命力,可被稱爲“歷史的韌性”。對於一個擁有悠久且連續的歷史實踐的中國,歷史之於政治學研究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衹有從歷史維度研究國家化進程,纔能在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之間建立關聯性,並從關聯性中尋找和認識國家從傳統形態進入現代形態的過程及路徑。也就是說,關注傳統國家形態的生成及延續,與關注現代國家的形成同樣重要,因爲後者是在前一階段持續影響下累積演進的結果。
國家化是國家向社會持續輸入其意志,在社會中逐漸構建國家“整體性”“一致性”的過程。作爲對領土和人民主張其控制權的國家來說,自誕生以來,即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自主性。它通過摧毀以血族團體爲基礎的舊社會,並依靠其建制權開啓了對社會的再組織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實現了國家對社會的整合,也獲得了超越血緣氏族權力之上的公共權力形態,即國家自身的形態。
將國家化置於國家成長的歷史進程中考察,這一歷史維度包含兩條路徑:一是對歷史深度的強調,即國家化的歷史條件、起點對國家化進程的影響——人類社會是如何從一個無國家的自然社會進入到有國家的政治社會的?其進入的路徑、過程是如何影響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與社會對國家的回應的?二是歷史階段差異性的分析。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國家形態與社會結構有何差異?這些差異如何表現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並影響二者的互動?需要尋找或解釋導致階段差異的某些因素,識別出與“階段性”相關的某些“斷裂”或不持續的條件,並解釋國家化的不同結果。
(二)空間的維度:國家化歷史進程的空間差異
歷史是在特定的空間中發生的。從東西方國家的起源看,彼此充滿着鮮明的差異性。東方中國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起源並沒有遵循“公共權力的誕生與血緣團體被炸毀”①[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卷,第16頁。的路徑,即它並沒有炸毀家庭、家族這個原生母體或與其割裂,而是從這個原生母體中汲取養分,逐漸向其外的領域擴展並形成。
不僅國家形成的起點存在空間差異,國家誕生後的演進路徑也存在明顯差異。當西歐還處在漫長的封建主義國家時期,強大貴族控制着地方政治主權,王權國家對地方社會幾乎無能爲力的同時,被視爲“將社會行動改造爲理性的有組織行動的特定手段”的現代官僚制早已在秦始皇以來的中國得到充分發展。②[德]馬克斯· 韋伯:《經濟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林榮遠 譯,第2卷(上),第1103頁。正是通過官僚制、郡縣制的建立,秦始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支撐國家起源並成長的家族血緣關係的制約,實現了對家族、貴族等分封性地方權力的限制,加強了對地方社會的控制。
在通往現代國家的道路上,當中國的“皇權”不同程度地隔離於“郡縣”以下的基層社會之外時,最先出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西歐,國家在資産階級與封建貴族爭取發展空間的推動下,開啓了進入社會之中的進程:擴張的法院體系向社會灌輸國家意志並打破碎片化的習慣法或封地法;完善的徵稅機構爲國家機構的擴張提供能力保障;標準化的軍隊爲徵稅提供有力支持。伸向社會的這“三大觸手”,幫助國家獲得了“強有力”的權力。但是,推動國家變得“強有力”的資産階級也對國家的力量保持警惕,其結果是促進了制衡強有力國家的市民社會的成長。③[加]卜正民、傅堯樂 編:《國家與社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張曉涵 譯,第9頁。因此,進入現代國家階段,“控制與反控制”“制衡與反制衡”構成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主導進程。
然而,歷史“各行其道”,造就近代歐洲的關鍵因素——工業化、資本主義並未在中國發生。中國經歷了漫長的農業社會,農民是這一社會的主體部分。郡縣制在打破地方社會權力對國家權力阻隔的同時,也造就了城鄉分離的二元政治格局。郡縣城市成爲國家權力的中心,廣大的農村社會位於這一權力體系之外。高度分散的農民基於血緣、地緣、習俗等自我整合,與國家保持着若有若無的聯繫。直到20世紀,中國開啓了現代國家建設,面臨的仍是一個沒有商品和資本等生産要素進入的傳統農村社會。時至今日,農民仍然構成中國社會的主體部分。中國的農民社會具有“韌性”特質,深刻影響並伴隨着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的進程。④陳軍亞:“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中國社會科學》12(2019):82—99。
農業社會和商業社會在社會結構、組織化程度、組織方式等方面的質的差異,決定了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及二者的互動模式存在根本差異。如果說國家控制與市民社會的反控制主導着西方現代國家形成進程的話,那麽,對於中國的國家化進程而言,誕生於血緣關係的擴展與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國家具有何種特質?這種特質如何介入、滲透、整合農民社會而進入現代社會?農民社會又以何種行爲作出回應?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甚至更具主導性的內容。
(三)經驗的維度:中國國家化進程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處於不同歷史條件與發展空間中的中國的國家化,産生了豐富的政治實踐,但理論的生産和供給相對於實踐的豐富性要貧瘠得多。基於先行現代國家形成路徑與模式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作爲處於這一實踐進程中的重要參與者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卻並未産生與之相匹配的理論,這些素材的價值更多是體現在對先行模式的驗證或對已有理論的註釋。鑒於此,國家化研究的中國議題的提問方式或重點,並非是“標準的(或預設的)現代國家”在中國如何形成,而應是“現代中國”如何形成。這二者之間存在研究視角、認識方位的根本差異。前者是由外向內看,即將外部先行者作爲參照,遵循“(作爲標準的)現代如何—如何轉型—如何接近(標準)現代”的思維邏輯;後者則是基於中國內部的經驗視角,遵循“傳統如何—如何變化—現代如何”的認知順序。
古代時期的中國國家形態,人們多以“皇權不下縣”加以描述和概括;但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無論是橫向覆蓋還是縱向深入,都存在着豐富的差異性。在有些地方,國家對社會控制程度的差異可能和地方與中央的距離成正比——在地理空間上處於邊緣位置的地區,往往也是國家政權的邊緣地區,郡縣建制並未覆蓋,即使是賦稅也難以進入地方社會內部,國家權力“懸浮於”村落社會之外。但歷史同時也表明,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程度,也可能和地方與中央的距離成反比。例如,在中國北方的某些地區,雖然同樣處於地理上的邊緣地帶,但因爲戰爭和軍事上的重要性,國家建制及軍事力量較早進入這一地區。此外,同樣處於地理位置和國家政權核心地帶的不同區域,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也存在顯著的差異。如果從賦稅角度觀察,國家在華北、東南地區村落社會中有完全不同的運行體系和控制方式。①陳軍亞:“因税而治:傳統時期國家治理的機理”,《雲南社會科學》4(2019):51—59。
從社會的角度看,處於“皇權之外”的中國社會內部也存在着豐富的地方差異性。雖然“家戶制度”是中國的基礎性制度②[美]弗朗西斯·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毛俊杰 譯,第11頁。,決定着中國社會的基礎結構。但由於國家整合力量的有限性,社會處在長期的自我演進中,並在演進中形成地方性制度的叠加。在家戶制度之上,叠加了區域性的亞制度形態,由此形成了以家戶制度爲基礎的多種區域性制度。例如,華南地區的家戶—家族制度,華北地區的家戶—村莊制度,西南地區的家戶—村寨制度,西北遊牧地區的家戶—部落制度,西藏地區的家戶—莊園制度,等等。這些多樣化的制度形態,構成了多樣化的社會形態。生活在不同社會形態下的農民,其行爲表現出多樣化的地方屬性。
差異化的地方社會,決定着20世紀中期以後中國國家化進程所面臨的不同起點,也爲其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議題。一是現代國家意志如何進入一個差異化的地方社會。對於有的區域,國家化的議題可能是通過某種策略或路徑在一個“無國家的社會”建立國家意識的問題;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則是國家意志如何更深地介入地方社會的問題。二是面對國家意志的輸入,差異化的地方社會以何種方式作出何種回應,二者之間形成何種關係模式。三是國家對地方社會的差異化回應做出何種調適,由此産生了何種結果。
三 作爲方法的“國家化”研究範式
國家化是一種過程。在整合社會的過程中,一方面,國家通過與社會的互動成就了自身形態,即國家建構;另一方面,國家也實現了對社會的整合,將一個離散的、與國家保持鬆弛聯繫或者可能存在離散張力的社會,建構成一個在國家政權影響之下的政治共同體,它體現的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雖然這兩個方面都是國家理論研究的重要主題,但在實際運用上,二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範式與場域”之間的張力。國家化的研究範式,是通過認識視角的內在性、解釋路徑的歷史性、研究範式的包容性,來克服二者之間的張力,並獲得作爲研究範式的一般性意義。
(一)國家建構:“外在視角”的解釋限度
“國家建構”是國家研究中的經典概念,體現了國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西方話語體系中,預設了一個通往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制度的邏輯:先有現代國家的建構,之後纔有現代經濟的騰飛,然後纔有逐步民主化的過程。這一發生在西方特定空間事件上的先後順序,被賦予觀察和解釋其他國家的國家建構與民主制度之間的一般性因果邏輯。②[美]弗朗西斯·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毛俊杰 譯,第11頁。這種研究範式,在國家建構的議題設置上表現出兩種傾向:
其一,用西歐現代國家形成的動力機制去觀察其他國家的建構路徑後和成效。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中,這種觀察、解釋的參照維度得到特別強調。那些對歐洲歷史軌迹反思而得出的一些理論視角,如戰爭與社會動員、財政汲取、官僚機構的擴張、中央權威的增強等西歐現代國家形成的路徑,被運用於觀察和比較20世紀晚期獨立的新興國家的建設路徑。這些國家因無力從社會中提取足夠的稅收從而增強財政能力,或者因官僚體系在執行政策方面呈現出較弱的自主性,表現出“軟弱國家”“失敗國家”的特徵。“軟弱”“失敗”的原因在於,戰爭頻率的降低不需要長期的戰略動員,由此也就沒有帶來國家能力的擴張。①[美]卡爾斯· 波瓦克斯、蘇珊· C.斯托克斯 編:《牛津比較政治學手冊(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唐士其 等譯,第223、225、318頁。福山(Francis Fukuyama)對國家建構問題的特別關注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前提:對“軟弱”“失敗”的國家而言,如何實現強有力制度的移植是一個既重要又複雜的問題。②[美]弗朗西斯·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7頁。
其二,觀察和檢驗其他國家的國家建構與民主化進程的關係,即民主轉型問題。李普塞特(S.M.Lipset,1922—2006)將二者的關係概述爲現代化將會導致民主制。如同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左派對福山的國家建構理論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立場的批評,二者之間的關係源於歐洲這一地區性的經驗。歐洲商業、貿易與國家形成的路徑表明:對統治者來說,內部戰爭動員與經濟發展,通常意味着要在動員與參與之間進行取捨。簡言之,納稅就要有代表權。遵循這一解釋路徑的研究,用大衆參與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來觀察和解釋其他地區的國家表現。例如,瓦爾納德(David Waldner)通過比較土耳其、敍利亞、韓國、中國臺灣的經濟與政治發展的關係得出結論:土耳其、敍利亞由於過早的大衆參與,對經濟發展産生了不利影響;韓國、中國臺灣經濟的成功,在於消解了政治參與和分配壓力。③[美]卡爾斯· 波瓦克斯、蘇珊· C.斯托克斯 編:《牛津比較政治學手冊(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唐士其 等譯,第223、225、318頁。
然而,適用於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理論,衹能得到有限經驗的支撐。例如,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研究表明,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之間並無直接關聯;它們在統計上的相關性,源於富裕民主國家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因爲,貧窮的民主國家更容易崩潰,而類似情況在富裕民主國家較少發生。久而久之,富裕民主國家在統計上就佔據了較大比例。④[美]卡爾斯· 波瓦克斯、蘇珊· C.斯托克斯 編:《牛津比較政治學手冊(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唐士其 等譯,第223、225、318頁。理解民主化的方式,首先需要將其區分爲不同的進程,對不同進程進行不同的理論分析。對於成長於20世紀晚期的國家而言,其國家建構在完全不同於早期西歐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中發生,不僅切斷了戰爭與國家形成的直接聯繫,而且不同程度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削弱了傳統重商主義在國家形成與現代化之間的紐帶關係。戰爭、動員與參與的研究路徑,對於驗證歐洲國家建構理論的解釋力做出了貢獻,但對於認識這些國家形態建構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表現出“外在視角”的限制。“外在視角”的解釋路徑所具有的風險是:它“規定”着人們的觀察視角和思維方式,影響人們的學術洞察力。因此,可能忽視那些被遮蔽於這些視角之外的事實,以及這些事實的理論生産力。
對於中國的國家建構而言,歷史過程始終是“本土化”的,中國的現在不是歐洲的過去,歐洲的現在也不可能是中國的將來。對於政治學研究而言,比較是一種重要且有效的研究方法,它有利於在差異性或共同性的比較中更好地認識事物的本質特徵。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案例和指標選擇的有效性。對於兩類完全不具備可比性的國家而言,以一類國家建構的路徑和指標爲參照,顯然並不利於發掘被比較者真正的動因和路徑。這可能正是主張“本土研究”的學者所強調的:通過對特定場域的研究,發現國家建構的本土動因和路徑,而不是在比較中檢驗已有動因和路徑的“本土適用性”。因此,中國國家建構的認識視角和解釋路徑,既不是“爲什麽中國沒有成爲西方”,也不是“爲什麽西方沒有成爲中國”,而需要從中國的國家發展和形態演進的政治實踐中提煉研究議題,並探尋這些實踐背後的規律。
(二)國家與社會:與特定地域相聯繫的研究範式的解釋力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衍生於國家研究領域。它的出現,代表着國家研究範式的轉換。從二者的關係而言,國家研究範式的轉換大體經歷了“社會中心論”“回歸國家學派”“社會中的國家”三個階段。每一種範式轉換的背後,有其關於政治實踐背景的深刻理解和認識。
以多元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爲視角的“社會中心論”取代將國家視爲有影響力和自主性的傳統解釋模式後,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仍是西方社會科學中的主要研究範式。這一研究範式將“國家”視爲一個沒有自主性、衹是爲社會集團提供競爭場所的平臺,政府的政策由社會集團之間的競爭或結盟所決定,決策過程則是在利益集團之間進行利益分配的過程。①[美]彼得· 埃文斯、迪特里希· 魯施邁耶、西達· 斯考切波 編:《找回國家》(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3、7頁。它具有鮮明的英美國家特徵。因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似乎是自發産生並自主演進的,與作爲政治組織的國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由此,不同國家的組織形式和形態差異既不重要,也無需解釋。但是,“社會中心論”對“社會很重要”的強調,逐漸在政治實踐中遭遇到“忽視國家”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應對30年代經濟大蕭條逐漸興起的凱恩斯主義將國家干預及其重要性帶入政治實踐場域;另一方面,70年代以後,大量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出現也使得人們很快看到,歐美的自由民主模式並不能在這些國家被簡單移植或複製。“西方宏觀社會科學領域正在進行一場範式轉移,該轉移蘊含着對國家與經濟和社會之間關係的一種根本性重新思考。”②[美]彼得· 埃文斯、迪特里希· 魯施邁耶、西達· 斯考切波 編:《找回國家》(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3、7頁。思考的結果使人們認識到,“國家很重要”;於是,將國家視爲獨立行爲主體並對社會施加影響力的“國家中心論”研究範式被以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爲代表的一批學者“找了回來”。20世紀60—70年代,還在求學中的米格代爾(Joel Migdal)看到了亞非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社會衝突,以及國家與社會衝突之間持續不斷的鬥爭,爲他思考國家與社會之間誰決定誰、誰影響誰提供了思想源泉。在反思“社會中心論”“國家中心論”將國家和社會視爲“整體性”“同質性”的概念、忽略不同國家與社會形態內部差異的基礎上,米格代爾提出了“社會中的國家”的分析範式,將國家區分爲一個具有觀念整體性和實踐多樣性的綜合體,從社會形態的多樣性中解釋國家實踐的差異性,從而實現了國家研究範式的轉移。
從本質上說,以上三種範式,都是以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立—衝突”關係作爲共同研究取向。儘管“社會中的國家”路徑對“社會中心論”和“回歸國家學派”各執一端的偏激取向做出批評,通過建立國家與社會之間“關聯和互動”的分析框架,實現了二者從“各執一端”到“更加平衡”的轉變③[美]喬爾· S.米格代爾、阿圖爾· 阿里、維維恩· 蘇 主編:《國家權力與社會勢力》(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郭爲桂、曹武龍、林娜 譯,第334、339頁。,但這並未改變“對立—衝突”的認識取向,衹是“對立—衝突”關係的結果不同。米格代爾將國家與社會之間爭奪控制權的鬥爭視爲一個競技場。“這些鬥爭也不總是在大規模的社會力量(如整個國家、社會階級、市民社會等)之間、在宏大的層面上進行。爭奪統治地位的鬥爭發生在社會各種不同競技場中。”④[美]喬爾· S.米格代爾:《社會中的國家:國家與社會如何相互改變和相互構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李楊、郭一聰 譯,第104頁。因此,“更加平衡”的“社會中的國家”範式,強調的是國家與社會在控制權的爭奪中實現了彼此增強的正和博弈,而不是“你強我弱”的此消彼長。
“對立—衝突”關係之所以成爲共同的認識前提,源於特定的實踐背景。18世紀的歐洲,成長中的資産階級尋求獲得參與國家事務的政治權力,希望能夠在家庭、生意等私人領域與國家領域之間構築一片空間以防備國家對私人權益的侵犯。雷蒙· 威廉斯(R.H.Williams,1921—1988)將之表述爲將“我們的厠身之處”與作爲“權力機器”的國家區分開來。⑤[加]卜正民、傅堯樂 編:《國家與社會》,第8頁。雖然對“市民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界定,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存在歐陸的“二元和對立”傳統與英美的“衝突和控制”傳統的區別,但無論哪一種傳統,將其分析框架簡單挪用於中國,都存在拉抻這一框架的歷史內涵及其適用廣度,從而産生誤讀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風險。
由於缺乏對“歷史場域和過程”的理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中國研究呈現出兩類傾向:一是靜態研究的碎片化。表現爲,對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即使在同一時期,由於觀察視角的不同,不同研究之間也存在彼此矛盾的結論。二是“植入式”研究的簡單化。“市民社會”的解釋模式暗示着中國的社會變遷採取了與歐洲相類似的形式,並將導致類似的結果。但是,“市民社會”這種早期歐洲民主制發展的概念,顯然並不適合研究中國這樣一個完全不同且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不斷有研究表明,中國國家和社會所發生的變化,與社會對國家的反抗並沒有太大關係,發生在這一關係之外的力量表現出更大的影響力。①塗肇慶、林益民 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第68頁。另一些研究也表明,中國市民社會的成長路徑,並非在於從制衡國家中獲取力量,而是在國家的主導下成長。②[加]卜正民、傅堯樂 編:《國家與社會》,第51頁。國家進入社會填補“私人”與“國家”之間的空白,是一種被社會“需要”的力量。
(三)“國家化”在中國研究中的取向和立場
作爲“過程”的國家化研究,在認識視角、解釋路徑、研究取向上與以上研究有所不同。在認識視角上,國家化將“現代”置於從過去出發的歷史進程來認識,將國家形態的建構視爲一種從歷史出發的連續進程。現代國家的特徵由其內部的歷史條件及演變過程所決定。在不同國家,由於歷史和傳統不同,國家化的起點和條件也不同,這決定了其路徑、方式、國家形態的不同。歷史和傳統因素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重要作用,意味着通往“未來”或“現代”的路徑不可能是一種“單一進程”,或者終結於一種“單一形態”,而是一個充滿了差異,在既有經驗中難以“推導”或“預測”的進程。基於國家化是一個多樣性的過程,對多樣性過程的研究必然帶來理論的豐富性。
在解釋路徑上,國家化研究更加強調國家建構的社會基礎,更加關注國家建構在何種社會基礎之上發生。從歷史過程的“多樣性”“差異性”中探尋國家的起點、條件與其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從內部因素、歷史軌迹中觀察和解釋這些國家在通往現代國家過程中的路徑差異,以及導致這些差異的因素和機制。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中,國家化更加強調“歷史中的過程”。米格代爾“社會中的國家”的分析路徑,雖然將“過程”因素引入其中,相對於以往的結構—功能主義分析而言,它更加強調“互動”過程對結果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拋棄了由結構決定結果的“功能主義”路徑,但他強調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而不是互動本身的長期歷史過程。他雖然將歷史因素引入視野之中,但更多體現的是靜態的歷史,將橫切面的歷史作爲分析問題的起點。作爲一位從事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學者,他也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發展,認爲這些國家存在大量的家族、部落、宗教組織等社會勢力,國家權力與社會勢力之間爭奪控制權的努力決定了國家能力。但是,這些不同的社會組織在歷史上如何形成,經歷了何種變化,這些形成和變化過程與國家之間是何種關係,在他的“過程分析”中並未充分展現。簡言之,歷史之於米格代爾,衹是一個分析起點,一個結構性存在。而“國家化”的分析路徑,是將當下社會形態的豐富性、形態內部的差異性置於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大歷史進程中來認識,既關注當下國家與社會“整合與回應”的複雜互動過程,也關注決定當下互動複雜性的長期歷史形成過程。雖然魏昂德(Andrew G.Walder)在20世紀末曾指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面臨着從靜態描述向變遷解釋的挑戰;但遺憾的是,囿於既有研究框架的“規定性”,在已有的文獻中很少看到適合“變遷解釋”研究框架及其成果的出現。注重“過程”的國家化研究,不僅具有米格代爾意義上的“互動過程”的解釋視角,也具有魏昂德所關切的“歷史變遷過程”的研究維度。
在研究取向上,國家化更注重研究範式與其實踐場域之間的匹配性。中國擁有與歐洲不同的歷史進程,因而需要將這種“不同”置於學術研究中並獲得其重要性。國家化的研究範式,在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中包括兩個面向:一是參照和比較的面向。在通往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的國家與經濟、社會的轉型是否帶來“市民社會”的興起與成長,中國的“市民社會”具有何種特徵,與國家之間如何互動、發揮了何種作用。二是本土和歷史的面向。如同西方資産階級在其現代國家形態演化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中國的農民群體與國家形態演化進程相伴始終。新中國建立後,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開啓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任務所要面對的也是農民這一廣大群體。作爲中國社會群體的主體部分,他們的行爲及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通往現代國家的道路和方向。這一群體及其與國家的關係,既不容許被政治學研究的國家議題所忽略,也很難在西方經典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框架內尋求嚴絲合縫的解釋力。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所有政治實體都會面臨的問題。對於中國的國家化進程而言,回答這一問題有兩個前提: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什麽樣的國家”“什麽樣的社會”,其次纔是“什麽樣的整合”“什麽樣的回應”以及呈現了“什麽樣的關係和邏輯”。從中國國家形態演進和社會變遷的長時段歷史進程中,分析二者的關係與關係的演進,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形態的變化,以及對這種變化做出更具解釋力的模式界定。鑒於國家化研究的目標是,發現未經既有理論表達的一般化邏輯;因此在研究取向上,更加注重理論“建構於田野”而非“取自於書架”。
(四)國家化:一種“可通約”的研究範式
國家化是一種基於中國本土經驗的研究範式,但通過概念、邏輯、方法上的“通約性”,它可以整合既有研究框架,獲取超越本土經驗和範式競爭 性的“一般”研究能力。
從概念而言,無論“國家”的定義展示了多少種描述角度,“政權”是其核心要素。作爲國家核心要素的政權需要在由人口和疆域組成的“社會空間”中運行。無論作爲何種形態的國家,其誕生以來,無時無刻不在實踐之中。無論政權的組織形式存在何種差別,國家向社會輸入意志,建立其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將人口和疆域控制在政權範圍之內,是作爲政權組織形式的國家的共同目的。這一實踐過程,在傳統國家時期,主要通過直接支配或強制實現;隨着現代國家的建立,主要採取間接滲透的方式。①[美]克里斯多夫· 皮爾遜:《論現代國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64頁。正是在此意義上,國家扮演的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建構者的角色。②[美]邁克爾· 曼:《社會權力的來源》(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第2卷(上),第105頁。其建構的目的,是將一個分化、離散或者具有分化、離散張力的社會,整合爲一個擁有國家意識的政治社會共同體。否則,面對社會分化及由此帶來的危機,國家將會面臨社會發出的“我們是誰”的質疑。但整合並非一個單一進程,作爲國家整合對象的社會,會對國家的整合行爲做出回應。國家在與整合對象的互動中,既完成了整合社會的實踐過程,也完成了自身形態的建構過程。因此,國家整合社會,社會回應國家,是國家實踐的一般化邏輯。
不同的研究方法,服務於不同維度的國家研究。國家的實踐,可以表現爲制度形態的變化,也可以表現爲組織結構的變化。但無論制度還是結構,人都是其實踐主體。制度或結構的豐富性和差異性,可以通過人或人的行爲表現得以觀察。人的行爲處在特定的制度或結構之中,受到制度或結構的約束,也決定着制度或結構的形成與變遷。因此,人或人的行爲,不僅可以打通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也得以觀察國家與社會形態的互動和變遷。國家化以處於制度、結構中的人和人的行爲作爲分析依據,可視爲其研究方法的“一般性”。
通過概念、邏輯和方法的“一般性”,國家化的研究範式,將國家形態、社會形態和二者互動方式的差異,置於其“概念和邏輯的一般性框架”之下。這一“一般性”研究範式,不僅有助於推動基於中國經驗的國家理論研究,也有助於對不同時空中差異化國家實踐的理解和認識,從而豐富國家理論的研究範式,拓展研究領域,構建更爲多樣性的國家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