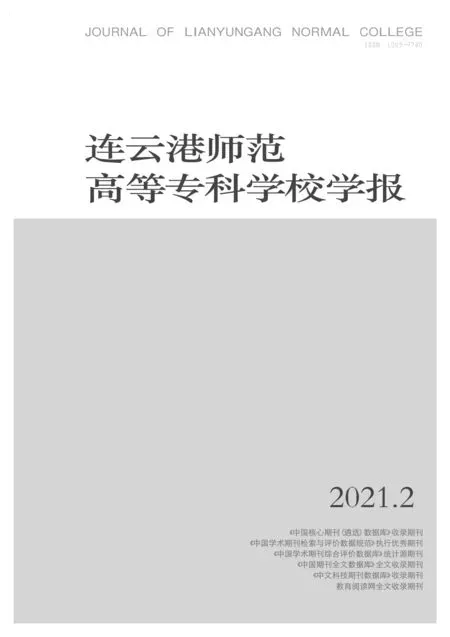实然与应然视域下奈达的功能对等论
杨司桂
(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遵义 563006)
实然与应然是哲学领域中的一对范畴,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实然是应然的前提和基础,为应然之源;应然是实然的向往和追求,为实然之归。近年来,译学界的一些学者借用了这两个术语,对翻译研究或翻译教材中存在的混乱现象做了澄清与厘定,为认识、解决翻译学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视角。冯全功指出翻译的忠实应该属于应然范畴,应该放在第一位[1];蓝红军认为不能把翻译研究中的实然与应然混为一谈[2];苗宁与刘扬分别运用实然理论与应然理论对翻译教材的设计与编写谈了各自的看法[3-4]。笔者在此也借用哲学上的这一对术语重新审视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借以说明这一理论在翻译学上的独特价值。
一、翻译的实然及其影响因素
实然指涉的是现实的实有,是事物的实际存在状态,属于事实陈述和认知理性的范畴。翻译的实然指的是现实中的翻译状况,也就是翻译的实际存在状态。按理说,翻译把意义从一种语言传译到另一种语言,其实质是使固定不变的客观意义越过语言疆界,使之在另一种语言中得以“存活”。但是,“面对两种语言与思维的转换,翻译总是‘失去’的艺术,想完全传达出原文的一切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5]87。对于翻译的这一实然状态,奈达曾做过很好的阐述:
不管是针对对应符号被赋予的意义来说,还是针对这些符号排列为词组和句子的方式而言,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就有理由认为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等。这样,也就不存在完全精确的翻译。翻译的整体效果可能会接近原文,但不存在细节上的完全对等。[6]156
我国近代翻译家、文学家林语堂也发出与奈达相似的感慨:
译者所能达到之忠实,即比较的忠实之谓,非绝对的忠实之谓。字译之徒,以为若字字译出可达到一百分的忠实。其实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到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可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7]51
现代翻译家许钧指出,“语言之间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对等关系和对应关系,因此在翻译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的翻译”[8]245。实际上,任何译者都不可避免地给译文加进主观成分,不仅在理解原文信息,选择译文词汇、语法形式和语体时受到自己对原作者及原信息所持态度的影响,而且可能出于对政治、社会或宗教信仰方面的考虑而有意识地改变信息内容[6]154-155。可见,绝对对等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翻译家的一种向往、一种精神追求。
现实中的翻译,即翻译的实然,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文本内和文本外因素的限制,不得不采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技巧与方法对目标语文本进行调整、改写或操控的结果。那么,翻译的实然是如何产生的?笔者认为,翻译实然状态的形成主要与语言、文化、思维、意识形态、赞助者以及诗学观等因素有关。
第一,翻译之实然与语言因素有关。翻译之存在是语言差异造成的,如果没有语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翻译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语言之间的差异也导致翻译必然存在实然状态,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语音给翻译实然状态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歌翻译之中。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诗歌翻译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语音节奏感和韵律感的处理。节奏感和韵律感属于语音特性,翻译起来难以处理,比如中文诗歌中的平仄声就难以译成英文,英文中的押头韵也难以译成中文。词汇给翻译造成的困难也不少,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完全对等的词汇不是很多,这不仅体现在一个词的外延上,更体现在其内涵上。例如:汉语中的“颜色”一词包括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而英语的“colour”一词只包含red、orange、yellow、green、blue、purple 六种颜色;汉语“狗”“龙”等词的内涵与英语“dog”“drangon”词的内涵就无法对译。语法对翻译实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序、单复数和时态等层面,如印欧语系语言的语序比较自由,因为它们一般用词性变化来表示句法关系,但汉语的语序则相对比较固定。
第二,翻译之实然与文化语境有关。文化语境指的是交际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整个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非语言场景[9]199。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言行举止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处处都有文化的烙印,时时可见文化的踪迹”[10]V。语言活动如此,翻译活动亦然,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一个个词语,但面对的是两大文化圈层[11]19。民族文化或特定文化语境对于一个词语或语句的生存及发展具有巨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词语或语句的灵魂。诚如奈达所言,要准确了解一个词语的意义,就需了解该词所处的文化语境,因为一个词只有被放在整个文化语境中才有意义[6]244。由于不同语种的使用者在地理环境、价值观念、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翻译就不可能实现两个语种之间的绝对精确与对等,只能做到相对对等。奈达曾就此表明,“我们在文化语境中进行翻译,我们所进行的翻译也是为了文化语境,而我们又是文化语境的一部分,所以,在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内,绝对客观的翻译是不可能存在的”[6]244。
第三,翻译之实然与思维因素有关。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知活动的过程”[12]1194。这里所说的思维因素主要指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13]30。个体的思维方式因职业、性别、知识结构、教育程度等不同而有所差异,“同一民族的人,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同一文化氛围中,其思维方式存在共性。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14]25。相同的思维方式使不同语种的翻译成为可能;不同的思维方式给翻译造成一定的困难:两者都能导致翻译的实然。一些译论家曾围绕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展开讨论。翻译家傅雷在给罗新璋的信中曾明确指出,中西思维方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维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偏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殊难彼此融洽交流”[7]772。陈宏薇与李亚丹归纳了中国与英美等国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注重伦理,英美人注重认知;中国人重整体、偏重综合性思维,英美人重个体、偏重分析性思维;中国人重直觉,英美人重实证;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英美人重逻辑思维[14]25-30。这些思维差异,势必对汉英互译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四,翻译之实然与意识形态有关。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12]1495。在翻译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及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框架,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这样,意识形态对原文的正确传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许钧对此做过阐述:
就译者而言,他可以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以积极方式去选择拟译的文本,去确定翻译的策略或方式,去解决原文语言与“文化万象”给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障碍;译者也可以不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在翻译委托人的强权下,消极地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范围内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8]216-217
可见,不管译者是否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会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如此,译者还会竭尽全力利用各种翻译策略或方法,力所能及地通过译作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一倾向在中国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林纾、鲁迅等人都曾借翻译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抒发远大的政治抱负。
第五,翻译之实然与翻译的目的有关。“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受到一定的动机所驱动,都为着一定的目的去进行。”[8]227如“达志通欲”“传令知会通耳”“使相解”“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15]147等,这些不同的翻译目的对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了翻译的实然。一些特殊文体的翻译如商品广告、旅游广告等尤为如此,例如我国出口美国的“轻身减肥片”英文译名原本是“Obesity-reducing Tablets”,后来改为“Slimming Pills”,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人乐于接受这一产品以打开销路。显然,译名的更改受到了目的制约——为了促进产品营销,翻译者不得不弱化汉英语言之间的对等性,形成了独特的翻译实然。
第六,翻译之实然与主流诗学有关。勒菲弗尔认为主流诗学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文学手段、文学体裁、象征、文学主题,以及原型情景及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文学作用的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16]26。生活在任何一种文化圈里的人,都有特有的主流诗学,而翻译是不同语言间的跨文化交流,因此主流诗学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在所难免。比如,译者在理解原文阶段常常带着一定的主流诗学观去阐释或解读原文本;在译文表达阶段则在主流诗学的引导下将原文译为符合社会审美取向或诗学特征的译本,目的是为了取悦目的语读者,以保证译作有人阅读并为目的语社会所接受。
二、翻译的应然
应然指的是事物应当如此,说明事物将要怎样并使事物不断趋向完美的境遇,指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具有前瞻性及预测性。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及道德信仰,具有主观意图性,希望客观世界能满足主体的愿望。具体而言,就是希望把客观世界的实然状态改造成符合主体的意图或理想的愿望。而翻译的应然指涉的是翻译应当如此,或者说,根据翻译的实然状态决定其走向的问题,使主体的应然取向这一主观愿望得以实现。
关于翻译应然的走向问题,古今中外很多的译论家和翻译流派所提出的翻译原则或标准均有所涉及,反映了译界变革现实翻译活动实然状态的愿望。笔者试对此进行梳理,以便读者对诸家翻译应然之立场有进一步的了解。从三国至唐宋时期,我国的佛经翻译较为盛行,翻译者所提出的翻译主张便体现了翻译之应然。例如,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所说的“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实则为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所说的“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以及慧远的“厥中之论”、鸠摩罗什的“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论、玄奘的“圆满调和”论,均表达了其翻译应然之主张。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奉先贤译论为圭臬,不越雷池”[15]44,因而在翻译方面并无建树。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科技翻译本身的性质有关。然而,从清末到民国初期,学术及文学翻译并举,许多翻译家和理论家提出了各自的翻译应然观。例如:马建忠提出“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7]192的主张;林纾结合自己翻译《黑奴呼天录》的体会,在该译作的例言中表达了翻译应该“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7]229的见解;严复则认为翻译应该做到“信、达、雅”,具体而言,就是“译文要‘信’,辞必‘达’意;辞要‘达’意,必求‘雅’正”[15]172。
在现当代翻译史上,有更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应然观,最为典型的要数鲁迅、陈西莹、曾虚白、林语堂、傅雷、钱锺书、刘重德、许渊冲以及辜正坤等学者。鲁迅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7]373,而陈西莹于1929 年在《新月》期刊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的《论翻译》一文,对严复的“信、达、雅”提出了批评,认为翻译应该追求“三似”,即“形似”“意似”及“神似”。对于陈西莹的翻译应然取向,曾虚白进行了批判。曾虚白认为“好的翻译,当然要注重‘神韵’,要把作者灵魂的手指在我们灵魂中音板上所叩出来的声音,用最精巧的方式表现出来”[7]489。之后,林语堂提出了翻译应该“忠实、通顺、美”,傅雷认为应该追求“神似”,钱锺书指出翻译应该“化境”,刘重德提出翻译应该“信、达、切”,辜正坤则提出了翻译“多元互补”论。可见,翻译应该结合多种标准,发挥各标准之优势。
很多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翻译实践或理据,对翻译应然之取向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较为典型的有西塞罗、哲罗姆、奥古斯丁、路德、多雷、德莱顿、泰特勒、卡特福德、施莱尔马赫、韦努蒂等。西塞罗认为不应进行字当句对式的翻译,而应把原文语言总体风格保留下来,进行演说家式的翻译。哲罗姆也认为翻译不应字当句对,而应灵活处理,不过对于《圣经》这一特殊体裁,他认为应该直译。奥古斯丁尽管没有从事过大量的翻译实践,却对翻译发表了独到见解。他认为翻译应该依靠上帝的感应,翻译时应把着眼点落实到词的形式上和结构上。路德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兼翻译家,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去翻译《圣经》,同时提出翻译活动应该遵循七条原则。法国语言学家、翻译家多雷则认为翻译活动应该依照五条原则进行。多雷为了坚守自己的翻译观,不幸被教会处以火刑。德莱顿把翻译分为逐词译(metaphrase)、释译(paraphrase)及拟译(imitation),认为逐词译与拟译很极端,应该采用释译。较为系统且科学的提法要数英国翻译家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1)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3)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性[17]9。卡特福德则认为,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替换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18]20,卡特福德突出的是“等值”,是一种理想化的翻译应然。
此外,以歌德、施莱尔马赫、沃尔特·本雅明、贝尔曼等为代表的新直译派,以及以韦努蒂为首的异化论者都认为翻译应以保存原文的异质性为导向,主张翻译就是要力求翻译原文的异质元素。当代译家由于各自的研究语境及其出发点或目的不一,有关翻译之应然的立场或见解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格特认为翻译应该是一种跨语际阐释行为,翻译功能目的论者认为翻译应该是一种有目的之行为[19]105;霍恩比觉得翻译应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翻译活动来处理[20]39;列维认为翻译应该是一种不断做出决定的行为[21]40;女性主义翻译论者认为翻译应为女性服务,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22]20;后殖民主义翻译者认为翻译既是殖民化的工具,又是消解殖民化的工具,主张翻译应该为反对欧美霸权、重塑殖民地民众文化身份服务;国内学者陈历明认为翻译应该是一种复调的对话[23]。总之,各家各派根据各自的研究背景及目的对翻译应然之立场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充分展示了翻译应然的多维性,使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
三、奈达功能对等论的应然属性
奈达对西方世界的传统翻译理论进行深入阐述后,根据自己在翻译工作坊的切身经验及体会,对翻译的实然做出判断,提出了他的功能对等论,这一观点主张翻译应该追求一种交际上的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对翻译的要求与一切翻译理论的应然追求一样,都为翻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规范,即要求翻译“应该”是什么。
奈达的提法非常在理。张冬梅认为论证一个应然命题是否有效必须涉及两种根据:一是命题设立者心中的价值目标;二是应然之原则与价值目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若按此应然原则行动的话就会实现目标[24]55-56。这为我们推论奈达的应然命题是否有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奈达提出的翻译应然命题的价值目标是,使翻译能发挥交际作用,让接受语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意义以及原作者的意图。为了达到这一价值目标,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这一翻译原则,并把它细化为最低标准和最理想化标准。奈达提出的这一翻译原则能否达到其价值目标呢?换言之,如果按照功能对等这一原则去做,能否实现“让接受语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意义以及原作者的意图”这一价值目标呢?奈达的交际功能对等论要求翻译必须“清晰地反映原文的意义和意图”[6]166,并就意义、风格、表达和读者反应四要素强调注重原文意义的翻译以及原作精髓和风格的传达[6]164,主张翻译的首要之点就是翻译原文的意义[9]13。交际本身就是要使交际主体理解对方的意义及意图,因此奈达提出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要想使译文的意义及意图抵达目的语而为受众所接受就必须考虑读者因素:倘若译文生硬别扭、晦涩难懂而不为读者所接受,翻译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如果考虑到读者因素,翻译就会取得成功。这几乎是中外译学家达成的共识,就连一贯主张异化的韦努蒂也曾一度做出让步。韦努蒂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指出,译文要注重流畅性及可读性,要充分考虑到接受者的感受[25]273。奈达的功能对等论蕴含的重要一维就是要考虑读者的反应,做到译文流畅、不带翻译腔。奈达为了让《圣经》得到更好的传播,要求译者准备三种译文[9]31,分别是用于教堂或其他宗教场所的译文、为高文化水平读者准备的译文、为一般大众准备的译文。可见,奈达非常注重译文对于读者而言的可理解性,他还把译文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列为重要的考量参数[9]173,作为对译文的评价标准。鉴于此,翻译如果遵循功能对等的原则,就能实现其价值目标——让接受语读者能够理解原文的意义以及原作者的意图。
此外,“道德原则之应然有效性强调的是原则内容的正确性以及在道德意义上的公正性,强调的是道德原则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所谓道德原则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可以归结为合目的性”[24]115。“这里的合目的性,指的不是合乎个人或少数人的目的,而是合乎规范适用范围内的全体或多数成员的目的,即公共意志。规范只有在符合公共意志也就是全体或多数人的目的的情况下,才会被广泛认同、广泛接受。”[26]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强调翻译的交际性以及意义的可理解性,是符合大多数人的交际需求的,因为翻译源于语言交际,“译即易,谓换易言语相解也”[27]3,目的就在于使双方的表达能够为彼此所理解。翻译“就是要把‘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变成使人理解的‘人语’,就是要让讲不同语言的民族达到沟通”[28]2。既然翻译是因语言差异而生,其首要任务就在于促进理解,而“使相解”的关键在于把源语言的意义和表达者的意图传译过来,这正是奈达功能对等论的核心所在。因此,我们认为奈达的功能对等论这一应然性命题颇具有效性,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一种公共的善。当然,翻译实现功能对等的过程未必是一帆风顺的,也许经常陷入悖论。即便如此,翻译不应也不可能放弃对功能对等的应然追求,因为“道德应然的存在本意正在于规范、引导、改变事物的实然状态,以‘应然’规范‘实然’”[24]155。翻译一旦失去“对等”这一停靠的港湾,就很有可能变成一艘“醉舟”而失去方向[29]159。
综上,实然是实实在在的翻译结果,而应然则是翻译应该具备的状态和追求。“对现实实然状态之‘是’的认识导致了主体产生变革现实的愿望,也正是对现实实然状态的了解为‘应然’的现实提供了指导。”[24]175奈达的功能对等论是基于现实的翻译实践并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经验总结,更是一个有关翻译有效性的应然命题。
——再论奈达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