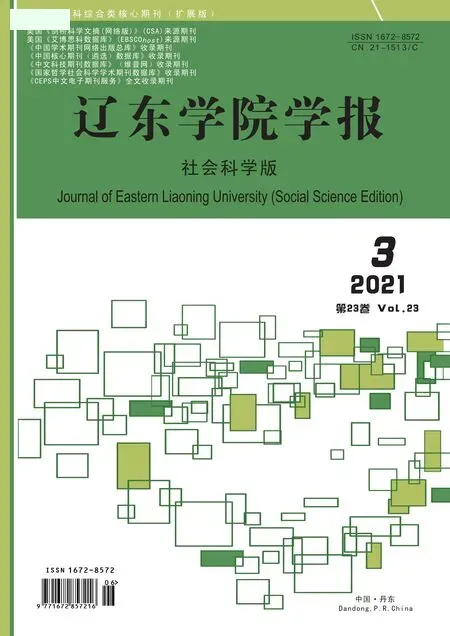陈维崧骈体哀祭文三论
陈建秋
(湖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湖南 长沙 410081)
引 言
所谓哀祭文就是指用于祭奠与悼念死者的相关文体,如诔文、哀辞、吊文、祭文等。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1]154也就是说,祭文是源于早期用于祭天地神灵和祖宗的祝文。两汉以来,逐渐出现由辞赋派生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出的哀悼性散体祭文。在后世文学发展中,祭文的抒情气息也大大增强,内容和写法也更为自由和多样化;诔文,与谥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为了在隆重的祭奠仪式上表彰死者功绩,其作用是为死者定谥号;哀辞,是与诔文性质相近的一种哀祭文体,原来是用于少年早逝的人和年长但不以寿终者,后期题材才逐渐扩大。
元明清三代,为我国哀祭文传统的持续阶段,虽创新不多,但在继承上却成绩显著(1)关于哀祭文的发展脉络,参见章明寿《古代哀祭文发展简说》,《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吴承学、刘湘兰《哀祭类文体》,《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以骈文选本来说,哀祭文体历来都有一席之地。姚燮《皇朝骈文类苑》作为清代少有的“以体系文”的骈文选本,以14大类来析分、概括清代的骈体文佳作。其中卷十则为“哀诔祭文类”,将用于“庙堂”的谥诔哀策和长于“指事述意的诔祭合而为一,收录了洪吉亮、孔广森、李光洛在内的13位作家的23篇哀祭文,哀祭对象包括将军大臣、地方德高望重之士、好友及好友之妻、母等等,比较清晰地展现了清代骈体哀祭文的创作成就”(2)关于《皇朝骈文类苑》的系文方式,参见路海洋《〈皇朝骈文类苑〉对〈骈体文钞〉体例的承与变》,《兰台世界》2013年第29期。。陈维崧作为清初骈文的主要代表作家,与吴绮、章藻功并称“骈体三家”,在其《陈迦陵俪体文集》中,收录15类骈体文167篇,其中骈体哀祭文共有15篇。可见,哀祭文在情感抒发上具有先天的题材优势,常受到众多作家的关注,其题材中“生存与死亡”的主题是非常容易触动人情思的敏感话题,具有很强的情感力量;同时,作者在写作哀祭文时,也常引发自我身世之感。以哀祭文体为切入点研究陈维崧的骈文创作,解读陈维崧骈体哀祭文的结构模式、艺术技巧和文化意蕴,更易于探究陈维崧的情感世界、创作偏好和价值追求,也能更直观地展现陈维崧在提高骈文抒情性和文学性上的贡献[2]。
一、结构模式:随体而变,因人而异
哀祭类文体包括祭文、诔、谥、哀辞,等等,其文体功能虽随着时代发展产生了一些交融和变迁,但不同的哀祭文体仍保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文体体制。王先谦的《骈文类纂》收录了先秦至晚清三百多位作家的两千余篇文章。他在分类整理骈文时,诔为39卷、哀辞为40卷、吊文和祭文为41卷。陈维崧在写作哀祭文时,也注意到了各类哀祭文体的不同应用环境,诔和哀辞、祭文使用了不同的结构模式,并根据哀祭对象的不同,内容侧重点也不同。其诔文和哀辞都是“序文+正文”的模式,而祭文则大体可以分为“写哀+述德+写哀+告飨”的四段式和纯述哀情式。
陈维崧骈体哀祭文中的诔和哀辞,全部采用了“序文+正文”的结构模式。序文部分采用易于叙事的骈散体,主要交代逝者死亡的日期、身份地位、写作这篇哀祭文的缘由,以及作者的哀伤之感。而正文多为四言骈体,把写作的重点放在逝者的事迹、德行、才华、贡献等方面。这种“序文+正文”的结构形式也是六朝最为流行的诔文体制,《文选》所选的8篇诔文均有序文,这是陈维崧对六朝骈俪文体制的继承。但陈维崧会根据不同的哀祭对象,调整序文和正文的内容占比,这种结构安排在保留诔文作为庙堂文学的功能性和应用性的同时,为述哀情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哀祭对象为大臣名儒及其家中女眷等具备名声、威望之人时,陈维崧基本恪守了诔文作为庙堂文学礼文功用的要求,集中笔力颂德,甚至通篇都是溢美之词,文学性和情感性有所减弱。例如《宣城文学施公诔》,在介绍施公的学术追求和文学素养时,用了近十个句子来铺垫当时经文煨烬、人心陷溺的学术背景,以此来突出施公为“光辉笃实之君子”[3]484,典故繁复至于啰嗦庸俗。
但在为相知相契但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好友作诔或哀辞时,陈维崧会格外增加序文和正文中的述哀情部分,甚至出现序文长于正文的情况。如《嘉定侯掌亭先生诔》,这篇诔的序文部分篇幅很长,除表明逝者死亡日期和身份地位外,叙哀情占了很大一部分。陈维崧抱着悲痛、哀伤的心情记叙了侯掌亭的一生:年少遇到战乱,亲人朋友多死于这场离乱,然“雨不终朝”[3]487,他挣扎于乱世,侥幸地活了下来又谨慎地在新朝生活着。陈维崧在序文中段还铺陈了三个“未喻”之处,凸显人世不公、命运难测之恨:一是君姿超凡脱俗,却未能长命;二是君之文采直登班范之堂,却不第且不寿;三是君家三世忠清,一门英烈,却遭覆巢破卵之伤。三个“斯其未喻”递次排开,其中悲痛、愤慨、无可奈何之情跃然纸上。而与之相对的正文则篇幅较短,主要集中笔力描写两人的往日情谊。这些故事和画面无一不洋溢着浓烈的感情:从前的他们同读书、同游玩,翩然于山头与河舟之间、诗文琴篪之中;现在的他们是“萍梗飞翻,一悲甫草”[3]489,阴阳永隔,悲伤无法言说,只能以一句“呜呼哀哉”作结。大概是因为逝者是陈维崧相熟的挚友,且与陈维崧同为由南入北、羁旅漂泊之人,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陈维崧在哀祭朋友的同时也在自怜,所以该诔在内容的安排上情感浮动更胜。
而祭文则大体可以根据哀祭对象的不同分为“写哀+述德+写哀+告飨”的四段式和纯述哀情式。祭奠对象为颇有声誉的王公大臣及其女眷的祭文,如《公祭大司空在调周公文》《公祭封侍御王太翁》《祭周侍御母夫人文》等文,都采用了“写哀+述德+写哀+告飨”的四段式。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指出中世以来祭文的文体功能为赞言行、寓哀伤。和陈维崧同年举博学鸿词科的朱彝尊,其骈体祭文就是这种传统模式。如朱彝尊为纳兰性德作的祭文《祭纳兰侍卫文》,就是先赞纳兰“敏学博通,文咏书法,靡有不工”[4]594,最后以“侑以荒辞,泣下如绠”[4]594寓哀伤。在这种模式中述德的比例一般要大于写哀部分,作者哀情的抒发也略显单薄。而陈维崧的四段式中有两个写哀部分,与旧模式相比,哀情的表达更具有层次感,且内容也更为丰富。
如《祭王敬哉先生文》:“呜呼哀哉!地坼幽燕,峰颓恒霍,珠斗芒寒,苍穹气薄,咸阳之树西靡,箕尾之星夜落……盖贤亮道丧,固率土之所同悲;而师弟情深,犹微忱之所独觉。声因激楚而不成,管以哀伤而难握。”[3]463这是文章首次述哀部分,作者先以“地坼”“峰颓”“气薄”极写王敬哉先生逝去之悲,又以东平思王刘宇冢上松柏皆西靡的典故表达在世之人的思念之情,更提到世人闻哀讯罢讲咨嗟,率土同悲。从山川自然和人文社会两个方面夸述哀情后,再写自己更是因为哀伤悲痛声音激楚不成,手颤抖无力甚至握不住竹管。哀情由大及小,由广及狭,情感更为真挚具体。接着文章转入述德部分,作者先简述王敬哉人生经历,再从论事、晰理、诗歌、纂录、议礼几个方面论述先生之德:“乃其学术醇深,文辞卓荦,汪汪千顷之波,矫矫半天之鹤,论事而颉颃韩欧,晰理而折衷濂洛……虽履功名之盛,贵以弥温;即当耆耋之龄,老而逾恪。”[3]464再通过回忆自己和先生的交往,感叹先生“高风之岳岳”[3]464。此部分与旧模式相比,述德内容要精简许多,且于述德之中尚有哀情的抒发。最后,作者表达了希望先生能“得圣之和”并“优游不死之庭”[3]464的美好祈愿,并用霜雾、鹃啼、猿啸的哀景写哀情,以“而某之哭公者,因世道人心而叹作”[3]464再次表明悲痛之情。
收尾的“有蔬载搴,有酤载酌”[3]464作为告飨部分,也是因祭文来源于古之祭祀,而古祭祀便止于告飨。第一次正式以“祭文”命名的曹操《祭桥公文》,便是以“尚飨”作结,后代祭文也多采用这一形式。整篇祭文情感抒发由浅至深,从痛其逝世、述其德行到以哀景写哀情,叹世事兴会难以琢磨。多形式有层次的表达哀情,不仅使情感饱满,赞德行部分也更显真挚。
哀祭对象为交情甚为深厚的挚友,如《祭侯仲衡先生文》《公祭同年陈子逊文》《祭同学董文友文》等,陈维崧更是基本舍弃颂德部分,将大部分笔墨倾注在哀情的抒发上。
如《公祭同年陈子逊文》,作者以伯牙子期、惠子庄子、苏武李陵等典故开篇,着重表述了两人深厚的感情。“伯牙逝而赏音亡,惠施去而微言绝”[3]473,而挚友陈子逊的逝世带给陈维崧的悲痛,同于伯牙去子期、惠子去庄子,“是则罄安仁之诔笔,何能叙此酸辛;殚庾信之铭言,未足形兹凄恻矣”[3]473。在作者眼中,他是人间谪仙人,“问天无买赋之金,阅世少翘材之馆”[3]473,才华横溢。紧接着,作者又回忆了与陈子逊相识相知的经历:两人同年赴考,举博学鸿词科,同修《明史》。人生正充满希望和生机,但挚友却突遭厄运,及第之时的笑语音容犹在,挚友却已经离开。美好过往与残忍现实两相对比,更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强烈深厚的哀情。在悲痛挚友逝世之后,陈维崧更感叹道:“三千里吴关越岫,驿路偏长;十二日金马石渠,流光甚短。槐宫之蚁阵空酣,椒殿之鹤书恨晚。”[3]474挚友经历战乱,由南入北,一路艰辛困苦,却在征聘入翰林院后不久便离去。流光甚短,鹤书恨晚,人生的遭际变幻无常,难以琢磨。这一句从悲友逝世进而到感叹上天不公、世事无常,哀情更增一层。“园内之茱萸遍插,已少斯人;阶前之芍药徒翻,长思我友。”[3]474作者于末段再次发出哀呼,结构上形成一唱三叹之势,哀意强烈深厚而又延绵不绝。
诔和哀辞使用“序文+正文”的模式,根据哀祭对象不同灵活安排述德和写哀的内容;四段式祭文中两段写哀内容,甚至直接舍弃颂德部分,对至亲好友采用纯述哀情式的祭文。陈维崧在书写骈体哀祭文时,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祭文重情的传统”[5],以“情”为中心,构成哀祭文随体而变、因人而异的结构模式,提高了骈文在应用性文体中的文学性和抒情性。从晚唐李商隐的《樊南四六》至清初的骈文,其应用都多集中于应用性文体,政治性较强,抒情性更弱,很少抒发个人真实情感,文学性和情感性都不够。陈维崧却跳出了前人的局限,在应用性文体中重视骈文的情感蕴藉,为骈文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二、艺术技巧:以事、景寓哀情
上文已经提到,同代作家在写作哀祭文时多采用赞言行、寓哀伤的固定模式,这种模式从中世以来已趋于模板化,使得作家在创作中较少运用一些艺术技巧,甚至出现很多谀辞巧语和虚文蔓说,令人生厌(3)关于哀祭文的谀辞巧语和虚文蔓说,参见[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而陈维崧哀祭文的结构模式随体而变、因人而异,这种创新使文本创作有充足的空间,可以运用更多样的艺术技巧,更好地表达哀情。
陈维崧在哀祭文写作中常叙述自己与逝者生前的交往回忆,取具体事例刻画逝者人物形象,真正做到以事寓哀、因事抒情,并不虚为文。如《祭侯仲衡先生文》,这篇祭文是陈维崧为侯方域所作。文章回忆了其父、其弟以及自己与侯仲衡的交往。其父同侯公同游画溪,同登铜官山,二老举杯谈笑,觚飞爵腾;其弟受侯公养育维护,帮助他立其户枢;而陈维崧和侯公则是一同“跌荡词场,激扬文薮”[3]470,聚会时一起吹竹弹丝,饮酒作乐,酒食弄脏了衣服也毫不在意,极乐之时,摘花戴头,就蔗竿而舞,侯公也同其一起仰天大笑。这些回忆画面再现了侯公的坦率风趣、耿介不俗,处处可见两人的深厚情谊。可如今,这位挚友再也不能与陈维崧谈文作诗了。梦回现实,陈维崧不禁发出“高山不作,流水无声,呜呼已矣,尽此生平”[3]471的感叹。全文以回忆往昔的方式,再现了与侯仲衡亲密交往的画面,以具体事例寓哀情,悲怆痛惋的唏嘘之情如同行云流水,绵延不绝。又如《祭同学董文友文》,这篇祭文是陈维崧为董以宁所写。董以宁,字文友,武进人士,工于填词,与邹诋谟齐名。陈维崧在祭文开头先描写了董以宁逝世前一年众人相聚饮酒的场景:“呜呼我友,去年今夜,栎园司农,酌余官舍。秋霖氵虢氵虢,街鼓礌硠。子先在焉,傫然以尫。广陵宗生,新安汪子,与我与君,四人而已。君时惫甚,觅几而凭,食一溢米,酒不半升。”[3]465-466当时,董文友还在为未中进士而颓丧感伤。那个疲惫失意、凭几而伤的董文友还历历在目,如今却是天人永隔。陈维崧在生离死别的痛苦中描写好友仕途失意的画面,两相叠加,更显哀情之沉重。
陈维崧在创作骈体哀祭文时,还注重景物描写,营造或悲伤凝重或色彩明丽的环境氛围,以哀景写哀情或以乐景衬哀情。如《祭王敬哉先生文》中的“霜凄凄而入帷,雾阴阴而袭幕,鹃啼而雪缟千峰,猿啸而风悲万壑”[3]464,以霜、雾、雪、风四个寒冷刺骨的意象营造悲怆痛苦的氛围,再加“鹃啼”“猿啸”,哀景中又添哀音,愁苦哀怨又进一层。同样的在《祭同学董文友文》中也有体现:“灯阑泪尽,溅雨惊砂……庭空无人,明河欲斜,我之哭君,醒耶梦耶?”[3]466-467房间里燃尽的蜡烛象征着挚友已到尽头的生命,屋外不断落下的雨也暗示着陈维崧哀痛的心情。挚友的住处也是空荡荡的,再不能见其音容。在这一系列的景物描写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朋友的逝世令陈维崧心潮起伏,伤心叹惋。同时,陈维崧的骈体哀祭文也多写乐景,其乐景多色彩明丽。如《公祭同年陈子逊文》,写到他与陈子逊共举鸿词科、征召翰林院时,当时之景是“紫禁啼莺,红墙语燕,草缬青袍,柳飘金线”[3]474。陈维崧接连用了“紫”“红”“青”“金”四种颜色,用来描绘两人及第后“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美好场景,生机与希望都蕴藏在这一景色中。可生机和希望之后却是陈子逊的死讯,世事变幻难料,乐景急转直下,倍增失去挚友之痛。同样的还有《王母张孺人哀辞》,作者描写了张孺人庭院内百花齐放的英姿:“胜业坊前,乐游原左,每值春来,秾花胜火。雨浥千枝,晴开万朵,紫菂璘斑,琼葩璀瑳。”[3]499而张孺人仙逝后百花枯遍,两相对比突显孺人的贤良和时过境迁之感。可见,在陈维崧的骈体哀祭文中,写景之句虽少,但却不失为点睛之笔,是陈维崧哀祭文的风神。
正如陈维崧在《佳山堂诗集序》中所言:“且夫言以旌心,文原载道。若使情弗笃乎君王,志不存乎民物。色工朱紫,徒成藻绩之容;韵合宫商,未便克谐之奏。”[6]陈维崧认为文章优劣的评定标准,不单单在于词藻、音韵,更要看作者的思想、情趣、德行。他在哀祭文写作中以情为文,将叙事、写景与抒情自然融合,情挚意浓,感人肺腑,摈弃了哀祭文作为应用性文体凝滞、呆板的缺点,提升了骈体哀祭文的情感底蕴和艺术魅力。
三、文化底色:儒士的价值追求
哀祭文属于应用性文体,但又和人类历来逃不开的“生存与死亡”问题息息相关,加之其多元性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对象不同,必然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陈维崧有祭亲友文、祭王公大臣文,还有被祭者为女性的哀祭文,不仅体现了挚友逝世的无限悲痛和贤达之人离去的不尽惋惜,还展现了哀情之下其直面生死、反省人生的思考与领悟。从文化角度解读陈维崧的骈体哀祭文,可以发掘陈维崧作为儒士的价值追求。
(一)积极入世、达成生命不朽的传统儒家人生观
在至真至纯、相知相契的祭友文中,如《祭同学董文友文》《公祭同年陈子逊文》《嘉定侯掌亭先生诔》,文章任由无限悲痛的思念情感自由挥洒,又多感叹挚友空有茂才却无处施展自己的才华,无法实现人生价值。《祭同学董文友文》,闻挚友死讯的陈维崧是“痛缠心髓,重趼狂奔,哭君百里”[3]466,又回忆其往昔两人的对话:“君曾语我,人生何有。谁为后死,讬之不朽,谁知君碣,遽落吾手……何知今日,果谶斯言,方干罗隐,万古同冤。”[3]466董文友文章、绩学、行谊皆为上乘,却同方干和罗隐一样不第进士,更无人整理继承其文集,只能由自己收集整理。此之悲,是感叹友人空有文学才华却无人赏识;《公祭同年陈子逊文》,陈维崧极尽渲染对挚友的敬重之叹、思念之感,大力赞美其文学才华,称其“云移雉尾,诗成而两省传亲;日映螭头,赋奏而九重称善”[3]474,又遗憾其授鸿词科不久便仙逝而去,有“用武之地”却走到了人生终点,此之痛,是痛惜生命短暂、虚幻无常,友人无法卒其著书之志;《嘉定侯掌亭先生诔》,陈维崧怀念友情,悲怆痛惋,更痛友之生途坎坷——遭逢战乱家破人亡、文登“班范”却埋冢中、一门英烈却罹覆巢之伤。此之恨,是忧愤上天不公,哀痛挚友命途多舛、一生颠沛流离。可见,这三篇祭友文在表达挚友逝世的悲伤和怀念之余,都蕴含了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思考。陈维崧的哀痛不是本于消极的人生观,反倒是因挚友未能达成积极入世的人生实践而悲痛可惜。这种人生观集中体现在儒家“三不朽”信条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7]。陈维崧或悲友人未能“立言”,只能由自己收集整理其诗文,以求无负其才;或痛友人的生命太过短暂,来不及“立功”。总的来说,都是因友人未能实现人生价值,达到生命之不朽而痛呼“呜呼哀哉”。
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还体现在陈维崧为王公大臣所做的哀祭文中,如《宣城文学施公诔》《公祭大司空在调周公文》《公祭封侍御王太翁文》。这类哀祭文都以赞美逝者的德行、成就为中心,虽有哀情也多是悲痛贤达之人的离去。在《宣城文学施公诔》中,陈维崧在末段提及“而我识公,学定神全,彭殇一致,生死齐观”[3]485。在这里陈维崧不再似祭友文中的“痛”和“恨”,反而赞赏施公齐生死的人生观。这种豁达人生态度的前提是施公长寿,且已经在其人生旅程中达到了“学定神全”,成为国之名臣、时之大儒,实现了人生价值。同样的,在《公祭大司空在调周公文》中,陈维崧也提及周公立德立功,实为君子。“公登大耋,达人孰媲?……公之哲嗣,文犀琅玕,公著亢吕,忠彦与韩。备斯三者,云何不乐?”[3]469周公已经达此三者,实在没必要悲切感叹,甚至可以谓之喜丧。
“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8]陈维崧虽历朝代新旧交替,身世飘零,但仍怀揣着儒家积极入世、实现人生价值的信仰,在哀祭文中也在抒发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决心。
(二)柔淑遵礼、家族昌盛的理想女性
在被祭者为女性的哀祭文中,如《祭徐母顾太夫人文》《公祭梁老师母吴夫人文》《祭周侍御母夫人文》《尤母曹孺人诔》《顾夫人哀辞》及《王母张孺人哀辞》,陈维崧描写并赞美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受哀祭文“传体而颂文,荣史而哀终”[9]的文体要求和“善终”“慎终追远”文化思想等的影响,哀祭文中展现的多是积极正面、对后代有标榜和教化功能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虽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差距,但此类哀祭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恰恰反映了以陈维崧为代表的士人对理想女性的期待,以及当时社会中对女性的真实定位。从陈维崧祭奠女性的哀祭文来看,其理想的女性大多具有以下三个特质。
一是柔顺为本,性情安静柔和。其哀祭文中对女性柔顺特质的表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女性柔顺特质的直接认同与肯定。《尤母曹孺人诔》:“柔嘉维则,淑慎其仪。”[3]492《顾夫人哀辞》:“至若性多幽静,质本柔嘉。”[3]495第二,常用一些与“柔”字意思相近的字眼来赞美女性,如婉、顺、静、淑、和等字。《祭周侍御母夫人文》:“呜呼太母,幼传贞淑,颂就春椒,铭成秋菊。”[3]480这都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婉婉有仪、静以和命的期待。这种期待在清代其他作家的女性哀祭文中也出现过。如刘嗣绾《潘君妻周孺人诔》:“翳欤淑姬,令德来佩”[10];洪亮吉《适汪氏仲姊哀诔》:“端敏之性必宜尔家,柔仁之资亦仪其母,为中外称首矣。”[11]这实际上说明“柔顺婉静”是哀祭文中传统女性形象的典范形态,文化主流中的女性是缺乏自主独立性的,仍处于依附地位。
二是恭肃遵礼,敦睦亲族。陈维崧骈体哀祭文中被祭的女性,都是为人妻者、为人母者,这一角色多要求女性事其母而孝、助其夫而贤、爱其子而养。如《尤母曹孺人诔》中,陈维崧赞美曹孺人“习礼敦诗……妇职攸勤,女红无旷”[3]492,认为其懂礼循制,做好了妇女的本职工作。《公祭梁老师母吴夫人文》中,提到两人夫妻和睦,琴瑟和鸣,夫人侍夫颇为用心:“夫人在家,摒挡箕帚。桄榔叶黑,荔子枝鲜,铙歌返旆,花鸟归船。亚相还朝,夫人从焉,象服翟衣,犀翘爵钿。”[3]478吴夫人在家操持家务,且甘愿随丈夫职位调动而奔波流离,确实可当“坤范”。在《祭徐母顾太夫人文》中,陈维崧也重点称赞了顾太夫人在育子方面的尽职尽责,“纵令健笔凌云,丽燦蛟龙之咏。难形寸草之心,莫罄慈萱之行”[3]476。曹孺人遵礼勤孝、吴夫人为贤妻、顾太夫人为良母,三人都堪称当时女性的典范。
三是其夫、其子或其婿社会地位高,负有盛名,有一些妇女甚至因丈夫官居高位而受封为命妇。这一特征也是陈维崧为这些女性写作哀祭文的原因之一。《公祭梁老师母吴夫人文》就提到了吴夫人因其夫之地位,荣封一品,其来往之人也多是命妇。《祭徐母顾太夫人文》中,陈维崧先言顾太夫人之婿“掇名省之巍科”[3]476,顾太夫人之子“夺曲江之上第”[3]476,又叙其家来往之人多是名士,“一坐尽贞观将相,屏间识彼豪英;半堂皆濂洛生徒,帐后资其酬酢”[3]476。《祭周侍御母夫人文》中,陈维崧也是先称赞逝者之子周侍御“维大司空,朝之硕辅,帝曰师臣,人尊尚父,在殷伊陟,在周山甫”[3]480。无独有偶,章藻功在《朱大中丞淑配毛夫人祭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堂前色笑,配佳妇以佳儿;庭下宁馨,将难兄而难弟,矧其从官两浙;列位三台,信杨震之公廉,服胡威之清慎。”[12]此文集中赞美了毛夫人家中男性亲属的德行和成就。可见在被祭者为女性的哀祭文中,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以陈维崧为代表的士人群体,其理想的女性是以柔淑为本,且能为家族发展作出贡献。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只能限于女、妻和母三者,大部分女性的人生只能囿于家庭。再者,陈维崧本就出生在一个以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黄宗羲在《陈定生先生墓志铭》中写道:“陈氏为止斋之后,由永嘉徙宜兴,遂为望族。”[13]陈维崧祖父陈于廷是明朝的左都御史,父亲陈贞慧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先辈坚毅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影响了陈维崧的家族情结。这些因素都使陈维崧在评价女性时,会基于她对家庭所作的贡献,以家族社会地位、家族男性亲属的品德和功绩来衡量女性的人生价值。这也注定了男性在评价女性时会漠视女性本身,忽略女性本身的情感追求和价值观念。
结 语
陈维崧的骈体哀祭文,注意到各类哀祭文体不同的应用性,并根据写作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思路和结构布局,极尽变幻之能。他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哀祭文的抒情传统,十分重视骈文的情感蕴藉:其骈体哀祭文中不仅有丧亲失友的叩心泣血之痛,更将自己乱世之际遇融汇于文中,将叙事、抒情、写景自然融合,情文并茂,感人肺腑,并展现了其积极入世实践、达成生命不朽的传统儒家人生观,提升了骈文在应用性文体中的文学性和抒情性。同时,陈维崧的骈体哀祭文中,哀祭对象为女性的文章占有一定比重,反映了以陈维崧为代表的士人对女性的理想期待,以及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真实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