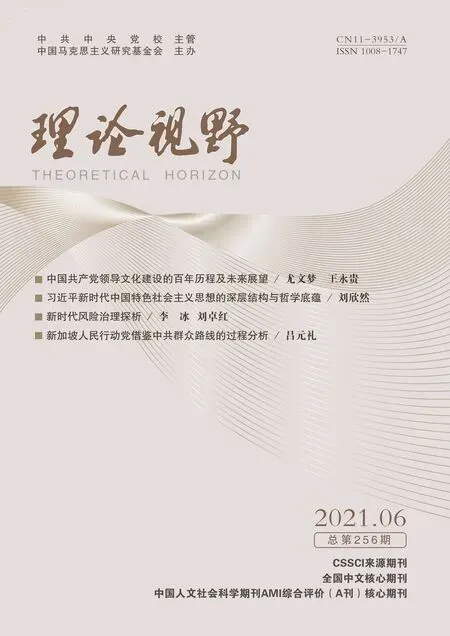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的路径探析
■孙 林
【提 要】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基础要件和价值体现,是组织建设的根本性议题。政治和服务功能建设作为对全功能型基层党组织功能消蚀的回应方案,在促进组织转型过程中基于结构-功能、调校-功能、风格-功能三种范式形成三条选择路径,而新时代加强基层组织功能建设则有赖于这三条路径的协调推进。
功能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体现,我们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历史方位发生重大变化,功能取向从“冲突”转变到“整合”,基本功能被本土化为领导与执政、政治与服务、管理与治理等多维功能。在基层,政治和服务功能被赋予基层党组织并作为其基本功能而被反复强调。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1]在实践中,各级各类党组织多采取显性与隐形相结合的路径推进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即将突出政治功能寓于服务功能之中,以服务功能彰显政治功能。然而,功能建设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需要在接续传统资源、回应时代问题、厚培理论基础和明晰路径选择中不断探索完善。
一、螺旋演绎: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变迁
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以往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功能建设的历史资源,应得到足够的关注。换言之,应“重视本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2]。这些本土资源的历史叙事可以概分为三个阶段,基层组织功能在此演绎出从建构、解构到重构的历史螺旋。
近代以往,中国县域以下基层社会有悠长而深厚的自治传统,即皇权不下乡,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基层自治以上,以知识竞争为主渠道形成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和基于武力并以血亲传承为纽带的皇(王)室集团分享着统治权,由此形成代表“统”权的皇(王)室集团,代表“治”权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和代表“民”权的宗族士绅集团,三方通过一系列资源汲取与救济、信息宣教与表达、精英选拨与退出等方式进行沟通,共同构筑一个相互依存的“周期性瓦解和重建”[3]的超稳定治理结构。张东荪用“双橛政治”,费孝通用“双轨政治”来描述这一治理结构的内在运行机制,即“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还自如的双轨形式”[4]。这一双轨机制通过自下而上的利益代表、民意表达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资源汲取,来保障传统治理结构的稳定。
“双轨政治”及其塑造的传统超稳定治理结构和静态社会,能够长期存续的基础条件有两个:一是基层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治单位没有遭受根本性破坏;二是双轨边界稳固且沟通基本顺畅。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工业力量入侵,导致以乡村为主体的基层自治单位完整性遭到溃散性破坏。具体表现为传统家庭手工业在西方优势近代机器工业冲击下走向全面破产,失去家庭手工业的津补贴,“土地不能同时养活地主和佃户的事实暴露了,形成日益严重的土地问题”[5]。原有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维持的传统土地制度和社会基层稳定结构开始瓦解。此外,伴随着外源驱动的城镇化扩张,以乡村为主体的基层自治单位又面临严重的人员、财富等资源外流问题,特别是传统“官于朝,绅于乡”人才对流链条断裂,乡土基层治理因人才匮乏导致土豪劣绅充盈其间,“双轨政治”逐渐失效,乡土基层自治功能残缺乏力,治理陷入破碎无序的状态。延宕至国民党执政,但国民党不重视、不深入基层,其地方和基层组织“空、穷、弱、散”[6],导致基层党组织治理无能、无效,国民党另觅他途通过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铺设自上而下、入乡入户的行政轨道,企图以行政主导基层治理。然而这种以单轨代替双轨,不仅导致下情不能上达,而且继续破坏自治传统的同时又无法整合原有治理结构,各种力量相互僵持,基层治理陷入低效甚至无效的境地。
我们党虽受俄国革命经验的影响,但对基层组织的重视不仅早于也高于俄国党,俄国党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17年后才开始大规模重视基层组织建设。1934年,联共(布)17大对党的组织结构作出重大调整,设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按地域和生产部门建立,以便于党的领导更加有效地体现在基层工作中,也使基层群众的活动更多地纳入党的组织体系。[7]而我们党对社会基层和组织的重视,则肇始于大革命后期。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起始,以三湾改编为标志,我们党不断深入基层、扩大党在基层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此总结道:“我们共产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时,首创‘支部建在连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也确立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8]三湾改编两年后,中共中央在《给龙兄及前委诸同志的信》中要求红军普遍推广“班排设党小组,连队设党支部,营以上单位设党委”的做法。又过两年后,党组织跨界嵌入基层组织的做法又被移植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体系之中。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组织不断进行跨界并延伸组织嵌入,重构了党领导的基层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组织的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的基层组织的内涵和战斗堡垒作用的进一步明确,以及“支部下乡”和“支部进居”运动的推进;到了1961年,党的基层组织延伸至生产大队,至此我们党通过基层党组织实现了对全国基层行政、军事、经济、社会等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一个全功能、全覆盖管理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建立起来了。
在革命、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初期,全功能型基层党组织是社会基层组织中最重要的管理者。基于时代任务的需要,全功能型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虽全但并不均衡,管理、动员、宣教等功能权重明显较大,而服务、治理功能偏弱。在政治与服务功能二分框架中,全功能型基层党组织可以更为精细地定义为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其以组织和工作全面覆盖为基础,以自下而上的资源汲取和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双轨”动员为手段,以管理和控制为主要特征,发挥组织的政治功能。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是适应革命、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需要的组织模式,在不同时期围绕政治中心任务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20世纪80年以来随着基层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组织以及新兴媒体的发展,社会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思想观念多变化,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为主体结构的单位制社会逐渐解体,农村、社区、企业、“两新”组织等社会基层组织等逐渐成为自我管理、自主决策的自治群体,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在新形势、新变化面前出现“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社会基层管理和治理问题的不断增多,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面临新转型挑战,基于“领导就是服务”“服务巩固领导”的转型思路逐渐成为共识,基层党组织通过服务重构社会基层治理结构,实现社会基层再组织化成为基层党建的重要任务,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建设也遂即成为议事日程的重点。
二、问题导向:基层党组织传统功能的弱化
功能建设因时代而成,也因时代而变。对于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而言,以组织嵌入和功能重构方式介入遭受严重时代冲击的社会基层,在促使基层治理传统发生革命性变化之后,塑造成形的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下单位分立的社会。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以政治功能为统揽,在社会基层中进一步细分为政治划定、组织生产、社会管理、资源汲取、政治宣教等子功能,依托这些功能基层党组织实现对社会基层的统一领导和管理。然而,时代变化所催生的制度变革等外源性因素不断内渗,持续解构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所领导的社会基层管理格局,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功能消蚀。
一是政治划定功能消失。阶级划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观察和分析社会的基本方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就点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9]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和划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阶级斗争、革命的前提。然而,1978年以后,以阶级“成分”为界线的社会格局逐渐瓦解。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原有通过划定“成分”来决定个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高低的政治划定功能消失了,个人在社会基层中的地位越来越主要取决于个人自身因素,个人与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紧密型依附关系逐渐减弱。
二是组织生产功能削弱。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都是一个生产过程,不论在农村社区、工厂企业、机关单位还是院校部队,虽然生产的“产品”形式不同,但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都是生产的组织者。然而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组织生产的功能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其中尤以农村基层党组织最为典型。新中国成立后,“支部下乡”运动的组织延伸最终确定党在农村的组织主要设在生产关系链条上,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其中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是各种生产关系的领导者和协调者,是生产的组织者和实现者。然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发展,农村生产逐渐与组织解绑并开始以原子化的户甚至个人为单位进行。近年来,随着“新四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正在从‘耕者耕其田’的分散化经营向‘耕者耕他田’的集中化或集约化转变”[10]。在农村生产方式发生大调整、大变革的新形势下,以土地入股、租赁、流转为主要资源集合方式的合作社,成为诸多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形态。在这种情势下,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原有组织生产的功能被大幅削弱。生产是财富的重要来源,组织生产功能的削弱直接导致物质供给能力下降,又加之农民收入日益多渠道化,以及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国家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以建卡形式超越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而进行直接输济,使传统党群关系中农民对党组织基于利益认同而形成的政策乃至政治认同都不同程度地减弱了。
三是社会管理功能削减。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社会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在革命、建设乃至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是社会基层各项公共事务的最终、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管理主体,这种管理不仅是全能的而且是全覆盖的。但随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农村、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管理自主性逐渐增强,加之社会基层治理议题的形成和扩散,治理事务逐渐弥散化、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基层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精细化诉求不断高涨,构建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各方政策共识。在这种情势下,依赖地方党委的组织和权威资源的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社会管理功能面临两个过程的双重挤压即上级支撑资源在传导过程中的散失和转移,以及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功能竞争和分享,这导致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普遍面临社会管理功能削减和新治理功能未发育成熟的“成长烦恼”。
四是资源汲取功能消逝。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触及利益是政治对资源权威性分配的直接结果,也是政治动员有效性的关键支撑,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的组织细胞和功能枢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初期能够直接决定社会基层中个体利益的得失,因而能够通过“触及利益”进行有效地权威建设和政治动员。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组织转型,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基层的利益触点越来越来越少,甚至逐渐消失。以资源汲取最为典型的农村为例,随着税费改革和农业税的取消,“三提五统”“粮食交公”“义务出工”遂即成为历史词汇,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利益触点大幅消散,相应地原有附着其上的权威资源和动员能力也大幅减蚀。
五是政治宣教功能消减。政治宣教是基于“灌输”理论而形成的信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育化过程。对信息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是政治宣教的组织条件,信息源一、层层传递、回路控制、解释统一是政治宣教有效性的技术条件。在“千线一针”组织机制中的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是政治宣教的末端神经和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完成者。在前互联网时代,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借助组织权威和信息势能,通过政治宣教能够对社会基层进行有效地宣传、教育、动员,实现对社会基层的政治领导和思想引领。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12],在国家、政党信息优势增强的同时,社会相对优势则增幅更大,信息变的多源、多样、多量、多变,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由原来信息的单向流动变成信息的多向对冲,信息价值的检视也成为多主体、多标准重复博弈的新场域。在这种情势下,政治宣教原有机制在互联网跨时空的横向联系和跨层级的直接传播面前,信息迟滞、扭曲、失真等问题积渐凸显,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在信息势能大幅消减甚至不再的情况下,政治宣教的权威和绩效愈加难以实现预期。
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功能消蚀导致组织悬浮化,组织转型问题更加凸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议题就应运而生。对于该型党组织建设而言,先前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功能消蚀虽然留下了功能建构空间,但功能消蚀附带的组织悬浮、抓手弱化以及组织领导、动员、管理和控制力下降等问题,也使得服务功能建设和普及,缺失了可供依赖的路径。但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这里,不论政治还是服务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党在社会基层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在这个前提下,无论何种功能型建设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期以通过服务功能建设恢复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路径和功效,显然是本末倒置。服务型党组织的功能建设有自己的逻辑和原则,在实践中既可以彰显服务价值,也可以突出政治功能来与时俱进地巩固党在社会基层中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三、路径探索: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的路径选择
功能建设遵循着“冰山理论”的逻辑,即决定功能的不是功能建设本身,而是功能背后的支撑因素。对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而言,功能建设主要有三重路径选择。
第一重选择是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组织结构调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结构对整体平衡和功能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功能是结构的派生物,对组织而言,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决定什么样的组织功能。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结构—功能范式思考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倾向于以政治和服务为理念和价值目标,重构或重置基层党组织结构,使之反向支撑政治和服务功能。然而,结构—功能范式的结构转型面临两个实践挑战:一是基层党组织结构是按照党章设置和运行的,组织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变化无疑都与党章抵牾,即使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角度解释也难以有效规避“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政治红线;二是政治功能主导型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虽遭消蚀,但组织结构并未受到根本改变,这就产生结构功能主义的反证,即功能消蚀前后的结构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功能发挥程度却发生迥异对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寄望于基层党组织的结构调整和变革,并以此奠基并持久生成新时代政治和服务功能的路径选择,面临着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是结构—功能范式失效还是实践失败?显然都难以定论,但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是在结构—功能范式基础上加入新的变量,或可以修复理论解释力和实践瑕疵,这就涉及第二重选择的问题。
第二重选择是在结构—功能范式理论和实践面临难以逾越挑战的情况下,加入组织调校因素,以此回应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本文将其概括为调校—功能范式。调校—功能范式建基在结构之上,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补充,它基于以下事实判断:即相同制度结构下的不同组织调校,能够产生诸多甚至截然不同的绩效或功能,这些组织包括超国家、国家,以及次国家的政党、经济和社会组织,这说明结构不是直接决定绩效或功能的因素,而不同组织对制度结构的运用方式即调校差异影响甚至最终决定了绩效或功能的良莠、大小。反映在基层党组织建设领域,即政治和服务功能能否实现,取决于建基于一定结构之上的组织调校,当组织调校方向以管理和资源汲取为主时,就会产生强烈而直接的政治功能;当组织调校方向以治理和资源给予为主时,就会产生广泛而持久的服务功能。在治理现代化总目标下,包括基层党组织在内的党的组织体系都在向治理转向,在这种情势下,基层党组织基于调校—功能范式建构政治和服务功能,向突出政治功能的服务型转型的前景可以期待。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调校—功能范式无法解释相同结构、同一调校取向的不同基层党组织在政治和服务功能上存在的显著差异问题。显然调校-功能范式的实践困境说明,必须加入新的解释变量才能巩固理论基础并有效回应实践例外,这就涉及第三重选择的问题。
第三重选择是在结构—功能范式和调校—功能范式基础上回归人的本位,强调组织中的人特别是负责人或带头人,其党性、能力、素质、资源等因素对组织功能实现的影响,本文将其概括为风格—功能范式。该范式强调组织负责人或带头人基于各种能力、素质等因素综合形成的外在风格,对组织行为、绩效和功能的塑造作用。在实践中不论是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还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建设,无不将“选强配优”组织班子特别是书记作为当然选项放在突出位置,或者采用“双培养”即把能人培养成党员、班子成员或书记,把党员、班子成员或书记培养成能人也是一种较普遍的方式。对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而言,选配服务能力、意识强的组织班子成员特别是书记,对政治和服务功能建设以及功能绩效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然而基于风格—功能范式的工作实践也始终面临如下难题:组织结构、调校对组织中个人的塑造是潜在有力的,个人风格所产生的绩效在缺乏相应组织结构、调校支撑的条件下难以持久,除非个人反向改变既存组织结构、调校,但这样就会产生政治和法律的双重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张力松缓困难,导致政治和服务功能建设在“向后回到过去”和“向前越过雷区”的节点上逡巡不前,风格—功能范式也面临失效危险。
综合看来,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的三重选择都存在不足,割裂开来观察可以发现三重选择会造成三重困境,但整合起来思考却有全新的理论体验,即将结构—功能范式、调校—功能范式、风格—功能范式三者之间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沿着从结构—调校—风格的路径检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者则是前者的补充和深化,解决了前者效能发挥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所以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的应然路径是三线并进:第一条线是根本路径,即构建充分发挥政治和服务功能的组织结构,创新组织设置方式;第二条线是基本路径,即建立以政治和服务功能为价值导向的组织运行方式;第三条线是直接路径,即选强配优能力、意识强的基层党组织班子和书记。然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证明,仅仅进行功能的硬件和软件建设还不是能完全有效地驱动功能运行、完善乃至成型,还需要加入支撑件,即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保障和动力。保障包括政策保障即对基层党组织书记和专职党务工作者的社会保障待遇、职业发展激励,以及工作有待遇、干好有发展、退出有保底;资源保障即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和服务功能所需要的人员、场所、经费投入。动力包括信仰动力,即以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为导引、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先进典型为示范的动力,这需要不断地进行教育才能保持;制度动力即以制度化考核评价压力转化的动力;利益动力即以利益激励和惩戒双向调节的动力。
总而言之,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建设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多路径协调推进,软件、硬件和支撑件统筹建设才能让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和服务功能逐渐形成、成型,推动基层党组织由政治功能主导型向突出政治功能的服务功能主导型转型,并以服务和政治双功能引领基层“双轨治理”,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此不断与时俱进地巩固党在社会基层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2]赵晓峰:《公域、私域与公私秩序:中国农村基层半正式治理实践的阐释性研究》,《中国研究》2014年第2期。
[3]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4][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第377页。
[6]转引自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7]《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1982年版,第76~77页。
[8]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0]孙林:《农村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三个层面》,《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8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12]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