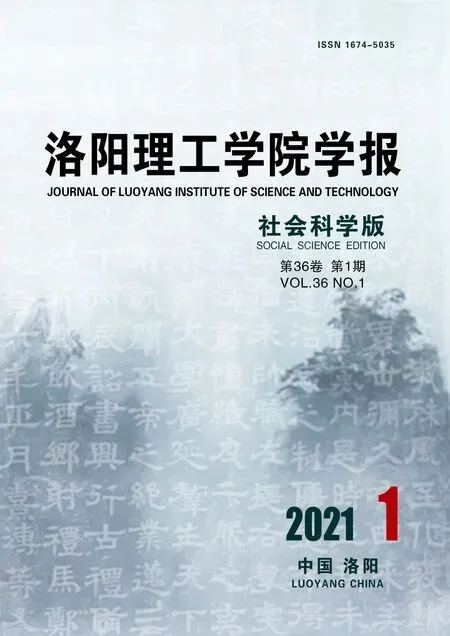从晋城书院看程颢对晋城的文化影响
聂宇洁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晋城书院是晋城文化的命脉之一,是古泽州的文化象征。程颢在晋城担任3年晋城令(宋时,地方官一个任期为3年),对晋城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晋城书院又是后人继承程子遗教以及程颢在晋城兴学办校的有力见证。从程颢在晋城任上的作为以及晋城书院的发展来探究程颢对晋城的文化影响,对研究程颢的为政思想、教育思想等都有重要意义。
此前关于晋城书院的研究不多。王欣欣、赵芊认为,晋城书院是程颢在治理晋城期间所创办,并肯定了晋城书院在晋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1]184-192。侯生哲对古书院的历史、现状以及程颢任晋城县令的时代大背景作了详细的描述,论述了程颢的晋城之治,并从晋城人才发展的角度阐明了程颢对晋城教育事业产生的显著影响[2]。此外,杜正贞在《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士社会的制度变迁》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程子乡校的源流,认为程颢与泽州的关系是元代以后才被文人演绎出来的[3]79-94;何慕在《宋金时期泽州的程子乡校》一文中,对程子乡校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乡校非程颢所建,程颢为晋城留下的是精神财富,流传于民间[4]。由于理学的大发展,元明清诸多文人追溯程颢的遗风遗教是事实,而正史和《二程集》中的记录也不全是夸大溢美之词。笔者从程颢担任晋城令的政绩入手,探析晋城书院发展与程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自宋代到明清时期晋城地区所形成的对程颢的文化认同。
一、程颢担任晋城令
(一)程颢任职背景简述
程家世代为官,程颢的高祖程羽、曾祖父程希振均为高官,其父程珦又以世家庇荫做官。程颢自幼聪颖,史书载:“先生生而神气秀爽,异于常儿”[5]630,“十岁能为诗赋。十二三时,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见者无不爱重。”[5]630自15岁始,程颢与其弟程颐一同受教于周敦颐。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已经在诸儒中颇有声名的程颢赴京师应举,次年即中进士第,时年26岁。与程颢同榜中进士的还有苏轼、苏辙、张载、曾巩、曾布、朱光庭等人。在宋仁宗主持的殿试中,程颢作《南庙试佚道使民赋》,提出“人情莫不乐利,圣政为能使民”[5]462的观点,认为“厥惟生民,各有常职;劳而获养,则乐服其事;勤而无利,则重烦其力”[5]462。
到晋城之前,程颢就已经很有名望了。程颢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新儒学逐渐形成,政治上也经过了多年的历练,在鄠县(今陕西西安鄠邑区)及上元(今江苏南京)任上受到了广泛赞誉。程颢宦海浮沉30年,做过许多官,多数是处在基层的地方官。因此,程颢能够直接接触最底层的百姓,为人民办实事。程颢的为人处世深受其父程珦的影响。程珦长期在地方做官,为人仁慈宽恕,做事果断。《宋史》载,程珦对“左右使令之人,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燠”,“所得奉禄,分赡亲戚之贫者”[6]12713。程珦的弟弟很早就去世了,留下妻子和一个儿子,程珦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照顾。同时,程珦用自己微薄的俸禄去赡养贫困的亲戚,其清廉节气之难得,受到了文彦博等人的称赞。程珦与周敦颐交游,崇尚周敦颐的学问,于是将两个儿子送往周敦颐门下学习。虽然后来的二程思想与周学有很大差异,但这期间的经历对二程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程颢将正在发展形成的儒家道德哲学和他自己的政治谋略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为政思想。在担任晋城令期间,程颢就将其全面而深入地付诸实践。
(二)施政晋城
北宋时,山西的文化教育经过五代战乱,相较之前落后很多。晋城也不例外,“其俗朴陋,民不知学,中间几百年,无登科者”[5]328。这样的描述一点也不夸张。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35岁的程颢来到晋城县担任县令。这是程颢做的第3任地方官。一到晋城,程颢就从以下方面治理晋城:一是整顿吏治和社会风气,二是发展经济,三是兴学重教。
1.整顿吏治和社会风气
“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6]12714。《宋史》载有这样一个事件:当时泽州有一个富人张氏,他的父亲去世后,一个老人来到张家,自称是张氏的亲生父亲,张氏就与老人一同到晋城县衙。程颢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审问。老人声称自己早年因家境贫寒而将儿子送与张氏现在的父亲抚养,并取出一封书信,上面写道:“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6]12714程颢看后说道:“张是时才四十,安得有翁称!”[6]12714那个老人十分惊骇,只能低头认罪。从这件小小的案子可以看出程颢具备公正断案的能力,具备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杰出的才干。另外,程颢还积极推行伍保制度,让人们互相帮助,增强邻里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加强社会责任感,从而改变社会风气。
2.发展经济
在晋城期间,程颢十分重视发展经济,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宋朝实行科买科配的购买制度,每当科配任务来临,即使是“至贱之物”,在向官府进行购买时,人们也要付出比市场价高好几倍的价钱。这也是频繁招致徭民反抗甚至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程颢为缓和这一状况,稳定社会秩序,事先预估所需粮食的数量,使富户预先准备好,到了征收之时再进行合理定价,卖给普通百姓。这样富家能得到一些利息,而普通农民的负担也不至于太过沉重,就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除此之外,程颢还实行了许多其他有效措施,例如根据家庭财产的多少来调整差役制度,由县库里出钱来补充民力。这些都为程颢行教化、办学校提供了有利条件。
3.兴学重教
程颢对晋城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办乡学、行教化。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吴中到了晋城。此时的晋城,五六十年间无一人登第。于是,吴中开始定学规,聚徒养士,教授学问[7]617。至和二年距程颢来到晋城不过10年。这是程颢在晋城办乡校之前最近的有关晋城学风的记载。
北宋右文,朝廷曾多次诏令各州、县办儒学。程颢认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5]448而要得贤才,必须重教化。程颢在晋城倡导“诸乡皆有校”,还在闲暇之时召集乡里父老,为他们讲述重视文化教育的作用。程颢注重蒙养教育,“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6]12715,还选择天资聪颖的学子亲自教授他们学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6]12715。程颢非常重视教师自身的素质,“教者不善,则为易置”[6]12715。程颢对教师考核有严格的标准,一旦不合格,就及时更换,这为教学质量提供了保障。程颢在晋城所办乡校,不仅有识字的蒙学,也不仅仅具有“诸乡皆有校”的普及性质,应该也有更高层次的读经。
俗话说“政声人去后”。明道先生行状称,程颢“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5]630。这里虽不乏溢美之词,但多少能够反映出一些程颢为政晋城的真实情况,也能够说明程颢在晋城有着实实在在的作为。
二、晋城书院概述
(一)晋城书院之发展及现状
晋城书院,当地人也称之为程颢书院、古书院,其原有建构为清代建筑。书院正门朝南,为四进院落,当地人统称为“晋院”。目前,二进院保存较好。二进院的大门、厅房、东西配房、倒座房以及上面的门窗棂,都保存完好。一进院、三进院、四进院均有不同程度的毁坏,但也有局部保存下来,能够依稀看到原貌。
晋城书院虽为清代建筑,但它的雏形实际上源于明代。陈廷敬在《体仁书院记》中提及,“前明州守王君,建文昌书院于张公祠之左”[7]635,现有天启年间“古书院”石碣嵌于书院的文昌阁上。现在从南面进入书院,仍然能看到这3个大字。崇祯末年,杨鄂又捐学田扩建书院,这时书院名称由“文昌书院”变更为“体仁书院”。在此时,书院的功能设施更加完善了。
前些年晋城书院还没有开始大面积修复工程之时,有专家到书院村进行调研,原有的文昌阁、教谕署、明道祠、花园以及望河亭等遗址都还能看到。现在,其中的一些只能靠当时拍摄的几张照片来观察了。笔者根据一些村中老人口述和查阅史料得知,书院主要由教谕署、礼圣殿、文昌阁、明道祠堂、望河亭、花园等具有不同功能的建筑组成。教谕署是古代学官的办公场所,是书院管理人员的办公之地。礼圣殿,顾名思义是用来祭祀的,供奉着孔子等大儒。开学时,在这里举行拜师仪式。文昌阁类似一座城门楼,有两层,上层是一个重要的礼拜场所,里面供奉文昌帝君。古代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诞辰,当地的官员和文人学士每年此时都要到文昌阁进行祭祀。文昌阁的下层供人们出入,是人们进入书院的重要通道。明道祠堂位于文昌阁东面,专门用来供奉程颢,原有建构初建于清顺治年间,后在嘉庆三年(1798)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间有数次修葺,于1975年被毁。望河亭位于文昌阁的东面,相传学子们闲暇之余便会登临亭上,四处眺望。康熙时,朱三才曾经描述书院周围的景色,“白水相萦回,万斛明珠泻”[8]472。由此可见,当时书院周围风景优美。花园是学子们放松心情、娱乐的场所,通往花园的一道拱门之上有“竹韵书声”石刻。
明末战乱,书院毁于战火。直到清康熙中期,伦可大任泽州知州,召集富人捐钱捐物,自己也拿出家财,开始重修、扩建体仁书院。陈廷敬《体仁书院记》也完整地记载了这一事件。
乾隆后期以后,由于汉学兴起,对理学的态度转向批判,书院的发展也转入低迷。从嘉庆年间对明道祠堂的重修也可以看出这个趋势。这次重修很有限。据记载,只有3间祠堂、3间南房和4间东房,并且没有官府的资助,主要由书院村的晋、魏两家出资,由于资金短缺,工程持续了20年。现今晋城书院明道祠堂内一通嘉庆年间的“重修明道祠碑”完整地记载了此次修葺过程。书院遗址明道祠堂中有一通石碑,上刻有“宋晋城令程明道夫子之神位”,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所立。祠堂早年已毁,但石碑仍然保留。嘉庆三年重修明道祠堂时,把它镶嵌在墙上。在石碑的两侧,嵌着2块横碑。一块是凤台县令葛周玉在嘉庆五年(1800)立,记载书院村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晋、魏、何等3家其中的晋家与何家的宅第争端以及判决书,因此也叫“明道祠界线碑”。另一块立于嘉庆二十四年,记载明道祠的由来、捐资建祠人姓名、时间等。嘉庆以后,由于当年晋、魏两家是修葺书院的主要出资人和管理者,因而得到了大部分建筑的产权,于是书院的讲学活动就逐步转移到明道祠堂。光绪初年,书院便直接取“明道祠堂”之名,称为“明道书院”。科举制废除后,各地兴办学堂,明道书院在这时成为一所小学所在地,当地人也把明道祠堂所在的这个院子称为“书院小学”。直到1975年祠堂被拆毁,这里就完全成为村办小学的所在地。现在,晋城书院修缮保护工程仍在持续,晋城市政府也致力于最大程度复原之前书院的全部设施。
(二)晋城书院之由来揣测
以上介绍了明晚期以来有史记载的晋城书院的发展状况,虽然之前的历史还无从考证,但可根据现有一些文字史料和书院中的遗迹做以下猜测。
现有明天启年间“古书院”石碣位于书院南面的文昌阁上,而陈廷敬在《体仁书院记》中也提及明天启年间泽州知州王所用修建了文昌书院,这一点也可与康熙《泽州府志》相印证。可以确定,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即以“书院”来称呼书院村,而晋城书院最晚在明代中后期就已存在。
关于书院的由来,陈廷敬在《体仁书院记》中说“泽州书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7]635,也明确提到“至其所以为晋城者,当五季迭乱,金革创残之余,礼乐诗书弦诵之习,久而未兴”[7]635。陈廷敬指出了程颢担任晋城令的社会背景,进而在后文阐明了晋城在熙丰年间发生的巨大改变,人们崇学尚文、敦行善道,出现了连中进士的局面。“其诸乡校之设最近治者,故在北城之外,此书院之所自昉也”[7]635。由此可见,陈廷敬认为位于城北的书院是晋城最早的书院,是程颢担任晋城令时所办。有此看法的,不止陈廷敬一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晋城书院创办的基础是程颢乡校。现在晋城书院中有一通立于清嘉庆二十四年的石碑,上面写道:“明道祠者,乃宋程明道先生令晋城时讲学处也。斯地旧无居人,因就教而遂家焉。是村特以古书院名。”[7]265这说明,在清代时,人们就明确认为明道祠堂是程颢担任晋城令时的讲学之地,并且认为书院村村名的由来就是因为程颢在这里讲学。
书院最早于何时存在,目前尚无法确定。但根据以上可知,陈廷敬的观点及一些学者的类似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程颢担任3年晋城令,确实对晋城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了晋城的文化面貌。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晋城书院有可能是在程颢乡校的基础上创立的,也很有可能在明代之前就已存在。
三、程颢对晋城的文化影响
金元以来,很多人把程颢在晋城办乡校作为泽州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二程对后世影响很大,晋城历代许多官员在建书院、修祠堂时,往往以继承程子遗教标榜之,于是程子牧晋的故事也在晋城坊间传为美谈。显然,程颢在晋城办乡校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时的影响主要是改善了晋城地区的社会风气和教育落后状况,起到了一种文化导向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经过历代士人的承认与发展,逐渐在晋城乃至整个泽州地区发展为一种文化上的信仰抑或是认同,仍然影响着今天晋城文化的发展。
史料中关于晋城地区书院的记载大多零散地分布在历代名人的题记、碑刻中,也有一些见诸地方志。以下主要从名人题记中选取一些进行分析。
(一)文化导向
自程颢在晋城办乡校之后,晋城地区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崇学尚儒精神逐渐显现。程颢弟子刘立之于熙宁七年(1074)到晋城任承议郎,此时距离程子担任晋城令已经过去10余年,“见民有聚口众而不析异者。问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5]328。可见程颢的教令在多年后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到了熙宁、元丰年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5]328。
元丰八年(1085),北宋诗人黄夷仲到晋城一带考察时写的《劝学诗》,展现了泽州学子的好学情景:“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去年校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赐袍。今年两科取进士,落钓连引十三鳌。迩来习俗益趋善,家家门户增相高。”[8]330自程颢在晋城兴学后,晋城的教育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据一些地方志书目记载,北宋时期泽州地区进士共有33名,其中晋城县有14名,居山西各地域中的第2名,仅次于太原府(并州),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同时期,太原府共有进士43名,潞州有13名,晋州(平阳府)有8名。
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此时距离程颢在晋城办学不过60余年。泽州置于金的统治下。金朝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是泽州地区的教育出现了繁荣景象。到了金末贞祐年间(1213~1217),蒙古发动对金战争,金宣宗决定求和并南迁,而河北、山东、河东等地兵乱,晋城也发生大规模战争。但也正是由于这场灾难,一些学者、学子迁往陵川等地,使得陵川在金元时期呈现人才辈出局面,赫赫有名的陵川郝氏家族也正是在这时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元朝郝经在《宋两先生祠堂记》中说道:“经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7]618而郝氏之学在金元时期成为陵川第一家学,显赫一时。
以上说明,自程颢在晋城兴学办校后,泽州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学习之风日盛,中进士的人数也仅次于当时的山西首府太原,晋城的文化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从程颢行教化的结果来看,程子乡校对人们的行为(好学)产生了一种文化导向作用。这种作用对后来晋城地区文化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文化认同
自元朝中期以后,二程的影响越来越大,供奉程颢的祠堂在晋城也开始出现,许多地方官员逐渐重视将地方兴学与程颢在晋城办乡校联系起来。
1.对程颢的供奉
郝经在《宋两先生祠堂记》中提到:“移书泽守段君,创祠于州学,以伊川先生配。”[7]618这是说,泽州守段直在元代州学附近建立了明道、伊川两先生祠。元代著名河防大臣、水利学家贾鲁(1297~1353,高平人)在《明道先生祠堂记》中也肯定了程颢在晋城的功绩:“宋明道程先生尝令是邑,分乡立校,民大化之。”[9]459元泰定年间(1324~1328),郡守在泽州署衙之阳修建明道祠。至正元年(1341),泽州知州南飞卿、同知张时举以及州判李士敏等人,又在旧县署修建了新祠。贾鲁这里说的“明道祠堂”,位于高平。从这篇文章来看,此时的高平也已经有供奉程颢的明道祠堂。说明最迟在元代,一些基层官吏已经开始认同程颢思想并利用程颢办乡校的事迹来宣扬文教。
明清时期,供奉程颢的就更多了。明代山西布政使祝颢在《明道先生祠重修告文》中写道:“先生道明千载,学淑万世,从祠庙庭,古今通制,维兹晋城,尝蒙教治,旧有专祠,日沦惰废。”[10]964卢玑在《明道先生祠堂记》中说:“洎先生去没,各乡校多建祠以祀先生之功德。”[10]964清代朱樟也曾写《明道程先生祠堂记》,其中说道:“先生去而乡校湮。元时县令亦有相继续兴者,而究不易久延。”[7]639并说道,乡校之兴乃“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责望也。”[7]639以上都是在说程颢离开晋城后,后人多建祠堂来纪念和感恩程颢的功德,将其作为神灵来供奉,逐渐形成了一种在民间的文化信仰。
2.地方兴学与程子乡校
至正年间(1341~1370),阳城知县赵绳祖重修文庙。赵绳祖在记载兴学过程时,并没有提到程颢在晋城办乡校的历史,但在后来的碑记中却提到了地方兴学,乃程明道尹晋城之遗意。这说明程颢办乡校在阳城地区的影响很大,赵绳祖以此来激励学子勤奋向学。明朝人姜润身在《晋城书院记》中说道:“宋程明道先生尝为晋城令,教化旁及,士风丕变……弘治初年,柳塘杨君子器始宰高平,慨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毁其淫祠曰新庙者,改为正蒙社学,乡人亦以书院呼之。”[11]1186姜润身认为程颢开晋城社会文化之风,并且到明朝时都有很大影响,于是利用程子乡校来增加自己所办书院的合理性,扩大在地方上的影响。到了清朝时期,晋城、高平、陵川等地都有明道祠堂和书院存在,渐渐地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文化认同。
另外,陈廷敬在《体仁书院记》中的观点上文已经有所提及。陈廷敬认为当时的体仁书院(即现在的晋城书院)是晋城最早的书院,是程颢担任晋城令时所办。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民间盛传程颢在晋城建乡校72所(或说40所、60余所)。《泽州府志》中有记载,康熙年间,泽州府曾下令勘察程颢办学遗迹。说明到了清代,人们对于程子乡校的历史更加重视,对其认识更加深入和具体。
以上表明,自元朝以后,地方官吏越来越娴熟地把程子乡校的事迹运用于地方兴学之中。程颢担任了3年的晋城令,郝经称程颢的影响,“达乎邻邑之高平、陵川,渐乎晋绛,被乎太原,担簦负□而至者日夕不绝。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7]618。从一些资料和实际来看,确是如此。程颢办乡校不仅使一些官吏、知识分子根据社会需要和实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动(兴办书院),也由于某种辐射作用,加强了泽州地区的文化联系。这也是明清时期泽州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原因之一。
上面列举这些名人题记的目的不在于证明晋城书院的历史价值如何,重要的是阐明程颢办乡校对后世晋城地区人们的文化心理产生的影响。现在,当地人普遍把晋城教育在金元以后的腾飞归功于程颢在晋城办乡校、行教化,对程颢心存敬仰。晋城书院已经成为晋城独特而有效的文化教育资源。现在的晋城书院还处于不断的修复中,当地政府把它命名为“程颢书院”,并在书院南面开辟了一个文化广场,建立了一尊程颢塑像,立起了一些刻有二程之语的石柱。目前,书院村已经围绕着书院形成了一个大的书院文化园区,形成了一个文化小镇,让人们的业余生活多了一些文化气息,也加深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四、结 语
程颢在晋城虽然只有短短3年,可是对晋城的影响是深远的。程颢实行的种种举措促进了晋城的发展,晋城书院是当今晋城人对程颢的永久纪念。笔者认为,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即以“书院”来称呼书院村,晋城书院最晚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存在。另外,一些资料和遗迹也表明晋城书院有可能是在程颢所办乡校的基础上修建的。自元朝以后,一些文人学士抑或官吏对明道祠堂的重视,当地百姓对程颢的供奉,甚至在修葺书院(包含高平、陵川等地与程颢有关的书院)时往往与程子办乡校相联系,使人们逐渐对程颢在晋城兴学办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认同,普遍认为晋城文化的大发展自程颢始。现在的晋城书院在2007年被认定为晋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成为晋城的文化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