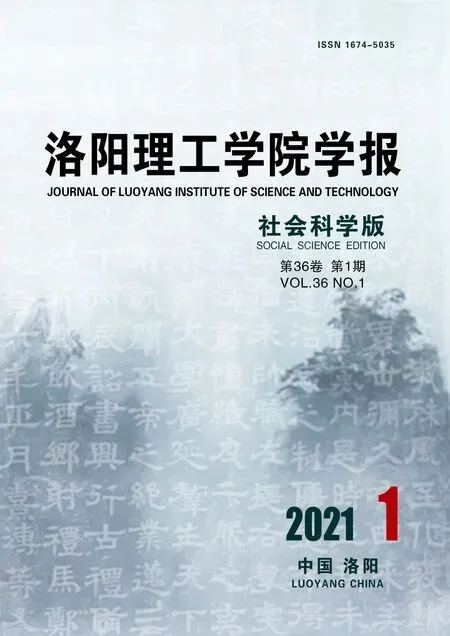论李准《黄河东流去》的黄河意蕴
刘保亮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1]随着国家“黄河”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如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成为重要而又紧迫的时代命题。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机构成部分。在目前河南省掀起的奏响“黄河大合唱”发展篇中,“中原作家群”对黄河的文学书写与文化表达,是我们深入挖掘、阐释黄河文化价值不可忽视的核心内容之一。
黄河,是“中原作家群”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突出意象,而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分析解读其文本中丰富的黄河意蕴,不仅可以开掘中原文学的地域特色,而且也能从文学角度彰显黄河文化的价值意义。
一、黄河:作家人生的情感地理
情感地理学是近20年来才“崭露头角”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关注与研究人、情感、地方之间的重要影响与相互作用。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地方”是人类生活的情感投射之处,“恋地情结”是指“人对所在的环境产生情感依附和依恋”[2],是人类最为普遍的一种情结。李准在黄河边出生与成长,成名以后又多次在黄河沿岸或黄泛区“劳动锻炼”,这使其与黄河结下不解之缘,由此也产生了对于黄河的浓重的“恋地情结”。
身体作为情感发生最紧密的空间尺度,受到情感地理学的高度关注[3]。出生地,是人的身体最初接触这个世界的地方,也往往是人生“恋地情结”的起始点。李准出生于洛阳市孟津县麻屯镇的下屯村,这里距离黄河不到20公里,靠近黄河最后一道峡谷深川小浪底。小浪底是黄河中下游分界的咽喉之地,在小浪底水库建成前是峻关险道。河水波涛翻滚、巨浪连天,这是少年李准眼中颇为雄壮宏伟、气势如虹的自然景观。“李准自从第一次来到黄河,投入黄河的怀抱,就有一个缠绕他一生的愿望:为黄河画一幅像,谱一支曲,唱一出歌”[4]34。
李准与黄河有着深厚的情缘。查看李准年表,1942年,为寻找生路,14岁的李准在去西安的途中与黄泛区难民一道行走,亲身体验了黄河泛滥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在其年少的心灵中烙下凄惨、深刻的印痕。1954年8月,李准到荥阳县司马村落户,近距离观察黄河和接触黄河儿女,对黄河的性格和黄河人的命运有了切身的感受。1960年,李准到黄河岸边的郑州郊区祭城公社落户,为体验生活还担任了该社的社长。1969年,李准全家被下放到黄泛区西华县西夏公社,先后在屈庄生产队、前高大队劳动。这里是1938 年黄河决口受害最重的村庄之一,是黄泛区的中心。这期间,李准应村民的请求,为20多位老死村民写“祭文”,从而了解了几十户人家的悲惨家史,倾听了“黄水劫”中难民的血泪控诉,更深刻地认识到黄泛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农民作家冯金堂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者,陪同李准了解黄泛区的农村及农民的生活,与李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冯金堂的《黄水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第一部以黄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黄河花园口决口事件给中原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从李准为冯金堂修改《黄水传》、到两人一起体验黄泛区的生活、再到李准为冯金堂鸣冤平反,两位作家的文坛交往不仅展示了二人之间的情深义重,还透露出冯金堂创作《黄水传》对李准日后创作《黄河东流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两位作家共同的“黄河”情结,为中原文坛演绎了一段文学佳话。
如果说在中外文学史上作家与大江大河的生命关联是一个惯常的文学现象,那么,李准与黄河的关系再次证明了河流是哺育文学艺术家的一个摇篮。在三门峡,李准看着从神门、鬼门、人门三道峡口飞流直下、奔腾而出的黄河之水,迎面就是千古有名的大礁石“中流砥柱”,上刻大字“照我来”。李准为黄河的磅礴气势和古人的胸襟、气魄所倾倒。1974年,为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李准沿黄河到济南,再到入海口,搜集黄河两岸的文献资料,体察民间的风土民情。1975年,李准又赴西安、咸阳等地,了解掌握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堤后中原难民的流离逃亡情况。李准发现,虽然中国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决口,但这次造成的“流民图”可能人数最多、区域最广、历时最长。黄河决口所带来的灾难场景与恶劣后果,使李准内心产生巨大的震撼,这种极度的悲哀和难忍的痛苦,以至使其几次想跳进波涛滚滚的黄河,有了却人生的冲动。随着与黄河越来越深的缘分与感受,李准决心要为20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30多年间中国各阶段的社会运动进行编年史式的立传,撰写一部黄河与人民的大型史诗。
黄河构成李准的情感地理,成为其写作的重要题材和思想内容。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认为,小说中的地理景观不仅是承载小说叙述内容的“容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反映,更是作家“情感结构”的文化再现[6]433。黄河作为李准文学作品的核心意象,寄寓着作家内心的“情感结构”,成为“让人感到价值存在”的精神母地。这从李准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他出生在黄河岸边,少年时期成长在黄河岸边,青年时期多次到黄河岸边体验生活,中年以后开始把黄河作为书写对象,以满腔的热情唱出“黄河颂”。李准与黄河似乎有着永远撕扯不开的神秘缘分,这也使其成为真正的“黄河之子”。李准越来越感到黄河的丰富与沉重,他好像是为这个使命——写黄河而出生的。由此,黄河在李准心中已不只是一条自然的河流,而是与其产生强烈的心理联系和思想纽带的“情感地理”,是立足这一“地方”瞭望大千世界的文学窗口。
二、黄河:中原生存的苦难境遇
山河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场域,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依托。在中原大地,如果要寻找标志性的地理景观,黄河是一个突出的自然意象。黄河自陕西潼关进入河南,河面逐渐开阔,特别是到了郑州桃花峪之后,水流平缓,大量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成为著名的“地上悬河”。黄河之险,险在河南。在有历史记载的2 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 500余次,2/3发生在河南;河道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20次发生在河南。中牟境内不到40公里的河堤,历史上曾决口 45 次。黄河多次的决口与改道,改变了中原大地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活、人文环境等。由此,“黄河”这一生动而又形象的“造化演示”,成为中原作家最爱书写与反复表达的对象。
“黄河”走进李准的文学世界,主要因为郑州花园口决堤事件。“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军南下,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水淹豫、皖、苏三省44县,淹死和冻饿而死的人数达89万……天灾人祸不断,使原本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成了一个灾难重重难以生存的地区”[7]17。“以水代兵”的黄河决堤改道,使牲畜、庐舍尽付波涛,嘉禾良田悉成泽河,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生命朝不保夕。并且,由于河南境内存在大面积黄土台地丘陵区、丘陵垄岗区,缺乏保水、蓄水的条件,这一地理因素导致洪水过后往往是“水继以旱”,“大旱之后,必有蝗灾”。因此,花园口决堤还引发了1942~1943年连续2年的大规模旱灾,形成饿死300余万人的“河南大饥荒”。花园口决堤事件是中国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花园口决堤及其之后的旱灾,造成了河南人沿着陇海铁路线向陕西逃难的“流民图”。对此,李准在《黄河东流去》中有着逼真的描写:“黄土大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像一条黑色的河流,缓慢地艰难地向西流动着”,“路两旁,到处是饿毙的死尸”,“地上躺着坐着的衣不蔽体的难民群,简直像一堆堆破布片”,“最令人寒心的是,已经倒在地上还伸出双手乞讨、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的濒于死亡的乞丐”,“灰黄的天空中,嘎嘎叫着成群成群的抢啄死尸的乌鸦。”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对“黄水劫”的现实主义书写,是对国民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涂炭生灵的愤怒控诉与激烈批判。这是发生在中原大地的一场纯粹人为的灾难,随着历史真相的揭开逐渐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暴露了迷雾背后的罪魁祸首。《黄河东流去》中的“黄河”意象,在作品中与其说被动地扮演了灾难造成者的角色,还不如说它更多的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见证者。
“黄河”意象饱含着中原大地的沉重苦难,李准对《黄河东流去》的小说叙事,也是对中原人民生存境遇的苦难叙事。作品以黄泛区为叙事背景,以赤杨岗村的李麦、徐秋斋、海长松、王跑、蓝五、春义、海老青等7户农民的命运起伏为叙事线索,以人物的迁徙奔命、辗转生活、生存挣扎为叙述核心,真实地描写了他们“各有各的不幸”。李麦,是一个因她娘一辈子没有吃过几次麦子而给她取名“麦”的农村女性。李麦4岁丧母,从小跟随失明的父亲四处流浪、沿路要饭,后来定居赤杨岗。父亲给地主家当“磨倌”,累死在磨房中,丈夫被海骡子栽赃冤死,有着“九蒸九晒”般的受难史。海长松,无论是给人挑水来换取粥舍,还是挖防空洞来养家糊口,做的都是出蛮力而不挣钱的粗活儿,无法改变一家人饥寒交迫的困境。海老清,在洛阳给人做长工,腰杆累得弯曲,被地主沉重剥削而惨死他乡。王跑,因为一场“石头梦”,险些丧命。最为悲剧的是蓝五,聪明、智慧,一杆五眼唢呐,样样曲调都会吹。就是这样一个颇有才华的民间艺人,与雪梅相识、相恋,而后私奔、离别、重逢,最后的结局却是对爱生死不渝的无奈殉情。《黄河东流去》叙述了一个又一个悲剧故事,令人难以卒读,使我们深深领悟到“黄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是一条受难的河流”。
“某种程度上,河南人的历史就是一部黄河的变迁史”[8]68。中国古代历史上,黄河频繁的决口、改道都给河南带来灾祸,河南人民灾难连绵、苦难沉重,这也铸造了中原文学源远流长的苦难叙事传统。苦,是河南的一大特点。如果说李准《黄河东流去》里的“黄河”意象蕴涵与凝聚着中原的苦,那么这一“黄河”意象并不为李准所独有。冯金堂的《黄水传》、梅桑榆的《花园口决堤前后》、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魏世祥的《水上吉卜赛》等,都以“黄河边的故事”描写了中原人民生存的苦难境遇。分析、解读这一系列作品中的黄河故事,呈现出“中原作家群”对黄河毫不掩饰的文学偏爱。这偏爱不仅因为通过“黄河”可以书写中原大地曾经的多灾多难,而且从中更能再现中原人民乃至中华民族抗争苦难的精神毅力。
三、黄河:中华民族的精神表征
李准在《黄河东流去》的代后记《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中谈到作家在接触黄泛区难民时的场景:在临时居住的席棚中,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也要先捧到老人面前,遵守着长幼有序的伦理观念;一个青年妇女自卖自身,以换取粮食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一家大小5口人在洪水来临之时选择了“同归于尽”,骨骸堆积在一起。李准从这些具体的场景开始认识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伟大的人民。李准说:“中华民族是个大仁大义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必然有伟大的生命力,必然有伟大的前途……我们平常说的伦理道德究竟是什么?黄泛区的人民在那样艰难困苦、濒临死亡边缘的情况下,人乱伦不乱,这是什么东西?我以为形成一个民族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的伦理。伦理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本身也是一种精神。”[9]247这种精神“一旦在民族危亡、大灾难临头的时刻,便会焕发巨大的力量,放出灿烂的光辉”[10]。李准创作《黄河东流去》的主要意图就是以黄河东流、奔向大海的气势和信念,书写中华民族“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11]70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黄河东流去》第一章“黄河”的引言。小说中写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是祖国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人民勤劳勇敢性格的象征。李准曾看到黄河里的舵公撑船,任凭波涛汹涌澎湃,漩涡像车轮般翻滚,而船却稳稳地行驶在青黑色的激流里。在三门峡的鬼门关,艄公沉稳地掌舵,船随着飞流在大漩涡里转一圈,顺着水势刚好绕过砥柱石。黄河舵公、艄公从容的气势,使李准深深震撼,感受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与勇敢。黄河人与黄河故事,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
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集中反映在《黄河东流去》中的底层人物身上。李麦,苦难的生活遭遇没有使其沉沦,她有着不信神、不认命而勇于同命运抗争的精神,任何困苦艰难都能坦然面对,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强者的气质。大水来临,她跑前跑后为春义举办“水上婚礼”;在寻母口找到了拆被子的活计,使村里每家都能够暂时生火做饭;在西安承揽了一宗手工活,顾住了难民们的吃住;当众撕毁“良民证”,唤醒大家不要卖身给鬼子当苦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黄泛区,带领乡亲们重建家园。在李麦的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有情有义和侠肝义胆。徐秋斋,一个乡土社会民间寒士的形象,忠义、仁厚、有骨气。徐秋斋“平素常给穷人办事”,在赤杨岗颇有人缘;在寻母渡口,他听说难民被盐行老板坑骗,便出主意帮助难民讨回工钱;沿街摆摊算卦糊口,替穷人看八字分文不取而只挣富人的钱;在西安城墙下的席棚里,他强调人与畜生的不同在于道德和尊严,他的智慧、正直、节气呈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美。此外,还有四圈非常义气地拯救小响,海老清对雁雁的父女关爱,长松帮助乡邻做篱笆门,海春义对土地的无限热爱,陈柱子对凤英的经商指点,蓝五与雪梅、天亮和梁晴的忠贞爱情等,读来无不感人至深。《黄河东流去》通过对黄河流域的这些普通民众的书写,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那就是在极端困苦下自力更生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生存能力,是在绝望境地中体现出的那种相濡以沫相互支持同甘共苦的互助精神,是那一颗在任何时候都正直、清白、向善的心。”[12]86
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有着浓重的劳动人民情怀,这既表现于其对黄河流域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关怀与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还表现于对黄河流域人民身上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的热情赞美和由衷尊敬。李准认为“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11]2。的确,从《黄河东流去》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命意志、机智的生存策略和真挚的伦理情感,这是黄河流域人民乃至中华民族抗御天灾人祸、追求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石。
四、结 语
黄河古代曾被称为“高祖河”“中国河”,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具有指向性作用。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纵观古今的文学作品,黄河不仅是中原文学的核心意象,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书写主题。李准对黄河有着浓重的恋地情结,其《黄河东流去》不仅描写了中原黄泛区人民的生存苦难,更是从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李准在作品中讲述的“黄河故事”,有着丰富意蕴和人文价值,饱含着浓郁的家国情怀,深藏着传统文化记忆,昭示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前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