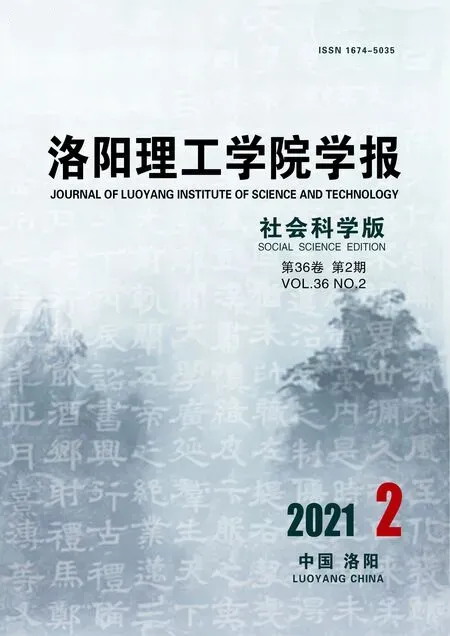曹植《赠王粲》作年新辨
——兼论与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的赠答关系
刘 璐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关于曹植《赠王粲》诗(以下简称《赠王粲》)的作年,林婧在《曹植〈赠王粲〉诗作年考辨》[1]一文中将前人说法归纳为三类,否定了“拜侍中前”的两种说法,肯定了“拜侍中后”说,并在此基础上将《赠王粲》的作年定在建安十九年(214)春。笔者以为此说有误。此外,作为《赠王粲》的唱和之作,王粲的《杂诗·日暮游西园》(以下简称《杂诗》)是判断《赠王粲》作年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历代学者对于这两首诗之间的关系只是简略提过,未作详细论证。因此,这一工作的完成便显得十分必要。
一、《赠王粲》是答《杂诗·日暮游西园》之作
刘履在《选诗补注》中提出,《杂诗》应是王粲(王仲宣)在荆州时为答复曹植赠诗所作,且“词意终篇相合”[2]33。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3]、黄节的《曹子建诗注》[4]也认为这两首诗之间的赠答关系十分明显,但是在先后顺序上存在分歧。刘履、吴淇认为曹植赠诗在前,《杂诗》应是王粲答曹植而作。黄节认为:“自羲和逝不留句以上,皆逐句相拟。重阴二句乃拟粲诗人欲二句,谁令云云始是植意。君指王粲,多念、百忧,指粲诗言也。”[4]55
现代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如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5],俞绍初、王晓东的《曹植选集》[6],郁贤皓、张采民的《建安七子诗笺注》[7],顾农的《王粲论》[8]等,都认为《赠王粲》是拟《杂诗》唱和而作。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赠王粲》与《杂诗》之间存在的唱和关系基本认同,但对于究竟谁先谁后,仍有争议。通过对这两首诗的诗文内容以及思想情感进行分析论证,笔者认为应是《赠王粲》在《杂诗》之后。
《杂诗》:
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上有特栖鸟,怀春向我鸣。褰衽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飚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7]110-111
《赠王粲》: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欲归忘古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5]44-45
从诗文内容上看,《赠王粲》与《杂诗》极为相似,几乎到了句句相拟的程度。如“愁思”与“忧思”,“西游”与“游西园”,“清池”与“曲池”,“发春华”与“敷丹荣”,“孤鸳鸯”与“特栖鸟”,“哀鸣求匹俦”与“怀春向我鸣”,“顾望但怀愁”与“伫立望尔形”等。《杂诗》的写景顺序是先“池”后“树”,《赠王粲》是先“树”后“池”。在《杂诗》中,作者“欲从之”,但因为“路险”而“不得征”。在《赠王粲》中,作者虽然“愿执此鸟”,但因为没有舟楫而作罢。通过对比两首诗的字、词、句可以发现,尽管两首诗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首诗的唱和关系十分明显。
从思想情感上看,《杂诗》表达了诗人虽然思念友人,但囿于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矛盾而无法与友人相会的忧郁苦闷的心理状态。诗文开篇便点出“忧思”之情,确定了诗歌的情感基调。接着又描写了“特栖鸟”向诗人殷勤鸣叫,诗人虽然很想上前与“特栖鸟”亲近,但因为路途险阻所以无法成行。末尾两句“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诗人心情看似转向乐观,其实却是用反话正说的手法传递出更深的悲苦。再看《赠王粲》,诗人也描写了有“鸟”求“偶”,自己有心与之亲近却因为没有“轻舟”所以无法渡河的无奈。当然,在这两首诗中,两位诗人都并非真的要与“特栖鸟”或者“孤鸳鸯”相会,而是用鸟喻人。“轻舟”自然也是某种时机或者方法的隐喻。在《赠王粲》的最后,曹植开始宽慰友人“重阴”会滋润世间万物。据《文选》李善注:“重阴,以喻太祖。”[9]443所以,也就是曹植告诉王粲不必因担心被忽视而忧心忡忡,曹操迟早会对其委以重任。顾农在《王粲论》中也认为:“王粲到底是不甘心无所作为的,而又不便直接向曹操提出,于是写一首诗送给曹操最为垂青的儿子曹植……表达了深切的遗憾和恳切的希望,曹植……回敬了一首《赠王粲》……请对方耐心等待。”[8]显然,从诗歌的思想情感上看,《杂诗》与《赠王粲》两首诗,前者倾诉,后者劝慰。再结合常理先倾诉再安慰的顺序,所以应该是忧思在前、劝慰在后。
综上所述,《杂诗》与《赠王粲》应属赠答唱和关系无疑,并且是《杂诗》在前,《赠王粲》为拟《杂诗》所作。
二、拜侍中前、后两说评议
历代学者对《赠王粲》的作年判断,总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作于“拜侍中前”,另一种则认为应作于“拜侍中后”。
(一)“拜侍中前”说
对于“拜侍中前”说,这种看法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对《赠王粲》的作年判断具体到年份,代表人物为俞绍初、王晓东等,他们认为《赠王粲》应作于建安十六年(211)[6];二是没有明确创作年份,代表人物有古直、赵幼文、顾农等。
古直《曹子建诗笺定本》曰:
玩“重阴润万物”等句,知此时王粲尚未显用,诗作于王粲未拜侍中以前无疑。[10]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曰:
王粲初归曹操,未任显职,对当时政治待遇抱着悒郁不满之悲思,欲见曹植申诉而无机会,故写诗借以倾诉自己的愿望。[5]46
由上可知,古直认为王粲作《杂诗》时“尚未显用”,所以《杂诗》应作于王粲被拜为侍中之前。赵幼文认为,《赠王粲》为答复《杂诗》之作,结合王粲的生平履历可以判断《杂诗》的作年应在王粲拜侍中前,那么《赠王粲》作为唱和之作,自然也创作于拜侍中前。顾农在《王粲论》中也认为,《杂诗》以及作为和诗的《赠王粲》应是作于王粲归曹之后、建安十六年王粲升任军谋祭酒之前[8]。
对于古直、赵幼文的看法,林婧主要从以下三点进行反驳。
第一,“重阴润万物”等句,逻辑上只能说明王粲主观上认为自己“未显用”,并不足以证明王粲此时真的未任显职。
第二,林婧认为,《赠丁仪王粲》诗应作于建安十六年。此时,王粲虽未任显职,身处“末位”,但却积极乐观,对前途充满信心,并非赵幼文所言“对当时政治待遇抱着悒郁不满之悲思”,更与《杂诗》中自怨自艾的形象难合。
第三,从王粲作于“归魏初期”的其他作品中也可看出其对仕途功名的热情与信心。由此可见,古直、赵幼文之说不当。其一,林婧认为“重阴润万物”等句只是王粲主观上认为自己还未获得重用,并不足以证明王粲的实际待遇。然而,这句诗是出自曹植的《赠王粲》,从逻辑上来说也只能是曹植主观上认为王粲当时未获显用,对王粲来说无疑是客观的。其二,林婧认为《赠丁仪王粲》作于建安十六年,而且据林婧所说,这一说法取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然而笔者了解到,关于《赠丁仪王粲》的作年在学界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就是林婧所认同的建安十六年,代表人物有古直、张可礼、俞绍初等;另外一种却是建安二十年(215),代表人物有李善、刘履、丁晏、朱绪曾、黄节、徐公持以及郁贤皓等人。此外,在由王云五主编、邓永康编撰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魏曹子建先生植年谱》中,也将《赠丁仪王粲》诗的作年归于建安二十年[11]。显然,后者才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由此,林婧以《赠丁仪王粲》作于建安十六年这一很可能是误判的说法来反驳古直、赵幼文,难以服人。其三,林婧认为,王粲在建安十六年从征马超之际所作诗文如《咏史诗》《吊夷齐文》等,都属昂扬进取之作。所以,此时的王粲不应该发出忧愁感叹。笔者以为此说有失严密。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六年)秋七月,公西征。”[12]24可知,西征马超时已是秋天,而《赠王粲》既然是拟《杂诗》作于春季,那么《杂诗》的写作时间一定早于《赠王粲》诗并且同在春季(根据诗中的景物描写判断),春秋有两季之隔,况且在这期间王粲还很可能经历了一次升任军谋祭酒,心情从忧转喜也未可知。因此,林婧仅以2首作于秋季的诗便断定王粲整整一年的状态,有些武断。
综上所述,林婧所引为证来反驳“拜侍中前”说的论据无法成立,有的论据甚至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暂时无法排除“拜侍中前”说的可能性。
(二)“拜侍中后”说
持此说的代表人物有张可礼,其在《三曹年谱》中提出: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杜袭传》……知粲虽为侍中,然亦悒悒不安。《赠王粲》……诗当是时为劝慰王粲而作。诗又曰:“树木发春华。”考《武帝纪》、《文选》卷五六曹植《王仲宣诔》,粲于建安十八年十一月为侍中,二十二年正月卒。则诗当作于是年春或明后年春,暂系于此,备考。[13]131-132
按照张可礼的说法,王粲因打听曹操与杜袭对话而被和洽批评,所以判断王粲当时虽已拜侍中但仍“悒悒不安”,再加上《赠王粲》又是为劝慰王粲而作,因此《杂诗》与《赠王粲》应作于王粲被拜为侍中后。笔者以为,仅凭他人的一句间接评价就断言王粲拜侍中后依然闷闷不乐,略显单薄。
首先,《三国志·魏书·和常杨杜赵裴传》内的“至其见敬不及洽、袭”[12]495一句,很值得琢磨。“见敬”一词,可理解为被尊敬、受敬重,那么“见敬不及洽、袭”便是说王粲不如和洽、杜袭受曹操敬重。然而,王粲却又“多得骖乘”[12]495,岂不矛盾?事实上,如果说曹操对和洽、杜袭是敬重,对王粲却是亲近。由《三国志·魏书·和常杨杜赵裴传》可知,和洽、杜袭二人有3个共同点:第一耿直敢谏,令人敬重;第二确有治国安民的才干;第三性格沉稳,持重守礼[12]。曹操却是“为人佻易无威重”[12]39。对比之下,王粲那“通侻”“躁竞”[12]495的性格无疑与曹操的脾性更加相投。这样一来,曹操敬重和洽、杜袭,但亲近王粲便在情理之中了。“见敬不及洽、袭”并不能证明王粲受宠不及和洽、杜袭,恰恰相反,“粲……多得骖乘”,“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14]1026。由此可知,王粲在被拜为侍中后,不仅没有遭受冷遇,还很受曹操欣赏、重视。《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挚虞《文章志》道:“太祖时征汉中,闻粲子死,叹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12]44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于王粲二子因参与魏讽谋反案被杀,曹操不但不打算严惩王粲,反而考虑为其留后,可见曹操对王粲的情深义重。
其次,曹植在《王仲宣诔》中对王粲的描述:“我王建国,百司俊乂。君以显举,秉机省闼。戴蝉珥貂,朱衣皓带。入侍帷幄,出拥华盖。荣曜当世,芳风晻蔼。”[5]243据曹植描述,王粲被拜为侍中后出行和装束都气派非凡。由“我王建国”可知,此时魏国已建,而“君以显举”应该是指王粲被拜为侍中一事。不仅如此,前文提到的应作于建安二十年的《赠丁仪王粲》诗也从侧面表现出王粲被拜为侍中后的春风得意,尤其是“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5]197句,表现了王粲被拜侍中后志得意满的生动表现。也正因此,曹植才作诗规劝丁仪、王粲二人“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5]197。劝告他们无论是过于得意或者过分愁怨都不应该,只有保持谦卑中正之心,才是正确长远之道。如此看来,被拜为侍中后的王粲显然意气风发,这并不符合张可礼“知粲虽为侍中,然亦悒悒不安”的判断。
最后,林婧将王粲在升任侍中后所作的5首《从军诗》作为反证,试图以“虽每首篇末亦有歌功颂德,但所占比例很小,其间反复言说的,主要还是征夫之悲与无用之恨”[1],以此证明王粲在拜侍中后依然忧郁愁闷。笔者以为,仅凭只言片语,难以说明整首诗的思想。
学界对5首《从军诗》的作年众说不一,但判断大致集中在建安二十年与二十一年(216)。也就是说,这组诗作于王粲被拜为侍中之后基本是可以确定的。从诗文内容可以发现,王粲的心态总体上还是积极的。笔者随机选取2首进行分析。如《从军诗·其一》: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昼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7]79
诗人以“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句奠定了诗歌赞颂的基调。以“震天威”“俯拾遗”“一举”“再举”等夸张之笔,热情赞扬了曹操用兵如神、所向披靡的神武之态。接着又以“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写军中饮食、宴乐之盛和俘获物资之多。“歌舞入邺城”以下写班师凯旋,并讲述了诗人励节入仕、协理朝政的志得意满。整首诗语言明快,感情昂扬豪迈,洋溢着大军胜利后的喜悦之情。
再如《从军诗·其三》:
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征夫心多怀,凄怆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7]89-90
乍一看,作者似乎是在感叹军旅生活的艰苦与征夫离家的乡愁,但后四句,作者笔锋一转,一扫思乡的悲怆,以一句“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表现出了军人般坚毅果敢的气质。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粲即使在困境中也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远大抱负,即使偶尔思乡也不会放任自己一直沉溺在这种情绪中。正是这种情感的落差,反而突显出诗人慷慨豪迈的情怀。
综上所述,王粲升迁为侍中后意气昂扬,其满腔抱负终于有机会得以施展。且王粲当时很受曹操欣赏、器重。因此,“忧思”满满的《杂诗》以及为安慰王粲而作的《赠王粲》便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其拜侍中后。
三、建安十六年说补证
前文已提到,顾农认为《杂诗》是王粲在升任军谋祭酒之前所作。而俞绍初、王晓东更是直接在《曹植选集》中将《赠王粲》的作年定在建安十六年,但他们未对这一推论作详细说明。笔者在此试对其作一补充论证。
《曹植选集》认为:“建安十六年正月,曹植被封为平原侯,大概在其后不久,王粲写有《杂诗》‘日暮游西园’一首,其间隐约地流露出想与曹植朝夕相处的愿望……此诗写后不久,王粲被任命为军谋祭酒,果与曹植一起跟从曹操西征马超,终于实现了愿望。”[6]13针对这一判断,林婧提出质疑:“《王粲年谱》中俞先生既已提到建安十六年邺下文人集团‘行止相随诗赋唱和’的盛况,那么《曹植选集》中王粲想与曹植‘朝夕相处’而无法实现的结论又如何得出?《曹选》中‘大概在其后不久,王粲写有《杂诗》’的说法,只能算是俞先生的一种猜想。”[1]按照林婧的逻辑,既然王粲已经同曹植“行止相随诗赋唱和”,那么,再要求“朝夕相处”显然矛盾。事实上,非但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合理。
之所以说不矛盾,是因为从《赠王粲》“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句可以明显看出,曹植从《杂诗》中所领悟的,除王粲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外,还有他得不到重用的哀诉。按照曹植的才能与心性,自然一点就通,其很快就对王粲的言外之意心领神会。所以,曹植一定是在十分了解王粲当时境况的前提下,又收到王粲的倾诉诗文,才会作诗对王粲进行安慰勉励。正如黄节所言:“植虽拟粲持为赠,然亦就粲之身世立言。”[4]55因此,不能将《杂诗》与《赠王粲》定义为单纯的怀人传情之作,《杂诗》看似是王粲思念友人的诗,但其实更多的是希望被重用提拔的政治意愿。若从这一角度理解,那么林婧的上述困惑便迎刃而解了。
再说合理。笔者将从史实、情理两个角度进行论证。
上文已经论述,判断《赠王粲》系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要找出曹植和王粲在春天都身居邺城的年份。那么从史实上看,由《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知,在王粲拜侍中前,王粲与曹植在春天同时居邺的年份有建安十五年(210)、十六年、十七年(212)[12],也就是说,王粲与曹植有可能在这3年中的某一年进行诗歌唱和。
《杂诗》有“日暮游西园”句,《文选》吕向注:“西园”即“邺都之西园”[9]546。与曹丕《芙蓉池作诗》中的“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9]405中的“西园”应是同一处。也就是刘良注左思《魏都赋》“文昌殿西有铜爵园”[9]125中的“铜爵园”,又称“铜雀园”,铜雀台便位于此园之中。然而,铜雀台是建安十五年的冬天才开始修建[12],王粲又怎么能在春天游园?显然从时间上无法对应。因此,应排除建安十五年,只剩建安十六年、十七年可供筛选。
关于王粲在建安十七年的记载不多。然而,对于曹植而言,却是特别且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那就是曹植因创作《登台赋》而得宠。曹丕《登台赋》序言:“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15]15《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12]416很显然,这期间的曹植正春风得意。但《赠王粲》诗中的“惜哉”一词却传达出曹植的落寞之意。诗人有心前去与友人相会,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想“渡河”却没有“轻舟”。对此顾农也认为:“曹植……说‘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表示自己并无用人之权,爱莫能助。”[8]这显然和“特见宠爱”相矛盾。因此可推测,当时曹植在其兄弟中的地位并不十分优越或得势,所以有心无力,无法对王粲施以援手。所以,《赠王粲》作于建安十七年的可能性也不大。当然,仅凭这一推测是不够的,再看建安十六年的事。
建安十六年,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曹植受封为平原侯[12]。《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记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并见友善。”[12]447由此可知,王粲与曹植相交,也许便是从这时开始。曹植的《王仲宣诔》中有“乃署祭酒,与君行止”[5]243句,而建安十六年七月,曹植和王粲确实一同随军征战马超。王金龙在《王粲行年系地考》中也认为,由曹植《王仲宣诔》中的“乃署祭酒,与君行止”可以得出,以后历次军事行动,王粲多与曹植同行[16]。由此可以推测,王粲升为军谋祭酒应该就发生在从征马超前不久。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理出一条王粲在建安十六年的行迹:春季与曹植相交,不久之后升迁军谋祭酒,到了七月和曹植一同从征马超。这时,若将王粲在春季与曹植相交后创作《杂诗》向曹植倾诉,且在不久后收到曹植答诗劝慰的事件嵌入其中,毫无违和之处。
从情理的角度看,王粲在建安十五年曾创作《七释》一文。在文中,王粲隐约表现出在“无为无欲”与“进德修业”这两种选择中摇摆不定、彷徨消极的情感。然而,到了建安十六年从征马超时,王粲却一扫萎靡之风,作出《吊夷齐文》,抛却个人所谓的气节主动入世,表现出不凡的眼界与积极的态度,这和其创作《七释》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测,也许是中间发生了足以让王粲重振信心的事,而收到知己回信安慰并升迁为比丞相掾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军谋祭酒,就是这样的事。
如果按照这样的推论,建安十五年,初归曹魏的王粲正因一腔热血与才华无处施展而愁闷不已,后在建安十六年春天结识曹植。于是,王粲写诗给曹植以纾解愁闷,并且很快便收到曹植予其安慰的答诗。之后不久,王粲升迁军谋祭酒,和曹植一起随军西征马超。此时。王粲不仅自己的雄心和才能有了更好的施展机会,还得以与曹植行止相随。于是,王粲一扫苦闷,信心勃勃,跃跃欲试。
笔者通过结合史料、诗文、情理逐年分析论证、筛选排除,认为曹植《赠王粲》应作于建安十六年春最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