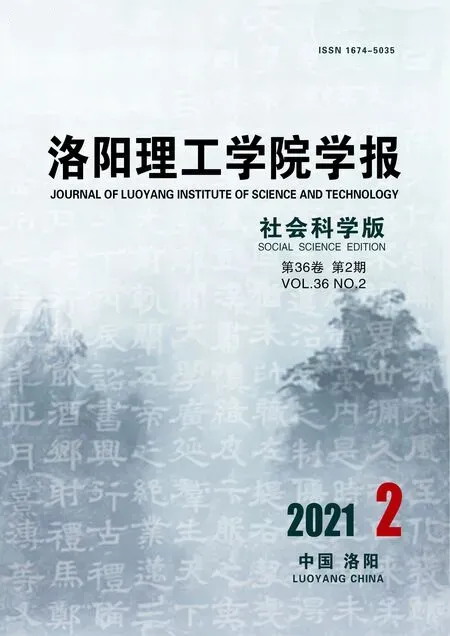二程“敬”思想研究
张 国 策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关于二程“敬”思想或者说修养方法的研究,自近代以来已经有些研究成果。钱穆的专著《宋明理学概述》在程颢、程颐两章,就涉及二程的“敬”思想。钱穆将二程的“敬”解释为用心,是一个如何养心的问题。陈来在其专著《宋明理学》中对于二程的“敬”也有研究,主要研究二程在对待“敬”上的区别。漆侠的著作《宋学的发展与演变》对二程的“敬”也有研究。漆侠认为,“敬”是程颢、程颐两兄弟的认识论,但他们两兄弟在“敬”这个认识方法或者修养方法上也同样存在分歧。此外,漆侠还认为“敬”问题是洛蜀党争的一个问题。但是上述学者的分析大多是分散的,不系统的,还缺少对于二程“敬”问题较为全面的研究。笔者主要从二程“敬”思想的起源、内核、分歧以及传承等几个角度来分析理解二程的“敬”。
一、儒学在宋代的变化:由外王向内圣偏斜
就哲学层面而言,宇宙观与人生观是哲学的两大范畴。入世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大的趋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就有“三立”的说法。范宣子问叔孙豹何为不朽,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466中国思想所传承的入世思想,从叔孙豹这句话里便可以体会。宋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是新儒学的形成时期。儒家自孔子以来便讲求入世,称“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儒家并非不信奉鬼神,否则也就不会出现3年孝了。但儒家还是注重入世这一焦点,即宋儒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儒家自汉武帝一统思想之后,儒学越来越走向经学训诂、师传家法。汉以来形成的传统儒学在经过中唐社会经济思想方面的变革之后,终于不可逆转地走上了革新的道路。邓广铭说宋学是对汉学的“反动”。在宋代新儒学中,儒家的内圣与外王区分得非常明显。先期宋学带有炳革宇宙、颠倒社会的伟大气魄,意图在“外王”方面,给社会重新形成一个合理秩序。这一时期的宋儒在政治上大力作为,回向三代不仅是一种口号,更是一种实践。但在经历庆历、熙丰两次变法失败之后,宋儒逐渐将重心放于内圣,“他们认为若果在社会下层学术、心术基础没有打稳固,急遽要在上层政治图速效,那是无把握的危险事”[2]222。
当然,也要明了宋儒探究“内圣”也有其区别。周敦颐、邵雍、张载,他们更偏向于一种宇宙观,想从宇宙观来直接指导人生,用宇宙论的规范来规治个人。而二程兄弟则直接从人的本心、从生活经验来指导人生。他们虽有各自的宇宙观(理),但他们更提倡直接地从人生观来指导人生,修养内心。“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形成了一个代表新的风气的学派”[3]59。就像程颢所言:“吾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569二程“喜言工夫,不喜讲本体,又重内心之直证,而清物理之研寻”[4]206。所以,“敬”字在程门就极其重要。而二程的“敬”又是浑然自家体贴出来。朱熹说:“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要,到程子始关聚出一个敬来教人。”[5]208朱熹又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要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6]210漆侠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是程氏兄弟修养方法中最根本的方法,“敬”是程门修养的最重要的方法。钱穆也说“敬”字是程门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字。
二、二程“敬”思想综述
(一)二程“敬”的来源
敬的最早源头出于《诗经》与《尚书》,主要是一种敬天思想,此后发展至敬鬼神、敬德。考释儒家的“敬”,《左传》中有“敬,德之聚也”之说。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敬天体德”,孟子也曾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但在孔孟思想中,敬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体系。宋儒时期,修身得道已经是一个大的理想,大家都认同有一个“道”,但对于如何修养得“道”,入圣门方法却各有不同。二程将“敬”字找出来,并赋予其极高的地位。二程的这个“敬”除吸收儒家传统思想外,同时也受到佛家“静”的影响。佛家认为人性没有分别,是本“性空”的,但是,由于受到种种“遮蔽”“染污”,人性才表现出善恶种种情形。佛家养心的方法便是“静”,用佛家语言讲就是“禅定”,用静坐的方法来专注精神,排除一切杂念从而达到一种彻悟。二程从佛家的“静”中汲取养心的方法,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但是,二程的“敬”却与佛家不同。佛家“静”是要达到空,万物虚幻不实,通过静坐来达到“以定证慧”。二程的“敬”有更多的内容,追求的是天理。所以程颐讲:“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7]203
(二) 二程“敬”的内核
二程“敬”成为一个体系主要体现在“涵养须用敬”这一言下。程颢提出“涵养须用敬”,程颐将此句扩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诚、敬二字在程门中内在地关联在一起,成为程门中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笔者将此修养方法编为一个进阶的形式,即:近取诸身→涵养→敬。近取诸身的诀窍是涵养,涵养的方法是“敬”。反过来也就是说,要通过对于自身的涵养来达到“敬”。从此进阶方式可看出,“敬”实是程门的修养工夫论,“敬”是修身之法。程颢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8]70程颐也说:“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8]374可见,要得内圣,在程门必求之于“近取诸身”。而“近取诸身”的诀窍则在于“涵养”二字。朱熹评价程颢之学时曾说:“明道之学,从容涵泳之味恰。”[7]2363涵养功夫是程门修养工夫的诀窍,“敬”即从此出。下面来看几条二程的言论。
学者当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之深厚,涵养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终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8]64
李吁问:“每遇常事,即能知操存之意,无事时如何存的熟?”曰:“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养。今皆废此,独有义理之养心耳。但此存涵养意,久则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8]58
闲邪则固一矣,主一则不消言闲邪,有以一为难见,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1]624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8]65
这些言论,前2条是程颢讲的,后2条是程颐讲的。从这4条言论中,可见“涵养”二字在程门的重要程度,它是程门修身处世的一大关键。更进一步,涵养的方法就是“敬”,“诚敬存理”。以“敬”来涵养,进而反躬,而内圣,再往外扩便是重建社会新秩序,“回向三代”的外王之道了。
三、二程对于“敬”的不同阐释
在关于内圣、修养的“敬”上面,程颢、程颐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 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对“敬”的不同理解
程颢性格温文和平,程颐性格严毅庄重。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记载:“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也。”[9]957而“伊川直是严谨,坐间无尊卑长幼,莫不肃然”[1]644。《宋元学案》中也有其性格之对比:
二程随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先生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先生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先生严重,人不敢近也。[1]644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明道学案》的案语中提到:“顾二程子虽同受学濂溪,而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1]540程颢、程颐性格上的差异自然引起他们在对待“敬”这一修养方法上的差异。程颢言“敬”,往往带有寻孔颜乐处的意味,其在对待“敬”的问题上,往往是和乐的。程颢讲敬,说“敬要和乐”。程颢主张从鞭辟近里处寻得天理。这里的“鞭辟近里”便更有生活上的气息。从这一点来说,程颢的“敬”如果找对头绪,是更加简单明了的。在这种宇宙观的引导下,“敬须和乐,只是中心没事也”,可见其平淡温和。而程颐的“敬”,更注重于内心的敬畏与外表的严肃。程颐说:“严威俨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须自此入。”[8]217程颐又说:“如何一者,无他,只是严肃整齐,则心便一。”[8]197再进一步来讲,程颢讲“敬”更显自由活泼之姿态。如程颢说:“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8]113又说:“今学者敬而不见,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来做事得重,此恭而无礼则劳也。”[8]85在这种性格影响之下,程颢的修养方法比起程颐来得更加简约。程颢认为无论是知识还是修养方法在既得后都需放开,不然便只是空守。所以程颢认为:“学者今日无可添,只有可减,减尽便没事。”[1]566但我们需注意到二程思想实同出一门,而又归于同途,其大方向终是一致的。程颐虽未说得减,但对于事物也怕其复杂而疑惑人心,使天理不明,难以找寻。程颐说:“闻见之知非德行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8]375这与程颢讲的“贤读书慎,不要循行数墨”,终是一途,大方向并无不同。
(二)程颐“敬”中的格物、集义
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程颢早逝,程颐继承程颢的大体思想,但对于“敬”有所损益和扩展。程颢在认识论、修养功夫论上认为敬只是敬,敬上更添不得一物。程颐则不同,程颐的敬上更有格物、集义的韵味,注重探索研寻。程颐说“格物致知”,又认为格物而愈见天理。陈来在《宋明理学》中说:“程颐认为,人不仅应当不断地修养自己的心性,还要不断从知识上充实自己,在理性上提高自觉性。因此精神修养与格物穷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广义地说,格物代表的活动也是一种修养的方法。”[5]87所以程颐的“敬”是将程颢的“敬”在己意上再扩大,更增添了格物、集义。如程颐所讲:“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当须集义。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8]256有学生就问程颐:敬义何别?程颐回答说:“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为孝,不成只守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所以奉侍当如何,温情当如何,然后能尽孝道也。”[8]256从这些来看,程颐较其家兄在涵养功夫上实是在细节上更进一步,更加精细了。既讲持敬,又言集义,合内外之道,养浩然之气,如此方是人欲合天理处。由此也可见程颐之严肃、精密。但程颐的集义、致知,仍是不脱“敬”这一方法的。程颐说:“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1]601可见程颐的敬是贯穿在整个致知过程中的,致知过程本身就是“敬”。黄百家说:“孟子师说‘必有事焉’,正是存养工夫,不出于静。”在一定程度上说,虽说程颐学说相较于程颢更加精密,在给人生以指导上更加明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讲“敬”,仍会走向另一极端,即程颐的学说较程颢的学说更加窄了,只向着格物上而去,“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陆九渊批朱熹“支离”的根源更可上溯至此。较之程颢只讲“敬”,而不在“敬”上添任何他物,更可见程颢、程颐之异。
(三)程颐学说之“主一谓敬”
宋儒尤其是理学家经常说到思虑纷扰这一问题。《二程遗书》载:
吕与叔尝言,患思虑多,不能驱除。曰: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8]56
宋儒常常出入释老,最后合于六经,他们的思虑纷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他们出入经史,出入释老,各家理论混杂其中,自然会产生众多的思考。张载是主思的,但转至二程,主内心之涵养。针对如何处理这众多的思虑问题,程颐便提出主一。程颐说:
学者先务,固在心智,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8]215
此可见程颐的主一主要是使心有主,心中充实一物一理,自然会解决思虑纷患。程颐的主一的内容是什么呢?程颐说:“如何为主,敬而已矣。”[8]215程颐又说:“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1]636通过程颐的话我们可知,“一”的内容便是“敬”。我们可以从一些生活的小事上来探究程颐的“主一谓敬”和“惟是心有主”。如:“昔贬涪州,渡汉江,中流船几覆,舟中人皆号哭,伊川独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问曰:‘当船危时,君独无怖色,何也?’曰:‘心存诚敬尔!’”[7]979只要内心充实,养浩然之气,以敬养之,又何必惧怕身体遭祸,这正是程颐以敬养身、主一谓敬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程颐的主一,主要是敬,用敬来充实心中。“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敬存心中,从而养浩然之气。同时可见程颐的主一,主要还是针对于“内圣”而言。程颐说:“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至于不敢欺,不敢慢,苟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8]216程颐的修养论,终究要比程颢的修养论严肃得多,于主一更可见程颐之严谨。当然,程颐的路子也是更加严密与清晰的,后人修养程颐的路是明了、方便的,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相比于程颐,程颢的“敬”就有些缥缈了。
四、二程“敬”思想的不足
在修养问题上,“敬”是程门的一大法宝,但是二程修养论上讲求“敬”也是存在问题的。宋学是一个大的概念,专就宋代理学而言,这是一门伦理重于宇宙论的学问,其要求是将伦理提升至本体地位,此伦理即代表着此世间的道体,是道体在人世间的具体体现,要求以伦理道德来重建人世间的秩序。在这里,理想是广大的,但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敬”是作为修养功夫而提倡的。这个修养是内向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或者说这个理论更进一步讲,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和道德修养问题。虽然程颐讲“格物致知”,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如钱穆所言:“颐之所谓‘格物穷理’者,并不如近代人的观念,认为所穷在物理。他之所穷,则仍是颢之所谓天理,只是欲穷性之理……程颐所欲穷者,仍是人文世界之理,即性理或者义理,而非自然世界之理。”[4]88所以,即使有“理”“气”等宇宙论,但是二程所开创的理学,并没有使中国走向自然科学的方向,而是走向伦理修养的心性之学,导致后人只言心性,高谈道德性命,于实际问题反而置至不理。
“敬”放在宋学来讲仍是内圣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宋儒转向内圣之学,导致宋代学术走向精致和狭隘。程门又极提倡道统,使得此后宋学转向理学,全然失去其初期之宏大。只讲诚敬表现在政治上,更显其问题。儒学作为一门入世的学问,讲求“学而优则仕”。文彦博对神宗皇帝说:“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8]5370二程的诚敬讲求人在达到内圣阶段之后,才能真正地回向三代。因为内圣毕竟是一个主观的评断,所以就出现一些极大的问题:什么才算内圣?怎样达到真正的诚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不仅会导致学术上的争论,而且在政治上也会产生大的分歧,甚至引起互相倾轧。
二程学问继承周敦颐,又糅合邵雍、张载之学,应当更加浑然博大才对。然而二程讲“性即理”、讲“敬”,以诚敬修养来达到克制人欲、明天理,这个学问却越作越狭窄。这也导致二程学问越向后发展越压抑人的本性,越来越讲“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谭嗣同在《仁学》中说:“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9]124二程的修养论虽说较佛门的“空”来得更加广阔一点、现实一点,但其专一内里,只谈养心,进而达到“礼”,达到“三纲五常”,其问题依旧是很大的。
五、门人对二程“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程门高足当属谢良佐、杨时、游酢和尹焞。杨时门下,两传而至朱熹。谢良佐、杨时对于“敬”,都有自己的说法。黄宗羲说:“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独得以发明师说者也。”[1]925《宋元学案》说谢良佐近于程颐、杨时近于程颢。但是谢良佐对于“敬”的理解,不同于程颐“主一之谓敬”之说,而主张“诚是实理,不是专一”。谢良佐说:“事至应之,不与之往,非敬乎?万变而此长存,奚纷扰之有?夫子曰:‘事思苟’正谓此耳。”[1]921谢良佐的“敬”,主要在于“常惺惺”法,这是谢良佐自己的发明。朱熹批评谢良佐入禅,说:“伊川之门,谢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差。”[7]2555谢良佐的“常惺惺”法便吸收了佛教禅宗的“主人翁常惺惺”的修养方法。解“惺惺”二字,朱熹注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谢良佐的“敬”主要还是保持心不昏昧,正心诚意。谢良佐的主敬虽吸收了些禅宗方法,但终是与释家有别的。谢良佐说:“敬是常惺惺法,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1]924于此可大体见谢良佐之诚敬。
杨时对于“敬”并没有什么发明。杨时学问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强调体验未发,又讲格物致知,反身格物。在诚敬问题上仍是继承程颐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杨时说:“敬与义本无二,所主者敬,而义则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实义亦敬也。故孟子言义,曰‘行吾敬’而已。”[1]948杨时又说:“学者若不以敬为事,便无用心处,致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1]950这些还是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和“主一谓敬”。杨时的“敬”不出程颐的教诲。
尹焞不主于对“敬”作概念性的发挥,而主于在实际生活中来践行诚敬的修养方法。尹焞讲“敬”只是严格持守,秉持师说。黄百家评尹焞:“和靖在程门,天资最鲁,而用志最专。”[1]1004朱熹也说:“和靖不观他书,直是持守的好。他语录中说持守涵养处,分外亲切。可知学不在多,只在功专志一。”[1]1004
杨时以下出胡宏、朱熹,而程门“诚敬”的修养功夫论更加丰富。
六、结 语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程对于诚敬问题的开发,显示了儒学在不断地发展转变,儒学进一步向哲理推进。这也更加突出了自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之后新儒学的特点。这是一种“内圣”的儒学,虽然他们仍讲“外王”,但在“内圣”之前,“外王”是不可能实现的,“三代”也无法回溯。如果不能“内圣”,那么“回向三代”的外王之学只能是一种空想。在“内圣”没有达到的情况下,转向“外王”,在理学家看来,就会导致产生王安石改革的后果,最后祸国殃民。在理学家看来,王安石的改革和王安石的“回向三代”都是“内圣”功夫不到位。张栻说:“王氏之说皆出于私意之凿。”[10]1053余英时认为:“王安石不分儒释道的疆界,他的著名的道德性命之说,已吸收了释老的成分。所以二程认为整顿介甫之学是当务之急。”[11]56这已经明白道出,二程认为王安石的“内圣”已经走上邪路,在此条路上去寻求“外王”,只能导致祸乱丛生;而要拯救这种弊端,要从心直接入手,以“敬”来修养自己。一个思想家,对于心性的看法和对于修养论的看法,决定着其思想的路子。从这点看,二程“敬”在其门内的重要性突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