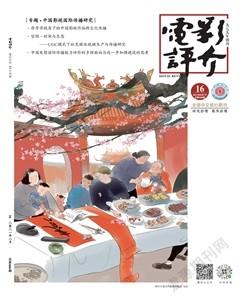老年群体的网络实践
刘阳 冷凇
当前中国社会两大鲜明的特征是老龄化和数字化,面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老年群体作为大众视野中的“数字弱势群体”在新媒体浪潮中逐渐边缘化,但短视频的出现正深刻影响着当下的传播生态,为积极老龄化贡献力量。同时,“银发网红”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的爆红成为一道网络文化景观。本文分析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潮”兴起的原因,探究“银发网红”现象蓬勃兴起的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银发网红”的出现给传播生态和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一些思考。
一、研究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认为,人类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产生的社会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早在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老龄化与健康”作为重点关注主题,老龄化必然给各个国家诸多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1956年,联合国对老龄化判定的具体界定如下,某个国家(或者地区)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将被视为老龄化国家(或地区),此项数据公布在《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中国在20世纪之后,即在2000年起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5月11日,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2.6亿。联合国人口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达到3.58亿,占人口总数的25%左右,2050年,这一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到36.5%,届时中国将步入高度老龄化社会。目前,在各国全球老龄人口横向比较中,中国老龄人口数量最多,而且老龄人口增加速度最快。
二、媒介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
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老龄化与飞速发展的社会媒介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中国的人口結构日趋渐“老”,但中国的媒体形态却日“新”月异。现代社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观:青年一代在享受着信息时代,中年一代在追赶着信息时代,老年一代被遗忘在信息时代。老年群体被贴上“信息难民”“新信息穷人”“社会边缘群体”“信息孤岛”等标签。媒介的议程设置使得大众对老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介对老年群体的形象塑造。2006年,“彭宇案件”“许云鹤案件”等一系列老人碰瓷事件开始引发社会热议,在“老年人摔倒该不该扶”争议后接连发生“公交车给不给老年人让座”的负面新闻讨论,一时间关于老年人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变得消极。加之在新媒体平台鲜有老年人发声的机会,公众在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中对老年人的误解不断加深,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也逐渐形成。媒介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大众的老年观,以及老年人自身和整个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老年人对媒介的使用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过度,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别之一在于互动性,即传受关系的差别。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以传者为中心,呈现一对多点覆面的传播模式。老年群体作为传统媒体的忠实受众,长时间养成被动的收视习惯,在面对新媒体截然不同的使用体验时必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2011年,互联网终端的普及和网络提速以及流量资费的降低,更加贴合用户碎片化内容消费需求的短视频迅速获得了包括各大平台、粉丝以及资本等多方的支持与青睐。自2016年抖音APP上线便一跃成为互联网的宠儿,是当下最流行的传播载体。无论是家庭数字反哺还是社会积极老龄化环境的影响,老年群体于近三年开始涉足短视频领域,不仅掀起短视频的老年使用潮,而且一些老年人开账号做UP主,收获大量粉丝。
三、老年群体短视频使用现状
在数字化时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影响力持续延展不断推动“媒介化”生存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诞生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短视频,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建构了全新的影像审美面貌,被认为掀起继文字、图片之后的第三次大众表达革命。[1]根据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2020年3月,我国短视频应用用户达7.73亿,占我国网民整体的85.6%,同年年底,短视频应用用户增长至8.73亿,占我国网民的数量同比也增加了2.7%。[2]2021年上半年,短视频作为基础的用户表达和内容消费形式,贡献了移动互联网的主要时长和流量增量。截至2021年6月,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28.0%,较2020年6月增长5.2%。2020年以来,相关部门大力推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水平及特殊群体的无障碍普及,《2020银发经济洞察报告》显示视频类APP是银发人群最主要的娱乐方式,短视频APP对银发人群的时间占有尤为突出。[3]作为国内短视频头部矩阵代表的抖音,截至2021年6月,短视频日活跃用户突破6亿,视频日搜索量超过4亿,随着5G的发展,5G商用落地有效降低创作者的门槛,短视频用户体验也将进一步优化。抖音及各大短视频平台顺势而为迎来了银发老人这一新生流量群体。
四、短视频平台老年群体“使用潮”的动因分析
(一)较强的操作感和在场感
时代飞速发展,老年人深陷数字鸿沟,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的问题被不断放大。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化社会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参与社会互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改变了老年群体对新媒体望而却步的局面。老年群体在不断地融入媒介生活中,由开始浏览短视频到如今拍视频成为UP主收获百万粉丝,与短视频简单操作、学习难度不高有很大的关系。加之短视频本身短小精湛、内容简明,音频设计加之动态效果给予老年群体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视觉感知下完全沉浸在行动中的情感,社会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将它称作“心流”。[4]在心流的状态中,用户会忽略时间和外部环境,从而达到具有在场感的体验。以抖音APP为例,其设计上的可视性以及易通性,直接呈现在视觉的示能、意符、约束、映射和反馈,而界面布局等一系列可能的操作是可见的,当控制和显示契合自然映射时,界面按键与人们的概念模型相匹配,呈现的明确性实体信息与暗示性实体信息清晰,符合老年群体的行为特征和浏览需求。
(二)老年PGC生产内容贴合需求
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老年领域的内容生产者往往不是老年人,对老年人的需求不能完全准确把握。传统老年节目的专业生产者只能凭借固有认知和过往经验制作他们认为老年群体需要的内容,用心但不一定贴心,兢业但不一定“专业”。在短视频领域,内容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内容的消费者,即“产消者”。“产消者”由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首次提出,指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意指一种生产者即消费者或者消费者即生产者的现象。[5]短视频平台的产消者中“银发网红”占多数,成为老年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中用户名为济公爷爷·游本昌为例,作为一名有近35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是视频创作者中的专业人员,同时也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年人。视频内容基于游本昌爷爷的日常生活趣事,搬演重温济公剧情、寓教于乐传播社会正能量,在不断结合年轻受众话语特征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短视频风格,衍生出新型老年文化。游本昌爷爷出演了很多影视剧角色,积累了许多忠实的粉丝,在抖音平台上粉丝数量有1074.3万,短视频作品获赞1.1亿次,专业“银发网红”在引导老年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向受众传播老年文化,让更多受众了解到老年网红群体。[6]
(三)短视频形式利于传播
短视频具有极强的社交属性,其时长短、内容丰富的特性有助于通过朋友圈或者社交群进行裂变式传播,抖音正在积极拓展与其他类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导流与连接,试图形成完整的传播生态系统,老年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仅次于新闻资讯平台,老年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记录日常所见所闻,分享生活所思所想,爆款视频容易在老年群体中产生并传播。另外,短视频平台采取特定活动增强老年群体的传播力,抖音社区挑战赛就是通过激励的方式鼓勵用户进行内容生产以促进视频传播。#老年生活欢乐多、关爱老年人#、#老人言分别达到121.5亿次、236.6亿次、40.4亿次的播放量,吸引近千万人参与话题,热门话题活动#高能老年团在2020年4月15日—2020年5月15日进行,点赞量第一的视频来自@只穿高跟鞋的汪奶奶,拥有255.4万的点赞、8.5万的留言、5.5万的转发量。汪奶奶不仅深受年轻人的推崇,不少老年人也以此为标榜。
五、老年“使用潮”到银发“网红潮”的发展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对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作用的一种高度概括。人类只有在拥有媒介之后才能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老年人只有融入媒介生活中,才能与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从而适应社会。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又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媒介是老年群体感知社会重要的方式之一,是老年群体与社会联结的中介和桥梁。[7]“银发网红”现象的兴起反映着老年群体主动活跃地进行沟通表达、价值体现以及社会资本积累的愿望。“银发网红”在新媒体技术的赋权下依托互联网实现社会身份的重塑与公众影响力的形成,构建了积极的老年主体性探寻与再青春化的文化生态。“银发网红”是积极老龄化要求下老年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模范,他们克服数字障碍拥抱新媒体,消弭数字鸿沟。老年学中的社会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有和青年人类似的社交活动诉求,短视频平台有助于帮助老年人重视自我价值,重寻社会角色,重塑生活自信。
(一)生成机制:“银发网红”兴起的成因
1.媒介可供性:个体需求的技术赋能
“可供性”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的大胆假设,[8]在《视知觉生态论》中,吉布森称环境客体的功能特征为“可供性”,即“动物与环境的互补性”。在银发网红短视频平台传播实践中的媒介可供性指代平台为老年UP主提供实现自我呈现的基础设施。有学者将媒介可供性分为三个方面: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9]在生产可供性上,短视频平台尽可能降低老年群体技术接入的困难,简洁的界面设置、清晰的流程指示、一键合成的操作、反复观看的制作教程等为老年人接受短视频内容制作提供便利。在社交可供性上,“银发网红”通过短视频平台分享内容,与粉丝及其他UP主互动留言的过程既在社会支持与社会认同中满足了自身的情感需要,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拓展,优质的爆款视频还能实现影响力的延展与内容变现。在移动可供性上,移动智能手机和5G技术为老年群体深入各类场景自我呈现保驾护航,既能实现短视频内容即时传输,也能实现随时“在场”的直播传输,为“银发网红”的形象建构和完整表达提供丰富且自由的空间。
2.社会建构:文化投射与社会关切
全社会不同行业各个领域积极践行和推动着“积极老龄化”的政策号召。积极老龄化可以具体解读成“健康、参与、保障”,理解为确保老年人在老龄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生活质量,能够充分发挥应有的权利参与到自己感兴趣的社会活动中,并得到政策制度以及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邬沧萍教授在1991年最早提出了“老有所为”的概念,指出老年人要自愿参与社会发展。[10]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精神的渗透,银发网红的兴起与当下的社会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体现着特定时代背景下老年群体积极“老有所为”的成果和大众对短视频的内容需求与精神需求。“银发网红”打破了短视频平台同质化严重的瓶颈,老年群体的加入丰富了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生态格局,为受众提供全新的社会视角和审美选择。另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观念触发大众的共情心理,容易对“银发网红”产生强烈的情感寄托,而情感传播是社交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此外,银发网红作为当下理想化老年形象缺失现状的应对方案,成为不少年轻人自身的心理投射。[11]
(二)辩证思考:短视频对老年群体的控制
短视频带给老年群体沉浸式的浏览体验不仅充实了大部分孤独的时光,还填补了情感空缺与需求。这使得近年来老年群体沉迷短视频的社会现象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短视频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对老年群体进行控制。
1.将老年群体异化成信息“劳动力”
不论新闻报道还是身边真实经历,老年群体长时间久坐低头刷短视频,导致头晕眼花、颈椎疼痛的事实比比皆是。在商业化大环境下,资本和经济是引领生产和发展的关键,对大众劳动的强化逐渐成为资本生产的重要一环。[12]短视频平台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辅助下,对老年群体的相关数据全面获取并进行整合加工、深度分析,从而在引导老年群体消费的同时,对银发群体的劳动进行强化与利用。数字时代的劳动不同以往实体经济的劳动形式,而是通过内容的生产、互动、传播。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平台的用户都可以划为数字时代的经济劳动力,但用户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对平台的使用,同时也是平台反向对自身劳动力的榨取,老年群体更是深陷其中。
2.技术驱动下的自我迷失
从技术批判的角度出发,不同的短视频平台都具有算法推荐和内容偏向推送机制,“银发网红”的活动平台、视频内容、审美风格、社会诉求不同,容易因平台的差异造成认知圈层区隔,在算法的控制下变成“单向度的人”,产生“回音室”效应和“信息茧房”现象。这种区隔随时间逐渐扩大,且在认知偏差较大的城乡环境中更为突出。另外,短视频平台优先推荐头部银发网红的视频内容,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粉丝数量较大的银发网红成为平台流量与注意力的主要获得者,对于新进入圈或者具有中部粉丝量的老年UP主并不有利。[13]
3.证实性偏差视域下的真理难辨
“证实性偏差”是指当一个人基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树立一个观念时,在接受有关观念的信息时,产生的一种仅寻找证实该观念的偏向。[14]老年群体成长的时代与如今数字信息化时代相距甚远,在较短的时间里更新更替固有认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持续不断地接受信息并积极解读信息。短视频的传播是老年群体接受外来信息快速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之一,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老年群体一旦接受了短视频内容中的某个观念或者想法,先入为主的心理使得他们认为最先接受的信息是正确的,无法辩证地看待问题。近年来,站在短视频的风口上,不少老年群体成为银发网红,平台上开始出现一些老年人不惜以身体和金钱为代价来换取视频效果的现象。在“证实性偏差”的状态下,与之相悖的意见被选择性忽视,真理被拒之千里之外。[15]
结语
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既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媒体的舞台。构建和谐的老龄化传播生态将成为老龄化社会的重要课题,短视频平台作为老年群体触网的入口之一,在引导社会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道路上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老年人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同时与其他群体是命运共同体,做好老龄化传播,建设顺应老龄化社会要求的传播体系,不仅仅针对现在老去的一代人,而是全社会范围内不同年龄段之间达成共识,共同面对老龄化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与挑战。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技术永远年轻。
参考文献:
[1]李淼.数字“新视界”:移动短视频的社交化生产与融媒传播[ J ].中国编辑,2019(03):82-86.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4/202102/t20210203_71364.htm.
[3]齐宇迪,钱静.传播学视域下“银发网红”热潮现象解读[ J ].新闻前哨,2021(08):93-94.
[4][美]唐纳德·A·诺曼.设计心理学·日常的设计(增订版)[M].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
[5]杨雯博.从受众商品论视角看抖音和用户的关系[ J ].科技传播,2019(8):127-128.
[6]吴晓东,王淮.引爆点理论视域下老年网红潮的成因与问题[ J ].青年记者,2020(03):41-42.
[7]陈会昌.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心理发展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5.
[8][11][13]吴炜华,姜俣.银发网红的网络实践与主题追寻——基于视频社交场景中的“老年UP主”族群研究[ J ].
新闻与写作,2021(03):14-21.
[9]景义新,沈静.新媒体可供性概念的引入与拓展[ J ].当代传播,2019(01):92-95.
[10]钱瑞,能茵.“积极老者”:银发网红的现实图景、生存与发展[ J ].北京文化创意,2021(03):71-79.
[12]宋佳伟.短视频对银发群体的控制研究[ J ].传媒论坛,2021(04):26-28.
[14]江蘇佳.银发群体的信息生产及传播优化[ J ].青年记者,2020(25):9-11.
[15]刘光胜.数字时代的老龄化之殇:迷失在短视频中的“银发群体”[ J ].视听,2021(06):19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