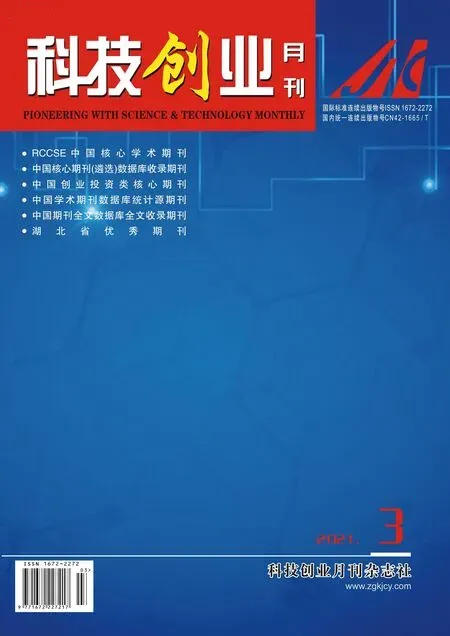小微企业网络协同组织研究综述及展望
——动因、路径、能力及效应视角
黄江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0 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创办一个小微企业不难,但是,要促其真正成长并做大做强,则非常不易。面对小微企业人们不仅会思考其弱势的根源,更想知道如何突破这种弱势。作为经济系统中的一个细胞组织,任何企业既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系统的孤立行动者,也不是完全按社会规范行事的受限者,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规制中追求自身多重目标的积极行动者,即“适度”嵌入者[1]。Powel等[2](1994)指出,与其他社会行为一样, 经济行为并不孤立存在,而是深深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由于很多机会和资源乐于聚焦那些大企业及其战略联盟[3],致使众多中小微型企业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致发展所需资源,此时,一个重要途径便是主动出击走组织网络化协同发展之路以寻求外在突破,借助组织关系网络协同获取互补性资源以支撑企业发展[4]。
组织网络化作为企业的一种常态性环境特征, 其形成、结构、治理与演化变迁、网络协同效应等都会影响企业竞争态势[5]。不过,从网络影响力看,面对相似的网络环境,不同企业通过网络协同实现目标的程度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网络成员运作网络能力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因此,正确认知组织网络化的本质含义及其具体形态,了解网络组织形成的动机、路径、网络效应、网络组织能力及其构成与提升,对于广大中小微型企业以科学合理姿态嵌入、参与或创建网络组织,借此达到网络协同发展并促其成长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价值。
1 网络组织界定及其特征
对企业组织的网络化研究始于20世纪下半叶,当时学术界就出现了各种有关此种组织形式的称谓,比如,组织网络、战略网络、网络组织、联合型组织、联盟式组织、无边界组织等,孙国强(2001)指出,随着企业网络化发展,新的各种网络组织型态,诸如企业集团、虚拟企业、垄断型联盟组织、互惠贸易协定等不断涌现。斯坦福大学教授尝试着将网络组织理论应用到管理领域研究中并于1987 年提出了“Hybrid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混合型组织安排)的概念[6],而Jarillo[7](1988)认为网络组织是企业通过合资经营、战略联盟、供应链等各种产业合作关系建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组织形态,Grandori ( 1993) 把企业间的协同网络定义为一种由一组拥有不同偏好和资源、通过一系列机制来进行协调的企业之间形成的组织形态。
Robbins和Coultar(1996)直接将网络组织定义为一种没有边界的混合型组织或类似于团队协作的形式,而Almer&Richards(1999)更是大声疾呼,在21世纪,企业应该尽可能将其组织结构改变为网络化型态。
国内比较经典的界定则是由李维安与林润辉在2000年提出的概念,即网络组织是一个由活性结点网络联接而成的有机网络系统,该系统介于企业科层组织与市场交易组织之间。
综上所述,所谓协同网络组织,其实就是一个企业为了与其他组织交换资源而建立的各种关系总和[8],与市场组织或者科层组织相比,它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员平等: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微企业,无论是科技型企业还是商业性企业,无论是生产型还是物流型企业,不论是盈利性还是非盈利性企业等,各成员均本着自愿互利共惠的目的走向一起,谁也不能对谁具有行政命令式的指挥与胁迫,它们均具有平等身份,如果在网络组织内部不具有平等权,或者受到一定歧视,那么,成员可以自由选择退出以加入适合自己的新网络组织。
(2)契约维系:科层制组织或者市场交易,都离不开契约这一运转维系的核心纽带,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缺乏了契约精神,这个经济社会都无法有序正常运转,然而,介于科层组织与市场之间的网络型组织,其契约效力亦介于两者之间但又有着自己的活力,它既不同于科层制组织内部严格而带有一定扼杀破坏性的契约,也不同于市场内部比较松散且具有太多投机性因素威胁的契约,建立在网络组织内部的契约,有很强的内部自我约束力,一旦某个网络成员不遵循相应的网络规制行事,或者给其他成员留下缺乏契约精神的不良印象,那么,它极有可能被网络组织所孤立而受限,因为这些加入网络组织的网络成员,一般都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性,它在网络组织内部成员间违背契约的行为将在产业内迅速被传递而使其声誉受损导致其发展受到严重约束,其违约成本相当大,毕竟,如果该成员想从产业系统中跳出来转向其他产业,其难度更大,因此,这种契约的网络化、产业化约束,给予了各成员极强的自我契约维系力,因此,有学者亦称之为自组织(Miles&Snow,1986)。
(3)资源共享:各企业管理者、企业组织加入不同类型网络组织,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突破自身资源约束,实现更多异质性资源互补,以创造更大竞争优势。而作为知识型或者技术型创新企业组织,其加入网络组织的目的,除了充分利用其它成员的资源外,还可以与之协同创造新的知识、技术,形成新的资源与竞争力。作为众多小微企业,其最大瓶颈就是资源受限,包括资本、技术、市场、经验等极为缺乏,加入一定的网络组织,就是为了得到上述各种资源支持。
2 网络组织形成动因
正如所认知的社会现实,企业走组织网络化发展是其成长必经之路[9],因为,任何企业不可能孤立于整个社会关系系统,而是有意、无意的嵌入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网络组织环境之中[10],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更需要通过主动嵌入协同网络组织以进行知识创新、消除知识孤岛、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新知识。至于各个网络组织形成的原因,不同的学者均给出了不同解答,汤普森[11]曾给出了互倚性或互依性的笼统概述, Czinkota(1992)将网络组织的动因归结为8个方面,孙国强[12](2001)则从经济学与管理学两个角度提出了规模经济论、企业协调论等网络组织存在的依据,通过对各种动因解释梳理发现,学者们有关网络组织形成动因基本围绕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2.1 产业发展互补论
阿博特·佩森·厄舍认为,企业是劳动分工日益复杂的结果。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分工是社会财富的来源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依托专业分工,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但是,也将整个社会个体与组织纳入一个更大的相互依存网络系统之中,因为,离开了其他组织与个体支持,专业化分工就无法深入展开,产业无法进一步拓展,社会亦无法深度发展。阿博特·佩森·厄舍认为:经济分工程度的增长需要一定的一体化发展支撑,缺乏了一体化支持,分工将无法展开,最终分工停止,正是借助于一体化力量,让产业发展有了继续的可能。专业化分工不仅促成了企业组织的产生,也决定了这些企业组织只是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必须依赖并促进其他子系统有效完成。因此,与其他经济子系统建立、发展各种关系是其生存的产业需求。各种企业集群式发展,或者以某个龙头企业为核心集聚大量中小企业一起发展抑或产业的上中下游的一体化发展,均是产业整体协同性发展的经济形态,也是企业基于产业网络化发展的根基,离开产业的整体网络化发展与支持,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获得生存与持续发展。
2.2 交易成本推动论
市场交易需要消耗大量成本,为了最大化降低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内部化就成为一种趋势,企业便有了存在的价值,但是,当企业组织成本过大时,一种介于企业组织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又出现了,它的存在具有降低组织与组织之间交易成本功能。正如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指出,不确定性、交易重复的频率和耐用交易专用性投资发生的程度这3个交易特性高低程度决定了市场、企业组织及其两者之间的中间经济组织形态。他将网络组织的形成归功于对较低交易成本的追求,尽管这种超组织型态(Williamson,1995)缺乏正式的层级权威以促成目标实现,但是,建立在信任、承诺以及因为背信弃义所引致的孤立等惩罚,能够有效保证各网络参与者借助该组织平台获取所需资源而节约相当的“市场交易”费用。
2.3 资源补充吸引论
Grant认为,资源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性投入要素,是新建企业创办与成长的基石。而传统资源观认为,资源特别是核心资源能够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石,但这种资源应该属于企业边界之内。
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认知不同的是,人们开始将眼光从内转向外界,因为外部行动者的行为将对资源分配、产业范式演变产生巨大影响[13]。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知识创造、技术创新要求更加强烈,因此,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至少,除了企业内部资源成为其竞争优势来源之外,获取外部资源支持亦是其竞争优势的基石之一,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型企业组织因为知识、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与交互性,更要求其走出去与其他知识技术人员联合开发,更早更多的创造新知识与新技术,以实现多方共赢。在追求外在资源时,应考虑自身需要特点,Sunhee youn[14](2011)认为资源应该是互补的,因此,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应寻求的资源联盟是不同的。只是,当各企业在寻求外部资源时,其获取效果常常受制于自身的资源及社会声望等因素,而一个企业一旦有了外部获取资源的平台、机会与能力,就有可能获得维系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因此,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与发展优势,应该与外部各种组织建立起广泛而牢固的联结甚至联盟。
企业建立参与或者建构网络组织的动因在于获取和利用网络内部关键资源,但是,作为新企业,其获取资源难度非常大,它必须克服资源获取的三大挑战:如何分辨资源、如何获取资源与如何消除资源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建立经常性的、彼此信任度很高的、相互依赖性极强的网络组织,可以在资源识别、不确定性等方面提供极大便利。目前,协同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期企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的最佳创新模式,通过整体协同,可以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增强灵活性,并增加信息交换,促进异质性资源的整合与流动,促进创新要素协同形成创新合力[15]。
3 网络组织的形成路径
3.1 借助于个体社会层面的网络联系
个体的社会关系或者网络扩展程度,是其创建与维系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那些关系网络链接很广泛的人,越倾向于自我创业,并且,其创办的组织发展亦很迅速。Powell和 Giannella[16]指出,个体间通过合作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可以有利于彼此的信息共享,同时,有利于集体发明。特别是那些创业的企业家,其关系联系程度是网络组织形成的核心,因为,他们利用个人关系网络,可以迅速的找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比如资本所有者、核心员工以及客户特别是潜在客户。Hoang&Antonci研究发现,企业家凭借个人关系网络,不仅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融资渠道,还可起到一定的信号传递。因此,那些个体社会关系广泛的企业家或创业者,不仅利用其个人关系创办成功企业,还能够为该企业组织的网络化构建提供便利,甚至可以为企业发展获取关键型网络资源。王庆喜与宝贡敏 ( 2007)指出,小企业主社会关系越广,其获取外部资源的可能性便越大,得到更多资源支持的基础更牢固,竞争优势更强大,成长业绩亦越佳。
3.2 组织层面的网络联系
企业组织作为整个产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细胞,其诞生之初就决定了其对产业系统的横向与纵向依存性。通过横向联接,以企业组织为中心围绕大学、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而展开网络联接;纵向层面,主要围绕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物流商、客户服务提供商展开。如此产业依存性,是不以是否需要网络化联接为前提的,它具有产业内在客观规定性。作为产业系统中的一个组织,必须与其他成员建立起可相互信任的网络组织,以获取相关资源支持。由于各企业组织自身竞争优势与社会声望,其在网络组织中的地位亦存在很大差别,因此,通过网络组织获取相关资源绩效的差异亦很明显,那些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组织,可以获致较高的网络绩效。Powell 等在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内组织间合作网络进行研究时发现,网络的中心地位程度对企业绩效起着相当的决定作用,同时,网络经验及网络多样性对企业绩效亦具有相当影响力,并在企业生命进程方面起着决定性关键作用。不过,网络中心性优势获取,有些是由自身所处位置决定,有些则因企业主管对企业网络的操作经验与操作能力决定,那些在网络组织中有着良好社会关系与声誉的企业主管常常可以获取其他组织的信任与支持,因此,其在网络组织中利用关键外部资源的机会与能力就大大增强。Gulati 和 Westphal(1999)分析企业外部董事间社会网络对企业战略联盟形成的影响时发现,董事之间关系信任程度降低亦会降低战略联盟形成的可能性,反之,增加彼此的信任会大大增加联盟形成的概率。
3.3 基于组织层面的个体主动追求形成的网络联系
个体网络是以个人为联接纽带,通过个体社会活动及其个人地位、声誉与关系往来、情感交互等而建立起来的网络,而组织网络则是以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为结点,为了获取外部信息、资本、科技知识、经验与市场渠道而借助一定的共同投资、合作开发、渠道共建、活动沙龙等途径构建的网络,有些组织网络突破了个体组织界限而走向一体化组织。个体网络与组织网络具有相互促进、相互支持性。一当拥有个体网络的成员加入某些企业组织时,便存在个体网络与组织网络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局面。个体网络特别是企业家个体的社会网络化程度本身便是企业组织网络化的基础,当其个体网络上升为组织网络时,便会借助于网络组织而变得更有价值。目前,网络组织与协作创新关系研究的新趋势是突破个体网络和组织网络界限,将两者的网络结合起来分析其相互作用[17]。
个体网络是组织网络的基础,但是,一旦组织网络建立起来并在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网络中心性时,个体网络组织将会得到更大的提升,这也是许多个体愿意追求大企业组织的动力之一,因为,借助于大企业组织及其所联接的广泛网络组织,其自身的社会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为其以后的事业发展或个体创业打下了网络基础。但是现在存在一种趋向,许多企业组织为了拓展业务,高薪聘请社会联系广泛的员工特别是一些高层管理者。因为个体网络的广泛性与优质性是其拓展组织网络联盟的依托之一,基于这样的认知,企业家关系网络能力吸引了众多学者深入研究(Tsai and Ghoshal,1998;Bhagavatula,2009;贺小刚,2006)。
4 网络能力论
网络能力是个体或组织为了特定目的而构建与拓展外部关系网络及利用其网络关系的能力。网络个体或成员组织利用网络组织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具有的关系谋取能力,当一个网络组织诞生后,如果某个参与者不能通过自身的角色去利用网络组织给予自己以网络支持或者服务,就表明该网络成员的网络能力较低,因此,需要该成员加强网络能力建设,以实现构建或者参与网络组织的目的。在组织网络化发展的同时,对网络能力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升温,其最先被西方学者广泛关注到的一个因素是将之视为网络行为的前因变量。作为较早提出此概念的学者哈克森对之定义为:网络能力不仅表现为企业强化自身在网络中相关角色的能力而且也体现为有效管理与外部关系合作的能力,而正式对网络能力开展系统讨论的是Ritter和Gemünden,他们认为网络能力是一种执行或者胜任网络管理任务的资格或能力。Hagedoorn 等将网络能力上升到战略高度,认为网络能力不仅表现为一般性合作参与能力,也体现出相当的谋划性与智慧性,以力争让自己处于网络的中心或者有利位置。Lambel等指出,企业的网络组织能力是企业运用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帮助其在市场中更好参与竞争的能力。国内学者参照国外学者的网络认知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金发,2001;方刚,2008;朱秀梅等,2010)。不过,Kale 等指出,“现有研究对于网络能力的确切构成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18]。人们对网络能力构成维度的划分存在很大区别。Moller 等认为,网络能力由网络远景能力、网络管理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4种能力构成;Ritter等则将网络能力视为由任务执行与资质条件两个维度构成;Hagedoorn等提出网络能力包含基于中央性与基于效率的两种网络能力,徐金发等基于战略、网络与关系层次三个层面而将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构想、角色管理与关系组合三个能力维度。任胜钢等(2011)则提出了四维度结构的观点,即网络愿景、构建、关系管理与组合管理等。
网络组织的治理既决定着网络绩效,对于各参与者的参与热情也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也面临着极大困境,因为,该组织作为一个非行政组织,依靠业务往来、相互信任与承诺而建立,其关系显得相当自主、松散,一旦当不利于自身利益时,各种投机行为便会发生而致使网络运行瘫痪。因此,需要网络组织的发起者或者领导者根据网络特点制定一定的运行规则,在愿景明确、关系维护、资源共享等方面做出一定的规定,以推进网络组织的运行效率。
5 网络组织效应
亚当·斯密曾经主张,市场经济的运行无须过多人为干预,一切均交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推动,钱德勒认为,科层组织的存在是为了能够通过组织最高权威这只“有形之手”来调节以实现其目的,而兰逊将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协调行为视为“握手”以促进经济有效运行。鲍威尔提出了网络是一种重要的组织间交易模式的观点。威廉姆森从产业创新环境构建角度提出,应当开展跨学科研究,寻求各领域的合作协同,因此,需要发展出一套能够适应21世纪企业发展的新的协同管理模式。我国学者陈守明从网络组织的经济效应出发,指出: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可以有利于企业挖掘自身优势,发挥资源组合效应,以达到“1+1>2”的协同效应[19]。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合作网络大大拓展了各个企业组织获取外部信息、资本、服务等关键资源的机会,也大大扩充了社会资本,减少了相互合作与创新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确保企业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得以有效提升。
创新已经越来越演变为一种网络化协作过程,更多的创新活动越来越离不开网络化协同,尤其是那些基础性、复杂性技术创新以及其市场化成功运作,任何单个力量都无法独自完成,只有通过网络化协同创新,才能实现经验、资源、市场渠道与知识的共享,才能加快信息的交流、技术的传播转移,才能促进新知识的不断创造,企业才可获取竞争新优势,才能真正获得持续成长。
尽管网络协同组织效应很明显,不过,大家一致认为,网络形成只是网络协同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孙国强,2003)。
6 评述及研究展望
网络组织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取得协同效应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必须进行有效的网络组织治理或者说提升网络能力。如果该组织不能为网络成员带来实际价值时,它们将会显得很怠慢而置身于自我封闭之中,最后致使联盟绩效下降,Dhanaraj 和 Parkhe 指出,网络成员企业并不仅仅只是对网络诱因及约束做出反应的被动实体,而是具有主动进行价值搜寻与联合互动的积极主体[20]。不过,人们亦发现,要使网络能力作用发挥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前提:网络关系必须建立在对等基础之上,而现实情况是,由于资源的非对等性依赖、对网络中心位置的抢占以及市场竞争的网络化态势,又决定了各网络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非平等性及网络权力的差异性存在,于是,大家寄希望于核心企业引领网络组织并肩负着整个网络价值共创的使命而非仅仅出于自身资源获取利益最大化[21]。
尽管如此,人们也几乎没有看到有关网络引擎在网络构建与管理中的重要性研究。不知其是否隐藏在网络能力的网络构建中还是人们刻意忽略网络引擎在网络管理中的重要价值。一个好的网络引擎对于网络的组织化、协同化发展至关重要,也许人们认为企业网络引擎就是核心企业,就具有发动网络与组织运行网络的功能,即便如此,现有文献也未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更何况,许多网络组织的发动组建引擎并非是一些所谓的核心企业,而且,不同网络引擎所发起的网络组织究竟有哪些类型,它们是如何运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企业网络化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毕竟,网络化决策与思考是所有企业特别是新创小微企业必须具备的战略之一。
主动开展网络化思维、提升网络能力、主动创建或参与网络并争取到较好的网络位置以获取网络协同效应是一个企业组织成功的保障,而要想确保这些组织的网络化发展需求,必须保障网络的有效运行,选择或者培育一个强有力的网络引擎是至为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