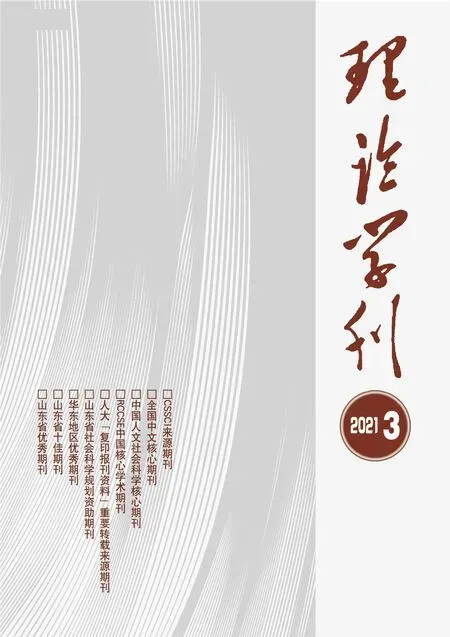从屈野河“侵耕”事件看宋夏边疆危机的管控
孙方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100732)
河川对于人类的军事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包括补给兵马维生所必需的饮用水、为军事调度和物资补给提供天然的交通线路,以及为河川沿岸地区的军事屯戍提供农业用水等。在宋夏战争中,河川的军事价值同样至关重要。韩茂莉先生曾指出,在宋夏沿边地区有延夏、环庆、镇原以及秦渭四条交通要道,宋军在沿线屯戍设防(1)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7页。。而这些军事要道的形成往往依托于河川,如延夏道之于无定河、环庆道之于马岭水、镇原道之于泾水和葫芦河、秦渭道之于渭水和洮河。程龙先生则进一步指出:“黄土高原地区地形破碎,交通道路多沿河谷,这使宋军不得不沿河布防,将大量兵力集结在河谷地带,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地区往往形成一个安抚使路辖区以便建立纵深的防御体系。”(2)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笔者亦曾对宋军在西北战区的饮用水补给及其水面交通情况著文作过专题讨论(3)详见孙方圆:《宋夏战争中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试论宋夏战争中的水面交通》,《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44—356页。。
地处北宋麟府路的屈野河(即今陕西神木境内的窟野河),就是在宋夏关系中产生过特殊影响的一条河川。宋夏双方围绕屈野河的纠纷已然超出了“战时”与“平时”的阶段划分,边民越界耕作、边兵武装冲突以及边官反复交涉的情况时有出现,而史书中则往往以“侵耕”指代这场发生于北宋庆历至嘉祐年间的边界纠纷事件。目前学界对于宋夏划界问题的讨论,多是从边界沿革或双方的边防政策(4)参见[日]前田正名:《陕西横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0—11世纪鄂尔多斯南缘白于山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杨蕤、尹燕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177页;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0—51、121—125页;陈旭:《宋夏沿边的侵耕问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杨蕤:《宋夏疆界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黄纯艳:《宋代的疆界形态与疆界意识》,《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等等。、特别是军事屯戍的组织实施等问题入手(5)参见尹崇浩:《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赵振绩:《宋代屯田与边防重要性》,《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版;魏天安:《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考实》,《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韩茂莉:《宋代陕西沿边地带的兵屯与土地开垦》,《西北史地》1993年第3期;史继刚:《宋代屯田、营田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刁培俊、贾铁成:《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等。,在对具体事件开展专题研讨方面则尚有发掘空间。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宋夏屈野河侵耕纠纷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双方的对策考量展开讨论,不当之处,伏望方家指正。
一、争端出现的背景
屈野河的主体河段位于北宋麟府路境内。通过相关研究可知,麟府路在今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的过渡地带,北部为风沙草滩区,有固定、半固定的沙丘分布;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表沟谷纵横。在这一区域中分布着包括屈野河在内的数条河谷,多呈西北—东南流向,河流沿岸冲积阶地发育良好,是理想的耕地。黄河沿岸的峡谷丘陵土薄岩露、谷深坡陡,十分有利于军事布防(6)参见杨蕤、乔国平:《宋夏沿边地区的植被与生态》,《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自唐代以来,麟府路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以府州折氏、麟州杨氏和丰州王氏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实力不容小觑。北宋建立后,麟府路的早期地方机构建置今已不详,有研究指出,至道二年(996)“卫州团练使河阳李重贵实为麟府路浊轮寨都部署”(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的表述,是“现存文献中关于‘麟府路’的最早记载”,其后至迟在宋仁宗时期,北宋正式设立了“麟府路军马司”,是为“麟府路的最高权力机构”(8)参见李昌宪:《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2—127页。。起初,麟府路自北向南辖有丰、府、麟三州,后来丰州于庆历元年(1041)为西夏所占,至嘉祐六年(1061)方又择址复建。
宋、辽、夏鼎峙时期,麟府路更是地处三方交界之地,“黄河带其南,长城绕其北,地据上游,势若建瓴,实秦晋之咽喉,关陕之险要”(9)[清]沈青崖等:《陕西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92页。。对于西夏而言,夺取麟府路“不仅能彻底消除西夏在陕北作战一直处于鄜延和麟、府腹背受敌的艰难境地”,还能掌握“以河为险,进退自如”(10)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的战略优势;对于北宋而言,麟府路“西南接银州,西北接夏州”(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7页。,且“麟、府辅车相依,而为河东之蔽。无麟州,则府州孤危。国家备河东,重戍正当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贼后,则大河以东孰可守者?故麟、府之于并、代,犹手臂之捍头目”(12)[北宋]张方平:《乐全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0页。。麟府路对于北宋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性由是可见一斑。
宋夏在麟府路境内的交锋多集中于南部,其沟壑纵横的地貌特征导致双方的军事调度往往需要依托河谷川途方能高效实施,于是屈野河的军事价值愈加凸显。屈野河系黄河支流,上游系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乌兰木伦河与悖牛川,两河在今陕西省神木县汇流后即为屈野河(窟野河)。史书记载:“窟野河路自麟州过河,西入盐州约七百里,南至银州约三百里,控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州,以西则地势平易,可行大军。”(13)[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7页。加之“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14)《宋史·司马光传》。,为当地军民屯戍提供了良好的水土条件,以致有学者认为,“麟州的设置是为了控制窟野河谷,府州则是为了控制黄河西岸”(15)⑩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04—105页。。对于宋夏双方而言,麟府路是河东路的外围屏障,而屈野河则是贯穿麟府路的战略要道。
雍熙元年(984),李继迁率部出走地斤泽,武装反宋。北宋发兵征讨。双方交兵不久,宋将李继隆、王侁等兵出银州,“破悉利诸族,追奔数十里,斩三千余级,俘蕃汉老幼千余”;继而挺进开光谷杏子坪,“降银三族首领折八军等三千余众”;又在浊轮川东、兔头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斩首五十九级,俘获数千计”;“吴移、越移四族来降,惟岌伽罗腻十四族怙其众不下”,李继隆“夷其帐千余,俘斩七千余级”,暂时制伏了横山各地追随李继迁的部族(16)《宋史·李处耘传》。。开光谷即《水经注》中的梁水所在(17)[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84页。。该河位于今神木县南,“出长城内,东入屈野河”(18)[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补》,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2页。;浊轮川即今悖牛川之古称,据此推测兔头川或亦属屈野河水系。至道二年(996),宋太宗为李继迁袭扰不断、灵州战事一再告急而勃然大怒,遂命五路大军全线出击,试图一举剿灭李继迁所部。其中,西京作坊使张守恩率军兵发麟州,据《武经总要》所载,其行军路线应当就是屈野河谷(19)[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7、515、517页。。由此可见,屈野河的军事价值在宋夏交兵之初便已显现无遗了。
此后,西夏对北宋麟府路的威胁日益增长。宝元二年(1039)闰十二月,直史馆苏绅建言:“今边兵止备陕西,恐贼出不意,窥视河东,即麟、府不可不虑,宜稍移兵备之”(20)[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庆历元年(1041)九月,宋廷令知并州杨偕“除并州合驻大军外,麟、府州比旧增屯,余即分布黄河东岸诸州御备,交相应援”(21)⑨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九月”。。同年十月,宋廷“禁火山、保德军缘黄河私置渡船”(22)[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而西夏虽成功占领丰州,但府州以“城险且坚,东南各有水门,崖壁峭绝,下临大河”(23)⑨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庆历元年九月”。而始终为宋军固守。史念海先生曾进行过实地考察,指出:“府谷县建于河边山上,巨石嶙峋,势甚险陡。黄河从东北流来,直冲城东南角下,顺山脚流向西南”,北宋时南门在城东南,其外另筑有水门以保护汲路,且“水门建在城东南,就是为了防止偷袭。因为由城东往南陡岸壁立,要绕过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西南城外半崖上可以勉强通过,城上守兵是能够控制得住的”(24)⑩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04—105页。。至于麟州,西夏试图通过“往来邀夺馈运”的战法困死宋军,宋将张亢、张岊等则寻机反攻,先“大败贼于龙门川”(25)《宋史·张岊传》。,再战柏子寨,又筑建宁寨;西夏军“数出争,遂战于兔毛川”,不意遭到被“斩首二千余级”的败绩。宋军得以进筑“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由是“麟州路始通”(26)[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龙门川系府州之北“入府州路”(27)[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7、515、517页。,兔毛川是西夏入侵麟州的“贼路”(28)[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7、515、517页。,宋军能够在麟府路稳住局面,同样得益于对上述河谷川途的有效掌控。
此后由于战事胶着,宋夏双方出于各自的考量,最终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实现议和停战。鉴于麟州不利于防守,宋廷一直有人主张迁移麟州治所、退守黄河东岸。知并州杨偕便曾提议:“建新麟州于岚州合河津黄河东岸裴家山,……河西对岸又有白塔地,亦可建一寨,以屯轻兵。又河西俱是麟州地界,且不失故土,见利则进,否则固守之。”(29)[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庆历和议”达成后,类似的论点曾再度出现。尽管杨偕前议看似能掌握一种“进退由我”的主动,但根据日后北宋与西夏在屈野河纠纷中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纸上谈兵极易造成严重的政治被动与军事风险。幸而有识之士对此极力反对,其中尤以欧阳修所言最有见地,其云:
窃详前后臣僚起请,其说有四,或欲废为寨,或欲移近河,或欲抽兵马以减省馈运,或欲添城堡以招集蕃汉。然废为寨而不能减兵,则不可,苟能减兵而省费,则何害为州!且其城壁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与府州各才百余里,若徙之近河,不过移得五七十里,而弃易守难攻之天险。以此而言,移废二说,未见其可。……今二州五寨,虽云空守无人之境,然贼亦未敢据吾地,是尚能斥贼于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移,则五寨势亦难存。兀尔府州,偏僻孤垒,而自守不暇,是贼可以入据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夹河对岸,为其巢穴也。今贼在数百里外,沿河尚费于防秋,若使夹岸相望,则泛舟践冰,终岁常忧寇至,沿河内郡尽为边戍。(30)[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
麟州及诸要塞乃“易守难攻之天险”,若轻易予以移废,府州便会真正成为一座“偏僻孤垒”从而“自守不暇”,西夏届时即可“入据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夹河对岸,为其巢穴”,一旦如此,恐怕就要“终岁常忧寇至,沿河内郡尽为边戍”。质言之,如果宋军不能在黄河西岸保持有效的军事实力而退守黄河东岸,就相当于放弃了黄河西岸的广袤缓冲地带,而让渡给西夏自由行动、随机渡河的战略空间。有鉴于此,牢牢掌握黄河西岸的前沿防线,便成为北宋日后保障麟府路乃至整个河东路安全稳定的关键所在,而纵贯麟府、可耕可战的屈野河正是实现这一军事部署的锁钥之地。
然而,由于宋夏两军在麟府路长期交战,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屡有变迁、模糊不定;“庆历和议”虽然明确了宋夏双方的政治关系,但对每一具体区段的边界划定却又难以周全;加之辽朝雄踞北方而宋夏双方又有各自的利害考量,因此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屈野河划界的遗留问题就变得日益复杂起来。
二、事态发展的进程
在李继迁起兵之前,麟州地界“西至俄枝、盘堆乃宁西峰,距屈野河皆百余里;西南至双烽桥、店子平、弥勒、长平、盐院等,距屈野河皆七十余里”,可知当时的屈野河两岸之地都是完全处于宋朝管辖之下的。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率部“陷浊轮、军马等寨”(31)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7页。。浊轮寨本系北宋边防重镇,“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且“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帐”(32)[北宋]曾公亮、丁度等:《武经总要·前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18页。。浊轮寨易手后,当地蕃部首领勒厥麻等族众被迫“相率越河内属”(3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大中祥符二年(1009),北宋“始置横阳、神堂、银城三寨”,而此时这三座要塞的位置已是“皆在屈野河东”了(34)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7页。。尽管西夏通过军事手段将北宋的沿边堡寨逼退至屈野河东岸,但并未趁势驻军或移民以确立对屈野河西岸的实际控制权。不过,彼时宋夏在屈野河的局面,已经与前述杨偕在讨论麟州州治与黄河关系时的构想相似,即北宋具有实际力量的军事要塞在河川东岸,而河川西岸则是政治意义上的“领土”。对于北宋而言,危机的伏笔已经由此埋下。
在此之后,由于北宋官员的利益纷争以及当地官府的处置失当,西夏日益注意到屈野河西岸的“有机可乘”,史称:
天圣初,州官相与讼河西职田,久不决,转运司乃奏屈野河西田并为禁地,官私不得耕种。自是民有窃耕者,敌辄夺其牛,曰:“汝州官不敢耕,汝何为至此!”由是河西遂为闲田,民犹岁输税不得免,谓之“草头税”。自此敌稍耕境上,然亦未敢深入也。(35)②④⑥⑩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
据上引史料,宋仁宗天圣年间,为消弭地方官员的利益纷争,宋廷将屈野河西岸有争议的田地划为“禁地”,而西夏正是利用北宋朝廷的这道禁令驱赶试图在此“窃耕”的北宋边民。“窃耕”禁地本是违法之举,北宋的边民对外无力反抗、对内无理申诉,最后只有退走,如此一来,北宋在屈野河西岸的“事实存在”愈发松动。但即便如此,西夏仍未公开进占,而只是“稍耕境上”、不断蚕食。
此后直至元昊自立、宋夏交兵,西夏“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于道光、洪崖之间,盗种寨旁之田”(36)②④⑥⑩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道光即道光谷,在银城寨南60里处;洪崖即洪崖坞,在银城寨南40里处(37)⑤⑧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22、7267、7268页。。鉴于彼时西夏在元昊治下占据着军事优势,其继续渗透屈野河沿岸地区不足为奇。不过,直至“庆历和议”达成,西夏在该地区的内侵仍不过“十余里”。对此,宋廷以和议甫成不愿节外生枝,遂指示知麟州张继勋:“若西人来,即且答以誓诏。惟延州、保安军以人户所居中间为定,余路则界至并如旧。未定之处,若西人固欲分立,则详其所指之处,或不越旧境,差官与之立牌堠以为界。”但是究竟当以何处为旧有边界?张继勋提出:“用咸平五年以前之境,则太远难守,请以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为定”,否则,如若“以河西为禁地,则益恣其贪心,进逼河西之地,耕凿畜牧,或兴置寨栅,与州城相距,非便”。宋廷表示同意,不过同时又明令其“不得明行检踏以致生事”(38)②④⑥⑩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所谓“大中祥符二年所立之境”虽难以全线考实,但屈野河西岸“禁地”归属北宋当毋庸置疑。
虽然张继勋等人通过实地考察、寻访故老等方式,提出旧有边界“无以复易”,但是西夏派出的交涉官员却主张“马足所践,即为我土”。这种立足于“实际占有”而提出的“既定事实”的领土主张,自然难以得到北宋认可。张继勋等北宋官员以禁绝宁星和市相威胁,才迫使对方同意包括屈野河在内的麟府路边界“一切如旧”(39)⑤⑧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22、7267、7268页。。然而此后不久,张继勋竟遭革职,史载“后知州事者惩其多事取败,各务自守,以矫前失”(40)②④⑥⑩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加之范仲淹亦曾将张继勋列为“所用主兵官员使臣”之中“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之人(41)[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因此或可推知张继勋的被革职与其积极整饬边防、修筑要塞有关,毕竟此类举措容易给西夏以口实,并且有也有悖于宋廷当时奉行的安边政策。
在此阶段,北宋对屈野河防务的态度更趋保守,遇有纠纷发生,宋廷多以严饬禁令、惩处相关人员来平息事态。如麟州都巡检王吉“尝过河西巡逻,州司辄移文劾之,自是无敢过者”(42)⑤⑧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22、7267、7268页。;又如麟州报“西界人马至屈野河西,寻令指使、殿侍魏智等引兵约回,智遇伏,为西人所执”,宋廷下诏“河东经略司累戒逐路务遵誓诏,今西人本无斗意,而以兵迫逐为边生事,其边吏并劾罪以闻”(4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7,“庆历五年十二月”。。加之沿边堡寨官员多以“民不过河”“敌无踰境”而“岁满得迁官”,因此更是“禁之尤急”。起初,西夏尚不敢轻举妄动,但“数岁之后,习知边吏所为,乃放意侵耕”,“州西犹距屈野河二十余里,自银城以南至神木堡,或十里,或五七里以外,皆为敌田”,及至后来,竟发展到西夏“明指屈野河中央为界,或白昼逐人,或夜过州东,剽窃赀畜,见逻者则逸去”。北宋巡边部队即便接到警报,也会慑于朝廷禁令而不敢轻易追击,即所谓“既渡水,人不敢追也”(44)②④⑥⑩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这些记载似乎表明,此时的屈野河俨然已经成为宋夏之间的实际“界河”了。
这种对北宋不利的局势,到麟府路管勾军马司贾逵巡边时又出现了变化。贾逵“见所侵田,以责主者”,“知州王亮惧,始令边吏白其事。经略司遂奏土人殿直张世安、贾恩为都同巡检,以经制之”(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8页。。然而西夏认为己方已在此长期耕作,特别是当地田产所得彼时已归名曰没藏讹庞的权臣所有,即所谓“田腴利厚,多入讹庞,岁东侵不已”(46)《宋史·外国传一·夏国上》。,故而其侵占之势愈发难以遏制。史载西夏见宋军来,“迫之则斗战,缓之则不肯去”,对此,北宋的策略是“屡列旧境檄之,使归所侵田”。面对北宋的一再抗议,西夏一度派出梁太后的亲信部细皆移前来交涉处置,经其勘验,“所耕皆汉土”,故而欲令讹庞归还;然而恰在此时,“皆移作乱诛而国母死”,权力得到巩固的没藏讹庞不仅不再提及归还侵耕之地,反而大举增兵数万,“又自麟、延以北发民耕牛,计欲画耕屈野河西之田”。只因西夏政权内部出现不同意见,没藏讹庞才作有限退让,“银城以南侵耕者犹自若也”,“盖以其地外则蹊径险狭,秋多陌丛生,汉兵难入;内则平壤肥沃,宜粟麦,故虏不忍弃也”(4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68页。。由是观之,尽管北宋持续对西夏展开交涉,但西夏最终还是在屈野河沿岸地区保留了至少一处可进可退的“桥头堡”。
在此阶段,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在巡边时,接受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的建议,提出了“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之策(48)《宋史·司马光传》。,同时亦希望借此达到“敌来耕则驱之,已种则蹂践之,敌盛则入堡以避”的战术效果,重新确立宋军对屈野河西岸的控制。于是在嘉祐二年(1057),并代钤辖郭恩等将领以“巡边”为名率部“循屈野河北而行”。但是由于与其同行的内侍黄道元昧于兵法,一再对郭恩用激将之法予以催促,造成宋军的冒险盲动,最终落入了西夏预设的埋伏而惨遭溃败。郭恩被俘自杀,“又死者使臣五人、军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还者百余人,亡失器甲万七千八百九十九,马二百八十”(49)[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此役的失败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北宋在屈野河纠纷中的被动地位,史称“自郭恩败,敌益侵耕河西,无所惮”(50)⑥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3,“嘉祐六年六月”。。
尽管西夏在屈野河占据了军事上的一定优势,但宋夏在“庆历和议”签订后整体关系趋向平稳,且北宋整饬边备的努力愈见成效,双方大动兵戈的条件并不充分,加之受到宋、辽、夏三方关系以及西夏政局变化的影响,至嘉祐六年(1061)六月,宋夏双方在经过数轮交涉之后,终于达成了屈野河划界的协议。史载:
其府州自桦泉骨堆、埋浪庄、蛇尾掊、横阳河东西一带,筑堠九;自蛇尾旁顺横阳河东岸西界步军照望铺间,筑堠十二;自横阳河西以南直埋井烽,筑堠六;自埋井烽西南直麟州界俄枝军营,筑堠三;自俄枝军营南至大横水、染枝谷、伺堠烽、赤犍谷、掌野狸坞西界步军照望铺相望,筑堠十二。
其榆平岭、清水谷头有西界奢俄寨二,从北讹屯山成寨一,次南麻也乞寨一,各距榆平岭四里;其大和拍攒有西界奢俄寨四,从北讹庞遇胜寨一,次南吾移越布寨一,次南麻也吃多讹寨一,次南麻也遇崖寨一,各距大和拍攒五里;其红崖坞有西界奢讹寨三:从北冈越崖寨一,距红崖坞二里;次南讹也成布寨二,各距红崖坞一里;其道光都隔有西界奢俄寨二,并系讹也成布寨,在道光都隔上。其十一寨,并存之如故。寨东西四里各有西界步军照望铺,亦筑堠十二。(51)⑥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3,“嘉祐六年六月”。
宋夏在协议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及其对策考量,下文将作具体讨论。不过由此不难看出,宋夏双方在这一协中议除了详细划定了边界地标而外,还对各自的边防管理措施作了明确约定:“自今西界人户,毋得过所筑堠东耕种”,“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丰州外汉寨及府州界蕃户旧奢俄寨,并复修完,府州沿边旧奢俄寨三十三,更不创修”;“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许两界人就近樵牧”,但不得“插立稍圈、起盖庵屋”,否则,“违者并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此外还约定,双方的巡边部队“各毋得带衣甲器械过三十人骑”(52)[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3,“嘉祐六年六月”。。至此,宋夏双方就屈野河的划界与管控达成了正式协议,其后虽然偶有摩擦出现,但就性质与规模而言,皆已不能与此前的冲突等量齐观了。
三、双方对策的分析
在大致梳理了宋夏屈野河纠纷的发生背景及其事态进程后,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双方常常针锋相对,但彼此却也都保持着相对克制的态度,避免事态的激化甚至失控。宋夏之间的这种不约而同,可以说是当时的情势使然。
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之间边民、边兵越界之类的事件并不鲜见,其中宋辽双方边民在界河捕鱼而产生边界摩擦的事件,便可与宋夏屈野河纠纷进行比较。宋真宗时,宋廷令“禁缘边河南州军民于界河捕鱼”,这其实是对此前“契丹民有渔于界河者,契丹即按其罪”的对应性回应(5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八月”。;至宋仁宗时,辽朝提出“雄州不当禁渔界河”,北宋则以“界河之禁,起于大国统和年,今文移尚存”相反驳,最终“辽人词塞”(54)《宋史·张耆传》。。宋神宗时,“北人渔于界河”,宋廷“虑彼国不知边臣不顾欢好,信纵小民,渐开边隙”,遂“诏同天节送伴使晁端彦等谕北使以朝廷务敦信誓,未尝先起事端,请闻之本朝,严加约束”(55)[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总之,在双方的及时沟通与管控下,宋辽之间的数次界河摩擦并未导致事态升级的情况出现。毕竟自“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南北朝”的格局事实上已经确立,直至宋金联合攻辽之前,宋辽之间再无大规模战事发生。与此同时,在各类各级交往中,宋辽皆注重礼仪上的对等,借以巩固、规范双方的关系(56)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29页;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2—85页。。在这种政治框架下,在处理边民界河捕鱼之类的问题时,不论是“禁渔界河”的举措还是“文移尚存”的举证,宋辽均能秉承一种对等的姿态,通过既有途径与程序和平解决问题。当然,这种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转,是以宋辽国家实力的旗鼓相当为前提和基础的。
反观宋夏之间,双方虽然达成了和议,但综合国力上的差距注定二者很难形成真正的战略均势,宋使张宗道对宋夏两国关系所作的“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5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六月”。的比喻是恰如其分的。不仅如此,“庆历和议”又进一步明确了西夏在政治名分上对北宋的从属地位,诚如黄纯艳先生所指出的:在宋夏交往的过程中,华夷观念和君臣名分是“得到双方认同和遵守的”,即便是在顽强对抗宋军的同时,西夏也“并未质疑和挑战宋朝站在‘中华’地位上所使用的话语”(58)黄纯艳:《宋代东亚秩序与海上丝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因此,与宋辽关系相比,宋夏关系更有其微妙的一面。以屈野河纠纷中双方的表现观之,天圣年间,西夏是利用北宋“屈野河西田并为禁地,官私不得耕种”的禁令驱赶北宋的边民,其兵马也仅仅是“稍耕境上”;至和议达成,西夏的理由又变成了“马足所践,即为我土”。尽管表面上看是西夏趋向强硬,但其领土主张先是乘隙于北宋禁令的有机可乘,后是强词夺理地制造既成事实,这种“投机主义”比之于宋辽间解决类似问题时的“对等交涉”,从“名正言顺”的角度而言高低立判。由是可见,“庆历和议”对宋夏主从名分的界定,在屈野河纠纷中是能够对西夏形成切实钳制的。
当然,在现实操作中突破一纸和约的限制绝非难事,特别是对西夏而言,其高层自元昊晚年便屡有异动、政争不断,通过军事冒险树立权威、转移矛盾,是参与政治角力的各方皆会考虑甚至乐于采用的手段。在屈野河纠纷中,不论是没藏讹庞下令增兵布防还是对郭恩所部设伏,均是西夏用军事手段巩固既有蚕食成果的事例。对此,北宋在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应该说是比较软弱的。由于宋军在战争之初屡遭败绩,至韩琦、范仲淹主持西北军政,也不过是勉强抵御西夏攻势,故而在屈野河纠纷中,进取乏力的宋军只好继续“扬长避短”。史载,宋廷曾令麟、府边吏巡防时“毋得蹂践田苗”,遇西夏内侵则“相视远近驱逐之”(59)[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3,“嘉祐元年七月”。。虽是声言“驱逐”,但“相视远近”实际上却又预留了避免冲突加剧的弹性空间。知并州郑戬曾提议:“麟、府二州有并塞闲田,可招弓箭手一二万人,计口给田,以为疆场之防。”(60)[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庆历六年九月”。其范围应包括屈野河,而招致弓箭手则是宋军固边的常用办法。此外,西夏常常于“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宋军则“敛兵河东毋与战”,至“敌屯月余,食尽而去者屡矣”(61)[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一个“屡”字,透露出宋军在面对西夏军事挑衅时的保守倾向。
不过,随着宋夏交涉的持续展开,北宋在政治上日益显露出优势。首先,北宋朝廷和历次派出交涉的官员从未承认过西夏在屈野河沿岸地区行动的正当性,即便是在面临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北宋也没有松动立场。至于宋廷惩处某些越界官员,其罪名多是“生事”,这种为维护边界和平而实施的内政举措,不仅能避免给西夏留下寻衅的口实,更令北宋在政治上重掌主动。其次,北宋对辽夏的分化对于解决此次纠纷至关重要。辽夏素来互为犄角,屈野河又地处宋、辽、夏三方毗邻之地,就原本的地区力量对比来说,局面应当是有利于西夏的。然而就在宋夏屈野河纠纷发酵之际,辽夏关系也意外地趋向紧张:随着元昊与辽兴平公主的联姻出现波折,双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此外,在庆历二年(1042)时,辽借北宋对西夏用兵失利之际发难,遣使北宋议“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62)《辽史·兴宗本纪二》。,企图坐享渔利;北宋经由富弼出使谈判,虽然付出了每年增加银、绢各十万的代价,却也促成了辽的转向,即诱使其向西夏施压停战。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6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而感遭到背叛,辽兴宗则愤然于“契丹之威不能使西羌屈服”(6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最终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重熙十八年(1049)两度大举攻夏,双方关系一度破裂。尽管西夏在战场上多有斩获,但身处宋辽两大国的双重压力之下,西夏势必难以长期招架;鉴于对辽关系一时难以恢复,西夏不得不继续缓和与宋的关系(65)参见杨浣:《辽夏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14页。。最后,西夏高层的政局变化也为屈野河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空间。此前北宋有官员提出:“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本没藏讹庞之谋,若非禁绝市易,窃恐内侵不已。请权停陕西缘边和市,使其国归罪讹庞,则年岁间可与定议。”宋廷遂禁绝“陕西四路私与西人贸易者”(66)[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这一政策给西夏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北宋嘉祐六年(1061)四月,谅祚设计剪除了没藏讹庞的势力并开始亲政,同年六月便与北宋就屈野河问题达成协议,其在政治上的缓和姿态与经济上的利益诉求显而易见。然而,宋廷并未因为协议的签订而同步放开互市,谅祚遂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袭扰环庆路,旋为宋军所败,最后只好以“边吏擅兴兵,行且诛之”为辞收场(6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治平三年九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次“西夏的军事动机与反经济封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68)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但其并未在此前双方矛盾聚焦的屈野河一线发难,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谅祚无意破坏既成协定,以免在后续的交涉中再度陷入被动。
西夏统治集团面对恶化了的对辽关系以及“庆历和议”框架下的对宋关系,在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展开务实的政治谈判,继而与北宋达成正式的划界协议,这应当是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最终凭借嘉祐六年(1061)的协议,北宋“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西夏实际上获得了屈野河西岸的控制权,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意图。对北宋来说,继续与西夏在屈野河纠缠不断不仅容易诱发军事冲突,更有安边固疆的其他潜在风险。如浊轮寨失守后,蕃部首领勒厥麻即率众内附,但北宋边臣言其“常往来贼中,恐复叛去”。鉴于边地蕃部反复无常的情况并不鲜见,宋廷遂将其“徙置宪州楼烦县,遣使赐金帛慰抚,俟贼宁谧即放还”(69)[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而前述辽朝的“趁火打劫”,更激发了北宋君臣对“西北二边”联合发难的警惕之心。因此,通过政治谈判遏制西夏在边界未定地区的侵蚀,对北宋而言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权宜之举,况且待到时机成熟之后,北宋便可运用综合国力上的优势而对西夏实施战略反攻。
随着宋神宗时代的到来,北宋开始更加积极地酝酿对西夏发动攻势,史载,“边事方起,河东岚、石、隰、麟、府州最是缓急应援陕西之地”(70)[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例如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诏河东经略司:“已严戒知麟州王庆民,如西贼犯境,即令诸城寨相度有险可恃者,专为清野自守之计;如贼入界无所得空回,虽不获一人一骑,亦当赏功等事。”同时叮嘱:“如蕃汉老小愿入河里安泊者,速具船械济渡,即不得令强壮一例入城,有误防守。”(7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273页。即以黄河为限,撤回西岸消耗军需而无补于战守的老幼,但能参战者必须坚守阵地,以免黄河西岸落入敌手。又如元丰五年(1082)四月,西夏以北宋在第二次灵州之战中兵败而侵入鄜延路,麟府路和鄜延路的宋军相互配合、声东击西,最后成功反击并进筑葭芦寨。宋廷以其与毗邻的吴堡寨“合用兵马并战守器具、粮草等,并令河东路经略、转运司管认”,又“缘隔大河,虑西贼侵犯”而令“鄜延路经略司以兵马照管应援”(72)[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葭芦寨地处麟府路与鄜延路之间,驻扎在此的西夏军曾长期对宋军构成威胁,此役的成功一举拔除了西夏在葭芦川—屈野河—黄河这一区域中打入的这枚“钢楔”。时至元丰七年(1084)十月,宋廷又令“葭芦、吴堡两寨各置水军一指挥,以百人为额”(7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元丰七年十月”。,借以加强水面巡视,防止西夏渗透。再如元丰七年(1084)三月,知太原府吕惠卿提出建议:“麟、府、丰三州两不耕地,可以时出兵开垦,不惟岁入可助边计,兼可诱致西贼蹂践田苗,设伏掩击,比于深入不测之敌境,劳逸不同。”(7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所谓“两不耕地”,应当包括屈野河沿岸地区;“诱致西贼蹂践田苗,设伏掩击”,更是意在善用“地利”。在上述军事部署中,麟府路的地位无需赘言,而屈野河的安全稳定对于宋军的调度乃至反攻无疑更具重要的军事价值。
四、余 论
鉴于屈野河在沿河设防、屯垦戍边、调度军需等诸多层面具有不容忽视的军事价值,宋夏在此展开对峙、争夺可以说在情理之中。然而由于双方在天圣至庆历初的战争中皆未能确立对屈野河沿岸地区的控制权,随着“庆历和议”的签订,如何在该地区完成划界便成了一个现实而微妙的遗留问题。经由笔者的梳理不难发现,在“庆历和议”构建的关系框架下,宋夏双方都受到了相应的约束,特别是西夏,它尽管一再通过蚕食方式侵入屈野河沿岸地区,并时常展现出强硬姿态,但与此同时又始终注意不挑起直接的大规模冲突,即避免承担破坏和议的政治责任和现实风险;而北宋则充分利用“庆历和议”对宋夏主从关系的约定,一方面在军事上采取守势、避免因战败而陷入更大的被动,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坚守立场、持续交涉,使西夏通过制造既成事实以扩大领地的策略大打折扣。与此同时,辽夏关系的恶化也令西夏前所未有地面临着来自宋辽两个大国的军事威胁,维系“庆历和议”框架下宋夏关系的和平稳定,对于彼时的西夏而言更是理性的选择。此后随着谅祚成功剪除没藏讹庞势力而开始亲政,西夏向北宋政治上示好、经济上求利的愿望更加迫切。最终,宋夏经过一系列磋商,缔结了屈野河划界协议,西夏获得了屈野河西岸的实际控制权,而北宋则赢得了固边守疆、整军备战的时间和空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屈野河侵耕纠纷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为北宋在日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5记载。绍圣四年(1097)四月,鄜延路经略司称,西夏兵民“遇夜直至大理河以来耕种,昼则却归贼界,公然往返,全无畏惮”,该司以为这是因为“本路军声不振,自来不曾敢出塞讨击,致贼界敢尔轻视”,遂请求与环庆路相互声援、择机出战。鄜延路是宋夏交兵的主战区之一,其境内除南北走向的黄河与洛水之外,自北向南分布着包括大理河在内的数条河川,这些河川基本呈西北—东南流向而汇入黄河,客观上为西夏军队的机动作战提供了极大便利,鄜延路由是一度成为西夏入侵北宋的首选,而北宋对于该地区的防务更是从不敢掉以轻心。对于此次鄜延路的奏报,宋廷的反应是“诏令熙河、泾原、河东经略司,……若贼界对境有屯聚贼马及耕种住坐人户,知得远近多寡次第,委是有利可乘,即不限时月,相度出兵掩击”。实际上,经由宋神宗以降的积极反攻,北宋已渐次扭转了被动态势,特别是“浅攻扰耕”战术的实施以及平夏城战役的胜利,更令西夏在战场全线感到了空前的军事压力。在此情形之下,西夏兵民在大理河的“夜耕昼退”,本身即可说明其忌惮宋军驱捕,侵耕的目标已然从“袭扰对手”收缩为“避免损失”;而鄜延路所谓的“全无畏惮”“军声不振”,似乎更应被理解为当地官员争取战机乃至战功的一种“说辞”。尽管如此,宋廷“不限时月”“出兵掩击”的决断与气魄,依旧与其在屈野河侵耕纠纷中的保守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其中“前车之鉴”的影响也当予以充分的估计。总而言之,屈野河侵耕纠纷的发酵与解决,既是管窥宋夏关系复杂性之一斑,更是中国古代不同政权管控边疆危机的一次独特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