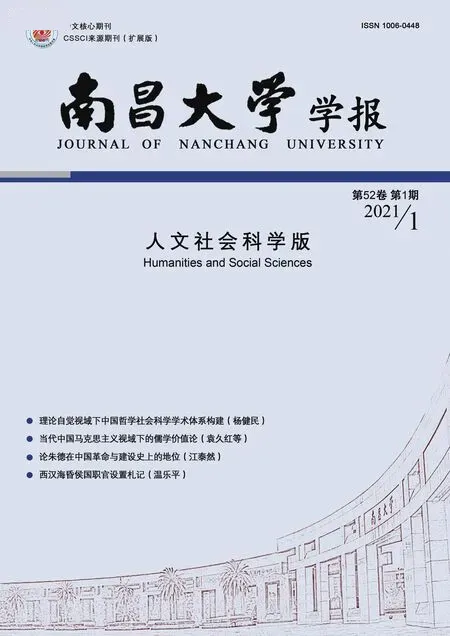马基雅维里的新德性观
骆 宣 庆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在政治哲学史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开启了一个通向政治科学的新时刻,“正如伽利略的动力学为现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马基雅维里也铺就了一条通向政治科学的新道路”[1](P161)。几个世纪以来,不仅关于《君主论》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而且学者们一致达成了共识:《君主论》的主题是教导新君主如何建立一个强大且安全的国家,亦即希冀一名新君主将意大利从被瓜分、侵略、蹂躏的苦难中解救出来。
围绕《君主论》这一主题,学者们的争论主要在于,新君主实现其最高目标的同时是否会与人们日常所珍视的道德相冲突,以及马基雅维里本人对这种冲突的看法是什么?施特劳斯学派认为,《君主论》通篇充斥着宫廷权谋的论调,马基雅维里在其中对君主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建言是全然不顾道德的,他就是恶行的传授者和君主的邪恶教师,所以这种观点将马基雅维里视作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sm)的开创者。不同于施特劳斯学派,以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为代表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1)reason of state既可以翻译为“国家理性”,也可以翻译为“国家理由”。国内学界对该词的译名未做统一,而是视使用的语境采取不同的翻译。学说则将政治与道德的分道扬镳归功于马基雅维里[2](P41)。在国家理性学说看来,马基雅维里眼中的君主应当是一个超善恶的人,即政治是一个独立于道德的领域,政治行动的衡量标准是其结果是否对国家有利,而行动的道德上的善恶则是不相干的。简言之,国家理性学说主张,政治分离于道德,权力优先于善恶是《君主论》的伟大内核。
尽管针对施特劳斯学派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解释路径,国家理性学说正确地指出了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一个以恶为善的大颠覆者,但是当国家理性学说在政治领域将“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的原则贯彻到底时,它就必然走向了政治功利主义:凡是对国家有用的就都是道德的,而这种以利为善的政治功利主义逻辑解构了道德在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的位置。然而,《君主论》文本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马基雅维里并未主张政治行动可以没有任何道德顾虑,道德在政治事务中全然无立足之地。当然,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的某些文本处的确指出政治与道德之间存在张力,即君主可以视情况的需要与否决定是否行不义之事,但这仍然不代表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国家理性主义者,因为政治与道德的张力从根本上说是新政治科学与旧道德观的冲突:旧道德中的好只是“显得好”(appears to be good),而非“真的好”(really good)。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国家理性学说的基本逻辑,表明其政治一元论的逻辑消解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其次指出,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根植于马基雅维里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颠覆,马基雅维里破除了那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的价值,将政治秩序和道德价值重新奠定在真实的经验世界的基础之上;最后阐明,为了解决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张力,马基雅维里并未走向去道德的国家理性学说,而是根据对事物本性的新理解,将道德奠定在经验的基础之上,区分了政治事务中的“真的好”和“显得好”,在解构旧德性的同时重构出新德性,从而重新安顿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
一、国家理性学说:概述与反思
众所周知,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十八章“论君主应当怎样守信”中的建议一直饱受争议和批评。他认为,人们公认君主守信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他的时代经验却表明,只有那些不重视守信和欺骗他人的君主才取得了丰功伟绩。因为世上本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属人的,即运用法律;另一种是属兽的,即运用武力。由于属人的方法常常有所不足,因此君主必须懂得如何用属兽的方法来补充前者。这就是说,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狮子和狐狸,因为狮子能够使豺狼惊愕,而狐狸懂得如何避免落入陷阱,那些单纯模仿狮子的人往往会掉入陷阱而不自知。所以,马基雅维里向君主建议道: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3](P81)
这意味着,君主是否守信要取决于行动结果对自己有利有否。不仅如此,马基雅维里赤裸裸地建议道:君主根本没有必要“真得”拥有一切传统道德观所珍视的德性,但却必须“显得”具备这些德性,因为“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3](P85)。
正如斯金纳所指出的,“人们经常声称马基雅维里在这些章节中的论点的独创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将政治与道德全然分开并因此强调‘政治的自律’”[4](P216)。不同于将马基雅维里塑造为“恶棍老尼克(Old Nick)”的传统观点,国家理性学说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反道德和以恶为善,而是行动的道德与否在政治事务中根本就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根据国家理性学说,政治是一个独立于道德的领域,其本质特征在于权力的维持而非伦理价值,因此政治行动是超善恶的,道德不应该成为政治行动的束缚。“马基雅维里把政治从道德中分离了出来——他主张,政治上必要的事情,会受到一般道德意见的谴责,例如为了国家利益而遗尸遍野”[2](P54),这种政治与道德二元论的解释路径为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国家理由”学说所继承,迈内克深刻地指出,“在一切依照‘国家理由’的行为后面,有着基本的、生物学意义上‘不顾一切代价的安全和自保追求’,谴责和诅咒这追求就如谴责和诅咒美洲豹身上的斑点一样没有道理”[5](P31)。当公爵切萨雷·博尔贾“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暴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3](P33),用残忍的手段立刻恢复了罗马尼亚的安全和统一时,马基雅维里本人对公爵此举不是毫不掩饰地大加赞赏吗?因此,国家理性学说断定,政治行动的评判标准就是其结果是否有利,政治与道德是两个互相独立的领域。
那么,在国家理性学说者的眼中,政治行动的评判标准是其结果是否有利(2)本文不涉及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行动的最高目标究竟是对君主个人有利还是对国家有利的争论。相对于所谓《君主论》通篇违反道德的行动都是以君主的私利而非共同福祉为依据的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老派观点而言(参见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M].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第107页),本文更倾向于将《君主论》和《论李维》看作一个整体,即认为二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将意大利从四分五裂的局面中解救出来,建立一个强大且持久的新国家,有关两本著作主题一致性的论证可参照G.H.R.Parkinson.Ethics and Politics in Machiavelli[J].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50-),Vol.5,No.18 (Jan.,1955),pp.37-44;pp.41.。现在,当国家理性学说为政治行动的超善恶寻求一种辩护,从而提出政治行动的最高目标是国家利益,统治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其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福祉时,就瓦解了政治与道德的二元论构架,且不可避免地堕入政治功利主义。因为按照国家利益是最高目标的辩护策略,相比于个人道德,国家的安全与福祉具有更崇高的价值,所以统治者应当根据行动之后果来决定是否行动,而被选择的行动必须是有利于国家的行动。由于政治行动之目标的崇高性,从而政治行动本身也被合理化了,就像罗慕路斯的杀弟行为被其建立罗马王制的目标立刻合理化了一样,当权力退到幕后,仅仅作为维持国家利益的手段时,国家理性学说就立刻获得了一种崇高的道德价值。“马基雅维里的伦理学是第一个这样的伦理学:判断一个行为不是根据行为本身,而仅仅根据行为的后果。”[6](P179)
如果说行为的后果会合理化行为本身,凡是有助于国家利益的行动就都是道德的行动,那么“马基雅维里在反对基督教道德的直线式途径的同时,铺下了另一条以它自己的方式同样笔直的道路,一条径直指向对国家有用之目的的道路。然后,他就怀着一种他特有的欣喜走下去,从中导出最极端的推论”[5](P101-102)。可以看出,国家理性学说者从政治与道德的二元论框架出发,断定政治是一个不考虑道德与否的独立领域,但当他们将国家理由看作政治行动的唯一标准,继而区分了政治特有的价值和道德特有的价值,并将前者看作更高类型的价值时,就不可避免地滑入了政治一元论,完全瓦解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应有位置。
然而,当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八章讨论叙拉古的国王阿加托克雷(Agatocle)时,他向我们指出的是,政治行动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道德上的优越。阿加托克雷的一生都过着邪恶的生活,他依靠暴力、残忍的行为获得了叙拉古的统治权,而且之后依赖很多勇敢的决策依然保有着这个城市。但是,马基雅维里写道:
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德性(virtù)的。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3](P40-41)
首先,马基雅维里对阿加托克雷的评判显然包含了道德上的谴责,他并不认为凡能保有一个国家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无可指责的。阿加托克雷可以被称作一名优秀的统治者,但他绝不是一个好人。其次,“德性”一词在马基雅维里这里并不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去道德性的概念,不能仅被看作无伦理旨趣的力量、技艺之类。最后,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政治与道德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关系,国家理性学说将国家利益奉为最高目标从而解构掉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国家理性学说也许可以辩护道,马基雅维里在有些地方的确指出“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3](P74),所以当道德与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治优先于道德。必须指出的是,对马基雅维里来说,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确存在冲突,但是,马基雅维里解决二者冲突的方式并不是走向去道德化的国家理性学说,而是通过将道德的标准重新拉回到经验的现实世界之内,在解构旧德性的同时,重构了新德性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
事实上,在马基雅维里的眼中,真实的世界是处于流变之中的经验世界,那个被古典哲学奉为至上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只是人们的虚构,当统治者用一种被古典思想视为德性的稳定的品质去应对这个变化莫测的政治世界时,就是用以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为根基的道德规范应对本身以流变的经验世界为根基的政治事务,这自然会造成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里对事物本性的理解,颠覆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形而上学思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思想对政治和道德关系的理解。
二、德性的解构和重构:以经验为根基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何为“理想国家”(ideal state)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1](P83)。对柏拉图来说,“理想国家”不是能从任何实践经验中获得的意见,而是一种从理念世界获得其稳定性的永恒不变的知识。所有在存在论上低于理念世界的单纯经验都被柏拉图宣布为虚妄不实的、徒劳无益的,这种对意见与知识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强调,是柏拉图认识论的根本原则。认识论上意见与知识的这种高低之分又是以存在论为基础的,知识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存在,亦即理念,意见的对象则是流变不驻的存在,亦即现象,流变的可感现象在存在论上低于不变的可知对象。由于经验世界的对象都是流变的存在,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对其形成稳定不变的知识。那么,无论是城邦的“理想国家”,还是个体的德性,都必须以对永恒存在的洞察为根据,而不能建立在经验世界的基础之上。
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眼中,城邦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的道德生活的目标都是实现正义。当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卷讨论个人的正义问题时,他将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进行类比:
“那么,”我说,“如果有两个东西,一大一小,它们都取了同一个名,那么就它们有同一个称呼来说,它们是相像还是不相像?”
“是相像的。”
“那么,一个正义的人,就正义的形式本身来说,和一个正义的城邦将不是不同的,区别的,而是相像的?”
“是相像的。”
“可是,一个城邦之所以被名之为正义的,那是由于在它之中存在着三个本性上不同的属类,每一个属类从事于只属于它自身的工作;并且,又由于某些其他的由这些属类而来的气质和风度,因此它是节制,勇敢,智慧的。”
“正是这样。”
“至于说到个人,我的朋友,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来期待他:如果在他的灵魂中也具有那些同样的类别划分,那么,由于它们和在城邦中的属类的同一气质,我们也应该能够正确地应用和在城邦里所用的同一的名目来称谓他。”(3)关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大字的正义与小字的正义一致性的论证是否成立,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对此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国内学者吴天岳、聂敏里则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辩护性的回应。可参见伯纳德·威廉姆斯.柏拉图《理想国》中城邦和灵魂的类比[J].聂敏里,译.云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3-19页;吴天岳.重思《理想国》中城邦—灵魂类比[J].江苏社会科学,2009第3期,第84-90页;聂敏里.《理想国》中柏拉图论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的一致性[J].云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30-43页。[7](P214-215)
据此,当灵魂中的欲望和血气听从理性的指导,从而具有各自的德性(节制、勇敢和智慧)时,个人就具有了正义的德性。城邦同样如此,当城邦的手工业者和护卫者阶层听从哲学家的统治,从而各自表现出节制、勇敢和智慧时,城邦也就成为理想中的正义的城邦。总之,当公民被教育成为一个道德上完善的人,并在行动中体现出稳定的德性品质时,城邦的政治生活就具有了合理的秩序,从而实现了正义城邦的目标。毫无疑问,这种正义不是从经验世界中得来的可变的意见,而是以对永恒不变的善的理念的认识为依据的。所以,在古典思想的语境中,政治与道德是大字的正义与小字的正义的关系,理念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为二者提供了一致性的基础,二者所具有的潜在冲突也被目标的一致性遮蔽起来了。
此外,对古典哲学来说,经验世界的一切意义,无论是政治还是道德,都是以理念这种终极实在为根据构建起来的,政治秩序和德性品质的稳定性、一致性也是以理念这种终极实在的绝对真实性为前提的。但是,对马基雅维里来说,那个处于流变之中、反复无常的经验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被柏拉图奉为实在的理念世界只是由于人们惧怕变化而虚构出来的幻象。政治行动发生于其中的世界正是一个流变不居的现象世界,政治的目标也不再是探询何为“理想国家”,并教导人们过上有德性的生活,而是要在这个反复无常的现象世界中保有自身。正是由于对真实世界的新理解,一套以不变的善的理念为根据的道德观才必然与那本身立足于经验世界的政治行动相冲突。所以,政治与道德的张力是旧的德性观与新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的产生从根本上则是由于,以理念为代表的终极实在对人类经验世界的统治崩溃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现在不再是大字的正义和小字的正义的同构关系,掩饰二者冲突的遮羞布被扯掉了。所以现在,无论是对政治还是道德,马基雅维里的理解都是崭新的,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现在走上了一条还未有人走过的新路径,因而在《君主论》著名的第十五章这样说:
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
可是,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3](P73-74)
显然,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言,“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不同于“事物的想象方面”,“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远不同于“人们应当怎样生活”,他的前辈们的确就“想象中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议论颇多,但是,还没有人就君主在实际上的君主国中应当如何行动做出指导,也没有人就“厕身于众多不善良的人”之中的君主应该如何作为做出建议。根据上文,真实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的区分在马基雅维里这里被颠倒了,马基雅维里的伟大变革就在于,他坚持了运动与变化的真实,并将其看作他的基本原则之一[8](P192)。真实的世界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处于流变之中的经验现象的世界,它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来自某个超验的不变的世界,相反,是由其自身建构起来的。那么,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之中,人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加以阐述:一方面,是命运作为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人间世事变动不已,有起有落在所难免;有许多事情,理智无法主导,却由形势促成”[9](P29-30)。现实的政治世界是一个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的世界,在其中命运女神是我们行动的半个主宰,然而她不会始终对一个人友好,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3](P119)。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本性造成的结果,即人们都不是善良的,而且“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为难、追逐利益的”[3](P80)。这就是说,在流变的经验世界中的人性也是不稳定的,人要被培养出并在现实中实施一种永恒不变的理想德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马基雅维里认为,在这个真实的现象世界中,“没有行动的永恒基础,也没有任何用来调整我们行为的规范”[8](P190),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所处理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有机体的城邦,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科学要处理的是彼此竞争、彼此侵蚀的、处于运动之中的国家[8](P197)。为了避免政治与道德的冲突,道德也必须如同政治一样,将标准拉回到这个真实的世界之中。“德性”这一贯穿马基雅维里思想始终的概念正是体现了他对立足于真实世界的道德的理解。现实世界是变幻不定的,命运在其中实施着她的威力,所以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行动应当始终“同命运密切地协调”[3](P121),马基雅维里指出,两个品性相同的人,例如为人都是小心谨慎,但一者成功了,一者却失败了;而两个不同的人,一个谨慎,一个急躁,却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不外乎都是由于“他们的做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3](P119),是否同命运相协调,那具有德性的人的命运是绝不会改变的。所以,“德性”在马基雅维里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指向灵活性而非古典语境下稳定性的品质,其能够使人依据命运的风向和时代的特性采取行动,辨认出什么是“真的好”和什么只是“显得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性仅是一个去道德化的技艺、力量之类的概念,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道德与否的标准现在并不是由永恒不变的以理念为代表的终极实在所确立的,而是由流变的经验世界自身所赋予的。
三、从“显得好”到“真的好”:新德性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
通过对传统政治哲学和德性观的这场革命,马基雅维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将政治从道德的“异质”枷锁中解脱出来,而是要将人们日常所珍视的道德从虚构的理念世界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将道德的标准拉回到经验的可靠基石之上。那些被人们解读为反道德的、抑或非道德的臭名昭著的建议无非是要告诉人们,道德必须匹配真实的经验世界。
那么,君主不应当守信的建议并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范,恰恰相反,马基雅维里的这条声名狼藉的谏言的施行是有条件的。首先,君主只是为了避免给他设置的陷阱才应该具有狐狸的狡猾。其次,在解释为何君主不应当守信的原因之后,马基雅维里立刻补充道:“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3](P74)只是因为人们都是邪恶的,他们都不会对君主守信,君主才不能向他们守信,而向那些不会向你守信的人守信根本就是愚蠢的行为。最后,至于马基雅维里对君主没有必要拥有一切传统道德观所珍视的德性的建议,实际上正是表明了马基雅维里对立足于虚构出来的终极实在的旧道德观的批评,因为“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3](P74),旧德性的好只是“显得好”,而非“真的好”,因为“真的好”是人类能够达到的经验世界的范围之内的好。
现在,通过将政治与道德都拉回到经验世界的范围之内,马基雅维里就解决了新政治科学与旧德性观的张力,重新安顿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一方面,当政治环境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政治与道德并不会出现明显的冲突,从而君主也必须遵守日常道德规范,否则君主只能赢得统治,却无法赢得荣耀;另一方面,当政治环境趋于常态,亦即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就是变幻莫测的状态时,君主的德性就在于能够辨别什么是“真的好”,而什么又只是“显得好”,用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行动的善恶,就是用刻板僵硬的道德规范来应对其并不适用的特殊的政治环境,这不仅会导致自我毁灭,而且在道德上才是错误的表现。“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觉察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3](P75)所以正如培根所指出的,马基雅维里的巨大贡献并不在于根据“人们实际上做什么”而降低道德的标准,而在于表明如何辨认出得体外表下的腐败行为,以至于保存道德的高标准[10](P3)。
在《君主论》第十五章展示了这样一条关于政治与道德的新路径之后,马基雅维里便开始教导君主如何识破政治领域中有着善的表象,但实际上却并不产生善的那些行动。人们往往认为慷慨是好的,吝啬是坏的,仁慈是好的,残忍是坏的,守信是好的,不守信是坏的。但是,马基雅维里指出,君主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他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尊重他。……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3](P76)。反之,如果一名君主刚开始就节约支出,不为慷慨之名而加重人民的负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主收入丰盈,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他反而最后落得慷慨之名。所以,君主对于吝啬之名不应有所介意,因为吝啬看起来是坏的,实际上却是产生好的德性。
马基雅维里断言,虽然每一名君主都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残酷,但是滥用仁慈,坐视国家的混乱,会使整个国家受到损害。相反,君主通过一时的残酷,平定混乱、凶杀之事,带来的则是整个国家长期的和平与安全。马基雅维里在这里以他个人的政治经验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在他1502年代表佛罗伦萨与切萨雷·博尔贾会面时,他目睹了博尔贾残忍地处死了雇佣军首领雷米罗。但是,公爵的残酷却给罗马尼亚带来了秩序,将其统一起来,并且恢复了和平与忠诚。对此,马基雅维里指出,“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被毁灭了”[3](P79)。最后,关于教导君主不守信的箴言,实际上也是教导君主,政治中的有些恶其实只是幻觉,德性就在于识破这些幻觉。
相比于古典哲学中的作为稳定性品质的德性,马基雅维里的德性是一种灵活的品质,这种德性的关键作用是能够辨别命运和时间带来的东西。“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3](P12),君主必须依据时间的特性和命运的风向采取行动,区分时间带来的好事与坏事,识破那些仅仅看起来是好事的幻觉。用一种刻板不变的品质应对命运和时间,就是把自己交付给命运和时间,等着收割命运和时间的好处,而不是收割“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3](P12)。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确存在着张力。为了弥合这种张力,国家理性学说从政治与道德的二元论出发,将“国家理由”看作政治行动的最高原则,主张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都是道德的行动,从而走向了极端的政治功利主义。如此,国家理性学说虽然消解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张力,但却是以瓦解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应有位置为代价的,而这与《君主论》的文本是不符的,因为马基雅维里在那里明确指出,政治行动的成功不代表德性的优越。所以,为了解决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里并未走向国家理性学说,而是通过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形而上学的批判,颠覆了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在存在论上的位置,指出政治与道德的冲突在根本上是旧德性观与新政治科学之间的冲突。
通过将政治与德性的标准都拉回到经验世界的范围之内,马基雅维里一方面解构了古典以终极实在为依据的永恒不变的德性,另一方面重构了以流变的经验世界为根基的德性,从而弥合了旧道德观与新政治科学之间的张力,重新安顿了道德在政治领域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