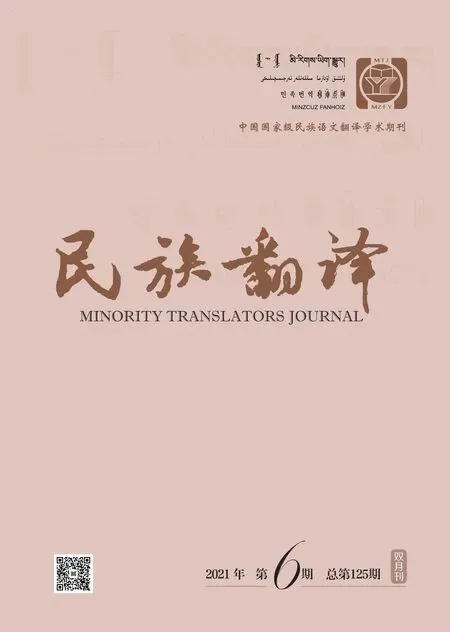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及其价值*
⊙ 徐 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北京 100062)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多元一体的格局具有很强的共性和特点。清代编纂的多语种文献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交融。本文着重探讨的多语种辞书主要是指满文和其他民族文字共同书写的辞书,为便于表述,文中表述为满文多语种辞书。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编纂在乾隆朝达到高峰,这一朝编纂的满文辞书涉及的语言文字种类多样,成书数目众多,其中部分词典历经多次翻刻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的编纂及其版本流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线索,为此类文献价值的阐释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一、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编纂
清代乾隆朝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为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中期,收复边疆,最终完成了祖国统一。统一的国家版图之内,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众多民族共同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交融为多语种词典的编纂提供了必要条件。乾隆皇帝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也有相当深厚的造诣,其在位期间,敕修了一些以满文为主的少数民族语文工具书,以满足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需求。
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基本上是根据皇帝旨意或命令编纂而成,许多文献都冠以“御制”“钦定”字样。这一时期的满文多语种辞书多为敕修,即皇帝敕命编纂。一般指定儒臣办理,或者修书各馆承办纂修。形成的本子多经过皇帝批阅后方才定稿。大多经武英殿刊刻,于各处陈设,颁赏各地使用。
乾隆朝官修多语种辞书从编纂主题来看,主要围绕满文蒙文《大藏经》的纂修、《清文鉴》系列纂修、对音标音词典和“钦定新清语”辞书的编纂。本文择要列举相关主题辞书进行阐释。
(一)《大藏经》相关辞书
乾隆皇帝在《满文大藏经》御制序中讲到编译缘起:“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稗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1]33认为梵文佛经既然都已经翻译成藏文、汉文、蒙文,有必要翻译成满文,教化世人尊君亲上、去恶从善。
满文翻译佛经时,同藏文、蒙文一样遇到梵文对音的问题。乾隆十三至十五年(1748—1750年)谕令和硕庄亲王领衔,由章嘉国师亲自主持制定了针对佛经中咒语梵文读音的标准注音系统,其中包括满文的注音系统。“这是满文首次建立直接针对梵文的注音系统,即通过借用一部分蒙古字母,用以完善其所缺音韵,这个系统就叫满文阿礼嘎礼字。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汇编成书,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同文韵统》。此书成为我们正确识读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及还原梵文名号最重要的依据。”[1]35《钦定同文韵统》六卷,是清朝廷编制刊刻的梵藏满汉四体对音辞典。
乾隆三十三年为庆贺皇太后八旬盛寿,又敕章嘉国师编纂了《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二十卷。这是一部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的标音词典,以《钦定同文韵统》为标准,纠正南宋平江(治所在江苏苏州)景德寺僧法云编《翻译名义集》中的错讹,并增加藏文阿礼噶礼音译词、满文阿礼噶礼音译词、蒙文阿礼噶礼音译词。主要收录梵语的有关佛教名词和地名。另有《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阿礼噶礼》也是为编译大藏经而修。
(二)续修《清文鉴》系列辞书
乾隆年间最重要的多语文辞典,是以康熙年间刊《御制清文鉴》为基础编纂的《清文鉴》系列辞典。《御制清文鉴》二十卷,是清朝皇帝敕修的第一部满文辞典,历经三十五年由武英殿刊刻成书。该书是用满文解释满文词义的单语分类辞典,共分36部280类,约收词12110条,其中收录许多汉语音译借词。乾隆帝敕命用“新清语”翻译、增补、修订《御制清文鉴》,并增加满文注音,以及满文的汉字切音,定名《御制增订清文鉴》,形成满汉双语辞典。乾隆三十六年由武英殿刊行,该书收入《四库全书》。
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为存留满、汉、蒙文音韵,敕命阿桂等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增入蒙文译词,纂修成《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一卷,四十五年武英殿校刊梓行。乾隆帝在《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序》中说:“……(蒙古)诸部互言音韵,刚柔虽略殊,而大段则一。即国语虽与蒙古语异,而亦有一二相同者。朕即位之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随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即能之。”[2]95可见,这部词典的编辑直接服务于朝廷对蒙古的治理,从中也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语言学上的造诣。这是清代第一部敕修的满、蒙、汉三体合璧辞典,确立了编纂满、蒙、汉三体合璧辞典典范,是清一代众多语文辞书中语言学价值最高的一部。该书收入《四库全书》。
其后,乾隆帝又敕修编纂了《御制四体清文鉴》与《御制五体清文鉴》。在“三体”基础上《四体清文鉴》增加藏文;在“四体”基础上《五体清文鉴》又增加了维吾尔文及满文注音。终使《清文鉴》系列臻于完善。
(三)标音对音辞书
《钦定西域同文志》是清代第一部新疆、青海、西藏地区地名、山水名和人名的满、汉、蒙、藏、托忒、察哈台六种文字对照的大型辞书,是“乾隆年间清朝灭准噶尔汗国,实现‘一统无外’的结果,也是清朝推行多语文政治,促成‘同文之盛’的产物。”[3]12大学士傅恒等奉敕编纂的《钦定西域同文志》四十八卷。该书按地域分布顺序分为天、地、山、水、人五类,地名、人名等都用汉、满、蒙、藏(西番)、托忒、察哈台六种民族文字对照注出。有乾隆二十八年武英殿刻本。该书收入《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敕撰《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是一部满汉合璧标音辞典。在翻译辽金元史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发现有很多内容不能准确翻译和对译。为了存留和规范辽金元三史中契丹语、蒙古语、女真语等音译借词音韵,选录了三史中人名、地名、官名等,在旁标注满文对音。该书是研究辽金元三朝以及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的工具书。
《御制清汉对音字式》是为简便对音应用而敕修的辞典。乾隆皇帝将此“著交军机大臣,依国书十二字头,酌定对音,兼写清汉字样,即行刊成简要篇目,颁行中外大小衙门,嗣后遇有满洲蒙古人地名对音,俱查照译写,俾各知所遵守,将此通谕知之。”[4]乾隆三十七年武英殿刊刻,并颁发各处通行使用。
(四)“钦定新清语”辞书
早在入关前,满语词语中已介入很多汉语音译借词,入关后满族人杂居于广大汉族群体中,汉化速度加快。康熙年间以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并将有关衙署名目、官职、典籍名等汉语词用满文进行音译。乾隆皇帝为强化“国语”使用,将之前汉语词汇中只用音译来翻译的部分词语进行改订,用满文翻译成意译词汇,并颁布谕旨广为推行,即“钦定新清语”。终乾隆一朝,自乾隆十二年颁布上谕推行“新清语”开始,乾隆皇帝不断颁布上谕推行,汇总“新清语”编订形成了《清文鉴外新语》《钦定清语》《新定新语》《满汉钦定清语》。这些“新清语”包括衙署、职官的满文名称,还涉及天文、时令、城郭、宫殿、动植物等多个门类。在清代中央和地方档案中,有很多关于颁布修改某些满文词语的上谕。“新清语”相关辞书是清代统治者有意识推动本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成果。
二、清代官修满文辞书现存版本及其流传
乾隆朝官修的满文多语种辞书,多有武英殿刻本,从档案记载来看,有颁赏各地官员,由于对于满汉文公文使用的需要,有些图书允准民间书坊翻刻,流布广泛。
(一)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内府及其他各本
在乾隆朝满文多语种辞书众多版本之中,以武英殿刻本居多。各本还有允许翻刻的坊刻本和抄写本。以下按成书刻印年代为序,适当梳理该部分辞书各版本。版本信息来自翁连溪著《清代内府刻书研究》[2]及《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5]。
(1)《钦定同文韵统》六卷,乾隆十五年武英殿朱墨套印本,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框高21.3厘米,宽13.9厘米。另有乾隆二十四年内府刻本、宣统二年(1910年)理藩部重印本、1925年蒙藏院重印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藏于国家图书馆。
(2)《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武英殿刻满汉蒙藏托忒察合台文本,八册,半页九行,白口,四周双边。版框高19.2厘米,宽14.4厘米。书口有汉文书名、卷次、页码。另有抄本、晒印本、影印本。《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藏于国家图书馆。
(3)《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二十卷,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二十册,经折装,半页二行,白口,四周双边。版框高25.8厘米,宽12.2厘米。
(4)《御制增订清文鉴》四十七卷,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满汉合璧本。四十七册,半页十六行,满汉文各八行。白口,四周双边,无鱼尾。版框高22.7厘米,宽17.8厘米。书口有满蒙书名、卷次、汉文类名、页码。另有抄本。《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藏于国家图书馆。
(5)《御制四体清文鉴》三十六卷,乾隆三十七年武英殿刻满蒙汉藏四体合璧本,三十六册,半页四行。白口,四周双边。版框高21.6厘米,宽15.3厘米。另有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北京嵩祝寺刻本。
(6)《钦定清汉对音字式》不分卷,乾隆三十七年武英殿刻满汉合璧本,一册,半页九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框高19.3厘米,宽14.2厘米。另有乾隆年间坊刻本、道光年间殿本,坊刻本,光绪年间坊刻本等。
(7)《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阿礼噶礼》,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刻本,一册,半页六行,白口,四周双边。版框高25.6厘米,宽13.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本满文手书,其他三体为刻印。
(8)《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二卷,乾隆四十五年武英殿刻满蒙汉合璧本,三十二册,半页十二行,白口,四周双边,无鱼尾。版框高21.2厘米,宽16.1厘米。书口有满文书名、卷次,汉文类名页码。《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藏于国家图书馆。
(9)《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刻满汉合璧本,十九册,半页十行,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框高21.4厘米,宽15.3厘米。书口有汉文书名、卷次、页码。
(10)《五译合璧集要》二卷,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梵藏满蒙汉合璧本,二册,半页七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框高21.3厘米,宽15.6厘米。书口有汉文书名、卷次、页码。
(11)《御制五体清文鉴》三十六卷,乾隆年间满蒙汉藏维合璧精写本,三十六册。白口,四周双边朱丝栏,半页四行。版框高33.7厘米,宽19.9厘米。书口有满文书名、汉文类目、页码。另有抄本、晒印本。
(12)《钦定清语》十卷。乾隆年间精写本。线装、白口,版框高28.6厘米,宽19.8厘米。另有抄本、精写本。
(二)乾隆朝官修的满文多语种辞书流布
官修词典编纂经内府刻印之后,部分颁赏各处,部分允准地方翻刻,在一定范围内流布。官修典籍呈览本、陈设本、颁赏本及中央地方各衙门请颁发等都是此类辞书得以流布的主要途径,允准翻刻之后流布更为广泛。
各级衙门公务文书翻译撰写的需求也是满文多语种辞书流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湖广襄阳镇总兵立柱奏请刊刻颁发《钦定清语》①,是因地方官员抄写文书时写错满文,经军机处议,俟增订清文鉴颁发。《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书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间,分赏各处,各地收到赏赐的官员纷纷上奏折谢恩。固山贝子允祁②,承办东陵事务盛常③,管理泰陵事务贝子弘昽④、察哈尔都统常青⑤、绥远城将军容保⑥、西安将军富僧阿⑦等收到赏赐《御制增订清文鉴》,纷纷具折谢恩。该词典目前在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南京、江西等地图书馆均有藏。再如,乾隆六十年《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颁赏两广总督长麟、伊犁将军明亮,此二臣均上奏折谢恩。
《钦定对音字式》更是广泛颁赏,允准地方翻刻,成为地方各衙署撰写报送满文公文时必不可少的翻译工具书。在道光年间,皇帝再次撰写御制序言加在乾隆本之前重新刊布。该本在乾隆、道光、光绪等朝均有数量较多的坊刻本存世。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价值的再思考
经清前期诸皇帝百余年的苦心经营,各民族文化开始繁荣起来。乾隆皇帝即位时,年富力强,继承了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精心经营而日趋繁荣的大清王朝,统治稳固,经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在乾隆时期得以奠定,为乾隆朝文化事业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审视,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作为文字语言转换的工具,在政治驱动和文化交流交融方面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众多的多语种辞书存留了清代中期类型丰富的多种语言文字的词语,如此丰厚的历史语言资料,为构建当时和后世各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桥梁和纽带。
(一)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在政治上推动了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多语种词典是跨语言交流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有清一代,满语满文作为“国语”“国书”,广泛应用于撰写公文、图书编纂、镌刻石碑等。清廷主导编纂的多语种辞书贯穿统治阶级推动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同文”之志。在“文书御天下”的年代里,中央和地方各衙门利用该类辞书准确传达政令,其编纂和流传应用为准确传播政令提供了必要工具。满文翻译汉文的各类书籍、翻译碑文等也要借助各类辞书,才能形成相对一致的准确表达,传达出原著作的语义,在体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同时,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对不同文化的认同。
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影响来看,在多语种民族文献互译的过程中,作为文字与文化转换的桥梁和纽带,乾隆朝的满文多语种辞书无疑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对构筑清代多元一体格局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乾隆朝编纂的满文多语种辞书在文化上为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工具
明末清初,满汉文化频繁接触、碰撞,彼此之间产生了渗透和融合的需求。到乾隆中后期,边疆收复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对边疆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乃至风俗习惯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清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更加有特色。满文多语种辞书深入而广泛地反映了众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交融。乾隆朝编纂的满文多文种辞书体现各民族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印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和认同,为后世留下各民族的历史传承和国家记忆。
(三)乾隆朝编纂的满文多语种辞书在文献上为后世留存了数量众多的多语种珍贵语料
留存至今的满文及多语种辞书不仅为当时的跨语言跨民族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也为今天我们解读清代多语种历史文献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工具。辞书虽然侧重内容不同,却通过词条保留了很多人文历史信息,为今天的多种历史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语料。如《同文韵统》中保留了清初藏语语音概貌,《钦定西域同文志》的记载为后续编纂《钦定西域图志》《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和续纂《大清一统志》西域部分提供了西域地名、人名、职官、区域行政地理沿革历史资料,同时标注西域地名、人名的各族不同语文的准确读音写法以及标准满汉译文。“这部书的研究实质上关乎清朝拓土开疆的政治史、统治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制度、西域诸民族语言文字、西域历史地理演变等诸多问题。”[3]12可见,辞书不仅保留了语言文字信息,也保留了当时的历史信息,是亟待不断挖掘的丰厚宝藏。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汇聚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研究民族翻译的历史,民族文字多语种辞书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清代乾隆朝满文多语种辞书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我们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
注 释:
①见清庆桂、董诰命等编纂的《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百三十六,乾隆三十年五月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大清历朝实录。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6-2546-020,固山贝子允祁奏谢赏《御制增订清文鉴》折。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6-2546-037,办理东陵事务盛常奏谢赏《御制增订清文鉴》折。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6-2547-020,管理泰陵事务贝子弘昽奏谢赏《御制增订清文鉴》折。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6-2547-024,察哈尔都统常青奏谢赏《御制增订清文鉴》折。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6-25553-008,绥远城将军容保奏谢赏《御制增订清文鉴》折。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满文录副奏折,档号03-0186-25556-005,西安将军富僧阿奏谢赏《御制增订清文鉴》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