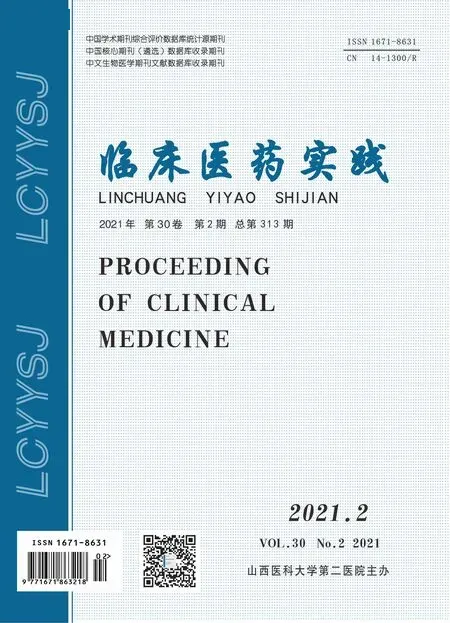194 例川崎病患儿临床分析及诊疗进展
俞小霞,陈捷
(福建医科大学省立教学院,福建省立金山医院,福建 福州 350008)
川崎病(KD)又称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是一种主要累及全身中小动脉的血管炎,好发于5 岁以下儿童。自1957年川崎博士报道首例病例以来,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目前病因尚不清楚。在发达国家,它是儿童期获得性心脏病发病的主要形式,如果不治疗,约25%的病例会导致冠状动脉瘤(CAA)[1]。早期诊断、尽快结束急性期炎症及减少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是急性期川崎病的治疗目标。本文回顾性分析了194 例川崎病患儿的资料,并搜索了国内外新的治疗进展报道,旨在为之后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通过查阅病历,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方法,获取并分析了2016年6月—2019年10月福建省立金山医院儿科川崎病住院患儿共194 例,资料包括患儿一般信息、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治疗方案及疾病转归等。采用Excel数据处理系统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患儿性别及就诊年龄
194 例患儿中男122 例,占62.89%,女72 例,占37.11%。其中以1~<3 岁的婴幼儿多见,共143 例(73.71%),学龄前期(3~<6 岁)儿童33 例(17.01%),学龄期(6~12 岁)儿童18 例(9.28%)。最小年龄为2个月零2天,最大为11 岁。
2.2 临床表现
194 例KD患儿均有发热,以高热为主,眼结膜充血156 例(80.41%),唇红皲裂、杨梅舌149 例(76.80%),皮疹108 例(55.67%),颈部淋巴结肿大137 例(70.62%),关节压痛4 例(2.06%)。194 例中不完全川崎者42 例,占29.90%,其中第二次再发川崎者2 例。
2.3 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
194 例患儿均行血常规+C反应蛋白(CRP)检查。白细胞(WBC)计数升高187 例(96.39%),其中大于20×109/L者44 例(22.68%)。血小板(PLT)计数呈不同程度升高188 例(96.91%),PLT计数下降2 例(1.03%)。CRP升高191 例(98.45%)。194 例患儿中192 例行B型脑钠肽(BNP)检查,其中BNP升高者142 例(73.96%)。所有患儿均行肝功能检查,其中肝功能异常者93 例(47.94%)。194 例患儿中96 例(49.48%)有不同程度冠状动脉扩张,其中2 例形成冠状动脉瘤。
2.4 临床治疗
194 例患儿中有187 例于急性期使用丙种球蛋白2 g/kg冲击治疗,7 例未使用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1 例为不典型川崎病,早期未给予明确诊断,于第10天自行退热;1 例为发热第16天开始出现川崎病临床表现,于第18天自行退热;2 例于发热第6天自行退热;3 例分别于发热第15,18,19天就诊,并分别于第17,19,20天自行退热)。187 例急性期使用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的患儿中,有6 例呈现丙种球蛋白不敏感,其中4 例出现冠状动脉扩张,1 例形成冠状动脉瘤。6 例不敏感型治疗情况如下:1 例为首次使用丙种球蛋白2 g/kg冲击治疗后热退,4 d后再次发热,第二次使用丙种球蛋白1 g/kg+地塞米松后热退,2周内再次发热,给予静脉滴注甲强龙2 mg/kg后热退;2 例为首次丙种球蛋白2 g/kg冲击治疗后仍发热,给予静脉滴注甲强龙2 mg/kg后热退;1 例为丙种球蛋白2 g/kg冲击治疗后48 h仍反复发热,再次给予丙种球蛋白2 g/kg冲击治疗后热退;2 例为首次丙种球蛋白2 g/kg冲击治疗后仍发热,再次给予丙种球蛋白1 g/kg后热退。194 例患儿均使用阿司匹林抗炎、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其中有132 例联合使用阿司匹林及双嘧达莫(抗血小板聚集)。194 例患儿中有2 例急性期合并冠状动脉瘤伴血栓形成,给予溶栓、抗凝治疗后瘤样病变均有缩小。
3 讨 论
据推测,KD发生有遗传易感性,其依据是:首先,一级亲属有KD病史的患者发生KD的风险增加;其次,KD在某些种族中发病率要高得多[2]。目前已发现多种导致KD易感性的遗传多态性,主要与免疫系统调节有关。虽然研究了几十年,但KD的免疫致病机制仍不完全清楚。遗传易感个体在遇到诱发因子(可能是感染)后可导致促炎和抗炎途径之间的不平衡。例如,白细胞介素1(IL-1)通路基因上调和IL-1浓度升高已在KD患者急性期外周血中得到证实[2];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在KD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中也发现了肿瘤坏死因子(TNF-α)显著升高[3];急性KD患者的中性粒细胞中自发的网状结构增强,这种网状结构参与了包括血管炎在内的各种疾病的发病机制。环境流行病学研究正在调查潜在的外部诱因[4]。
KD好发于5 岁以下儿童,男多于女,成人及3个月以下小儿少见。本组194 例病例中男122 例(62.89%)。发病多见于1~<3 岁的幼儿,占73.71%。学龄期儿童发病率逐渐降低(9.28%)。194 例中最大发病年龄为11 岁,最小发病年龄为2个月零2天。基于1 岁以下婴儿的研究表明,相较于完全KD,不完全KD更容易引起冠状动脉受累[5]。即使在患病的10 d内已经接受治疗,近一半的6个月以下的不完全KD仍会发展为冠状动脉瘤,所以这一人群应该更积极地接受治疗[6]。
实验室检查有助于KD的诊断。在急性期,WBC可升高,194 例中有187 例存在不同程度的WBC升高。KD患者的亚急性期,PLT增多是一种特征性表现,通常在发热后的第2周开始出现[2]。PLT计数被认为是KD患者发生冠状动脉异常(CAAs)的生物标志物。入院时PLT计数异常高或异常低的患者发生CAAs的风险较高[7]。本研究PLT计数升高188 例,PLT计数降低2 例,该2 例患儿均出现冠状动脉扩张。KD患者中约三分之一的患者血清转氨酶(AST)或谷氨酰胺转肽酶水平升高[8]。据统计,AST在不完全KD的患者中水平更高[5]。本组患儿中93 例(47.94%)有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损害。CRP升高者191 例(98.45%),其中CRP大于100 mg/L者57 例(29.38%)。血沉(ESR)可能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治疗后升高,因此不应单独用来监测炎症情况[2]。本组KD患儿未常规行ESR检测。BNP作为一种心脏内分泌激素,在KD患儿血浆中水平显著增高,可用于协助诊断KD。本组KD患儿BNP水平升高者占73.96%。KD患儿可出现无菌性脓尿,在多达80%的KD患儿尿液中可发现白细胞[8]。近年来,冠状动脉Z分数被用来预测北美人群中CAA的发生风险。Z评分≥2.0与动脉瘤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0%和74%[9]。
目前,IVIG(2 g/kg)已被确立为KD的标准治疗方法[1]。本组187 例给予IVIG(2 g/kg)治疗,未给予IVIG治疗的7 例为未及时诊断或就诊后自行退热者。187 例IVIG治疗的患者中有181 例对丙种球蛋白敏感,均于给药后48 h内退热并未再发热,治疗效果明显。有报道指出,未接受治疗的KD患儿中有多达四分之一将发展为CAA,而接受IVIG治疗的患儿中仅有4%[10]。IVIG可将CAA的风险从25%降低到5%以下,发热5 d内给药效果最好。对于病程大于10 d、反复发热、冠状动脉扩张或CRP或ESR持续升高者,仍建议给药[2]。有研究指出IVIG较糖皮质激素显著降低了冠状动脉瘤的发生率[11]。
阿司匹林(ASA)是最早发现的KD急性期的治疗药物,高剂量时具有抗炎作用,低剂量时具有抗血栓作用。194 例KD患儿均给予ASA治疗。有报道指出,虽然ASA治疗的病死率从2%下降到约0.2%,但冠状动脉病变的发生率仍约为25%,提示ASA单一治疗并不是预防冠状动脉病变的有效治疗方法[1-2]。关于一线治疗,大剂量ASA的真正有效性仍存在争议[3]。
糖皮质激素可单独作为二线治疗,也可与第二次IVIG联合使用。最近的一项分析得出结论,类固醇在退热方面比IVIG更有效,但在发生CAA风险方面两者无显著差异[12]。类固醇治疗发生非严重不良事件(电解质和血糖异常、高血压、体温过低、心动过缓和一过性胃肠道出血)的比例较高(24%)。本组194 例患儿均未使用糖皮质激素作为KD治疗的一线用药。
有研究指出,他汀类药物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改善内皮功能,减少氧化应激。研究发现阿托伐他汀可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来抑制KD动脉瘤的进展[2]。
187 例IVIG治疗患者中有6 例呈现IVIG耐药。IVIG耐药或难治性KD定义为首次输注IVIG后24~48 h内复发或持续发热,占10%~20%[2]。有文献[13]指出难治性KD是指初始IVIG(2 g/kg)完成后36 h至7 d内持续发热。Kibata等[13]报道,多达20%的患者对IVIG没有反应,这些患者患冠状动脉扩张的风险更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有各种治疗方法,但每种治疗都有难治性病例,这可能是由KD的病因和病理不统一造成的[1]。目前,对于难治性KD的二线治疗尚无强有力的建议,也没有一致的意见。2017年美国心脏协会(AHA)科学声明推荐了三种最常见的二线治疗方法:第二次IVIG(2 g/kg);静脉甲泼尼松龙30 mg/kg,连续3 d,可使用或不使用口服减量糖皮质激素;单一静脉英夫利昔单抗(IFX)5 mg/kg[13]。我院住院的6 例IVIG耐药患者在分别给予第二次IVIG(3 例)或糖皮质激素(3 例)后均退热。目前,对于难治性KD的文献报道较多,尚无统一的定论。Ogata等[14]发现类固醇治疗对IVIG难治性患者具有快速、强有力的抗炎作用。静脉滴注糖皮质激素(IVMP)联合IVIG作为难治性川崎病的一线治疗方法,可以更广泛地抑制mRNA表达[1]。IFX是一种抗肿瘤坏死因子的生物药品,可作为治疗难治性KD患者的二线用药[1]。相比于第二次IVIG,IFX缩短了发热持续时间,但两组患者的冠状动脉瘤发生率接近[15]。对于难治性KD患者,IFX或类固醇治疗的效果明显优于第二次IVIG[16]。IFX能更有效地解决发热问题,但其冠状动脉后遗症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17]。环孢素(CyA)是一种免疫抑制剂。2011年,Suzuki等[11]采用CyA治疗IVIG难治性患者,认为口服CyA可以作为IVIG难治性治疗的三线药物,其中78.6%能达到临床退热效果。Hamada等[18]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IVIG+CyA作为严重KD的一线治疗方案治疗顽固性KD是有效的。第二次注射IVIG和第二次注射IFX后6周,冠状动脉瘤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有学者报道[1]乌司他丁(UTI)对KD的疗效更接近于支持性治疗,没有明显的退热作用;根据指南,UTI可作为二、三线药物与IVIG结合使用。在急性期KD的治疗指南中,血浆置换(PE)是IVIG难治性病例的三线治疗方法[1]。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和血浆置换被用于KD的难治性病例[2]。对于难治性病例,目前缺乏辅助治疗或二线治疗的证据,那些发展为CAA风险最高的病例,有望使用生物制剂治疗,特别是TNF-α和IL-1阻滞剂[2-3]。近年来,脂肪组织源性干细胞(ADSC)被证实具有抗炎、免疫抑制和组织修复的特性,可能为严重KD提供新的细胞治疗策略[19]。
KD患儿大部分可自行恢复,预后良好。Nakamura等[20]采用平板运动试验(TMET)研究了KD对儿童长期站立和/或运动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发现KD组和非KD组的运动耐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KD组患儿立位时血管收缩较弱或延迟,提示KD对患儿血管紧张度存在长期影响。合并有冠状动脉病变的KD患儿需长期随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