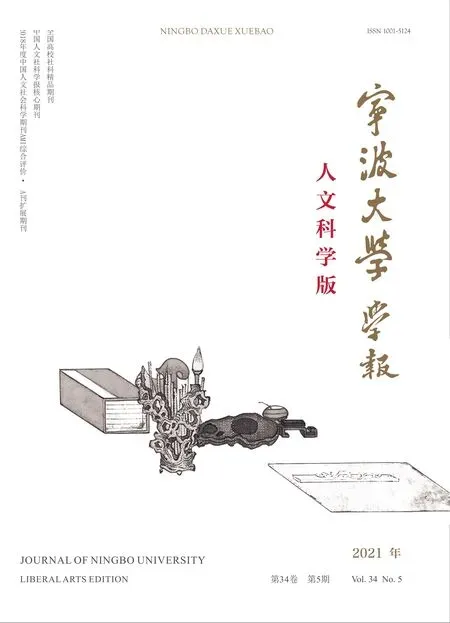初唐史家文论的建构策略
何长盛
初唐史家文论的建构策略
何长盛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初唐史家与一般的文论家有所不同,其文论观念有着浓厚的史学色彩。史家重新定位了“文”的意涵,指出了“文”具有“匡主和民”的作用,以及“述美恶”的史学功能,此种言说表明史家对“文”的功能的独特认识;同时他们将“文运”与“国运”的关系紧密联结,强调了文运的重要性;为了规制彼时文章写作的风格,他们在处理辞彩和内容的关系时,表现出较为矛盾的态度。初唐史家提出的这些文论观念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初唐史家;文学;国运;格调
初唐史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极具文才,善创作。如主撰《周书》的令狐德棻有“博贯文史”[1]3982的专长,与之类似的还有魏征、房玄龄、李延寿、李百药等人。初唐史家提出的文论观点也与其创作实践相关。较之其他文论家,初唐史家有较强的历史眼光,多从历史层面来审视“文”的作用与地位。在政权新创的阶段,他们对前代的文章写作得失进行深刻反思,提出极具问题意识的文论观念。关于初唐史家文论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他们观点的归纳和总结①,而对初唐文论家的建构策略探索较少。
一、“文”意涵的重新定位
先秦时期文史不分。汉代,《史记》中的某些历史叙事颇具文学性,与后世对史书所要求的“实录”精神仍有一定差距,这是司马迁史学观念的反映;但作为史家,司马迁对史学与文学之间差距的认识与后世还是有所差别的。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420,也表明了《史记》具有文学色彩。《史记》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也成为文学研究的素材。齐梁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对“文”的意涵进行了鉴定,他从原道、宗经、征圣等方面提出了为文应需恪守的原则,但这主要是从文学创作主体的行为而言的,而较少延伸到国家文制层面。
史家对“文”的定位在初唐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周书》中说:“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3]742这是令狐德棻的一种言说策略,他从天地两仪层面立论。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写到: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人,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忿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4]1729
魏征在此阐明了“文”内涵。他用《周易·贲卦》中“化成天下”的观点,引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人文”有风化天下的重要作用。这种观点与刘勰所言“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5]3相类似,皆是从文化角度来认识“文”的。为了指明“文”的含义,魏征从四重向度来叙述“文”的功能与价值。其一,从君主角度来讲,“文”可以教化下层民众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这也是汉儒思想的延续,与《诗大序》中的美教化、移风俗的观点是一致的。政治教化是儒家知识分子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结,化成天下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理想。不同时代的儒者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在旧有的文论中添入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材料。其二,从民众来说,“文”是向上传达情志的媒介,民众可以此传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得统治者可从“文”的内容中体察民情。“文”具有连接统治者和民众的沟通职能。其三,从处于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官员而言,“文”具有“匡主和民”的作用,所谓“匡主”,即指臣子可以凭借文章来劝诫匡正君主的过失,继承了汉儒以《诗》为谏书的思想,是谏政理念在初唐的继续阐发。这种从君臣关系立论在《文心雕龙》中较少出现。史家在文论中的谏政理念,也由此可窥。至于“和民”的思想,即孔子所言诗可以“兴观群怨”中的“群”,文士可以文会友,文章写作可以产生“群”的作用,由“群”进而达到“和”的状态。魏征显然借用了孔子的言说方式,提出以“文”和民,促进社会之稳定。其四,对于那些愤懑不得志的文士而言,创作“文”可以化解内心的苦痛。这与钟嵘《诗品序》所说“(诗)使穷贱易安”[6]卷首的功能相类似,即文艺创作有排解苦闷的作用。魏征认为文章写作对不得志的士人有着特殊的价值——“流风声于千载”。魏征从以上四个角度论述“文”的价值与功能,包括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对“匡主”的谏政精神给以较为明晰的阐发,这是其文论的独到之处,也是史家身份意识的表征。
房玄龄在《晋书》中指出,“文”不仅有化成天下的功用,还有移风易俗的作用[7]2369。初唐史家都认同“文”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作用。移风俗、美教化不仅是魏征和房玄龄的认识,作为史家的李延寿也有类似的观点。李氏在《南史·文学传》中指出,从大的层面而言,文章具有“宪章典诰”的作用,从小的层面讲具有“申抒性灵”的功能,还提出文章应该具有“通古今而述美恶”的作用[8]1761-1762。李延寿一方面重申了魏征、房玄龄关于“文”的看法,另一方面对“文”又有着新的认识,即它应有与《春秋》相似的功能。司马迁曾指出《春秋》具有“采善贬恶”[9]3299的功能,史学家对“文”赋予扬善惩恶的功能,是对文史合一形态的回归。但司马迁是以史书的体例来撰写《史记》的,只是在叙事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失控”[10],才造就了《史记》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而初唐史家显然是有意采取了这种具有复古意味的言说方式。因为唐代立国之初,人心思治,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在经历南北朝战乱之后又一次得以复苏。初唐史家自觉地回归儒家的政治教化之路,发挥“文”以载道的作用,因此化成天下是史家的愿景。刘勰《文心雕龙》侧重从个体审美角度对“文”的意涵给予确认,初唐史家对“文”的定义则从政治言说的角度切入,颇具政治美学的意味。
此外,王朝鼎革之际,复古主义往往会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多以儒家经典为矩镬,来拨正异端。唐初,不光史家有复古意识,其他文人也有此意识。诸如陈子昂在《感遇》诗中流露出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他主张恢复汉魏传统[11]15;李白提出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12]87。可见复古思潮在初唐已然成为一种“言说共同体”[13]155,史家深受影响。
初唐史家对“文”的定位,及对文史合流形态的倡导,影响了整个唐代的文学创作。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将“裨补时阙”作为自己的责任,使诗文辅时及物的功能进一步凸显。这种“诗史”精神也为后世具有济世情怀的儒家士人所继承,尤其是在王朝鼎革之际,诗与史的“互文性”写作成为了一种创作范式,譬如各个朝代出现的遗民诗,就是此种文化现象的折射。
二、文运与国运
无论是体制的因革还是内容的变化,文运皆与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初唐史家在评价前代文章时,往往采取寻根索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文章著述给以适当的评价。为修史能垂鉴后人,他们总能深入到著述现象的背后,从中寻绎出文运与时代、国运的关系。
魏征在《隋书》中指出文章著述呈现出“遭时制宜,质文迭用”的规律[4]903,认为文风与时代的关系极为密切。房玄龄在《晋书》中也对这一问题有独到的看法: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7]2346
自从晋代中期以来,由于崇尚华丽轻艳的文风,学者纷纷抛弃儒家经典而研习黄老之作,由此出现了轻视儒家经典、废弃礼法的风气。房氏指出,此种风气使得儒家纲常衰丧,使五胡有了可乘之机,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最终致使国家覆灭。从文风的变化来体察国家兴衰的道理,不仅是房玄龄的观点,也是初唐史学界的共识。李百药在《北齐书》指出梁末江左流行“弥尚轻险”“悲而不雅”的文风,从历史层面分析武平年间文采过甚、辞藻繁复的现象,指出这种文风出现与“政乖时蠹”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14]602。令狐德棻在《周书·儒林传》也认为推崇经术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他指出玄学盛行是晋代纲纪大坏的根由[3]805。
文运是指一个朝代的文教状况,与国家的“文治”秩序紧密相关,它往往与“武功”这一概念对举出现。提倡“武功”是维持国家政权的重要举措,但是国家的强盛也与文治密不可分。文运与国运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不少关于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的理论认为,社会现实是文学创作的来源和动力。刘勰在《物色》篇中所言的“江山之助”指出现实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5]695。清赵翼在《题元遗山集》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5]772。初唐史家所提出的观念与这些诗论家所言的并不完全相同。初唐史家关于文运与国运的看法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而言的,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话语构建,而刘勰等人的文论所言的是一种创作体会,是由个人创作经验升华。初唐史家从整个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并采取政令式的言说方式进行阐释。即初唐史家对文运与国运的看法是从国家层面上去考量的,而其他文论家是从作家个体创作经验的层面上去考量的。
对文运与国运关系的考量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颇为重视的事。统治阶层润色鸿业行为的出现就与之有一定关系。譬如汉大赋的出现,就与汉代统治者希图粉饰太平的心态有关,润色鸿业也成为一部分文臣的重要任务。初唐史家却与之不相同,初唐的“文运”从文治的角度上来说的,这与重新繁荣儒学的需求也有密切相关。因为初唐立国不久,史家更多地需要对前朝文弊进行反思,通过革新前朝文弊,为新朝的文德政治提供借鉴。陈飞先生指出:“‘史学’中的‘文学’则是‘文德’政治对‘文学’的要求在‘史学’系统的表达和实现。”[16]
初唐史家对文运与国运的现象予以关注,是他们希望将这种观念能够影响到当时的文章写作。彭亚非先生认为:“文治的实质是文化统治和精神统治,因此意识形态权力和话语权威的垄断非常重要。”[17]88唐太宗以国家政令要求修撰《五经正义》,其目的和初唐编撰史书的目的一样,皆是为了文化大一统的国家行为服务。经学在南北朝之际,南方和北方差异极大。《五经正义》的编撰,就是为了平亭南北学术的差异,以实现学术层面上的统一。有学者指出:“国家的分裂与政治的对抗性往往导致文化的分化与思想的对峙,而国家的统一也往往推出统一的思想文化。”[18]27初唐修史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也是国家大一统之后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初唐史家对文运与国运之关系的陈述是服从于唐初文治建设目标,其特点体现在:
第一,初唐史家文论是针对六朝文弊的。北周时期,宇文氏集团进行了文风革新运动,苏绰意欲采取复古的方式改造浮华的文风。隋文帝时期,李谔的《上隋文帝革文华书》是针对当时的轻浮文风有感而发,其目的也是为了革除绮靡的文风。初唐,史家继续北周和隋的文风革新运动,采用了更为理性的方式,吸收南北文风的长处,提出了“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创作追求。
第二,统治阶层对文风的影响。房玄龄在《晋书》中分析东汉文苑“主好斯文,朝多君子”[7]2346,强调统治阶层对文风的影响。党圣元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帝王的崇尚和提倡对文学产生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19]魏征认为梁代大同年间之后,出现了体格卑下的文风,其根源就在于梁朝统治阶层对此种文风的喜好,“简文、湘东启其淫放”[4]1730。对绮艳文风的爱好是齐梁文风颓靡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百药在分析宫体诗时,指出此种体裁的出现,“盖随君上之情欲也”[14]602。的确,萧氏集团的文学爱好对宫体诗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对传统乐论思想资源的有效利用。据《左传》记载,季札通过观乐就能推断国运昌明与否,比如当他听到郑声“其细已甚”,推断郑国政令繁冗,亡国不远;听到齐乐“泱泱”,不禁赞叹齐国政令畅通,必为繁盛之邦。上古时代诗乐舞一体,由于古乐的失传,诗与乐分离,但乐与政通在古代却比较常见。汉代《礼记·乐记》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20]978。此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提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5]102,强调诗歌和音乐的紧密联系。唐代,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尤为凸显。初唐曾参与过修史工作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乐一体”“诗乐同其功”[21]11。乐与国运相通,而乐又跟诗(文)相关,由此,文运与国运相关,即文章著述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联。从历史资源中寻求有效的材料,以此佐证自己言说的合法性,是史家构建文论体系的重要方式。
将文运与国运联系起来是史家有意识的言说行为,这是他们构建礼乐文化系统的话语策略。惟有如此,他们方可将文章赋予浓厚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更好地为新建立的政权发挥风化天下的文化职能。
三、对文风的规制
初唐史家品评唐之前的文风,试图提炼一种理论范式。对辞彩与格调二者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初唐史家对待文章风格的态度。传统文论认为文彩与格调似乎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辞彩过甚则格调会显得卑下。尽管刘勰对屈原的辞彩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在《文心雕龙·辨骚》篇认为《楚辞》有四个方面不合乎经典。魏征在《隋书》中认为屈原“后之文人,咸不能逮”[4]1056。魏征认为屈原不但才气过人,而且格调雅致清远,后世文人很难超越。令狐德棻亦认为屈原有“恻隐之美”,并对效仿屈原的宋玉评价甚高[3]743。刘勰虽然对屈原有褒奖之意,但也对《离骚》未能宗经的四个方面提出了批评,而初唐史家对屈原则采取了全面褒扬的态度。魏征指出:“文章乃政化之黼黻。”[4]909将文学看作政治的辅助性工具,提升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因此他们崇尚质朴的文风,贬抑那些文辞华丽的作品。然而对屈原等人的华丽辞藻却予以赞扬。这种理论言说所显现的矛盾之处,有着怎样的原因?
初唐史家在撰写文学传序时,尽管从历史的维度去评价文章带有某种重返政治教化的意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忽视了文章的审美特性。文章的审美倾向至魏晋之后颇为突出,骈文显示出文章的形式美风向。初唐以来,文章更是沿着重视声情、辞彩的方向发展,魏征等人虽站在宗经复古立场,强调文章的质实朴茂和政治教化,但他们也认识到文章审美属性的重要性。不仅是屈原,其他文采过人的文士也受到了初唐史家青睐。房玄龄在《晋书》中颇为认可那些“缛藻霞焕”的文人。然而,对那些颓靡的文风,初唐史家给予了尖锐的批判。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就批判了梁代大同以来的文风。梁代萧氏集团的诗歌辞藻华丽,但内容不符合雅正的要求,魏征还是将其贬低为亡国之音,这与齐梁之际文风的格调低下有关。令狐德棻在《周书·庾信传》认为庾信文章的格调低下,类似于郑、卫的亡国之音,并全面否定庾信,认为他是“词赋之罪人也”[3]744。因为在令狐氏看来,庾信的文章风格以淫放为本,辞藻以轻险为宗,这是亡国之音的表现。可见格调的高低成为了评价文风的重要标尺。
初唐史家提出格高、调高的概念标正文章的方向。魏征在《隋书·文学传》中认为王胄等人“学优命薄,调高位下”[4]1750,但魏征在《隋书》还是给他们立传,是因为这些人具有“调高位下”的特点。“调高”是指这些人的文章格调高远。魏征格外推崇“调高”之作,其实就是初唐史家对文风的一种现实规制。令狐德棻在《周书·庾信传》特别推崇屈原、宋玉等词人的辞彩,指出他们的作品具有“调也尚远”“旨也在深”[3]745的特点。他之所以认为屈原等人的作品能够流传久远,“调也尚远”是一个重要条件。可见,初唐史家有意识地追求文章的格调,对唐代中后期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22]117贞观末期,唐代文学有“格高”的特点,而到景云年间表现出“调远”的文学样态。史家所提倡的“格高远调”的文学标准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较为深远,陈子昂、李白、杜甫的诗文都有这样的特色。
令狐德棻还在格高调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声实俱茂,词义典正”[3]744的审美标准。他高度赞扬了许谦、高允等人,就因为他们的作品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而“词义典正”是从内容上说的,是指作品内容的雅正。这与魏征所言的“文质彬彬”具有一致性,都体现了初唐史家重视写作中文质关系的特点,希望使文章写作走上尽善尽美的道路。为此,令狐德棻还从儒家的中庸思想出发来规划文章写作的审美属性。他从文与质、繁与约、轻与重、古与今等种种关系来考察文章的体制。要求作家在考量以上诸因素的基础上,使文章达到“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艺术风貌,这与齐梁之际的文风并不相同。令狐德棻还对文章的色彩和声律也提出了要求。要求文章能够如“五色之成章”,这是对色彩美的强调。而他所提出的“八音之繁会”则体现对声律美的重视[3]745。
盛唐文学标举风骨、重视兴象,讲究声情并茂、文质彬彬的艺术风格与令狐德棻等人所言极为相似。令狐德棻等人的理论预示着盛唐文学的到来。如杜甫所言“窃攀屈宋宜方驾”表达了对屈原、宋玉的追慕之情,“转益多师是汝师”充分表现了杜甫熔铸众家之长的集大成气魄,这些艺术风尚与初唐史家的调和观点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
四、结语
初唐史家在文论方面的开掘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史家对“文”意涵的重新定位,标志着他们对“文”有着新的认识。由于在政权新创的特殊时期,他们对待“文”更多地从治国安邦的角度出发,寻绎往代文章写作的经验和教训,以使新朝的文章写作不再重蹈齐梁的途辙。他们对文风的规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亦是沿着这个思路出发的。他们希望将“文”纳入礼乐文化,以此发挥“文”化成天下。此外,初唐史家还提炼出“格高调远”,深刻地影响着有唐一代的文学发展。在对待文与质的关系时,史家也出现理论上的矛盾性,他们在极力敷陈文风朴实的重要性,但又难免显露了对华美辞藻的歆羡。究其原因,初唐文学整体向着审美方向的发展,但作为史学家,他们有着深刻的身份认同,不得不通过消解文学的审美特性来深化文学的实际功能。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112页),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6-397页),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25页),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0页),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262-267页)等著作都谈到了初唐史家的文学观念,但其侧重点在于对这些观念的总结与介绍,而对史家文论话语提出的逻辑及其建构方式尚未细致探析。陈飞《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与实现——以早期史学为中心》(《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认为唐初史家的文学建设是在“文德”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它完成了唐代文学“概念”系统的构建。刘绍瑾、王钰莹《唐初史家文学观与创作实践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指出唐初史家开启了唐代复古主义文学的先声。
[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董家遵,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3] 令狐德棻. 周书[M]. 唐长孺, 陈仲安, 石泉, 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4] 魏征. 隋书[M]. 汪绍楹, 阴法鲁, 邓经元,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5]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6] 陈延杰. 诗品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7] 房玄龄. 晋书[M]. 吴则虞, 杨伯峻, 陈仲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8] 李延寿. 南史[M]. 王仲荦, 卢振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9] 司马迁. 史记[M]. 顾颉刚, 贺次君, 宋云彬,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0]程苏东. 文本的失控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 164-184.
[11]陈子昂. 陈子昂集[M]. 徐鹏,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12]李白. 李太白全集[M]. 王琦,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3]哈罗德·罗伊生. 群氓之旅——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 邓伯宸,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4]李百药. 北齐书[M]. 唐长孺, 陈仲安, 石泉, 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5]赵翼. 瓯北集[M]. 李学颖, 曹光甫,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6]陈飞. 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和实现[J]. 文学遗产, 2005(3): 86-96.
[17]彭亚非. 中国正统文学观念[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8]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隋唐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9]党圣元. 通变与时序[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6): 46-55.
[20]孙希旦. 礼记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1]孔颖达. 十三经注疏: 毛诗正义[M].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整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1999.
[22]傅璇琮, 李珍华. 河岳英灵集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Historian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arly Tang
HE Chang-sheng
(School of Art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literary theorists,the literary theory of historian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Historians of early Tang dynasty have redefined the meaning of “floweriness” revealing that it plays the function of aiding ruling, harmonizing people and the historical function of beaty narration. In order to plan the style of writing at that time, they fell into the dilemma of logic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ction and content. These ideas of literary theory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historian of early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national fortune, style
2020-09-23
何长盛(1989-),男,山西忻州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论。E-mail:1304056578@qq.com
I206.2
A
1001 - 5124(2021)05 - 0082 - 06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