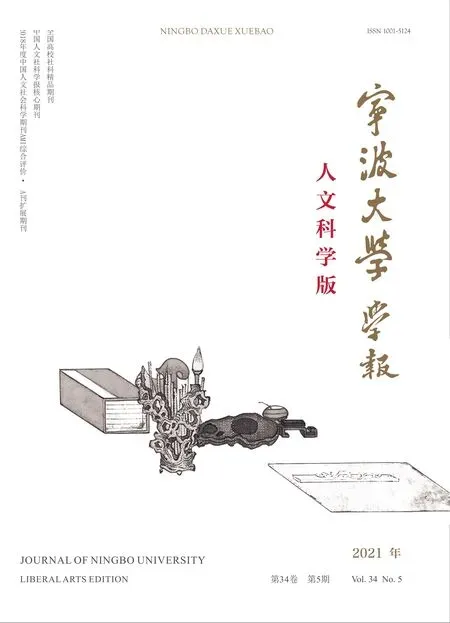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陈佳璐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的叙述形式
陈佳璐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家人离世和濒临死亡的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复活的渴望。尼·费奥多罗夫提出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坚定了他的复活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信仰复活,其作品也蕴含着精神复活的主题。“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简练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等共同建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活主题。“消失的”时间强化了小说的精神氛围,内视角展现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概括的景物描写和“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主观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主题;时间;内视角;自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均涉及到了人物精神复活的问题,即人物从对权力、欲望等的执迷转变为选择十字架,回归信仰上帝的道路上。学界多从内容①、信仰来源②、逻辑演绎③和东正教④等方面探讨其作品中的复活主题,但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在小说中以叙述来呈现复活主题则较少提及。本文试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生活和思想变化中探究其与复活主题的关联及其在叙述形式方面的构建。
一、复活信仰的来源与内涵
(一)人世之伤
复活作为宗教话题,是东正教信仰的重要部分。在东正教神学中,复活不仅寄寓了希望,也具有现实性。基督复活是人们相信复活的前提。俄罗斯神学家涅斯梅洛夫认为圣父的意志、神子的个性、人本质的永恒统一,以及作为新亚当的基督使得基督复活与人的复活联系起来,前者预示了后者的实现[1]279-286。另一位神学家弗·洛斯基曾写道:“自从基督战胜死亡之后,复活已变成了造物的普遍法律;不仅对于人,而且对于动物、植物和石块,对于整个宇宙都是如此……救赎意味着一场生命反对死亡的斗争,以及生命的胜利……道成肉身和复活,死亡被削弱了,不再是绝对的。”[2]96-98
复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中心话语,意味着“皈依上帝这一道德美和人性善的化身,意味着人性得以复苏,精神走向新生”[3]103。王志耕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灵魂的永生,人由堕落到复活的变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基督教人类学理论对时间中人的一种集中概括[4]104。张变革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话语就是人经历苦难并获得精神复活[5]51。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如果没有永恒和灵魂不死,就没有罪与罚的阶段,道德体系也会因此崩溃,人类社会将陷入混乱[6]4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年时期曾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宣扬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被抓捕后,一场精心策划的“假死刑”使他经历了一次“复活”,也给予了他常人难以体会到的精神感受。他在结束苦役后给一位十二月党人妻子写道:“在这种时刻,人就像一棵‘枯草’,渴求信仰,而且他也能找到信仰,这正是因为在不幸中真理显得明晰了……在这种时刻我在自己心中建立了一个信条……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加美好、更加深刻……”[7]145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寻求宗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活信仰和他妻子的死亡有着紧密的关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因肺结核而死于圣周期间。他面对着死去的妻子,由圣餐典礼想到了耶稣的复活,进而想到了人类的复活。1864年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非比寻常。同年,哥哥米哈伊尔猝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要开始接管《时世》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偿还杂志的债务,还要承担起照顾哥哥遗孀的责任。1849年的“死刑”经历和1864年的丧亲之痛联系了起来,濒临死亡的体验和丧失亲人的悲痛使作家产生了对信仰的需要和对复活的强烈期望。因此,复活就成为了作家解决疑问和痛苦的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活主张深深扎根于他的生活经历,具有十分明显的个体性。
在生命的晚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作家日记》发表过一篇虚构小说《判决》,设想了一个缺乏永生信念的青年如何由于丧失对生活的希望而自杀的故事,以此来强调复活信仰的重要性。但是,这篇作品并未受到大众的理解。因此,他在回应文章里做出了关于复活的重要宣言:“只有有了灵魂不死的信念的人才能够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全部合乎理性的目的……总之,灵魂不死的思想——这就是生活自身,就是生机勃勃的生活,是生活的最确切的表述,是真理和人类的正确意识的主要源泉。”[8]542另外,在1878年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一位农场主讲述了为何复活是必然的原因。他写道:“如果我定将在大地上完全死去,我又何必好好地生活和行善……我为什么(如果只要凭我的灵活和聪明就可逃脱法网)不去杀人,不去抢劫和偷盗……要知道我是会死去的,一切都会死去,一切都将不存在!”[7]1057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相信复活是必然存在的,是因为它是生活的真理和善念的来源。复活是人类生存最基本和最高的理念,它能抵抗虚无的猛烈侵袭,避免自杀和犯罪。
(二)尼·费奥多罗夫的复活事业哲学
俄罗斯哲学家尼·费奥多罗夫(N. Fyodorov)的复活事业的哲学也影响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罗夫将复活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他相信复活并不是基督教里带有空灵性和神秘性的复活,而是完全可以从实证角度出发,具有操作性的一项方案性事业。首先,他指出自然的盲目力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当我们还软弱无力、尚未成为它的意志之时,它是一种强大力量,当我们缺乏理性,尚未给它赋予理性之时,它是一种盲目力量。”[9]73在自然力量的桎梏下,死亡就成为了人类最大的不幸。费奥多罗夫认为死是一种最大的不道德。因此,他否定死亡的绝对性,不认为死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种状态。“死对于死去的人来说是一个在身体朽坏分解意义上的事实,但这不是终结;对于我们活着的子辈来说,死亡则是一种外部现象,人必有死只是一种归纳认识,复活则是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自然回答。”[9]132费奥多罗夫进而将“人必有一死”变成了“人本应不死”。他相信人是“超自然的理性存在”,而“理性是宇宙演化的结果,同时是宇宙过程的新质阶段,理性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因此理性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能改造自然物,支配自然力,逐步使世界由自在的世界变成自治的理性的世界……随着世界从自在走向自为,随着人类从‘未成年状态’进入‘成年状态’,打破死亡之必然性,达到长生不死,便是可以想象的了”[9]133。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尼·彼得松将费奥多罗夫的复活事业理念介绍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起了后者的极大关注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8年3月24日给彼得松回了信,写道自己十分赞同费奥多罗夫的复活理念,还强调了“我们即我和索洛维约夫至少是相信现实的实在的个人复活,也相信它一定会在大地上实现”[7]1063。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复活的希冀也反映到了他的小说创作里。经历过第一任妻子和哥哥的离世后,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于1978年失去了他的幼子阿列克谢。悲痛至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塑造了阿辽沙这个人物,而阿辽沙正是阿列克谢的小名。在小说结尾,阿辽沙身边围绕着一群儿童。他们刚参加完小男孩伊柳沙的葬礼。阿辽沙安慰着这群悲伤的孩子,向他们保证以后一定会再次见面。他说道:“我们一定能复活,一定能彼此相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互相讲述经过的事情。”[10]929
二、叙述“复活”:时间、内视角与自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复活主题的呈现方式主要由“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的运用以及对自然描写的艺术处理组成。
(一)“消失的”时间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复活主题的呈现中,时间是需要被重新认识和体验的事物。他对小说时间的处理体现了东正教独特的时间观念。东正教神学将时间视为上帝的造物而非凌驾于上帝的统治力量。时间是一种被上帝创造的存在形式,而永恒属于上帝[2]45-46。东正教神学否认在永恒中时间的变化——变成非活动性、静止性,它所相信的是活着的永恒,“一种必须超越流动的时间和静止的永恒之间的对立”[2]46。别尔嘉耶夫则提出“不能把永恒时间化,也不能把终结客体化:生存时间可以用主体的张力和强度来衡量,只有在这样的生存时间里才可能敞开通向永恒的出路,在历史和宇宙时间里无法思考终结”[11]17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中,复活的时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的、线性的时间,而是一种被意识和精神强度所充实的时间。这样的时间不是以均衡的速度流逝,而是极不规律地进行着自身的运动。在《白痴》里,身患绝症的伊波利特意欲宣读自己的自白书,小说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建议他明天再读,但伊波利特回答道:“明天‘不再有时日了’!”[12]436这句话源自《启示录》。其中,人们面临上帝的大清算,死亡即将到来,恶人堕入地狱,义人得到救赎,时间也在上帝的干预下停止。丽莎·克纳普(Liza Knapp)指出时间对于取消自然法则的重要性。“自然法则是否存在,机械法则是否成立,都取决于时间的有无。《启示录》承诺使时间终结,使行星脱离其轨道,这意味着自然法则的中断。”[13]132而伊波利特说出“不再有时日了”,则是希望自己进入《启示录》中的情景,呼唤神对自己进行审判。他希望凭借自己助人的善行,能够获得死后的永恒生命。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的是宗教意义上的时间观,对于世俗时间和空间的消灭不能依靠技术手段,而是应该凭借对基督再临的信仰来实现。
对于时间停止的展现还见于梅什金公爵发癫痫前的精神状态。公爵认为这种奇异的感受充满了和谐与希望。
在那些持续时间不比闪电更长的瞬息中,生命的感觉、对自我的意识似乎增强十倍。思想和心灵被一种异光所照亮,他所有的激动、所有的怀疑和所有的不安顿时都告平息,化为最高级的安谧,充满明朗、和谐的欣悦和希望,充满理智和最终的答案……的确是最高级的和谐、最高级的美,能提供迄今为止闻所未闻、亦无人猜透的充实感和分寸感,使你觉得同最高级的生命综合物重归于好,在虔诚的极乐中与之融为一体。……凭他充分感觉到的无限的幸福,这一秒钟恐怕抵得上一生的价值。[12]259-260
虽然事后有巨大的痛苦,但梅什金公爵仍坚信,为了这一秒钟不妨付出一生。他感叹道:“在这一刹那,我好像懂得了一句不寻常的话:不再有时日了。想必,这正是穆罕默德钵子里的水还来不及泼翻,而这位患癫痫的先知已经把安拉的住处览遍的那一秒钟。”[12]260梅什金公爵发病之前的感受是生命力度的极大强化,他通过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意识强度迎来出神的时刻,以致意志被湮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表明复活将意味着废除时间对于人的常规掌控,使高度集中和强烈的意识取代线性的、平均流动的物理时间,从而让人获得美与和谐的宗教体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消失的”时间来建构复活主题。米德尔顿·默里(Middleton Murry)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进行创作时并不遵守时间的规则,作品里人物的精神转变不能以地球上的时间加以衡量。“物理时间与蕴含在其中的精神内容达成了一致,这样的同一是不可思议且不真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受时间的管控,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夜晚和白天,太阳从未落下也从未升起。”[14]169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描写人物的心灵复苏,所以具有深刻含义的事件在历史时间和传记体时间里不可能得到完全展现。他呈现的是狂欢化的时间,其中包含着无数彻底的更替和根本变化[15]235。
除了《白痴》以外,《罪与罚》这部作品也充分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间艺术的高度浓缩性,导致时间“消失”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的时间跨度非常短。除去拉斯柯尔尼科夫生病的几天,《罪与罚》里所有事件总共在约九天半里发生。第一章讲述了头三天发生的事情,第二章讲述了第四天到第五天的事情,第三章只讲述了第六天早上七点到黄昏时分的事,而第四章则是从第六天傍晚到第七天中午所发生的事情,第五章交代了第七天的事,第六章讲述了第八天到第九天下午六点的事。菲利普·纳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创作的目的而压制了时间,使读者们不会特地注意到各个行动间的时间间隔长度。
事实上,《罪与罚》中没有真实的时间间隔,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持续并扩张的意识,其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紧密联系。有研究者指出,这部小说的时间纯粹是心理的,是人类意识的功能运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地将时间转换成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断变化的心理状态[16]104。
为了突出人物的思想意识变化,心理描写几乎充斥在整部小说之中,与密集的事件和长篇幅的内心独白相对应的是时间的隐形和压缩。时间在小说中仅有提示的作用,它本身不会对人物产生实质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切入小说叙述进程的第二天:“他(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夜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很迟才醒来。”[17]22紧接着,他开始描述主人公的心境。“但是睡眠并没有使他精神恢复。他醒来后,肝火旺盛,变得暴躁而又凶恶。他憎恨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斗室。”[17]22-23当天晚上,拉斯柯尔尼科夫从干草市场回到家后,他直接在沙发上睡到了第三天早上十点钟。女仆娜斯塔西雅把他叫醒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女仆就进行了几句简单的对话。之后,他头脑里不断地出现各种幻想,稀奇古怪的幻想[17]56。就这样,拉斯柯尔尼科夫沉浸于想象之中,这种状态直到下午六点才结束。而从早上到下午之间的描写只有寥寥数行的对话和一小段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幻想内容的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而是写道“也许已经敲过六点钟”[17]57。“也许”二字突出了时间的模糊性,显现出时间在小说里的弱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着墨于无关紧要的事件,不追求宏大全知的史诗时间。迈克尔·霍奎斯特(Micheal Holquist)也指出,在小说结尾里作者用几句话就讲述了几年的事情,而在其余的部分,几分钟的内容就占据了数页的篇幅[18]112-114。陀思妥耶夫斯基无闲笔的叙述风格削减了小说中多余的部分,使人物的内心活动更加突出,有助于构建复活主题。
(二)内视角的运用
内视角作为一种叙述视角,是指叙述者从人物意识的角度来进行叙述[19]214。它能深入到人物的视野来观照其他人物和外部环境,这样的叙述带上了人物本身的感情色彩和意识[20]20。《罪与罚》虽然以第三人称来叙述,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频繁使用内视角,使人物的精神世界完全敞开,有利于展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复活历程。
索尼娅的两次出场也从侧面反衬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变化。索尼娅第一次出场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当时同样在现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可能没有看见她。但是,作品并未给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于索尼娅的初次印象,取而代之的是叙述者对于索尼娅的描写。实际上,拉斯柯尔尼科夫内视角的消失就代表了他的看法。也就是说,在第一次见面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想法与叙述者是一致的,因此也就不用再通过内视角进行赘述。但是,索尼娅的第二次出场则改变了他原先的看法。索尼娅从一个妓女成为了一个柔顺的小姑娘,以致于当她害怕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到难过极了。这时,他也从之前冷漠无情的旁观者变成了关心索尼娅的人。通过内视角的运用,小说生动细致地展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变化。索尼娅的出现召唤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同情心,也暗示了她之后会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复活之路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听取索尼娅的建议到大街上向人们磕头认罪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通过内视角呈现了他那时的心理活动,直观地凸显了复活主题。小说里写道:
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在干草市场里,心情不再像之前那样烦闷。
他忽然想起了索尼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们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凶手!”……这种感情像疾病发作一样,在他心里骤然涌现出来:像一星火花在心灵里燃烧起来,突然像火一样燃遍了全身。他一下子浑身瘫软了,泪如泉涌。他立即在地上伏倒了……他跪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他站了起来,又跪下磕头。[17]466
其中,“疾病发作”“骤然涌现”“燃遍”“瘫软”“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展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经历自己的精神复活时的非凡体验,他勇敢地走向了以承受苦难为代价的复活。这一段内视角叙述将《罪与罚》的复活主题表达得最为明确。
(三)简练的景物描写与“复活的”自然
茨威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缺少泛神论因素,人物生活在永无止境的感情之中,他们的领域是心灵世界而不是大自然,他们的世界仅仅是人[21]122-123。季星星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时也提到作品中的景物描写几乎为零[22]141。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缺乏景物描写,也不缺乏泛神论的因素。但是,作家为了突出人物的精神,把景物描写进行了压缩的处理。作品中有具体景物描写的地方往往都是一种精神化的景物,这在作家的后期作品中尤甚。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外界事物的客观呈现通常是极具概括性的,他不注重描绘细节,而是简短地体现事物的概况。在《罪与罚》中,有多处可以体现作家描绘自然景色的特点。它们往往是速写式的描写,不会被细致地呈现。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马路上莫名其妙地挨了马车夫的一鞭子后注视着涅瓦河的景色。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河水几乎是蓝色的,在涅瓦河里,这是很少见的。”[17]95他没有继续展开景色描写,转而开始交代此时主人公的内心思想。在这个段落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将涅瓦河的景观概括为“壮丽的景色”,“华丽的画面”,语言单调并且缺乏表现力。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被突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注视涅瓦河的感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呈现精神化的自然时往往描写得很具体。这类自然描写往往在人物精神复苏时出现。不过,这时的自然不可视为通过外视角进行描述的客观对象,而是浸透了人物的思想意识,通过人物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和体验的自然。相对于小说中的其他部分,对于人物在体验精神复活时所看到的自然的描写会更细致,具有诗一般的意境。这样的自然描写还承担了宗教性的功能作用,即通过大自然的优美和谐向人物展现上帝的伟力,促使人物从思想迷雾中回归宗教信仰。“复活的”自然本质上是上帝对人的显现,是通往精神复活的道路。
“复活的”自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阿辽沙亲吻大地的情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阿辽沙在睡梦中进入了迦拿喜宴里的场景,见到了逝去的佐西马长老。他看到耶稣把水变成了酒,并不断地召唤着新的客人前来,因此感受到了耶稣对人们欢乐的珍视。喜宴上的欢乐冲淡了阿辽沙原本苦闷的心绪,狂喜的热泪从他的灵魂深处迸涌……接着,阿辽沙走出了修室,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病例5 男性,32岁。因“反复发作性上腹疼痛半年,再发3 d”入院。近半年来患者反复发作性上腹疼痛4次,曾在当地住院行胰酶、CT等检查,诊断AP,但病因不详。每次均住院治疗1~2周后好转出院。3 d前腹痛再发,为进一步明确病因收住院。入院后MRCP、EUS等检查排除复发性胰腺炎的常见病因,CA19-9显著升高,复查CECT薄层和MRI,提示胰尾部占位(图5),转外科手术,确诊为胰腺癌。
在他的上空,广袤无垠地伸展着星光柔和的天穹。从天顶到天机,银河分成模糊不清的两股。空气清新、万籁俱寂的凉夜紧紧拥抱着大地。礼拜堂的白色塔楼、金色圆顶与深蓝色的天幕交相辉映。屋前花坛中浓艳的秋花已入梦乡直要到天明。大地的静谧与天空的静谧融合为一体,泥土的秘密与星星的秘密交织在一起……阿辽沙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的一切,倏地像被砍倒似地趴了下来,贴在地上……他越来越分明地感到有一股坚定的、像这天穹一样不可动摇的力量正在注入他的灵魂。“在那一时刻,有人曾到我心中来过。”此后他一再如此说,并对自己的话坚信不移。[10]437-438
此段描写将东正教思想中“尘世教堂与天上教堂的绝对统一”的观念呈现出来了。正教的神学思想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不是根据图纸而是根据灵感,其过程充满了喜悦。尘世的生灵都吸收了上帝的呼吸、喜悦和恩惠,所以人不应该厌恶尘世,应把尘世当成唤起不灭之狂热兴奋的上帝的艺术作品来接受[23]187。阿辽沙的神秘体验有着东正教的思想基础。珍·凯洛格(Jean Kellogg)指出大自然的变容体现了俄罗斯思想具有的神圣大地的观念,而这源于古老的拜占庭教会。东方教父们将基督视为全能者,他使人类和大地都变得神圣。佐西马提出的地上的天国正是拜占庭教会的观点。世间既是天堂,而人类永远会直接地受到上帝圣光的照耀[24]139。阿辽沙原本因为佐西马长老尸体的腐臭而开始质疑上帝,想要抛弃信仰。但是在他做了迦拿喜宴的梦,并且在梦中见到逝去的佐西马长老和耶稣之后,信仰又开始逐渐地在他心中凝聚起来。当他看到了室外的自然景色之后,阿辽沙完成了自己的灵悟过程,和上帝进行了一次神秘的接触,使信仰得到了复活。“星光柔和的天穹”“银河”“空气清新、万籁俱寂的凉夜”“大地”“深蓝色的天幕”“浓艳的秋花”“泥土”和“星星”与阿辽沙同处于一个自然空间中。“礼拜堂的白色塔楼”意味着上帝的在场,它使人与上帝的精神交融成为可能。修道院外的自然构成了“人间天堂”的场景。上帝在塔楼上凝望着人间。伏倒在地的阿辽沙注视着天空、大地、泥土和星星。上帝通过自然将自己的喜悦传递给了阿辽沙,使后者与自然形成了某种秘密的、神性的联结。阿辽沙感到了上帝的触摸,他亲吻着蕴含有上帝力量的大地,和佐西马一样满怀热泪。这一切使站起来的阿辽沙成为了一个坚定的信仰战士,决心去人间传播爱的事业。
自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不是被呈现的对象,而是浸透了人物情感和精神内容的主观化投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眼中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客观景物描写。相反,它们是被赋予了宗教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符号。同时,简练概括的景物描写和细腻动人的“复活的”自然描写共同作用,形成了文本的描写张力和精神强度,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活主题营造了浓烈的氛围。
三、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致力于描写人物的精神复苏过程,这构成了他的复活主题。在叙述过程中,作家通过“消失的”时间,内视角的运用,景物描写的压缩和“复活的”自然来加强人物的思想意识。“消失的”时间凸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叙述故事的经济性,加快了叙事节奏;内视角直接从内展现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使小说成为了主人公的内心戏剧;简练的景物描写和细腻的“复活的”自然描写弱化了小说的现实感,也突出了自然的宗教功能和精神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活主题不仅在内容和情节走向等方面得到了体现,在小说的形式层面也同样为其搭建好了稳固的架构。内容没有大过作品的形式,而是和形式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塑造的统一体。
① 王志耕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灵魂的永生,人由堕落到复活的变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基督教人类学理论对于人的一种集中概括。同时,他还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其原型是地狱—炼狱—天堂,由堕落到复活的阶段就对应了炼狱的阶段。参见:王志耕《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5卷第3期第98-108页。张变革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话语中,犯罪和惩罚是人产生精神复活的契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话语就是人经历苦难并获得精神复活。参见:张变革《惊险情节中完成“罪与罚”的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赏析》,《名作欣赏》2013年第34卷第2期第50-52页。汪剑钊在分析《白痴》里的末世论思想时,强调了死亡对于复活的重要性,他指出纳斯塔霞的死亡其实是新生的萌芽状态,死亡就意味着复活,她用自己的死亡克服了心灵的死亡状态。参见:汪剑钊《美将拯救世界——〈白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末世论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6卷第1期第55-62页。卢群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活主题下了定义,提出主人公门的生命轨迹是堕落(死亡)—忏悔—人性回归(新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对死亡必然性和道德沦丧的恐惧而才产生了灵魂不死的信仰。参见:卢群《“一粒麦子”的哲学——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复活主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27卷第4期第102-105页;卢群《死亡边缘的思考——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不死”观》,《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2卷第2期第42-45页。
② 俄罗斯当代文艺学家谢苗诺娃认为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费多洛维奇·费奥多罗夫的复活事业哲学对于作家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有着影响。谢苗诺娃梳理了二人的精神交往史,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对费奥多罗夫的思想十分感兴趣,在信中提到自己完全赞同这些思想。后者对复活的设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并在小说创作中反应了出来。参见:C. G. 谢苗诺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之最高理念”》,郭小诗译,张变革主编《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249页。
③ 詹姆斯·J·斯坎伦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理性的论证来为永生辩护,即道德完善的要求,神圣正义,人类的正常条件,对于有机体的保存,人类意识的独特及对于道德的需要。参见:James S《Dostoevsky’s Arguments for Immortality》,The Russian Review,2000年,第59卷第1期第1-20页。
④ 林精华指出《罪与罚》体现了东正教对于俄罗斯的深刻影响。即使最底层的民众也会在启示录感召下获得一种灵魂上的“复活”。参见:林精华《末世论和复活:后苏联文学与俄国东正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7卷第1期第23-29页。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提出永生与人格主义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联结。永生不能被时间化,终结也不能被客体化。生存时间应该用主体的张力和强度来衡量,这样才能敞开通向永恒的出路。人们不能割裂时间。只有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永恒中,“婴孩的眼泪”才能得到认可。参见:耿海英《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92-93。俄罗斯当代著名的陀学研究专家塔吉亚娜·卡萨特金娜指出,小男孩伊柳沙死去时手摆放的姿势使人联想到领圣餐时双手的姿势。她认为小狗茹奇卡的重现,以及伊柳沙死去没有发出腐臭味道的事情凸显了作品的复活主题。参见:塔·卡萨特金娜,张变革《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作为创作手法的“主人公的错误”》。《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38卷第3期,第41-51页。
⑤据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可以发现,彼得松在1878年的3月3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寄书给他当时工作的克伦斯克图书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3月34日的回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彼得松询问他介绍给自己的这位思想家是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对这位思想家的积极回应来看,这位思想家应该就是费奥多罗夫。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这位思想家相信最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复活祖先的责任。这个使命完成了,生育就会被终止。而复活祖先和终止生育正是费奥多罗夫复活事业哲学里的重要特征。俄罗斯20世纪的重要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也指出了费奥多罗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在他1928年发表的文章里,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同费奥多罗夫的思想,并愿意把它当做是自己的观点予以接受。参见:Nicholas B《N. F. Fedorov》,The Russian Review,1950年,第9卷第2期第124-130页。
[1] 张百春.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2] 弗·洛斯基. 东正教神学导论[M]. 杨德友,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3] 卢群. “一粒麦子”的哲学——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复活主题[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27(4): 102-105.
[4] 王志耕. 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J]. 外国文学评论, 2001, 15(3): 98-108.
[5] 张变革. 惊险情节中完成“罪与罚”的探索[J]. 名作欣赏, 2013, 34(2): 50-52.
[6] 卢群. 死亡边缘的思考——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不死”观[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12(2): 42-45.
[7] 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信集[M]//陈燊.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郑文樾,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8]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家日记: 上[M]//陈燊.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张羽,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9] 徐凤林. 复活事业的哲学: 费奥多罗夫哲学思想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0]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M]. 荣如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1]耿海英.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12]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M]. 荣如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13]丽莎·克纳普. 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M]. 季广茂,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14]MURRY M. Introductory[C]//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 Vol. 2.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4.
[15]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M]. 白春仁,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6]PHILIP R. Dostoevsky in “Crime and Punishment”[C]//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 Vol. 7.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4.
[17]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M]. 岳麟,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6.
[18]MICHAEL H. Dostoevsky and the novel[C]//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 Vol. 2.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4.
[19]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0]阮永健. 论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话性的叙事艺术特征[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 2004, 25(2): 20-21.
[21]茨威格. 六大师[M]. 黄明嘉,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22]季星星.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3]赵桂莲. 漂泊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4]JEAN K. The Opposite predictions—Ivan and Zossima[C]//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 Vol. 43.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4.
The Narrative Form of the Resurrection Theme of Dostoevsky
CHEN Jia-lu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The death of Dostoevsky’s family and his own near-death experience prompt his desire for resurrection. In addition, the resurrection career proposed by Fyodorov also strengthened his belief of resurrection. He believed in resurrection and his novels also contained the theme of spiritual resurrection. This essay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at the “vanishing” time, internal focalization, the brief scenery description and the resurgent nature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the formal aspect of his resurrection theme. The “vanishing” time intensifies the spiritual atmosphere in the fiction. The internal focalization renders the subtle changes of character’s inner state. The profiled depiction of nature and the detailed depiction of the resurgent nature weaken the sense of reality, highlighting the religious function and subjectivity of nature.
Dostoevsky, resurrection theme, time, internal focalization, nature
2020-08-26
陈佳璐(1993-),女,贵州贵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E-mail: 15285068487@163.com
I106
A
1001 - 5124(2021)05 - 0117 - 09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