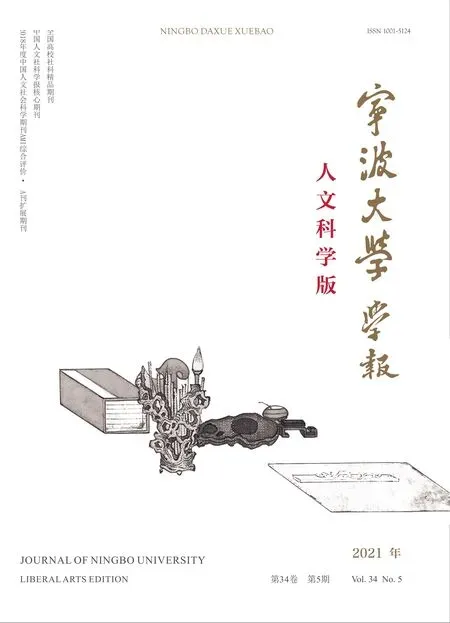从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关系中重温朦胧诗论争
南志刚
从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关系中重温朦胧诗论争
南志刚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从一开始就受到“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朦胧诗论争的焦点是当代诗歌话语权争夺,双方依据不同的诗学传统评价朦胧诗:一种为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所建构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诗学传统;一种是“五四”开拓的现代主义、个人主义、世界性的文学传统。论争出现新诗两种方向的较量:一种是大众化、民族化的诗学方向;一种是现代性、世界性的诗学方向。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远远超出朦胧诗本身,进入到中国现代诗歌传统和未来方向的讨论。从朦胧诗论争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关系中考察,激辩仍然围绕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走向世界的时代大潮展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既构成第三代诗人群体“反叛”朦胧诗的根由,也构成90年代以后,谢冕、孙绍振等“崛起派”代表人物反思“新诗潮”的内在动因。
朦胧诗;思想解放;新启蒙主义;历史评价
“跨越整个80年代的‘现代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开始的,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借助政治革新和社会思潮的变动而完成了对历史的‘改写’和对中国道路的重新抉择。”[1]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朦胧诗论争,中国新锐的启蒙精英知识分子,第一次以整体力量“崛起”,抱着与传统、主流“对峙”的文化态度,走到文学批评前台,成为20世纪80年代建构新启蒙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的重要力量。围绕朦胧诗的论争从一开始就受到“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朦胧诗论争显现为当代诗歌话语权争夺,表现出新诗两种方向的较量,一种是从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开始,直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传统,一种是回归“五四”文学革命所开创的现代性、世界性文学传统。论争一方是相对守成的老诗人和理论家,他们坚持大众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文艺”立场和诗学原则,严厉批评朦胧诗中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没落趣味”;另一方是相对年轻开放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朦胧诗中发现了现代主义和走向世界的“新的美学原则”,高度肯定朦胧诗创作方法和诗歌美学理念。论争双方“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先把对方设立在‘不正确’的状态,然后采取批驳、激辩和排斥的方式,以及所批评的‘对立面’的确立并使其丧失话语阵地的过程,使自己的诗歌观念成为诗歌界唯一通行的话语”[2]。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崛起派”与朦胧诗一起被视为“新的美学原则”的代表,赋予反叛者和启蒙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英雄”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人质疑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和英雄主义情结开始,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启蒙话语的生存语境和文化批评话语的多元化,“崛起派”的文化复古倾向逐渐浮出地表,可惜尚未引起人们关注,也没有进入文学史的相关叙述。
一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富有活力的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最初,‘新启蒙主义’思潮是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活动的……‘新启蒙主义’思想运动逐步地转变为一种知识分子要求激进的社会改革的运动,也越来越明显地具有民间的、反正统的和西方化的倾向。”[3]55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秉持启蒙式的评价机制与评价标准。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化上的‘新启蒙运动’之间构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同构性或共通性;而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以至于相互抵牾与冲突。这种文化启蒙话语与政治思想话语之间的双重变奏,表征着社会变革转型时期各种思潮观念的错综复杂性”[4]。改革开放后率先出现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然后才是文化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1978年7月22日,邢贲思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的启蒙与启蒙的哲学》提出“新启蒙运动”的概念。197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报告指出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是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的报告为知识分子重申启蒙立场签发了一张通行证,新时期启蒙话语得以纳入“思想解放运动”框架中。知识精英推崇启蒙精神,反思、矫正一体化文学评价机制与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新时期国家民族的整体发展和改革方向。因此,“重视‘新启蒙运动’与‘思想解放运动’之间的同构性关联,克服并去除‘两元对立思维方式’,积极寻求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沟通”[4],将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议题。仅仅用启蒙主义是无法涵盖和解读当代文学及其历史化的,至少是很不完整的。“源自‘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启蒙文学史观对当代文学的宰制与遮蔽已久遭诟议,如何调校启蒙史观、有效兼容‘人民文艺’,恐怕是需要20年才能切实解决的理论难题。”[5]
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既有容纳、又有龃龉。在这一社会思想语境中,朦胧诗争论很快从讨论诗歌形式和阅读效果,上升为现代诗歌评价标准和诗学话语的争夺,进而成为80年代思想交锋的重要事件,两军对垒、针锋相对。杨匡汉《评一种现代诗论》比较明晰地表达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与关于朦胧诗论争的关系:“‘改革’已成为各条战线热烈的话题。文学艺术也将在改革中前进。人们对诗歌同样寄予期待,创作要与平庸作斗争,评论也应更新知识结构,否则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要求太不相适应了。正因为如此,诗歌界应当鼓励继续解放思想,鼓励大胆创造,鼓励学术讨论的自由和艺术风格发展的自由。但没有意向的自由是不可思议的。”正是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要求与诗歌创作、评论关系出发,杨匡汉感觉到《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在艺术上提出了一些不无可取的新鲜意见,但文章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则偏离了科学的目的性而陷入混乱和糊涂”[6]。
朦胧诗论争经历了“古怪诗”“崛起派”“朦胧诗”等阶段。以顾城的《弧线》为契机,引发了“古怪诗”的争议。闻山、丁力等人认为顾城是故意刁难读者,下决心让人看不懂,脱离群众,脱离时代,体现一种堕落倾向,要加以引导。丁力发表《古怪诗论质疑》,批评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为“古怪诗论”,对青年诗人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手法,写作“很朦胧”、让人“读不懂”的诗深表不安[7]。丁力认为“古怪诗的出现是受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否定十七年和前三十年,反对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是“‘信仰危机’在诗歌上的反映”,断言“朦胧诗不是创新,是摹仿某些外国人已经不搞了的东西”[8]。王纪人对丁力《古怪诗论质疑》提出质疑,“大众化的诗只能说明诗的通俗易懂,却不能说明诗的整个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诗人不仅要“大众化”,而且要“化大众”,“艺术造就了审美的大众,因此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都有一个提高大众的任务,或者说‘化大众’的任务”。王纪人以郭沫若、闻一多、艾青和何其芳为例,强调新诗应该继承五四传统,立足现代生活,发展各种风格[9]。
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认为“叫人看不懂的诗却绝不是好诗,也绝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这种诗体占了上风,新诗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甚至给败坏掉的”[10]。诗人臧克家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朦胧诗根本不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没有考虑文艺有社会功能”[11]75-76。程代熙将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定义为“一篇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诗歌宣言”“一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言书”,认为徐敬亚力图否定或者极力贬低“五四”以来,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传统,全盘否定20世纪50、60年代诗歌创作成就,目的是为“带着强烈现代主义特色的新诗潮”扫清道路[12]。程代熙批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是“一套相当完整的、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具有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13]。针对这些批评,吴思敬明确表示:要以真善美为评价准则取替狭隘的政治标准,朦胧诗“是运用现代手法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又一代新诗,也可叫做现代诗……是现代的疾驰的社会生活酝酿就了一代青年的心灵,而这一代青年的心灵又凝成了现代诗”[14]224。
许多老诗人、诗歌理论家批评朦胧诗充斥着西方现代主义颓废堕落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从根本上背离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语言晦涩难懂,远离“人民群众”,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应该予以鲜明批判。艾青认为朦胧诗人“是惹不起的一代。他们寻找发泄仇恨的对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很骄傲。‘崛起论者’选上了他们,他们被认为是‘崛起的一代’”。艾青告诫朦胧诗人:“千万不要听到几个‘崛起论者’信口胡说一味吹捧的话就飘飘然起来,一味埋头写人家看不不懂的诗。盲目射击,流弹伤人。”[15]有一些诗人和理论家,主张对年轻诗人进行引导、培养和规劝。老诗人卞之琳建议朦胧诗人注意“五四”以来新诗的传统,袁可嘉谈到三十年来新文学运动存在两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的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16]112“自我”这一带有西方特殊意味的新鲜词语,自出现以来一直在国家控制的范围内“活动”,“人的文学”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评论者对社会生活的忠诚度,一群带有浓厚历史积淀的诗人在不断践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过程中,获取对当代诗歌传统的定义的权力。公刘认为顾城等新人新作是一个“新的课题”,他既不同意将朦胧诗视为“走在一条危险的小路上”,也不同意将朦胧诗的内容和形式视为“‘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回声”,主张朦胧诗人是“探索的一代”。“他们的悲观是和人民的悲观熔铸在一起的。他们不仅仅是止于探索,必要时,他们就挺身而出,起来抗争。”“我们不能嫌弃他们”,而是“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得愈多愈好”,“既要有勇气承认他们有我们值得学习的长处,也要有勇气指出他们的不足和谬误”[17]。顾工曾为顾城诗歌的“低沉”“可怕”“晦涩”而感到“不解”“失望”“愤怒”,试图用“革命、征战、老一辈走过的艰辛的路”“扭转孩子的大脑和诗魂”,让顾城“唱起我们青年时代爱唱的战歌”。但顾城这一代人“早已不是驯服的工具”,他们要用“我的眼睛、人的眼睛来看,来观察”,他们“不是在意识世界,而是在意识人,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和价值”。顾工希望“两代人的笔,要一起在诗的跑道上奔驰和冲刺”[18]。
孙绍振从评论舒婷诗歌开始,就主张“回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他认为“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就是“五四”所开创的诗歌传统,“舒婷正是继承了新诗敢于汲收外国诗歌的长处以弥补我国古典诗歌某种不足的传统。‘五四’新诗的这一宝贵传统,由于近十多年来片面地强调了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而被严重地忽略了”[19]。刘登翰认为舒婷诗歌“是对于新诗传统某些方面的否定,同时也表现出在自己基础上借鉴外国诗歌艺术的发展”,舒婷“把人作为诗歌表现的核心”,“呼唤那失去的人的最高本质的复归”,“表现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成为一种新的美学追求”[20]。
吴思敬着眼于“现代”对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回应了现代诗与传统的种种疑虑:“现代诗是诗歌现代化的产物。诗歌现代化则是新诗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它意味着对我国传统诗歌包括苏联美学理论影响下出现的某些定型的新诗的突破,意味着对古今中外诗歌珍品包括现代派诗歌的借鉴,意味着艺术个性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创作方法艺术流派的多元化,意味着以现代化的艺术语言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节奏,反映现代中国人的思想风貌和心理情绪。”诗歌现代化并不是要割裂传统,而是“要尽力吸收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现代诗尽管和西方现代派“心有灵犀一点通”,也“不会化到西方现代派去”[21]。著名诗人卞之琳认为“颇有些才气的青年诗人开始探索新的表现手法。他们的作品有时颇具个性和独创性,这个事实应该获得大家的尊重”,对“反对西化”的《汉语诗歌形式民族化问题探索》和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提出批评[22]。
20世纪8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界普遍有一种“去政治化”的思潮,要求“创作自由”和“文学独立”。这种消解政治中心地位、去政治化的社会思潮、学术思潮,与当时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目标“重合度”较高,得到部分政界人士或明或暗的支持,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话语一度处于“蜜月期”,文学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在表达“去政治化”学术欲求时,表现出堂吉诃德式的浪漫精神,批评态度和文字表述充分展现“个人化”风格。“三个崛起”提倡者对‘革命’‘主流’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其中不乏为了‘反叛’而‘反叛’的情绪化表达,这让一批老诗人和批评家不能不警觉。程代熙敏感地指出:“最近两三年,在我们文艺界就有一股不正常的风,他们力图否定或者极力贬低‘五四’以来,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传统。”[12]柯岩认为“三个崛起”“不但把挑战的目标对准了无产阶级文艺传统,甚至公开提出要允许‘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观点”[23]。争论的过程中,既能看到从预设立场出发对“朦胧诗”的指责,也能看到老诗人“尊严”受到“伤害”而引起的态度变化,“北岛被诗界公认之前(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与著名诗人艾青一度关系密切,受到他的影响。后来,因为贵州青年诗人黄翔写出‘把艾青送进火葬场’的诗句,艾青怀疑到北岛,两人终于交恶。”[24] 263。
顾城认为“朦胧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有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有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朦胧,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这种苏醒是“我们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开始懂得”的,他希望通过诗歌“去照亮苏醒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25],表现了一种类似于“五四”文学启蒙姿态。
二
“崛起派”诗论有明显的“五四”启蒙思想倾向,用“五四”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描述中国新诗发展,强调朦胧诗对于“五四”新诗精神的回应与回归,典型地体现20世纪80年代批评启蒙话语的价值追求。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依据中国现代诗歌向世界诗歌的融入度,评判新诗成功与否。他认为“五四”诗歌“坚决扬弃那些僵死凝固的诗歌形式,向世界打开大门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以帮助新诗的成长”。这种经验“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大众化、民族化和新民歌让新诗越来越“离开世界”,朦胧诗“要求新诗恢复它与世界诗歌的联系,以求获得更多的营养发展自己”,符合时代要求。他呼吁“接受挑战吧,新诗。”[26]徐敬亚宣告:“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是五四新诗传统(主要指四十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顺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27]诸多文学史正是着眼于“回归”五四文学传统,肯定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建构起“五四”标尺的新诗评价标准:“朦胧诗所指涉的不是某类诗歌创作,也不仅仅是一个诗歌集团,而是一种文学潮流,是一种重新回归‘五四’传统的文学潮流。”[28]103“将朦胧诗的崛起比况于五四新诗革命,实际上是对朦胧诗的崛起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史上的位置的一种肯定,这也成为了谢冕他们对于新诗历史的个人知识谱系的结构方式。”[29]646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对西方现代主义充满渴望,但了解还不够充分,把握也不够准确,对现代性的后果缺乏预判和洞见。“崛起派”对现代主义抱有一种迷恋式的想象,把现代主义视为拯救中国诗歌的唯一途径,对中国诗歌的古典传统和现代传统认识不足。在朦胧诗论争中,有学者对“崛起派”过分否贬传统、推崇西方现代主义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新诗的创新和突破,一定要有“基础”,把“亵渎和挑战当做最革命、最解放的表现,这只能带来思想混乱”[30]。2009年,余炀认识到“‘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学原则提出来,实际上暗示了朦胧诗论争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的对立面,即毛泽东时代的形成,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占据主流位置的现实主义诗歌文学成规和叙述语言”[31]。程文超发现“徐敬亚把18世纪的理性精神误读进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或者说在现代主义里误读出了理性精神”[32]112。尽管“崛起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误读”可以理解,且不乏意义,但将现代主义简单化和功利化,在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崛起派”强烈要求把“新诗潮”推到历史的前台,突出现代主义诗歌对中国诗歌的当下价值和未来意义,忽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的经验,将新诗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仅仅归之于诗歌/政治的直线式简单关系,制造了中国新诗六十年的“空白论”。这与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研究中“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遭到“冷遇”,形成了微妙的对应关系。朦胧诗的否定论者“分不清诗学实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界限……政治和文学的缠杂不清,既是他们长期以来诗学实践的存在形态,而且这缠杂不清还给他们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33]。
“崛起派”从西方近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和“五四”文学中汲取精神资源,主张用现代主义对抗现实主义,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强调现代诗歌的个人情感意志的独特表达,注重诗人主体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他们推崇“新的美学原则”,“对传统的美学观念表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姿态”,旨在提升“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的地位,弘扬个性和个人的价值。1997年,谢冕感叹“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诗歌“不对现实说话,没有思想,没有境界。诗人们都窃窃私语,自我抚摸,我不满意和我们无关的,和社会进步、人心向上无关的诗歌”[34];为很多诗人“对现实不再关怀!对历史很快遗忘!我特别难过”[35]。孙绍振批评新思潮“对诗人自我的生命缺乏责任感”“对诗歌本身,缺乏责任感”“缺乏时代的使命感”[36]67。由此看来,尽管“崛起派”竭力倡导西方现代主义的个性主义、个人主义,并在“五四”为起点新诗进化链条上找到了存在“合法性”[37],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理论冲击力。但诗歌是社会存在及意识的产物,它既具有个人性,也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群体,带着刻意的反叛精神和决绝的姿态,高喊着“打倒舒婷”“PASS北岛”登上诗坛。他们要捣毁一切意义和价值,消解朦胧诗人的崇高感,拒绝一切“专制性语言”的束缚,书写“日常生活的琐事,虚幻怪诞的胡思乱想”,以“口语入诗”,实践“自由随意”[38]33。他们认为诗歌是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拒绝用哲理或任何需要理论指导的东西去写作,主张拨开“象征”后的迷雾,展现眼中的现象真实。他们认为朦胧诗在社会舆论的威逼下成为意识形态同化物,承载了太多的道德与情感束缚,意象组合“苍白无力、虚伪、装模作样、故作深沉”[39]132,主张通过一种无需打磨的语言形式表达对自身处境的一种彻悟,用平凡代替崇高,以平淡代替激情,以满不在乎的语气代替前者诗歌中出现的忧虑感伤。经过第三代诗人的激烈反叛,朦胧诗和“崛起派”诗论所包含的启蒙中心话语和意识形态情结显现出来。实际上,1985年,谢冕就表达过这样的憧憬:“新诗潮……回到东方,沿着黄河入海处溯源而上,寻找这片古来的黄土地之根,使之在现代意识中梦醒。”[40]按照谢冕的期望,朦胧诗和“崛起派”通过现代主义回到世界,与世界诗歌进行对话,重建诗歌与人类人性的关系,这是现阶段诗学的最高目标;而终极目标则是回到东方、回到黄土地的原点。这一条复归的道路尽管绕道西方,绕道现代主义,但最终还是要回归本民族、回归中国社会历史现场。这看似与“崛起派”的观念主张相龃龉,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它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不乏传统士大夫的怀旧之风。“崛起派”“将‘自我’置于‘大众’的生存价值之上的精英视角”,“文坛精英们大量使用了‘五四’话语包括话语方式,但实质上,他们对‘自我’和‘大众’的认识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士大夫的基本概念范畴和视野。某种意义上,他们发动的实际是一场‘文学复古’运动”[41]。
三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被人道主义、启蒙话语所包裹,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将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置于二元对立关系中进行解读。“崛起派”从进化论的维度对主体性和自我进行处理,其始于20世纪80年代“人的觉醒”,以“中国式的自我”为切入点,平息质疑和诋毁的声音,实现从边缘向中心靠拢。这就使“崛起派”与当时社会思潮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崛起派”借助西方现代主义,要求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张扬自我和个性精神,以决绝的反叛姿态和犀利的语言风格构建启蒙主义诗歌批评话语;另一方面,试图接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主潮,强调20世纪80年代社会现场感和“五四”文学传统,以期进入文学的中心。在“崛起派”背后,小我与大我、社会责任与自我表现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综观关于朦胧诗及“三个崛起”讨论,不难发现:
第一,文化“共同体”中不同诗歌理想建构的论辩。“保守派”与“崛起派”的论辩尽管观点“对峙”,有些言辞激烈,甚至不乏扣帽子、打棍子,但双方辩论始终处于一个“共同体”中,离开双方赖以存在的“共同体”,这场讨论无法进行下去。这个容纳双方的“共同体”正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中国”。这个“中国”在很大意义上是由国家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这也许就是汪晖所说的“国家目标”。争论双方之所以勇敢地、毫不隐晦地亮出观点,均受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影响,受到“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主义”的启发。双方都坚信自己代表“正确”的诗歌观念,代表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与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目标一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社会共识,为诗歌批评提供了新的民族国家想象空间,“朦胧诗”为这种“想象”提供了“当下性”的言说对象。“保守派”也好,“崛起派”也好,都通过“朦胧诗”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期望,表达自己对中国诗歌“健康发展”的美好想象。
第二,新诗发展方向的博弈。“崛起派”高扬“新的美学原则”,更多关注中国新诗走向世界问题,这无疑符合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符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在“崛起派”看来,“世界性”是中国新诗发展方向,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新诗的发展道路就越来越宽广,而民族化、大众化、民歌化则使中国新诗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他们主张重新回到“五四”诗歌道路上,与世界诗歌发展潮流保持一致,弘扬现代主义精神,运用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保守派”主张民族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发展道路,他们要“改革”的是“文革”时期的诗歌,要坚持的是左翼文艺、延安文艺为代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这两种发展方向,实际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发展方向论争在诗歌层面的体现。从晚清的“体用”之争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争、文艺大众化讨论、提倡民族化气派与风格,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西文化讨论,“体用”思维在“向中”还是“向西”的选择中多次摇摆。中华民族历史沉疴与现实紧迫性,“启蒙”与“救亡”的复杂关系,一直困扰着现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是学习西方,融入世界?还是坚守本土,以我为主?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绝不是一场“诗歌”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所能回答的。朦胧诗论争触及到这个“长线”根本问题,表现出不同代际诗人、诗评家在具体时代语境下的历史担当和艺术敏感。
第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诗歌精神的选择。“新的美学原则”突破“集体主义”诗歌精神,肯定朦胧诗张扬“个体主义”诗歌精神,强调现代诗歌个人情怀、意志的独特表达,注重诗人主体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保守派”注重现代诗歌与现代中国的“同步”关系,肯定诗歌的集体主义精神,强调诗人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主张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理念和艺术手法。实际上,朦胧诗并不缺乏集体主义和家国认同,其中不少诗作承载“国家目标”,表达“爱国主义”“人民的声音”和“青年一代人”的集体意识,“新的美学原则”卸载诗人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概括,也不能全面反映朦胧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保守派”希望诗歌尽快走出“文革”阴影,快速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民”诗歌轨道,带着“历史的惯性”强调诗歌集体道德、集体认同。
第四,新诗历史评价的博弈。“崛起派”带着明显的“新启蒙主义”思维,在20世纪80年代重构个性解放和世界性的“五四”新诗,批评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新诗,把至少两代诗人打入“冷宫”,激起艾青、臧克家、柯岩等诗人的“义愤”。“保守派”既不能否认“五四”新诗的历史贡献,又必须在“新启蒙主义”“五四”新诗的认同中,肯定20世纪30年代以后主流诗歌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双发因“理解的基础”产生“对峙”,导致“理解的同情”缺失。从中国新诗发展道路而观,由“五四”诗歌、20世纪30年代诗歌发展到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既有其深刻社会动因,也不乏内在逻辑合理性。遗憾地是,争论双方对这种“外在”与“内在”互动的“合逻辑性”与“合历史性”缺乏“认同”,诗歌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因“站位”立场而破裂。这表明,今天重温朦胧诗论争时,“历史化”不仅阐释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必然途径。
1991年,张旭东在分析中国当代批评话语的主题内容和真理内容时意识到:“人们似乎习惯于从‘内部’,即由其体制的结构弊端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局限,而从‘外部’,即所谓‘全球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解释任何‘超越’历史条件的文化创造。”他提出“颠倒思路”的建议,“从‘外部’,即从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经济战略的社会主义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强大的扩张力和毁灭性诱惑中解释社会主义的困境,同时,以‘内部’,就是说,从作为历史主体的‘前现代’民族日益明确的自我意识,从这种历史意识下不可遏制的表达的必然性,从这种表达所激发的非西方的想象逻辑和符号可能性,同时,也从这种想象在全球文化语境中自我投射、自我显现的机制中解释作为‘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学的兴趣”[42]355-356。可惜,在朦胧诗论争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崛起派”,都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张旭东的“颠倒思路”。朦胧诗论争的焦点,一直集中于现实需求和未来想象,也就是“今天和将来”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新诗,应该出现怎样的新诗。尽管论争双方都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传统,但显然“崛起派”找到的“传统”更合时宜,更能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和“新启蒙运动”的欲求,也更容易引起诗人和读者共名。“崛起派”为自己找到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将现代性、世界性和个性解放视为新诗的现实需求和未来方向,在改革开放和新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保守派”所坚守的新诗民族化、大众化、民歌化的传统,在面对“五四”新诗传统时暴露出无力感。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急于走出20世纪50-70年代封闭、孤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久遭压抑的人们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全方位差距,“从体制的结构弊端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局限”,“从全球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解释文化创造,是一种必然选择。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民歌化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生存基础,遭受质疑。当“崛起派”批评民族化、大众化、民歌化为新诗不合理的“历史遗留物”之时,当“民族化”“大众化”“民歌化”与“五四”新诗现代性、世界性和个性解放被人为“对峙”,“保守派”也就失去了现实支撑力量。程代熙在文章中感叹孙绍振获得许多青年的“青睐”,既表现出程代熙的心理失落,也意味着这“一代人”文化理想和人生定位的“生不逢时”吧。今天看来,如果能够像张旭东所设想的“颠倒思路”,新诗民族化、大众化、民歌化的历史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还原”,不至于在“崛起派”面前,表现得那样无力吧。朦胧诗和“崛起派”因为符合“改革开放”和“新启蒙运动”的方向,取得了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基础。也因为汪晖所指出的“思想解放”与“新启蒙运动”的龃龉与分离,迅速成为“改革开放”的异己力量,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其“宏大叙事”的诗歌写作方式,也很快被“第三代诗人”消解了。
四
1993年,欧阳江河在评估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时,发现“预想中的对抗主题并没有从天上掉下来”[43]29。他认为从“诗歌写作方面的具体原因”而言,“一方面因为继《今天》后从事写作的诗人普遍存在‘影响的焦虑’,不大可能简单地重复《今天》的对抗主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有的对抗诗歌读者群已不复存在……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为它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它的读者不是个人而是群众。然而,为群众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43]29-30。
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朦胧诗与新诗“当代”传统、“五四”传统的关系。崔卫平从郭路生的诗歌中读出“能够战胜环境的光明和勇气”,郭路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忠直”“体现了那个时代备遭摧残的良知”[44]304。郑先强调朦胧诗从一开始就具有“反传统”的品质,这种传统当然是指新诗的“当代”传统,“它对1949年之后的文学构成一种挑战,或者可以说,这种新诗就是中国的前现代主义诗歌,虽然仍留有过去时代的痕迹,但是这种诗歌在精神上却是一种反传统的”[45]312,因此,他借用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的说法,视朦胧诗人为“现身诗歌艺术的殉难者”[45]326。张旭东认为新诗潮的特征是“在‘现代主义’的外衣下重新亮出了五四的题旨”,“在‘朦胧诗’成熟的美学型态中,我们甚至更为清晰地看到了五四文学的内在机制的活动:作为现代派特征的蒙太奇、隐喻、反讽等手法为集体生活和个人经验提供了个人化、风格化的聚焦点,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和意象间的审美张力则构成意识冲突戏剧性的对象化,这一切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如北岛、江河诗中的‘纪念碑’和‘墓志铭’意象,本身隐含着一个集体形象,并揭示出诗人同一代人的共生关系。‘新诗潮’运动在形式的历史上最终成为一次向‘现代主义’的冲锋,但在经验的历史上却仍然是五四意识的回光返照”[42]360。
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曾有过一段“蜜月期”,文化思想界的讨论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那时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46]。“如果简单地认为中国当代‘启蒙思想’是一种与国家目标相对立的思潮,中国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政治力量,那就无法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脉络。尽管‘新启蒙’思想本身错综复杂,并在19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与国家目标的分歧是在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展现出来的。”[3]55“崛起派”从“五四”新诗中继承了启蒙精神和个性解放,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解放的思想背景是一致的,与新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的整体发展方向具有重叠性。只看到朦胧诗讨论中“崛起派”与“保守派”对峙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相通或一致的另一面,必然遮蔽许多历史真相,难以准确地认识和评价“崛起派”。
程光炜用更加宽阔的视野观照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历史评价问题,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艺思潮“无论它们怎样反复、矛盾和出现不同历史解释的结果,这些‘小思潮’都是围绕着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这个‘大思潮’而发生和呈现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思潮’变局的是‘思想解放’的价值模式,它是在与新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互动情境’中被制度化的,这种制度化使后3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尽管激荡不已,但最终仍然风平浪静”[47]106-107。朦胧诗论争正是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小思潮”,这场多方参与的诗学论争尽管出现了多种不同声音,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声音,但不会从整体上改变80年代社会思潮影响而形成的思想解放的价值模式。朦胧诗论争不仅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整体格局中展开的,而且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种“整体性”与“新知识分子精英集团”这样那样“互动”过程中勃然而兴、骤然而息。因此,朦胧诗论争尽管在文学界和思想界掀起一阵硝烟、一时波澜,而终归于“风平浪静”。
[1] 张伟栋. 历史“重评”与现代文学的兴起——文学与政治双重视野中的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运动[J]. 海南师大学报, 2011(4): 19-27.
[2] 程光炜. 批评对立面的确立——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J]. 当代文坛, 2008(3): 4-13.
[3] 汪晖. 死火重温[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4] 李鹏, 谢纳. “八十年代”的思想现场: 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的复杂关联[J]. 文艺争鸣, 2015(5): 51-57.
[5] 张钧. 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J]. 当代文坛, 2019(1): 24-29.
[6] 杨匡汉. 评一种现代诗论[J].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 1983(3): 173-178.
[7] 丁力. 古怪诗论质疑[J]. 诗刊, 1980(12): 6-8.
[8] 丁力. 新诗的发展与古怪诗[C]//姚家华. 朦胧诗论争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89: 97-105.
[9] 王纪人. 对《古怪诗论质疑》的质疑——与丁力同志商榷[J]. 文艺理论研究, 1981(1): 109-111.
[10]章明. 令人气闷的“朦胧”[J]. 诗刊, 1980(8): 53-56.
[11]臧克家. 关于“朦胧诗”[C]//姚家华.朦胧诗论争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89.
[12]程代熙. 给徐敬亚的公开信[J]. 诗刊, 1983(11): 41-46.
[13]程代熙. 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J]. 诗刊, 1981(4): 3-8,17.
[14]吴思敬. 诗学沉思录[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15]艾青. 从“朦胧诗”谈起[C]//姚家华. 朦胧诗论争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89:157-168.
[16]袁可嘉. 论新诗现代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7]公刘. 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几首诗谈起[J]. 文艺报, 1980(1): 38-41.
[18]顾工. 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J]. 诗刊, 1980(10): 49-51.
[19]孙绍振. 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J]. 福建文艺, 1980(4): 58-72.
[20]刘登翰. 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论争谈起[J]. 福建文艺, 1980(12): 60-65.
[21]吴思敬. 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J]. 诗探索, 1981(2): 145- 151.
[22]卞之琳. 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J]. 诗探索, 1981(3): 8-11.
[23]柯岩. 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J]. 诗刊, 1983(12): 46-57.
[24]孟繁华, 程光炜.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 修订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5]顾城. “朦胧诗”问答[C]//姚家华. 朦胧诗论争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89:316-319.
[26]谢冕. 在新的崛起面前[J]. 诗探索,1980(1): 11-14.
[27]徐敬亚. 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J]. 当代文艺思潮, 1983(1): 14-28.
[28]黄修己. 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下卷[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29]吴思敬.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30]郑伯农. 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J]. 诗刊, 1983(6): 36-46.
[31]余旸. “朦胧诗”论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的艰难叙述[J]. 扬子江评论, 2009(6): 14-24.
[32]程文超. 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33]王爱松. 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J]. 文学评论, 2006(1): 113-121.
[34]舒晋瑜, 谢冕. 所谓诗歌,归结到一点就是爱[EB/OL]. (2018-03-28)[2021-03-15]. 中国诗歌网https://www. zgshige.com/c/2018-03-28/5662620.shtml.
[35]林凤. 谢冕访谈录[J]. 诗刊, 1999(6): 71-75.
[36]孙绍振.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37]杨庆祥. 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学”[J]. 文艺争鸣. 2009(2): 57-61.
[38]徐敬亚, 孟浪.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8.
[39]于坚. 诗人随笔丛书 棕皮手记[M].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14.
[40]谢冕. 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J]. 文学评论, 1985年(5): 43-52.
[41]程光炜.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J]. 山花, 2005(11): 121-133.
[42]张旭东. 论中国当代批评话语的主题内容和真理内容——从‘朦胧诗’到‘新小说’: 代的精神史叙述[M]//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下卷.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3.
[43]欧阳江河. 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的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分[M]//站在虚构这边.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44]崔卫平. 郭路生[M]//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下卷).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3.
[45]郑先. 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M]//王晓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下卷.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03.
[46]陶东风. 新时期三十年人文知识分子的沉浮[J]. 探索与争鸣. 2008(3): 15-19.
[47]程光炜.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Reviewing the Debates over the Misty Poetr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
NAN Zhi-g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of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The debates over the Misty Poetry that took place in the 1980s was deeply influenc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y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 of the times. The focus of the Debates over the Misty Poetry was the fight for the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poetry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Misty Poetry by two sid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iterary poetics tradition: one is the “people’s”, “socialism” and “realism” poetics tradition constructed by left-wing literature, Yan'an Literature and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the other is the modernist, individualistic and cosmopolitan literary tradition developed by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bate, it shows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two directions of new poetry, one is the direction of popular and national poetics, the other is the direction of modern and world poetics. Therefore, the debates over the Misty Poetry went far beyond the Misty Poetry itself and developed in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adi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However, it can be inspect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Movement that the debates over the Misty Poetry still revolved around the general trend of though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going to the world. This background not only constituted the desir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ets to “rebel against” the Misty Poetry, but also formed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ise school” such as Xie Mian and Sun Shaozhen to reflect on the “New Poem Tide” after the 1990s.
the misty poetry,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the new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 evaluation
2021-07-0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研究”(15AZW009)
南志刚(1964-),男,陕西省渭南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E-mail: zhigangnan@126.com.
1206.7
A
1001 - 5124(2021)05 - 0058 - 11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