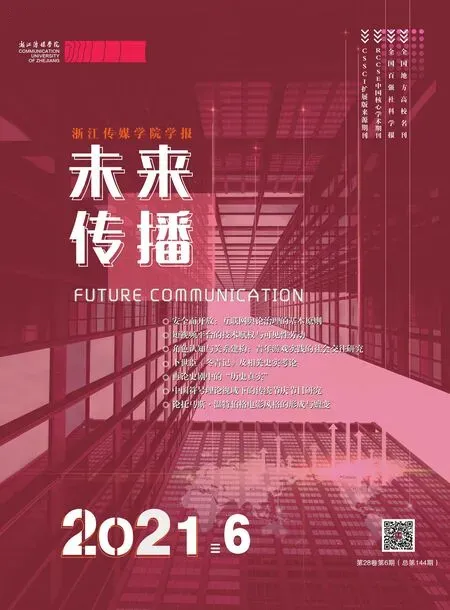论京剧《澶渊之盟》在新编历史剧创作中的典范意义
朱恒夫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京剧《澶渊之盟》自1962年5月19日首演于武汉市汉口人民剧场之后,不断地被搬演,已然成为京剧的经典之作。它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不仅仅因为出品单位是上海京剧院这样一流的戏曲表演团体和首演者为周信芳、赵晓岚、汪正华、孙正阳、李桐森、王正屏、李仲林等杰出艺术家,更重要的原因是陈西汀、周信芳[注]周信芳参与了剧本的创作过程。《周信芳初演〈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剧本是由陈西汀编写的,但在剧本结构、人物设计等方面,周信芳都曾花过不少的心血。当剧本刚开始编写时,周信芳就不断收集一些古籍上有关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始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并且经常同陈西汀交换意见;他还先后三次参加剧本的修改,每次都是一字一句地斟酌。演出以前,他曾严肃认真地参加了排练。”参见《戏剧报》1962年第5期。所编的剧本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作为戏剧“好看”的艺术性。它流传下来的意义,对于观众来说,可以由此欣赏麒派的艺术;对于编剧来说,则能体悟到创编历史剧的真谛;而对于理论界来说,因它是一个成功的历史剧的代表作,深入研究,可以从中提炼与概括出有关历史剧的理论。
历史剧是戏剧的一种类型,在戏剧史上一直存在着。戏曲根据剧目的内容,一般分为历史剧、古装戏与现代戏,故三分而有其一。然而,对于历史剧的内涵,至今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用“剧”的形式来反映“历史”,还是仅借助于“历史”的故事甚至仅用“历史”的名头来演“剧”。在20世纪40年代有关历史剧的讨论中,郭沫若提出了“历史”与“历史剧”的差别,说前者须“实事求是”,而后者可以“失事求似”,只要描绘了特定时代的风貌和反映了时代的趋向,不必拘泥于史实。[1]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茅盾则说:“历史剧既应虚构,亦应遵守史实;虚构而外的事实,应尽量遵照历史,不宜随便改动。当然,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改动史实,自当别论。如果并无特定目的,对于史实(即使是小节),也还是应当查考核实。”[2]他的观点很明确,历史剧尽管是“剧”,但也要尊重历史。现在的创作界和理论界,又有了新的理念,许多剧作家编写历史剧, 将“历史”等同于“传说”,只要能够表达剧意,讲述的可以是一个纯粹编造的古代故事。对此做法,理论界有人高度肯定,认为这样的编写方法“使得历史题材的创作走入了自由的天地。”
人们对历史剧的内涵认识何以会有这么大的区别?窃以为,根本原因是重“剧”轻“史”者不了解历史剧的功能,将它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戏剧”了。创演历史剧的目的是让观众在审美的同时鉴古知今,而鉴古知今,又是历史剧与一般戏剧最大的区别所在。历史剧欲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让观众认知现在和未来,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得到大至社会的发展趋势、小到个体的为人处世的启发。因而,所摹写的“历史”越真实,人们越会认真严肃地思考它所表现的历史得失,从而接受其经验与教训,自然地,它也就实现了历史剧的功能。反之,当人们发现它所表现的“古”并非真实的“古”,仅是“戏说”而已时,自然也就不会将它所表现的生活当作历史看待,更不会真心诚意地接受其总结的经验与教训了。
历史如此的悠长,历史上的人与事又是那样的繁多,用哪一段的历史、哪一个历史人物、哪一个历史事件作为素材,来编写历史剧,才能得到观众的欢迎呢?由京剧《澶渊之盟》来看,方法很简单,就是寻找到与当代精神合拍的历史材料。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处于内外交困时期,欧美围堵,中苏关系恶化,台湾蒋介石集团叫嚣要反攻大陆,而国内因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极度萧条。在此情况下,周信芳等人用寇准勇敢抗击辽军、保家卫国的史实,编演成该剧,旨在树立寇准这样的爱国英雄榜样,以号召人们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和一切凶恶的敌人进行斗争,以争取胜利。这样的剧旨应合了时代的需要,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一、高度尊重史实,呈现历史风貌
京剧《澶渊之盟》的创作者对于“历史剧”的涵义有深刻认识,且高度认同。他们尊重历史,绝不肆意虚构,不但所涉及的主要人物宋真宗、寇准、毕士安、高琼、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曹利用、萧太后、耶律隆绪、萧挞览、韩杞等皆是历史上的真人,就是所写的主要事件都有历史的根据。具体地说,有以下两点表现。
(一)以史家的严肃态度,正确地描绘历史面貌
宋辽矛盾的焦点是燕云之地,宋要收复,辽要占据。燕云之地是一个历史问题。公元936年,后晋“儿皇帝”石敬塘为答谢契丹即后来的辽朝帮助灭后唐建晋之恩,如约割让燕云十六州,辽朝因此将自己的疆域推进到长城以南。
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深山大谷,连亘万里,盖天地所以限华戎,而绝内外也。”[3]自古被中原王朝视为限隔夷夏之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它的失去,给北方草原民族的南下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自蓟而南,直视千里,贼鼓而前,如莞袵上行。”[3]公元959年,周世宗成功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邱)以及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等地,史称关南十县。
宋建国伊始,燕云的大部分地区仍为辽所控制。宋太祖根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而后收复燕云的战略,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起,开始对南方割据政权进行讨伐,对辽朝则采取“来则掩杀,去则勿追”的牵制防御策略。待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和吴越等割据政权相继灭亡后,宋朝对辽朝的战略也随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乾亨元年(公元979年)二月,宋太宗亲率大军分四路北伐辽朝的附属国和门户屏障北汉,揭开了宋辽双方争夺燕云之地的长期战争的序幕。灭亡北汉后,宋太宗乘胜北进伐辽,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但因谋划不周、仓促出兵而惨败。至乾亨四年(公元982年)秋,年幼的辽圣宗耶律隆绪继承皇位,辽太后萧氏摄政。宋朝以为此时的辽朝“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内忧外患,可以乘机收复燕云地区,于是,在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月,兵分三路,以东路军为主力,大举北进,史称“雍熙北伐”。然岐沟关一战,宋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雍熙北伐”失败后,辽朝势力猛涨,不断挑起战争。咸平前六年间,较大的战役就有11次,其中有9次为辽朝南侵所致,几乎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大的战役。而宋朝败多胜少,迭遭重创,损失惨重,使得北部边关几无安宁之日,生灵屡遭涂炭。两国间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三场,即澶莫之战、遂城之战、望都之战。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率众从河北大举攻宋。次年正月,辽军在瀛州东30里,击溃宋军。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辽国又集中兵力,从河北遂城(今河北徐水以西)西面之长城口一路进兵。当年十一月初,宋军大破辽师于羊山,然自己损失亦惨重。羊山之战后,辽军频繁对大宋实施报复性进攻。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辽不断侵掠大宋边境,几乎每战必胜,宋军严重受挫。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四月,辽军数万骑兵又大举入侵,深入宋境,包围定州之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与副都部署王继忠领兵向北驰援,后王继忠全军覆没,本人亦被辽军擒获。

辽朝恰恰相反,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与战争的胜多败少,助长了它觊觎中原、吞食宋朝的野心。萧太后与辽圣宗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倾全国之兵力,自幽州南下伐宋,气势汹汹,势如破竹,攻破德清军(今河南清丰),直逼京都汴京以北、黄河岸边的军事重镇澶州。澶州是汴京的重要门户,它夹黄河南北两岸而建,中有浮桥相连,据北道之会,扼大河之津,且距汴梁仅有250公里。当时河北防线已被突破,河南也成为战场,更为严峻的是快要进入冬季,黄河很快就会结冰,宋朝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快没了。若澶州有失,辽骑一两日即可驰抵京师。当警报“一夕五至”,飞递至汴京时,宋廷自然是惊恐万分了。
京剧《澶州之盟》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剧中的汴京君臣们于此时的表现可用三个字来概括:急,恐,慌。寇准是“三更闻得边关报,睡不成眠起上朝”,竟不怕破坏朝规,提前半个时辰,亲自操起木杵,敲起了上朝的景阳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深知形势危急,需要君臣尽快定下应对方略;毕士安此时推荐寇准为相,表面上是荐贤拔才,为国家的安危着想,但实质上是恐惧的表现,他怕自己在丞相的位置上,担不起救危存亡的重任。若不是出于这样的心理,为何早不荐晚不荐,而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才荐?至于王钦若、陈尧叟之流,更是恐惧至极,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逃命:“金殿之上,那王钦若口若悬河,引古证今,把辽邦兵力说得不可一世,老夫虽然苦苦争论,怎奈万岁心中惧怯,不敢提起‘迎战’二字。如今一面准备起程,一面命你点动军马护驾。”[4]“慌”的表现则集中在真宗的身上,他已经是六神无主,手足无措,王钦若建议他避难金陵,他不考虑这一行为的利弊,就贸然答应;寇准坚持要他御驾亲征,他也只得同意。作为一个三军统帅,却没有自己的主张。大将高琼的前期表现,也是一个“慌”字,他跑到丞相府责问寇准:“边关雪片文书紧,竟做旁观无事人。火烧眉头全不问,敲破了景阳钟你却充耳不闻”,掀翻酒桌,暴跳如雷。他若不慌,作为一个王爷,怎么会这样鲁莽?
剧目就是这样通过君臣面对辽军压境的表现,再现了真宗朝君臣对于辽朝的态度,构建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引领着观众进入到当时的情境之中。
(二)按照历史本来的样子来描写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基本上是“盖棺定论”,真正的“历史剧”就必须按照历史的评价去定位人物的品性和他们对社会的作用,尤其是在历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其形象更容不得改变,倘若好坏颠倒,或将“高尚”“卑劣”的品质虚空地加在他们的身上,都会引起观众的极大反感,他们会讥以“反历史”,而否定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京剧《澶渊之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一如他们历史上真实的表现。我们仅以毕士安、高琼为例,来看看该剧是如何表现历史人物的。
剧中的毕士安在澶渊之盟的前后,作用有三:荐举寇准为相;支持寇准的御驾亲征的主张;帮助真宗实现议和的目标。那么,历史上的毕士安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寇准为相,确实是毕士安举荐的。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宰相李沆卒,真宗选择新相,意属毕士安,然征求毕士安意见时,士安力荐寇准,认为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最后,真宗让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5]
在告急文书“一夕五至”,朝野震骇之时,江南人参知政事王钦若奏请真宗到金陵避难,蜀人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宋真宗到四川躲风,寇准则要求真宗御驾亲征澶州,以鼓舞士气。这时的毕士安与寇准同心同德,配合默契:“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5]在性格懦弱而又保守的真宗皇帝犹豫未决时,老成持重的毕士安的态度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真宗亲征澶州后,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宋军一战获胜,加上辽军主帅萧挞览被宋军床子弩射死,战局出现了有利于北宋的转折。在此情况下,辽主动“密奉书请盟”,真宗默许,然又担心辽方有诈,举棋不定。君臣讨论之时,寇准竭力反对,他主张乘胜战斗,将辽军击退之后再谈和议之事,说不定能收复燕云之地。这时,毕士安站了出来,支持真宗以和议来息战的想法,并认为辽朝请盟是可信的:“臣尝得契丹降人,言其虽深入,屡挫不甚得志,阴欲引去而耻无名,且彼宁不畏人乘虚覆其巢穴?此请殆不妄。(王)继忠之奏,臣请任之。”[5]于是,宋真宗决意议和。
可见,京剧《澶渊之盟》中的毕士安就是历史上的毕士安。
剧中的高琼和历史上的高琼,除了身份由殿前都指挥使换成王爷之外,也基本相同,就是王爷的爵位,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是之后晋升的。当他消除了对寇准的误会之后,对其抗敌计划钦服不已,主动配合寇准的部署。无论是起驾离京,还是在黄河岸边上船北渡,高琼都起了给真宗打气鼓劲的作用,尤其是在黄河之北的澶渊城下,敌军军营密布,夜晚一片灯火时,他先过了黄河,对守城的将军李继隆说:“少时你去见陛下时,问起河北灯火,就说是澶渊军民欢呼接驾。”李继隆怕担诳驾欺君之罪,高琼便转告了寇准的嘱托:“国家存亡,在此千钧一发,事已至此,不得不然。寇大人命老夫叮嘱将军,少时见驾,看丞相眼色行事。”(第七场)銮驾到了澶渊北城后,他依然坚定地站在寇准这一边,有力地遏制了王钦若的消极作用。那么,历史上的高琼在澶渊之盟前后是怎样的呢?
宋真宗亲征澶州,然到了韦城县(今长垣县)后,辽军已有渡河之势,王钦若再次提出徙都金陵时,真宗又迟疑不决起来,加之有宦官劝其“何不速还京师”。真宗便问寇准:“南巡如何?”准对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者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寇准为了坚定真宗亲征之意,便请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以军事将领的身份站出来讲话,问高琼:“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高琼毫不犹豫地回答:“琼武人,诚愿效死。”寇准随即拉着高琼来到真宗面前,对真宗说:“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盖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3]高琼还说:“敌之大入,去国远,斗势不可以持久,况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进则可以决有功,今止军不发,众情大惑。谁为陛下建此策者?”“天子亲御六军,蒙犯霜露,国之安危,事在转漏,尚何议也!”[6]
然真宗于二十六日到达澶州南城后,不打算过河幸北城,欲驻南城以观军势。寇准坚请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3]高琼也固请,认为:“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丧考妣。”签署枢密院事冯拯附和真宗之意,呵斥曰:“何得无礼!”高琼毫不客气地怒怼曰:“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以退敌耶?”[7]于是,真宗从之。但是进抵浮桥时,真宗又踌躇起来,这时,“琼乃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3]由此可见,寇准能按计划让真宗亲临前线,与高琼的力助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剧中的高琼和历史上的高琼,一模一样。
二、精心编织情节,着力人物性格
“历史剧”毕竟是“剧”,而不是史书,倘若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就不可能吸引观众。而没有艺术性的历史剧,其内容再怎么尊重历史、再现历史,也不会成功。京剧《澶渊之盟》的主演周信芳、剧作者陈西汀在用历史的材料编织故事和描写人物形象时,可谓匠心独运。具体地说,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法。
(一)巧妙安排情节结构
这部剧的主角,毫无疑问是寇准,故事主要表现了寇准与主和派君臣的矛盾,然而,开头的两场戏却既没有让寇准亮相,也没有让真宗等人出场,而是将场景置放在辽邦,让次要人物曹利用开了幕,由他的眼睛看到辽国境内“车辙满地,分明是频输粮草,忙于用兵之象”。接着表现萧太后等辽国君臣为侵犯中原厉兵秣马:“沙白风高塞草黄,长城万马卧秋霜;机谋如海深难量,要渡黄河夺汴梁。”萧太后绝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老王在世时,辅佐老王,统驭内外;老王晏驾后,代替幼主(她的孩子)隆绪执掌河山。她雄心勃勃,决意开疆拓土,威尊南面。了解到赵宋年轻的皇帝真宗信任参知政事王钦若,朝堂上下阿谀成风,边关将士武备废弛,她便暗暗调集人马,准备袭取汴梁。这样的情节安排,既渲染了迫在眉睫的战争气氛,也向观众交待了“澶渊之盟”的起因是由辽国引起的。
寇准得到边关急报后,剧目没有立即安排宋廷君臣朝议,而是让黄门官与寇准 “上演”了要不要提前敲打景阳钟的一场戏,一方是风急火燎,一方是慢慢吞吞。黄门官愈慢,寇准与观众愈急,最后寇准亲自举杵打鼓,不仅表现出了寇准对于局势严重程度的认识和以民族存亡为己任的品德,还因黄门官开始不敲、后来主动要敲的行为而在沉重的气氛中插进了风趣的场面,有了好看的“戏”。
朝会之前,寇准驳斥王钦若的轻敌言论,警告一帮漠不关心的臣僚们:“只怕萧后张弓搭箭,不是追打什么獐猫鹿兔,而是要将王大人你们一网打去。”王钦若希望丞相毕士安站在自己一边,有意挑拨道:“要是我等真被一网打去,你这丞相啊,还是大大的獐猫首领、鹿兔班头!”而毕士安只是打了哈哈:“獐猫魁首,鹿兔班头,哈哈哈。”要求大家“一同上朝去面圣,是非黑白自分明。”大笑着拉王钦若下。此时的王钦若与台下的观众,满以为毕士安定然站在寇准的对立面,不料,转瞬之间,他向真宗推荐寇准为相,且态度坚决:“(唱)寇大人他确是好刚任性,(白)只是万岁要知道,我朝优柔日久,若无此人担任呵!(接唱)无此人掌不住一发千钧。请万岁速降旨传封寇准,臣愿将老头颅保此忠臣。”本想让毕士安协助自己“上金殿狠狠地参奏一本,拔去了眼中钉我好安心”的王钦若,完全在意料之外,先是坚决反对,后来看到木已成舟,只好违心地说:“适才朝房之中,大人的议论,实在是高人十倍,越想么,越有道理,方才又经万岁与毕丞相一番议论,我此刻是豁然醒悟,茅塞全开,得益匪浅,承教!承教!”就连拿不准毕士安立场的寇准也大吃一惊。戏中的王钦若、寇准如此,台下的观众更是这样,但毕士安的行为并未在情理之外,只会让观众在情节的“突转”中获得美感。
剧中的王钦若是寇准的对立性人物,为了不断构建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剧目安排他随驾到了前线,让他识破河北灯火的真相:“启奏万岁,李继隆之言有诈,看这灯火之光遍布千里。河北之地,哪里有许多军民?!金鼓之声,一派杀伐之气,哪里是迎接圣驾,分明辽兵已到澶渊。”王钦若猜中真宗的心思,提出在河中停舟;他诬陷寇准,说寇准惊恐敌势,险些滚下城来。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钦若,但凭真宗一人的畏葸不前,就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张力,就没有这么多好看的“戏”了。那为何又安排王钦若在结盟之前去守大名府呢?当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如果还是让他留在澶渊,无非还是表现他的胆怯、谄媚和对寇准的中伤,必然会和他前面的“行为”重复;二是让毕士安来到前线,成为寇准主战的阻力,以促进澶渊之盟的签订。毕士安由力荐寇准到阻碍寇准抗战,其“戏”自然比王钦若的要好看得多。
该剧目有多条情节线:辽军攻宋行进线,主战派与主和派交锋线,宋军与辽军较量线,寇准与高琼等人的矛盾线,等等。然而,所有的这些情节线,最后都由签订“澶渊之盟”这一中心而绾结起来。或者说,这些情节线的功能主要在于表现“澶渊之盟”。如辽军攻宋行进线,开始萧太后倾全国兵马,气势汹汹,席卷而来,但在寇准的正确指挥和宋朝军民的英勇反击之下,不但损兵折将,粮草不济,连她自己也差点丧了老命,主力兵马还被宋军切断了退路,只得低首求和。然而,就在这“三军气吐山河壮,萧后金冠落道旁”的情况下,宋朝居然正式割让燕云多地,并每年赔偿十万银两、二十万匹绢,向战败的一方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观众看到此处,对于以真宗为首的主和派,能不义愤填膺?!至此,情节线便完成了表现主旨的任务。另外,情节线虽多,却繁而不乱,或平行,或交叉,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却都按照生活的逻辑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二)将写人作为剧目的重心
剧作家描写历史,是艺术的表现;史家撰写历史,是史实的还原。前者重心在于写人,后者的任务是运用真实的史料叙述事情的过程。京剧《澶渊之盟》的编剧准确把握了两者之间的区别,着力在剧中塑造出真实而又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周信芳在介绍创作方法时说:“把历史上真实的重大事件处理成戏曲,一方面要符合于戏曲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符合于历史的要求,所以首先必须解决历史剧与历史关系问题。戏曲的特点是以描写人物、发展人物性格为主要目的。既不能只管历史不管戏曲,叫人看了索然无味;也不能只管戏曲不管历史,叫人看了不真实。描写人物、发展人物性格的主要方法是抓住重点,进行发挥,扩大到全面。这些重点,一定要能够突出人物性格,便于人物的活动和发展。”[8]也就是说,作为“剧”,舞台上必须立起几个具有美学意义的人物形象。
京剧《澶渊之盟》不能说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鲜明的、血肉饱满的,但至少主要人物寇准、毕士安、王钦若的性格是突出的,能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我们以寇准为例,作一分析。
寇准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刚正”“刚直”,认准的事情,一定去做;认准的道理,一定坚持。剧目中只要寇准出场,都会表现他这样的性格。他让黄门官“提前半个时辰,敲起景阳钟”,如果是一般人,听了黄门官这样做会掉脑袋的警告,定会作罢,可寇准认为,个人掉脑袋比起国家存亡,算得了什么,便毅然举杵敲钟。作为丞相的下属,你不去奉承丞相也就罢了,却直言指责毕士安:“丞相得报之后,还不立刻进宫,奏明万岁,早作准备,直到此时,才与百官姗姗来迟。想他人来迟,咳,也不足多责,老丞相身负国家重任,倘有不测,岂不是轻误时机?”这句话的分量可重了,说毕士安身为丞相,却玩忽职守,有可能让朝廷错过了往前线派遣援军的最佳时机。至于毕士安对这样的指责会有怎样的反应,全然不管,他只按照丞相这个岗位的职责来衡量其是否尽责。王钦若要寇准感谢毕士安的举荐,寇准却说:“臣启万岁,想这封官任职,乃主上之权;举贤任能,乃人臣之份。毕大人若以臣有一日之长,堪居相位,则推举理所应当;万岁若以毕大人所荐不妄,则封臣亦所当然。臣一不感毕大人之恩,二不枉毕大人之荐,朝廷大事,堂堂正正,有何可拜?有何可谢?”待人处世,真可谓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对于臣僚是这样的态度,对于皇帝依然如此,真宗勉强依了毕士安的举荐,任命他为丞相,但提醒他说:“凡为宰相者,必须心气宽和,雍容有礼,卿平日好刚使气,作事任性,今身当大任,务须把你那‘刚’之一字,彻底戒除!”可他的回答却是这样的:“臣平生别无有奇能出众,只有这一字‘刚’藏在胸中。若陛下以臣刚直可尽微用,臣唯有刚上加刚答报九重;若陛下以臣刚不堪任重,请收回丞相命另选明公。”这种不带一丝世故、不杂一点私心的性格,连真宗也深受触动:“往日里只耳闻他好刚任性,今日里初领教实实惊人。”
这样表现寇准的刚正、刚直,会不会让观众感觉夸张而认为不真实呢?不会的,因为历史上的寇准就是一位刚正、刚直之人,如少年进士及第被太宗召见时,有人建议他虚报年龄,以便得到皇帝的重用,寇准却凛然拒绝:“准方进取,可欺君邪!”[5]一次寇准在殿中奏事,因语不合圣意,让太宗很恼火,欲拂袖而去,寇准却上前拉住皇帝的龙袍,“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太宗感叹道:“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5]这样的性格,不仅让皇帝有所忌惮,更让朝中百官畏惧。《莱公遗事》云:“惟公推朴忠,喜直言,苟有可言者,无所顾避,故当时曰:‘寇某上殿,百官股栗。”[9]所以,剧目这样写寇准,并没有有意拔高其形象,而是依据了史实。
三、余 论
《澶渊之盟》还有一部编者为赵麟童的剧目[注]标明为“麒派京剧《澶渊之盟》剧本”,作者赵麟童,剧本存于上海京剧院档案室,案卷号为(01)2839。,然与周信芳演出本比较,不啻有天壤之别。如果说周信芳演出本为历史剧,那么,赵麟童编写的,仍停留在“传说”的阶段,其内容和民间流传的有关辽宋战争的故事一样,几乎没有史实的依据,完全按照民间的道德观、价值观、政治观、战争观和审美观来虚构。拿两部剧中的王钦若进行比较,即可看出之间的巨大差异。赵麟童本中的王钦若被写成贪图富贵、勾结敌国、阴谋篡位、陷害忠臣、欲引狼入室的大内奸,他和寇准之间的争执,不是因主战与主和的政见不同所致,而是叛国者与爱国者之间的生死搏斗,其品性与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一样。而周信芳演出本中的王钦若,一如历史,虽然品性不高,在抗辽斗争中,常起消极阻碍的作用,但绝无卖国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周信芳演出本《澶渊之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剧,与以民间传说为素材的表现宋辽战争故事的文艺作品在对待史实的态度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周信芳演出本《澶渊之盟》在处理历史问题上也有瑕疵,譬如为了强化寇准在抗辽斗争中的无畏精神,有意矮化真宗的形象,似乎御驾亲征的行动完全是寇准牵引所致。其实,历史上的真宗并不是一个苟且偷安之人,澶渊结盟之前,辽宋间发生的三次较大的战争即瀛莫之战、遂城之战、望都之战,他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尤其是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九月,当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兵从河北大举攻宋时,真宗亲临大名府督战,甚至还拒绝李宗愕等文臣在与辽军决战失败后提出的立即返京的建议,直到莫州之战结束七天之后的咸平三年正月甲午(十六日),方才从大名出发返京。他之所以决意亲自领军到澶渊,是他认识到在这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若不如此,不能最大程度地激励士气,黄河可能会失守,京城可能会沦陷,南逃更无济于事。然而,剧目对于他对局势认识的转变,花费的笔墨太少。
由上文评析可知,在戏曲的三个类型中,历史剧是最难写的。它要求剧作家除了具有编剧的艺术修养之外,还须具有卓越的史才、宏富的史学与非凡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