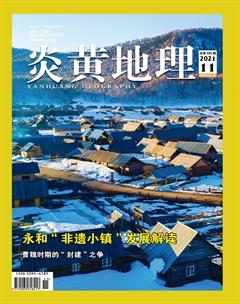黄州、惠州、儋州对苏轼的人生淬炼
王岩平

現代人喜爱苏轼的诗词文章,也喜爱苏轼对美食的痴迷,更喜爱苏轼作为鲜活的历史生命个体所具有的天真、幽默、温良、通脱、坚韧、旷达等品性。然而,苏轼的这些品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其在屡遭贬谪的多舛命运中逐渐形成的。尤其是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经历,让苏轼的生活遭受残酷的捶打,同时也让苏轼的生命得到了多重淬炼,更使其在精神上获得了超常的升华,最终让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上获得了恒久的关注、敬仰。
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心中的重要地位
公元1101年5月,苏轼从海南儋州北返拟到常州居住,路过润州(江苏镇江),到金山寺游玩时,看到好友李公麟在寺中为自己所做的画像,遂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此时已历尽劫波,从儋州万里归来,沿途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百姓的争相拥簇。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舟船行至汴梁,苏轼还会得到擢升和重用。但为何苏轼却在外人看来大有可为的人生境遇中写下这首格调有些黯然的诗作,并将“平生功业”放置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
根据苏轼年谱推算,苏轼在写这首诗时,离去世只有两月余的时间,也许此时苏轼已经预感到来日无多,彻底厌倦了宦海浮沉,心中只有超然物外的决绝。但诗作后两句又以自嘲、调侃的语气探讨了“平生功业”所系之所。整首诗造语苍凉,却又寓庄于谐。在预感也许不能留墨太多的人生晚年,在失意与自嘲交织的心境中,苏轼以此诗传达出这样的讯息:黄州、惠州、儋州是其人生中很重要的三个地方。
纵观苏轼的仕宦经历,苏轼一生分别在凤翔、汴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扬州、定州等地都做过官。其中曾两度到杭州做官,任通判(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和太守(市长),他在任期间创办了公立医院,留下了知名的水利工程“苏堤”;苏轼还在徐州任过太守,期间遭遇黄河决口,苏轼带领全城人抗洪救灾八十余天,洪水退去之后又加固徐州城墙和黄河堤防。若论“平生功业”,至少杭州、徐州这两地是值得一提的。但苏轼在人生晚年却把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视“平生功业”所系之地,可见这三地在苏轼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甚为重要,无能出其右者。通过阅读苏轼的传记和诗文可以看出,黄州、惠州、儋州承载着苏轼一生中最难忍的屈辱、贫穷、苦难、困厄、失意、孤独、绝望。这三地是苏轼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的地方,也是给苏轼带来深度生命体验和多重生命淬炼的地方。
黄州——从惶恐走向内省
1080年2月,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结案,被关押了将近五个月的苏轼在多方营救之下总算免于死罪,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史,不准擅离此地,无权签署公文。苏轼于旧年的农历除夕被释出狱,新年的正月初一便奉命启程往黄州。初到黄州的苏轼,暂住在定惠院(寺院),由于家眷尚未到达,便和僧人一起用饭。此时的苏轼犹如一只孤鸿,寂寞、孤独、惶恐、幽愤、孤高,“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乌台诗案”所遭受的不白之冤让他赴诉无门,一些原本交好的亲友唯恐受到牵连,对苏轼的书信也不回复,“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这对于喜爱结交朋友的苏轼来说更是一种新的打击。好在黄州的几位地方官和仰慕苏轼的文人对苏轼关怀有加,为苏轼带来了一抹亮色。
正值能够为国效力的壮年被贬至远离庙堂的黄州,苏轼的心理落差自然很大,故时常到附近探盛寻幽,或者到长江两岸的山边游玩。彼时并不甚有名气的黄州自然山水让苏轼开启了生命的自省模式,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闭门扫却,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良方。”苏轼一度很沮丧,“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归临皋》)苏轼也曾试图从佛教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但随后到来的二十多口家眷的生计问题又将他拉回到现实。他去东坡开荒种地,像陶潜一样躬耕自资。“筋力殆尽”的农事劳作让他体会到农人生活之艰辛。潜藏在心中的儒家思想让他始终没有忘怀士大夫的家国责任:“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在黄州不断调适着自己的内心,努力化解“处江湖之远”所带来的苦闷与彷徨。
四年的黄州谪居生活,苏轼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丰收期,写下了文学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前、后)等。这些作品是他在黄州内省的精神成果,也让后世无数身处困境的人获得走出困境的勇气和力量。从这些诗文来探究苏轼的内心,苏轼已从“乌台诗案”百口莫辩的沮丧和挫败逐渐走向不屑争辩的淡定与从容,从初来时的惶恐走向平静与超脱。“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黄州是苏轼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他曾在这个远离庙堂和朋友的偏僻之地自我省视、自我疗伤,所以他晚年回顾“平生功业”时要把黄州写进诗中。
惠州——从忧虑走向旷达
“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一直贯穿在苏轼的仕途之中,随着两党之间力量的较量,1085年之后,自黄州被召回京城的苏轼就陷入贬谪——启用——再贬谪——再启用的循环之中。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初夏,“新党”一派中的章惇为相,“旧党”中的忠义之士三十余人同时遭到贬职、流放,“独以名太高”的苏轼自然在其列,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太守。此时的苏轼已经对屡遭贬谪无甚讶异,更不屑于同一帮惯于玩弄权术的佞臣辩解,在三子苏过的陪同下从容就道,踏上了一千五百多里的贬途。在到达大庾岭之前,苏轼又接到了三次被贬低官阶的命令,改派到广东的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苏轼只好改道惠州,于1094年10月到达这个风光迥异的南国小城。
苏轼被贬谪到惠州这一年已经58岁了,苏轼在去惠州之前给朋友钱济明的信中曾有过隐忧:“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在翻越大庾岭时,苏轼说“山林雾瘴老难堪”(《过岭寄子由》)。朝政的混乱也让苏轼更为担忧,司马光已经去世,正直的老臣吕大防、范祖禹、范纯仁、刘安世等皆遭贬谪或流放。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都令苏轼忧思深重。
到達惠州之后的苏轼却发现当地的老百姓对他这个不见容于庙堂的戴罪官员十分友好,“父老相携迎此翁”,临近几个城里的太守更是把苏轼左迁至惠州看作是当地的一大幸事,争相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与大学士结交。况且“岭南万户皆春色”,苏轼很快便忘情于惠州的山水,再加上在惠州可以实现荔枝自由,所以苏轼几乎要“不辞长作岭南人”了。
苏轼在惠州的官职并无甚实权,但苏轼仍然坚守着儒家以苍生福祉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很多惠及民生的好事。他建议当地官员不要向百姓征太高的税;他还同几位太守和县令在惠州建了两座桥,并说服他的弟媳、苏辙的夫人捐出朝廷封赏的钱。1096年元旦,惠州管辖的博罗城发生大火,一城尽焚,官衙也需要重建。苏轼担心地方官在重建官衙时趁机盘剥百姓,就通过相熟的京官去监督地方官,禁止从民间征集物资,只能在当地市场公开购买,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惠州百姓更加喜欢这位心怀黎民的戴罪官员了,并希望他能在惠州定居:“邦人劝我,老矣安居。”(和陶诗《上梁文》)而苏轼也爱上了惠州。苏轼给好友王巩(因曾“乌台诗案”受牵连,被贬至广西宾州,但对苏轼毫无怨言)写信,“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已念不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苏轼的内心已从最初的忧虑重重转为坦然接受命运不公的安排,放弃了北归的幻想。“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与程正辅》)在惠州两年多的生活,没有让苏轼失意消沉,反倒让他达到心安的状态,内心从忧虑疑惧走向了达观放旷。虽然他在这里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伴侣朝云,但他却并未对惠州产生嫌恶之感,反而把惠州视为人生旅途中很重要的一处逆旅,写进《自题金山画像》这首带着自况意味的诗作中。
儋州——由惊惧走向无畏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惠州是一个没有文化却懂得善待文化人的“蛮夷之地”,连更夫也不舍得打扰苏轼睡觉。但苏轼这首随意记录生活的小诗竟然传到了京城章惇的耳中,还春睡美呢,那就再贬远一点吧!1097年4月,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
当时,贬谪海外是仅次于处死的惩罚,章惇不过是碍于苏轼在朝野的名望,不敢直接杀死苏轼,而把苏轼的生命交给一叶扁舟、一道海峡、一个瘴疠遍布的蛮荒岛屿,交给大自然的造化。尽管已经历了黄州和惠州的生命淬炼,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大、性情足够旷达的苏轼,这一次也产生了惊惧和幻灭,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苏轼启程前给在广州任职的好友王古写到:“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1097年的北宋朝廷已被章惇一帮小人操控,能够和苏轼一起为大宋这艘大船掌舵的君子辈或被罢黜或已离世,大宋在未来究竟会驶向何方,苏轼的内心也是疑惧的。
然而没想到,儋州又是一处没有文化却对文化人尊崇有加的“蛮夷之地”。儋州太守张中原本就仰慕苏轼,所以苏轼(苏过陪同)到来之后就热心为他们提供官舍居住,并经常同他们下围棋,但后来却因对苏轼太过优待而遭革职,苏氏父子被逐出官舍。当地穷读书人的子弟就动手为苏轼盖了一处房子,苏轼后来还在儋州办了一所书院。苏轼很快就同儋州百姓熟络起来,指导他们打井取水,为他们看病开药,听他们讲鬼故事,而且生蚝的味道又是那么妙不可言。这位落魄失意的贬官又一次被蛮荒之地的淳朴憨厚的百姓接纳、温暖、感动。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文化人滋养了民间,民间感动着文化人。
原本很担心瘴气的苏轼在儋州安顿下来之后给好友僧人参寥的信中说:“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得死人,何必瘴气?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苏轼被贬儋州的恐惧已被淳朴的儋州民风冲淡,瘴气已不在其忧惧之列,远亲别友、忍饥挨饿、缺医少药、无纸无墨,这些也都是可以忍受的,苏轼甚至觉得自己原本就儋州之民:“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儋州的被贬经历让苏轼的内心达到了像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的境界,走向了生命的无畏。
1100年6月,苏轼遇赦北归。苏轼父子登舟时,儋州许多老百姓挑着酒水与干粮为他们送行,如此感人的场景让苏轼也写下了名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儋州如大海般宽阔的胸怀拥抱了被逼向死地的苏轼,让苏轼从惊惧走向无畏,所以“问汝平生功业”,儋州务须在其列。
苏轼在中国文化史中可以算是经受打击和磨难最多的一位文人,苏轼在黄州、儋州、惠州这三地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磨难愈深重,所受到的生命淬炼便愈纯粹,所获得的精神升华也愈加高尚,他的名字在后世也愈加耀眼。
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