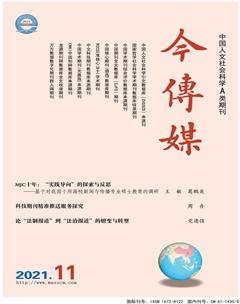智能媒体时代人文关怀回归路径探析
任泽阳
摘 要:智能媒体时代受众愈发渴望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却被“转评赞”的仪式陷入了更强的空虚感和疏离感。人文关怀在智能媒体的数据算法、消费主义、工业生产中悄然出走。基于此,本文提出实现智能媒体时代的人文关怀回归的路径需要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动力共同作用,坚持求真、扬善、创美,为实现新时代媒介内容的价值引领提供思路。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智能媒体;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1-0112-04
智能媒体时代主要以互联网为依托,以移動设备为载体,以应用软件为支撑,不仅建立了“地球村”,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更重要的是AI介入内容生成、5G赋能内容传输、VR介入用户接收,智能媒体把人、机器、社会紧密融合。不可否认智能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让受众体验到了更多的“快感”,畅游世界的快感、明星互动的快感、“王者荣耀”的快感,而快感背后涌动的是与自然的疏离感,精神的孤独感,甚至是“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媒介技术使物理距离缩短,反而成为了现代城市人生存的新障碍,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成反比,人与人近在咫尺却在精神上相隔甚远。媒介环境学对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探究,因此,媒介环境学为我们找回出走的人文关怀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 智能媒体时代媒介环境变革中的发展
信息技术正在逐渐消解传统传媒业的边界,新的传媒生态在众声喧哗中经历重构。大变革、大转型、大融合是当今媒介环境的主要特征。智能媒体时代的媒介环境,以其强大的技术力量,作用于思维模式、业态发展、群体成长,重构社会形态。
(一)新思维:智能思维,数据思维
智能思维的核心在于“智能+”,即AI新思维。基于万物互联,重新审视人与物的关系,并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战略等进行重构的思考方式。数据思维则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麦克卢汉的观点中看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智能时代媒介技术延伸了人的思维,AI介入内容生产机器学习、图像识别、自然语言语音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新闻传播行业中,媒体融合的方式将发生深刻变革。大数据的算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测和趋势分析的作用,可使创作者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内容生产,避免资源浪费。网络可视化工具可以展示社交网络上的关系网,追踪网站第三方插件的信息记录,分析话题热度和搜索频率,最终分析用户行为,服务于新闻内容和广告的精准投放。
(二)新业态:跨界融合,百花齐放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通信技术配置的数据域,是催生新经济天然的温室。在“万物皆媒”的时代,针对生物智能、人机融合的方向开展了大量硬件、软件和模式的研发,并在教育、医疗健康、交通安全、智慧城市、文娱产业等领域形成产品线,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建立与用户的连接。借助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网红经济,不仅开启了直播带货的新纪元,同时也为乡村振新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网红经济以时尚达人为形象,以品味眼光为主导,依靠社交群体上聚集的人气向粉丝进行营销,粉丝群体以实际购买力带动产品消费。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经济平台,催生了“社交+电商”双向延伸的经济模式,抖音通过个性化算法增强用户黏性,场景内容与电商生态融合;快手则是基于社区的“老铁文化”构建关系链,奠定电商发展基础。此外,智能媒体时代下数据思维、智能思维是认识的变革,跨界融合是方法的变化,从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来看,智能媒体时代的本体已超越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二元划分,媒介与社会将会融为一体,互融互通。基于媒介技术行业跨界融合发展,将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三) 新群体:高度重视,主动融入
“Z世代”主要是指成长期与互联网发展完全同步的1995~2010年出生的人,受互联网、智能设备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亚文化根植于“Z世代”群体,亚文化圈层有极强的势能,活跃度极高。该群体主要关注二次元、国潮、电竞、偶像圈等,愿意为社交性、高溢价、兴趣性、高颜值的产品买单。“盲盒经济”是“Z世代”消费取向的一个典型体现。“Z世代”一方面接受着国外的潮流元素,另一方面也更热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李宁、故宫文创、国货崛起其背后蕴藏的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二、人文关怀出走的原因
受众从接受者转变为生产者,体验到自我议程设置的快感,也催生了极大的失落感和孤独感,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感觉生活在社交媒体的“镜像世界”。智能化的媒介环境正在以强大的智能算法,以急速的内容生产、以强大的科技力量主导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过度使用智能化手段使得媒介产品蕴含的人文精神被控制。人文与科技的关系走向主客对立,人文关怀无家可归,主体性认同感缺失将导致人类疏离的状况。人文关怀的核心“真、善、美”,在日趋同质化、依恋性增强的媒介环境中逐渐被绑架、消解、侵蚀。人的主体性在逐渐走向异化,智能时代的科技霸权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一)信息茧房绑架“真”
麦克卢汉把媒介隐喻为媒介环境,即媒介可通过信息流创造一种新的环境,这种环境隐蔽性强,可通过一种无形的塑造力,使得人们在媒介营造的环境中对其浑然不知。同时,技术对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环境是浑然不觉一样。智能媒体时代,数据成为第一生产力,数据不仅可以为内容生成者提供精准的用户画像,还会通过不同的算法为用户提供消息推送。在你享受感兴趣的信息的同时,却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信息茧房之中,由此带来的是信息同质化、群体僵化的负面作用,久而久之甚至会让你认为在这个“房间”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殊不知你已被算法控制在不真实的世界中。如果将媒介社会中的人比作一个整体的钟表,那么人的心脏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游丝,关节不过是齿轮,高度机械化使主体丧失了思考“真”的能力。
(二)消费主义消解“善”
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品《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娱乐至死》中,他揭示了电视技术使得娱乐化增强,摧毁印刷时代人类的理性与知性。在《童年的消逝》中他谴责技术带来全方影像,使得童年的纯真状态趋于消逝。智能媒体最典型的特点是带来更便捷的娱乐享受,更丰富的视听体验,更刺激的感官冲力。导致我们更加趋乐避苦,消费欲望膨胀,在享受的过程中消解了对价值的判断,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智能媒体产生的注意力经济,为了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而不择手段。
(三)工业生产侵蚀“美”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如果说我们是看门狗,那我们往往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媒介内容这块鲜嫩多汁的肉上,而媒介却是如同贼一样无声无息地潜入我们的精神世界。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智能媒体时代,规模生成的内容,偷走了受众的思考能力,当理性判断缺席,丧失思考能力的受众主体,将被媒介异化。智能媒体时代内容生产同质化现象极为严重,以短视频生产为例,各种美妆博主、旅游博主、时尚博主生成的内容如出一辙。当媒介内容变成工业批量生产时,人文关怀的光晕将会消失,美的元素将被工业生产侵蚀。
三、人文关怀形成的作用
媒介环境会重构原有的社会环境,文化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在媒介环境中孕育人文关怀。从个人层面来看,媒介技术的发展有助于受众主体实现自我价值;从社会层面来看,通过构建媒介场景为展现文化提供场域,在更多元更丰富的场景中体悟到文化魅力。
(一)个人层面:有助于实现自我价值
保罗·莱文森提出了媒介进化论,媒介总是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媒介在进化中满足了人的两种需求,一种是渴求和幻想,另一种是弥补失去的东西,这是媒介的补偿性功效。马斯洛把需求层次划分为五个层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自我价值需求。当前受众越来越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并寻求心理慰藉。媒介为实现自我价值需求提供渠道,从原来内容生成方式PGC到UGC,再到PUC与UGC融合,现如今呈现出AGC的智能生产方式。受众从单纯受众,转变为传受合一,既是接受者也是生产者。普通用户在视频创作时也可以像导演一样把自己的生活进行蒙太奇艺术手段处理,用镜头语言、声画关系表达对生活的理解。
(二)社会层面:有利于构建媒介场景
媒介环境中的精神价值往往不是直接显现,而是隐藏在媒介背后,为精神价值的“在场”提供场所。梅罗维茨提出媒介情境论。电子媒介使地域构成的界限消失,形成新的时空观。通过新的情境重组构建新的信息环境,导致新的情境产生。智能媒体时代的数字博物馆、数字非物质文化遗产、VR观看艺术作品,VR景区参观等都是在打破原有的时空界限下,依靠技术产生的新体验。未来智能化的媒介环境将构建更多我们无法想象的场景,正如在罗伯特·斯考伯《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所说,大数据时代后,下一个科技趋势就是场景时代。
四、人文关怀回归的路径
回归路径以真、善、美的精神内核为引领,坚持正确的意识导向,恪守职业底线、法律红线;坚持以人文本,避免技术宰制下的人性沉沦,避免技术专制下的媒介逻辑,以文化善治、主流价值观领航。秉承中华民族接受美学的心理期待,营造东方美的意境。从而,满足受众的人文精神需求,实现人文关怀的回归。
(一)求真:以议程设置为外在动能
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受众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中蕴含着怎样的价值观。在智能媒体时代,人文关怀的回归需要通过外在议程设置的动能,主流媒体依然要坚守议程设置的核心阵地,坚持主旋律、坚守良性可持续的传播秩序。相关管理部门、专业的技术人员要履行好“把关人”的职责。当前,权力不仅掌握在权威机构,自媒体博主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着议程设置的权利。媒体人还应履行义务,遵守法律法规约束个人行为,不生产和传播虚假有害信息。
(二)扬善:以价值理性为内生逻辑
对于生产而言,生产者需要恪守职业操守,不被算法所控制。即使在智能媒体时代,算法是第一生产力。生产者与算法是主客二元的关系,生产者控制算法,让算法传递正能量,让正面声音主导社会舆论。已经到来的“赛博格”时代,使得人与机器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制度治理无法与智能时代发展相契合,应该走向文化善治。在科技向善的基础上,实现人与机器、算法、数据合理发展。数据算法坚守价值理性,有助于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监测、预警和服务。智能媒体发展应秉承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传媒创新动力的同时,更要担负起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任。
在智能媒体时代,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心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利益并非内容生产的唯一驱动力,信息弱势群体也不应被推向信息鸿沟,丢向信息贫瘠的荒漠,成为数字难民。从长尾经济角度来看,以弱势群体为代表的老年人、农民工、残障人士等很有可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也不容小觑。对于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不仅需要受众提高安全意识,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的掌握者要坚守行业底线,遵守法律法规,不触碰法律红线,不把用户数据泄露或做其他非法交易。媒介治理的动力机制要警惕单纯借助技术实现资本赋能、提高生产力的商业化发展,从资本主导的市场逻辑向追求人类福祉的公益逻辑转变,坚持价值理性的内生逻辑是媒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创美:以东方美学为内在力量
在英尼斯看来,媒介具有偏倚性。因此,媒介既要为学也要为用,不是“器”而是“道”。当前,媒介环境更应指向文化内核、民族基因、精神灵魂。林文刚在《媒介环境学》中作出阐述,“媒介即是环境”“环境即是媒介”并提出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理论命题。媒介的物质属性和符号形式具有规定性的作用,对信息的编码、传输、解码、储存产生影响。媒介环境会重构原有的社会环境,使文化发生深刻的变革。
“美”的期待是内容生产的依据,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受众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观念结构、心理图式,受到民族、心理、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定向性期待。因此,在人文关怀的回归上不能忽视受众的精神需求,应把中华民族传统人文情怀和审美价值融入内容生产中,用专业化的技术创新内容和形式。
美的意境成为内容的核心竞争力,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她的创作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带动周边东南亚一些博主生产相似的内容。在她的视频中,每一帧跳动的画面,每一个吟唱的音符,每一句诉说的言语都蕴藏着浓郁的东方美学色彩。袅袅升起的炊烟,缓缓降落的夕阳,潺潺流动的水声,生活静穆而恬淡,仿佛走进了陶渊明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境界,又仿佛看到了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再或者着走进了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禅境。智能媒体为实现“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和“忘我之境”三種境界提供更便利的条件,通过媒介建构的一系列审美符号,传达出特定的艺术表征形式,实现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审美反思,这些空间符号恰恰弥合了主体异化的精神生态,实现主体间的精神交流。
五、结 语
在媒介环境学视角下,智能媒体技术的发展是助力文化繁荣的重要手段,两者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过度重视科学技术而忽视文化传统,甚至将技术视为媒介主导因素将走向唯科学主义的歧路。人文关怀的回归是人的精神需求,当人文精神领域被科技侵占,也许阳光将不再明媚,鸟儿将不再歌唱,鱼儿将不再畅游。乡愁也将会是残缺的邮票,过期的船票,无法到达的坟头,那时我们是否还能回到精神家园?诗意的栖息也许将如梦一般美丽。未来发展应人文关怀与技术关怀双管齐下、双轮驱动,技术向善成为自觉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华君,涂文佳.5G时代全媒体传播的价值嬗变、关系解构与路径探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4):1-5.
[2]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廖祥忠.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的三大问题[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1):1-6.
[4] 徐琦,赵子忠.中国智能媒体生态结构、应用创新与关键趋势[J].新闻与写作,2020(8):51-58.
[5] 龙耘,吕山.AI时代媒介治理的伦理体系:内涵、特征及实践原则[J].现代出版,2021(4):32-38.
[6] 胡翼青,王焕超.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4):24-30.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