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风景话语与民族认同
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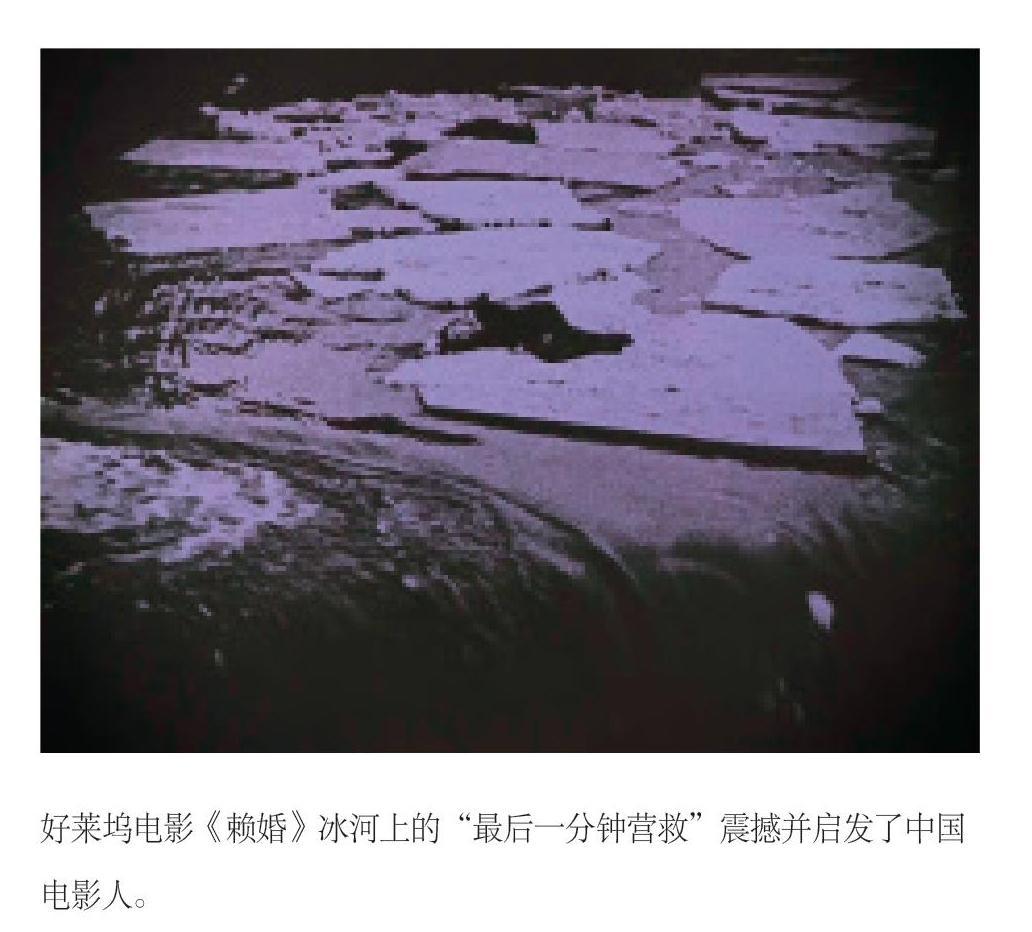


【摘 要】 风景是近年来西方艺术研究中的关键词。风景与权力、风景与绘画、风景与记忆、风景与民族认同等议题都受到关注。西蒙·沙玛、温迪·J.达比、W.J.T.米切尔等学者从人文地理学、艺术史、绘画史、人类学、文学等角度展开研究,释放了“风景”跨学科、跨越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研究范畴的潜能。风景话语在中国早期电影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在好莱坞电影“影响的焦虑”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通过风景话语探路东方美学,将中国诗学传统融入早期电影的视觉风景中,实现了民族认同和现代性的交织,促成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主体性显影。
【关键词】 风景;民族认同;景语;族群景观;湖区场景
风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中国型”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的名山大川、各色风景伴随着电影走向普罗大众。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话语的风景介入了观众的国家和民族想象之中。风景不同于环境,马丁 · 列斐伏尔(Martin Lefebvre)通过辨析“风景”(landscape)与“环境”(setting)的概念[1],揭橥电影中的风景话语,是由观察者的文化背景能动地决定的,“风景如今构成一文化习惯和感性,其形自现”[2]。镜头唤起了观察者对风景的凝视,是电影和风景的中介。中国早期电影人对风景的论述如吉光片羽,却富有真知灼见,对于风景与政治、民族身份认同的论述体现了早期电影人对风景的政治介入的可能性的认识。在好莱坞电影的风景话语影响下,中国电影从业者一方面以中国式的诗学思维去分析理解它,另一方面又摄制国内胜景,能动地建构东方式的风景话语。回顾中国早期电影人关于风景的论述,围绕着风景话语的文化自觉一直贯穿其中。中国早期电影既有《燕山侠隐》这样对风景的直接纪录,也有影评人对好莱坞电影《情铁》(Hearts Are Trumps)中风景话语的创造性“误读”。在对“风景的凝视”中,观察者暂时中断了动作与叙事的联系,还原了空间的自主性,实现了观察者对空间本身的思考。这时,风景话语脱离了导演的主观意图,其意义取决于观众和他们的文化背景,这是风景在电影中存在的主要方式,也是观众在电影中体验风景的主要模式。
一、风景与民族身份认同
风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建构自身文化主体性起到了重要作用。1919年,商务印书馆在给北洋政府的呈文《为自制活动影片請准影片免税》中,便开宗明义地强调:“外国人在中国拍摄影片运往国外者‘又往往刺取我国下等社会情况,以资嘲笑。”[1]对此,商务印书馆拍摄了《长江名胜》《普陀风景》《西湖风景》《南京名胜》《钱塘观潮》《庐山风景》来提振民族自豪感;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拍摄《倭子坟》[2]《南京风景》,民新公司1925年拍摄《安徽九华山风景》,同年长城画片公司拍摄《西湖风景》……中国早期电影人自觉地通过风景片,来体现文化主体性和民族身份认同,并在风景片中或暗指或明说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人与风景之间存在着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识形态和恋物化的认同”,“土地修辞学能够负载政治性的绝望和愤怒”。[3]
《申报》上署名“忍讽”的作者,献策历史剧本选材时,建议把风景话语融入革命话语和中华民国成立史的书写,在拍摄武昌起义、清廷逊位、孙中山任大总统等关键事件时,将中国名胜摄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坟和北京的皇宫都可入选”[4]。相较于单调的风景纪录片,忍讽将历史故事、新闻事实与风景话语结合的思路,体现了风景话语从吸引力向叙事性的转变。风景被不少制片公司自觉地纳入革命话语,比如复旦影片公司摄制以清初历史为题材的影片,将郑成功的事迹解读为革命,“南洋华侨对郑氏革命事迹,莫不熟悉”[5],外景全部取自福建,水操台、读书处、屯兵地、演武亭均实地拍摄。又如《王氏四侠》用古装剧“解释现代的革命思潮及其起因”[6],危城古堡、景色萧疏,别具风格。
中国观众充分感受到风景话语的叙事性力量,始于《赖婚》(Way Down East)、《待客之道》(Our Hospitality)等好莱坞故事片。《赖婚》中,戴维和安娜并坐于绿荫芳草,喁喁情话,“遥对两道飞瀑悬崖直下,谁不发生一种惊人的美感”[7]。这和《孝女沉舟》中的曲江幽花等风景话语功能相似,能引发观众的美感,美景还用以衬托其爱情高洁,并使观众神往、代入和同化。国产片一开始尚不具财力摄制精致的外景,如《父母的希望》中有闲听瀑布的场景,但背景中的瀑布明显是画片,美景仅被片方用作营销的噱头。如《红荷花》中有一幕在瀑布前拯救情人的戏,假瀑布竟也被夸为“胜《赖婚》中之冰瀑百倍”[8]。《赖婚》结尾冰川奇观的“启蒙”,引发了一系列的模仿和“竞争”。《赖婚》在中国放映后,观众将风景作为评判电影的一项关键因素,默片时代“凡是天然美丽的影片外景,是极受一般观众的览赏的”,“尤以美国西方做背景的影片”,因为其“怡心悦目的山水景”为观众所欢迎。在好莱坞电影风景话语的影响下,国产电影“以这种天然美景的趋向,导演者差不多都于每片仲(中)加多外景的接驳”[1]。
在20世纪20年代,有风景片、纪录片与故事片联放的习惯,尤其是同一公司出品的影片在一起联放,更容易超越单一影片,凸显制片方连贯的内在逻辑,且在电影类型、情绪、内容、商业策略等方面形成互补。如新中央戏院放映《好男儿》时,加映明星公司的西湖风景影片;大中华百合公司摄制的关于中国飞行家的纪录片《广州号抵沪》与《热血鸳鸯》联映,《广州号抵沪》激发的民族自豪感与好莱坞电影的联合放映,体现了片方的商业民族主义策略。
除了《赖婚》的水景,孔雀公司译配的好莱坞影片《热血鸳鸯》(Hearts Aflame)[2]则在火景方面引发早期电影人的注意。《赖婚》等“均以水景之险为观众所欢迎”,国产的火景片甚少,而且多通过拍摄时“所假近者”实现,而《热血鸳鸯》的制片公司则购买了一座森林铺设轻便铁道,放火烧山,火势大涨后,“有青年男女在烈焰中乘机关车来往”,剧组动用了20部摄影机布于四周,“故各方面之火景均得摄入,真从来未有之大观”[3]。《热血鸳鸯》公映的当年,早期影人便推出了火景片,如《苦儿弱女》主打“焚烧真屋”,火景“最有精彩”。[4]电影报刊上推出“揭秘”火景倒摄正放的实操文章等。“火景”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北伐胜利,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泪世界”的感觉结构发生转变,感伤情节剧逐渐让位给注重身体和冒险的“火景”武侠剧,如《火烧红莲寺》及一系列跟风之作等,风景话语的嬗变指涉了情感世界的转变。包卫红将“火里英雄”的形象与海派京剧、中国现实和民族认同结合起来进行分析:1916年根据西方侦探小说《火里罪人》(The Sinner in the Flames)改编的新剧《就是我》,是一出轰动的现实主义剧(sensational-realist play)[5],舞台上的水牢和火都是真实的,在包卫红看来,武侠电影中的“火景”滥觞并非是电影类型的自然进化使然,而是电影与海派京剧、好莱坞电影的竞争所致,电影无法像剧场那样与观众互动,于是通过身体与火景的互动,来表达现实的感知,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勾连同构。少飞对于火的说法,颇能反映时人的心理,火可以“烧毁罪恶、照耀光明”,“一个人小天地中燃烧着的爱情的烈火、烈火、烈火,是爱情具着伟大力量的表征,超过世界上任何伟大的力量,太阳如张开血盆似的大口一般地升起,打首领无所寄托之热情,正向着此永远千古的精神里加快逝去”[1]。
此外,好莱坞的救火队员题材影片也影响了“火景”片的创作。哥伦比亚出品的《火窟鸳鸯》(Scars of Jealousy)、米高梅的《救火队》(The Fire Brigade)都在国内上映过,后者在少年救火队员与富家女的恋爱故事中穿插救火队员的生活场景。火景的使用还跟演员的专业素养有关,演员张惠民本身就是救火队员出身,因此频频在电影中使用火景。他编剧、主演的《海外奇缘》《火里英雄》都有火景,前者是火中格斗,后者不仅将1928年8月18日万人争看钱塘潮的场景拍入电影,还有张惠民饰演的国雄在猛烈火光中,从七层楼上抱着女主角娟娟一跃而下的场景,片中穿插了救火队员拿水龙头嬉戏、练习救火的场景。
在处理天然外景时,电影人所采取的策略是“所含‘美之分量低微,则以人工帮助其天然之不足”,且早期电影格外注重“外景之章法尤须具审美之眼光”;但同时风景一定要为人物和故事服务,“首先根据剧情之需要,再又审辨剧中人之性,及其环境”。[2]“电剧外景的摄取,固然有着天然的景物,比舞台剧的全恃布景来得容易。但要求适合剧情的背景却也很非易。”[3]一开始,国产电影的外景取材,对苏杭、庐山美景有滥用之嫌,演员表演、剧情不能与风景形成有机互动交融。有的影片因为太注意外景,“完全取景于杭州,几乎无一幕,不在西子湖畔,把杭州著名的胜迹和著名的庄墅极力介绍,因为要介绍风景的缘故,不得不把演员的动作敷衍延长,观众对此天然幽蒨的风景,有如卧游,要叹为观止了。因为别的影片中,也有采用杭州作背景的,可是万万比不上他……对于剧情一方面的兴趣,却因此而减了”[4]。中国早期影评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外景与叙事的关系,如分析《骑石者》(The Stone Rider)中的外景,不合理的、歪曲的建筑线条与故事情节相辅相成,“很吻合当时的故事”[5]。
中国电影初创时期,受制于制作成本、人才和技术,无法与好莱坞电影正面对抗,早期中国电影摄取天然美景时由于交通不便,以致裹足难行,只好就近摄取外景。以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出品的《松柏缘》在天平山等地取景为例,早期电影初兴之时,外景摄制地“不是西湖就是天平山。把几个离上海近的名胜地方都让观客在银幕上看得熟而又熟了”[6]。好莱坞则“一年四季之景物,可无容费许久之时间,亦可得矣”[7]。中国电影的“小资本和初学的表演”,远不及好莱坞电影,像制片巨头美国环球公司即便有世界各地的人工内景,仍旧外出寻找文学意味的“地方色”[8]。美丽的花草树木,明媚的山水之类的“美术这东西”,则“很能振起对方的精神”[9]。早期电影的置景亦捉襟见肘,盖不起玻璃棚,若经过“一阵微风那么更笑话百出了,好好的墙壁竟会颤动,好好的电灯字画也大摇大摆起来了”[10]。
随着《孤儿救祖记》带动民营电影资本的兴起,国产电影公司开始在玻璃棚里搭外景。风景补足了叙事的疏略和表演的生涩,如《火里罪人》,“结局似不合情理,不过那遇熊时的几幕却补叙得很圆满”,天平山景是“该剧中最有精彩的所在”。[1]
中国早期影人认识到,外景并非需要绝对美景,关键是能否通过调度、摄影拍出美来。中国早期电影人以好莱坞电影《渔家女》(Tess of the Storm Country)为例,认为《渔家女》的外景很少,陋弄荒野、河边屋内的简陋未必不能成为美景,关键是“摄影机之能否得其宜耳”[2]。
随着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人除了在电影中直观地展示风景,将风景用作单纯的“美术”来提振精神,还试图将风景融入叙事,转化为叙事场景,承担叙事功能,通过风景和场景体现民族性格。好莱坞电影《边外英雄》(The Covered Wagon)[3]的风景话语与美国的垦边精神结合,描写美国人开辟西部的故事,“见到美利坚伟大的国民性了”[4]。《抱得女儿归》(The Winning of Barbara Worth),讲述沙漠殖民史,“其理想欲变沙漠成为耕植之地”[5]。国产的《殖边外史》脱胎于《边外英雄》,“发挥吾国之耐劳习苦之国民性”,“垦殖为富国强民之基础”[6] ;中国人“辟一个新天地,避去那种普通言情影片陈陈相因的习惯”,“发挥吾国伟大的国民性”[7]。《殖边外史》外景取自绍兴、杭州、郑州、洛阳等处,片中穿插了乡农工作、吃饭烧菜的生活场景,黎明晖饰演的阿贞表现出家庭生活中“一种极普通的性情”。
然而,《殖边外史》的观念先行与成片对生活细节的处理失真,让此次探索几近失败。影片中胡天八月飞雪,角色穿的都是单衣马甲,始终未换其他季节的衣服,与真实生活不符。影片把郑州当作边外来拍受到诟病,郑州风景无法体现边地的特點。除了边地场景名不副实外,风景上的虚假也被影评人指出来,之江以南、徐州以北的树林和中部的不同[8],浙南多杉树,齐鲁产柏树,江淮间柏树不茂,种杉不育,故青松为多。而且边外和中原的植物也差得远。与之对照的是,好莱坞电影中的风景“牺牲巨大的资本,并由专家指导”。村夫以某外国电影为例,虽然是爱情片,可是片中的伐木、运材、锯板、出口以及森林失火施救的场景甚至达到了教育片的科学严谨和真实,“福特公司的教育片,堪与颉颃”[9]。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长年战乱,外景拍摄颇为受限,同时电影制作单位的资本单薄,就近的“金陵道属的六合金坛溧水句容等县,荒地荒山,不知若干万顷”,更适合拍《殖边外史》。《殖边外史》移民殖边的场景,车辆衔接而行模仿了《边外英雄》,对好莱坞垦边电影的机械模仿,被认为“缺乏创造的精神也”[1]。
好莱坞电影所张扬的冒险精神,主人公在名山大川活动,探险、夺宝、打斗,也影响了国产电影的风景话语。“冒险电影,类多注重外景,且须天险奇景,为人迹所罕至者,欧美电影因摄冒险表演而至牺牲者,时有所闻”[2],当时国产的冒险类电影和冒险场景,大多通过“摄影术以成之”。张惠民主演的《白芙蓉》外景在汕头、厦门、潮州以及沿海深山中摄取,摄录了崇山峻岭、危崖深谷等天险奇景。《白芙蓉》中有一场救白芙蓉的戏,张惠民饰演的主人公须越过一绳桥,桥架在二山间,下面是深谷,张惠民上了绳桥,绳桥却被贼党砍断,张惠民顺势下坠,绊在古树枝上,场面惊险。片中潮州瘦西湖等外景,皆用彩色染成青山绿水。除了张惠民,其兄弟张慧冲在《劫后缘》中“跳楼及危崖悬索数幕极见精彩”[3]。联合公司出品的《情海风波》在普陀摄取,“以写真含有美术为前提”[4]。《情海风波》原名《水落石出》,大海是洗清沉冤的重要意象,同时又是沉冤发生的关键场景,片中胡礼国对狄志光的诬陷,就源自于他在海边遗落的水果刀。张慧冲在高崖肉搏,扑浪涛声,“仿佛观美国电影明星范伦铁拿之影片”[5]。《关东大侠》取景虞山,主人公在悬崖石壁恶斗、攀绳越城。“尚武”一方面是对标好莱坞同类型电影和明星,便于商业标识;另一方面则是体现中国人的强健体魄,洗刷好莱坞电影中华人的病态形象,提振民族精神。
W.J.T.米切尔(W.J.T. Mitchell)认为,“风景的再现不仅事关国内政治,民族或阶级观念,也是一种国际的、全球的现象,与帝国主义的话语密切相关”[6]。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建筑和其社会有内在文化上的一致性,遍布“次殖民地式的建筑”“充满了烟煤的空气、充满了诱惑的环境”[7],上海被认为不配做中国的好莱坞。当时北京观众评价上海出品的国产影片中,男演员女儿态过重,像拆白党;女演员则往往不似良家妇女,“这都由于摄影场所设在上海所受的恶影响”。因此,陈大悲主张在中国开辟“新好莱坞”,杭州风景如画,“是画景的世界”,现代题材的影片可随处取材。至于历史影片,则“非到北方去拍摄不可”[8],一是黄河以北存留着不少富有汉族色彩的古建筑;二是北方有民风雄健朴厚的古人之风。到20世纪20年代末,《木兰从军》的外景横跨直、豫、鄂、湘,以古喻今,呈现一幅流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图景;《黑猫》泰半取景北地风光,辽阔空疏,江南观众见到“感到特殊之快感”[9]。
二、景语即情语
在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理解中,风景不等于自然,电影的风景话语与传统诗学画论更具有亲近性。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中写道:“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道:“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风景话语被用来理解电影中的表演和情调氛围。“爱情片中不可无好风景观以衬之”[10],当时电影能充分使用景语,便被认为是艺术的。
在中国早期电影的理解观念中,风景话语引发了震惊、暴力体验等视觉性经验和周蕾所谓的“原初的激情”[1]。因此,在电影的理解实践中,中国早期影评人通过略显“陈词滥调”的文字去对应风景话语呈现的视像,反倒颇为贴合。如点评好莱坞电影《情铁》时,片中的雪景与爱丽斯塔的表情被联系起来,片中雪山上的冰块雪团如簇而下,大雪纷飞。这场奇观与“拒绝强暴一幕之表情”呼应,在对爱丽斯塔表演的表述中,“艳若桃李,冷若冰霜”[2]等表情被影评人用文字与雪景联系起来。这体现了中国电影人的“空气”美学思维,冰冷的景观,营造了一种整体的冰冷“空气”。形容女性贞烈与美艳不可方物的文字修辞,将片中的风景话语点染出一种女性气质和女性视角,从剧情来看,风景话语是为了突出叙事层面角色所面临的困难,爱丽斯塔倒在了暴风雪中;而借助汉语表达引申出的这层理解,体现了时人理解好莱坞电影的思维方式,时人的影评文字“冷若冰霜”与风景话语的联系激活了情景交融的共情想象。
在中国的诗学和画论中,一般用“山水”指代“性灵的风景”。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宗炳的《画山水序》写道:“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风景能够引导人,在品味和体验风景的过程中,实现精神的愉悦,提升自身的性灵。陈醉云将中国诗学画论中的山水哲学和风景话语引入表演教育,并称其为“艺术的感化”,“最好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常常去游览附近的山水名胜,使心胸开展,神志清明……老是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面,耳朵听见的,不过是些小贩叫卖的声音,有时候闲着没事做,也不知不觉地会学小贩地声音”,风景可以使人“钟灵毓秀”,“山水秀丽的地方能够产生人才”,“要在银幕上显现高雅优秀的内心表演,还得去和高雅优秀的山水親近”。[3]
在中国早期电影观念中,风景话语要参与叙事和情调氛围的营造,有影评人以贾克 · 柯根(Jackie Coogan)的影片为例,黄昏日落,贾克 · 柯根站在灰白色的高大墙壁下显得孤零渺小。惨淡的月华,映着年老失意的乐师拉着小提琴,悲凄的情调跃然银幕。有些国产影片尽管风景美丽,但与影片的情调冲突,最终影响了表达。如《女侠李飞飞》将“扁舟容与于水清明媚,柳细风轻的景地”用于一个悲惨的故事便不太成功;若能像诗歌一样表达“月夜归棹”“凄怆的情调”,便“颇有艺术意味”。[4]与影片情调合辙的影片则言近旨远,如《不堪回首》中的河埠、寓舍等野景幽秀可爱,“少年从冷屋中出,举足踌躇,惘惘然没有去处,全局戛然终止”[5],意味悠然不尽。
中国早期电影人在建构风景话语时,格外注重风景的动态美。早期电影人注重风景内部错落点缀,节奏上如展名画家手卷。程步高认为,“自然界中的静美,造成动美,全在摄影的功能”[6]。近年从海外发现的《风雨之夜》残片取景绍兴,摄影师周诗穆“就山阴道上摄来、古木遥水、长堤曲水、危桥小径、密雨斜风”,脱离了风景片中把所有景色都铺陈在观众面前的窠臼。风景片常常“长江大河,一大片白茫茫地,使人一览无余”,内部缺乏动态的叙事和抒情功能,而《风雨之夜》使用了长焦镜头拍风景,在前后景的虚实变化中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外景清丽幽雅、幻景清晰。影片通过镜头表现的山水田园之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城市文化礼崩乐坏的补救和寄托,在叙事性的场景中,导演则颇省笔墨,“回忆兵燹情形,仅见烟火,既省事,又不离剧情”。[7]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风景话语,注重与传统诗学相通,注意风景中的时间流动。文逸民导演,留日摄影师洪伟烈掌镜的《儿女英雄》,外景多摄自苏州,给人“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小朋友》中的游船外景,孤帆、晚霞、画舫、明灯和木头人戏台、傀儡戏台都出现在银幕上,黄昏夕阳残照的水光泛红,与明月初上的扁舟碧波相映成趣,夜阑珊后的万籁俱寂,月落后的黑夜沉沉,红日东升的雀噪树梢,熹微晨光中舟行荡漾,只见玻璃罩里的灯光由舟中射出,一场有一场的景致,一场有一场戏的情况,诗意犹如苏东坡的《赤壁赋》月夜泛舟。
中国早期影评人敏锐地注意到了风景话语的音乐性,在对好莱坞电影《情天劫》的外景评价中,朱认为其“明茜悦目”,尤其是片尾江流钟声的“清韵逸响”,“好似从幕中透出”,洗涤了观众的“不满意”,影片附带说明书中的“‘江流自千古,钟声吊夕阳也满含着诗意”。[1]朱的说法与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的概念不谋而合,默片中的风景“发出”了清韵逸响,风景作为声音的造型因素出现,“无声电影时期由影片造型结构本身负载着的那种内在‘造型音乐。这一使命多半由风景来承担。这类在影片中作为要素的情绪性风景,便是我所谓的‘并非冷漠的大自然”。“无声的面孔能从银幕上‘说话一样,图像也从银幕上‘发出音响”,“因为风景是影片中最自由的因素,最少承担实在的叙事任务,最能灵活地表达情绪、感情状态、内心体验……朦胧多变而只有音乐才能充分表达的那一切东西”。[2]
风景还被用作内心视像,体现人物的主观世界和心理幻象,风景能用自身的感染力塑造恐怖“心理学之眼光”[3]。德国电影经常通过山峦危立、古木森然、崇阶高楼、羊肠小道、曲径幽深、荒野千里等来体现噩梦的可怕。万籁天执导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被侵犯后的幻想,亦通过怪石崎岖、洞穴潜伏、妖魔盘旋作势、阴森如入鬼窟来体现心理恐惧和创伤,突破了国产片以牛鬼蛇神突目吐舌来表示噩梦的窠臼。
出外景即“外景拍摄”,“一般指以自然环境或生活环境作为影片的拍摄场景,如原野、山川、村庄等自然景物,城市中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以及内景搭设的室内场景……专指走出本埠以外拍摄和影片内容有密切关系的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4]。中国电影第一次“出外景”是《红粉骷髅》剧组在苏州外拍,在苏州宝带桥拍“水中搏斗”,还发生了演员误入漩涡而死的悲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出外景不啻流动的社会空间生产,剧组在不同的地域,或反复在同一地域拍摄,除了将风景吸收到电影中,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还将现代性的文化实践—拍电影,与现实中的生产关系、生活秩序互动碰撞。出外景是现代性的“液化”(liquefaction)[5]过程,在农村拍外景时,经常与传统的封建观念发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融化瓦解了封建传统。《好兄弟》剧组在杭州拍外景时,有一场戏是恋人间相追,被群众认为是侮辱女性,群众围住演员殴打;《小情人》拍外景被乡民认为不吉利;《殖边外史》剧组在绍兴、郑州两处遇到了拍摄障碍,经过几番努力,“使民智不大开通的乡民都破除了迷信”,“感化了那班不知影戏为何物的乡民,也在影片中现身,并且有五六百辆牛车,也作片中的点缀物”[6]。《殖边外史》的外景被周瘦鹃赋予崇高感,称其伟大高妙。《难为了妹妹》在杭州蒋庄拍摄片中最悲痛一幕时,演员与角色的“感情同化”,边演边失声大哭,旁边的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被感动。在城市出外景,则在都市空间建构了现代的感知空间,电影风景对城市空间的“征用”,与居民的城市生活构成了现代性的自省关系。天津英美公司的Three Castle电影院,于1924年12月24日上映哈罗德 · 劳埃德(Harold Lloyd)主演的《永不示弱》(Never Weaken),当晚,英美烟草公司影戏部在该影院门口和院内拍摄电影,前往看电影的观众都有被摄入的机会。摄成的影片仍将在该院放映,“故是晚前往观戏者,较往日尤多”[1]。与之相似的是苏州观众喜爱电影的原因,平均每个月都有一两家电影公司来苏州拍摄,到了阳春三月更是有两三家电影公司不期而遇,“因了这一点,苏州人格外高兴,听见这部影片里有天平山、灵岩山、留园、西园的背景,一定要去瞧瞧。指点旧游之地,更觉得亲切有味啊”[2]。闽南观众喜欢看本地风景[3],复旦公司的《通天河》外景取自厦门,上映当日就已经满座,即使如此,后来的观影者还是络绎不绝。
中国早期电影外景多在上海周边或苏浙地区的苏州、常熟、无锡、绍兴、杭州、宁波、温州、扬州等地拍摄。因为外景之取材,大都在上海租界内的各马路,要么在半淞园,要么在富人的宅邸前。海景大多在吴淞,山景则在苏州天平山等各处取景,稍远点及至杭州普渡等处,已算极远的行程。由于公司周转资本的原因,摄制周期不能太长。要想出快片,只能就近摄制。长此以往,布景就“江浙化”,“故每一片出,观众都能指示何景为何地所摄,何景脱胎于何片,致观众信仰新片之心,因而减少其兴味”,中國适合作外景的名山大川、浩瀚戈壁,不知凡几,风景成为民族想象的公共媒介,驱动着中国早期电影的取景范围越来越广。在中国早期电影报刊中,不时有关于本地取景与提振本地电影业关系的论述,同时,自觉地将本地的风土人情融入风景话语。电影中的美景“引起欢迎国产影片之动机”,“使观众得以游佳景之乐”。[4]
为了给观众新鲜感,《飞行鞋》《大义灭亲》剧组奔赴庐山取景,后者把名胜古迹都摄入片中,《大义灭亲》的室外背景有黄河、铁桥、火车、三叠泉飞瀑、铁船山云海、大林寺天桥、御碑亭夕照、黄岩寺石塔,“尤以牛乳色的叠泉及夕照为最美”,“得见庐山真面目”。[5]在处理内景时则缺乏美感,公堂和会议室的部分光线太暗,同时,与风景片中对风景的处理相类,“缺少动性”。程步高推崇景物的动性,若没有动性,就要制造动性,比如将摄影机装在火车头或者火车尾部。上海观众对闽粤的风景美丽“但闻其名,未能身列其间”[1],为此,《海角诗人》《复活的玫瑰》剧组专门奔赴香港,选峻岭和清丽大海为“绝俗之境”,将风帆沙岛、波光涛声、高崖崇川、灯塔危矶悉数摄入;《白芙蓉》《情奴》《夜明珠》等剧组奔赴闽粤二省拍外景;大中国公司摄制的《貂蝉救国》《七擒孟获》《玉泉山》《姜子牙》在南京、苏州取景。
电影人还尝试改进风景的摄入质量,梅雪俦在无锡拍摄梅麓鼋头渚等名胜时,使用新设备将近景拍出模糊的意味,“较原来背景,更形美丽”[2]。周诗穆委托美国万国新闻社范济时购买了袖珍摄影机,在《探亲假》《美人计》中使用,尤其是在苏州、镇江拍《美人计》外景时多有使用。《守财奴》剧组在宁波摄取天洞等景色时,使用了一部德国新式的摄影机,能在极暗的光线中摄取风景。
出外景还播撒了电影的“种子”,刺激了取景地的电影事业发展。《白芙蓉》在汕头取景,催化了汕头影业发展。蔡楚生就是通过参与《呆运》的摄制,生发了向往电影之心。出外景还刺激了取景地发行放映业的发展,如杭州青年会电影部等机构与神仙影片公司签订协议,凡该公司出品赴杭开映,其放映权须属青年会。
三、风景话语与“族群景观”
张英进在使用风景话语批评中国当代电影时,在国族电影和导演代际分法之外,提出了“自然风景”“心灵风景”“民生风景”(ethnoscape,一译“族群景观”)[3]三种分法,通过对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风景话语的梳理,将国族与个人、意识形态与艺术本体等二元对立的表述整合进风景话语。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无论是作为主流受众组成部分的南洋华侨,还是上海熙熙攘攘的各色电影受众,乃至片中的各种流动人口,都构成了中国早期电影中的族群景观。族群景观是“游客、移民、难民、流亡者、异国劳工以及其他迁移的群体和个体,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着民族之中(及民族之间)的政治。这并不是说,由亲缘、友谊、工作、休闲、出生、居住及其他关系形式所构成的、稳定的社群和网络已不复存在。但它意味着,这些稳定性与人群的流动处处经纬交错,因为更多的个人和群体都面对着不得不迁移的现实,或怀有迁移的幻想”[4]。通过残存的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及文字记载,仍可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族群景观记载,以及影像本体和风景话语如何表里互证。
在20世纪20年代,人口的流动规模和频次尚未像全球化的今天这般,但南洋华工和侨胞已经是影响中国电影制作的重要参数,如天一等公司在南洋设立办事处,任矜苹、郑益滋在南洋活动,各大片厂的选材、风景话语也受到南洋口味的影响。“当时私营公司的经济不可能到南洋去拍实景”[5],因此,直到1932年拍摄《母性之光》时,美术师吴永刚也仅仅是在杭州山区择地制作了南洋矿山的场景。因此,在20年代,南洋族群景观几乎不能直接出现在国产影片中,其审美口味和个人意志,通过风景话语与故国保持互动,电影中的风景话语在某些时刻必须适时调整来满足侨胞的故国想象。苏杭等风景名胜的外景,在很大程度上用来“满足南洋观众追求新奇的观赏口味”[6]。南洋侨胞“大半经商,工余之暇,亦未必尽嗜电影”,“欧美影片,开映虽多,而华人观者则甚少”,国产片受欢迎的原因,一是为爱国心所驱使,二是侨胞“渴慕故国之风土人情者,然而重洋万里,修阻云山,则惟有藉影片以消其渴忱”[1]。《上海之夜》《透明的上海》等以上海命名的影片,某种程度而言或是为了满足南洋华侨的上海想象。
此外,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上海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地缘、亲缘、阶级等多种元素经纬地分割了人群和社群,如《上海一妇人》《多情的哥哥》等;当时北洋军阀混战,导致了大量的流民迁徙,“非战”影片中的流动人口构成了流动的族群景观。在历史战争片《木兰从军》中,导演侯曜在湖北省花园镇选中一条沙河为《木兰从军》的背景,冬天干涸,河底全是黄沙,“面积长约20余里,广约10余里”,“河边有怪树衰草沙丘,很像一块沙漠”。[2]族群景观在侯曜的影片中或在场,或以“抽象的人民”[3]的形式出现,但从《木兰从军》的摄影记录中,可以发现族群景观在自然风景和心灵风景间的转换与相互赋能。在拍摄《木兰从军》的过程中,侯曜从赴孝感的京汉火车上眺望窗外的景物,直到夕阳西下才回自己的座位,“闭目冥想刚才所见的一切,我眼膜上所留给我最明显的印象,就是一班可怜的老百姓的彩色的面孔和终日不展的愁眉……愁眉苦脸。这就是现在中国人的生活”[4]。耐人寻味的是侯曜观看火车外百姓的族群景观时的视觉构造和观看位置,从火车的窗框往外看,无异于从火车上观看到的一幅幅快速闪过的人群拼成的“全景画”(Panorama),从白天到夕阳西下,时间的流动和光线的变化,在侯曜的眼膜上过滤出老百姓彩色的“愁眉苦脸”。眼膜所换喻的视觉行动,在侯曜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海角诗人》中视力复明是对爱情失而复得的象征。
即使像《赖婚》这样确立了早期好莱坞叙事规范的故事片中的冰川雪景,依然具有汤姆 · 甘宁(Tom Gunning)所谓的吸引力(modernity of attractions)特点,以及现代性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特点。在张真、付晓红等学者的研究中,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雪景”有“异质性”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对《赖婚》的模仿。事实上,回到历史语境,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雪景充分具备现代性的“吸引力”“碎片化”和“异质性”三个特点。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制作中心,拍摄大规模雪景的条件先天不足,雪景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中较为稀罕的风景,对南方观众和南洋华侨具有吸引力电影的属性,在南方亦是异质的。范烟桥曾在济南小广寒影院观看苏联电影《雪里鸳鸯》,他认为片中情节“殊弗合于逻辑”[5],但片中的冰天雪地在国产影片中罕见,雪景对处于热带气候的南洋观众来说是奇观。张真认为,“亚热带地区上海和附近江南地区的影迷,以及热带地区的南洋(东南亚)华人”[6]喜欢国产电影,却“从未见过暴风雪”,并把1929年的影片《雪中孤雏》中雪景归于对《赖婚》雪景的模仿。事实上,中国观众在国产电影中见到雪景,应始于1924年的《好哥哥》,“雪景为最佳……为我国自制片中所仅见”[7]。“今年的雪是三日晨第一次下的,明星公司即于当日把他摄取插入《好哥哥》中,手段既敏捷情节又吻合。”[8]这一即兴创作收效甚好,小演员“舍命狂奔于寒天风雪之间,其时其境倍觉惨苦残忍”[9]。1927年,《天涯歌女》制造了人造雪景,沦落天涯的歌女在一个沉黑的雪夜彷徨奔走,无家可归,终受寒气袭击跌倒于深雪之中。其孤苦凄楚和《赖婚》中丽琳 · 甘煦雪地狂奔的戏,“同样的使人得着深刻不忘的印象”[10]。风景话语一方面承担了叙事,一方面又制造了奇观,在与好莱坞电影的对话中,做到了在地性的风景呈现,同时又通过雪景等自然景观的影像叙事,满足了南洋华侨观众的故国想象。
四、中国湖区场景与民族话语
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过程中,“湖区成为早期风景旅游场所”[1]。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后,上海到杭州等地的短途旅游迅速发展,“旗营既毁,新市既开,沪上来此朝发夕至,愈觉便利”,西湖“几成中国之大公园”。[2]旅游业的发展刺激了电影观众对风景的观赏期待,得益于交通的发展,与上海的毗邻位置,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和绝美的自然景观,杭州西湖成为中国早期电影银幕上的代表性场景:来西湖取景的电影众多且西湖场景从选材、故事、历史、美学等角度勾连了新兴媒介—电影和传统的文艺形式。友谊影片公司在杭州狮子峰还建设了摄影场。田汉说:“一定要把世界上的人才引到雷峰塔下去。”[3]田汉计划取材《聊斋志异》,借鉴济慈讲述蛇女拉弥亚恋爱史的七百行叙事诗,以“情与理的凄惨的斗争为脚本”写一出蛇与人的恋爱戏。《到民间去》《湖边春梦》的外景在西湖拍摄,日本画家三岸好太郎说,蓬莱三岛被物质化了,已经找不出奇幻(fantasy)了。田汉深表认同,“西湖已成了军阀资本家的西湖,不是诗人美术家的西湖了”[4]。田漢拍外景的时候,为等一片白云,说白云“没有国境,用不着疲劳,他不知道束缚……超出人类狭窄的范围”[5]。风景寄托了田汉的自由理想,以及通过电影反抗军阀和资本家的努力。
笔者推测,西湖场景的滥觞始于1922年的《好兄弟》,“开影后,营业颇佳,盖因西湖背景,能引起观众之美感也”[6]。1925年摄制《空谷兰》时,张石川带组去杭州西湖拍,“上海有许多人,从未到过杭州西湖”,杭州有“使观众开眼”的噱头,即使是杨耐梅、张织云这样的明星也不曾作过湖上之游。由此可见,取景杭州在1925年之前还不成规模。中国早期电影中,风景的东方美与“欧化太深”的内景扞格,《好兄弟》外景“足显东方之美”,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悉数展现,“实为中国自制影片最佳之一剧”[7]。
1923年,日本东京在大地震后几成废墟,上海继而成为远东唯一能与西方现代大都市媲美的现代化城市,在此背景下,毗邻上海的杭州变成了一个兼具文人传统与田园牧歌的象征空间。明星、神州、天一、华剧、英美烟草、上海影戏、模范电影、大亚影片、百合影片、新开心、神仙等影片公司都到杭州出外景,《空谷兰》《她的痛苦》《难为了妹妹》《茶花女》《火里英雄》《险里夫妻》《寻父遇仙记》《山东响马》《柳碟缘》《劫后缘》等各色片种影片中的杭州场景各具特点,如《险里夫妻》摄入杭州险要山景以及角色滚入湖中,较为有特色,片中还有因地制宜的缘木、攀绳、水战、跳溪、大雪及火车奇异花园等。《她的痛苦》外景多摄于西湖,跳舞场摄于派利饭店的屋顶花园。《西厢记》在西湖刘庄、灵隐寺、虎跑泉、六和塔、葛岭、北高峰等处摄取外景,在玉泉寺,女主角林楚楚、李旦旦经该寺方丈特许,前往该寺摄取鱼乐园处莺莺、红娘观鱼的场景。杨小仲导演的《儿子英雄》外景取自西湖,影片诗画一体的味道甚至被认为胜似真实风景。此外,连环戏剧组也爱去杭州拍摄外景,如共舞台连环戏《莲花公主》等。
诚如陈大悲所说,杭州因为深厚的人文积淀,除了适宜历史片,还适合拍现代题材的电影。田汉的原创故事《湖边春梦》以湖、镜和梦境的镜像关系结构了一段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1]故事,西湖是这部电影的核心场景。田汉1916至1921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受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影响,谷崎润一郎来杭州旅游时,在游记中以一个年轻女性的尸体作为结尾,并简单构想了关于这个女性的一些故事。《湖边春梦》结尾,白发妇人点醒了主人公“南柯一梦”,体现了田汉对新浪漫主义的反讽。导演卜万苍在《湖边春梦》中将西湖名胜悉数摄入镜头,杨耐梅所饰演的美丽少妇逐一介绍西湖的古迹佳话和风物人情,让人“从画面上醒人的景色中聊慰乡愁”[2]。卜万苍于1928年初春,率领《湖边春梦》摄制组12人,从上海乘火车抵达杭州,住宿在西湖饭店。12人中,除了“卜万苍和几位工作人员”,都是“初临西湖”,“远离灯红酒绿的上海”,“如花景色”让身心“尽情舒展”。剧组在杭州“拍了十二天”。该片的摄影师—留美摄影家石世磐将“诸如在烟水空濛、苏堤花柳的晨间散步镜头,‘断桥春水绿初柔的断桥”“‘塔影初收色暮的‘雷峰夕照”“‘爱渠阵阵香风人的‘曲院风荷”“平湖秋月”“花港观鱼”“南屏晚钟”“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双峰插云”等胜景一一摄入镜头,石佛山、宝俶塔、苏小小墓、风林寺、秋瑾墓、栖霞山、岳王庙、岳王墓、秦桧、王氏的铁铸跪像、灵隐寺、虎跑泉等名胜古迹,无一遗漏。[3]
《湖边春梦》风景话语中的“全景画”很有现代性意味,在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过程中,全景画在下层百姓中普及了国家风景,替代了带有精英属性的俯瞰画。在1948年的电影《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中,导演马克斯 · 奥菲尔斯(Max Ophüls)直观地展现了19世纪末,通过道具火车观看全景画的场景;在20世纪初,国内亦放映类似的全景电影[4]。《湖边春梦》剧组为了制作全景画煞费苦心,男女主人公在火车上邂逅,剧组参照同时期的好莱坞电影《红字》(The Scarlet Letter)、《将军号》(The General)等,模仿从火车内摄制外景的技术已经非常纯熟。《湖边春梦》为了还原火车的真实质感,“椅座窗户悉仿真设置”,剧组尤其注意火车车厢与车厢外风景的关系。火车内景的表演居多,布置火车外处于动态中的乡村景色较有难度。董天涯用高约八尺的大圆轮,周长一丈,四周布置成白色,在上面画上乡村风光,拍摄时由火车窗望去,看到转动的圆轮,仿佛火车在行驶中一般,且快慢自然。火车改变了现代人的知觉经验,将“世界转化成一种全景,一种能够被体验的全景”[5],这种全景模拟从大都市到乡村的知觉经验,前后景被压缩,是一瞥而过的风景,瞬时的时空感和知觉经验的加速感,与《湖边春梦》中主人公对田园牧歌和浪漫主义情绪的追求构成了张力,湖区的田园牧歌并非是解决现代性焦虑的理想方案,片中理想的幻灭和电影中的反讽精神,让影片具有了现代色彩。
除了西湖,扬州瘦西湖、太湖、洞庭湖也是中国早期电影理想的湖区景地。风景话语在不同电影类型中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镇江富于武术片之外景,扬州多花园,宜于哀情片……外埠各地,宜于外景者多,且富东方之美”[6]。苏杭外景也适合做哀情片的外景。武术片的外景不宜纤巧,而应雄伟壮丽,如《王氏四侠》外景崇山峻岭,森林叠嶂,路转峰回,《荒唐剑客》中的大荒漠苍凉荒寂。[1]湖区场景典型的特点是人文积淀深厚,同时又是世俗生活的聚集地,人文性与世俗性交织。在拍摄《沙场泪》时,程步高率剧组20余人寻遍镇江扬州的历史人文风景,如在金山寺,将苏东坡玉带摄于银幕,清乾隆帝莅扬时钓鱼的黄色亭用于《沙场泪》中的钓鱼场景,欧阳修读书的平山堂等也都被取入景中。程步高等人先至徐园,即扬州徐宝山家园,摄取了片中捉迷藏的花园外景,又摄取路景及竹林深处,在陈家花园(又名凫庄)摄取外景,还取景了五亭桥。合群影片公司出品,洪深导演的《猪八戒大闹流沙河》在苏州等地拍摄外景,将太湖作流沙河。《马浪荡》外景取自无锡及太湖。《玉洁冰清》的外景取自洞庭山,系洞庭山首次出现在银幕,太湖洞庭山的渔村与影片的世外桃源之风颇为相配。导演卜万苍将一对恋人在梦中飞翔的场景叠印在天上,仙风吹衣,瞬息万里,二人在渔村分别时烟雨柳荫,恋人说情话时蜂蝶缠绕,镜中窥影,旖旎水边散花,凄楚之情都寓于景中。
与《湖边春梦》中火车的现代性不同,《沙场泪》的船上风景,体现了婉约悠然的节奏,惊险的情节与水上悠然的划船知觉体验形成了反差,“湖中攝‘归舟遇弹,湖中水面有反光,可资借助”,程步高分解了表情与风景话语,“先在动船中摄特写,特写毕即装机于别一小舟,共摇而进,随进随拍”。拍摄过程中,剧组在瘦西湖湖湾处遇到当地人带了数百只鹅,在湖中遨游。程步高“遂装机于船首,先追逐而摄,摄其各种背形侧形游泳姿势,次舟泊湖中,于岸上驱赶,摄其正面各种姿势”[2]。当地人的鹅就是世俗性的一面,与瘦西湖的人文性共同构成了《沙场泪》的背景。如刘勇强所说,“场景有时就是地域性最集中的体现”,同一场景在近似描写中反复运用,“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具有叙事学意义的环境”。[3]湖区场景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复现,既是现代性的背面—田园牧歌、山水烟霞的象征,又兼具人文性和世俗性,将鲜明的地域文化整合为富有东方特色的风景话语。
结语
中国早期电影人自觉地通过风景话语构建文化主体性,实现民族身份认同,国产电影中的风景话语是面对外来电影和外来文化殖民的抵抗性表达;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风景话语具有现代性因素,剧组“出外景”是流动的社会空间生产,“风景话语是把‘自然纳入现代性合法化中的关键手段”[4];在大银幕上,风景成为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化体验,并在大众中传播,成为构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媒介和“神圣的沉默语言”[5];江南文人和电影人主导、介入、参与的电影摄制,自然而然地将江南风景导入电影实践,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风景话语,勾连起江南文人的诗学传统和小说戏剧中的湖区等典型场景;中国早期电影放映活动满足了观众对风景的观赏诉求。
限于篇幅,本文将笔墨主要集中在早期电影中的风景话语本身,但“风景”的潜在价值不止于此,“风景”作为理论框架和话语形态,除了将其与20 世纪初新视觉经验的发生、形成、视觉机制和革命性实践结合外,立足中国本土,还能有效地用来整合中国早期电影发生现场中视觉主体知觉经验的片段,从电影接受层面理解西方电影话语的中国化。顺此路研究下去,将会发现更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电影与新文化运动后的现代中国相榫合的实证,而“风景”对于中国民族电影话语建构的价值就在此处。
[1]风景和环境都能用来指涉空间,前者侧重美学,后者则关涉叙事层面。
[2] Martin Lefebvre, Landscape and Fil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50.
[1] 高維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0页。
[2] 20世纪20年代的风景片目录可参见刘文婧:《20年代中国纪录片研究》,高小健主编《中国电影:20世纪20年代现象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页。该文论述了风景片《济南风景》《倭子坟》的拍摄背景和影片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
[3] [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4] 忍讽:《对于电影界的小贡献》,《申报》1925年8月25日第17版。
[5] 佚名:《复旦新片清初革命史摄制过半》,《申报》(本埠增刊)1928年8月14日第25版。
[6] 佚名:《〈王氏四侠〉六大特色》,《申报》1928年1月28日第1版。
[7] 佚名:《影戏与美术》,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三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8] 彦明:《电影明星拿佛罗之近讯》,《申报》1925年3月23日第7版。
[1] 何仲英:《在老旧的亚省》,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二十册,第136页。
[2] 此为孔雀公司发行的好莱坞电影《热血鸳鸯》,并非大中华百合版。
[3] 此系广告语,《申报》1924年1月1日第4版。
[4] 佚名:《明星〈苦儿弱女〉试映记》,《小时报》1924年7月24日第13版。
[5] Weihong Bao, Fiery Cinema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52.
[1] 少飞:《介绍〈妖光侠影〉影片的思想》,《申报》(本埠增刊)1928年8月5日第25版。
[2] 陈天:《初级电影学》,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二十七册,第283页。
[3] 朱:《电剧的艺术》,《友联特刊》1927年第3期。
[4] 姚啸秋:《背景上的疑问》,《友联特刊》1927年第3期。
[5] 此系剧照图注,《德国育发影片公司名片“The stone Rider”的外景的一幕》,《银星》1927年第14期。
[6] 沈小瑟:《谈谈布景和化妆》,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二十八册,第200页。
[7] 记者:《藿莱坞》,《申报》(本埠增刊)1927年7月3日第23版。
[8] 志伊:《朝气独锐楼影话》,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一册,第76页。
[9] 刘笑口:《电影与美术》,《申报》1925年5月27日第7版。
[10] 沈小瑟:《谈谈布景和化妆》,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二十八册,第200页。
[1] 朱:《银灯过眼录》,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十五册,第99页。
[2] 雨客:《评〈苦儿弱女〉》,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三册,第54页。
[3] “一八八九年,美国政府决以吉禄基平原开放,使白人自由往彼垦殖。”“在美国历史上认为奇迹,至今犹能道之”,“剧中背景,类多天然外景,有绵亘数十里之大大广漠,暨巍峨之高山,又有无数之辐重车辆人马等参杂其间,声势浩荡”。参见秋云:《美国拓殖史之电影》,《申报》(本埠增刊)1926年3月14日第20版。
[4] 周瘦鹃:《大刀阔斧之〈殖边外史〉》,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0页。
[5] 记者:《〈荒漠丽史〉略述》,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二十四册,第20页。
[6] 宛:《急起直追的大中华百合公司》,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十五册,第156页。
[7] 周瘦鹃:《大刀阔斧之〈殖边外史〉》,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1160页。
[8] 连斋:《可惜的〈殖边外史〉》(下),《小时报》1926年8月26日第10版。
[9] 村夫:《可惜的〈殖边外史〉》,《小时报》1926年8月21日第10版。
[1] 彭年:《〈殖边外史〉之我见》,《大公报》(天津)1927年4月25日第8版。
[2] 此系《白芙蓉》广告语,《申报》(本埠增刊)1927年9月30日第20版。
[3] 树森:《谈〈劫后缘〉》,《申报》1925年8月19日第18版。
[4] 《情海风波》广告,《申报》1925年2月6日第7版。
[5] 毅:《我之〈情海风波〉影片观》,《申报》1925年2月7日第12版。
[6] [美]W.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7] 陈大悲的表述,透露出朴素的对建筑与殖民主义关系的批判观念。参见陈大悲:《中国电影之将来》,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732页。
[8] 陈大悲:《中国电影之将来》,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734页。
[9] 红豆:《看〈黑猫〉之后》,冯沛龄编《电影月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10] 元吉:《影谭》,《申报》1923年6月8日第21版。
[1] 指涉技术巨变的背景下,文字符号的错位,正体现在《情铁》的评论中,“原初的激情”概念范畴可参见周蕾:《原初的激情》,孙绍谊译,远流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2] 澹菊:《评爱丽斯塔〈情铁〉影片》,《申报》1923年8月1日第18版。
[3] 陈醉云:《影戏演员的修养》(续十五期),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九册,第300—301页。
[4] 石佛:《評〈女侠李飞飞〉》,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1139页。
[5] 懒圣:《偏重表情之自制影片—即神州新片〈不堪回首〉》,《申报》1925年2月13日第7版。
[6] K.K.K:《艺术上的〈大义灭亲〉》,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1099页。
[7] 倚虹:《评〈风雨之夜〉》,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1131页。
[1] 朱:《银灯过眼录》,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十五册,第99页。
[2] [苏]C.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富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6页。
[3] 毅华:《述西席导演之〈再生缘〉》,《申报》1927年6月13号第18版。
[4] 张伟:《沪渎旧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5]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6] 周瘦鹃:《大刀阔斧之〈殖边外史〉》,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1161页。
[1] 佚名:《天津电影院在门首拍摄电影》,《申报》1925年1月6日第8版。
[2] 范烟桥:《电影在苏州》,《电影月报》1928年第3期。
[3] 叶逸民:《电影在厦门》,《电影月报》1928年第8期。
[4] 竹生:《影片外景之选择问题》,《银星》1927年第5期。
[5] K.K.K:《艺术上的〈大义灭亲〉》,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1099页。
[1] 记者:《华剧影片公司同时摄制三片之新贡献》,《申报》1927年2月14日第17版。
[2] 佚名:《长城赴锡摄影队昨返沪》,《申报》(本埠增刊)1928年8月14日第25版。
[3] 张英进:《民族文化,个人视野,多地记忆:当代中国电影的真实风景》,郑焕钊译,《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4] [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4页。
[5] 顾也鲁:《忆著名导演卜万苍》,《上海电影史料》1992年版第1卷,第87页。
[6] 徐文明:《南洋对早期中国电影制片发展的介入与影响1923—1949》,《电影新作》2018年第2期。
[1] 郑益滋:《导演〈上海之夜〉以后》,《神州特刊》1926年第4期。
[2] 侯曜:《万里摄影记》,冯沛龄编《电影月报》,第68—69页。
[3] 张真:《银幕艳史》,沙丹、赵晓兰、高丹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第568页。
[4] 侯曜:《万里摄影记》,冯沛龄编《电影月报》,第67页。
[5] 范烟桥:《济南之电影》,冯沛龄编《电影月报》,第72页。
[6] 张真:《跨国通俗剧、文艺片以及孤儿想象》,《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7] 疯僧:《新片〈好哥哥〉述评》,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七册,第71页。
[8] 毅华:《〈好哥哥〉影片中之天才》,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七册,第68页。
[9] 飞:《观明星新片〈好哥哥〉试片记》,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七册,第69页。
[10] 保衡:《〈天涯歌女〉完成记》,《申报》1927年3月4日第19版。
[1] [美]温迪·J.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红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2] 舒新城编:《杭州西湖游览指南》,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页。
[3] 田汉:《银色的梦》(一),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资料汇编》第十四册,第320页。
[4] 田汉:《银色的梦》(一),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资料汇编》第十四册,第319页。
[5] 田汉:《银色的梦》(一),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资料汇编》第十四册,第323页。
[6] 记者:《国内电影界新消息》,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三册,第83页。
[7] 梦朱:《评〈好兄弟〉影片》,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三册,第52页。
[1] 解志熙:《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 — 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
[2] 龚稼农:《龚稼农从影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3] 龚稼农:《龚稼农从影回忆录》,第117—118页。
[4] 张隽隽:《影院之外:早期电影上海多样化的放映空间初探》,《电影新作》2018年第6期。
[5] [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世间的工业化》,金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6] 程步高:《扬州摄影记》,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六册,第70页。
[1] 绿竹:《谈〈荒唐剑客〉》,《电影月报》1928年第3期。
[2] 程步高:《扬州摄影记》,上海图书馆编《民国时期电影杂志汇编》第六册,第70页。
[3]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4] [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5] [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