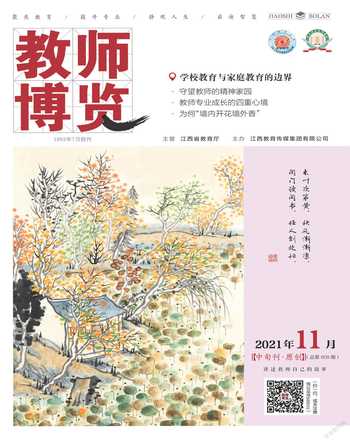修心(外一篇)
胡曙霞
友人喜去寺庙做义工。能在寺庙做义工,结善缘,净心性,我以为是好事。
旁人却说,来往寺庙之人也杂,各色人等,品性不一,未必就能求得真清净。
友人淡淡地说,与各色人等接触,仍以微笑待之,是另一种修行。
那晚相聚,独独对这句话品味许久。或许真正的修行不是避世,而是于喧嚣中、于混杂处、于红尘中,向暖,向善,向光,不怨不憎,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以宽容,以柔软,以原谅,与世间形成交集。
这一日日的交集,如腕上的手串,捻动搓揉后形成一层包浆,滑熟可喜,幽光沉静。它用温存的旧气告诉人们,除却千百次的摩挲,更有指尖的温度、主人的脉动与心性。
这足以照见人影的光鉴,是经年累月的修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浮气、躁气、戾气,慢慢褪去,终以无棱无角的圆通替之。
忆起自己,年轻时好美衣,好名利,好赞美。喜欢鲜花着锦,喜欢争强好胜,如绷紧的弦,受制于得失计较。
若不是母亲的一场大病,不知自己还要虚浮几时?
二十六岁那年,母亲与死神擦肩而过,眼睁睁地看着,心上如油煎刀剐,那种无能为力,几乎让人万念俱灰。待母亲康复后,幡然醒悟,往日追逐之东西皆虚幻,而眼前至亲的平安才是世间最珍贵的守护。
一夜之间,看穿世事,卸下所有。至此,喜内敛,喜低调,喜平和,喜朴素,喜寻常。
所谓寻常,便是有屋住,有衣穿,有饭食,灯火可亲,家人围坐。所谓朴素,便是居陋室,食蔬野,穿棉麻,一箪一瓢,安心知足。
朋友越发少了,可心之人,唯二三,高山流水,无须常联络。彼此知道,在呢,都在呢,足矣。还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吗?不了,除却少有的几个人能影响你的情绪,大多时候,波澜不惊。
日子因为简单而丰盈,时光因为安静而醇美。且收敛,静心写作,专心阅读,十年如一日,攒出一二朵意外的花。得了一些微名,听了一些赞美。也曾飘,喜滋滋,意洋洋,以为美。偶尔妄我,偶尔急躁,偶尔还会忍不住人前论是非。待得夜深人静之时,审问自己,一颗心,是否晶莹?
俗世名利,使人迷失,尝其甜头,越发想“得到”。每每此时,总会下意识地抚了抚腕上的手串,它经日月,历风尘,得摩挲。它用一颗颗的圆润告诉我,平心,静气,勤勉,通透。
也就悟了。有人在平淡之日守得初心,有人在得意之时忘了自己。引以为戒,莫失莫忘,保持天真,保持安静,保持淡泊。
玉不琢不成器,心不修染尘埃。勤拂拭,常反思,勿流于庸俗。
常思,常诫。有空的时候去大井巷的“静思书轩”坐一坐。那是台湾证严法师开的一家义吧,供奉佛家典籍,义卖绿色素食、环保物品。择一角落,临窗而坐,竹影葱茏,乐曲悠悠。店里的女员工,一律和蔼,脸带慈悲。如果你愿意,她们会与你细说,说慈善,说佛缘,说证严法师传奇的一生。
点一杯咖啡或茶,静静地聆听,走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走近“慈悲济世”,走近“因果轮回”……
也就净化了,一颗心,洗涤过一般,通透无瑕。
通透无瑕的还有一辈子积德行善的母亲。近段时日,婆母因眼疾居住在我杭州的小家。母亲怕我有分别心,每每致电于我,第一句便是:“囡啊,一定一定要善待婆母,她正病着呢。”我总是恭敬地回答:“知道了,妈妈,一定善待。”如此这般,母亲才放下电话。
想起自己年轻时,因为争强好胜,常遇挫折,常与母亲吐苦水。母亲呢,微微一笑,教我“吃亏是福”“以和为贵”“良善宽宥”。我那疾风骤雨般的委屈,到了母亲那儿,被三言两语抚平了。如今忆起,母亲才是生活的智者,她以其行其言,谆谆教化我。母亲的修心在日常,她以一个农村妇女的淳朴引领我,向暖而行,向善而生。
有一段时日,因身体欠佳,工作琐碎,困顿在“班主任”一地鸡毛的烦躁与不安中。各色学生、各色家长,一一从脑海掠过,只觉与人相处,是世上最大的“难题”。常常地,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心情起伏,言辞激烈。当懊恼、不平、愤懑显露于我的神色之间,我知道自己又陷入大动干戈的悲喜之间了。
走进大自然吧。看蝶飞,看叶落,掬泉水在手,弄花香满衣。草木若诤友,向阳而生;流云如良师,聚散随缘;松烟是箴言,孤寒清凉。
修行者,修心也。
再遇不平之事、不堪之人,微笑待之。不怨不憎,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以宽容,以柔软,以原谅,与世间形成交集。
做那红尘中的散淡之人,不在世俗标榜之列,不在功名利禄之间,不在俗世相争中。
读书、教书、写字,与天真的孩童一起,与四季草木一起,与日月星辰一起。光阴如水,蔓草生香。
食 鲜
一入秋,杭州就成了年代久远的临安城,它既有古香古色的文化底蕴,又兼具烟火人间的可亲可爱。秋天的早晨,清爽透明,薄凉的气息像不出聲的鸟,持续而缓慢地飞,这沁凉让人想起薄荷,绿茵茵的,抚一抚,清气氤氲。
穿过香喷喷的桂花树,穿过薄淡淡的晨光,走在气息幽深的大井巷,转过河坊街,走过花鸟市场,到了知味观。
来一屉热气腾腾的小笼包,要一碗清淡可人的“猫耳朵”,亦是恰好。就说那“猫耳朵”吧,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跟豌豆瓣似的,用勺子舀一勺,五六朵在清汤里晃,是白梅花还是白纽扣?不,都不是的,是猫的耳朵,悄悄地、轻轻地、伶俐地,竖着,倾听。你张口,把五六朵“猫耳朵”全部放进嘴里,咬一咬,韧、弹、绵,一碗“猫耳朵”下肚,“耳朵”变得轻盈透明。秋风摇、白露滚、红叶飞,每一个细微的声响,都在耳畔放大,再放大。
如果你不喜欢知味观,移步往前走,有一条街——高银街。皇饭儿、好绍兴、张胡李、咬不得高祖生煎、五芳斋、西月楼,数不清的店铺,数不清的美食。沿着街道,挨着店铺,一家一家地走,隔着玻璃,你能望见好看的餐盘、美味的食物。每家店的门口照例会站着一位迎宾的小姐,她们穿着旗袍或其他古风的衣裳,对你甜甜地笑,软软的杭州话,一句一句飘过:进来吧,进来吧,正宗的杭帮菜,尝一尝。
你的脚不由自主地迈进去了。适合点一个小钵头桂花甜酒酿,这甜酒酿选用新打的糯米,又白又甜又圆,放在桶里,用虎跑泉的水浸泡,蒸透,晶莹剔透,玲珑别致,如珍珠,若雪子。而后,把自家制造的酒酿药放进去,盛在小钵头里,挖个散热的孔,在棉花胎里裹着“焐”两天,便可出锅了。撒上一点干桂花,打上一两只糖氽蛋,香气扑鼻,逗人口水。
且看它,桂花匍匐,酒酿浓稠,黄花白米,色泽迷人。秋天的体香带着糯糯的气息从一碗小钵头桂花甜酒酿中热热地走来。捏住细瓷白勺慢慢舀,一口一口,细细咽,微软,微甜,微醉,微微的心动。
眼神迷离,杏花、桃花一起绽放;嘴角微甜,白露、霜降一起融化。你会疑心,是把杭城的秋含在嘴里了吗?一时之间,肺腑空明,双眸澄澈,心境如晴朗朗的天,晶莹、剔透、辽阔。
不过瘾,且再来一碗麻栗果儿烧肉。肉是桐庐的土猪肉;板栗是野生的“麻栗果儿”,个头小,颜色紫,细毛多,炒熟后,又粉又糯又甜。将剥好的栗子放进土猪肉,慢慢炖。咬一口,板栗的粉,猪肉的香,渐次传递,丰富的味觉如跌宕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眼神迷离。
还不过瘾,那就再来一盘小葱炒青菱。清淡可口的青菱,如同初秋的晨露,清新可人。老杭州人烧这道菜,只放盐,不放酱油,色泽白,味道醇。小葱炒清菱,鲜嫩水灵的一道菜,将秋天的白露、月光、薄霜,全都收在味蕾。吃得足够饱,可以去满觉陇坐一坐。
也只是寻常的农家,种着花,栽着柿,一张张桌椅摆着茶具,只要你愿意,可坐在桂树下,品一盏龙井,把秋天的空明一缕一缕收进来。随意走一走,遇到一个路边摆摊的老婆婆,她在秋风里朝你暖暖地笑,问,要藕粉吗?
你答,来一碗。
黏稠细软香糯的藕粉盛在白碗里,上方照例撒着桂花,用白瓷的勺子舀,一小口,一小口,将这些甜含在舌尖细细品尝。
你的心,忽然变软了,变糯了。一如这秋天的桂花藕粉,沁出一点一点的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