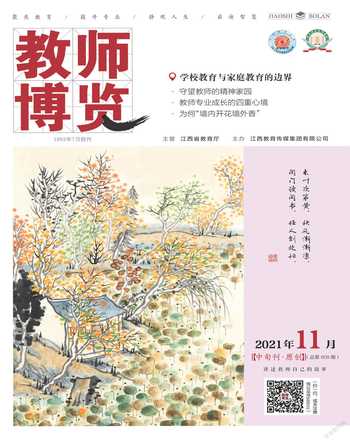为何“墙内开花墙外香”
杨林柯
接到一位教师朋友的微信诉苦,他说自己课上得好,又爱读书,所带班级考试成绩也很优秀,就是不善于搞人际关系。工作十八年了,依然评不上高级职称,在本校常遭冷遇;但在校外的影响还不错,常被外地邀请去讲课或做讲座。但他其实很想为自己学校做点事情。
我告诉他,这其实是社会常态,也很符合社会规律。远看月亮像玉盘,上到月球才发现原来是块大石头,看不到多美,更不会有嫦娥、玉兔。远距离容易产生美,近距离则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人性脆弱,经不起精细打磨和透视。小人物具备的缺点,大人物其实也具备。许多大人物被社会崇拜着,却被身边人瞧不上,甚至受到排挤,这个你是没有办法的。
有一句很励志的话:“山峰,对外界是风景,对自己则是高度和挑战。”如果你觉得你的方向是对的,就坚持下去。事实上,当你向自己的目标奔跑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给你让路。
每种社会环境都存在一种异己的力量,你必须和这种异己的力量做斗争,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可能找到自己。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自我的成全,不是要成为别人,而是要成为自己。
汉语中有一个词叫“安分守己”,“安分”是一种生命本能,守住自己才需要修炼。当然,你需要有对自己的发现,是鱼就去游水,是鹰就去飞翔。
尼采说,你飞得越高,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越是渺小。人是社会动物,社群不会容许你抛开他们独自行走。这和《圣经》里说的“先知不被家乡悦纳”是一样的道理,虽然优秀的个体不一定就是先知,但往往具有先知的素质。
人生需要等待,更需要容忍。有时候,你得容忍凡俗众生对你的不接纳,但这并不代表你不优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行事原则如果和普通人不一样,必然会招惹不一样的眼光,关键是你能不能在看清外界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方向,成长必然要接受风雨雷电、雨雪冰霜。
西方人说,太阳底下无新事。
耶稣在传教活动中,一度回到家乡拿撒勒弘扬己道,但并不能被家鄉人理解。耶稣叹息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的。”耶稣不仅不被悦纳,而且被冷落,遭人告密,受到犹太正统知识分子的排挤歧视,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再看看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虽然他没有像耶稣那样殉道而死,而且他的教义遍布整个东亚,但他身为印度人,印度本土的佛教徒人数却非常少,大部分人信奉的是印度教。
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老子出关远遁,苏格拉底在雅典被杀……所以,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思想最初往往都会被社会流俗抵触,会被熟悉的环境排挤,容易让真正优秀的个体陷入一种文化的孤独,这很正常。
鲁迅说:“造化往往为庸人设计。”《传道书》中有“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行走”一类的话,似乎是造化的有意安排,体现出一种凡俗众生无法参透的大智慧。“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的历史现实,中外皆然,否则,中国文学史上不会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诗歌。
许多优秀的个体往往在本地并不受待见,甚至遭到歧视、排挤或打击。这有人性的弱点,也有文化制度的因素,当然,也可能和人的个性有关。也许和环境没有兼容好,只是因为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于是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关键是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保持自己的优秀。如果被社会流俗中那些异己的力量同化掉,说明自己还不是那么坚强,或者内心有恐惧,还不能勇敢地站在自己所坚持的真理一边。
陈寅恪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一种孤独的壮美,也是人格追求完善的必然遭遇。
陈子昂说:“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精神的苦况是无所依托、无家可归的孤独。
爱因斯坦说:“我从未悉心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的亲人。在这一切面前,我总感到有一定的距离。我需要保持孤独,这种感受正一年比一年强烈。”
看清了这一点,你就可以坦然活着,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外界顶多是一种背景。优秀会遭遇各种挑战,有来自自身的,也有来自外界的。
我们常说“热爱生活”,其实,你只能热爱自己的生活。每个生命都是孤独的,不管生还是死,都须独自面对。那些优秀的个体往往更加孤独,这大概也是人格完善的表征。区别在于,普通个体容易找到价值同类项,而优秀个体与普通个体的精神差别太大,与共同体难以兼容,于是孤独就是他们的宿命,这也符合自然界的规律。驯良动物喜欢群居,而翱翔的雄鹰则独来独往。
活到一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不是为了与世界和解,而是与自己和解,在“自我”与“他我”的交战中,最终要成为自己的朋友。
对世界的态度,是交换友善,还是交换轻蔑;是活在自己的天空,还是活在他人的草庵,在于自己的选择。毕竟,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别人能够接纳,当然好;不接纳,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