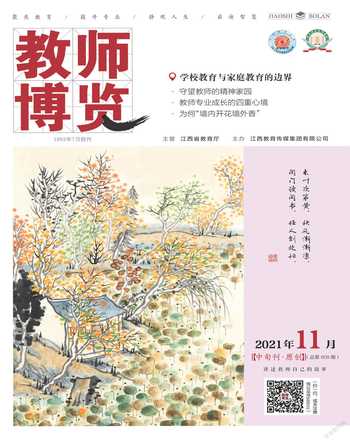守望教师的精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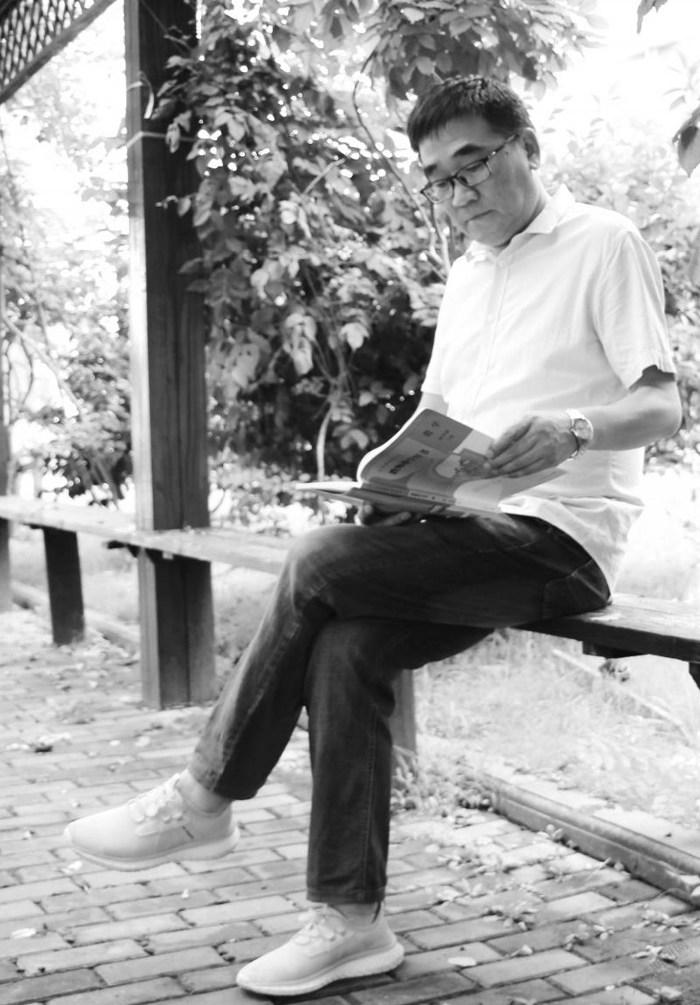
鲁兆周,安徽省中小学高级教师,安徽省马鞍山市师德标兵、优秀教师,马鞍山市中小学高级教师专家评审组成员和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考官。《教师博览》“签约作者”。在《中国教育报》《教师博览》等教育报刊上发表文章两百余篇。
从文学青年到优秀教师
我是怀揣着文学梦走上三尺讲台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一批特殊的青年,他们痴迷文学,眼神澄澈,一如那个时代一样透明,充满朝气。那时的我正在师范学校读书,学校坐落在“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敬亭山脚下。在学校,我担任学生会副主席,负责学校广播站、黑板报和校刊编辑等方面的工作。不知不觉中,我与文学结缘了。
毕业了,像落叶飘向大地——我回到了家乡,有更多的时间做我的文学梦了。
刚参加工作时,工资基本上用来订了文学杂志,《十月》《收获》《小说选刊》等文学期刊堆满我的陋室。一道毕业的同学忙着参加自学考试,拿文凭、改行,我却参加了南京青春文学院的函授学习,每周至少寄去一篇短篇小说。指导老师说我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我劲头倍增,写下两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只是没有一个字能变成铅字。大家都说我傻,我一笑置之。
校长是位民办教师,总说我不务正业。我不服气,主动要求上公开课。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全学区的语文老师都来听我上课。乡村道路泥泞不堪,老师们一身泥水走进教室,我很感动,课上得极富感染力。老师们都说我天生是块做语文教师的料。校长很高兴,年年让我教毕业班,一教就是八年。
1990年,组织上安排我当校长。我领着一群青年教师加班加点地工作,给学生补缺补差,没过几年就把一所薄弱学校打造成当地“优秀学校”。其间,我仍痴迷于文学创作,“为伊消得人憔悴”!
2002年,我参加芜湖师专教育专业函授学习。那年腊月二十四的晚上,我留在学校參加最后一场考试。学校地处郊区,乡村送灶神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惊醒了栖息在香樟树上的小鸟,发出“啾啾唧唧”的叫声。我不能自持,泪水夺眶而出。回到家,我连夜写了篇散文《鸟鸣嘤嘤》,寄到《教育文汇》杂志社,想不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居然发表了。我连着给《教育文汇》投了几篇教育随笔,都发表了。主编打电话给我,说我读的书多,文笔好,鼓励我多写教育叙事。我的头顶上终于有了一片属于我的蓝天!
2004年春天,我应邀参加《教育文汇》杂志社举办的“黄山笔会”。我们下榻在花溪宾馆。在宾馆里,我经常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他衣着极为朴素,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见到我,老人便亲热地和我打招呼,拉家常,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桂生教授!
见贤思齐,我们总爱往陈教授的房间里跑,听他谈教育,谈人生。在美丽的黄山脚下,我的“文学梦”渐行渐远,“教育梦”渐渐清晰起来。
从此,我开始恶补教育理论,开始改变我的课堂和我的教育管理,我的教育文章不断发表在全国知名教育报刊上。我劲头十足,到市里上观摩课,到偏远农村支教。我先后获得了马鞍山市师德标兵、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还曾作为唯一的教师代表在市委市政府举办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发言。如果没有我的“文学梦”,也就没有我的“教育梦”——正是有了大量的人文阅读和写作的体验,才奠定了我后来的精神底色,构建了我一生的精神格局,让我拥有了悲悯情怀和仁爱之心,在教育的星空下吟唱我的教育理想。我始终认为,没有阅读和写作相伴的教师是平庸的,他们的激情会很快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爱上阅读和写作的教师,自然会打通成长过程中的“任督二脉”,会保持着纯洁的童心和纯净的教育情怀,将个人的隐忍放大,将内心的小我驱除,将人性的伟大留驻。阅读和写作给我的内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让我感到生命的柔软与美丽,使我能在满山骤来的风雨中卸下所有防卫,只用最简单的装备和心情,吟啸徐行。
做个“农夫校长”也幸福
我的乡村小学四周都是庄稼地。家乡的田野给了我太多的欣喜与思考:一粒种子是有无限潜能的,只要给它提供良好的土壤、阳光、水,用心耕耘,这些懂得感恩的种子就会为你带来丰厚的馈赠。我就是要做一个“农夫校长”,我的教育理想就是让我的学生成长为挺拔的麦子。
“农夫校长”要像农民热爱土地一样热爱自己的学校。农村学校地处乡村,少了迎来送往,少了约束和模式化的禁锢,少了孩子们身上的不良习气和老师们身上的急功近利,校长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农夫校长”应该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常说,农村学校最可怕的不是物质条件的简陋,而是保守和封闭导致的“精神囚笼”。而打破“精神囚笼”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我的阅读就跟呼吸、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遇到好文章,我会用红笔标下来,写上批注,推荐给教师阅读。校长要坚持读书,书读多了,就会“腹有诗书气自华”,浓郁的书香自然会浸润出一双慧眼,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提升文化修养,很容易让你的学校管理变得有智慧,有文化品位。
一个有教育思想的“农夫校长”的身边必然汇聚着一群爱思考的“农夫教师”。农村教师由于经常和农民打交道,身上往往具备了一些农民的品质:淡定、朴实、勤劳、乐于奉献。他们都知道,农村学校发展无捷径可走,必须走科研兴校之路。因此,我一直保持着和县教研室的联系,只要有教研活动,我就安排教师参加。一次,我在教师会上提出要开展课题研究,以课题研究引领教师成长,老师们都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是,一些城区学校还没有开展课题研究,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能行吗?两个月后,我主持的市级课题获得立项。事实胜于雄辩,老师们心悦诚服。接下来,学校为每一个教师量身打造了一个个“草根小课题”,并把教师的课题研究纳入教师考核中。在一系列的“强制”措施下,老师们反而找到教师职业最为充实的生活方式。许多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有的还在教育报刊上发表了教育教学论文。很快,我这个“农夫校长”和许多“农夫教师”也有了自己的教育博客。有教师问我:“校长,你的教育博客为什么叫‘风语者的博客’呢?”我问他们,看过吴宇森导演的好莱坞大片《风语者》吗?风语者是美国的土著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我们是农村教师,是中国教育的“土著”,在气势恢宏的中国教育改革的交响乐中,应该有农村教育的声音,哪怕只是短促的笛音。
“农夫校长”要像农民离不开土地一样离不开课堂。我工作38年,教了38年的小学语文。我不喜欢别人的思想在我的头脑中纵横驰骋——这是我的教学信条。我是一名语文教师,我不是教语文的,而是教学生学语文的。长期以来,我一直运用批注式阅读来教课文,教学活动主要是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批注,将批注成果在课堂上展示,并提出质疑,教师和学生一道对这些质疑进行探究。阅读教学重在学生自己的读、思、悟、诵,要和烦琐的内容划清界限。通过细读文本,教师做好教学预设,学生进行圈点勾画,写批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展示和质疑可以作适当点拨,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供学生探究,不断总结读书方法。在我的课堂上,学生总是会说“老师,我读懂了这个片段”“老师,我有个问题”“老师,我不同意作者的观点”“老师,我来帮他补充”……
我深深地体会到,农村教师的爱应该是持久的,要像农民那样,按农时和庄稼生长的规律去安排农活,怀着一颗平常心期待收获季节的到来。许多农村校长认为,与城区孩子相比,农村孩子缺少的是知识,而不是素质,所以他们对抓应试教育乐此不疲。我认为这是对农村教育的误判。为了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我们千方百计为他们搭建平台。春天,我们领着孩子们到长江岸边的沙洲上去野炊;夏天,我们在校园里举办瓜果蔬菜展览会;秋天,我们带着孩子们去远足,踏遍家乡的山山水水;冬天,我们在操场上开展雪雕比赛……2008年六一儿童节,学校舞蹈队参加“童心向党”文艺汇演,孩子们表演的歌伴舞《映山红》一炮打响,不但在县里获了奖,还参加了市里的文艺汇演。听到观众私下打听台上的小演员来自市区哪所学校时,我心中的幸福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这就是我期待的农村教育。
2009年6月末,我接受了《南京晨报》记者的采访,该报以《做一个乡村教育的守望者》为题报道了我的相关事迹,孩子们簇拥着我这个“农夫校长”的照片也一同登上了报纸。打开了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孩子们笑了,老师们笑了,家长们笑了,我也笑了。
把自己种在课堂上
十年前,我的老家被划为县经济开发区,我的乡村小学被撤并到城区,我的“农夫校长”梦戛然而止。
新的生活开始了。校长说要发挥我的特长,让我担任学校教科室主任。教学之余,我写了大量的教育叙事,尝试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破解教育管理难题寻找“灵丹妙药”。《做一个会说话的校长》《做一个有亲和力的校长》《好校长有一颗仁爱之心》《和而不同,提升校长管理内涵》……一篇篇教育管理论文发表在《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上。可是,我发现校长看我的眼光变了。一天,县教育局某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他告诉我,《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的编辑老师曾打电话到教育局了解我的情况,还说想派记者来给我做一次专访;这位领导说我已经不是校长了,婉言谢绝了他们提出的请求。我内心五味杂陈。《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栏目是为一线校长展示先进教育管理和育人理念的舞台,作为已经不再是校长的我,心中又一个梦,碎了。
怎么办?当现实无法安顿你的灵魂,自我救赎的路又在哪儿?我发狂地读书,拼命地写作。为了寻找写作素材,我整天“混迹”于学生中间,变着花样教课文。孩子们的欢笑声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完成自我救赎——对于教师而言,教书、读书和写作才是通往自由之路,物质世界不可能有自由,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由。一个学校,当校长、教师和学生都不读书,也能考出“好”成绩,教研工作就成了鸡肋,教科室主任就形同虚设。我再也不能图可怜的蜗角虚名而把宝贵的时间出卖给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材料写作,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辞去所有的领导职务,成了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
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教师,面对现实的不如意,常常痛苦得不能自拔。其实,痛苦的根源无非是形形色色的欲望。不能战胜欲望,就注定在痛苦中沉沦。我完全可以和大多数学校领导一样,退居二线,提前过上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但是,我就是要把自己像种子一样种在课堂上!
教了几十年的小学语文,我深感阅读教学烦琐而低效,教师疲于奔命,学生苦不堪言。阅读教学总是被考试牵着鼻子走,从字词句篇到段落大意,从主题思想到写作特色,而且,这一切都有约定俗成的规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美育缺位的现象。语文教學给予学生最重要的并非知识,而是对学习的热情,对规则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学生作为感性的人,只有经过审美教育,才能成长为审美的人,最终成为道德的人,即全面而丰富的人。只有这样的学生,才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中去,会学,乐学,高效学习才能发生。
许多青年教师问我,为什么自己在课堂上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学生却总是反应冷淡呢?我告诉他们,教材中的课文大多文质兼美,审美性很强,而你们总是被教师用书束缚了手脚,看不到字里行间流淌的美,把美文当作社论去教,没有把学生领进课文所描绘的美妙境界中去,学生怎么能对你们的课产生兴趣呢?语文教师就应该抓住课文每一个层面的美,展开教学活动,让点点滴滴的美像和风细雨一般渗入学生的心田。
于是,我努力将我的语文课堂打造成“审美语文”,“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精致化的审美和精致化的表达。如果我们每一堂语文课都能做到向美而生,给学生以审美体验,给学生以灵魂冲击,就能不断促进学生生命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师的工作是极为光荣的,他们雕塑人的灵魂,开发人的潜能,为人的发展奠基,通过教育为学生创造美好的明天。正如崔峦老师所言:“语文教育是花的事业、根的工程。”
审美语文最重要的便是使学生通过品味优美的文字,学会认识美,发现美,创造美。每天和“审美语文”相伴,潜移默化中也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提升了我的阅读水平和鉴赏能力。我喜欢读《红楼梦》,几乎每年都通读一遍,往往一经入目,便不能释手。几年来,我以审美的眼光审视《红楼梦》的伦理和美学价值,领略文字中所呈现的伦理和美学内涵,甘之如饴;流连其间,我忍不住思索“红楼与教育”话题,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读书心得。
“审美语文”让我的课堂花团锦簇、芬芳馥郁。我就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在花海中徜徉,采花酿蜜,一篇又一篇携带着“审美语文”基因的课堂叙事和教学论文如翩翩彩蝶,从花丛中飞出。我是个爱做梦的人,梦想着用自己手中笨拙的笔,给我的课堂涂上“审美语文”的底色。所以,我不敢也不能离开我的三尺讲台。守望讲台,也就是守望着我们教师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安徽省当涂县团结街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