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非子立赏设罚的若干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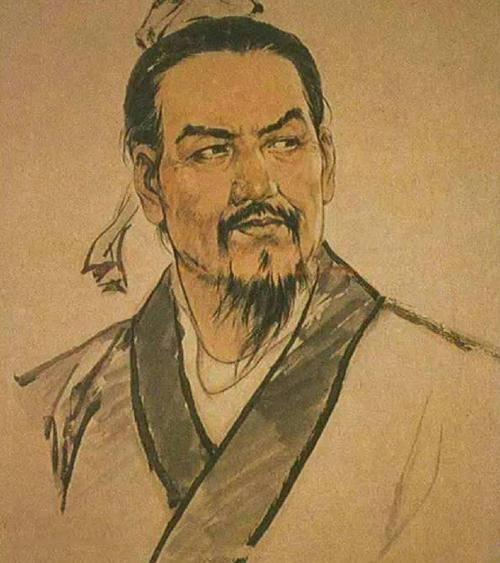
虽然我们常常为古代中国没有形成法治传统而遗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治的因素。“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我们甚至说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在古代,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或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
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订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偃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守株待兔”的宋人和“宁信度,无自信”的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
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与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以保持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地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
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够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子用镜子和衡器与法作类比来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就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的“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时也说明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放弃自己在做的事,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使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们苦不堪言。因此,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
“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子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子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效果。人都是好利恶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得奖赏去做“法”所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致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用“殷法刑弃灰”等事例说明这一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殷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孔子解释说,在街上倒灰会迷到别人的眼睛,继而惹人发怒,引起争斗,甚至导致家族之间的残杀。在街上倒灰这样的小事却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可行的。此外,人们都厌恶、惧怕重刑,而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做到容易的事,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
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值得庆祝。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和治病。他还引用先圣的言论,“规有摩而水有波”,作为衡量标准的圆规会有误差,再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则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韩非子讲了“墨子为木鸢”的故事。墨子耗费三年时间制成木鸢,只飞了一天就损坏了;造车的工匠使用细小的木头、耗费不到一天的功夫制造出车輗,能牵引三十石的重量,又经久耐用。墨子制作木鸢投入多,收益少,是“无功”,而制造车輗投入少,收益多,是“有功”。“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可以制定和施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施行。
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況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方能确立、施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终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王威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责编 王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