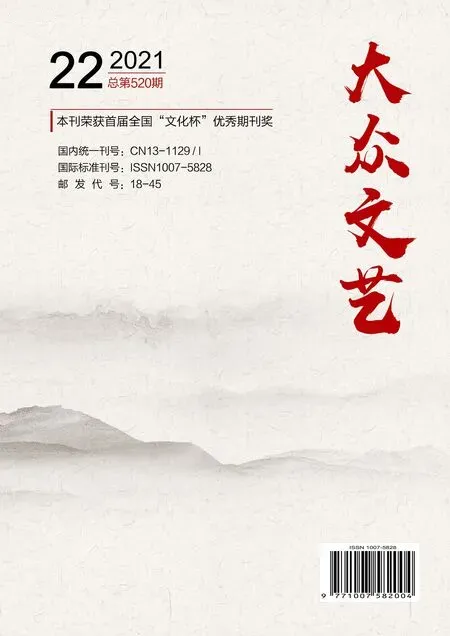董乐山话剧剧评活动评析
李姝杭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一
董乐山(1924—1999),曾用笔名麦耶、史蒂华、蒂华、乐山、伊文思,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和学者。
董乐山出生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少年时接受新式教育,1937年进入中学后,他开始大量接触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广泛阅读《创造》《新月》等文学刊物,培养了自己的文学素养。1938年初三时,他开始尝试创作,以笔名田禾写了几首抒情短诗,被《浅草》主编柯灵选中刊登,至此,他以文学青年的身份出道。也正是在此时期,抗日战争爆发,董乐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上,同时开始接触到左翼思想并参加地下活动。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上海租界里的大、中学校掀起了反对悬挂伪国旗和反对向汪伪政权登记的斗争,董乐山在此次活动中作为学生代表成功阻止了学校向汪伪政权登记的行为,但同时自己也被勒令转学,之后他另考几所高中而不中,只能于一所规模较小的中学中就读,董乐山认为这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教育条件的限制,他没能系统地接受理工科的教育,终以文科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941年,董乐山考取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孤岛”沦陷,众多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文学创作几无出路。但在娱乐方面,话剧却很繁荣。同时,同为地下党的董乐山高中好友白文为发展地下工作而深入到费穆主持的“上艺”剧团,当了一名龙套演员,董乐山因此有机会和白文经常出入剧团后台观看他们排戏演出。由此,他开始对话剧发生兴趣,也结识了黄佐临、李健吾等编导和石挥、韩非、李德伦等演员,在剧团时,作为旁观者的董乐山经常默坐一旁,听前面这些戏剧行家高谈阔论。当然,董乐山的戏剧素养还不完全是这样“蹭”来的,进入圣约翰大学后,他也辅修了王文显教授的戏剧课,对西方戏剧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掌握了一些专业戏剧知识的基础。后白文在剧团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就将董乐山介绍给了剧社管宣传的王季琛,希望他能在报上为剧团写些宣传的文字,以文学青年身份出道的董乐山本就喜欢舞文弄墨,此时又遇到别人的邀约,便一拍即合,开始了他此后三年间的剧评写作。
1942年—1944年,董乐山分别用麦耶、史蒂华、蒂华、乐山以及伊文思等笔名为《杂志》《女声》《太平洋周报》《上海影坛》以及《海报》等报刊撰写剧评,据不完全统计,董乐山三年间所写剧评60余篇,评论对象涉及当时上演的剧目——既有《秋海棠》《金小玉》等高票房的“热门剧”,也有《儿女风云》《新女性》等票房一般的剧,剧评对演员、剧团、剧评和剧坛现象进行了讨论,其客观的评析、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剧评数量让他迅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剧评人之一。
但董乐山的剧评写作到1945年时便停止了,一方面是因为从大环境上来讲,这一年抗战结束,上海重归国民政府的管辖,文艺活动开始转向电影,话剧失去了沦陷时期的繁荣景象。1945年—1947年还有一些话剧演出,但1947年后就很少有新的剧团再出现了,职业剧团多解散,许多剧人也纷纷转行。大环境的萧条以及朋友们的离开,让董乐山逐渐对话剧失去了先前的热情。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董乐山个人的原因,1945年董乐山正值大学毕业之际,在职业选择的关键时期,他急于寻求一份稳定且正当的工作,“对自由撰稿人的不稳定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慢慢疏于文笔,同一些报界旧友来往日稀。”由此,董乐山便搁笔于剧评。
二
董乐山于1942—1944年间所撰剧评虽出自一个不足20岁的青年之手,但其成熟老练的思想与笔法今日读来仍觉犀利和受启发。综观董乐山的剧评,他的风格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老辣的文风。直爽且犀利的表达是董乐山剧评留给读者最直观的感受,绿宝曾上演《秋窗梦》一剧,但没有公开剧作家姓名,董乐山看过此剧后直言:“《秋窗梦》恐怕也是没有一个够得上水准的编剧者和执行导演的…我把它列入新春四个新戏中,却生怕会辱没了真正的戏剧艺术…《秋窗梦》更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不知是否是这个缘故,编导者有自知之明,而隐姓埋名?”谈到剧坛上流行的《锦绣天》这样的“新文艺”风时,麦耶如此评价:“它除袭取了巴金风的最恶劣的劣点(一切作品皆脱不了恋爱、说教,以及脱离现实生活等)一无可取,与鸳鸯蝴蝶同流合污,却自以为是新文艺而沾沾自喜。”董乐山此种犀利的评价并不仅仅针对隐姓埋名之辈,即使面对剧坛已很有名望的剧人,他也敢于直抒己见,如对有“话剧皇帝”之称的石挥,他认为其在《福尔摩斯》一剧中的表演有些过火:“观众的浅薄反应冲昏了石挥,他把握不住自己,他忘记了戏剧艺术了…石挥巴不得把他所知晓的东西全搬出来呵!”而对开创了中国话剧职业化演剧先河的“中旅”剧团,他也未曾笔下留情,在评价“中旅”的《姊妹心》时,他不仅批判了“中旅”近些年的无所作为,更对大牌明星唐若青的恶劣舞台作风进行鞭挞:“她对话剧界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是罪不可恕的,必然地,她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而毫无姑息地撇弃!”他这种直率的文风与“谩骂式”剧评是有很大区别的,“谩骂”是只以个人喜恶为批判标准的纯粹主观式批评,而董乐山的批评虽也体现了自身的审美偏好,但批评标准依然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和戏剧艺术的规律上的,如他对“中旅”的指摘便不是毫无根据,其台柱唐若青的明星作风在当时可谓众所周知,不仅非主角不演,更是在台上抢台词,抢地位,影响了整个剧团的发展前途。
第二,独立的品格,客观的评述。董乐山与不少话剧界人都熟识,甚至他跨入剧评界的契机也是应“上艺”剧社的宣传部门之邀来写些宣传文字的,虽也有文章批评他做过以宣传为目的的颂扬式剧评,但纵观他的大部分剧评,他并没有在评论中失去客观的立场。他一贯推崇李健吾,认为《金小玉》和《青春》都是难得的佳作,在评论《花信风》一剧时,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李健吾的喜爱与尊敬:“我不用多啰唆来诉说我过去对两位先生(李健吾,吴仞之)的衷心的敬仰。尤其是李健吾先生,我爱他们底流畅而又简洁的对白,绮丽而又通俗的辞藻,充满机智的轻快而又风趣的俏皮话,而更爱的是他作品里底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气息。”但在具体讨论《花信风》一剧的主题时,他又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一出沾染着“鸳鸯蝴蝶派”气息的话剧,在主题上“说不出什么社会价值的意义来。虽然作者观察事物的眼光是如此深刻,他的作品的弱点却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思想。”董乐山这种就剧论剧的批评态度是剧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而他的剧评的价值正是建立在这种精神之上的。
第三,整体的戏剧批评观,以艺术为本位的批评意识。文本批评和舞台批评是构成话剧批评的两项内容,由于“一向,在中国演剧中,剧本是超乎导演与演员而为演出的第一义。”许多剧评家也因此更重视对戏剧文本尤其是戏剧文本社会意义的批评,但因为沦陷期上海严酷的政治环境,对话剧社会政治性的批评开始让位于艺术性的批评,董乐山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对舞台艺术的关注是董乐山话剧批评的一个典型特征。《影剧一年来的回顾》一文中“导演与演员推荐”一节、《话剧女演员论》是评论演员的专篇,《岁尾影剧评》中的《话剧商业化的表征——兼谈舞台装置》则是评论舞台装置的专节。除此之外,董乐山对每一部剧的评论几乎都涉及了对演员和舞台的评价,这既体现了他对舞台艺术的重视,也体现了他整体的戏剧批评观。在评论一部剧时,他对该剧的演员、导演、舞美以及主题、人物等都要有所涉及,同时又主次分明。例如,同是改编剧,在评论费穆的《杨贵妃》《浮生六记》等作品时,他更多地着墨于其特殊的导演风格和舞台风格,而鲜少分析费穆对原剧的改编状况,但在其他一些改编剧,如对《京华尘梦》的评论中则详细分析其改编的得失,对演员和舞台装置都总结式地带过。
董乐山剧评的价值基础建立在客观的批评精神上,而价值的体现则在于他敏锐的戏剧眼光和开阔的视野。纵观其剧评,虽很难总结出一种鲜明的戏剧观,但可以发现透过每一个剧,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其背后的剧坛现象,如对于剧荒和话剧商业化问题的探讨,沦陷期的上海话剧是自抗战以来上海话剧繁荣的顶峰,但董乐山却一再提出所谓话剧繁荣的背后是戏剧文学的贫瘠和戏剧人才的匮乏,而这其中的原因又和职业化剧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息息相关,在剧运工作者之间,经常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有些剧团正是在同仁间的互相倾轧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虽看到了繁荣背后的许多问题,但董乐山并没有将问题全部归结于职业化和商业化并完全否定这样的繁荣,在《话剧应该商业化》一文中,他对话剧的商品属性以及商业化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合理的商业化是有利于话剧发展的,他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商业化,而在于如何制造优良的商品,也即如何商业化的问题。在他看来,话剧商业化的命运固然是掌握在观众手中,但他也认为观众是随着时代进步的,剧人不能只依靠过去低级的东西来吸引观众,而应该与观众一起与时俱进。他因此呼吁剧团要相信观众的鉴赏力,提高话剧的制作水平。董乐山独到的戏剧眼光和较高的戏剧鉴赏力为当时的剧坛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