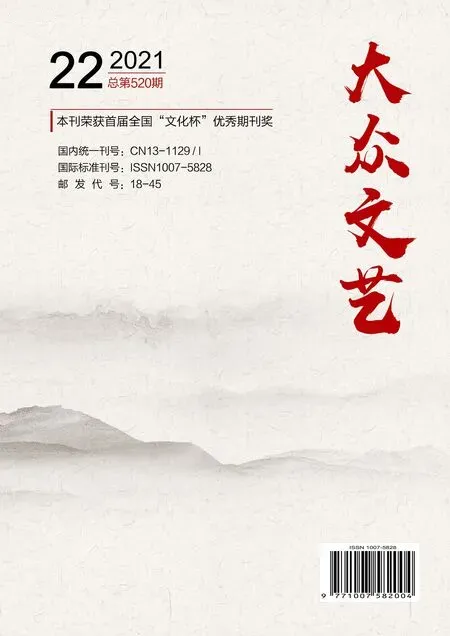论《寒夜》中汪文宣悲剧感的艺术手法
何可儿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
《寒夜》中的主人公汪文宣是一个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妻子出走,最终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死去的悲剧人物,学界也有一些专门针对汪文宣身上的悲剧作出原因分析的文章。那么,为何汪文宣身上的“悲”能得到共鸣呢?笔者发现,作者并非单纯地将矛盾、不幸加在主人公身上,而是通过多方面“对照法”、意象的运用以及人物的隐喻三种艺术手法来深化主人公汪文宣的悲剧感,从而加重小说“悲剧气氛”的意味,达到控诉黑暗社会的小说主旨。本文着意解析小说中的三种艺术方法,并探讨这些艺术方法对营造悲剧气氛所发挥的作用。
一、多方面“对照法”
在《寒夜》中,作者采用了“对照”的手法。这种“对照法”是以汪文宣为中心的经济、身体与精神、自我此时与彼时的多方面对照。这些对照意在更突出汪文宣这一小知识分子从物质到精神理想方面滑落的悲剧感。
小说中最明显的一组“对照”就是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的对照,二人经济状况、身体与精神情况乃至于生命状态都形成了对照的关系。
经济情况的对照。做校对的汪文宣的收入没有妻子做银行职员的收入丰厚。当汪文宣无法解决儿子小宣需要补缴的“三千两百块钱”学费时,妻子曾树生却用轻快的声音答应下来,她认为自己即使暂时支付不起,但她也可以借,总比汪更“有办法”。在后期汪文宣患病,曾树生甚至以一人的收入承担起他们一家的生活费时,这种对照显得更为强烈。汪文宣的穷苦潦倒反映了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第一次遭遇了为一日三餐所烦忧的生存困境,连传统男性养家糊口的责任亦难以承担起来,所以汪文宣一直陷入对自己的能力的怀疑里。这种经济上的困境也会影响到身体和精神状态。
身体状况的对照。汪文宣本身身子孱弱,染上了肺病之后更是掠夺了他最后一丝生气,他的双手黄瘦,没有一点肉,“脸色灰白,像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的皮纸”,整个人半死不活。而曾树生则展现出“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蓬勃朝气,连汪文宣自己都察觉出来了,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的身子和走路姿势,还有他疲乏的精神,他觉得他们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人。除此之外,一心仰慕曾树生的陈主任同样与汪文宣构成了对照。陈主任“身材魁梧,意态轩昂”,可以轻而易举地帮树生提箱子,连声音也是“年轻而有力”的。于是,这种男性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钝化了汪文宣身上传统的男性自尊。
精神状态的对照。汪与曾的身体情况可以解读为一种精神状态的外现,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与身体情况是一致的。汪文宣总体呈现一种“向下”“被动”的精神与生命状态,他的精神需求最终从“办一所理想的中学”滑落至“我要活”。面对抗战时代环境的骤变,汪文宣不能适应,而且一直沉湎于往昔那个和平的时候,将所有的希望托付在“等待抗战胜利”之中。面对婆媳矛盾和上司同事的鄙夷,汪文宣只能以一种“老好人”的态度默默忍受,过度压抑自我产生了病态畸形心理,也消耗了他的精力。无论是家庭琐事还是社会变迁的大事,汪文宣总是无能为力。曾树生的生命状态则恰恰相反,她充满生命活力,“爱动,爱热闹,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主动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旦发现生活变得寂寞、冷清,曾树生自己便会要求自己“自救”逃离,她的出走是她“向上”“向外”生命状态的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两人精神和生命状态的对照是很不和谐的映衬,这更能深层地反映出汪文宣苦苦挣扎无果后的精神萎缩与自我意志的覆灭。
汪文宣自己彼时与此时的生活也形成了对照。彼时,八九年前的汪文宣心中怀揣着与妻子创办一所乡村化、教育化学堂的理想,这份理想不仅能发挥他自己的价值,践行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同时自在许多,不用看别人脸色做事;他在那时也拥有独立的爱情婚姻观,与曾树生由自由恋爱到步入新式婚姻,勇于反抗传统礼教。但此时他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理想,埋头于永远校对不完的长篇译稿中,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而这份令他疲倦不满的工作却仍需要“靠一位同乡大力得来”。正如汪文宣自己所说,他为了一点钱,“竟堕落到这个地步”。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有着自觉的身份认定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而如今这些都无法实现。这种自我的此时与彼时的对照对于汪文宣来说才最让他难以接受。
造成这样结局自然有汪文宣性格缺陷的原因,但作者显然并非要一味贬低汪文宣,或者是在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生命状态之间做一个高低抉择,而是通过对照关系去凸显,从前精力充沛、生活美满的汪文宣在如今的生活中处处“不如”曾树生、陈主任和过去的那个自己,自己所拥有的丈夫的、男子的、自己的尊严一一被摔碎的这种巨大的错落感,从汪文宣自身的错落感中引人深思,为何好人不得好报,进一步传递出悲剧的意味。
二、意象的深层意蕴
在《寒夜》中出现的“光”往往具有深层的意蕴,内含作者的主观情思。这里所说的“光”不仅指的是照明意义的“光”,而是带有象征意义性质的。在这里,象征意义的“光”具有持续时间短、颜色暗淡、微弱的特点。举例说明如下表:

“光”指向的就是汪文宣的希望。在小说中,这种指向义已有明示。抗战时期,由于空袭频繁等原因汪文宣一家总是停电,家里的电灯光时亮时灭,且多数时候是一片昏暗,一次停电中汪文宣败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这一句话很自然地能让读者从真实具象的“光”联想到现实环境中的光明与希望。而汪文宣本身又是一个“追光者”,小说中的他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但对面那条街灯光辉煌,他便朝着灯光走去。暗示着汪文宣尽管迷茫,但内心仍选择了“光”的那方。但小说又指出,汪文宣所向往的这些微弱的、暗淡的转瞬即逝的“光”很容易就会被一股更大、更冷的黑夜所吞噬,这股黑暗自然就是作者一直提到的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光”从亮至灭的过程与汪文宣的理想满满至理想覆灭的生存环境相对应,这个意象的运用营造了一种无形的悲剧氛围,带有暗示性地展现出汪文宣的悲剧人生。
三、人物命运的隐喻
对汪文宣的结局,小说不止一次地采用其他人物进行暗示隐喻。首先是唐柏青。在小说的前段,汪文宣就遇到了中学同学唐柏青。消极颓废的唐柏青所遭遇的是事业和家庭幻梦的双重破灭。自己无法照料生产的妻子,间接使得妻子死去,而自己作为一个文学硕士也顾不上实现自己的写作梦。实际上,唐柏青的现实处境与汪文宣出奇相似,既不能圆梦,也不能与妻子长相厮守,所以当汪文宣亲眼看到唐柏青因一辆卡车驶过这般无常地结束生命时,那个“完了、完了”的声音才会不断涌进汪文宣的脑海中,那是因为他也从中窥见自己的前景。
此外,当说道人物的隐喻时,读者往往只注意到了唐柏青一人,而没有留意到那个时隐时现的“炒米糖开水”的人。作者不吝笔墨地以汪文宣的视角对他进行描写,从这个老人的叫卖声,汪文宣觉得老人是衰弱的、空虚的、寂寞的。汪文宣透过这个老人似乎看到了他的将来,孤身一人、凄凉无助。后来小说又再次给了“炒米糖开水”的镜头,但此时售卖者已经换成了年轻人,那么之前的老人现在是死是生呢?汪文宣想到这里,更是陷入了新旧生命交替的担忧中。
悲剧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命运的透视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汪文宣身上的“悲观主义”因子,而上升到了一种更为抽象超现实的含义,人在命运面前尽管怎么挣扎也无法摆脱命运怪圈的无力之感,这无疑是悲怆的。唐柏青、“炒米糖开水”的人的悲凉结局放入到汪文宣的眼中,会产生与自己的命运相联系的一层悲哀之感,而小说外的读者透过汪文宣的一声哀叹又会产生怜悯之心,所以读者所接受的其实是叠加的悲剧感。
除了人物隐喻之外,《寒夜》中的“梦”也是汪文宣命运的隐喻。小说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梦”都是由主人公汪文宣完成的。他所做的梦有明确内容的是第二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十四章的“梦”的内容较为特殊,汪文宣梦见的是“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这个梦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唐柏青之死给汪文宣的震撼,而更是汪文宣透过唐的死在冥冥之中也预感到了自己即将下来的处境,只剩孤独的自我。而剩下的第二、二十一、二十二章的具体梦境内容都是围绕妻子曾树生的出走和婆媳矛盾,这是汪文宣梦境的主要组成内容。这些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可怕、可怖或是诡异的。汪文宣害怕这些梦会变成现实,所以做梦过后总会有“吓出冷汗”的惊惧反应。而从这些梦的内容便可知,它们恰恰都是汪文宣所选择逃避的现实问题的反映,他所压抑的“自我”会在梦中不期然地出现,提醒他妻子会离自己远去,家庭的裂痕很难缝合,他与树生共同的爱和理想也会随之破灭。
“梦”是命运的隐喻,在命运的无形力量下,汪文宣注定要面对梦变为现实的绝望处境。从汪文宣的角度看,如果说人物的隐喻是浅层次的隐喻,那么相比之下“梦”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隐喻,因为在“梦”中,自己不是站在别人命运的边缘地带,而是站在了等待命运主宰的中心。而后者无疑制造出了更现实也更无力的凄凉之感。
四、结语
《寒夜》中汪文宣悲剧感的成功营造得益于小说中内含的三种艺术方法的助力。三种艺术方法各自承担了营造悲剧感的任务,多方面“对照法”通过几组对照关系,在对比下显出汪文宣的强烈的错落感,进一步流露出悲剧感;“光”的深层意蕴在于作者借助光渐弱的特点,来暗示黑暗社会对汪文宣希望理想的腐蚀;在人物命运隐喻中,一层是唐柏青和“卖炒米糖水的人”作为汪文宣悲剧命运的隐喻,另一层是汪文宣“梦”的隐喻,两种隐喻都注定了汪文宣所预感的不幸之事会变为现实的不幸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