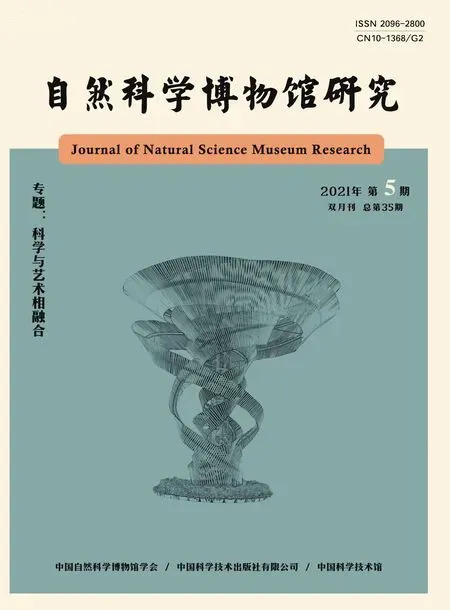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变迁
——从以文化和艺术为主的综合性视角出发
孙 淼
经过数百年沉淀与积累,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收藏、展陈和研究体系。自然历史博物馆大约和艺术类博物馆同时期出现,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通常不是来自艺术家以艺术品为目的的创作,而是矿石标本、动植物标本模型等直接表现事物与自然景观形态的物品。它的收藏和展陈随着不同时期哲学思想、社会环境、艺术和技术手段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并且折射出人类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认知的变化。
自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或许更加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出发,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从珍奇柜/珍奇屋、动植物标本、实景模拟、恐龙模型,到冷战时代开始的巡回展、新自由主义时期中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流行文化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近现代历史上对于自然的观念和认识始终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来回摇摆。疫情之后,如何通过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再创造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打造一个新型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也是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在未来必将担负的历史责任。
在关于博物馆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是基于理论的论述性著作。博物馆在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收藏和展示,则是博物馆的“所做和所为”。研究博物馆的历史,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克里斯·希利(Chris Healy)曾论述过,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考古学的现场,其中层叠着的过去一直延续到今天。”[2]本文将通过对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历史上的展览陈列的挖掘、再现、认知、研究和诠释,以揭示一些在文字中没有表达、甚至被隐藏的历史。
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边界从自然历史博物馆诞生之前的西方自然收藏开始,下延直到当代。这期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学科细分。如果需要从较为全面的学术视角来审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陈历史,跨学科的综合性角度是必须的。无论是思想史、沿革史、学术史、艺术史学、人类学,在需要时都可以作为研究中的工具,去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其中的艺术史学由于可以用于剖析展览陈列的视觉构建方式,是研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综合性的研究方式是对这段历史的尊重,也是思考面向未来的自然博物馆展陈时所需的学术思维方式。
一、 珍奇柜与珍奇屋:早期现代西方自然收藏与展示的滥觞(17—18世纪)
从17世纪开始,随着启蒙运动中西方的研究者对于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自然界中带有一定视觉特征的奇异物体。这种收藏从今天的学科分类视角看,是杂乱无章的。各种贝壳化石、红珊瑚可能会跟宗教器物摆在一起。这种混乱还表现在它的称谓上,法语中是Cabinet de curiosité,德语中是 Kunstkammer / Wunderkammer。法语直译成中文是“奇趣物品收藏间”(1)Cabinet 在法语中的意思是“特殊用途的小房间”,也可以指“带抽屉的柜子”。,德语则是“艺术品收藏间/奇异物收藏间”。收藏品分为来自大自然的物品(Naturalia)和人为创造的物品(Artificia)。欧洲大陆的王公贵族和一些学术机构在17—18世纪建立了自己的珍奇屋收藏,其中一部分最终成为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
(一) 佛罗伦萨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早期植物模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任佛罗伦萨大公期间,于1775年在佛罗伦萨建立的La Specola(2)直译:天文台。就是典型的由珍奇屋扩张成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今天的La Specola挤在皮蒂宫附近一栋18世纪建筑物的顶层,保存着大量动物标本、蜡制人体模型以及各种材质的植物素描与模型。为了在没有防腐技术的时代保存植物的形象,一种方法是用素描、水彩等艺术手段再现植物形象。更形象的方式是用纸浆、玻璃等制作仿真雕塑,甚至用来自中国的象生瓷(3)象生瓷:中国清代模仿禽、兽、虫、鱼、植物等形象造型的瓷器。制品保存植物的形象。在医学的人体研究方面,为了在天主教教义下满足医学教学和研究对尸体解剖的需要,从17世纪起就用蜡雕和颜料制作人体解剖的标本模型,以此替代医学教育对尸体解剖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从珍奇屋开始的收藏。
(二) 林奈与植物标本收藏
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先驱、自然历史学家林奈(Linnaeus)曾有一套极为丰富的植物学自然历史收藏。他于1783年去世后,其自然历史收藏和私人图书馆被英国植物学家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整体打包买下,由今天的伦敦林奈学会代为管理[3]。这部分自然历史藏品保持了极为难得的完整性,但很可惜没能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或许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展览上才能和观众见面了。
(三) 收藏自然的英国博物馆
从私人收藏的自然物到公共博物馆公开展示的自然物展品,这个关键的转折发生在17—18世纪的英国。伦敦的特雷德斯坎特(Tradescant)父子是当时著名的花匠和园丁。两代人从远至土耳其的广阔地域收集各种植物标本和活体以及其它稀奇的古物,其中自然物占大部分。特雷德斯坎特父子生前已将藏品向公众开放参观,并且不筛选观众。在他们去世后,其家族律师阿什莫尔于1683年将特雷德斯坎特父子的收藏捐献给牛津大学,成立了阿什莫林博物馆。初设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从藏品上看,大部分是和植物与园艺相关的自然物以及自然物的再现[4],但是并没有选用“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馆名。成立于1753年的不列颠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在初创时,从收藏上看也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历史”博物馆[4],就像一个戴上了大名头的珍奇屋。但是很快,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林奈的学生丹尼尔·索兰德用林奈的植物分类系统对其中的植物收藏进行了分类整理和造册。如今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已经从不列颠博物馆独立出来,其对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它是第一个用林奈的分类学规则整理和分类收藏品的珍奇屋(见图1),这也就让它的馆藏具有了博物馆的特征[5]。

图1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晶体石展厅
17—18世纪,欧洲诞生了大量珍奇屋类型的自然历史收藏,它们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先驱,收藏种类繁杂丰富,能反映当时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二、 动植物标本: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初步构建(18世纪末—19世纪)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爆发出一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浪潮。在此之后成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其藏品很大一部分来自王公贵族的草药和岩石等自然历史收藏。还有一部分收藏直接受益于16世纪以来的大航海和殖民运动。这些藏品为自然科学和自然历史收藏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 从博物到自然历史,更大规模收藏的建立
生活于18世纪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通过派遣学生跟随航船,到全世界搜集标本并接受传教士的植物标本捐献,拥有了几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植物标本[3]。他以此为基础创造的植物分类方法为自然历史藏品中植物标本藏品的整理、归类和排序提供了框架性的理论基础,让囤积式的收藏有了分类陈列的依据。到了19世纪,达尔文亲自踏上旅途,通过旅行中对动物的观察和分析论证了进化论。后世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重新为生物类展品设计了以进化论为线索的展览陈列。
(二) 自然历史收藏和陈列的命名及其理论起源
各种西方文字中代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词汇有统一的拉丁语来源:Naturalis Historiae。今天所用的“Natural History Museum”,直接来自1793年由法国皇家植物园和自然历史收藏馆合并而成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National d’ Histoire Naturelle)[6]。法语中的“自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老普林尼所著的NaturalisHistoriae,中文一般译作《自然史》或《博物志》。此书从文艺复兴至17世纪启蒙运动期间被多次整理和出版。法国生物和博物学家布丰(Buffon)自1749年开始发表的《自然通史》(HistoireNaturelle,直译为:自然历史)无疑是为巴黎这座博物馆命名的直接来源。在巴黎之后,纽约、伦敦和维也纳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命名。这批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已有的药用植物、标本、绘画等藏品以及珍奇屋中的自然类收藏为主构建了藏品序列。而在展览陈列方面则多是以类似图书馆式的陈列方式进行展示。
(三)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标本收藏与展示
标本,特别是动物填充标本的制作工艺,本是贵族保存和展示狩猎战利品的方式之一。这一形式在1803—1804年正式被自然历史学科接纳,作为保存和再现动物形象的方式[7]。从此之后,标本作为一种超越了素描和绘画的手段,可以更“真实”地收藏和展示动物,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自然收藏者的基本收藏品。在标本展示方面,博物馆从19世纪末起开始用大尺寸的封闭式玻璃柜展示对灰尘较为敏感的兽类和鸟类标本;一些动物骨骼标本的收藏,比如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比较解剖学展厅,则是用密集展示的方式,强调不同动物骨骼之间、人和动物之间的比较性展示。
(四) 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与殖民主义
19—20 世纪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陈列,从珍奇屋无序的收藏和展示,到构建“百科全书”式的藏品,最终进入了“科学化”和“学科化”的时代。这一巨变在学科上主要以林奈的植物分类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但在实践中也有不少殖民地原住民的凄凉。
西方主要国家在建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伴随着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出现,特别是1872年成立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从当时主流的“创世论”出发,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和国家公园都是在“收藏上帝创造的自然”。
在北美洲,弥补自身建国历史短暂这一缺憾的心理也影响着自然历史观念的形成。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内战结束之后的美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凝聚和容纳由分裂重获统一的国家。于是美国人把自然历史纳入美国历史中,认为美洲大陆是上帝留给美国人的宝地(4)从这个角度讲,纽约的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或许应该理解为“美洲自然历史博物馆”,而不仅仅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但是“American”可以同时理解为“美洲”和“美国”,这一双重解读可能是应该被提起的。,它的历史应该从更早的“纯自然”状态开始算起,而不是仅仅从“美洲的主人”——欧洲白人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后才开始计算。他们由此获得一种和历史深厚的欧洲一较高下的内心满足感,也为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大陆的掠夺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美国的这种自然历史观,没有把北美印第安人当作与欧洲殖民者平等的人类,而是仅将其视为人类学研究和展示的对象。居于统治地位的殖民者把印第安人看作“无历史”即“自然”的一部分;而殖民者作为“天选之人”,就应该改造自然和其中“更原始低等的人类”,这样就把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迫害堂而皇之地合法化了。这些观念和理论,最终都折射在美国19世纪末建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中。
在欧洲,19世纪高涨的殖民运动为宗主国的自然历史藏品收集创造了有利条件,甚至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借口。英、法、美等国的非洲、南美洲、亚洲的动植物和岩石类标本收藏主要建立于这样的背景之上(见图2)。

图2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非洲动物陈列
19世纪,欧洲最早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已有的来自珍奇屋和自然历史收藏的藏品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具有民族国家意味的国家级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且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之下构建了新的藏品陈列方式。
三、 实景模拟[8]: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艺术性、戏剧性的加入(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
从20世纪初开始,这种具有科学性和学科性的展陈形式开始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死板,不够吸引观众;动植物标本和原始生境也是割裂的,就像是狩猎和采集的战利品。此时一种原本主要用于宗教节日的缩比模型进入了展览设计的视野。这就是最早的“实景模拟(Diorama)”的起源。
(一) 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实景模拟的应用
自然历史展览陈列中最早的实景模拟是瑞典自然历史学家古斯塔夫·科尔索夫(Gustaf Kolthoff, 1845—1913)创造的。其展陈以动植物标本为核心,构建带有油画背景和生物生境的实景模拟,展示瑞典渺无人烟的荒原上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动物群落。在科尔索夫的实景模拟设计理念中,这种展陈方式的目的是以视觉方式表现科学的描述性文字所包含的动物生命和行为。
实景模拟设计是西方美术传统、动物解剖和标本制作工艺的结晶。其中的解剖和标本制作技法再现了动物的解剖结构和外形;绘画和雕塑的技法构建了背景和透视;利用戏剧化创作原理来设计标本所处的位置和姿态,构成一组实景模拟。此类展陈在视觉上类似于一幅生动的动物油画,但是本身是立体的、以拟真的动植物标本展示为核心的“装置”,在拟真和像形的描摹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够用细节极为丰富的视觉图像吸引观众。从根本上说,实景模拟更像是一种混合了科学标本和风景油画的视觉艺术作品。而在西方风景和动物绘画中,业已存在的对于上帝造物和伊甸园形象的愿景,也就不断地反复渗透在实景模拟的图像构成中[7]。
(二) 阿克利的实景模拟创新:艺术与自然的高度结合
从雕塑角度创作实景模拟的集大成者卡尔·阿克利(Carl Akeley)充分利用了西方古典雕塑艺术的技法。一件场景还原从标本开始,而标本要从动物骨骼开始:用陶土和石膏做肌肉和填充,恢复原动物尺寸,最后再将毛皮覆盖上去。这套方法从骨架开始,到肌肉、皮肤、毛发或服饰(取决于动物或人),从1648年的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开始,就是西方学院派美术要求的训练。传统的动物标本,多是用木屑等物质填充标本的空腔。这样的标本造型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形。阿克利结合传统雕塑手法塑造了骨架的动物标本避免了这种情形的出现。在阿克利曾供职的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非洲哺乳动物厅里,有28个实景模拟橱窗环绕着一群非洲象的标本,氛围感十足[9]。
在用实景模拟表现自然的展览中,艺术加工的痕迹无处不在。不仅仅是标本制作本身,包括背景绘制、背景和前景的距离和空间关系、前景中动物的位置和姿态,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艺术造型训练才能支撑。美国的实景模拟在100年前就能做到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与其幕后一批接受学院派美术教育的艺术工作者密不可分。
1910—1930年,美国各大自然历史博物馆都热衷于构建“实景模拟”。这也是很长时间以来,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动物原始栖息地环境的重要手段(见图3)。在那个只有黑白电影,报纸和书籍上也少有印刷照片的时代,博物馆里栩栩如生,充满细节、色彩和质感的三维立体动物生境具有令观众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尤其是橱窗里来自非洲的珍禽异兽处于原始的自然环境,以及背景中壮美的异国风景,这一切无疑是当时其它媒体无法提供的。
(三) 从博物馆展厅到文学与电影:殖民主义的渗透
20世纪20年代,卡尔·阿克利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制作了一个银背大猩猩的实景模拟。堂娜·哈拉维认为,这具死于1921年的银背大猩猩标本独自站在整个场景中,仿佛是阿克利自己的塑像站在位于刚果的坟墓上的场景[10]52。

图3 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狼标本和实景模拟制作过程
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它象征了美国殖民者对统治非洲的臆想。这种从实景模拟中传达出的视觉意象,对于文学创作和电影制作都有很深的影响。
这种用视觉方式复原史前生物的做法,带给电影领域新的制作灵感。1933年的电影《金刚》(KingKong)中,美国人在非洲殖民地遇到的巨型大猩猩“金刚”最终死去,表现出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生物的恐惧、异化和戕害。这样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本应是博物馆反对的刻板印象,但却首先来自当时的博物馆(见图4)。

图4 阿克利的银背大猩猩实景模拟与电影《金刚》的海报
源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电影上,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端倪。海明威作品《老人与海》(TheOldManandtheSea)中,主人公老人与化身为大鱼、鲨鱼和大海的大自然搏斗,最后在杀戮中获得一副大鱼的骨架。对这副骨架的描述酷似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暗示着人类和自然搏斗的成果也是可以进入博物馆的“纪念品”。这种人与自然通过杀戮建立关系的理念,也是海明威在 19 世纪末经常造访的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和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实景模拟用戏剧化的手段尝试构建的(白)人征服自然和其他人类“种族”的自然历史观[10]57-60。
截至20世纪初,这一轮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变革中,美国的自然和科学博物馆完成了展览和陈列设计的美学化,将展览空间三维化,同时把艺术视觉设计广泛应用于展览陈列的创作中,从而成功超越了当时的黑白电影和其它媒体,赢得了科普工作所需的关注。在用实景模拟对自然“再表现”和“再设计”的过程中,是以美术创作中“重建伊甸园”以及“戏剧性表现”的理论作为框架,借鉴当时的商业橱窗设计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混合式表现方式。在学科发展方面,为了不断完成新的展现栖息地的实景模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研究人员推进对栖息地本身的观察和研究,以便能够完成在博物馆内的栖息地展示设计。
由于搭建实景模拟的费用高昂,在 1928 年大萧条开始之后,新的大型场景几乎销声匿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自然历史博物馆都没有再次掀起如同20世纪初那样的热潮。但是已经修建好的岩石标本、动植物标本和实景模拟,一直都是在校学生和老师在学校之外的优良教育场所: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可以直观地向学生传授有关自然以及如何观察和描述自然的知识和技能。
这一时期,人类修正大自然的意识,以及以现代机械和化学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大规模对抗,为那个因过度使用化学杀虫剂而导致的“寂静的春天”埋下了伏笔。
四、 冷战时代: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专业化、主题化与科技化(20世纪60—80年代)
从大萧条开始到二战结束,大多数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都缺乏进行大规模展陈更新的资金,相关领域的新理论亦发展缓慢。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资助多为科研项目,展览陈列更新项目被搁置。但是在此期间也有个别新的展览,比如以人类身体和解剖学为主题的“人体”展览[11]126。
(一) 政府对展览的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工具
这种情况在 1957 年之后突然发生逆转。苏联在 1957 年 10 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经过美国媒体的放大和渲染,这颗卫星彻底改变了美国科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发展轨迹。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恐慌,对于冷战中的敌人在科学上超越自己的恐惧主导了美国社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方向。他们突然意识到:要让恐慌的公众对美国重拾信心,必须让他们接受更多的科学教育,才能消除内心的恐惧;或者说“要坚持给公众洗脑,让他们相信美利坚永远强大”。这样一来,教育机构成为了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联邦层面的资助成指数级别增长,让中学和临时展览成为了冷战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11]163。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与教育界对于博物馆如何完成“对公众的教育”这一职能的思考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化。自然科学教育正式被看作一种“对抗苏联威胁的武器”[11]176-178。
(二) 专业展会设计的介入与游乐场中的模型
在美国的第一轮自然科学教育改革中,博物馆并没有成为主要受益者。博物馆界对此并不甘心,重新寻找变革的方向。它们开始雇佣来自博物馆外的设计师,为展品陈列加入叙事线索,从而吸引更多资金发放机构的认可,尝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教育基金的拨款[11]183。博物馆领域之外的展览设计师把原本用于企业会展的设计思路创新与现代设计思维理所当然地带入博物馆的相关展陈设计之中。比如来自芝加哥的“新包豪斯”运动设计师内德尔昆(Nederkorn),就曾指导过 1962 年西雅图世界博览会的科学馆搭建工作。
专业设计师的介入意味着来自艺术、建筑、工业设计和大众传媒领域一整套设计体系的介入[11]186。来自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对于叙事方式的改变也影响了自然历史展陈。在此前的“实景模拟”中,设计师更多使用暗藏叙事的手法。但是新的展览设计要求叙事更加直接,不需要观看者推理或猜想,让从“看见”到“看懂”的过程更加顺滑和直接。这一时期,已经有大量的、同样由专业设计师创作的主题公园在美国开放,如1955年的迪斯尼乐园,以及1971年开放的迪斯尼世界。这些主题乐园既是博物馆的竞争者,也是新的影响来源。
(三) 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主题化
主题性展览突破了原有的物种分类学和进化论学科分类,能让观众在融入主题性叙事的同时接受一定的科学教育,并利用叙事性故事的引人入胜,弥补当时一般博物馆陈列的冰冷和生硬。这一尝试最早在史密森尼学会下属的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应用于“海洋生命”展厅,但是遭到了馆内分类学家的反对。这一尝试的最终结果仍然创造了历史。1963 年开放的该展厅布置成深蓝色,在墙上悬置了一个等比例的蓝鲸模型,从而给观众一种“浸入式”的体验感,仿佛置身于海洋之中。在此之后,这种布展方式成为自然历史展陈的常用手法。
20世纪60年代后的卫星时代,部分有资金的富裕博物馆在不断翻新的展陈设计理念启发下,开始利用工业和商业展览设计的理念和方式重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将其主题化、戏剧化。一方面扩大此前展箱式“实景模拟”的尺度,构成一个观众可以走入的,包含整个展厅空间的沉浸式实景模拟;另一方面是拟人化及叙事化,以具有本国历史特征的叙事方式,集中展示动物的等比例标本,提高观众对于展览陈列的认同度。从“自然的科学陈列”到“科学和自然的叙事”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博物馆接受来自外部的、对展览陈列革命性影响的结果。
五、 环保主义: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新机遇(20世纪70—90年代)
同一时期,在美国诞生了一种新的对自然与环境的反思,这就是环保主义。20世纪60年代,两本书的出版对塑造公众的环保意识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雷切尔·卡森出版于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其二是保罗埃·里希出版于1968 年的《人口大爆炸》。
(一) 二战后早期生态观念的发展
早在1945年,美国人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在他出版的回顾性文集《沙乡年鉴》中就曾提出一种新的自然观念,即“土地共同体(Land Community)(5)此书的中译本将Land Community译为“大地共同体”。实际上该理论主要涉及的对象是农业和农业生产所用的土地。将Land翻译为“大地”或许受到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地艺术(Land Art)”的影响,但在此处并不适用。”[12]。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工业水平,他并不能预见二战后出现的由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杀虫剂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但就是这种具有“原始意味”的自然观念,创建了一个“大土地”的概念,在农业的层面上将人与土地、水、植物和动物都包融进去。但是同样受制于当时科学发展对生态、环境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了解,他的推演也只能给出一些受到时代局限的答案。这样的理论并没有引起什么能够让媒体抓住公众的新闻,因而湮没在战后喧嚣的繁荣中。
(二) 《寂静的春天》:被危机唤醒的环保意识
《寂静的春天》一书同样是已发表文章的集结出版。该书作者卡森认为:大自然不是服务于人类的,人类只是自然的“见证者”,只有过度自大的人类,才会想控制自然[13]。卡森成年后虽然不是宗教信徒,但是接受过新教的洗礼。如果说“大自然服务于人类”是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毒,那么“人类只是自然的见证者”则更像是源自《圣经》的思想变形,将其中“神”的地位,换成了“自然”。人类由“神迹”的“见证者”,转变为“自然”的“见证者”。她带有绝望色彩的自然观被此后的极端环保主义继承下来,继续神化自然,并且把自然和人类割裂、对立起来,期望人类成为自然的“旁观者”。这种割裂和对立观念的传播,直接导致了系统性地放弃对自然的主动认知和主动作为。卡森在身患癌症的最后几年里写下的几篇文稿,越发显示出一种末日审判的图景。在有神论仍然拥有众多信徒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就这样走入了二元论的死胡同。
事实上,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改造自然。人类本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构成有机的共同体。人类作为一个集体,也必须认识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未来的自然观念和自然哲学,更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设计中不可能回避的主题。
存在已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环保主义的兴起中并没有起主导的作用。其影响甚至远不及作家、媒体和政客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批判来得猛烈。这个时期,大多数自然历史博物馆对于环保主义的回应主要体现在一些临时性的主题展览策展中。这不得不说是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面对时代潮流无法适应的一种失败。
六、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结合巡回展览和电影产业的市场营销探索(20世纪90年代—21世纪)
面对冷战中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及不断发展的带有自然历史元素的游乐设施,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在寻找新的方式以满足新一代观众的需求。这一时期的展陈设计思路更多地从自然科学和博物馆自身的学科桎梏中挣脱出来,越来越多地运用了二战后在美国诞生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工商管理学科所创造的营销理论指导展陈设计。市场营销理论开始影响博物馆展览陈列的价值取向。
博物馆意识到科学知识是自己提供的“产品”,这种产品可以是“教育与娱乐的结合”。在市场层面,这也是在资本控制下应对娱乐产业争夺公众注意力时的对策。但是任何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都绝无能力独立持续地推出高质量的展览。于是,一种半商业性的巡回展览应运而生。
(一) 大型巡回展览的出现
美国公立博物馆的巡回展览诞生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冷战中的社会氛围让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成为了公众舆论中的梦魇。为了安抚恐慌情绪,美国政府和史密森尼学会资助了几十场与冷战相关的展览,用以宣传美国文化和科学的光辉荣耀。最早的巡回展览是艺术与考古类展览“图坦卡蒙的宝藏”。该展于1972年在伦敦首展之后,1976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1977年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地举办过巡回展览。这样的巡回展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渲染,结合本身就极具话题性的展览主题,成为吸引观众入场的磁石。但是对于自然历史博物馆而言,仍然需要找到更符合自身定位的主题。
(二) 用机械重建活动的恐龙形象
制作大比例恐龙模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本杰明·沃特豪斯·霍金斯(Benjamin Waterhouse Hawkins),他的作品曾在伦敦水晶宫旁露天展出;有关恐龙的绘画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查尔斯·奈特(Charles Knight)为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绘制的图像。
二战后,有关恐龙的主题展览更是历久弥新。从1964年起,迪斯尼乐园就在以史前世界为主题的展览中使用仿真恐龙。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公司专门制作使用机械动力的可活动恐龙模型,并且向博物馆、主题公园、动物园和商场提供租赁服务。1987年,西雅图太平洋科学中心(Pacific Science Center)为新展览“恐龙:一场穿越之旅”购置了多套可动的仿真恐龙。结合出色的空间布置,该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展览设计中结合了科学知识和商业化设计思路,着重强调用机械模型模拟“活着的”生物,让模型在展厅里动了起来。这样的展览设计让观众在展厅里感受到史前巨兽逼真的动态体量,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中小型自然历史博物馆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自身没有能力设计制作这样的展览,但是仅靠永久馆藏又无法吸引到足够的观众以支撑日常运营。于是,租赁“恐龙”这样的展览就成为拯救中小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摇钱树”。有了此类新的收入来源,部分中小场馆的财务状况随之大为改观[11]267。
(三) “大片”式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博物馆与好莱坞的结合
“大片型”自然历史类巡回展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前期成本非常高昂,但只要推出后获得观众认可,有足够多的博物馆愿意出资借展,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收取展览租赁费用,从而支撑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下一轮的展览设计。这就像好莱坞电影工业产出的影片,制片公司完成制作后,由电影院线负责发行。这里的中小自然历史博物馆便成了大博物馆的“院线”。
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就要遵循商业化的法则。此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必须更多地关注“票房收入”,展陈设计也必须以激发观众兴趣、引导其继续参观为导向。从这个角度看,科普和娱乐的界限逐渐模糊,博物馆越来越像主题公园,自然历史展陈便愈发倾向于回应潜在参观者的需求,而不再以科学内容作为唯一的视觉传达依据。
这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展览设计策略,毫无疑问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把博物馆商品化,然后再资本化。如果在策展过程中放松对科学性的追求,转而迎合公众趣味,就很容易放松公共教育的职责。毕竟电子游戏的参与度可能非常之高,但博物馆却不能简单地变成娱乐场所。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电影和娱乐业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里常见的恐龙化石、动物标本、动物实景模拟在吸引观众方面疲态尽显,在充斥视觉特效的好莱坞大片和游乐场的仿真模型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如1993年上映的电影《侏罗纪公园》和奥兰多环球影城中的侏罗纪公园部分,就是这一类型的组合。
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银幕上“活化的恐龙”出现后,终于抓住了好莱坞大片的尾巴。在《侏罗纪公园》上映的同一年,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美国恐龙协会联手打造了一个好莱坞大片式展览——“《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The Dinosaurs ofJurassicPark)。该展览为博物馆带来了巨大收益,开展仅10天便有4万名观众入场。在纽约之后,该展览进行了“环美巡展”,全程如同电影大片一样火爆。该展览将银幕上的大片搬到博物馆中,让观众可以走进电影后台,同时获得关于恐龙的知识。然而这样的展览何尝不是电影的延伸,是在市场与资本的控制下,制片方和博物馆共同构建的一个新式浪漫主义自然历史幻境。
在市场化导向下,自然越发地被塑造成如电影一般的幻境,越发与人类和人类活动割裂。这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新自由主义自然历史观”。在一定条件下,会把“自然的自然”“地球的地球”这类理念传达给公众,让公众错误地认为自然是一种人格性的存在,作为人类最好不要干预自然。最终导致政府在对自然的管理策略上受到公众压力,部分或全部放弃对自然环境的管理。
七、 更多的疑问: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未来愿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变迁实际上有内外两条线索:一方面是内在的自然观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博物馆展览陈列设计不断寻找更加符合时代的设计理念和展陈模式。
(一) 自然观的发展
西方社会自然观的发展演变,一直以来都是由研究者主导的。文艺复兴时期懵懂地寻找探索自然的科学方法,尝试在神学的边缘寻找突破,此时的自然观是一种朴素的原始形态。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欧洲的早期自然科学研究以“自然是上帝的创造,应当为基督徒服务”为信条,其发展受益于欧洲的殖民运动,也为殖民运动背书,同时反哺着对殖民地资源的开发和掠夺。19世纪在美国发展出对自然历史的崇拜,将自然历史作为“建国神话”的一部分,在瑞典则成为民族主义萌芽的一部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为了给压迫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族群提供合法依据,以猎奇和“新探险者”视角回顾和美化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神奇动植物的向往,并且在自然科学特别是人类学发展中强调所谓的“种族”理论,背后隐藏着称霸全世界的野望。
二战前,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构过程,其科学研究、科学展示与所在国家的荣辱、殖民地多寡密切联系在一起;自然历史和科学史的展示也因而染上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在二战后的冷战期间,美国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为了保证自身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资助宣传本国成就的自然和科学观念进行展示传播。随工业化社会而来的严重环境危机衍生出以基督教“末日论”为内核的自然观,但炙热的环境运动并没有催生出新的自然观和环境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政治和经济活动日益渗透到展陈设计中,改变着展陈设计的理念和形态。
以上自然观的变迁,在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收集和展陈设计与制作的历史过程中,通过视觉艺术手段传达给了观众。即便时间已经进入21世纪,仍然能在那些已经固化的展品中寻觅到历史的痕迹。这些依然显而易见的“历史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反思,每当这些问题被提及时,博物馆往往只是将历史事实抛给观众,任其自行判断。
(二) 展览陈列设计的发展脉络
通过上文的梳理,自然历史展陈的设计发展脉络逐渐清晰:最早的杂乱珍奇屋和玻璃橱柜里的岩石、动植物标本构成了百科全书式的陈列。随着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的发展,比较解剖展厅、进化论展厅以及实景模拟展示日益发展。对于将自然展示得更真实、更科学的追求,最终在20世纪初期的实景模拟制作中达到极致。这种模拟自然的构建,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西方风景油画中“自然是不完美的”哲学理念。展陈设计从美学出发,尝试构建一种完美化和神化的自然,从而满足设计者表达特定思想理念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后,受到奥本海默“探索馆”互动展示和主题游乐园娱乐设施的启发和挑战,出现了以观众为核心、以科技和电控机械技术为主导的自然历史陈列。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大片型”自然历史特展设计。时至今日,新的展示技术早已进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各个角落。
科技发展与设计理念带来的展陈方式创新,一方面满足了不同时期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的视觉和媒体需要,另一方面对观众的观展方式和喜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日观众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的要求早已今非昔比,仅靠稀有标本已经很难吸引观众入馆参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随着展示技术的不断创新,观众可以获得的观展体验日益丰富和逼真。自然历史博物馆需要持续立于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潮头,在展览陈列设计中努力创新,方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与青睐。
(三) 走向新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如今,从创新自然历史博物馆设计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博物馆可以在自然观、设计理念和博物馆学习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在展陈设计与博物馆教育/学习方面,近年来我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专著和译著,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也多有发表。这就为今后的展览设计和教育活动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自然观方面,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人类诞生以来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加深。无论是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污染物的排放,还是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而日益缩小,亦或是人类随着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而开始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其基础都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种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加深的关系会在将来遇到拐点吗?也许有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或许由此可能。未来在核聚变等超级新能源的支持下,可能将人类活动的污染物排放降到极低的水平,食物可以通过完全脱离土地的方式在工厂中培养。这似乎是一个“把自然还给自然”的方向,那么这样的人类活动是否可以看作是部分脱离地球的生态圈而存在?但无论未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发展,只要我们仍然生活在地球上,整个星球便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即便人类飞出地球,依靠宇宙中的其他资源生活,仍然是身处一个更大尺度的“自然”之中。面向未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与陈列,更应以新型的自然观为基础,激发当代观众对美好未来的无限畅想。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偌大的地球已经变为万物互联的“地球村”。自然历史博物馆从诞生之初的雏形发展至今,已经历了数百年的积淀。笔者不揣冒昧,大胆设想:以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为依据,以人类改造和认识自然的历史、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史及人类的自然哲学观、自然伦理观的发展史为线索,创建一种新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中的展陈设计,不仅表现人类自然观的变迁,更要表现自然历史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历程。这座博物馆在展陈设计思想上立于高位,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博物馆(the Museum of Museu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