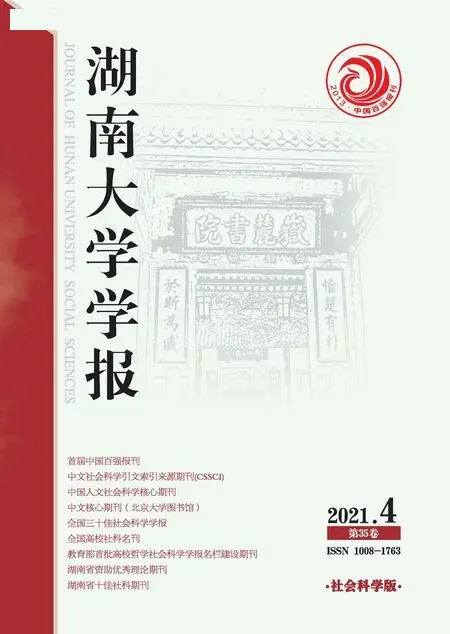叙事有序如何可能*
——何心隐道统叙事的先验法则
童 伟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叙”与“事”合用,指的是有先后次第地叙述变化的事情。“叙”与“绪”“序”通,“次弟也”[1]126,“叙事”必然包含次序。“事”与“史”通[1]116,是变化发展的产物,叙事遵循某种统一有序的先验法则,在泰州学派何心隐(1517-1579)阐扬儒家正统思想谱系的道统叙事观中,揭橥叙事有序的形式法则乃是“数”。学界虽已指出中国古代道统体现了思想史叙事的一种脉络[2]48-60,也注意到心学学者对道统叙事形式的“心学之史”的编撰书写[3],但是未从经史合一的视角考察道统叙事有序的本原。宋明理学都重视以道统制衡治统,而宋儒有经本史末的传统,轻忽“事”或“史”,注重道统授受的载道之文,如朱熹主张“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4]2950,确立了以“四书”作为儒家道统的独立经典体系。因此,“数”的思想资源虽出自宋儒,但直到明代心学兴起才转化为道统叙事有序的范畴,成为经史合一的重要中介。心学认为心外无事,求至善只在人心。王阳明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五经》亦只是史。”[5]11把经史等量齐观,因为“事”或“史”可以激发人内心之“仁”,即善恶之“理”;王艮反对皓首穷年于经典文本,倡导于百姓日用之“事”上“学”;何心隐的叙事思想溯源道统谱系,“经史一物”或“六经皆史”的思想雏形已然显现。何心隐关于道统历史的想象旨在确立“叙事”或“讲学”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叙”的先验次序“数”内在于“事”的展开次第,也显现于承祧道统的次第。在形象与事象的组合中蕴含了迁变流转的必然性,先验地设定了一种有意味的、优越于具体时空进程的整体次序,它主导了叙事时间、叙事顺序(如顺叙、倒叙、插叙等)、叙事速度、叙事节奏、叙事频率等的分配。探讨道统叙事有序的先验法则“数”,有助于深化理解经史合一的中介环节,从而理解中国叙事独特的有序性,即使时间线索模糊、因果关系松散,也可以因为契合“数”而做到井然有序。
一 外显内隐的道统叙事次序
在这充满偶然性、随机性的世界里,哪些能够进入叙事,由叙事次序来测度。概言之,道统叙事外在显现为“五事”,内在隐含仁心。叙事的“事”并非客观事物,系指“五事”,即诸种影响作用于“貌”“言”“视”“听”“思”的人化之“事”,其中“貌”“言”分别具有叙事的第一、第二优先性;叙事以仁心为内核,世界存在意义由人心生出,契合道统的先验道德属性。对人的“貌”“言”等形象加以叙述,将形象感知与道德体认相结合,让读者或听众对叙事加以感知观察,叙事的意义就存在于对人事形象的感知之中。
明代泰州学派复兴师道,在践履和理论上颇具独创性,创始人王艮以行动力强劲著称,他以一介布衣身份践履道统,面向平民广设杏坛,大倡讲学之风,但缺乏师道谱系的理论阐释。何心隐不仅行动力超强,而且擅长理论阐释,这与他优渥的家境和良好的教养有关。何心隐原名梁汝元,生于江西永丰大族,后因讲学蒙冤遭缉拿,为避祸而更名。明人沈懋孝指出王、何二人弘道的差异是:“心斋先生遡言格物于正本澄源之处,令后学敦行树标……至如梁先生言尧舜对局、道大行统合于上,孔孟对局、道大明统合于下,又言天地交而万彚生,君臣交而豪杰用,师友交而英才成,皆慨然自任以斯道之重。”[6]可见时人已意识到何心隐擅长道统诠释,他认为“学”与“讲”或称“讲学”,就是意义神圣的“叙事”[7]2,继承孔子及早期儒家通过整理《六经》建构的道统脉络:伏羲、神农、尧、舜、禹、文、武、周公,又以师道作为主线加以调整,君臣之间对治家事国事天下事,“学”“讲”的交流互动中产生“叙事”行为,以叙事为契机,治统中的君臣转化为道统中的师友,“学”与“讲”就是师道统绪下两种紧密相关的叙事行为,“讲学”也就是“叙事”的代名词。道统是号为正统的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史叙事脉络,在何心隐将儒学思想史叙事化背后,有一种借助历史系谱建立正统思想权威,为当下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垄断性辩护的意图,这种意图被有意凸显,放在明中晚叶历史、政治、社会语境下,呈现出多维发散特征。诚如葛兆光所言,道统叙事究其实“只是一种虚构的历史系谱”[2]49,那么何心隐有意凸显道统谱系的叙事能指,也就表明叙事所指独尊的真理性地位,道统叙事理论与弘道实践互为表里。
“事”指内心之仁在“貌”“言”等外在形象的显现,道统叙事的关键是“叙貌”“叙言”,叙事旨在使人臻于“仁”。因为人不同于其他形类之处在于人能感知外物、产生意识,这就是何心隐所言之“事”,它内隐于人心深处,难以把捉。“事”又外显于人的形色辞气,从容颜面色的变化、言说气流的波动,可以直观心上“事”,故“有貌必有事”“有言必有事”[7]1。儒家认为“貌”“言”是内仁外礼教化的成果,“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8]1671,其中“貌”是最直接的体现,如面容、相貌、表情、形象等。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邢昺疏云:“人之相接,先见容貌,次观颜色,次交语言,故三者相次而言也。”[8]2486人以修身为本、孝道为先,曾子所云三项礼仪准则是“容貌”“颜色”“语言”,人的外在形象塑造背负了仁义道德的重担,在人际交往中谨慎管理形象极为重要,而叙事行为有助于塑造“仁”的形象。
如此,儒家心性修养问题遂转化为且“学”且“讲”的“叙事”行为。心性修养的分寸感极难拿捏,只有极高明睿智才能兼顾“心”与“貌”,普通人不是“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就是“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5]110。何心隐从“叙事”行为入手对治“心”“貌”难题,主张所“学”者在“貌”,所“讲”者在“言”,将“貌”“言”的心性修养问题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且“学”且“讲”的叙事行为。“乃学乃讲其原,不人而形,不人而声,而首而貌而口而言其原耶?”[7]16“是故学其原于貌者,原于人其貌也。原于仁其人,以人其貌,以原学也。徒然原学于貌以学耶?是故讲其原于言者,原于人其言也。原于仁其人,以人其言,以原讲也。徒然原讲于言以讲耶?”[7]9仁是人之为人的先天条件,于外显可感的容貌语言上即“学”即“讲”,具有叙事的优先性。
具体而言,叙事的先验次序首先见诸“五事”的次第“貌”“言”“视”“听”“思”,其出处在《尚书·洪范》。对具体可感的“五事”加以言说生成为“叙事”的意义世界,“貌”居第一,“叙事而必叙貌于第一事”;“言”处第二,“叙事而必叙言于第二事”[7]2,“叙视”、“叙听”、“叙思”依次为第三事、第四事、第五事。始于一,终于五。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次第不是发生先后,而是叙事的先验次序,所谓“不容不”如此。叙事次第与“事”本身的内在次序一致,人之为人的先天规定是人生而有“貌”有“言”,“事”见诸形貌、经由言说得以传承。把握在世的意义,就在于感知、模拟、塑造人的形貌,通往内仁外礼之君子,此即“貌其事而学”;人出于言说叙事的冲动获致当下在世生存的意义,此为“言其事而讲”[7]1,“叙事”建构起一条成“圣”之路,即人发展完善的极境。“貌”讲究表情恭敬、态度端肃,“言”需要语句顺从、持论公正,“视”必须目力清明、识见超群,“听”则要耳力发达、深谋远虑,“思”追求反应睿智、超凡入圣。叙事在当下的、具体的人事上落地生根,叙事赋予文字在人情深浅中一探究竟的力量。因此,道统叙事以“事”为出发点,以“圣”为叙事世界的意义归趋,所谓“圣其事者,圣其学而讲也”[7]4。
叙事由人作,在叙事的深层次象征意义上通往心上“事”内隐的“仁”,人借叙事建构了一条成圣的通途,叙事被赋予天启神授的规定性,惟有天地、乾坤堪称其本原。乾之为乾、坤之为坤,以“仁”为先验属性,而“仁”在人心,为变化不息的“事”和“叙事”行为,包含了实质性的价值内容。人之圣者揣摩效法万物得其神意,乃现河图洛书,遂制《易》作《范》,于学于讲,延续传承圣哲经典。“事”和“叙事”的任意性被扬弃,基于叙事行为人类不断走向“仁”,从而萌生了道统的演化形态。叙事不仅赋予人的在世生存以意义,而且在相统相传的叙事行为中发展演变,超越凡庸。一切发展演变都可以在源头寻觅到某些重要依据,故本文接下来将探究作为叙事源头的河图洛书。
二 互文关系的河图洛书次序
尊奉河图洛书作为经学本原,汉儒已开风气,后儒不断加以发明。上古三代茫昧无稽,后世一代代按照当时时势、政治需要将河图洛书踵事增华,顾颉刚揭开古史的面纱,是“积薪般层累起来的”[9]63,距离河图洛书的时代越遥远,对其层层积淀的历史想象和创构愈加言之凿凿。关于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的神话想象一直聚讼纷纭,河图洛书是否客观实存属于真理问题,目前尚无法得知。它作为思想资源在历史中层层积淀,属于价值问题,其内在底蕴和先验法则值得探寻。
河图洛书的经学本原地位,为叙事行为“学”优先于“讲”的先验次序备书。何心隐在道统叙事谱系上的重要举措是拟定《周易》《洪范》为经学的双重源头。他认为伏羲仿效河图创《周易》,禹取益洛书作《洪范》,叙事得自上天,非人力可为。“不人而圣,以则物而神”[7]16,“则物”的意思是趋近物。这里的“物”并非指客观存在的“万物”,而是“与《周易·系辞》‘精气为物’思想有关,透过神话时代的鬼神想象,以及逐步摆脱鬼神想象后的道境想象,显示出的物像,因此万物迁移运转是鬼神或道境之显像”[10]。“物”具有神韵进入人心,人人并非生而为圣,因为秉承神意创作经典叙事文本而成圣。“不圣而羲,以《易》以则河之所出神而图,不圣而禹,以《范》以则洛之所出神而书”[7]16,受上天神意启发,有忠实模拟地“学”,还需发挥自主创造性地“讲”,二者缺一不可。亦即叙事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形态:“学”是仿效、模拟上天神意的显现,择取其精髓,“讲”是伏羲、大禹分别发挥河图洛书精神意蕴的独特叙事,各自阐释上天昭示的龙图龟书,所“学”之中内蕴“神物”,确定“学”先于“讲”的先验次序;“讲”是对河图洛书等“神物”的物态化叙事,是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学”必有“讲”方得圆满。后人习惯使用“讲学”一词,实应为“学讲”,从道统叙事溯源看“学”先于“讲”,是就无“学”则无“讲”的意义而言。
道统所叙之“事”意味着变化与发展,静止不变则“事/史”无从谈起,从圣贤所学所讲看,叙事呈现为《易》之“画”-“卦”、《洪范》之“叙”-“畴”、武王与箕子之“访”-“陈”等变化形态。以《易》的叙事形态是“画”与“卦”为例,“必羲必亦有事于貌、于言、于视、于听、于思,以画而卦也,以卦而《易》也”[7]5。伏羲作《易》,河出图,“画”“卦”流芳百世,凝结了伏羲曾经的且“学”且“讲”。而大禹作《洪范》,洛出书,其叙事形态是“叙”与“畴”,“必禹必学、必讲于畴于范,以叙其事,而学而讲也”[7]4。另据《史记·周本纪》及《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后访箕子问以天道,箕子陈说治国安民恒长不变的条理法度,作《洪范》。“范”辖九畴,“畴”系五事,何心隐想象大禹用洪范九畴所叙之事,周武王与箕子也曾在且“访”且“陈”中叙述过。它们的共性是都凝结了“五事”叙事,差异性体现了圣人“学”与“讲”时叙事形态的演变,在演变中道统的思想史叙事得以建构。
一般认为《周易》比《洪范》更古老,何心隐既承认《周易》是《洪范》的本原,又把二者共同视作叙事本原,使之互相兼容,蕴含的叙事理念耐人寻味。这表明《周易》采用“画”“卦”的拟象范畴,范导了《洪范》采用“叙”“畴”的叙事范畴,“叙原于画也,畴原于卦也,《范》原于《易》也”[7]5。“叙”是有顺序地陈说五事,在“畴”中分门别类析出条理,契合线性或次第推进的叙事表达;“画”是拟取物象或事象,创构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卦象,制成八卦,卦形由阴爻阳爻构成特殊符号,卦形形象类似图画引人遐想,暗示某种哲理意义,冥然契合整体浑沦的诗性表达。换言之,《洪范》的叙事范畴“叙”“畴”,归原于更为古老的《周易》诗性象征范畴“画”“卦”,那么“叙”与“画”、“畴”与“卦”以“象”为共同基因,相辅相成建构了中国人使用符号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一为叙事的,一为诗性的。诗性象征传统更为古老,而叙事次第以及人事归类的条理叙事出现较晚,它们由诗性拟象转化而来。
进言之,“叙”-“畴”与“画”-“卦”的互融,表明叙事形象与抒情意象的互文关系。在叙事形象之中潜含抒情意象,反之在抒情意象之中蕴含叙事形象。何心隐写道:“又况《易》而卦而画,又即《范》而畴而叙其事也。”[7]8线性时间观告诉我们,晚期经典可以吸收继承早期经典,反之早期经典则无法未卜先知地包含晚期经典。但是《周易》与《洪范》效仿天地神物而生,不受线性时间观束缚,“括书以《易》”是说伏羲拟河图作《易》涵盖了洛书,而“括图以《范》”是指大禹效洛书作《洪范》也涵纳了河图。因此,《周易》《洪范》是互文关系的经典,《周易》探究世间万物变易之道,“即乾坤而复姤乎”[7]18,这里的乾、坤、复、姤都是卦名,乾卦坤卦为至纯至仁,阳气至刚、阴气至柔。复卦震下坤上,一阳五阴,阳气初始生发;姤卦巽下乾上,一阴五阳,阴气初始发生。乾卦坤卦阴阳对立中蕴含变化,初始发生变化者复卦姤卦,表明至纯者必然萌生新变,变化到极致则纯阳而生阴,姤卦向坤卦演变。反之纯阴而生阳,坤卦尽则复卦阳来,阳渐长则转为乾卦。这种对万物演变的叙事,超越具体时空和事物的自身限制,无疑比线性时间叙述更具有概括力和象征意义。《周易》《洪范》在超时空的万物变迁次序上共同遵循阴阳消长、相遇、变化的规律,彼此互融互涉,所以说“则图则《易》,自足以括《范》于书,则书以《范》,自足以括《易》于图,莫非圣人则神物也,莫非《易》,(作者按:逗号疑误加。)《范》则图书也”[7]18。
《周易》与《洪范》的互融在叙事次序上体现为,与“学”优先于“讲”的次序一一对应的是,第一事“貌”对应第一卦“乾”,第二事“言”对应第二卦“兑”。何心隐曰:“原学其原,则原于《范》之五其事之一而貌者,原于《易》之一而乾也。”“原讲其原,则原于《范》之五其事之二而言者,原于《易》之二而兑也。”[7]9-10亦即“学”有双重本原:《洪范》第一事“貌”和《周易》第一卦乾卦,“学”“貌”“乾”三者呈现互文关系。同理,“讲”的双重本原是第二事“言”,以及第二卦兑卦,“讲”“言”“兑”亦为互文关系。需要补充的是,乾卦兑卦在《周易》中的“一”“二”次第,取自宋儒所传《先天八卦方位图》,将八卦相交错,标示八种方位次序,乾居南位,称“乾一”,兑位于东南,一阴一阳,相偶相对,次序上紧邻乾卦,故称“兑二”。何心隐从《周易·说卦传》引用象例说明八卦的取象:“乾为首”“兑为口”,《正义》曰:“乾尊而在上,故为首也”,“兑西方之卦,主言语,故为口也”,口能以言语悦人,故合“说”义。所举人体器官的象例“首”“口”,恰与《洪范》五事之“貌”“言”呼应。何心隐之所以大费周章地论证附会,清晰地传达出为“叙事”或“讲学”确立正统源头的努力,带给后人的启发在于,叙事所及的视听形象,从本原上讲与诗化的“象”或“意象”融通,“形象”与“象/意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没有森严的壁垒,二者本来为一体。叙事的所“学”所“讲”给予人化世界以内在法则,《周易·系辞传》有“观象制器”的说法,古人把“卦象”作为器物、工具等一切创构的本原,那么将叙事本原归结为卦象也可视作这一传统的延伸。具体到叙事的先验次序,“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8]78。有变化才生发出事,圣人诠释变化预知未来走向。本文从变化的维度上考量《洪范》《周易》互融互济的理据:依托“数”确保了叙事的有序性。
三 因数明理的太极皇极次序
道统叙事依托“数”确保叙事有序,是《周易》《洪范》经学之理的数量化表达。何心隐吸收南宋理学大儒蔡沈的范(《洪范》)数易(《周易》)学,改造为叙事之数理。“数”是人的在世体验进入叙事所遵循的先验形式法则,也是哲学意义上对一切演变的量化表达图式,是经史合一的枢纽。在即“学”即“讲”的经学史叙事中,“经”相统相传的叙事即成为“史”;叙事旨在昌明心学之“理”或“仁”,因此“史”的叙事本原为“经”。何心隐因讲学罹难,存世文献有限,他行文中糅合大量概念术语,往往关涉深邃的思想渊源,比较晦涩费解。为此,探寻这些概念的可靠出处,是理解其叙事思想不可或缺的支撑。
有确切证据表明何心隐融通《周易》、《洪范》、因数明理的叙事思想,受蔡沈(1167-1230)《洪范皇极》一书的深刻影响。此书由数图和文字解说两部分组成,何心隐对其推崇备至,他甚至在被押解途中,上书陈说冤情时抄录《洪范篇》呈示赣州蒙军门[7]101-102。蔡沈父亲、兄弟、祖孙皆为朱学干城,其父蔡元定(1135-1198)与朱熹亦师亦友,极受器重。何心隐也极崇仰蔡元定,可能因为他们都有讲学遭禁遭荼毒的惨痛经历而心生戚戚焉。当年朱熹遭朝廷“伪学”之禁褫职罢祠,蔡元定主动前往就捕,何心隐褒赞他“表表于宋者又一人也”[7]80。蔡沈传世著作有《书集传》和《洪范皇极》,前者遵朱熹师命撰写,后者遵父命传承家学。《书集传》诠释《尚书》的帝王谟诰之旨,融汇众说,在元、明两代是科举考试士子的必读书。在蔡氏家学方面,蔡元定指派其子分工治学,长子蔡渊“宜绍吾易学”,三子蔡沈“宜演吾皇极数”[11]。蔡元定认为,传统易学属于“象”学的经学,而皇极学属于“数”学的易学。蔡沈遵父命以《洪范》为根据构造出“数”又称“范数”的系统。
蔡沈的“范数之学”以宋代河图、洛书学说为介质,以《洪范》为根基,汲取邵雍《皇极经世书》用“数”表达易理的易数学思想。传统易学为“象”学,蔡沈发挥潜藏于《洪范》中的“数”学,将《洪范》引入传统易学,使得《洪范》成为与《周易》互补的同等系统。“范数之学”的独特视角在于“因数明理”,弥补了朱学理论建构的欠缺。因为“数”在孔孟学说中一直付之阙如,宋代周敦颐、二程子昌明理学之时,邵雍的因数明理学说罅漏补缺;朱熹、张栻、吕祖谦讲学倡道之时,由蔡元定承担因数明理学说,最终由蔡沈完成,蔡沈既是承继家学,也满足了师门朱学建构的需要。蔡沈通过援用《洪范》,为范数学确立了堪与《周易》经传齐肩的经典来源,与传统经学的象学易学形成互补,殊途同归。一言以蔽之,《周易》和《洪范》的融合点就是以“数”穷尽天下之理。
因数明理的“数”是“理”的量化图式,数以明“理”,理显于“经”,“理”是“数”的经学本原。蔡沈的“数”不是古人用于计算的算术、算学,也不是研究“数”的客观规律的学问。“数”的本体论中糅合了自然宇宙观、政治伦理、人事变迁的经验,用“数”表达中国人对于人事吉凶、悔吝、灾祥、休咎变迁的一种量化体验,旨在以“数”的量化测度把握变化,把人事放在“数”的阵列中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转机。理、气、形皆有定数,形数、气数具体可感,理数无法触摸感知,但是提供了判断一切变化的依据:“知理之数则几矣。动静可求其端,阴阳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万物可求其纪,鬼神知其所幽,礼乐知其所著,生知所来,死知所去。”“礼”给予世界以外在秩序规范,“数”安排“礼”的次序,“数者,礼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圣人之道,知序则几矣”[12]704。所以,“数”的先验次序主导了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的变化。范数学不以科学价值见长,严格地讲甚至缺乏基本的数学科学思维,但这无损于它的人文诠释价值,即对天理演变规律采用量化图式加以诠释。后人对此书多有误解,到了清代《四库全书》将此书归入子部“术数”类,有轻视其理学价值的倾向,殊为可惜。
何心隐叙事思想中河图洛书的互文关系,放置在范数易学框架中就不难理解了:河图或《周易》呈阴阳之象二元对立的偶数模式,洛书或《洪范》是三元化生的奇数模式,要理解长时段变化,就要统一河图洛书两种不同的“数”理模式。宋儒的“数”理思想已很成熟。蔡沈曰:“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12]699将《易》《范》在道统中并置,以整体把握道统流变历史,《易》之象是对天地事物的体知与拟造,《范》之数则是对天地事物的有序记录。蔡沈的范数易学融合了理学对“数”的认识论倾向与价值论归宿,沟通经学与经学史。河图洛书的区别在“数”有奇偶之分:“卦者阴阳之象也,畴者五行之数也。象非偶不立,数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数之始也。”[12]708河图呈阴阳之象二元对立的偶数模式,象为偶,彼此对待,画为八卦,体为圆、用为方,动而之乎静,体之所以立;洛书是三元化生的奇数模式,五行迭运,流行变化,叙为九畴,体为方、用为圆,静而之乎动,用之所以行。概言之,河图之数定于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主定性;洛书之数始于一,由一而三,由三而九,主流行。“一,变始之始。二,变始之中。三,变始之终。四,变中之始。五,变中之中。六,变中之终。七,变终之始。八,变终之中。九,变终之终。数以事立,亦以事终。”[12]710三个数为一组变化,经历三组变化,从一开始,以九为终,构成流行变化基本模式,在此模式基础上可以继续推衍,无穷无尽,广为人知的九九八十一变模式即出于此。
何心隐的道统叙事次序是对蔡沈“奇”“偶”相辅相成“数”理的发挥和改造。象偶是以二为基数的推衍,师道传承中“学”与“讲”、“师”与“友”成对出现,为偶数之象的对立转化,在道统叙事中是定性的主力。奇数是以三为基数的推衍,师道叙事经历了由隐微到显达直至昌盛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羲、尧、舜、禹、汤、尹的“隐隐学而隐隐讲”,师道刚刚萌芽;第二阶段是高宗、傅说、箕、文、武、周的“显显学而隐隐讲”,师道展现勃勃生机;第三阶段是孔、颜、曾二三子师道显扬道统确立,“显显以学以讲名家”。已有研究指出:“河图对应八卦,八卦表达的是阴阳之象,象以偶数的方式呈对待的形态;洛书对应九畴,九畴表达的是五行之数,数以奇数的方式呈流行的形态。”[13]152从思维方式上看,偶数之象带有朴素的诗性思维色彩,阴阳对立制衡,为静止的、单调的、高密度的稳态结构,内蕴跳跃性转化的契机,适合诗性的断点式情感表达;范数九畴以奇数把握世界运动变化的三步走规律,突破了象数对立循环转化观,类似正反合的辩证思维,有助于呈现变化渐次发生的、低密度的有序性,变化有序方成叙事。较之单一的奇数或偶数观,象偶-数奇相结合有助于叙述事物长时段的曲折变化并揭示其规律。
河图洛书“奇”“偶”图式虽不同,但都承认穷极通变的绝对性,太极皇极在对立转化中居于叙事的优先地位。何心隐认为《周易》的太极数“九”、《洪范》的皇极数“五”都是以“数”呈现的“象”,喻示变化所能达到的极限。“有太极之极,以变以通乎九之其穷其极者于其《易》也。有皇极之极,以变以通乎五之其穷其极者于其《范》也。”[7]12太极皇极为至大至善,太就是大,指仁,太极化生两仪、四象、八卦,阴阳之象在偶数模式中蕴含对立转变的契机。皇极是《洪范》第五畴,为人君至极之道:中德。“建立其至极之道,使人往而归焉。是之谓建用皇极也。”中之至极,事物发展到至极、极盛,也就走向自身的反面,事物发展转化环节中的极致化发展被强调。极数象征变化已达极限、转折在即。叙事的卦象或五事经历曲折达到极数、抵达太极皇极,五事变化的完整链条才清晰浮现,未来发展也就可以预知。
道统叙事高度重视太极数“九”与皇极数“五”,也就是特别强调一切变化发展的价值极点或转捩点。将所“学”所“讲”的价值内容附丽其上,遂有“九”“五”之用,见诸每一个变化:“是故《易》之九而极于其九,以用乎其九者,用于文则以元,用于孔子则以仁,而仁其极于九于《易》也。……是故《范》之五而极于其五,以事乎其五者,事于武则以圣,事于孔子则亦以仁,而仁其极于五于《范》也。”[7]11叙事中用九用五,如周文王与周公的道统叙事,价值极点是发明以“元”为乾卦初始的卦爻;周武王与箕子叙事的价值极点是以“圣”为五事之归宿;孔子叙事的价值极点是阐发“仁”。“以易乎《易》之所未尽易,以范乎《范》之所未尽范。”[7]13《易》《范》开启道统源头,而其相统相传没有止境,《易》之所未尽易,《范》之所未尽范,这是开放的统绪,留待后人且学且讲、用九用五。孔子如何效法《易》并穷尽其变易之道,取法《范》并穷尽其九畴大法?那就是聚天下英才传道授业,以仁学为统而传之后世,传孔子作《易传》七种凡十篇,诠释《周易》经文大义,如经之羽翼,故称十翼。那么十翼就是孔子的尽性至命之学:“以括《范》于《易》于十其翼之尽乎其性于命之至焉者也。”[7]19所谓“于皇极建”“于皇极会”“于皇极归”[7]20,圣人且“学”且“讲”的叙事,汇入道统的尽性至命之学。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何心隐借助对道统本原和历史的虚构想象,以“学”与“讲”构成的正统叙事经验重塑道统谱系。所叙之事优先给予第一事“貌”和第二事“言”,“叙”包含先“学”后“讲”两种形态,在继承吸收经典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地叙事,以穷尽经典叙事的诸种可能。道统叙事的先验法则是“数”,凡叙事就会受到“数”的统辖,它使得叙事有序,区别于西人叙事所看重的时间整一性,而彰显出本土文化特色,“数”呼应时间的展开,顺应万物的生成,照应人事的变迁。《周易》的象数“偶”和《洪范》的范数“奇”,二者相因为用,叙事次序在“奇”“偶”交错阵列中推进,对于理解明中晚叶叙事观念有以下启发:
其一,叙事次序意义上的“偶”数是“象”之“偶”,源自《周易》阴阳卦象,以“二”为进阶表示稳定性和对立性,在对立中蕴含隐蔽的转化可能。经典文学叙事文本——长篇章回小说与此颇为契合,每回有对偶的双句回目,回目里的形象成双出现,构成回目的偶数特征,偶数象征静止和稳定,构成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每回的双句回目里关涉两个主要人物形象、构成两个事象,具有偶数的对称和对立效果,两个事象看似跳跃,内在包含“象”的偶数性关联。“象”的偶数性关联还表现为章回小说叙事整体上吉-凶、福-祸、盛-衰、兴-亡、热-冷的演变。象“偶”中有数“奇”,每回开头和结尾的诗词与正文叙事相辅相成,诗性的跳跃的象“偶”与连续的稳定的数“奇”在交错中向前发展。
其二,叙事次序意义上的“奇”数是“数”之“奇”,源自范数易学,代表变化的绝对性和渐进性,任何一个连续的变化都包含“始-中-终”三阶段,大变化中包孕无数小变化,最终构成连续不断的变化流行。从具体量化图式看,由三推衍,三三而九,九九而八十一,取成数八十,昭示变迁发生的重大转捩点,以此为分水岭,叙事急转直下。“数”奇不能简单等同于抽象的量变发展成质变,它由无数具体可感的事象与形象构成,在“数”奇与“象”偶的协同配合下实现连贯叙述。借此理解长篇章回小说的回“数”不仅用于计数,而且本身遵循连贯叙事的先验次序。《西游记》第九十九回回目“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数的完满也就是取经之旅的终点;《水浒传》第八十回、《金瓶梅》第七十九回、《三国演义》第八十回,共同指向九九之“数”的叙事临界点,昭示“象”偶的对立转化在即。
其三,“数”主宰了叙述时间、叙事节奏,使得叙述连贯有序,其中太极数“九”、皇极数“五”象征连贯叙事的价值极点或转捩点,是对“经”中之理“仁”的量化显现。叙事中有“数”,“数”包孕“史”或“事”渐变发展之理,赋予叙事堪与“经”比肩的意义,因此“数”是尊经重史、经史合一的重要中介范畴。“数”之“始”起于几微,古人讲在几微之际要谨慎从事、防微杜渐,以维系事物之间静态的和谐稳定。而叙事遵循事物由几微发展到穷而极、变而通的定数,是理解急剧变化下社会人心的动态维度,范数与象数结合的叙事次序,提供了理解人情人心变化的历史,在万物生长发展“始-中-终”的逻辑序列中考察,暗示出繁华兴盛过后是衰败速朽,热闹喧哗终归于凄凉冷寂,借助叙事通往象“偶”与数“奇”的否定之地,前述叙事皆成为对自身的否定,因此“数”中潜含了悲剧性意味。由于太极数“九”与皇极数“五”在叙事中居于价值极点,用九用五的重要转折发生前后的叙事载量分布上,在通往太极皇极的上升通道,叙事穷形尽相、充满旺盛的生机;抵达极点后,叙事密集仓促、生机活力急剧萎缩。可以推论,文学叙事就是一场人与叙事次序的游戏,凭借“数”的出场和测度,虚化了客观物理时间,调整了叙事分布的密度和节奏,成全了叙事自身的连贯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