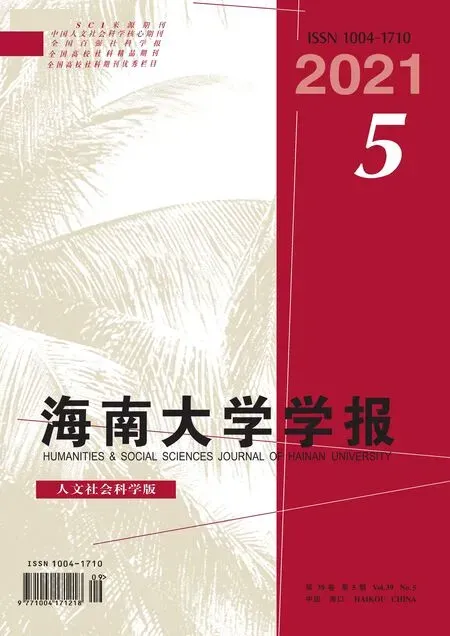文体学与年代学:柏拉图作品定序方法概述及反思
郭昊航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般柏拉图哲学研究者,常常不得不屈从于某种基于既定的作品次序而确定的既有的解释模型,因此,只好在研究开始之初,大而化之地使用柏拉图作品三分这种大尺度的时间范畴来加以描述,以至于最终结果往往是一笔带过,草草了事,而且经常把研究过程同柏拉图作品的时间线索相切割,使之不至于对研究结论产生较大影响。这固然说明柏拉图作品定序问题的确构成一个问题,然而,本着审慎的态度,我们至少要静下心来审查一下,针对柏拉图作品次序以及其思想模型之建构的既往研究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以及这些工作脱胎于一种怎样的基本思路。柏拉图作品定序方法所得结论的应用遍地开花,但大多仅仅是参考,大抵就是因为柏拉图研究所赖以维系的次序模型之确立或许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牢靠。但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仅仅是从方法论层面对文体学和年代学加以总结和反思,厘清该方法的理路,而无意于提供任何关于柏拉图作品次序的确定结论。
一、文体学与文体测量的基本方法
不论是谁,只要妄图以一种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方式进入柏拉图,或将柏拉图置于所谓“历史”之中,都不得不直面一个不可不谓繁难的挑战:为柏拉图对话设定一种先后次序①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1,p.1;纳托尔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理念论导论》,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页。。即便仅仅是对柏拉图作品集团中的一篇对话进行研究,似乎意欲合理规避这个也显得不够厚道,因为抛开于柏拉图作品集团中定位出某篇对话并以之作为一种研究的框架或背景的做法,必然会使对于该对话的阐释丧失一种基于整体进行的高屋建瓴的观照。由此观之,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心存侥幸,想要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着实不可取:设定柏拉图作品次序是基础的,因而也必然是先行的。
从荷兰著名的古典学家特斯勒夫(Holger Thesleff)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窥见此问题对整个柏拉图作品从哲学性、文学性、政治性等方面展开全方位解读的重要性:他将这一问题冠以专名,称作“柏拉图问题(Platonic Question)”。在他眼中,这一问题似乎贯通古今,伴随着柏拉图的解释史,支撑着柏拉图作品的起承转合②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Las Vegas:Parmenides publishing,2009,p.147.。
对于我们而言,因乍然碰到这一问题而感到手足无措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被一种主观解释的疑云所笼罩:似乎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对此发表一番见解。但是,柏拉图作品本身作为一种文本,无疑具有一种客观性,因而框定着解释的边界。在确定文本次序的问题上,历代解释家都在力求一种克服并超越主观性的办法。在万众瞩目的期待之中,文体测量学(Stylometry)的方法应运而生以担此重任。这种兴起于十八世纪末,进而于十九世纪初开始大行其道的方法,乃是基于长期以来古典学界对于古希腊文本文体学(Stylistics)研究逐渐发展之后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走向:在针对柏拉图作品所展开的文体学研究中,此法之始作俑者当数德语世界的里特(Constantin Ritter)和迪滕伯格(Wilhelm Dittenberger)以及英语世界的坎贝尔(Lewis Campbell)①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5-106 页;林云峰:《风格学与柏拉图》,《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6 年第2 期,第84-102 页。。
所谓文体学,简单而言,就是通过古典文本当中的语词、语法和句子结构来对某一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或在某一具体作品中的写作技巧、文风、笔法加以描述进而总结归纳出该作者用笔行文之惯常套路的一门学问。文体测量学作为一项综合的文体学方法或者说一种将文体学带入到可操作层面的工具,乃由文体学发展而来,自然也离不开这几个层面。就如迪滕伯格在开展统计研究时所选取的两个对照组就属于以语词上的变化为对象进行的测量:第一,与μήν 所搭配的小品词组合②Wilhelm Dittenberger 只统计了作为肯定回答的τί μήν(surely),而没有计算表示疑问的τί μήν(what indeed…);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第106 页;Leonard Brandwood,“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1;剩下个词组分别表示不同程度的转折,可译为yet truly 或but indeed。;第二,一个重言词组(plaeonastic combination)和两组同义词)③分别表示:相似、就像(like 或as);直到(until);也许可能(maybe perhaps)。。接续了迪滕伯格的山茨(Martin Schanz)所选取的一系列表示“实际上”“当真地”的语词也属于这种情况:第一,;第二,;第三,。与此二人不同,里特敏锐地注意到了柏拉图对话当中被提问一方脱口而出的套话,即所谓对答公式(reply formulae):这一套话语无非表示一种肯定或认同的回答,就比如,“你说得对”“无疑”“差不多”等④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第113-114 页;Richard Kraut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98-99.。由此观之,里特为统计测量所选取的对象乃是作为回答的短句,所以该方案就属于在句子结构层面所进行的文体测量。
选定测量对象无疑是文体测量中的重要环节,但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对象并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在对柏拉图作品进行文体测量之前,必定有一套公认的普遍设定作为基准和原则,而这些原则来自古代某些足以被采信的观点或者柏拉图作品内部线索中的证据。在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罗列:
(1)《法义》(Laws)写于《理想国》(Republic)之后:这一说法来自亚里士多德,因而被公认为较为可靠⑤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第104 页。。
(2)《法义》是柏拉图最后一部对话: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记载,柏拉图驾鹤西行时将《法义》留于身后,尚未修订,多亏学生奥普斯人菲利珀斯将之誊抄于蜡板之上⑥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37:此处亦有录,《厄比诺米斯》乃是出自誊抄《法义》者之手;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对此附议;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第104 页;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p.1;但是,紧随其后的一段文字(3.38)中记载,《斐德若》是柏拉图的第一部作品,因为带有年轻人的清新气息。。
(3)《泰阿泰德》(Theaetetus)先于《智术师》(Sophist)先于《治邦者》(Statesman):这一点乃是柏拉图作品中戏剧情节上可以提供的内证⑦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第1 页;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p.8.——苏格拉底在忒奥多洛斯(Theodorus)的引荐下结识了泰阿泰德,在进行了关于“知识是什么”的对话后,约定第二天再见;《智术师》即是第二天的对话结果,对话中抓住了“智术师”;而“治邦者是什么”的问题则留给了《治邦者》去解决。
(4)《蒂迈欧》(Timaeus)与《克里提阿》(Critias)前后相继:两篇对话拥有相同人物设置,甚至可以共用同一开场,克里提阿则在两篇对话中用两段讲辞描绘了一整个关于大西岛的故事⑧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第104 页。。
(5)《泰阿泰德》与《智术师》分别暗示接续《巴门尼德》(Parmenides):前两篇对话中,巴门尼德的大名屡屡被提及,并且被冠以智者的雅号,甚至对话中交谈正欢的苏格拉底干脆直接透露,在自己年纪尚小之时就见过巴门尼德——而这似乎是柏拉图对话中所设定的戏剧背景下才独有的情节,真实史实或许与此相距甚远,此二人极有可能压根没有碰面①关于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会面以及二人对话内容的真实性,参见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p.7.;《蒂迈欧》暗示接续《理想国》:对话的开场,无时无刻不在提及“昨天晚上”那场关于理想城邦中阶层划分和政治制度的谈话。
从这里表述的几点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法义》作为柏拉图最后一部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广泛认可的。由此,《法义》似乎能够为文体测量学提供一个参考的基准和尺度,同时也是梳理柏拉图对话的原点,因为《法义》当中遣词造句的文体特征可以作为标准来测定其他作品同它之间的亲疏远近②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p.1.。相对而言,作品之间的内证则可以作为另一层面的参考系,为柏拉图作品定序提供辅助。拥有这些参考基准之后,再同先前选定的测量统计对象相结合就可以完成文体测量学的重要一环——测量的模型已经搭建完毕。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凭借耐心的工作来统计测量对象在柏拉图诸对话中出现的次数。在此,我们仍旧以迪滕伯格的研究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取各组大鼠右侧踝关节组织适量,经4%多聚甲醛溶液中固定2 d、EDTA脱钙液中脱钙10 d后,用大量水清洗,经乙醇(体积分数分别为80%、95%、100%)梯度脱水、石蜡包埋、切片(厚度5 μm)后,行HE染色,以中性树胶封片,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大鼠踝关节组织病变情况。
IIa:《会饮》《吕西斯》《斐德若》《理想国》《泰阿泰德》
IIb:《巴门尼德》《斐勒布》《智术师》《治邦者》《法义》
由于IIa 里对话含有较少《法义》中由这组语词频次规律所描画的文体特征,而IIb 则与《法义》更为接近;又根据上述原则(1)和(2);迪滕伯格确定,IIa 组早于IIb 组。而剩下来的对话中根本没有出现这两个语词,因而更加偏离《法义》所呈现的文体特征,所以被归为一个更早的时期:
I:《克力同》《游叙弗伦》《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拉克斯》《小希皮阿斯》《欧绪德谟》《美诺》《高尔吉亚》《克拉底鲁》《斐多》
似乎有心人已经发现,《申辩》《蒂迈欧》和《克里提阿》这三篇著名对话并没有被纳入考察范围③Leonard Brandwood,“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p.11.。但是,于接下来一组统计测量中,这三篇对话被成功纳入由这三组语词所刻画的文体特征的考察范围内。相应地,这三篇对话也各得其所:《申辩》于I 起首处;据原则(4)作为前后相继的对话组的《蒂迈欧》与《克里提阿》被置于IIb,紧随《治邦者》之后,位于《法义》之前。
由迪滕伯格的文体测量案例④Leonard Brandwood,“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pp.11-20.可以看出,当我们选择的测量对象不同,对于柏拉图对话的文体特征就有不同的刻画,进而可能有不尽相同的排序结果出现。从单纯试验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若要力求真实地呈现出某种试验结果,有两条路径:第一,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第二,增大样本的基数。具体到针对柏拉图作品的测定问题,这两条路径可被表述为:第一,选择更能刻画柏拉图文体变化的语词与语句;第二,扩大统计测量参考组的规模。其实,接下来的研究者也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路径前行。就如上文言及的山茨,他不但选择了在他看来更好的指标,而且对文本有着更为细致的划分。他将《理想国》分为三个独立对话,同其他对话一起加以考察。另有陆托劳斯基(Wincenty Lutoslawski)遵循第二条路径,极大地扩大了考察规模。将考察对象从里特40 种的规模扩大到了500 多种⑤克劳特编:《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王大庆译,第110-111,116-117 页;Wincenty Lutoslawski,“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Plato’s Logic”,London:Longmans,1897.。然而,据此趋势可以想见,这种操作似乎已经在技术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尤其当计算机在文体测量学上被加以应用之后。
二、文体测量方法的扩大及其批判
但是,莱杰的这种过于技术化的文体测量方法,难免遭受非议。杨(Charles Young)在面对莱杰的测量成果时就丝毫没有手软,以至于自己似乎情绪激动,口不择言③Charles Young,“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vol.XII,1994.。不过,我们尚且能够较为清晰地将杨的挞伐之辞加以梳理。
首先,他所攻讦的不乏技术细节层面的问题④Charles Young,“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pp.248-249.。莱杰在选择字母以及制定变量时有不少错误,最具代表性的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没有单独统计带有“iota subscript”的;第二,统计-ων 结尾时将并不代表复数属格的克力同的名字计入其中,第三,针对大量出现的并没有在语义上加以区分:分别统计表示析取的(可被译为or)和表示比较的(可被译为than)。其中,第二和第三可以归结为在选取样本时对于语词本身的语义不加区分,而第一则根本属于统计指标选取错误。杨直言,这种小错误累加起来无疑会使人担忧莱杰的测量方案本身的可信度。但其实,这背后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从技术层面出发选取的样本本就不具有说服力,换言之,精细化到这个尺度的采样标准似乎已经不能被用以描述文体这样一种大尺度层面的东西了。
其次,杨指出⑤Charles Young,“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p.243.,莱杰的测量结果可以佐证,通过他选取的样本而搭建起来的具有描述性的数据模型,即便可能同柏拉图作品在文体上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他却颠倒了具有相关性的两种因素之间的因果性。正如不能通过轮胎磨损的不同,来推断驾驶方式的不同,而完全不考虑诸如路况等其他影响轮胎磨损程度的因素,我们也不能仅以数据模型所反映的变化和差异,来充分地推导出某种文体风格变化的差异。也就是说,即便莱杰测量的数据能够刻画出某种柏拉图文风上的变化,也不代表这种变化就是客观地真实存在于柏拉图作品当中的变化。
再次,莱杰的模型搭建需要借助某些线性的假设⑥Charles Young,“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pp.245-246.。必须以线性假设作为前提的这种局限性首先来自这种方法本身,因为这种模型只能刻画和描述一种线性的变化。另外,模型的构建也需要某种线性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某些被认可在先的对话中出现某种特征较少,而被认可在后的对话出现该特征较多,那么,依据该特征而构建的模型就必须是:在柏拉图作品中,含有该特征越多的对话在时间序列上越靠后,含有该特征越少的对话在时间序列上越靠前——构建模型必须依赖这种线性描述。所以,莱杰模型要想绝对有效,必须要求这种线性变化是客观的。这就意味着,不但用以进行描述的模型本身是基于线性的,而且作为描述对象的柏拉图文体之变化也是一种严格的线性变化——这种要求显然有些出格。
最后,杨的批判落脚在莱杰对某些命题主观上先入的“相信”⑦Charles Young,“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p.247,250.(尽管莱杰用的是“知道(known)”一词⑧Gerard Ledger,“Re-counting Plato:A Computer Analysis of Plato’s style”,pp.210-211.)。比如,莱杰似乎最终也没有跳出布兰德伍德(Leonard Brandwood)在汇集了先前各种关于柏拉图作品分期以及排序的所有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而在我看来,这一点更体现于莱杰构建模型进而为柏拉图作品定序时必须采信的某些被普遍认可的前提。即便莱杰通过如此技术化的手段企图追求一种客观性,他也还是不得不像上文谈到的前辈学者一样,以某些主观上的先入之见作为大前提。
至此,我们其实已经不难看出,杨的批判或许并不仅仅是针对用计算机玩出新花样的莱杰,而是针对文体测量学-文体学方法本身。而杨在文章副标题中将英语世界文体测量学的集大成者布兰德伍德并置于莱杰之后的举动,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坐实我们的推断。而结合我们先前对于文体测量学本身的介绍以及对杨的批判的梳理,文体测量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于众目下。我们不妨归结为:第一,统计数据(i)同文体特征(ii)的脱离;第二,文体特征(ii)同柏拉图作品分期定序(iii)的脱离。简言之,这两重断裂就是,统计得到的数据模型不能理所当然地刻画文体特征,而另一方面,文体特征上的变化和差异不能理所当然地对应于柏拉图作品在时间上的次序先后。接下来我们不妨审视一下这两种断裂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必须要强调,在通过文体测量的手段为柏拉图作品定序的工作中,这构成断裂的三个环节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只有通过某种手段将这三个环节依次串联起来,才能达成最终目的。完成从(i)到(ii)的演进时,我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建立数理模型,意图用某种数据上的差异或变化来刻画出文体之间的差异和不同风格之间的变化。而在完成(ii)到(iii)的演进时,我们则必须借助某些所谓普遍认可的观点,将顺位“已知”的柏拉图对话的文体特征作为基准“代入”到先前的模型当中,进而按照同基准作品的亲疏远近依次排列其他对话。然而,如果我们现在将本节开篇时谈到的文体测量学的初衷拎出来重新审视一番就会发现,在文体测量学的两步演进中,浓重的主观意味已经同采用文体测量学的办法来追求所谓客观性的出发点彻底背离——这两种断裂似乎也“理所当然”。在统计数据(i)同文体特征(ii)的脱离中,为建立模型而选择样本的特征指标本身就是主观选定的;而构建出的模型本身还要符合主体的认知习惯,亦即呈现一种线性的回归;同时通过这个模型所刻画的文体特征也仅仅只是片面的,仅仅是“某人眼中的”柏拉图的文体特征。至于文体特征(ii)同柏拉图作品分期定序(iii)的脱离就更无须多言,被用以作为基准的只是主观上的确信。所以每当我们力图用主观建构的办法进行一步跨越之时,就会在茫然无知近乎执迷不悟的情况下跌落进深渊之中。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借用品达之诗句“下至大地,上达天穹”所描绘的理想哲人俯测地理仰观天文的形象想要追求的正是一种超脱的绝对客观的视角(173e)——如上文所言,文体测量学力图将文体学拼命拖入数理世界当中去追求的应当是同一种东西。但是,主体的桎梏始终是人难以逃脱的囚笼。理想哲人终归是一种理想,同时,文体测量学在实践其理想上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客观性的追求完全沦为一种关乎主观解释的问题。然而,人类理性的本性难移,总在欲求更多。杨在文章中表露了对这种数理技术手段丧失信心的同时,却对柏拉图作品中文体特征上的差异和变化表现出积极的态度①Charles Young,“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p.243.。或许,有一种较文体测量学尺度更为宏大的方法,能够承继文体测量学的问题,并尝试给出解答。
三、对文体测量方法的修正
响应理性召唤的是提出所谓“柏拉图问题”的古典学家特斯勒夫。文体测量学受制于某些主观因素而其结果同进行研究者的个人意见纠缠胶结在一起的事实也是特斯勒夫颇有微词的主要理由②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7-8,p.24.在他看来,文体测量学的样本选择都是随机的,所以缺乏一种作为标准的原则。。他并不否认文体测量学对于文体学的积极意义,但是,特斯勒夫在行文的字里行间还是力主一种直接从文体学本身入手的方法。然而,在此必须强调,他的方法不同于传统文体学所采用的对语句或语词等文体特征割裂地加以描述的方法而更强调各个文体特征之间的联结、贯通与渗透,并基于此综合地搭建起不同的式样(pattern),进而通过式样对目标文本加以描述③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21.——姑且不论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法还是一劳永逸地规避了第一重断裂——即数理模型同文体特征之间的断裂。所以,接下来我们似乎有必要审视一下综合的文体学方法。
特斯勒夫方法背后的理论支撑大体如以下所示④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22-26.。他首先区分了通用的文风和个体的文风。其中,通用文风对应一种标准的文体类型。所谓标准之为标准,则是由时代所决定的。某一时代的流行文体因其普泛而广为当时文人骚客眷顾,反过来,那些彼时普泛文体形成的流行风潮又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身处那个时代的作家的创作,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标准文体①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22.。而与通用文风相对的个体文风,在特斯勒夫看来,则对应一种针对个别文段的文体结构谋划或润色。某篇具体文章的形式、语词、表述方式或表述类型②这些因素被称作语言单元(linguistic unit);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22.,均会由于受到各种各样通用文体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多多少少呈现出一种经润色后的文体色度(shade of style)。所以特斯勒夫认为,个体文体是标准文体式样的复制和再生。通常而言,所谓润色都不会只仅仅使用一种色度。在润色一段文字的过程中,有可能先后出现不同的色度,也有可能部分有色度而部分无色度;而当一整段文字均是同一种色度时,润色就等同于添加色度。但是,为了描述这种色度,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引入文体标记(style marker)的概念来表示各种典型的通用文体式样,并以此断定某一文段中的文体色度。每种通用文体都应有与之相应的文体标记③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23-24.。
正是基于这套理论,特斯勒夫通过自身古典语文学的积累针对柏拉图作品总结归纳了十种通用文体以及相应的文体标记④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51-64;林云峰:《风格学与柏拉图》,第92 页。。它们分别是:口语体、半文学对话体、修辞体、煽情体、学术科研体、神话叙事体、历史体、仪式体、律法条文体、增大体量⑤这种文体被称作“onkos(γκος)style”;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63-64.。十种文体式样都有各自的文体标记。比如,口语体的标记就有:句子断续错乱⑥一种在口语中才出现的完全不合乎语法的典型情况。、滑稽效果、相类似之物的比喻、使用昵称等等。只要某段文字含有某一文体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标记,我们就有理由判定该段文字具有某一文体特征。通过对柏拉图全部作品的考察,以及和同时期其他作品的对比,特斯勒夫从单纯文体层面出发,从足够宏观的角度,为柏拉图的作品划分了几种不同类型:模仿类型、申辩类型、教学指导类型、报告记录类型、批判类型以及晚期类型⑦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16-20.。
但是,一直致力于解决柏拉图问题的特斯勒夫绝不愿止于仅归结出这几种柏拉图作品的类型,他终究还是想把柏拉图对话置于一个时间轴之内。所以,他也不得不使用一些普遍公认的观点,甚至直言舶来了文体测量学的某些成果——尽管他一再称文体测量学不大可靠⑧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16.。当然,对于特斯勒夫的非议不止于此:他这种直接从文体特征层面进行的研究被指责过于粗放,无法应对精细化的研究⑨林云峰:《风格学与柏拉图》,第93 页。。的确,相比于文体测量学选取的考察对象,特斯勒夫的十个文体类型式样着实显得有些粗枝大叶。但不要忘了,特斯勒夫其实在大的式样内部还设置了无数小的标记。恰恰由于这一点,特斯勒夫的方法当中并没有完全排除在小尺度的层面进行精细操作的可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这些标记完全可以被灵活机动地应用于任何一段柏拉图文本⑩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21.,因而可能比文体测量学总结出来的某些特征指标更具有普遍性。但是,特斯勒夫在凸显了这种方法于大小尺度之间切换自如的弹性之后,仍旧选择从这种较大尺度的层面进入柏拉图文本,正是他在对比了文体测量学这种路径之后做出的决定。而他如此抉择,认为自己的方法优于作为文体学传统方法的文体测量学,个中缘由想来定与其研究目的紧密相关。所以,至少在特斯勒夫自己看来,这种方法既能满足确定具体文本先后次序的要求,又能在宏观的角度上将柏拉图一生的历程同这些文本串联起来。可见,特斯勒夫没有丝毫偏离那个足以作为其研究核心的“柏拉图问题”:不仅使柏拉图作品的先后次序得到确定,而且还要使这些作品在时间的长河中找到独属自身的片段。如此一来,这便已然超出了文体学的范畴,转而进入年代学(Chronology)的考察视域。
四、文体学与时间线索结合后的年代学
无论是文体测量学方法还是特斯勒夫全新的文体学方法都是仍然隶属于文体学这个大类。而针对柏拉图的文体学考察的更多贡献在于,确立不同的柏拉图作品之间(甚至同一作品不同卷目之间)的亲疏远近。当然,我们还是于其中看到了某种与时间(chronos,χρόνος)相关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仅仅是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也就是一种相对的“早”或“晚”。这种相对的时间尺度构成年代学所需,因为年代学考察所要求的是将相应的作品置入历史的时间坐标轴之中,从而使作品得到一种时间上的定位。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是彼此相关,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年代学就是文体学的延续,文体学的研究最终必然指向年代学的考察,而年代学又有必要充分借鉴文体学的成果和结论。从实践操作的具体层面讲,我们不妨简单地将年代学理解为把某些确定的时间节点代入到文体学基于作品亲疏远近而得出的先后次序的排列中去①施莱尔马赫:《论柏拉图对话》,黄瑞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年版,第80 页。。在此,仅举几例以作示范:
(1)《申辩》不可能早于公元前399 年的苏格拉底审判②围绕着公元前399 年这一时间点的是柏拉图文本考订上的最大争议:柏拉图在此之前究竟有没有写过对话。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p.150;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171;W.K.C.Guthrie,“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ol.IV:Plato,The Man and His Dialogues:Earlier Peri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p.54-56.;
(2)《会饮》193a 讲到“阿尔卡德人被斯巴达人分开”一事大约在公元前385 年③这个事件可能是斯巴达人把阿尔卡德的曼提尼亚城成分成四个村庄,色诺芬《希腊史》有载,发生于前公元前385 年或公元前384年,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p.5;Charles Kahn,“Plato and Socratic Dialogu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2;但刘小枫所编《会饮》集注(朱光潜注)中称,此事件亦有可能指公元前417 年斯巴达人解散阿尔卡德人联盟,参见刘小枫编:《柏拉图的〈会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年版,第53 页。;
(3)《泰阿泰德》开篇142a,讲到泰阿泰德身负重伤被送往雅典城即将死去,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69 年④此事也有不同说法,詹文杰译:《泰阿泰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2 页;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173.;
(4)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 年左右,亡于公元前347 年,偏差不超过一年;
(5)柏拉图三次出访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时间分别应是公元前389 年或公元前388 年、公元前367 年或公元前366 年、公元前361 年或公元前360 年⑤David Ross,“Plato’s Theory of Ideas”,pp.9-10;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167-185.。
从上面这几个例子不难看出,这些时间点有些是柏拉图作品内部涉及的历史事件,有些是对柏拉图个人生平的考察。这两者在年代学中应当相互嵌套互为佐证。所以,柏拉图作品的年代学和对柏拉图个人生平的历史学研究近乎可以等同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对柏拉图作品相当熟悉,还要对这个时间范围内整个古希腊历史进行深入的考察。特斯勒夫就有这样一段堪称典范的关于柏拉图年代学成果的概述⑥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16-20.。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年代学本身的反思。在他看来,基于文体学的年代学有其自身根本无法把控的问题。首先,柏拉图自己很可能反复修改并梳理过自己的作品,而且常常会出现信手拈来一篇之前的草稿直接进行再创作的现象⑦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14;Charles Young,“Plato and Computer Dating”,p.227: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言之凿凿,柏拉图持续不断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量“梳理和加工”直到暮年。关于以草稿再创作,参见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14.。就比如《泰阿泰德》在古时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开场同时流传于世⑧关于《泰阿泰德》的两个开场,参见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14-1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好证明了柏拉图的确有可能亲自操刀进行了一些修改的工作。同时,旧瓶新酒的再创作现象也说明,柏拉图的某些作品不见得是一蹴而就的,创作的时间极有可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跨度,而在此之间,柏拉图可能同时创作了其他作品:就比如《理想国》⑨Leonard Brandwood,“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p.18.。另外,我们也不能排除学园内部某些署名柏拉图的修改和套作。这种学派内部人员反复进行修改并最终仍冠以学派掌门之名的现象在柏拉图的时代实属稀松平常,而且根本不会被视为学术不端⑩Holger Thesleff,“Platonic Patterns”,pp.11-12.。所以,柏拉图的作品可能不止经历了他自己的修改,而且还有弟子们的修改。单就这几点而言,基于文体学的年代学就已经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了。就如卡恩(Charles Kahn)略带一丝反讽的评论,这种为断定作品时间顺序而进行的年代学考察所需要的是文学鉴赏力、历史想象力以及个人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心理暗示⑪Charles Kahn,“Plato and Socratic Dialogue”,p.47.。所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大方面上进行的估计,而一旦触及过于精细的层面便会缺乏可信度。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年代学最基本的判断,卡恩认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学者都可以排列出一组令人信服的柏拉图作品的年代学顺序。因此,他力图从可谓柏拉图断代之传统方法的文体学的框架中跳脱出来,选择另一条进路描绘柏拉图的发展:以空间来置换时间。只考察文本之间互相引证的关系来区分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而划分出由两三个相关对话组成的小组,同时以《理想国》为核心,将各个小组区分为“《理想国》之前”“《理想国》之后”和“与《理想国》接近”三个大组。在卡恩看来,柏拉图所有作品所谈论的内容都指向了《理想国》,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一个大的主题。而卡恩理论里所谓的“空间”即是与《理想国》这一对话的关系,由同核心接近与否区分内外——由此,卡恩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年代学中“时间”的束缚①Charles Kahn,“Plato and Socratic Dialogue”,pp.46-48.。
我们姑且不论卡恩的这种方法是否可取,他在反思传统方法的过程中给出的几个建议倒是都可谓相当中肯。卡恩再三提请我们注意,文体学三个阶段的划分,首先不能和柏拉图作品内容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在关系相混淆②Charles Kahn,“Plato and Socratic Dialogue”,pp.44-45;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北京: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36 页。,其次更不能和柏拉图真实的写作顺序相混淆③Charles Kahn,“Plato and Socratic Dialogue”,p.47.解释学的进路就是,不与文体特征上的柏拉图作品三分相混淆。。尽管不论如何审视,卡恩的说辞都像是在为自己的方法张目,但是,柏拉图作品基于文体学的某种顺序,的的确确不必是作品的时间顺序,更不必是柏拉图思想的演进顺序——卡恩的攻讦对于年代学来说无疑是一击致命——对于我们而言,这也许就是年代学乃至文体学在柏拉图研究上的命门所在。
五、对柏拉图作品定序方法的反思
对于柏拉图哲学的研究者而言,柏拉图的思想究竟如何,只有通过文本本身才可通达。当一切都归于直面文本继而让意义在理解与阐释中敞开并释放的解释学问题时,文体学研究似乎就可以焕发新的生机。这些研究可以更好地帮我们勘定柏拉图究竟在以怎样的形式诉说以及他笔下人物言说的语气:例如,究竟是在戏谑地讲一个神话还是在严肃地进行论述④施莱尔马赫:《论柏拉图对话》,第90-91 页。——以特斯勒夫为代表的综合的文体学研究不单单是语文学皓首穷经式的考察,而且直指柏拉图思想中迸发的跳跃着的生命冲力——这固然是文体学与年代学研究在确立柏拉图作品次序模型时所能提供的积极帮助。因为横亘在模型与柏拉图作品之间的巨大鸿沟,或许唯有通过文本解释才可天堑变通途,而聚焦于文本本身变化可对柏拉图文本细节加以描述的文体学研究,自然可以增进我们对于柏拉图作品文本的理解与把握,对通过作品反映出的思想之解释有所助益。这与文体学研究最基本的定义完全相符,换言之,文体学研究诞生之初的原初任务也就在于对文本研究加以辅助。但是,要知道文体学与年代学的积极意义或许仅止于此:任何越界使用都难以幸免于针对文体学和年代学运用中过于数理化之操作的固有指摘。
再来总结一下文体学与年代学方法的基本思路。在得到了技术化了的文体测量学的加持并在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流后,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如下:第一,通过某些“已知”的柏拉图作品次序节点,确定柏拉图文风的大致变化趋势;第二,通过某种或某几种文体特征(语法、语词甚至字母),利用统计学方法,来建立能够描述这种变化趋势的模型;第三,用此模型衡量“已知”次序以外的柏拉图剩余作品,将其嵌入该模型中一个合适的位置,使柏拉图全部作品回归于一个呈现特定趋势的线性变化之中,最终实现为作品定序的目标。
在此基础之上,年代学也拥有了自己一展拳脚的空间:将文体测量研究得到的结论,即柏拉图作品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通过某些“已知的”历史节点置于历史的时间范畴之中。可见,前者得到的结果是柏拉图作品之间相对的时间关系,后者则意在将此延展至历史的绝对的时间当中,将历史的背景同柏拉图作品产生联系。
在这种看似合理的研究方法背后,其实先前所谓越界使用已经悄然发生,而且在三个层面上上演。第一,文体学研究之本意在于对文本的理解加以辅助,这也是直面特斯勒夫所谓“柏拉图问题”的学者提出文体学进路时所抱持的态度,而文体测量学则摒弃了辅助理解的地位,利用统计学模型刻画的作品次序反倒在对文本的理解中占据优先地位,造成了模型取代文本占领了柏拉图解释之高地的事实。第二,文体测量学素来标榜,要以所谓文体特征的客观性克服解释当中的主观性,却在实际操作中再次落入主观性的陷阱。
针对第二点,我们需要不惜笔墨地加以分析。首先,不论是文体学还是基于其上的年代学,在其实际针对柏拉图作品定序断代的实际操作中,均起始于确定一些节点作为建立参考系的基准点,而这些所谓“已知的”事实,也不外乎来自某些学者的记录或者某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诚然,我们必须承认,学者的记录和流行的观点自有其学术价值,但若就此盖然地认为对其可以排除主观性因素直接加以使用进而得出全然客观性的结论,则多少显得缺乏审慎。所以,追求客观性的文体学和年代学之底层逻辑在起始之处就无法排除主观性的影响。另外,在建立文体测量模型的过程中,针对描述文体变化的参照物,即某些特定的语词和字母,其选择标准来自建立模型者的主观意愿;对统计过程中所涉及的样本数量,也来自其主观抉择,亦无法做到穷尽。所以,最终建立的文体测量模型以及由模型所确立的柏拉图作品次序从根本上讲无法排除模型建立者的主观因素,无法尽然做到完全客观性。
眼下,即便仅仅根据这些天然缺陷,我们就已然可质疑文体学和年代学在运用过程中的基本逻辑的可靠性,然而,质疑之声绝不应止步于此,如前文揭示,文体学研究领域之内就已有认为文体测量之法失之偏颇值得商榷的反对意见,而且这种驳斥意见甚至更为致命——这就涉及此法越界使用的第三个层面:即便根据选定参照物建立参照系以及填充样本后所架构的模型有足够的描述力,足以反映柏拉图某些遣词造句之间风格扭转而产生的文体特征变化,但模型的有效性并不能够支撑其将描述力从文体特征变化顺理成章地扩展至整篇对话,更无法扩展至柏拉图作品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文本与妄图以柏拉图文本之名建构的模型之间的断裂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甚至这种断裂还延展到了所谓柏拉图思想的解释模型之上。
因此,即使是积极继承文体学与年代学成果后提出的柏拉图作品次序的模型,仍绕不开文体学和年代学研究,因为都是基于该研究而提出的柏拉图作品次序之模型。所以模型与文本的断裂仍旧存在,只不过在这里,裂隙显现于柏拉图思想与柏拉图的文本之间。而反观,文体学与年代学的断裂则在于被切片采样后的肢解了的僵死词句与富有鲜活生命力的对话文本整体之间。两处断裂之间,唯一一处共同的坚实的大地,那就是柏拉图对话本身。每部作品甚至其中的片段或许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或线索联结起来,以便提供一种尝试进入柏拉图文本及其思想的方式。就如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所言①伯纳德特:《美之在》,柯常咏,李安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 页。,面对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式的反讽言辞构筑的迷宫时,每一条单独的线索一旦被意识并加以信赖随即便会灰飞烟灭,只有当线索连接起来后,我们行走在柏拉图作品之间时,才不再有失衡跌倒之虞。
所以,在此对柏拉图作品定序工作中扮演举足轻重地位的文体学和年代学研究加以总结分析之要义时,并非只为揭示其基本思路当中所存在的矛盾以及其中包含的不牢靠的成分,进而消极地武断拒斥。要知道,毕竟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是目前我们对于古典文本断代考订最为可行的办法。但是,我们还是要时刻警惕,此方法所得之结论并非无懈可击。所有关于柏拉图作品的研究,在面对柏拉图问题之时,都要重回柏拉图文本本身,更应该以是否能够呈现柏拉图活的思想为其解释是否站得住脚的评判标准,而不再纠缠于死的文字。直白地讲,柏拉图哲学的解释者本人,或许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学术责任,减少某些对于文体考察的依赖,通过自己在理论上的解释力使柏拉图作品之间内在的关系和次序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