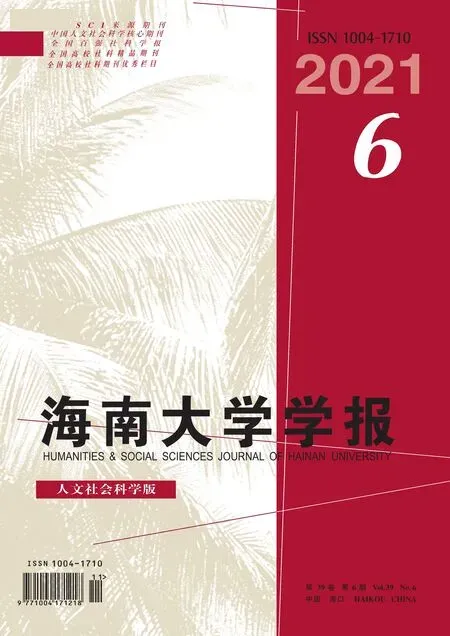《诗序》的诠释功能与《诗经》的经典化
郭亚雄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在《诗经》研究史上,有关《诗序》诠释功能的论断显现出两种倾向:汉唐学者将《诗序》标举为通达诗旨的津梁;而自宋学首倡“废序”,直至近现代的疑古思潮,《诗序》多被学者指斥为诗义阐发的最大阻碍。然而,无论主张“尊序”还是“废序”,论者均聚焦于《诗序》对诗义的诠解是否合理,其所设定的诗篇背景是否真实等问题,却较少注意到《诗序》在诗篇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据序言诗”代表了《诗经》被编纂、写定,亦即,被“文本化”之后的诠释径路,而“三百篇”由“诗”升格为“经”的关键则在于解说方式从“口传”到“书写”的转换。就此而言,对《诗序》诠释功能的考察应将其置放在经典形成的语境中,比较“书写”与“口传”阐释模式的差异之后方能凸显①按:三家《诗》是否有序,编纂形态如何,诸家各有异说。朱彝尊、王先谦与洪湛侯等认为三家《诗》皆有序,程元敏则认为“以序论诗”是毛诗派的独创。本文认为,即使三家皆有序,其说诗亦并不遵从“据序言诗”的规程。从《诗经》诠释史上看,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缺乏体系化的诠释规则,故其虽早立学官,但在《诗经》经典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用似不及《毛诗》。如《史记·儒林传》载:申培公“疑者则阙不传”,此种解说方法致使经文意蕴存在缺失,不利于文本词句与意义的完整与稳定;齐《诗》以阴阳五行之说附会诗义;韩《诗》采杂说以释经,二者之解说皆游离于诗篇本文之外,其效果诚如王世贞所云:“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故多浮泛不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85册,第67页)与之相比,毛《诗》则以解说本事、训诂词句、标明修辞等方式“就诗论诗”,更通过谨守“据序言诗”,掌控诗义阐发的空间,从而将多义的“诗”收束为单义的“经”,真正完成了诗的经典化。。
一、《诗序》与《诗经》关系的反转
从字源上说,“序”字本义为“墙”,用来指涉区隔“内外”“亲疏”所形成的标记。此种内涵恰可隐喻序次篇目的编纂行为,故卢文弨、余嘉锡与王凤阳等以《序卦传》《诗序》为据,将“序”的原始功能界定为对文本编次情况的说明②卢文弨《钟山札记》,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9册,第685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页;王凤阳《古辞辨》,沈阳:辽宁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嗣后,“序”逐渐转变为依傍正文而生,以“叙作者之意”为主的文体专名③刘知几:《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但从《诗经》诠释史上看,《,《诗序》却通过对编纂义例的阐述以及“序先诗后”的文本形制彻底颠倒了其与正文的主从关系,成为《诗经》文本的实际开端与论者阐释诗篇的逻辑起点。
圣人借伦次诗篇以寓微言大义是古代学者的共通信念。司马迁祖述今文《鲁诗》说,认为诗篇经由孔子删削、编次方呈现出“四始”之微旨,“礼乐自此可得而述”④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45页。。欧阳修认为:“《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①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4页。学者们崇信诗篇序列遵循某种规范,但面对“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的窘境②孔颖达等:《毛诗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3页。,根据《诗序》的解说,探寻圣人编诗义例便成为唯一选择。例如,王安石便依傍《诗序》,以“妇德”为线索,彰显《周南》诸篇排布的谨严③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四部丛刊》本,第1页。。在疏解《周南·麟之趾》之序文“《麟之趾》,《关雎》之应”时,孔颖达展示了《诗序》通过叙述编次缘由以“垂法示教”:
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时,不为有《关雎》而应之。大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岂一人作诗,而得相顾以为终始也?又使天下无犯非礼,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难化于天下,岂其然乎!明是编之以为示法耳④孔颖达等:《毛诗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83页。。
孔颖达将《麟之趾》的诗义区分出两个层次:一是诗文的“本意”(“美公子信厚”);二是个体诗篇在组诗整体中呈现的“编次之义”(“《关雎》之应”)。前者仅与诗篇自身有关,而后者则必须比照其他诗篇的位次方能获取。《关雎》与《麟之趾》构成一组对立项,《,《关雎》居《周南》之首,故昭示“文王之化”的滥觞,《,《麟之趾》居末,故为“文王之化”的响应。即使《周南》组诗之外的诗篇同样具备“美公族”之意(如《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但由于对立项的缺失,其也绝不会生成类似“《关雎》之应”这样的“编次之义”。
较之于诗篇本义而言,《,《诗经》的“编次之义”因由圣人“序”(编次)诗时添缀,故更为学者所重。刘始兴基于“一篇之义小,而孔子编次之义大”的认知而展开的“小”“大”之辨便是上述观念的明晰表述:
或问诗一篇之义小,而全诗之义大,何也?曰:《诗》有诗人之志焉,有孔子编次之义焉。二者不同,而其义之大小亦有辨。夫一篇之诗之为义也,系乎其人与事而已,义系乎人者,言其人之美恶而其义止焉;义系乎事者,言其事之美恶,而其义亦止焉。繇其义之所起,而观其义之所止,所谓诗人之志也,故曰小也。……然则孔子之意亦系诗人之辞而见耳,果何以独著其大乎?曰:孔子之编《诗》也,凡列于风者,皆足以验国攻[政]之盛衰;凡列于雅者,皆足以考王道之得失;凡列于颂者,皆足以见古先王创制垂统之精义⑤刘始兴:《诗益》,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册,第166页。。
刘始兴认为,“诗人之志”或关乎事、或系于人,其指涉相对单一,意蕴较为狭隘。孔子编《诗》则借助更定次序(“如时代在后,或列于前;及在下民俗之诗,或先国君之类”)、同类缀合(“或以其义,如《小雅》雅歌诗相次,或以其事,如颂诗相次之类”)、“引譬连类”(“如二南附《何彼秾矣》、衰周之诗之类”)与“比而讽切”(“如《柏舟》、《墙茨》反王之诗之类”)等编纂手法,在“诗本义”外添加了“编次义”,为读者考察“国政盛衰”“王道得失”与“先王创制垂统”等精微“大义”提供了可能。
《诗序》不仅藉由对编纂义例的阐发而成为圣人志意的真正负载者,还通过独特的文本形制昭示出其不同于普通传说的特殊地位。按照西汉经学“经传别行”以及“序”在文本之末的编纂定例⑥孔颖达等:《毛诗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9页。,《,《诗序》本应单独成卷,或置于《诗经》正文的末尾。然而,早在西汉毛公传《诗》之时,“序先诗后”的文本样态便已固化,且成为后世刊刻《毛诗》之定势。即使在敦煌《毛诗》写卷(斯3330、6346、6196号)与《开成石经》(837年)等“白文本”经书中,《,《诗序》仍被单独抽出,缀于各篇诗题之下。这就表明,《,《诗序》已然可以与传、笺分离,成为《诗经》正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郑玄笺释《南陔》等“逸诗”之序时曾谓:“(《南陔》等)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⑦孔颖达等:《毛诗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8页。陆德明襄助郑说云:“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诗亡。”⑧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社1984年版,第294页。郑玄、陆德明既将《诗序》作者系之于子夏,以证《诗序》为孔门嫡传,又把“序先诗后”的体例溯源至西汉景帝《毛诗》初传时期,以言其渊源有自。根据以上诸说,《,《诗序》早于《故训传》业已先行流布,而毛公引《序》附经,仅是将《诗序》与诗文的联系在文本视觉上进一步明晰。此种“序先诗后”的文本形制虽有违西汉经学成规,但却曲折地透露出《诗序》在汉代经学语境中的文本性质。设若《诗序》为经师传说,固不当杂厕于经;但若《诗序》本即《诗经》不可或缺的部分,并非经师所传,则“经传别行”的成例便无法规限毛公“引《序》附经”的编纂行为。
“序先诗后”也确立了《诗序》在诠释诗篇时的优先地位。从阅读次序上说,诠释者在未览诗篇正文之前便已先行释读《诗序》,而《诗序》对诗篇创作背景的补充更成为学者追索圣人之旨时不可或缺的索引。以《郑风·将仲子》为例,《,《诗序》认为该诗系反映“祭仲谏而公弗听”之事,故毛传、郑笺均将诗中“仲子”确认为祭仲,并牵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相关记述,认为“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是“无干我亲戚,无伤害我兄弟”的隐喻。再如传、笺对《齐风·南山》“葛屦”“冠緌”数量与属性所做的分析,对《邶风·静女》中“女史彤管之法”的申说,均意在回应《诗序》对诗篇历史背景的设定,以至于完全排斥了将“葛屦”等释为妆奁、信物的可能。当诗篇意涵与《诗序》产生冲突时,诠释者往往“舍经就序”,以回护《诗序》的释读。如孔颖达为证成《诗序》对《郑风·有女同车》“刺忽之不昏于齐”的解说,将诗中“同车”读为假设之辞,并谓“不可执文以害意”①以上四例分别见于《十三经注疏》:第337页,第352页,第310页,第341页。。质言之,在“据序言诗”的诠释规范下,不可因细绎诗篇正“文”而损害序“意”。由是观之,表面上依附于诗篇的《诗序》实际统摄着诗义生产,诗篇反而成为《诗序》的注脚。
诠释者“舍经就序”,无视诗篇意涵的操作并非简单的“穿凿附会”或“强经以就我”,而内蕴着深刻的经学信仰:如若没有《诗序》的说解,则诗篇非但不能体悟圣道,反而会诲人邪思。在有关《诗经》是否存在“淫诗”的论争中,清儒毛奇龄曾以黎立武的读《诗》经验为证,极力标举“序不可废”:
故宋元中子(黎立武)作《经论》谓:“少读箕子《麦秀歌》惄焉流涕,稍长读《狡童》而淫心生焉,一若邻人之妇,皆目挑而心招者。既久读《小序》,然后知《狡童》刺忽,爽然自失。”盖读《诗》之全系于说《诗》如此②毛奇龄:《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册,第161页。。
黎立武读《诗》却生起“淫心”的体验证明:若无正确的“读法”,《诗经》本文确有导人邪思的可能。事实上,由阅读《国风》而生起“淫心”绝非个体事件。宋代以降,在经筵中禁讲《国风》的动议与实践时有发生③清代学者王棠《燕在阁知新录》载:“经筵不讲《国风》由来久矣,胡安国常非之。宋学士真德秀《大学衍义》‘》‘戒逸欲’一条,郑卫淫辞之诗亦载焉,盖使人君味其言,方不以淫佚导其民也。”王棠:《燕在阁知新录》,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7册,第113页。,个中原因当如程元敏所说:“人臣进讲,惧犯名教,不便字斟句酌,故有请禁之议。”④程元敏:《王柏之生平与学术》《附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版,第39页。正因为诗篇易惑人心魄是诸多士人共通的阅读体验,毛奇龄才着意提出“读《诗》之全系于说《诗》”的命题,借以祛除《诗经》“诲淫”之嫌。汤显祖在《还魂记》中借陈师父之口道出了读者消弭《诗经》“淫辞”的绝佳方法:“《毛诗》病,用《毛诗》去医。”⑤毛晋编:《六十种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册,第54页。所谓“《毛诗》病”实因不假《诗序》,直寻诗义而起;“用《毛诗》医”则意味着读《诗》者必须明晰《诗序》所提供的历史背景与“美刺”等诠释框架,必须在明确所谓“淫诗”乃是“刺淫”“刺奔”之后方能不惑于辞藻,不染“《毛诗》之病”。设若没有《诗序》对诗义阐发向度的规约,则“圣经为录淫辞之具”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0页。;反过来说,由于《诗序》对诗旨的统摄,尽管诗篇所叙“皆乱状淫形”,然其所指却可以被悉数归之为“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⑦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72页。。
正因《诗序》是诗篇义理的真正负载者,是“诗”得以升格为“经”的关键,故“据序言诗”早成定例,成为诸家恪守的解《诗》传统。即使在宋代经学的变古风潮中,依然有许多笃信《诗序》的学者。正如程颐所言:“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⑧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46页。“尊序”学者或认为《诗序》出于子夏(郑玄、陆德明),或认为出于圣人与国史(二程、程大昌)⑨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29页;程大昌:《考古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页。,甚至认为《诗序》乃“诗人自制而圣人录之”(王安石、马端临)⑩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35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2页。。学者将《诗序》撰述时间不断前移意在塑造《诗序》的权威,并以此确立其统摄诗义的合法性。借助《诗序》的说解,诗篇在将自身纯化为载道之具的同时,亦使其与《诗序》原有的主从关系发生了倒转。
二、“口说”与“书写”注《诗》之别
作为对文本整理情况与意涵的解说,“序”显然是书写文化的产物。“据序言诗”所代表的正是《诗经》在形成定本之后的诠释模式。然而,早期的儒家教谕却多以口传的方式完成。荀子倡导的“君子之学”即是“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过程①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页。。阮元亦认为:“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传者少。”②阮元:《揅经室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6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早期经典传播与诠释中的“口耳相授”现象称之为“口传注经”③参见杨乃乔《口传注经与诠释历史的真值性——兼论公羊学的诠释学传统和体例及其他》,《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第10期;韩大伟《孔子之口授注经考辨三则》,《国际汉学》2010年第19辑;韩大伟著,唐光荣译《中国经学史·周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231页。。我们认为,“口传注经”的基本形式即孟子所谓的“答问之教”④孟子曾将“君子教之道”归纳为五种类型,其中之一即是“答问之教”。根据孙奭注疏,此种“答问之教”重在启发学者,而并非纯粹的知识宣谕与灌输:“有答问者,以其在于答问之间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为有答问之教也。”《孟子注疏》见《十三经注疏》,第2770页。;孔子与子夏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卫风·硕人》)的研讨则是“口传注《诗》”的典型事件。
根据《论语·八佾》的叙述,在孔门师徒的这次“答问教《诗》”中,子夏首先作为提问者询问诗句意涵,夫子作为答者应之曰“绘事后素”。当子夏以“礼后乎”再次设问时,孔子则感叹道:“起予者商也”。显然,子夏之所以能得到夫子的赞许,实缘于其并未亦步亦趋地接受夫子的教诲,而是在经由反思之后,充盈了夫子之所教。相应地,夫子亦未以全知者自居而拒绝子夏对诗义的推演,反而欣喜地认同学习者(提问者)对自己的启示。
由上述“答问教《诗》”的场景,我们可以归纳出“口传注《诗》”的几点特征。首先,问者与答者、教者与学者的角色在答问过程中发生了转换。《说文解字》释“启”曰:“启,教也。从攴启声。”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释名·释言语》亦以“起”“启”互训:“起,启也,启一举体也。”⑥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页。故就语义而论,所谓“起予者商也”实则意味着“教我者商也”。朱熹在集注《论语》时便明确将“起予”释为“相长之义”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3页。。宋代学者陈祥道在阐发《学记》之旨时亦曾恰切地指出“答问之教”中教者与学者身份的互易性:“方其学也未尝不教,及其教也未尝不学。”⑧卫湜:《通志堂经解》(第13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第177页。答问双方正是在身份转型中彼此获取教益,在互动交流中践履着“学学半”(《礼记·学记》)的原始意涵⑨按:《韩诗外传》亦载录有与上引文字相似的辞句,可见“教学相长”是早期教学中的流行观念:“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尽师而熟。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8页。然郑玄注“学学半”云:“学人乃益己之学半”;孔颖达疏云:“上‘学’为教,音斆,下‘学’者,谓习也,谓学习也。言教人乃是益已学之半也”。(孔颖达等:《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第1521页)二者均明确将“学学半”之所指界定为教者,打破了教、学双方的互惠模式。此种改变恰是“教化”新模式的展现,详本文第三部分论述。。
其二,“口传”(或“问答”)预设着注经者(教者)与传承者(学者)共同在场,较之于书写注经、阅读传经的模式,“口传注《诗》”具备鲜活的现场感与即时性。一方面,问答者对语词的选用与理解均受控于彼时情境,故对话可通过语境得到即时理解。一旦将口头话语从对话现场中抽离,其语义自明性亦随之丧失。在前引例证中,“绘事后素”对身处答问现场的子夏或许并未构成理解困难,但却成为后世的诠释难题;设若将“礼后”从答问语境中抽离,我们亦无从经验子夏言谈的机敏与深刻。另一方面,在问答现场中,语词并非唯一的信息承载者,语句与言谈的语调、对话者的肢体动作以及周遭环境等因素共同构成理解情境,召唤对话双方做出相应的反馈。此类反馈往往与对话双方对现场情势的判读相关,而与诗句自身含义无涉。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叔孙于宴飨时赋《相鼠》,而庆封“不知”。此“不知”应非不明诗句语义,而是不理解所赋诗句与场景的关联。
其三,就意义的出场方式而言,“口传注《诗》”与《诗序》所代表的“书写注《诗》”模式颇有不同。作为“答者”的“师”摒弃了以判断句(如《诗序》)直接给定诗旨的方式,而是先由“问者”申说其困惑,再由“答者”对“问者”之论说予以驳斥或补足(另可参看“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四简、第十简)。在此种“答问之教”中,诗篇诠释不再遵循“教——学”的单向传递,而转变为问答双方的交流;同时,诗意不再具备唯一指向,而是在“问——答——反馈——再答”的循环中得以逐步累积与丰赡,以至于呈现出纷繁多义的发散状态。在上述场景中,“巧笑倩兮”等诗句的意涵被孔门师徒延展至对礼法的探讨,且仍然葆有继续诠释的空间。
与“口传”的现场感、诗句的多义性相对,“书写”切断了对话与对话者、创发情境的关联,从而造就了封闭、稳定的文本空间。以《卫风·硕人》为例,无论是《诗序》“闵庄姜”《列女传》“防女未然,使无辱先”①王照圆:《列女传补注》,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9页。,还是《诗经原始》“颂卫庄姜美而贤”②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7页。均直接点明诗旨,规避了“口传(答问)注诗”中的诗意演绎。同时,通过文字记录,《,《诗序》等“书写注《诗》”文本得以有效地固化与传续,从而锁闭了诗义阐发的空间。此种对文本多义性的收束,恰恰成为古代学者尊崇《诗序》的根源,也是《诗经》经典化的关键。晁说之认为因为《诗序》乃“断会一诗之旨而序之”,故“说诗者或不可以无序”③晁说之:《全宋文》(第51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册,第174页。;程大昌将《毛诗》胜于“三家《诗》”归因为《诗序》对诗旨多义性的排斥:“毛氏之《传》固未能悉胜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该括章指,故训诂所及,会一诗以归一贯,且不至于漫然无统”④程大昌:《考古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页。;魏源认为《诗序》的价值在于终结诗义的含混状态,从而守护诗篇的“正确”意涵:“盖风诗寄兴无端,惟藉序之一言为指归,稍失毫厘,顿歧燕郢。”⑤魏源:《清经解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册,第662页。上述言论深刻地表征出儒者对诗旨多义性的恐惧,而《诗序》恰恰凭借将口头话语从对话场景中抽离,避免了诗篇意涵的多向延展,将纷繁的诗义“会归一贯”,圆满达成了历代注《诗》者孜孜以求的诠释目标,也让意义散漫的“诗”真正转型为载道之具的经典。
不仅《诗序》因整合诗意而受到尊崇,事实上,整部经典诠释史充塞着对书写的信赖,对意义稳定性的渴求。司马迁述《左传》之作因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孔子)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⑥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册,第648页。遵奉“书写注经”模式的儒者认为,口传话语在传播过程中会逐渐偏离其始源(“失真”)⑦例如,《公羊传·隐公二年》“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诂云:“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故有所失也”。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见《十三经注疏》,第2303页。,而书写则是摆脱该困境的唯一方式。即使书写会造成口传信息(如问答仪式等)的损耗,也远胜于多元意义的相互攻讦。经古文学者刘歆指斥今文经师“信口说而背传记”⑧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全汉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8页。按:此语是刘歆在欲立古文《左传》的背景下说出的。与《左传》相比,今文《公羊》《穀梁》二传保持了更多的答问之教与口传注经的痕迹。。这一命题以可信度为依据,确立了“书写”对“口传”的压制。“传记”所以可信,缘于其书于竹帛,无所阙疑,且终结了文本意蕴“纷然殽乱,莫知所从”的混杂状态⑨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更为重要的是,“传记”推迟了“口传注经”中意义的即时出场,且在这一延宕中为经文添加了新的内涵(如《诗序》对诗篇历史情境、“编次之义”的说明)。此种意义的增添使往古经典得以适用于当下境遇,正是学者“通经致用”的现实体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诗经》诠释史中,倡导经典意蕴多元化的观念虽时而可见,但这并非意味着阐释者对经典多义性的追寻。例如,董仲舒虽谓“《诗》无达诂”,但根据“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天)”的要求,无论诗篇存在多少意涵,其必须被整合、升华为“一”。诚如苏舆所说:“盖事若可贯,以义一其归;例所难拘,以变通其滞。两者兼从,而一以奉天为主。”⑩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5页。所谓“《诗》无达诂”,不过是公羊“经权”思想的演绎。降及有宋,宋儒操用“理一分殊”的观念处理经典意蕴“变”与“常”“多”与“一”等问题。在道学语境中,由于“理一”在逻辑上先于“分殊”⑪此论断涉及宋儒对理气关系的讨论,本文不拟展开论述。要之,道学一系,尤其是朱子多承认“理在气先”,但这只是逻辑层面上的区隔,在实际格物中,朱子又强调不能“离气言理”。,而考察“分殊之理”的终极鹄的在于体认“理一”,故经典诠释仍是具有唯一指向性的活动。
三、从“声教”到“诗教”:“据序言诗”与“口传注《诗》”的终结
以《诗序》为代表的“书写注经”模式不仅阻断了诗旨的自由演绎,而且破坏了口传(或答问)场景中问答双方的共同在场,从而造成了教者与学者在时空上的疏离。这一分离预表了《诗经》诠释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亦即,从先秦“乐教”到汉唐“诗教”的转轨。
我们先对汉唐“教化”观念的基本构型做一考察。匡衡在向汉元帝陈说“教化”特质时谓:“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颜师古注云:“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劝说也。”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35-3336页。《孝经·广至德》章称引孔子之说云:“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李隆基注云:“言教不必家到户至,日见而语之。但行孝于内,其化自流于外。”②李隆基,邢昺:《孝经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7页。由是观之,“教化”并不要求教者与学者实际接触,教谕在教、学双方时空分离的状态下依然可以传递。显然,与“答问之教”的现场教授模式不同,“教化”得以施行的前提是将“经书”作为“教者”的“代现物”,以文本“再现”圣人之教。章学诚在追溯“经”之始源时称:三代之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故无需经”;孔子亲身教授,故无经名;夫子殁后,“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③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94页。。质言之,将典章书于竹帛(即“经”)或许是不得已的权变,但孔子既没,依经托义成为儒学承续与教化的必然选择。
“以经为教”不仅意味着教学模式从“口传”到“书本”的转型,更意味着教谕理念的重塑。汉儒对“教”字的释义便已透露出此种新变。《说文解字》释“教”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凡教之属皆从教。”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释名·释言语》则以“效”释“教”:“教,效也,下所法效也。”⑤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根据许慎、顾野王与朱骏声等人的释义,“效”即是“像似”与“法效”之意。由是观之,在教化观念中,“教”意味着某人施予他者可供仿效的物事或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教化行为被严格区隔为“上”(施事)与“下”(效法)两个谨严的层级:处于低阶位的仿效者一旦处于教化场域,便被要求精准地摹仿与再现在上者之所施,却无权对加诸其身的种种规训进行质疑。当汉儒以“效”诠释“教”时,“口传(答问)之教”中教学双方的互动结构便被塑形为“等级传递”结构。作为高阶位的“教”,其功能是“统摄”;与之相应,处于低阶位的“学”,其属性被设定为“遵从”。显然,由于“等级传递”所构筑的森严序列,教谕成为“教者——学者”的单向线性过程,其间不复有教者与学者在对话中的身份转换。
从先秦“答问之教”到汉代“教化”的转轨显明了“书写注经”的兴起与“口传注经”的衰微。“教化”奠基于“六经”,其本质是操用书写技术固化圣人的口头教谕,以使后者恒常在场的实践。诚如汉儒贾谊所言:“令人缘之(‘六经’)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⑥贾谊:《贾谊新书》,见《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5页。所谓“自修”明晰地揭示出“教化”之“教”是受教者不断趋近、效法经书的单向活动,其过程是学者通过对经书(而非教者本人)的体验与诠释,形成自我理解,让自身回返至与“六经”所蕴之道同然的状态。从根源上说,“教化”——“以经为教”——是书写语境中的产物,是“再现”(书写)对“在场”(口传)的替换与压制。
我们再来考察从先秦“乐教”到汉唐“诗教”的转轨。三代之时,帝舜“以诗为教”,启发胄子之志:“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⑦孔颖达等:《尚书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段文字中,“诗言志”与“声律”“典乐”共同出场。“诗”不是在“志记之志”的意义上发挥“言志”功能⑧贾谊在《新书·道德说》中从“载录”的角度理解诗书定名缘起:“书者,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故曰‘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志徳之理而明其指,今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见《二十二子》,第756页。,而是凭借其韵律达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境界。与此类似,孔子将“诗”“礼”“乐”视为“三位一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汉书》亦将“讽诵”作为《诗经》“遭秦火而全”的原因。近代《诗经》研究者徐英(澄宇)根据先秦诗、乐的协同性,将早期“诗教”界定为“声教”:“声之为教,比语协音,以利远布。上世文字未兴,所赖以交通知识、传播教化者歌谣耳,故谓之声教,或谓之诗教。”⑨徐英:《诗经学纂要·论诗教》,《安徽大学月刊》,第2卷,1934年。先秦“教诗”以“声”为重的特质表明:彼时“教诗”系通过聆听诗乐而兴起学习者中正平和的志意,其所依托的媒介不是文字而是声音,专注于口耳而非阅读。
先秦“声教”目标之一在于培养学诗者牵合诗句以应对不同语境的素养。《论语·学而》载子贡引《卫风·淇澳》之句,将“贫乐富礼”的抽象意涵转换成“切磋琢磨”的具象,并以是证成孔子“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之义。孔安国对此评注道:“子贡知引《诗》以成孔子义,善取类,故然之,往告之以‘贫而乐道’,来答以‘切磋琢磨’。”①邢昺疏:《论语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58页。孔安国所谓“善取类”即是赞誉子贡善于在事“象”(类)之间做出转换。缘于对修身与治物(骨、象、玉、石)之间“同气之应”的体认,子贡恰切地施用了“引譬连类”之法,既使抽象义理通过诗句得以明晰,又将修身的训诫灌注到“切磋琢磨”这一具体事件之中。此种“牵此以合彼”的语义迁移能力被孔子视为言《诗》的基本条件(“始可与言《诗》已矣”)。在上述语义转换中,《,《淇澳》自身的意蕴始终未曾出场,而这恰是“声教”的关键所在。通过抛弃诗篇“本义”,“声教”实现了对学诗者“达政专对”(《论语·子路》)能力的培养。清代学者劳孝舆曾对先秦引诗不重“诗人之志”的倾向做过说明: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作诗,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庚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②劳孝舆:《春秋诗话》,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02册,第5页。。
先秦引诗既着意于言己之志,故无需关注诗篇作意,且因要适应不同场景,故不能拘泥于诗篇本旨。诗篇并非为其作者所专有,而属于“公共素材”③徐建委,马丁等分别以“公共素材”“文本库”等概念指称篇章的独立性,可任意组合的特点。参见《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9页。,故“有诗而无诗人”;诗篇意蕴并非为文本所限,而临时产生于引诗言志的行为中,故“诗无定指”。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④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00页。,恰切地展现出先秦用诗的场景化特征以及诗篇意涵的不稳定性。
与先秦“声诗合一”的“声教”模式相对,汉唐经学则力主“声诗有别”论。孔颖达曾如此疏解《礼记·经解》篇中“乐教”与“诗教”的意涵: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⑤孔颖达等:《礼记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10页。。
孔颖达认为,从源起上说,诗与乐均与音律相关,故“诗乐是一”;但就教谕方式而论,“乐”以“声”感人,“诗”则以“义”晓谕于人。职是之故,孔颖达将“诗教”与“声教”区别开来,前者重“义”,后者主“声”。在对“诗言志”的训解中,孔颖达更为清晰地展现了汉唐“诗教”的运作模式:“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故教其诗言志以导胄子之志,使开悟也。”⑥孔颖达等:《尚书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页。显然,孔颖达在“记录”的意义上理解诗之功用:“习诗者”正是通过诠释诗人志意的书面记录(《诗经》)而“开悟”。
孔颖达对“诗教”与“乐教”的区分表明:作为教化的一个向度,“诗教”归属于书写传统,其目标在于辨识诗篇“美刺讽喻”之意,诗篇作者、创作背景、文本意图等问题由是成为研究重心。正是在《诗经》诠释的“重义”时代中⑦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诗序》“叙作者之意”的功能愈显关键。通过《诗序》的标示,诗篇作者被确认为“国史”(《周南·关雎》)、“国人”(《秦风·黄鸟》);诗篇创作动因被总纳为“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更为重要的是,《,《诗序》以“美刺”为诠释框架将诸篇诗旨汇于一贯,避免了“声教”带来的“诗无定指”,从而在“诗义”与“教化”之间建立起对应。以《诗序》对“变风”的阐释为例,在言及“变《风》发乎情”之后,《,《诗序》便立即给出“止乎礼义”的断语,申明“变《风》”皆中礼。孔颖达曾标举变、刺之诗“温柔敦厚”的修辞特征,以论证其契合“礼义”:若此辞揔上六义,则有正变而云“主文谲谏”,唯说刺诗者,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虽论功诵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说作诗之意耳⑧孔颖达等:《毛诗正义》,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1页。。
孔颖达认为“刺诗”虽曝人君之恶,述“时政之疾病”,然其言皆婉曲,其意皆出于劝谏之心,故无犯于“温柔敦厚”。由是,孔颖达将“美刺说《诗》”的诠释框架、“主文谲谏”的修辞方式与“正邪防失”的教化目标圆融地编织在一起,并由此划定了“刺诗”的诠释边界。朱子认为若以“美刺说诗”,则有相当数量的诗句“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殊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⑨朱熹:《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册,第361页。。马端临则沿袭孔颖达的思路驳斥朱子,认为“刺诗”虽言辞激切,却不失“匡正人君”之旨:“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爱国,不能自己之意”⑩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0页。;陈启源则更为直白地申明:“(刺诗)惟其怨所以为温柔敦厚也”⑪陈启源:《清经解》,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册,第450页。。孔颖达等“尊《序》者”的论说表明:借助《诗序》对诠释径路的锁闭,汉唐“诗教”实现了由释《诗》体悟“教化”,由“教化”诠释诗义的循环,彻底终结了“口传注《诗》”时代诗义的漫然无统。正是在先秦“乐教”到汉唐“诗教”的转轨中,《诗经》诠释迎来了“书写注《诗》”与“重义”时代。
《诗序》在历代《诗经》诠释实践中的地位虽历经起落,但诠释者对诗篇多义性的排斥却是一以贯之。《诗经》经典化的实质便是由“书写注《诗》”造就的诗篇意蕴封闭史。先秦“口传注《诗》”“以声为教”的教、学转换被“上施下效”的“教化”模式所取代,“诗无定指”的意义多元性被《诗序》终结。“口传注《诗》”的衰微与“书写注《诗》”的兴起所表征的不仅是传播媒介更替,更为“经学”与“教化”等话语实践的运作奠定了基础。归根结底,《,《诗经》不是“诗”而是“经”,而“经”的“名”与“实”已然表明其为书写文化的产物①许慎释“经”云:“经,织纵丝也。”(《说文解字注》,第644页)章太炎论“经”之名曰:“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2页。。经学凭借“书写”形成“经典”,掌控了意义创发的始源,并以此成为意义的终极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