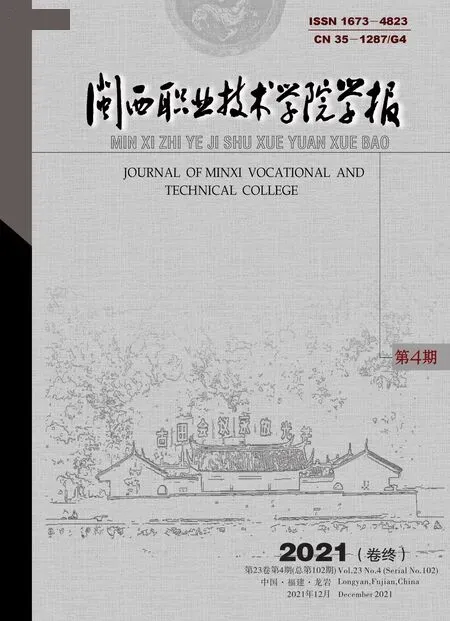论何凯旋小说的民间性特征
——以《江山图画》为例
任 雨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出生于黑龙江密山的何凯旋,是黑龙江本土作家群的中坚力量,著有长篇小说《昔日重现》《都市阳光》《江山图画》,话剧《红蒿白草》《梦想山峦》《1945 年以后……》,先后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精品工程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和第十六届、第十九届田汉戏剧奖,首届“大益文学双年奖”最佳小说奖等。2009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江山图画》以黑龙江省六大山脉之一的完达山为故事发生地,叙述农场两户人家日常的生活,呈现苦难与温情、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中的民间风貌,是一部书写黑龙江民间生活的小说。 何凯旋在小说中不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而是从个人和家族的生存本相微观叙事,打破以往固有的农村与政治、 农村与城市或对立或融合的模式,还原最为真实平凡的东北民间世俗生活。
文学理论中的民间概念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 这一概念被人们广泛关注和讨论源于20 世纪90年代,由陈思和首先提出。 他在《新文学整体观续编》一书中认为,“当代大学里的民间概念,包含两个层面意思: 第一是指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度向, 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 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第二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 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 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并采取尊重的平等态度而不是霸权态度,使这些文学创作充满民间的意味”[1]。本文从文学理论中的民间概念出发,探究小说《江山图画》在内容、艺术手法上所表现出的民间性特征,以及作家民间立场的表达。
一、多重包容的民间生活状态
完达山是一个美丑并存、善恶共生的民间世界,有着无限的包容性。在这种空间背景下,何凯旋不但洞察到民间世界的劣性与野性, 而且捕捉到民间存在的美好品质,构建的民间世界既有愚昧、自私、野蛮、算计等劣根性,又有朴实、善良、富有活力和生命力的美好品德。
何凯旋在小说中借助一个生长于这片土地少年的视角观照人物的生存状态,摒弃“轻易站出来指手画脚完成他们自有规律的习惯”[2], 保持一种客观尊重的态度,既不歌颂人的善良与美好,也不掩盖人的丑陋与肮脏。当人受到现实生存困境的制约,金钱的欲望被挑起时,“小聪明”的劣性与野性一同迸发。小说中的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算计到雨天公路上有钱可赚,开车拉着“我”带上绳子驶向公路,有偿拖拽陷进水坑的油罐车,趁机加钱;帮三杨母亲送葬误工后爹蛮横地抢来他家的新牛车拉化肥;因国顺丢失“我”家的马,爹抢占三杨一家的新房子作为补偿。 三杨一家则更是像民间的痞子,无赖、自私:三杨总以他母亲的由头向“我”家理所当然地借东西, 国顺不靠自己劳动经常偷鱼偷马, 杨香向“我”家卖鱼、吃酸菜时耍赖与胡搅蛮缠,他们在“我”家马被人牵走时表现出看戏的冷漠。 面对普通民众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狡黠、算计等性格弱点,作家并没有刻意回避,而是以民间的自有法则进行审视。除此之外, 何凯旋还在小说中表现民间神秘的神灵观念和愚昧的迷信。 神秘的神灵观念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伴随自发性的信仰崇拜,成为一些人的精神支撑。三杨母亲去世时手里紧握一炷香向着青铜佛像;三杨烧香祈求女儿生产顺利以获取自我安心; 完达山农场的人们认为人死后要扎够七天的白麻布, 烧三炷香都升起就会大吉大利,乌鸦是报丧的不祥之物。何凯旋用这些表现民间生存状态中的封建与迷信。
何凯旋在展现民间糟粕和人性恶的同时, 着重突出完达山农场民间生活的美好元素。 爹是一个勤恳务实的普通农民,精通各种劳作技术,带领“我们”一家开荒种麦子,每天都忙于养马、砍柴、耕地、播种、追肥等各种劳作,总是一副忙碌坚毅的样子,用自己的双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脚踏实地而又安分守已。爹沉默寡言的外表下有一颗温暖的心,“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小键呆了短短几天就要回城里时,爹非常细心地准备了钱给他。在三杨母亲去世时,虽然爹总是与三杨一家产生矛盾, 他主动出力帮三杨安葬他母亲。 小说还描写了国顺奋不顾身冲进火海砍树阻挡火势蔓延的勇敢行为、三杨孝顺母亲、杨香努力过日子等,展现民间人们的美好品质。
作家通过人性的张力使民间成为自由、包容、充满无限可能的象征。一方面,作家以“我”的视角进行叙事,儿童的所言所思总是单纯无所顾忌,加强了“我”面对善恶事件的主观色彩。 “我”的妈妈桃儿原来并不属于完达山农场,因未婚先孕执意生下孩子被发配到这里,由于生长背景的不同,妈妈有着与民间观念相冲突的道德准则,像是一个“说教者”。她认为杨香与国顺住在一起是伤风败俗的事情, 爹耍聪明赶走三杨家的新车在“我”看来是非常厉害的事,但妈妈却轻蔑地说“像贼一样,一点道理也不讲”[3],并经常教育“我”和姐姐。但长期的民间生活,使妈妈逐渐认同了民间的生存哲学。三杨与“我”妈妈评理爹赶走他家的新车时,“我”妈妈以这是帮他母亲送葬耽误农事的补偿为由打发了三杨, 马军与姐姐恋爱时的亲密举动同样并没有遭到“我”妈妈的制止与训斥。另一方面,何凯旋运用全知视角进行叙事,对民间的价值观给予充分的尊重。翟木匠与挤奶工公开调情,三杨在其母亲刚下完葬就与寡妇郑喜凤在一起,这些原本会受到排斥与唾弃的事情, 通过作家的民间立场描写,使人的生命有了率性鲜活的感觉。在何凯旋的笔下,民间是一代人、一方土地的真实缩影,民间生活状态自在包容。
二、日常生活叙事的民间审美趣味
日常生活叙事以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为书写对象,还原日常生活,解析小人物的世俗欲望与生存,“成为观察时代转型和人性变迁的舞台”[4]。 在《江山图画》中,作家将视点放置到对民间日常生活的关注上,叙写的是一幅不受外界渲染、生动活泼的民间日常影像,纯粹而富有生命活力。与部分知识分子拒绝和改写日常生活的写作姿态不同, 何凯旋认为朴素的东西更有力量。他在小说中强烈关注现实生活,用简约朴实的话语, 试图将民间日常生活的繁杂与琐碎真实记录下来, 忠诚于写实手法, 钟情于世俗生活,作品富有烟火气息,富有民间审美趣味。
小说细致描摹农耕场景, 表现具体可感的百姓日常生活。何凯旋出生于密山农场,从小见闻农场的点点滴滴,亲身经历农场的生产劳作,受到童年经验和历史文化的熏陶, 在创作时将自己对农场日常生活的个人记忆融进小说, 对民间图景进行再现式还原。农业生产作为农村重复的惯常行为,成为作家日常生活叙事的对象。 作家将笔触延伸到农民所生存的世界,细致描摹农耕场景,娴熟地再现底层人民的生活面貌, 表现民间自给自足的生存本相。 小说以“我”和爹买马准备开荒为起始,以庄稼生长的不同时间段展开情节的叙述,将人物的日常劳作活动贯穿全文。“我”和爹在自家园子前开辟一块荒地,从用斧子砍树开荒到耕地播种,从给麦子追肥到收割晾晒,展开一系列的农业劳作,“妈妈和姐姐, 她们俩站在牵引架后面挂着的播种机上面, 用棍子搅拌着播种箱里的种子,麦种通过一排胶皮管流进垄沟里面”[3]。小说高度还原化的细节描写,生动展现“我”家播种时的劳动场景,在日常生活的真实再现中完成文本的架构。何凯旋不仅实录传统的原始劳作方式,而且契合小说的故事时间, 将农业活动融入机械现代化的发展浪潮,展现当时农村农耕发展二元融合的现状。小说再现耕种、收割等场景时,出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农具的身影,呈现劳作场景的时代特色,突出时代浪潮中农村的选择与顺应。 何凯旋有意打破传统文学对民间或苦难或理想的两极书写趋势,将农耕场景拘囿在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完达山脉,既满足诗意的民间风貌,又肯定劳作自给自足的价值。
“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是鲜活的生命个体,生活的简单与复杂、平凡与丰富……就是一块值得去发现和言说的领域。 ”[5]除了田野劳动,夫妻拌嘴、邻居纷争、婚丧嫁娶成为被叙述的主体,何凯旋在琐碎杂事的叙述中为读者展现原生态的生活。 他以平视的姿态贴近民间的普通民众,把那些看似无味的日常琐事当作叙事的主体加以展现,使生活本身产生意义。小说围绕两户人家的日常生活、情感纠葛展开叙述,以细致的描摹揭开生活的面具。 小说安排“我”家开荒种地、三杨以他妈妈为由头向“我”家强要东西、国顺偷鱼受伤但屡次不改、三杨母亲安葬、“我”同母异父哥哥来访、姐姐与周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妈妈与爹先弄院子还是先弄门而争执等琐事,将民间的百态生活娓娓道来。在小说中,何凯旋不刻意书写那些苦闷无助、无所适从的世俗情境,而是赋予人物个体意识的觉醒,每个人都在诠释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日常生活成为个体自由意志的表达。何凯旋将艺术技巧与自己对现实的握力相结合,去饰求真,展现普通民众真实生动的生存状态,塑造更加鲜活灵动的民间世界。
三、质朴亲切的民间意味
方言、 俗语作为这片土地的先辈们创造出来的语言,被生长于这片土地的民众所接受吸纳,成为融入血脉的第一语言。当作家回首故乡进行创作时,方言成为其文学独特的外在表现, 金宇橙的上海沪话写作,刘玉堂的沂蒙小说语言,迟子建和韩少功等人对地域文学的书写, 构成了区别于他人的地域创作风格。何凯旋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作家,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不断践行文学“须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的原则[6]。 在《江山图画》中他不避俗,运用大量东北方言和具有民间特色的语言表现民间生活, 锻造质朴亲切和地域鲜明的美学特征。
《江山图画》大量使用“垄台”“火墙”“玉米楼”“障子”“窝棚”等具有地方生活化的方言,构建宁静祥和的东北民间生活图景: 在散发着纯净淡蓝色光芒的完达山脚下, 两户人家的身影总是穿梭在被耙过的荒地、新背起的垄台上;夜晚他们则顺着风化石的道路走回家,或睡在玉米楼上,或躺在叫火烤热的炕头。小说以农场为故事空间展开叙述,在刻画人民劳动场景时,大量使用“镢头”“镰刀”“笤帚”“镐头”“簸箕”“铡草”等词语,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情状,增加细节的真实感。 同时,使用“瞅着”“光说”“招呼”“叫唤”“吱声”等词,生动传达出农场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 此外,小说还记录东北民间的风俗习惯,描写“我”和姐姐以及杨香玩抓“嘎拉哈”的游戏,用特有的日常游戏忠实反映东北民族的历史文化。“嘎拉哈”又叫羊拐,是东北“旧十怪”之一,多见于妇女和孩童之间的游戏,代表着勇敢、财富和吉祥,是东北地域文化之一。 何凯旋运用质朴亲切的黑土语言探索民间世界,小说的语言与故事呈现有机结合,更好地塑造文学意义上的民间空间。
《江山图画》的“土气息、泥滋味”不仅体现在方言上,而且体现在在通俗化意象上。何凯旋在牢牢把握小说故事情景氛围的基础上, 围绕故事的民间性特征选取农村常见的、 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动物作为恰当的意象,渲染小说的民间意味,使小说兼具文学性与大众化色彩。自在的鱼、勤劳的牛、仁义的狗、柔顺的马等动物意象在小说中频繁出现, 这些动物不仅以物的形式存在,而且具有人性化的特征,隐含内在深意。 鱼的意象反复出现在男欢女爱的故事情节中,是男女爱情的象征与性关系的表现。在描写三杨与郑喜凤的性爱时, 连用九次鱼表现郑喜凤的情态和三杨的内心活动。 马军与“我”姐姐确定爱情关系时,送了姐姐一个鱼形的耳坠作为礼物,当这段爱情走向崩溃后,鱼也早已死在姐姐的兜里。牛与狗则在小说中高度拟人化,成为人性的象征。下雨天爹准备靠拖陷进泥里的油罐车趁机“打劫”时,特写了雨中横冲直撞的牛,将铁链拽得哗哗响,然后写道“爹也是这样, 他身上的那种东西也在不断地涌动不断地冲撞,不断地需要一种方式解脱”[3]。爹作为北大荒农民的代表,像头牛一样始终保持勤劳朴实、任劳任怨的秉性,但在雨水的刺激中,爹的内心欲望与野性一同爆发,这时的牛被赋予野性与力量象征意义。小说中的狗意象也是如此,映射出三杨的性格特征。在三杨妈妈死后,狗一直陪在她身边,在下葬时也趴在棺材上面, 但在棺材快被埋住的最后一刻狗改变了主意,疯狂逃离。 三杨因母亲去世悲伤哭泣,一安葬好母亲就与郑喜凤欢好, 狗的行为正好与三杨的表现相呼应。马是整部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柔顺的母马则与杨香的处境和命运相关联:马怀孕,杨香也怀孕;马因怀孕而不用下地,杨香因怀孕逃避劳作;母马与杨香差不多同时生产, 一匹小马出生, 一个孩子去世;最后,一匹母马死亡,一个女人活着。通过设置马这个意象,含蓄地预示杨香的悲剧命运,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作品中乌鸦的意象也被赋予告知灾难死亡来临的能力,烘托悲凉的氛围。
四、结语
《江山图画》真实再现了20 世纪90 年代东北农村的现实生活状态,浓墨重彩的山村风景、通晓人性的动物牲畜、庸凡的人物群像、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共同组成了这一方江山的图画。在这方极具包容性的民间大地,何凯旋以尊重的、客观化的叙事立场,用平淡朴实的话语演绎着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和生存哲学,肯定民间的价值与魅力。同时,何凯旋把质朴亲切的黑土语言完美地融入小说之中,对民间日常生活等进行记录描写,形成极具黑土情怀、泥土气息的美学风格,增强了小说的通俗感和艺术魅力。这种民间性特征是何凯旋一贯的创作风格,体现在他的多部作品中,《红蒿白草——我的家园》演绎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与生存哲学,《三匹马》展现民间小人物顽强的生存意志。 自在的生存状态、客观化的叙事立场、质朴亲切的黑土语言构成独具魅力的民间审美趣味,独特的创作风格使何凯旋成为民间文学的一方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