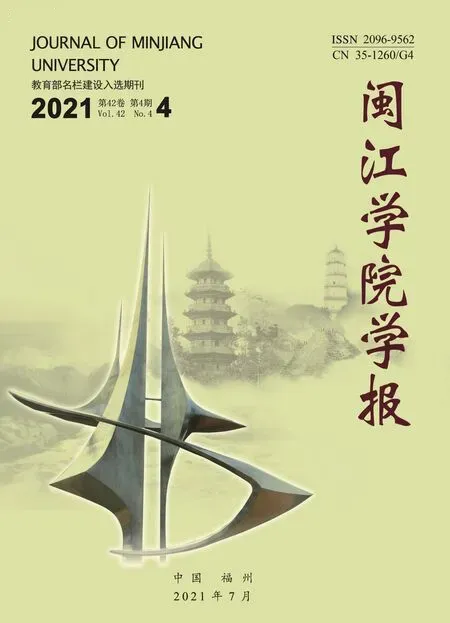语言选择与价值判断
——清末癸卯学制的语言规划意义分析
史玄之
(闽江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清末语言规划指的是晚清政府在新政时期对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在地位、功能、语言内部结构等方面做出的具体规定。语言是清末近代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近代教育发展的基础,因此清末语言规划实际上也是教育规划的一部分,其规划范畴既包括单纯的语言教育,也包括以语言为媒介的非语言学科教育。[1]晚清时期并未成立任何专门的语言政策与语言管理机构,语言规划由清政府中的管学大臣和晚清学部(职能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制定。清末新政十年间,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和之后围绕癸卯学制的增删政策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教育规划政策。
由于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肇始,因此对该学制的剖析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热点。先前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研究侧重剖析癸卯学制的内涵、目标、制定过程及影响,包括癸卯学制与日本近代学制的对比[2],癸卯学制规范下中国近代文学教育、生物教育等学科知识谱系、教育方法的更新[3-5],张之洞“中体西用”学务思想与癸卯学制的关系[6],以及癸卯学制对中国女性思想解放、近代公民意识培育的推动[7-8]。另一类研究则从历史学视角聚焦癸卯学制中的语言文字变革,在研究主题方面与本文更加接近。王东杰[9-11]以翔实的史料为支撑,分析清末切音字运动如何在中西学战和思想交锋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时世平[12]分析清末语言文字改良、普及民众知识和国家民族富强三者关系,将汉字改革视为民族救亡复兴的一种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刘晓明和郭莹[13]的研究则从清末社会群众对切音字改革的反馈视角分析切音字改革的实际效力。
先前的学术研究多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清末新政的实质和影响,但缺乏从社会语言学,特别是从语言规划理论视域剖析清末语言政策与新政改革、社会语言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少数关于清末语言文字改革的研究聚焦“切音字运动” “官话运动”等发生在汉语语言文字内部的规划,而对清末新政时期汉语语言文字外部的规划,特别是外语规划、外语与汉语的地位规划和教育规划研究较少。事实上,在清末中西学战的背景下,外语和以外语为载体的西学知识对汉语和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学知识带来巨大冲击,对清末语言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分析清末语言政策必须全盘分析晚清政府对汉语和外语在地位、结构、功能、教育方面的管理行为,并从中分析清末语言政策所折射出的语言价值观。
本文以语言规划理论、语言价值理论为理论框架,选择癸卯学制中的语言选择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对癸卯学制语言规划文本、政府奏折、谕旨、官员报告、信函和相关报刊评论等一手史料的内容分析,重点研究癸卯学制中汉语与外语二者选择、汉语变体选择、外语语种选择等三方面内容,透过清末语言文字内外部的规划和改革,剖析清末语言选择与社会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语言规划理论与语言价值理论阐析
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德国语言学家汉兹·克洛斯(Heinz Kloss)根据语言规划的目标和对象,将其分为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两类。语言地位规划确定一种或多种语言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例如一国官方语言的选择、本国语与外语的关系等。语言本体规划旨在促进国语、民族共同语等强势语言不断规范、完善,例如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一国(或地区)语言进行改革。[14]随着语言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语言教育规划(也可称为语言习得规划)成为语言规划的新增类别,主要涉及母语教育、外语教育等问题。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规划都与规划者的语言价值观密切相关,以色列语言政策研究专家博纳德·斯波斯基教授(Bernard Spolsky)提出的“语言政策理论模型”中将“语言价值观”称为“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ies)/“语言信仰”(language beliefs),即同一言语社区对一种语言(或其变体)形成的态度、认识和价值判断,是影响群体或个体言语行为的内在因素,也是语言管理机构制定语言政策与规划的重要依据。[15]
语言价值观是语言规划过程的重要一环,涉及对语言价值的基本判断。归纳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语言价值大致可分为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三类。语言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上,一种语言(例如当今的英语)使用人数越多、分布范围越广,这种语言经济价值就越高;语言文化价值基于语言资源观,即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具有历史价值、美学价值、情报价值或战略价值,例如古汉语、繁体字因其独特的造字与会义上的关联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语言情感价值基于“身份认同”的语言观,即语言选择满足语言使用者的身份需求,引发使用者的情感共鸣,例如一种方言起着一个言语社区人员身份认同、情感纽带的作用。[16]这三种语言价值分类实际上有明显的交叉重叠之处,国家(或地区)语言规划者根据实际社会语言生态环境综合考虑三种语言价值对语言规划的影响,对国家的官方语言、区域性语言、外来语言做出合理的规划和选择。虽然语言规划理论和语言价值理论提出于二战之后,与清末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这并不影响将其运用于本文对癸卯学制语言规划的分析之中。清末癸卯学制对汉语和外语进行地位、本体、习得三方面的规划,而每个方面的规划背后渗透着规划者的语言价值观。
二、“正心术”与 “练艺能”:汉语与外语的选择博弈
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汉语与外语、儒学与西学的“道器”之辨并未真正动摇汉语在中国语言体系乃至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到了清朝末年,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与军事武力相伴的是西方文化思潮、知识体系对传统儒家文化和知识结构的冲击,因此语言文字领域中汉语与外语的选择博弈甚至被赋予了清末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使命。
根据癸卯学制的规定,汉语和以汉语为传播载体的儒学为教育之本。语言是教育的载体,教育也为语言文字改革提供实践舞台,因此关于清末汉语与外语的选择博弈可在语言教育政策中得以体现,具体表现在癸卯学制对各级各类学堂汉语和外语地位、功能、学习次序等方面的规定。作为晚清第一个颁布且实施的近代教育制度,癸卯学制对汉语和外语的地位和功能做出了具体规划。癸卯学制主要起草者之一的张百熙在1904年1月13日的《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将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学宗旨阐述为:“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17]而癸卯学制中的纲领性文件——《奏定学务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汉语和经学的关系,汉语文字是经学的载体:“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18]493而这里“中国文辞”和“文学”指的就是汉语。汉语的基础地位还体现在癸卯学制对新式学堂汉语课程设置和授课时长的要求上。癸卯学制规定:在小学堂和中学堂中,汉语课程和以汉语为载体的修身和经学课程排在课程列表的最前列,每周授课时数也明显高于其他课程。例如,《奏定初等小学堂》每星期授课时刻表显示在每星期30小时的总学时下,汉语课程和经学课程的总时长达到16小时,比其他课程的总和还多[19];而《奏定高等小学堂》课时列表中,汉语和经学课程的总时长达到20小时,超过全部课程总时长(36小时)的一半[20]。到了中学阶段,虽然学生开始学习外国语、博物等西学课程,但汉语课程和儒学课程(包括修身和读经讲经)时长(14小时)仍占总学时(36小时)的1/3以上。[21]
花青素还能延缓脑神经衰老,对由糖尿病引起的毛细血管病也有防治作用,它在增强心肺功能的同时,还能预防老年痴呆。
与汉语“正心术”的价值不同,外语在清末语言规划中被赋予了“瀹智识、练艺能”的工具性价值。《奏定中学堂章程》指出:“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课,各国学堂皆同……(习外语)使得临事应用,增进智能。”[21]320根据癸卯学制对中学堂各学科每星期授课时间的规定,中学堂前三学年外语课程每星期授课8小时,后两学年每星期授课6小时,每周授课时长仅次于“读经讲经”课的每周9小时,这体现了外语课程在中学堂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要求学生须学习两门外语,外语课程每周课时数接近总课时数的一半,以备“将来进习专门学科之用”[22]337,而所谓的“专门学科”,就是指学生高等学堂毕业后进入大学堂所主攻的西学专业,由此可见,癸卯学制凸显外语的工具价值,强调学习外语与掌握西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癸卯学制对汉语和外语教育次序也做出了相应规定。《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第二章“学科程度及编制”中提道,“中国文字”科第一学年开设,总共开设五年,主要教学任务是帮助学生“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19]295。关于外语学习,《奏定学务纲要》明确要求“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18]495,等到学生汉语通顺并考取中学堂的时候,才允许兼习洋文。由此可见,在清末语言规划者眼中,汉语学习应早于外语学习,小学阶段专心于汉语学习,等到学生进入中学堂后再学习外语。在中西学战的背景下,清末语言规划仍将汉语和儒学教育摆在重要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的影响,是甲午战争后清末教育改革师法日本的真实写照。晚清教育家姚锡光在考察日本各级各类学堂后发现,虽然日本学校开设西语课程,但“实以其国文为重”,所授课程“皆译成本国文”,即使是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也必须具有扎实的国文和国学功底,方可“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可见日本新式学堂培养的人才并不是“弃本国学术而从事西学者”[23],而是以本国语言和国学为基础兼通西语和西学的人才。
三、助教育与启民智:汉语变体选择
汉语与外语的选择博弈是清末语言规划中对不同语言之间地位与功能做出的价值判断,属于语言外部规划范畴。而语言规划的另一面是对语言内部的完善和规范,在清末新政时期表现在对汉语的简化、统一和纯净化上。甲午战争后,一大批学者开始反思战争失败、国家贫弱的原因,在对比中日学制、考察日本新式教育发展后,普及教育、开启民智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侮侵略的根本途径,而切音字改革、简化汉字等一系列汉语本体规划和变体选择则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语言通路。汉语本体规划和变体选择超越了语言文字内部改革的范畴,不仅起到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实用功能,更被赋予了国家认同的政治功能。癸卯学制提出:“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18]499这说明清政府有意识地促进国语统一,虽这一目标在清末新政时期未能完成,但对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卢戆章、沈学、王璞等一批晚清学者提出各种汉字注音方案,通过切音字改革帮助下层人民掌握汉字,进而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中国汉语拼音文字首倡者卢戆章将切音字视为增强国家实力的基础:“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24]1892年,卢戆章以闽南方言为基础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成为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从1892年卢戆章创制切音新字到1911年清朝灭亡,这20年间出现了28种切音字方案,包括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原序》(1900)、陈虬的《新字瓯文七音铎》(1903)等。[25]
除了切音字改革外,简化汉字也成为清末语言改革热潮的一部分,汉字繁难被晚清学者看作是造成社会底层人民识字率低的一大原因。晚清著名教育家吴汝纶认为汉字繁难是普及教育的主要障碍:“吾国文字深邃,不能使妇孺通知。”[26]特别是对于学习格致等自然科学,繁体汉字课本会让学生在识字方面花费过多时间,导致他们无法专心学习科学学科。中国速记法创始人、西方复式会计科学引进人蔡锡勇也认为汉字虽“最为美备”,但也“最繁难”,导致“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27]因此,简化汉字可以避免因汉字字形繁重而导致识字率低的问题。
清末不少学者也曾质疑汉字改革的科学性和精密性,认为切音字改革、简化汉字有抛弃传统中华文化之嫌。事实上,这些发生在汉字内部的改革目标并不是废除汉字,而是通过降低习得汉字的难度达到提高识字率和普及教育的目的。因此,这些关于汉语本体规划和汉字变体的选择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少数精英,而是社会大众。1906年,晚清学部在与外务部的咨文中强调切音字改革的目的不是废除汉字:“汉字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我国累代相传,岂可反行废弃?”只是由于汉字“字形繁重,施诸初等教育,实有劳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28]日本文部省普通学部局长泽柳君曾在接见清末中国教育使团时建议中国在小学教育阶段以切音字教学,可以避免“缘汉文太多(致)小儿识字颇苦”的情况,进而“谋教育之普及乃便”。[29]但同时他认为切音字只适用于初等教育,而高等教育须用汉字教学,新式学堂应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认知水平选择不同的汉字变体。
晚清学界掀起的汉字改革对清政府的语言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1904年清政府出台的《奏定学务纲要》中提到汉语教育应从“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18]499,这表明从学界发起的拼音文字已直接影响了清末语言政策的制定。然而,切音字改革方案多是以某地方言为基础来创制拼音字母,例如卢戆章以闽南音为基础创制拼音,王照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创制拼音,劳乃宣在江浙皖方言的基础上又增添若干字母。倘若不对这些不同的拼音方案进行统一,将容易造成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撕裂,也容易造成各地区人民沟通的障碍。1902年2月13日,教育家吴汝纶在与张百熙的信函中就提出“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30]14。他推荐王照的简字拼音方案,以北京话作为官话基础,“使天下语音一律”[30]16。
四、富国与强兵:外语语种选择
清末语言政策除了包括汉语和外语的基本价值选择和汉语变体选择外,还规定各新式学堂西学课程的外语语种选择。在清末新政时期“富国强兵”目标的引导下,外语学习为专业学科学习服务。根据癸卯学制的规定,学生进入大学堂前须在高等学堂学习三年大学预科课程,从以下三个类别中选择今后大学堂主攻的一个学科类别:(1)经学、政法、文学和商业;(2)格致、工程学和农学;(3)医学。《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主修法律的学生除了学习英语、法语两门必修语种之外,还须兼习拉丁语,这是因为拉丁语是19世纪、20世纪初西方国家法律领域的通用语,国际法律术语皆为拉丁语[31];主攻第二类学科的学生除了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之外,还须选择德语或者法语作为第二外语,其中主修化学、电子工程、矿务、冶金和农业的学生必须学习德语;主攻第三类学科的学生须选择德语作为第一外语,英语(或者法语)作为第二外语[22]。
癸卯学制对高等学堂外语语种选择的规定体现了清末语言规划者在语言选择方面重实用性和功能性的价值取向。学生在高等学堂、大学堂选择的外语语种与该国在某个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不无关系。例如,德国在20世纪医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32],主修医学的学生须选择德语为第一外语,这样方便他们阅读德国原版医学教科书,进而掌握先进的医学知识。
从语言价值角度分析,清末语言规划对外语语种选择的规定突出了语言的经济价值,以某一学科的通用语和强势语言作为语种选择的首要因素。外语语种选择与专业学科内容密切相连,而不以该语言在世界上的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来决定,即在专业学科范畴内选择最适宜、最先进的外语语种,以更好地培养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因此,清末外语语种选择体现了经济价值类别下的实用价值,是晚清近代教育转型、语言文字变革“急用先学”“洋为中用”的缩影。
五、清末语言选择与社会语言环境的关系
研究清末语言规划中的语言选择问题不应停留于静态文本分析,而须将语言选择、语言价值判断放置在清末社会语言环境的大背景中进行剖析。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认为:“所有的语言规划都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之中,只有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才能彻底地理解这些语言规划的性质和范围。”[33]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清末新政肩负着挽救民族危机、团结民心、开启民智的重任,而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也自然与这几大任务紧密相连。
一方面,由于外语是先进西学知识传播的载体,外语教育就成为清末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重要路径。外语是中学堂以上学堂的必修课,不同学科的外语语种选择与学科内容直接相关,这体现了语言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外语成为移植西学的工具,语言选择则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综合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惨败让一部分年轻人产生深深的“文化自卑感”,自认为中华文化低人一等。为了在青年人中树立国家意识,癸卯学制注重维护汉语在国家语言体系中的核心基础地位,促进汉语的统一性和普及性。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禁止教授学生外语,须将全部精力放在汉语以及以汉语为载体的经学学习上。癸卯学制对统一官话、汉字注音的规定,实际上是19世纪90年代起“官话统一运动”“切音字运动”等语言文字改革的成果。这些语言文字变革方案并不旨在废除汉字或者抛弃以繁体字、地方方言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而是为广大中下层群众提高识字率、阅读书籍、传播知识创造基本条件。“简化”汉字以开启民智与使用“繁难”汉字以保存国粹,这两种语言价值观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矛盾,在民国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也曾一度出现过摩擦与对抗,但在清末“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社会大环境下,二者可共存共生,成为中国语言政策中的一种“双轨制方案”。两种方案的受众对象不同,简化字、切音字的受众为广大中下层群众,而繁体字的受众是社会精英群体。从清末对汉语的本体规划可以看出:语言规划者在语言选择时除注重外语经济价值外,也考虑汉语的政治价值、历史价值和情感价值,将统一的汉语官话作为树立国家意识、团结民心的工具,这是在清末内外交困的社会语言环境下做出的必然选择。然而,对汉语的本体规划其实并没有离开语言实用价值的范畴,统一国语、切音字改革等语言选择方案降低了汉语的繁难程度,解决汉语原有“言文不一致”的问题,为清末社会提高识字率、开启民智、传播先进知识创造语言条件。汉字从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的核心位置开始逐渐向“世俗化”“大众化”等“器”用之路转向,这是清末汉字道器观的重要转变。
清末民族危亡、经济凋敝的社会语言环境促使语言规划者树立“师夷长技”“开启民智”“富国强兵”等语言意识形态,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对语言选择做出具体规划,形成外国语言经济价值、实用价值与本国语言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对立与统一。而清末语言选择对语言实践和语言传播的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语言环境,通过癸卯学制等语言规划推动民众国家意识的增强、西学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为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奠定思想基础,进而推动社会语言环境的变化。
20世纪初,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语言教育肩负着移植西学、富国强兵、开启民智的历史重任,癸卯学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言环境下应运而生的。语言选择是癸卯学制的重要部分,癸卯学制规定汉语为学生语言学习之本,是新式蒙学堂、小学堂学生的第一语言。而癸卯学制对汉语的本体规划和变体选择,其目的是降低汉语学习的难度,让更多人通过学习统一的汉语变体树立国家意识,并通过掌握简易汉字阅读书籍,掌握知识。外语虽然不是蒙学堂、小学堂的第一语言选择,但从中学堂开始,外语被列为新式学堂的重要课程,在各级各类学堂中的地位仅次于汉语和经学课程,而外语语种选择也与学生主攻的学科专业紧密相连,这再次验证了外语对移植西学知识的关键作用。
语言规划中的“语言选择”问题体现了政策制定者的语言价值观。前人所归纳的语言价值三分法(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在清末癸卯学制中均有体现,但这三种价值并非孤立分离,而是彼此交叉与混合,而政治价值、实用价值更是癸卯学制体现的新特点。癸卯学制中选择汉语作为学生的第一语言,这是对汉语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维护,是实现国家认同的关键路径;同时,切音字运动、汉字简化运动等发生在汉语内部的变革又是对民族语言文化符号系统的完善,促使汉语在传播普及过程中发挥开启民智等实用价值的作用。选择外语作为新式中学堂及其以上层次学堂的必修课,将外语语种选择与学科内容相连,这是癸卯学制中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具体表现,也体现了清末语言政策“急用先学”“拿来主义”的特点。至于外语在传播过程中是否也体现了外国文化价值,对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产生了真正的冲击,则须以更长的历史时间维度进行验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仅实施七年的癸卯学制走到了历史的终点。由于施行时间较短,后人无法以相对较长的时间期限来客观评价癸卯学制的成效,也无法以更长的时间轴来剖析清末语言选择、语言价值判断和社会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然而,癸卯学制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制度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中国近代语言规划的发端。未来研究可将其他历史时期的语言规划与癸卯学制中的语言规划进行对比,从中梳理、分析我国语言规划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特点。同时,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语言规划中语言选择、价值判断等问题展开比较研究,可以丰富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价值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当今中国语言规划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