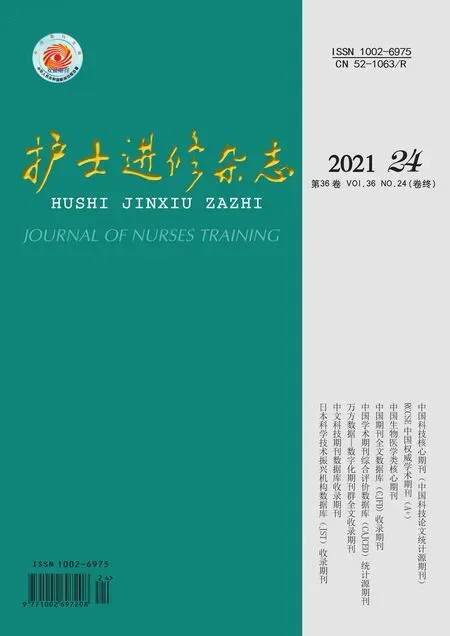母亲罹患乳腺癌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及干预研究进展
余骏雯 黄晓燕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上海 200032)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类型和最主要的癌症死因[1]。2020年全球乳腺癌新增病例226万例,占所有癌症的11.7%,成为世界第一大癌症。中国新增女性乳腺癌患者42万,占所有女性新增癌症的19.9%,位列第一[1]。有研究[1]显示,中国乳腺癌发病日益呈年轻化的趋势,40~49岁是女性的发病高峰期,15~44岁育龄女性乳腺癌标化发病率为24.1/10万,明显高于其他癌症。近年来,中国女性的生育年龄逐步提高,这说明很大一部分乳腺癌患者可能养育有未成年子女,承担着社会及家庭双重责任[2],且随着现代乳腺癌诊疗技术的发展,乳腺癌长期生存率不断提高[3],这部分特殊乳腺癌患者数量将越来越多。乳腺癌诊断不仅影响患者本身,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也是一种预期之外的突发性创伤事件[4]。目前,国外开始探讨母亲的乳腺癌诊断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而我国相关研究却很少。因此,笔者就母亲罹患乳腺癌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理解未成年子女的经历并提高其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1 母亲罹患乳腺癌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
1.1消极影响
1.1.1精神困扰 母亲被诊断为乳腺癌不仅会给患者本身带来焦虑及抑郁等精神困扰[5],也会影响其未成年子女的心理状态,使之产生抑郁、焦虑、担忧和恐惧等消极情绪,甚至感到自卑[6]。Chan等[7]采用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和后代癌症需求量表(Offspring cancer need instrument,OCNI)调查了120例乳腺癌患者的子女(14~24岁)发现,他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高或极高程度困扰者占31%。John等[8]采用优势和困难量表(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及儿童和青少年生活质量清单(Inventory for quality of lif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ILC)调查了116名母亲患乳腺癌的3~14岁儿童发现,在总体生活质量和心理症状上,尤其是心理健康和情绪反应方面,其调节适应能力比一般人差。Furlong[9]采访了28名7~11岁的学龄儿童,发现其不安全感显著增强,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和母亲陪伴及支持的减少,尤其是住院期间与母亲被迫分离的痛苦对他们产生了极大困扰。但Inbar等[10]对58例完成乳腺癌治疗8个月后的母亲及其青春期女儿的研究表明,此类负面精神影响仅在母亲的依恋焦虑评分或女儿的依恋回避评分较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另外,有部分研究[3,11]表明,乳腺癌家庭的子女与其他孩子间几乎没有差异,未发现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适应能力和心理调节均表现正常。Vannatta等[11]调查了40名母亲在6个月内确诊为乳腺癌的8~16岁儿童,发现儿童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及父母评估的子女内在化行为、外在化行为和总体能力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rown等[3]调查了40例有乳腺癌病史的母亲及其子女,采用儿童多维焦虑量表(Multidimension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MASC)和儿童行为清单(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LC)进行评估,发现2项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乳腺癌家庭的子女不存在异常焦虑、情绪低落和适应困难。目前,母亲罹患乳腺癌对未成年子女的精神情绪是否存在影响或影响程度尚无统一结论,可能是因为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所选用量表不具有特异性,且大多数研究对子女的评价均由母亲完成,并非儿童的自我报告,母亲的乳腺癌诊断对未成年子女心理状态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1.1.2乳腺癌相关忧虑 母亲的乳腺癌诊断和治疗会使未成年子女产生一系列相关的忧虑[12-13]。Almulla等[12]调查了140名母亲于6个月内被诊断为乳腺癌的7~12岁学龄儿童,分析其对开放式问题的书面答复后,归纳发现其核心词是“失去她”,表现在与母亲分离、担心母亲的状态、发现母亲的异常行为表现及日常生活的改变等4个方面。当看到母亲因化疗而变得疲乏虚弱、日常行为改变和出现脱发等外观改变时,常常担心母亲的病情发展,怀疑医生是否使用了错误的治疗方法。Huang等[13]研究发现,即使暂时没有出现经济短缺的问题,许多孩子也会担心家庭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知道乳腺癌的治疗价格高昂。Altun等[14]认为,母亲罹患乳腺癌等具有遗传倾向的癌症会增加女孩的内在化问题风险,因为她们会担心自己有更高的患病率,建议未来研究针对母亲罹患乳腺癌对女孩疾病感知风险的影响展开进一步探索。
1.1.3行为问题 母亲罹患乳腺癌不仅影响未成年子女的精神情绪和心理调节能力,还可能造成外在化的行为问题和举止异常[14]。Altun等[14]的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选取了40名乳腺癌患者家庭的6~17岁学龄儿童,采用父母填写的SDQ进行调查发现,乳腺癌患者家庭子女的行为问题、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及总体困难评分显著高于健康家庭组。但也有多项研究发现,母亲患乳腺癌的子女不存在外在化问题[4];没有出现调节适应困难[15];在亲社会行为、领导能力和同伴友谊等方面也没有明显差异[8,16]。Stephenson等[6]的系统综述总共纳入了15项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患乳腺癌的子女的总体行为问题显著减少,外在化问题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不存在侵略性或破坏性行为,但作者表示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良好的调节适应或结论有误。此外,Huang等[13]访谈了40例1年半内确诊为乳腺癌的母亲和8名8~18岁的未成年子女,发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祖父母会帮助母亲承担照顾者角色;但有3名孩子表示他们的学习受到了负面影响,因为母亲患病后无法指导或监督他们。这可能是由于未成年子女试图用这种方式来隐藏自己的低落情绪,保护并帮助母亲应对癌症诊断[6]。另外,家庭中角色功能的相应调整或许可减轻孩子受到的负面影响[6]。在研究过程中,部分研究对象选择中途退出,愿意参与研究并坚持到最后的家庭及其子女可能本身存在的行为问题较少,这使得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1.1.4创伤后应激障碍 既往研究很少针对乳腺癌患者子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相关症状进行调查,2项针对PTSD的研究[3-4]得出了相反的结论。Tuller等[4]采用CBCL及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指数等对40例诊断8周内的乳腺癌患者和39名未患乳腺癌的母亲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患有乳腺癌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有更多的PTSD症状。但Brown等[3]调查了40例患乳腺癌的母亲及其子女,结果儿童创伤后应激症状量表(Chil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 scale,CPSS)得分显示子女自我报告的PTSD症状无明显组间差异。但这2项研究均样本量较小,建议未来研究增大样本量,适当缩小所纳入未成年子女的年龄跨度,并从母亲和子女2个方面评估孩子的行为表现,围绕PTSD相关症状进行深入研究。
1.2积极影响
1.2.1保护机制的建立 为了应对母亲患病所带来的一系列改变,未成年子女需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以保护自我[9]。Furlong等[9]使用经典的扎根理论,选择了28名母亲在4个月内被诊断为早期乳腺癌的7~11岁学龄儿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发现他们采用了一种自我保护策略,经历了3个周期性和迭代性的过程,从感受并意识到日常生活规范和环境的改变,到评估疾病相关信息并减少其负面影响,最后尝试维持生活平衡。这一过程有助于孩子建立新的自我认同,并融入新的角色功能和责任义务。
1.2.2适应能力和家庭、社会责任感增强 母亲罹患乳腺癌使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角色和责任义务发生转变,可能反向推动他们自我适应调节能力的提高[9]。Vannatta等[11]采用CBCL和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FES)等调查了40名母亲患有乳腺癌的8~16岁儿童发现,子女和家庭都表现出显著的适应能力。Huang等[13]访谈结果表明,在母亲患病后,孩子能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母亲,主动完成以前从来不做的家务。同时,他们也表现得更加懂事乖巧,尽量不激惹父母生气,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所增强。Stephenson等[6]系统综述也发现,乳腺癌家庭的子女在学校里表现出比同龄人更好的社交能力和积极的亲社会行为。未成年子女为应对挑战,避免引起母亲担忧,而在生活和学习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自主性,并逐渐承担起家庭责任。
1.2.3亲子关系改善 养育子女是罹患乳腺癌母亲的主要任务[17],乳腺癌的诊断使患者的“母亲”角色受到挑战,治疗的需求与照顾子女之间的矛盾可能造成母亲家庭角色和亲子关系的转变[18]。Kim等[19]访谈了7例50岁以下罹患乳腺癌的母亲,发现多数母亲选择告知子女疾病诊断以帮助孩子克服远期焦虑,与孩子共同承担和相互支持。母亲在养育观念上变得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和坚强品质,不再将目标仅寄于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机会。父亲的帮助弥补了母亲在养育子女方面的部分缺失,这也有利于促进父子关系的改善。Mackenzie[20]访谈了32例28~55岁的乳腺癌患者,发现其均是优先考虑照顾家庭和子女,而非自己的治疗和需求,孩子也会主动帮助她们,如尽量避免不适时的打扰,遇到问题时转而向父亲或其他人寻求帮助,亲子关系趋于改善。Tavares等[19]对23项研究的系统评价表明,乳腺癌家庭中亲子关系的特殊变化和适应过程及父母养育方式、角色功能的转变过程尚未可知,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2影响因素
2.1人口学因素 母亲罹患乳腺癌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大部分女孩一般表现出更多抑郁症状[3]、压力反应和回避行为[21-22]。Chan等[8]研究发现,女孩的心理困扰水平显著高于男孩,且在实际援助、情感与朋友支持等方面存在更多未满足的需求。Altun等[14]调查了40名母亲患乳腺癌的6~17岁学龄儿童,发现女孩在情绪困扰、同伴关系及总体困难评分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明显高于男孩,而敌视心理和易怒反应在男孩中更为普遍。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女孩更担心自己将来也会患病,另一方面由于男孩较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而隐藏了部分情绪困扰[14]。
Altun等[14]发现,12~17岁青少年的心理及行为问题多于6~11岁儿童,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作者表明可能是样本量小所致。Edwards等[21]调查了56名11~17岁的青春期子女,结果发现压力反应率高于既往其他对非青春期未成年子女的研究,表明青春期儿童群体可能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女孩的回避得分显著高于男孩,但在心理功能上未发现性别和年龄差异。Chen等[22]调查了96名母亲患乳腺癌的12~25岁子女,发现女孩的压力水平高于男孩,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感知压力水平不存在年龄差异。由此可知,关于未成年人受母亲乳腺癌诊断和治疗的影响程度与性别和年龄的关系尚无统一定论,这可能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表达方式、认知发展存在差异有关。
2.2疾病相关因素 母亲患病时间、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方式等疾病相关因素可能影响未成年子女的精神与行为反应,但现有研究[6,21-25]结论不一。Stephenson等[6]研究表明,与患病时间相比,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副反应对预测子女的行为功能更重要,母亲存在严重治疗副反应时,子女表现出更少的情绪、行为困难和更强的适应能力,预后较差时,反而可能产生更积极的亲子关系。有严重并发症时,子女的行为调节能力反而更强[23]。Chen等[22]研究发现,当父母病情恶化时,孩子表现出更严重的压力反应,相比于化疗或放疗,父母接受内分泌治疗的子女压力水平更低,但这种结果并不显著。当父母存活时间<1年时,子女具有最强的家庭适应能力,随着存活时间的推移,子女的生存能力急剧下降,,可能是累积压力所致。但Edwards[21]等研究表明,自母亲诊断以来的时间长短及是否接受化疗等因素均与子女的压力反应或情绪行为问题无关。不同疾病相关因素之间可能相互影响,应完善研究设计以避免混杂因素干扰,另外,建议开展纵向研究以探究母亲罹患乳腺癌不同时期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
2.3母亲的情绪 抑郁、焦虑及敌视心理等负面情绪增多在乳腺癌患者中非常常见,患病母亲严重的精神困扰是子女适应困难的危险因素[23]。Edwards等[21]研究证明了母亲抑郁症的高发与儿童的精神问题之间存在显著联系。Bradbury等[11]研究表明,女儿心理社会调节和精神困扰与母亲的心理调节密切相关,母亲高水平的焦虑情绪和乳腺癌特定困扰会导致女儿的内在化问题增多。但有待进一步探讨,因为大多数研究均通过母亲的报告来评价孩子的身心状况,而不同信息提供者的评价有所差异[6],母亲可能由于自身情绪低落或对子女照顾不周的自责愧疚,而主观夸大子女的负面情绪和行为表现[23]。
2.4沟通交流 乳腺癌患者患病期间养育子女的总体目标是保护子女,开放的疾病信息交流可使子女免受恐惧情绪或负面想象的困扰[24]。Chen等[22]研究发现,家庭适应力与亲子交流呈正相关,有效的交流有助于家庭成员缓解压力、减轻悲伤并提高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而青少年与母亲的沟通率始终高于父亲。Fisher等[25]研究表明,公开交谈可促进亲子关系的发展,释放负面情绪。Zaben等[26]调查了28例乳腺癌患者,发现疾病信息交流可改善孩子行为举止及其对待母亲的方式,促进亲子关系的发展,但对孩子学业存在潜在负面影响。Huang等[27]访谈了8名母亲被诊断为非晚期乳腺癌的8~18岁子女,发现得到详细信息的孩子对母亲疾病和治疗副反应的接受度更好,充分的交流和信息有助于减少孩子的担忧和焦虑。但许多父母不愿意与孩子讨论乳腺癌和死亡相关话题[28],部分中国母亲受传统文化影响而倾向于间接性及隐蔽性的被动交流方式[3]或不确定如何与子女沟通[29]。因此,解释沟通的必要性,指导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正确时机和方式,对改善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2.5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 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是影响癌症患者子女总体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3]。Brown等[3]研究表明,他人的同理心和同伴的支持可减少未成年子女的抑郁症状,增强心理调节能力。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及扩大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是子女适应水平的预测指标。Edwards等[21]采用CBCL及儿童事件影响量表(Child impact of events scale,C-IES)等调查了56名11~17岁的青春期子女,结果发现,家庭功能低下会导致青少年的一系列内在化与外在化问题,增加子女的压力反应,使得心理总体困难水平增高及亲子沟通减少。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往往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因此,需考虑不同阶级研究对象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另外,横断面研究设计限制了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需要前瞻性研究来检验此结论。
3 干预措施
3.1提供疾病信息,鼓励沟通交流 未成年子女往往对癌症存在幻想和误解[30],与家人、有相似经历的朋友或医疗专业人员交流有利于孩子应对癌症和减少心理困扰[31]。孩子生命中的勇敢时刻(Children’s lives include moments of Bravery,CLIMB)[30]是一项针对父母罹患癌症的未成年子女的小组干预计划,组建同伴小组通过艺术及游戏活动等方式让孩子们了解癌症相关知识,同时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从而提高癌症应对能力。Semple等[30]对7名儿童和6名父母的一对一访谈表明,对此心理社会干预的总体评价良好,它所创造的安全空间让孩子掌握了更多疾病信息,情绪和行为也得到改善。Kobayashi等[32]将其改编为日文版,通过对24名父母和38名6~12岁学龄儿童的研究发现,干预后儿童的PTSD症状有所减轻,且更易于在家庭中开展疾病交流,计划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而且无需特殊设施,成本较低。但研究缺乏随机对照,选用的效果评估工具可能并非最佳工具,且研究干预效果仅考虑了短期影响,而未评估长期影响,研究结论有待检验。
Davey等[33]为制定具有种族敏感性的临床干预计划,对12名母亲罹患乳腺癌的11~18岁非裔美国青年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发现建立1个由具有相似经历的同伴青年支持小组有利于分享经历及克服孤独和忧虑等负面情绪,而且他们认为父母参与到其中非常重要。在此基础上,Davey等[34]将12个非裔美国家庭分为文化适应性家庭干预组和心理教育干预组,家庭干预组注重改善亲子依恋和沟通,鼓励他们直接进行癌症相关交流,结果发现,与心理教育干预组相比,家庭干预计划更有利于改善亲子交流,但焦虑或抑郁症状无明显改变,可能是由于评估时间过早或亲子交流并非抑郁情绪的来源。此研究仅在美国东北部开展,规模较小,限制了研究结论对其他社会和人口结构地区的家庭的适用性,由于研究对象为弱势群体,招募速度较慢且数量较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2减少母亲抑郁情绪,提升育儿技能 加强联系项目(The enhancing connections program,EC)[35]是一项癌症育儿计划,目标是减轻母亲的抑郁情绪和焦虑,改善育儿行为,并改善其子女的行为和情绪调节。干预措施包括5次患者教育咨询会议,同时提供1份关于乳腺癌的小册子,由母亲给孩子朗读[35]。Lewis等[35]选取了176例在6个月内诊断为乳腺癌的母亲及其8~12岁子女开展随机临床试验,发现母亲的抑郁情绪和养育技能显著改善,儿童的总体行为困难、外在化问题和抑郁情绪显著减少,但对母亲的自我效能和儿童的焦虑情绪的影响有限。改良后的基于通讯的加强联系项目(The enhancing connections-telephone Program,EC-T)[36]通过电话联系来开展教育咨询,减少了患者接受教育咨询的往返路程耗时,对109例养育有5~12岁子女的乳腺癌早期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EC-T与原计划成效相当,甚至更好,教育咨询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其传播途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此计划对晚期癌症患者同样有效[37]。父母患病子女咨询组织(Children of somatically ill Parents,COSIP)是一个关注父母罹患严重疾病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影响因素的国际组织[38],基于此组织理念提出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咨询服务是一项短期干预措施,旨在预防儿童心理问题[39]。John等[8]调查了116例养育有3~14岁子女的乳腺癌患者,结果发现,将肿瘤康复治疗和以儿童为中心的心理社会干预相结合对母亲和子女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因此,医护人员应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为家长提供以儿童为中心的咨询服务和健康教育,引导其关注孩子的身心状态。
3.3改善家庭功能,提供社会支持 社交网络的癌症心理教育项目[40]是一项针对父母罹患癌症的家庭及其社交网络成员的干预计划,旨在通过心理教育,优化社交网络支持,以提高父母养育能力及保证子女的安全和生活质量。心理教育涉及孩子及父母的总体需求、社交网络支持的重要性、不同社会支持的类型及如何长期维持社交网络支持等方面[40]。Hauken等[41]选取了35个父母在5年内被诊断为癌症并养育有8~18岁子女的家庭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CPP有助于维持家庭功能的稳定,这对于儿童的长期发展非常重要,但对焦虑及总体生活质量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CPP对儿童的具体需求关注不足、干预时间过短或样本量不足所致。CPP聚焦于增加社会支持,但结果反映儿童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多维的,无法仅通过社会支持来解决。
3.4增强自信和自我掌控感 母亲罹患癌症使得未成年子女感到失控和沮丧,增强孩子的自信和自我掌控感可能会给予他们力量来应对母亲患病的挑战[42]。On Belay[42]是一项基于冒险活动的青年支持小组项目,目标在于帮助癌症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发现自身的力量,并以此来面对挑战。项目以小组形式展开,活动内容包括合作性游戏、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及难度不等的挑战性课程,不强调疾病知识教育或讨论。Anita等[42]对9对父母和12名10~15岁子女的访谈发现,孩子们认为这一项目可有效地提供一个相互理解和关心的团体,从而减少孤独感并使癌症经历正常化,从中获得的力量和自我掌控感有助于应对现实的挑战。
目前,针对乳腺癌家庭的干预措施研究较少,且多数干预措施聚焦于母亲本身,而缺乏对以儿童为中心干预计划方案及效果的研究。同时,普遍存在样本量不足的问题,部分研究未采用随机对照,而且缺乏标准化的效果评估方法或评估工具,因此,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检验。
4 小结
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母亲罹患乳腺癌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问题,并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尚无统一研究结论。既往研究样本量较小,且多数研究对象局限于中产阶级和白种人家庭,结论缺乏普遍性和推广性。未来我国研究者可借鉴国外的研究方式及内容,结合我国国情,探索母亲的乳腺癌诊断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经历,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支持,帮助未成年子女提高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