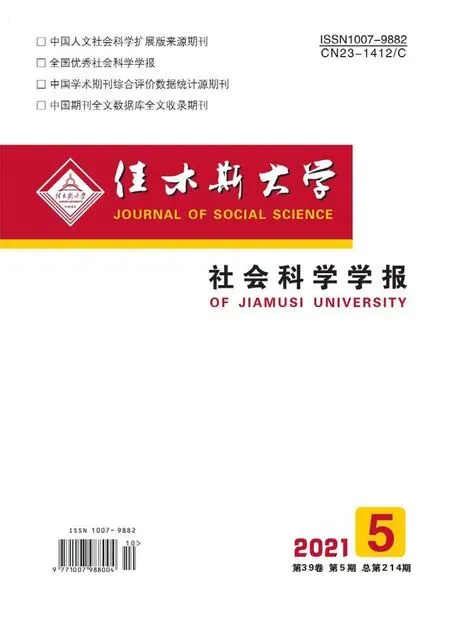阎连科与卡夫卡权力书写比较分析 *——以《日光流年》与《城堡》为例
柏蕴真
(重庆大学 博雅学院,重庆 400044)
一、引言
人的生存是建立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之上,且权力的运作既控制着社会的话语与秩序,同样也主宰着人的行为与命运。卡夫卡的《城堡》透过疯癫之人K的遭遇映射人在权力场中的生存体验与人性异化。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则在揭示底层社会对权力的角逐中,营造出远离现代文明且受权力宰制下的耙耧世界,人的生存陷入不断轮回的怪圈之中[1]。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基础,探讨阎连科与卡夫卡小说世界中的权力呈现、权力规训以及权力凝视,以此探讨权力场中人性异化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二、权力呈现的文本
面对被权力规训的社会与凝视的心灵,卡夫卡与阎连科结合自身处境与经验,采用充满想象力的寓言化的表达方式,完成对权力运作整体过程的解剖。虽然,二者展开权力书写的艺术手法是有较大差异的,并集中体现在符号化人物塑造上,以及小说艺术语言运用上。但是,在对人类普遍生存的关照与反思层面,则呈现了权力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形态内涵,且共同揭露了人性在权力场中的异化表现。
(一)权力符号的比较
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并始终生活在现实社会的阴影与夹缝中。虽然这些小人物由于权力束缚,生命渐渐萎缩,但他们均是身心健全的,原本他们只会按部就班地生活,但是外在因素的介入却将他们推入发疯的深渊,他们无法也无处反抗,因为他们始终存在于权力运作之中。这也是卡夫卡对于世界荒诞性最有力的展现。然而,阎连科笔下的人物,则大多是直接与传统封建权力畸形连接的“非常态之人”,他们在精神与肉体上均是残缺的,无意追问致使他们残缺的原因,因为在阎连科的小说世界里,非常态的人集中展现了非常态的世界[2]。
无论卡夫卡与阎连科塑造的人物,起初是正常的也好,畸形的也罢,等待他们的均是那个被权力规训与凝视的世界,他们要么异化为权力的附属品,要么沦为权力的牺牲品,并无二路。尽管如此,卡夫卡与阎连科的作品从未停止对劳苦大众的关切,始终代表着各自文化语境下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并趋向于对生命本质和世界本相的深层探索,并将自身权力书写隔绝在世俗功利化之外。面对世界的虚无性与非理性,他们拒绝在现实社会的强大话语体系下完成对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将社会作为异己力量进行书写,通过构筑自己的小说世界,言说着普遍存在但又被规训遮蔽的权力秘密[3]。
(二)权力话语的比较
在语言运用方面,卡夫卡与阎连科有着各自的风格特色。卡夫卡小说世界是由大量的隐喻性语言构筑的,需要过滤语言的表层意义,才能窥探其书写文本的思想大厦。而且,为了能够真实再现小说人物的内心映像,以及为了客观展露权力社会的暴力与威慑,卡夫卡的小说语言格外冷静节制,但又在最深处或最低处潜存着情感的暗流。而阎连科则惯用奇异怪谲的小说语言,遣词造句上大胆粘稠、肆意妄为、直白露骨。这些语言早已超越了表意符号的范畴,以自身的力量承载着丰富的抽象涵义。在阎连科小说的话语狂欢之下,混沌的语言自身几乎上升至权力结构的顶层,并和那些真正的权力形态一样凝视着小说世界的一切。至此,我们得以亲历着权力世界的畸形与荒诞[4]。
卡夫卡与阎连科小说世界里那些语义漂浮的象征符号,需要深入挖掘,才能透过语言塑造的故事外壳,真正发现那些摄人心魄的现实寓意和世界本相。除此之外,卡夫卡与阎连科在审美意趣与创作精神上也十分相似。如在架构文本时均选择寓言小说体式,以此满足对权力书写荒诞性的艺术需求。再如面对权力运作的现实社会,始终保持着对人类生存的追问与关照。可以说,卡夫卡与阎连科通过荒诞性的故事情节与梦幻式的叙事技艺,完成了对权力运作整个过程的深层解剖,呈现了权力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不同内涵,揭露了人性在权力场中的异化表现。
三、权力规训的社会
在《城堡》中,卡夫卡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权力网遍及各处的世界,人的存在及其全部存在形式完全处于高地势的城堡俯瞰之下。而在《日光流年》中,阎连科以底层社会的权力角逐为根基,集中描述了一个远离现代文明或者被现代社会遗弃的“耙耧世界”。无形的权力遍布于社会的所有实践活动之中,人在权力场的规训与凝视之下,最终导致人的存在异化为权力的附属品。想要洞察卡夫卡在《城堡》里塑造的悲剧社会,只有深入到小说世界的细枝末节里,才能发现隐藏其中的规训手段。
(一)权力生产的比较
《城堡》的权力书写是围绕K作为城堡之外的人而被视作“疯癫人”展开的。而《日光流年》中的权力书写则与阎连科的民间立场与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其中,K作为“疯癫人”的原因有三:对于这个来自外地不受城堡统治的K心怀芥蒂;K无法与城堡的村民相融合而被视为异己的力量不受待见;K与城堡世界的主流价值相悖因而被迅速隔离开来。而“耙耧世界”作为与世隔绝的乡村社会,其专制且血亲的权力形式渗透于历史的各个角落,微观上支配着个体命运,宏观上决定着社会走向。在权力场下的底层民众,一面诅咒着权力对自身的制约束缚,又一面幻想着权力给自身带来的荣耀与权威,可谓对权力的心理体验既是崇拜又是恐惧。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指出《城堡》这种异己力量存在的“疯癫”,是西方人文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内在矛盾的历史表现,是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必将历经的内在危机,即人的存在与社会制度的冲突,并受社会制度规训和管控,最终对于人性及其精神世界造成毁灭性的冲击[5]。简言之,疯癫之人象征着西方文化精神心理的巨大漏洞与无限割裂。此外,福柯在《权力与规训》中阐明了权力如何将自身纳入到知识系统之中的,即如何确保自身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虽然,《日光流年》的权力书写,并不是借助福柯式的知识体系完成,但在乡村社会中,那种基于“血亲关系”的权力形式,却有着与知识体系一样的作用,并持续完成着权力生产的神话。
(二)权力形态的比较
没有与生俱来的权力形态,只有被社会界定的权力形态。就是说,社会自身向前推进的过程或者权力形态形成的过程,将一切与之相异的力量视为疯癫经验,并予以清除或隔离。那么“城堡”与“耙耧”之中的疯癫经验和权力形态源自哪里呢?或者具体由什么确立与界定的?《城堡》暗示了答案:现代社会通过将文化、知识和经济结构的外在化与理性化,并在完成对其内在因素与感性因素的侵袭与规范中,通过加剧分化最终确立了自身的疯癫经验与权力形态[6]。而“耙耧世界”的疯癫经验或权力形态,是以血缘裙带关系为根基上的封建血亲权力。最明显的例子是,村长家大儿媳是支书家的大姑女,副支书家的大儿媳又是支书家的二姑女,而支书家的大儿媳则是经联主任家的大妹子。如此稠密的血缘裙带网络,编织了《日光流年》的整个权力场域,而那些游离在权力结构之外的底层百姓,只能千方百计地通过成为血亲符号,实现自身对于权力的追逐。
具体层面,“城堡世界”中的权力形态表现为将人专业化与工具化,并将人完全视为自身前进的手段,个体与他人的隔阂逐渐增大,作为目的之人逐步退出并消失,当到达极限,精神病或疯癫之人也就随之产生了。然而,现代精神病治疗学作为被规训社会的附庸,理所当然利用自身的知识权力,将社会中的“异端”成员分离出去,作为管辖对象排除在外。而“耙耧世界”中对权力的崇拜不单单是一种原始欲望,更是底层百姓摆脱苦难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说,老百姓们在抨击权力的同时又渴望着权力,种种疯癫心理,在最本质上根源于对权力的普遍恐惧。正如《日光流年》里的村长所说,“我是村长,我就是王法。”因为生活在权力阴影下的底层百姓,必将历经权力的日渐扭曲化与暴力化。
四、权力凝视的心灵
面对这个被规训的世界,面对这个代表巨大权力统治机器的“城堡”,卡夫卡意识到或痛切体验到这台机器具体运作时,那些“异端”分子在历经规训之后,并未结束,因为等待他们的还有“全景”式的、赤裸的且精神与肉体全方面的惩罚[7]。而掩藏在《日光流年》中的权力运作,则始于大量的性欲描写,即对性的服从直接源自对于权力的渴望或恐惧。阎连科对性欲的描写除了具备权力视觉的特点之外,还另外增加了嗅觉与听觉的成分,并以此强化了女性被权力凝视为客体对象的表现形态,深刻指出了女性作为权力运作中的客体对象,处于被动地位,且需要接受权力的评判与规训。
(一)权力运作的比较
具有“环形全景监控监狱”特征的城堡,遍布于整个小说世界的权力,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城堡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整个村庄的中心,较之于完全暴露在监视日光之下的村庄,具有浓雾与黑暗般的隐蔽性,如同占有城堡的人占有了绝对的权力,身处村庄的人则身处规训之中。其次,作为权力实施的城堡代言人“克拉姆”,在小说世界里从未现身,村民也只是零星听闻些“克拉姆”的言行事迹,或许这个权力代言人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村民由于对权力的恐惧而臆想出来的,尽管如此,这个代言人“克拉姆”的权威并未缺失,且以权力的方式无时无刻注视与监管着城堡里发生的一切[8]。最后,在《城堡》里,权力的执行还扎根在村民的自觉服从中,即所有的村民均在自身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驯顺被制伏,当然,也只有遵守并坚定这些权力才能被城堡认可,成为集体一员,否则将被视为异类,如K,并遭受惩罚,排除在社会之外。
而在“耙耧世界”中,男女在性经验上存在巨大差异,即存在施动者与受动者的明确界限,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之下,成为了欲望的客体。然而,这种规训的力量并不因为性高潮的结束而间断,相反,作为权力客体的女性始终处在持续不断的凝视目光之下,其直接后果则是女性变得具有自发性与能动性,其自发性表现为在权力观念下进行自我规训,并为了仅仅由于接近权力而产生的虚荣满足和自我麻痹,而甘愿成为权力的奴隶;其能动性则表现为利用性达到相互利用的目的,待当利益链断裂,权力消失,性的关系便自行解除。最后,这种对于性的凝视在本质上实为对性的监视,完全处于客体地位的女性不能违背或抵抗权力意识,因为一切对于权力的背叛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二)权力美学的比较
无论是卡夫卡的“城堡世界”,还是阎连科的“耙耧世界”,二者均将视野投注在那个由权力制裁的人文环境之中。由此,我们得以窥伺在对性欲与权力追逐下的,事关生存苦难与悲惨的且关乎整个人类的心灵困境。与此同时,透过本文世界,也向读者吐露作者自身的现实经验与美学认知,并通过梦幻式的表达方式,完成了权力书写的现实指向与艺术表现的美学平衡。其中,卡夫卡在权力美学集中体现在其对被孤独异化的敏感,以及对权威审判的预见,这无疑导致其内心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归属感缺失。而阎连科的现实主义风格,决定了其权力书写力图通过对现实的揭示展现人类对存在的体验[9]。如果《城堡》中权力美学是对悖论循环与审查目光的前瞻回应,是对现代人受制于权力驱使而负重前行的有力揭示,那么《日光流年》中的权力美学则融合了现实内容与梦境世界,并在情感疏导与权力现实之间建立美学平衡。
概言之,卡夫卡的创作灵感源自其复杂且敏感的情感体验以及其身处的社会对现实人的控制与异化。而在权力现实与梦想世界的煎熬中,卡夫卡在夹缝中找到自身的栖息之所,并努力融合外部秩序世界与内心艺术世界。而《城堡》则是对现代人异化形象与普遍困境的艺术揭示,使文学创作跃然于生命之上,这足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真理的线索。而阎连科将对权力的指责转化为荒诞的表达,既缓和了权力带来的尖锐矛盾,又使原本压抑、敏感、权威的权力得以接近,从而达到将作品的意义准确地从作者传递给读者的效果。《日光流年》以底层社会的权力角逐为根基,指出无形的权力遍布于社会的所有实践活动之中,即便是在那个远离现代文明或者被现代社会遗弃的“耙耧世界”中,人的存在也被异化为权力的附属品[10]。简言之,虽然卡夫卡与阎连科的权力书写方式不同,但归根结底是人类生存的问题,并且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个问题:如何生活得更好?
五、结语
通过结合福柯的权力理论,具体分析了《城堡》和《日光流年》两部作品,展现了中西方语境下权力的表现形式、运作方式、特点以及影响。尽管卡夫卡与阎连科呈现的权力书写有所不同,但指向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并处理人的生存与权力运作的关系。结果如何,还需要反复重回卡夫卡与阎连科为我们缔造的“伊甸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