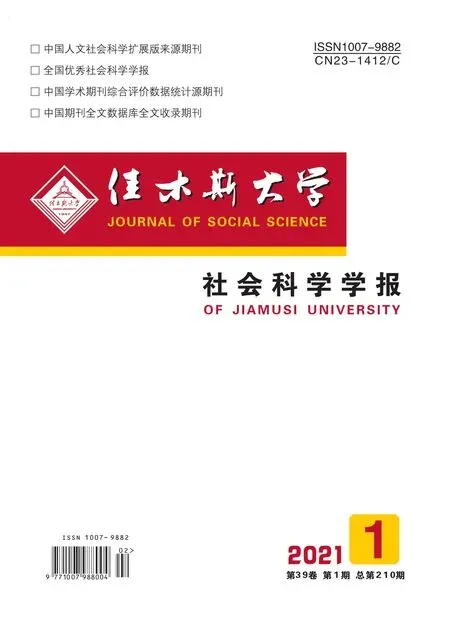文化传承视野下阮籍和嵇康述祖主题创作与人生价值研究*
姚素华
(湖南信息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以述祖为主题的文学创作自先秦时期萌发,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述祖诗文彰显出的士人之宗祖理念又是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敢为天下先的人格情怀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其价值并进行了阐述,但仍留有更深入研究的空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述祖诗文因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赋予了其创作在坚守传统中新的人生价值理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明确以述祖为题进行创作者见于谢灵运、陆机、阮籍、嵇康等,以《述祖德诗》《祖德赋》等为代表,诗文表现了士人对家族功德业绩的歌颂,充满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同时憧憬建立自身功业德绩,构建出迥异于其他时期文人的人生价值。分析这一时期述祖诗文的创作及其思想特征,是揭示其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传承路径的方法之一。纵观这一时期的述祖主题诗文创作,可以说歌颂祖德祖业已成为士人的自觉行为,作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底层士人。从内容上看,魏晋南北朝士人的述祖怀德不仅止于专门以祖德、述祖为题,还在赠贺、碑文、颂赞、感怀、山水等篇章中追念祖德功业。即便是以谨慎避祸和“非汤武、薄周孔”为行事准则的阮籍与嵇康,在身处崇敬祖德祖业的社会现实中,有看似是对祖德祖业的“悖反”的诗文,也不乏将继承祖德祖业为志的文章,前者实际上是彰显家国天下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虽篇目不多,但却是阮籍与嵇康将济世之志视为当世之责,循道践义,也是中国古代士人为国为家的责任深埋于自身的立身处世中的明证。
一、述祖之风的兴盛
与汉前述祖诗文对比,这一时期的述祖诗文无论从篇目数量还是文学成就上均有较大突破,其中不乏佳作的士人如谢灵运、陆云、陆机、陶渊明等。如陶渊明《命子》“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1]28陆云《祖考颂》“烈祖丞相邵侯显考大司马武侯明德睿哲,□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继迹前期,惠成□顾者也。”[2]2054王融《赠祖叔卫军俭诗》之“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质超瑚琏,才逸卿云。摇笔泉泻,动咏英纷。□风乎不极,卓兮靡群。”[3]1394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肇基既远,而戎祖盛德大业,足以缵先绪,光祖宗。”[2]3179丘雄《诣阙上书》“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4]292。
魏晋南北朝士人以祖德祖风的弘扬为傲,从他们所创作出的述祖主题文章来看,士人所颂赞的祖德功业多有共同之处,第一,以祖德祖业为傲,并将继承家族功绩德业立为自身的责任。陆云《祖考颂》:“我考纂戎,爰究爰度。远除寻轨,崇基式廓”[2]2054。第二,士人认为家族中值得发扬光大处是德业与功绩的结合,其后世子孙均围绕德与功进行叙述。具体到士人,既有不能建功施展抱负的惋惜;又存有强烈的德业功绩兼有的使命感;亦或是建功则驰骋沙场,立德则功成身退不居功自傲。如曹操《又上书让封》:“谓先祖有大德,若从王事有功者,子孙乃得食其禄也”[2]1058。曹操以功不能胜劳为由,推辞皇帝任命的镇东将军、费亭侯之位,虽有故意推脱之嫌,但不能否认士人是以不居功自傲为普遍人生价值准绳。另有王昶《家戒》:“夫立功者有二难,功就而身不退,一难也;退而不静,务伐其功,二难也。”[2]1255第三,当士人德业功绩之念求而不得时,或寄厚望于后代子孙,或自知不能践行祖先功德之业而深感悲痛,但并不寄希望于后世子孙行践行之业。以践行德业功绩为人生价值理想的士人从家族出身上可以分为底层士人与高层士人。底层士人家族的现实处境较为艰难,所以他们对自身重振家族功业的实践条件有清醒地认识,因而并未有过多期待,只能将弘扬家族德与功的希望寄托于后世子孙。如陶渊明《命子》“尔之不才,亦已焉哉!”高层士人出生在豪门家族中,常常以自我为标杆,且自视甚高,如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4]1775,家族文化熏陶让他们对践行家族德业功绩有着先天的自信,所以,高层士人并不将践行家族德业功绩寄希望于后世子孙,而是寄希望于自身。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不管是底层士人还是高层士人,他们的述祖文章充满了对家族功德业绩的歌颂,表现出对祖先难以抑制的崇敬之情,极力宣扬宗族门楣的德业武功,对自我祖先的德行与功业表现出为人子孙的崇敬。从人生阶段来看,士人在青壮年时期特别看重自身德行与功业的建立。在这一时期士人看来,祖先的武功德业是值得为之自豪的,更是应该为之浓重书写的。因此,记录家族曾经的辉煌也就是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寻找渊源与传统。士人以述祖为主题的诗文中描述的宗祖德行功业高下不尽相同,然而救民于水火、功成身退不居功的价值选择则无太大差别,这些皆可为士人之楷模,亦可为士人之所乐道。多数士人也以之作为人生矩范,以功成身退为人生最高境界,即将家国命运与自身人生抱负紧密结合起来,憧憬建立自身功业德绩,以实现自身人生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或愤懑或慷慨,又或是悠然或者对抗,构筑起仅属于这一时期的士人生价值观。
二、阮籍与嵇康人生价值的悖反
这一时期的士人,以述祖为主题进行创作构筑起了家国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其中阮籍与嵇康以述祖为主题的作品为数不多,但内容较为丰富。作为“竹林七贤”中最杰出的代表,阮籍与嵇康表现出的旷达、放诞,随性而为,不与当权者合作的态度异常鲜明,将自我而适发挥到极致。《世说新语·简傲》描述阮籍:“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5]766晋文王司马昭功劳极大地位也很高,在他面前受邀的客人都很庄重严肃,只有阮籍我行我素,他痛饮啸咏,不改常态。《世说新语·任诞》中另一则曰:“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5]731《世说新语·简傲》第三则曰“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5]767钟会出身高门贵族,是司马氏集团不可或缺的人物,因善于政治投机更成为司马昭的心腹。司马氏集团在夺权的过程中自然要争取嵇康这些名望显赫士人的支持,于是司马氏便派钟会往嵇康处试探。嵇康对钟会的态度并不好,嵇康更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云“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6]113,直指当权者与屠夫无异,更是与当权者的彻底决裂。
阮籍与嵇康礼法上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及行为上的异于常人让他们呈现出一种怪诞的处事方式。阮籍自认为“才非允文,器非经武。适彼沅湘,托分渔父。优哉游哉,爰居爰处,”[7]200悠游自在才是自己的理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到了他的理想:“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又说“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6]117仕进荣华对于嵇康并非心之所向,唯有放任率真的本性才是自己所追求的正道,正是由于天性不同,所以士、农、工、商都各有所长,都以达到自己的志向而感到快乐,这一点通达之人早已心照不宣。可见,他们二人所追求的理想与这一时期士人述祖文章中表现出的人生价值理想格格不入,即可视为对这一时期人生价值理想的悖反,但是从阮籍与嵇康的人生价值理想的描述来看,阮籍与嵇康的人生价值理想与同一时期的士人是相同的,正如嵇康所言“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人生际遇不同,君子所表现出的处事方式虽然各不相同,在人生价值理想的指引下,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阮籍年少成名,虽幼年家道中落,仍成为当世名士,在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漩涡中,他为保身全命采取退守的态度,不与统治者直接发生冲突,或闭门读书,或佯醉不醒,《晋书》评价其为人“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8]1361在经历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后,他对政治形势已然洞若观火,为此极力规避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风险。然而作为一位士人,以功名德业为个人理想的坚守自始至终没有因退守的人生态度而产生动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仁风广被,玄化潜通。[3]495(《咏怀诗十三首》其八)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3]499(《咏怀八十二首》其十六)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3]504(《咏怀八十二首》其四十一)
岂不志远,才难企慕。命非金石,身轻朝露。[3]496(《咏怀诗十三首》其十三》)
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3]50(《咏怀八十二首》其二十一)
自己并不能够掌控人生理想的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士人饱尝价值的失落,这种趋势让士人在拥有相对达观的精神境界中表现出强烈地无所适从与愤懑。
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从容在一时,繁华不再荣。[3]502(《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一)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3]503(《咏怀八十二首》三十三)
无法通过建功立业及德行修为来实现人生价值的士人,在闲适之语中显示出强烈的抑郁情怀。只是面对不能实践祖德以及自我人生价值的愤慨,阮籍表现得相对和缓。阮籍自己也十分清楚,他的这种处事方式是不为统治者接纳的,《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5]735这就不难解释他的儿子打算效法他而被言辞拒绝了。
如果出身高层士族就能为士人功业德行的建立带来先天优越条件,那么,嵇康必然应该是德业、功绩相得益彰。然而,纵观嵇康的仕途之路与阮籍相比更加艰难曲折。嵇康的妻子是沛王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这一场政治上的联姻让嵇康巩固了自己的高门地位,因此,一方面是高门的地位,再加上名声在外,大权在握的大将军司马昭想要拉拢他,就连司隶校尉钟也持盛礼前去拜访他,但都遭到他的冷遇。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是嵇康的好友,山涛在离开尚书吏部郎之职时,曾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位。嵇康则以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为由,严词拒绝出仕,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凡此种种,招致司马氏的忌恨。
不求得到君主的赏识,也无实权,嵇康的建功立业成了一纸空谈,加之个性狷狂,或嘲讽或不参政事。同时,在诗文中抒发对理想不能实现的强烈不满,也在高洁玄远之语中隐藏着不甘寂寞失意无奈之迹。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2]1321(《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开诚布公表露欲成为“并介之人”兼济天下,然而当朝统治者并非自己实现人生抱负的理想君主,更不愿随波逐流,只希望自己内心保持正道。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的实践与现实完全不能相联接,回望祖先的功业成就,始终无法排遣自我郁结、愤懑的心情。然而,高门士族价值引领的威望与传统价值观的坚守终给他反抗不公社会现实的勇气。
从社会地位来看,嵇康属于名副其实的高门望族,但他旷达狂放,个性十足,有着强烈地对自由的向往,生活习惯上以懒散为乐,“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养,不能沐也”[2]1321,“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2]1322,(《与山巨源绝交书》)年轻时的嵇康傲世而立,对礼法更是不屑一顾。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2]1375嵇康处处激愤,终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8]1373遭杀害。因性格的狂放不羁再加上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进而遭受谗害不能保全自身成为高层士人难以避免的人生之路。
“轗轲丁悔吝,雅志不得施。”[6]36(《述志诗》其一)
“何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6]37(《述志诗》其二)
“天道害盈,好胜者残。”[3]497(《代秋胡歌诗》其三)
“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3]486(《五言赠秀才诗》)
阮籍与嵇康二人因人生际遇、社会现实等原因,都未能实践祖先的德业功绩,阮籍不论人之是非,以退守的态度面对残酷的政治状况,然而闲适畅达的外表却有着难以排遣的悲哀,生命止于郁郁;嵇康虽出身高门,却并未为他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康庄大道,反而因名声显赫受到当权者的猜忌横尸街头。阮籍与嵇康选择的处事态度不同,但是因人生价值理想未能实现进而愤懑一生,郁郁而终却是相同的。
三、结语
阮籍和嵇康二人的处事方式可将其归结为对祖德祖业的“悖反”,但是从述祖诗文作品分析来看,他们的人生价值是彰显家国天下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向世人展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名士在缺乏实践人生理想的具体环境中,或洞察世事,毅然选择明哲保身,维护自我人格,或激烈反抗,不与统治者合作,始终胸怀济世为民之志,立身处世自觉遵循道义,将中国古代士人为国为家的责任深埋于自身的立身处世中。
——以马克思对俾斯麦“功业”的评价及两人的“交往”为例